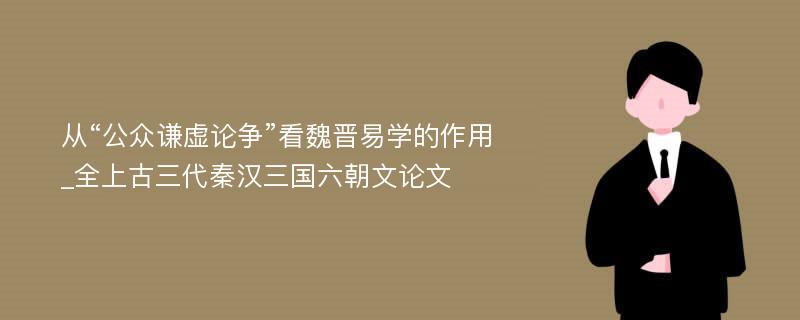
从“公谦之辩”看魏晋义理易学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理论文,魏晋论文,易学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4)06-0041-08 东晋中期的玄学思想界出现了一场重要的论战,讨论“公”(公开坦诚)与“谦”(谦虚退让)两种品德的关系,史称“公谦之辩”。论战中各派均通过对《周易》卦义解释,支持自家的学说。东晋易学大家韩康伯卷入其中,留下了一篇论文《辩谦》。学术界对“公谦之辩”的研究,多从伦理哲学角度展开。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从易学角度梳理相关史料,以揭示魏晋玄学义理易学在实践中的真实作用。 东晋“公谦之辩”发生的时间不详,从卷入论战的人物有王坦之(330-375)、殷康子、袁宏(328-376)和韩康伯(约332-380)的年龄看,时间应当是他们已经成年并健在的公元360-375年之间,即东晋升平至宁康之际。从年龄上看,均为东晋第二代士人——永和名士。王坦之《公谦论》和韩康伯《辩谦》,较为完整地流传至今,袁宏的《明谦》仅存少量佚文。从文献看,在“公”与“谦”的问题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理论,并且都引用《周易》经传文字,作为立论的哲学基础。下面分别论述这三种观点: 第一,论战发起人王坦之的观点。据《晋书》的说法,他将所著《公谦论》给殷康子看,开启了关于“公”与“谦”关系的论战,“尝与殷康子书论公谦之义”。王坦之的主旨是“公”胜过“谦”,论证理路可归为以下三个层次。 夫天道以无私成名,二仪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无亲而非理;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由斯论之,公道体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谦义生于不足,故时弊而义著。故大禹、咎繇,称功言惠而成名于彼;孟反、范燮,殿军后入而全身于此。从此观之,则谦公之义固以殊矣。① 乾坤之道的运行,公开坦诚,无我无亲,以适合万物的自然之性为原则,故功德无量。可见“公”是宇宙间最完美的品德,属于“大道”层次的概念。出现了争名夺利的社会风气,“谦”德才得到重视。在人类社会中,像大禹那样体“道”的圣人,能以自然真诚之道成功;而像孟之反那样的普通人,则要通过谦逊持后保全自己。 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贵,我不可取。诚患人恶其上,众不可盖,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损焉。隆名在于矫伐,而不在于期当;匿迹在于违显,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谦光之义与矜竞而俱生,卑挹之义与夸伐而并进。由亲誉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余;良药效于瘳疾,未若无病之为贵矣。(《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第1968-1969页) 厌恶他人居自己之上,是人类的普遍心态。因此,君子降低自己的名誉,不是实事求是——“期当”,而是为了避免自我夸耀的嫌疑,采取了自我贬抑的自保措施——“谦下”。应当看到,谦逊退让永远与骄傲争夺并存,不是最美的品德,只是用来纠正争名夺利之风。犹如良药能治病,却不如无病。 夫乾道确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简矣。二象显于万物,两德彰于群生,岂矫枉过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观之,则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谦伐之义,险巘于人事。今存公而废谦,则自伐者托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党以致惑,此王生所谓同貌而实异,不可不察者也。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则玄指自显,若寻其末,弊无不至。岂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贪而忘于谅哉。(《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第1969页) 为了证明论点的正确性,他引用了《系辞下》“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②之语,乾道阳刚与坤道阴柔的性质,毫无保留地昭示天下,没有任何隐匿。王坦之以此证明“公开坦诚”的美德源于天地之“道”,而“谦虚”则产生于险恶的人事。为什么不能仅存“公”德而废弃“谦”德?因为这样一来,小人便会打着公开坦诚的幌子自我夸耀,混淆视听,以假乱真。可见,“公”德也会产生流弊。但是,不能因存在流弊,而怀疑“公”德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二、袁宏的观点。针对王坦之的《公谦论》,袁宏与殷康撰文予以反驳。“康子及袁宏并有疑难”(《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第1969页),除此外,各类史书均未有殷康子的资料。有的学者推测,殷康子,极可能是殷康。殷康生卒年不详,但属于东晋第二代士人,著名的陈郡殷氏家族成员(父殷融,子殷仲文),官至右卫将军,与王坦之、袁宏、韩康伯为同时代人,社交圈子亦相同。《晋书》载,宁康二年(公元374年)七月,“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晋书》卷二○《礼志中》,第617页)对简文帝的丧事,共同发表看法。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九,有殷康《明慎》两条佚文:“犇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盖言慎也。”“古人云:骄奢,人之殃;恭俭,福之场。”③由此可知殷康是极力宣扬谦恭之道,但无法得知他是如何反驳王坦之论点的。袁宏的《明谦》佚文,则展示了他们的主要观点: 贤人君子,推诚以存礼,非降己以应世;率心以诚谦,非匿情以同物。故侯王以孤寡飨天下,江海以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下行。”《老子》曰:“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此之谓乎。(《全晋文》卷五十七,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788页) 袁宏认为,君子谦恭待人,同样是发于自然本性,不是刻意伪装以求生存。帝王自称“孤”、“寡”,江海地势低下,正是遵循了“谦”德。他引用《周易》和《老子》之语,证明“谦”道不是源于人类的矫情,同样是天地之道、宇宙大道的表现,与“公”德无高低之分。文中所引《周易》文字,来自《谦·彖传》的文字。 第三、韩康伯的观点。读了王坦之《公谦论》和袁宏《明谦》后,韩康伯认为两派都有合理性,但都存在问题,“遂作《辩谦》以折中”(《晋书》卷七五《韩康伯传》,第1993页),即折中两家观点,著《辩谦》一文。该文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段落: 夫寻理辩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夫谦之为义,存乎降己者也。以高从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孤寡不谷,人之同恶,而侯王以自称,降其贵者也。执御执射,众之所贱,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贤者也。与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岂殊哉?舍此二者,而更求其义,虽南辕求冥,终莫近也。夫有所贵,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谦焉。譬影响之与形声,相与而立。道足者,忘贵贱而一贤愚;体公者,乘理当而均彼我。降挹之义,于何而生!则谦之为美,固不可以语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晋书》卷七五《韩康伯传》,第1993-1994页) 《辩谦》开篇,韩康伯便以形名方法,辨析“谦”名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原因。“夫寻理辩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认为“谦”的意思是自我贬低,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地位高贵,自视为卑贱;二是德才优异,自视为愚笨。如帝王自称为“孤”、“寡”以降低自己的高贵地位,君子自称“仆”以降低自己的德才品位。内心存在是非、美丑观念,才会产生自我贬低的“谦逊”。如果达到了“道”的无我高度,则会忘掉贵贱、贤愚、彼我的差异,以公开坦诚态度,反映事物的真相,不会采取歪曲真相的“谦逊”品德。可见,“谦”不是宇宙大道的品质。他引《谦·象》“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作为理论依据。为什么要推行谦德呢?韩康伯这样解释: 然君子之行己,必尚于至当,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无私,而动之于降已者何?诚由未能一观于能鄙,则贵贱之情立;非忘怀于彼我,则私己之累存。当其所贵在我则矜,值其所贤能之则伐。处贵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贵;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骤称其能。是以知矜贵之伤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骤称之亏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则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则贵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尽,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内,岂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滞哉?(《晋书》卷七五《韩康伯传》,第1994页) 大意为:君子为人处世,理论上以公开坦诚的最高境界为努力方向,而实践中则实施自贬的谦逊之道。为什么要扭曲自我呢?原因在于,君子不是圣人,不能从思想上消除事物差异,人物贤愚不同,则心有贵贱观念;无法消除彼我差异,不能达到忘我之境,故仍被私心所累。因此,自己有美德而希望得到社会赞赏,会有夸耀的欲望。但是,又深知自夸属于不良品质,故以谦卑态度接人待物。这样,无疑是在隐匿真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君子们有情有欲,没有达到“忘情”“无我”的高度,只有通过谦下的途径,抑制内心的私情,才能成君子之德。 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惩忿窒欲,著于《损》象;卑以自牧,实系《谦》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馀者也。王生之谈,以至理无谦,近得之矣。云人有争心,善不可收,假后物之迹,以逃动者之患,以语圣贤则可,施之于下斯者,岂惟逃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内也。(《晋书》卷七五《韩康伯传》,第1994页) 值得注意的是,韩康伯认为,“谦”德并非君子所特有,而是圣贤与君子都要遵循的,只是两者遵循的思想基础不同,这正是韩康伯折中观点的关键所在。 首先,圣人本质完美,达到了无我境界,故能以无为顺应外物,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谦下品德。所谓“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的意思,是说圣人虽然已经无心、无欲,达到了“无”的境界——“拟无”,但是他仍要从事有形的政治活动——“体有”。这个观点,在韩康伯的《系辞注》中有段文字可以佐证:“圣人虽体道以为用,未能至无以为体,故顺通天下,则有经营之迹也。”(《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42页) 再者,君子本质不完善,内心有我,为了获得好名声,有意地抑制私欲,采取谦下的处世态度。韩康伯认为,袁宏论点的正确之处,是指出圣贤亦须遵循谦德;失误之处,是将谦德提高到天地之“道”的高度。王坦之论点的正确之处,是指出了“公”与“谦”属于不同层次的品质:“公”属于圣人之道,“谦”属于君子之道;失误之处,是忽视了圣人与君子均须实施谦德,并且没有看到圣贤与君子实施谦德的境界不同:圣人无心,自然具备顺应社会的谦德;君子有心,通过节欲的自我修养,才能获得顺应社会的谦德。 王坦之与韩康伯文中都提到了一个叫“王生”的人。所谓“王生”泛指王姓男子,类似现在的“王先生”这一称谓。魏晋文献中“王生”的用法,既可以称历史人物,如袁宏《三国名臣颂》赞美王经:“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晋书》卷九二《袁宏传》,第2396页);也可以称时人,如西晋嵇含《吊庄周图》中称时人王粹“今王生沉沦名利”(《晋书》卷八九《嵇含传》,第2301页)。由此可见,王坦之与韩康伯文中的王生可能不是一个人。韩康伯《辩谦》说:“王生之谈,以至理无谦,近得之矣。”(《晋书》卷七五《韩康伯传》,第1994页)从上下文义看,他笔下的“王生”,有可能指王坦之。而王坦之《公谦论》中提到的“王生”——“此王生所谓同貌而实异,不可不察者也。”(《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第1969页)无疑不是王坦之。按当时的行文习惯,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可能称自己为“某生”。从各种迹象看,极有可能是指王弼。 王坦之在东晋上层士族社会中地位显要,既是朝廷重臣,又是著名玄学家。桓温死后,他与谢安同为辅政大臣,累迁中书令,属朝中当权派。同时,作为玄学阵营的务实派,反对放达之风,著《废庄论》,以批判庄子的名义,矛头指向玄学的“越名教任自然”思潮。王坦之玄学思想的特点主张儒道融合,以《老子》反对《庄子》,“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第1966页),故推崇正始名士,将何晏视为反庄学的思想前辈:“何晏云‘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第1965页)由此可见,王坦之笔下作为重要思想家提出的“王生”,肯定不是小人物。而遍查魏晋玄学家主张融合孔老的王姓思想家,只有王弼,而王弼与何晏是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 王坦之《公谦论》与韩康伯《辩谦》的共同理论特点,是将“公”与“谦”划分为两种不同层次、有本质区别的美德。“至公无私”是宇宙大道的品质,体现在天地的运行中、圣人的活动中,表现为《周易》《乾》《坤》二卦的卦德。“谦虚退让”反映了大道的丧失,为了避免受到争名夺利风尚的伤害,而不得已产生的美德,表现为《谦》《损》诸卦的卦德。而这些理论,正是王弼《老子注》与《周易注》的主要学术创建。 其一,老子《道德经》只说宇宙大道无为,并没有将天地之道的性质定为“无为”。而王弼在其《老子注》中,则认为天地之道与宇宙大道的性质完全相同:“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王弼集校释》上册,第13页)“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王弼集校释》上册,第14页)“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王弼集校释》上册,第93页)在此基础上,王弼发挥了老子关于“大道废,有仁义”的说法,强调人类所谓美德与天地之道对立:“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门。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王弼集校释》上册,第43页)又说:“圣人有则天之德……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26页) 其二,关于王弼援《老》解《易》,即以老子哲学解释《周易》,自古至今一直是学术界的共识。在天地生成问题上,王弼用老子的“道”解释《周易》的“太极”,将其改造为玄学家笔下的宇宙本体——“无”。“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47-548页)因此,《系辞上》中“太极生两仪”的思想,便顺利转化为“无”生天地,天地之本就是“无”,为其重新解释《乾》《坤》二卦的卦德,奠定了哲学基础。《易传》认为《乾》是“自强不息”,《坤》是“厚德载物”,时刻处于生化万物的有为状态。对此,王弼并不否认天地的生生不息活动,其新意是:天地看起来有为的活动背后,是无心顺应自然的运动。乾道“健”与坤道“顺”是无形,却是天地生化万物的决定力量。 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13页) 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夫用雄必争,二主必危,有地之形,与刚健为耦,而以永保无疆,用之者不亦至顺乎?(《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26页) 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王弼集校释》上册,第227页) 众所周知,韩康伯是继王弼之后最重要的玄学义理派易学家,所著《系辞注》上下、《说卦注》、《序卦注》、《杂卦注》五篇,是东晋玄学的代表作。孔颖达主撰《周易正义》,将韩康伯五篇注合三卷,附王弼《周易注》后,合为一书,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易学史中的主流地位,成为历代官方易学的“底本”。在天地之道无心无为问题上,韩康伯将王弼贵无论与郭象的独化论结合,作了明确而系统的解释。他否认了太极的存在。认为天地是自然生成,无法考证其终极来源。他说:“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大虚。欻尔而自造矣。”(《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43页)但是从“有”生于“无”这一普遍现象推理,有形的天地也是从无形中产生,所以用太极表示“无”。故他又说:“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43页)天地产生之后,均被自身的规律所控制,规律是无形的,可以称之为“无”。 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而道可见矣。故穷变以尽神,因神以明道,阴阳虽殊,无一以待之。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41页) 天地的活动是有形的,却受无形的易道控制。“夫唯知天之所为者,穷理体化,坐忘遗照,至虚而善应,则以道为称。”(《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43页)。《系辞下》:“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韩康伯注:“确,刚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简易也。”(《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57页)《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韩康伯注:“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41页)显然,由王弼首创,韩康伯发扬光大的关于天地之道无私的易之理,是王坦之与韩康伯在“公谦之辩”中立论的哲学基础。“夫天道以无私成名,二仪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无亲而非理;成名在乎无私,故在当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圣人所以济化。……夫乾道确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简矣。二象显于万物,两德彰于群生。”(《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第1969页) 从“公谦之辩”这一典型个案出发,全面梳理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则不难发现,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义理易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真实作用,没有实现其原初的设计要求——为周易“时位”的分析作出正确决策,其实际作用,是通过文字的哲理,为社会政治与人生哲学的一般原则提供理论支持。 关于《周易》对人类社会的指导作用,《系辞》的作者认为有四个功能:“《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50页)从实践活动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卦爻辞的文字,阐发其中蕴含的思想“义理”,为各种社会活动提供正确的普遍哲学原理;二是分析占卜获得的卦爻象,解释其中蕴含的“象数”玄机,为即将发生的事变提供具体的决策依据。“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39页)《周易》本身就存在着“义理”与“象数”这两种功能,在实际运用中,不可能孤立地只用其一,不同时代不同的易学流派,侧重点差异甚大,故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特点是:认为人类社会受宇宙卦气控制,《周易》六十四卦表达了宇宙意志;《周易》的智慧是通过筮法占卜吉凶,以预测命运,指导决策。因此汉易对传统的占卜方法作了大发展,将五行学说与天文历法引入占卜,其结果是陷入繁琐与妖妄,使象数易学在汉末走向了衰落。王弼《周易注》的突出特点是扫除汉代象数,否定天人感应与卦气说,反对占卜活动。他激烈批评了汉代象数易学的“五行”“互体”方法:“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09页)王弼认为“爻象”模拟的是人情的变化,由于人数众多且人情变化无常,因此用数字演算来预知人情变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巧历不能定其算数,圣明不能为之典要。”(《王弼集校释》下册,第597页) 王弼《周易注》的突出特点是以社会人事解《易》,认为人类社会受自身规律控制,可以概括为“时位”说:时,指六十四卦象征六十四种社会大环境及其规律;位,指每卦的六爻象征大环境中的各种具体条件,如地位、机会、社会关系等。卦时和爻位是《易传》的重要思想,但在不同的篇中,各有侧重。《彖传》注重讲卦时,解释时义;《系辞传》则多阐述爻位的功能。王弼将《易传》关于卦时与爻位的分别论述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以卦时与爻位的关系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即从社会形势与行为主体条件的结合中,探讨命运的形成,以及如何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决策。很明显,王弼提出“时位”学说的目的不是讨论抽象的哲学原理,而是试图在反对象数占卜的基础上,保留《周易》的决策功能——通过理性分析主客观条件,作出正确的预测。 尽管王弼《周易注》的目的是通过“时位”分析,达到科学决策目的,但这种方法操作性较差,或者说几乎无法操作。例如,怎样判断我们所处的“时”与“位”,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分析的。因此,王弼《周易注》在实践中并没有成为这一时期士人与政府决策的工具。作为一般知识存在的元气论与阴阳五行学说,仍是一般士人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因此建立在“卦气”学说基础上的象数易学,不可能退出思想舞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如何规避风险,作出正确决策,除了理性的审时度势外,如果运用《周易》的智慧获得帮助,无疑是占卜。即使对玄学家来说,占卜仍是他们作出人生选择的重要方法。以下是玄学流派人物及其政府运用占卜决策的案例: 正始名士何晏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孔颖达《周易正义》与李鼎祚《周易集解》都曾引用何晏之说,可见何晏有易学著作。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共辑得四条,题为《周易解》。从占卜大师管辂对何晏易学思想的评价看,无疑属于义理学派:“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④但是,何晏在正始九年面对政变危机时,还是请管辂为他占卜,“晏谓辂曰:‘闻君着爻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三国志》卷二九《管辂传》,第820页) 竹林名士嵇康与好友阮德如之间,就“风水”问题展开了论战,尽管两人对“风水”是否存在观点不同,但都承认通过《周易》的占卜方法能够获得未来命运的信息。都力图以深通“象数之理”的思想家形象出现,指责对方“惑象数之理”,所以他们对传统的相命论、占卜方法,都予以肯定。阮德如说:“夫旧断之理,犹卜筮也。夫凿龟数筴,可以知吉凶。”⑤嵇康说:“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干有刚柔,统以阴阳,错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时日是其所由。”(《嵇康集校注》卷九,第296页)戴明杨说:“此篇上文‘乾坤有六子’,似言纳甲之法。”(《嵇康集校注》卷九,第308页) 西晋元康名士张轨,也是义理派易学家,著《易义》,收录于张璠的《周易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张轨字士彦,安定人,凉州刺史,谥武公,为《易义》。”张轨见天下将乱,准备到凉州任职以避难时,便卜了一卦:“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晋书》卷八六《张轨传》,第2221页) 东晋时期的易学领域,尽管王弼易学已经立于官学,但这并不影响占卜活动的升温,例如,王导辟郭璞为参军,数次请其占卜吉凶:“时元帝初镇邺,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晋书》卷七二《郭璞传》,第1901页)王敦之乱时,无论是保皇派的温峤和庾亮,还是作乱的王敦,均找郭璞预测吉凶,希望从他的占卜中获得胜利的信息。郭璞的占卜甚至影响了政府决策:永昌元年(公元322年),郭璞以占卜为依据,上奏元帝要求大赦天下:“以囹圄充斥,阴阳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荡涤瑕秽。不然,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蠢戾之妖。”(《晋书》卷七二《郭璞传》,第1907页)这个奏疏竟然被皇帝采纳:“疏奏,纳焉,即大赦改年。”(《晋书》卷七二《郭璞传》,第1908页) 从曹魏到东晋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看到运用王弼“时位”方法分析决策的案例,并不意味着以王弼《周易注》为代表的义理易学没有影响力。相反,在思想文化领域,魏晋时期玄学家的义理易学在不断发展,在这个时期《周易》注释著作中占了绝对的压倒优势。两晋之际的张璠,编撰了一部《周易集解》,收录了曹魏西晋时期二十二种易学家的著作,笔者曾撰文《张璠(周易集解)考》,对此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该书所收录的作品全部属于义理派。⑥既然如此,那么义理派在实践中的作用表现在哪里呢?从文献中反映的事实看,义理易学的作用主要是引用《周易》的文字,阐述一般原理。换句话说,实践《系辞传》所说“圣人之道”中的“以言者尚其辞”,即“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打开史书,在各种评论、政论、奏议、诏书中出现的《周易》语录,都在实践着这一功能。 正始名士李胜与夏侯玄在是否恢复肉刑问题上发生了一场论战。李胜反对肉刑,在《难夏侯太初肉刑论》中云:“《易》曰:‘履校灭趾,无咎。’仲尼解曰:‘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灭趾谓去足,为小惩明矣。”(《全三国文》卷四十三,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300页)文中的“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出自《系辞下》引孔子语。李胜强调文中的“此小人之福也”,认为肉刑为轻刑,不足以遏制犯罪。夏侯玄主张恢复肉刑,其《答李胜难肉刑论》:“圣贤之治也。能使民迁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惩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惩戒则无刻截,刻截则不得反善矣。”(《全三国文》卷二十一,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167页)则强调“小惩而大戒”,认为是轻刑能够遏制犯罪的理论依据。 竹林名士向秀,为了证明嵇康禁欲主义的养生方法违背人类的自然本性,他引用《周易》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富贵天地之情,贵则人顺己以行义天下,富则所欲得以有财聚人。”(《嵇康集校注》卷四,第162页)“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出自《系辞下》;“崇高莫大于富贵”,出自《系辞上》。向秀通过对《周易》思想的发挥,证明人类自然欲望的合理性,以及积极入世获取功名富贵的合理性。 西晋元康玄学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两大派,均以《周易》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其一,贵无派领袖王衍,发挥了王弼将“太极”称之为“无”的理论,建立了贵无论玄学。据《晋书》记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开物成务,无往不存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而“衍甚重之”(《晋书》卷四三《王衍传》,第1236页)。“开物成务”一句,出自《系辞上》:“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王衍、乐广复制了何晏、王弼“以无为本”学说,将《周易》的理论主旨,说成是以“虚无”为本,为其自由放纵的虚无主义价值观提供哲学依据。其二,崇有派领袖裴頠在《崇有论》中批评“贵无”论时,同样借助《周易》。指出“贵无”派的错误,是将《老子》的虚静学说附会《周易》之《损》、《谦》、《艮》、《节》诸卦,将《周易》的主题说成是“本无”。“老子既着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晋书》卷三五《裴頠传》,第1044页)他认为谦虚退让只是君子行为的一种方式,是君子之一道,将其视为《周易》的理论主旨与行为之本,则是错误的。 东晋永和之际清谈再次出现高潮,《周易》的解释仍是热点问题。连桓温都亲自讲《周易》,每天阐述一卦的义理,“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⑦。并出现了以殷浩为代表的义理派与以孙盛为代表的象数派关于“易象妙于见形”问题的辩论,结果是义理派取胜而告终。在义理派玄学家内部,发生了运用《周易》哲学讨论理想人格问题的“公谦之辩”,为我们理解魏晋义理易学的实际功能,留下宝贵的资料。 东晋时期玄学义理派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决策实践中一直存在的占卜方法也持续升温。面对两晋之即战乱带来的命运的不确定性,渡江南下的士人心中的神秘文化因素也在发展,对占卜决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象数易学复苏提供了文化环境。在这个神秘主义与宗教情感浓重的时代,以摈弃象数占卜为特色的王弼易学显然不能适合时代需要。为了保持玄学对社会的影响力,王弼《周易注》在东晋时期开始被士族思想界作修正性“解读”,即开始了玄学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再次融合过程,韩康伯的《系辞注》是阶段性成果,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⑧经过南朝的二百多年的发展,最终成果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 ①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8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卷数、篇名与页码。 ②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7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③严可均《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九,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01页。以下所引《全三国文》、《全晋文》均为此版本,仅随文标注书名、卷数、篇名与页码。 ④《三国志》卷二九《管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21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篇名、卷数与页码。 ⑤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7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卷数与页码。 ⑥王晓毅《张璠〈周易集解〉考》,载《文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辑,第73-88页。 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7-218页。 ⑧王晓毅《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载《周易研究》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