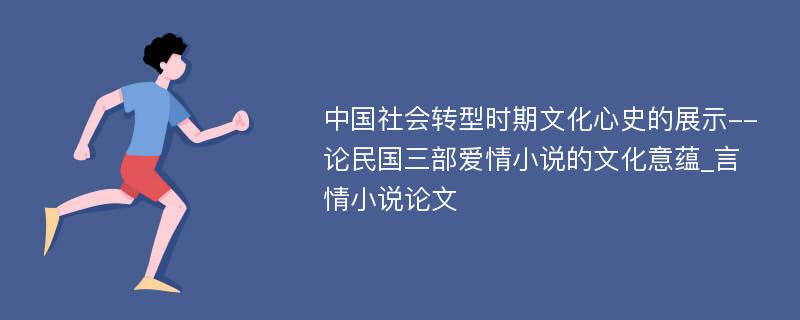
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心史的展示——论民国三大言情小说的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意蕴论文,转型期论文,三大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民国言情小说是二十世纪通俗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支,《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是民国言情小说中三部划时代之作。长期以来,由于偏于单一的批评模式,对其缺乏应有的评价。本文试图从文化这一角度剖析民国三大言情小说,透示其情爱追求中孕含的文化意蕴。《玉梨魂》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期“提倡新政体,保守旧道德”的文化心理;《啼笑因缘》则表现在中西文化撞击中,人们反叛传统又回归传统、向往现代又排斥异端的复杂心态;《秋海棠》则展示了现代人格的铸成、现代健全文化心态的形成。从这三部小说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世纪转换期人们的心态史,形象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换过程中人们文化心理的嬗变。因此,这三部小说不仅是民国言情小说的三大高峰,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丰厚文化意蕴的通俗小说精品!
关键词 玉梨魂 啼笑因缘 秋海棠 文化意蕴
鸳鸯蝴蝶派是清末以来产生广泛社会影响、而又屡遭漠视甚至歧视的文学流派。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十里洋场相伴生的,以有闲阶级和都市小市民读者为对象,以消遣和趣味为美学追求的都市通俗文学。其中,言情小说是该派中最繁盛、最重要的一支,最能体现该派的文学精神。
民国言情小说内承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之余韵,外师异域文学之菁华;既继承中国小说传统章回小说的体式,又部分吸收西洋文学的表现技巧;既与新文学在竞争中保持其独特品格,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认同、相通,最终自觉地完成了与新文学的合流。
民国言情小说自“言情鼻祖”徐枕亚的《玉梨魂》以后,佳作迭出,经久不衰。《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分别出现在1911-1912、1929-1930、1941-1942,它们是民国言情小说的三座高峰,也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中三块划时代的里程碑。
《玉梨魂》最初在《民权报》连载,反应强烈。1912年单行本出版后,风行不衰,再版三十多次,销量十万,还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等,成为民国初年影响很大的一部文言言情小说。时人称曰在中国近代小说中“没有比这两部书销场再大的了”①(指《玉梨魂》及《鸿哀史》),从而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奠基之作。
《啼笑因缘》是民国言情小说的最高峰。与《玉梨魂》相比,不仅在语言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在内容上有新的发展,“到我写《啼笑因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②。《啼笑因缘》的问世,产生了比前者更大的轰动。明星、大华公司为争夺拍摄权,大打官司,不可开交,成为当时新闻的焦点,“一时文坛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记录”③,形成“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的盛况。
《秋海棠》是民国言情小说的回光返照,也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最后辉煌。《秋海棠》四十年代初在上海连载时所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啼笑因缘》。也曾改编成话剧、电影,享誉大江南北。与《啼笑因缘》相比,其时代感更为强烈,它以通俗的小说形式和严肃的主题,完成了民国言情小说与新文学的合流。
民国言情小说尽管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我们习惯于一元视角,偏重于文学的功利性,政治尺度成为衡量文学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因而,对鸳鸯蝴蝶派文学存在评价过低、批评过严的倾向,这样势必会将脏水和婴儿一同泼出,也违背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能摘下文学批评的有色镜,调换一下批评视角,也就能从貌似荒芜里发现一片新绿。
民国言情小说家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新旧体制的激烈竞争、中外文化的强烈撞击、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的强烈犯冲……这一切必然会影响作家的心理,也必然会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因此,表现世纪转换期人们的文化心态、表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国人文化心理的嬗变,就成为民国言情小说的一条主线。
《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作为民国言情小说发展中的三块丰碑,典型地体现社会转型期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流变史。
《玉梨魂》鲜明地体现出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人们普遍存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新政体、保守旧道德”的文化心理。小说的基本情节是望风洒泪的才子何梦霞与对花伤怀的佳人白梨影真诚而痛苦的爱情故事。何梦霞“惊其幽艳、复感其痴情”而春心萌动,钟情梨影;白梨影作为一美貌寡妇,因惜其人怜其才而死灰复燃,热恋梦霞。然而,他们热烈的情感并未化为外在的行动,一面战战兢兢地坠入情网,一面又自以为悖礼违俗;一面对幸福满怀憧憬,一面又以礼教观念关闭了通往幸福的大门。在传统的道德观念面前,他们只能遥寄希望于来生:“造因今生,收果来世。”于是,薄命佳人为保全名节而“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以小姑筠倩许配梦霞,自己则“以死报君”;多情才子却做“情场怨鬼”而终生不娶,后来留学归来,殒命疆场,以身殉国。从而导演了一曲缠绵绯恻、低婉哀吟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的悲剧。
过去,我们分析《玉梨魂》时,总是批评其对封建礼教的维护,但往往忽视其中蕴含的一个时代人们共同的文化心理。
众所周知,中国对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接纳,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动适应。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古老而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在铁一般残酷的事实面前,国人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被迫放弃“天朝中心”的古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其所长”。但由于对西方的皮相认识,对老大帝国本能的维护,他们极力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中国现代化进程是缓慢而沉重的。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在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这个世纪中叶以后,当西学在日本迅速成为全民族注意中心之际,它在中国却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之中。在18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的渗透,就思想交流而言,收效甚少,但事实上,这种渗透引起了社会文化之冲突,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们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④这样一种社会机制,就必然形成“提倡新政体,保守旧道德”的文化心理。
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体现在婚恋观上则是新旧思想畸形的混合,其基本倾向是总体上捍卫传统又部分背叛传统,一方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男女终身大事、以及由此造成的青春毁灭悲剧深表不满,一面又坚持婚姻大事须经父母依允,不得违背孝道;一面标举男女相爱应忠贞不二,一面又极力宣扬发乎情止乎礼。这之中既蕴含对婚姻自主、人格独立等现代意识的认同,又流露出对封建伦常观念的依恋;既有对人的真实情感的大胆肯定,也有对传统礼教不自觉的背叛……。
《玉梨魂》正是将这一复杂的文化心态形象地表现出来,因而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如前人指出的那样:“民初的言情小说,其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制度渐渐动摇,‘门当户对’又有了新的概念,新的才子、佳人就有了新的要求,有的已有了争取婚姻自主的勇气,但是形隔势禁,还不能如愿以偿,两性的恋爱问题,没有解决,青年男女,为此苦闷异常,从这些社会现实和思想要求出发,小说作者就侧重描写哀情,引起共鸣。”⑤可以说,正是小说中表现的亦新亦旧的文化心态,与社会转型期人们心理相合拍,这才引起读者广泛的关注和心灵的震颤!
与《玉梨魂》相比,《啼笑因缘》体现的文化心理有了明显的变化。与前者表现出的整体上维护又部分逸出传统不同,《啼笑因缘》表现的则是随着欧风美雨进一步深入、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猛烈撞击中,一代人冲出传统又囿于传统的二难境地:理智上清醒地反叛传统,向现代靠拢;情感上又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对传统自觉地回归。
如果说《玉梨魂》表现的是爱而不能的悲剧,那么《啼笑因缘》则体现出爱什么的艰难抉择。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平民化大少爷樊家树与贫寒鼓姬沈凤喜、豪门仕女何丽娜、江湖女侠关秀姑之间曲折复杂的情爱纠葛。樊家树是一个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既留恋传统又向往现代的矛盾人。与何梦霞相比,他有着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婚姻自主等现代意识,但骨子里对传统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依恋之情。他对东方情调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十分欣赏北海的美妙:“你看北岸那红色的围墙配合着琉璃瓦,在绿树之间,映着这海里落下去之日光,多么好看,简直是绝妙的暮色图画。不仅是西湖,全世界也只有北京有这样的好景致。我这次回到杭州去,我觉得在西湖盖别墅的人,实在是笨。放着这样东方之美的屋宇不盖,要盖许多洋楼。尤其是那些洋旅馆,俗不可耐。倘若是照宫殿式盖起红墙绿瓦的楼阁来,一定比洋楼好。”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使他“很醉心北京之美的,尤其是人的方面。”
这种文化心理决定了樊家树情爱追求的导向。沈凤喜、何丽娜都对他一往情深,长得又非常相像:“她的面孔和凤喜的面孔,大体上简直没有多大的分别,只是何丽娜的面孔略为丰润一点,在她的举动和说话上,处处持重一点,不象凤喜那样任性,这两个人若是在一处走着,无论是谁,也会说她们是姊妹一对儿。她模样儿既然这样的好,身份更不必提了,学问自然是好的。除了年岁而外,恐怕凤喜没有一样赛得过她的呢。”尽管在现实的砝码上,何明显重于沈,但在樊家树情感的天秤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东方情调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依恋。
在生活方式上,他崇尚平民化,反对豪华气。他喜欢凤喜素朴的装饰、清淡的生活,看不惯整日周旋舞场、影院的生活,对于过去暴露的“现代文明”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何丽娜富贵气逼人,是不能成为同调的。在为人处世上,他也有独钟:“凤喜是小儿女的态度居多,有些天真烂漫处;何丽娜又不然,交际场中出入惯了,也世故很深。男子的心事怎样,她不言不语之间,就看了一个透。这种女子,好便是天地间唯一无二的知己;不好呢,男子就会让他玩弄股掌之上。”在审美情趣上,他特别欣赏沈凤喜犹存的东方少女之自然神韵:天真烂漫而又温柔多情、体贴入微而又美貌惊艳、委婉含蓄而又娇羞妩媚。尽管沈凤喜后来失身刘德柱,樊家树对她还是一往情深,显示出对东方情调追求的执着深沉。
樊家树是以沈凤喜为尺度来衡量何丽娜的,在他心中,何丽娜是受外来畸形文化侵蚀的时髦女郎:“有一种过分的时髦,反而失去了那处女之美和自然美。只是成了一个冒充的外国小姐而已”、“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放荡了”。因此,樊家树亲沈远何就自然而然了。至于后来的结果求沈得何,既归因于东方情调的毁灭,又得自于摩登女郎向传统的回归。
《啼笑因缘》反映的文化心理实际上是处在东西文化夹缝中人们反叛传统又依恋传统,向往现代又排斥异端的“心理情结”的真实流露和形象表现。
伴随着中国社会艰难而缓慢的裂变,中国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无数仁人志士艰苦卓绝的努力,近百年不断的探索,中国人逐渐走出传统的巨大阴影,直面惨淡现实的人生,获得了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现代意识。这在《秋海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与《啼笑因缘》相比,《秋海棠》体现的文化心理更具有现代色彩。在这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和心灵契合的最基本因素。小说虽也是写名旦秋海棠与军阀姨太太罗湘绮之间的爱情悲剧,但其实质与前两部小说有明显的差异。
与何梦霞、樊家树相比,秋海棠没有进过学堂,至多只能算个业余知识分子。但由于他生活在现代气氛浓厚的时代,于潜移默化中受到现代思想的感染,形成其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其实暗示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再加上一位颇具现代意识的良友袁绍文的贯输:“物必自腐而后虫蛀之。……你要人家看重你,就得自己看重自己……”、“做戏子没有什么可耻,可耻的惟给人家做淫伶的人”,“因为你们唱戏的人,往往要和好人家的妇女乱混,所以才有人会把你们同样的当做玩物看!只要你自己守得清白,别说一个镇守使,就是大总统、大元帅,也不敢小看你。”时代的熏陶和友人的忠告,使他获得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等现代意识,才使他摆脱了军阀的缠纠,又顶住了荡妇的诱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现代人。
罗湘绮更是一个集传统美德与现代意识于一身的女性,她有着中国女性温柔美丽、善良多情的品性,又具有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人格独立等现代意识。与白梨影相比,她有追求幸福的勇气和大胆行动,又比沈凤喜多一份现代人的独立和尊严,虽与何丽娜同属时代新女性,但又少了一些洋气。
秋海棠与罗湘绮的爱情追求,体现出特定的文化意蕴。他们对于爱情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想寻找一个理想的伴侣,而且都有勇敢的行动。虽然也有片刻的犹豫和短暂的迟疑,但他们没有在道德的祭坛下低头,也没有在恶势力面前屈服。虽然他们也曾有过一丝的负罪感和片刻的不安,但相同的命运使他们心灵相通,对自由幸福的追求使他们摆脱了世俗的束缚,强烈的现代意识使他们走出了传统的阴影,他们以自己勇敢的行动,坚韧而执着的爱恋,谱写了一曲觉醒者的爱情悲歌,喊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最强音!
由此可见,《玉梨魂》表现人们在传统范围内现代意识的萌生,《啼笑因缘》表现了中西文化冲突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依恋,《秋海棠》则展示了现代人艰难的觉醒。从这一意义上讲,《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体现出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人们文化心理的嬗变,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纪转换期人们的文化心态史。
收稿日期:1994年9月19日
注释:
①严芙荪:《徐枕亚》。
②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
③严独鹤:《啼笑因缘·序》。
④《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14-315页。
⑤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