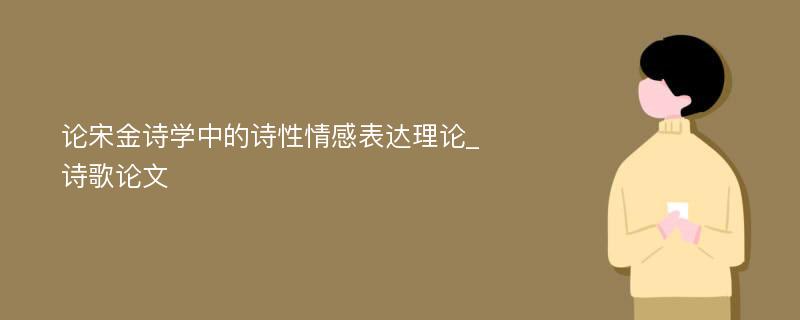
论宋金诗学对诗情表达理论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情论文,理论论文,金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194(2001)02—0181—09
一、诗情表达向自然的回归
整个宋金时期诗情表达理论在继续发展,其总动向是向自然回归。
说到向自然的回归,人们往往想到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名观点:回到自然。“回到自然”,或曰“返回自然”,都是人们根据卢梭在《爱弥儿》等著作中提出的“顺应自然”的观点而归纳出来的结论。其实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之后,就有不少人呼唤向自然的回归。回归大自然,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话题也表现在诗歌领域。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古希腊文化(Hellenic culture),一是希伯来文化(Hebrew culture)。古希腊人对人类与神灵的关系特别感兴趣。在希腊神话中,往往是神人共存。在古希腊的戏剧中,命运悲剧是大宗。即使在古希腊的喜剧中,我们往往也可以见到神明对人类的作弄。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二者相互结合的时间很早,它们合成一股宏伟的力量,称为“二希文化”。“二希文化”是我们中国学者的说法,如果用英文来表达,可以称为double H culture。在西方文学中,很早就有了回归自然的呼声。整个《圣经》就是一部记载人与上帝对话的书。据此而形成的圣经文学,在本质上也具有人与上帝对话的性质。西方文学受《圣经》的影响极大。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尽管西方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但是它依然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圣经文学的传统,还不时出现人与上帝对话的作品。至于那些声明反对圣经文学传统的文学创作,正好说明了圣经文学依然对它们存在着影响,否则就不必声明了。
中国文化中,《尚书》、《老子》、《庄子》等都是记载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的文献。这种关系,叫做“天人关系”。研究天人关系的努力,称为“穷究天人之际”。屈原写下了不少天人对话的名篇,整个《楚辞》实际上都带有天人对话的性质。表现这个主题较为集中的则是《九歌》、《天问》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屈原不仅描写自然,也写进了他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到了汉代,穷究天人之际的学问更加发达,表现了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探求和对终极关怀的关注。汉代和以后都有大量的诗歌描写天人关系。可以说,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地描写自然,或为写自然而写自然的。这就赋予了各种歌咏自然风光的诗篇以一定的哲理性。在唐代,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写下了穷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著作,用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人和大自然的对话。在唐诗中,咏物诗很发达。边塞诗则将自然风光、天人关系、爱国情怀、个人抱负等等情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新的诗种。到了这时,在中国诗歌中,对大自然的歌颂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差不多与生死、爱情等同样重要的主题了。历代都有不少诗人写下歌颂大自然的不朽诗篇。宋代是思辨哲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宋代又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鼎盛的时代。在宋诗中存在大量的歌颂大自然的作品。它们大都打上了思辨哲学和道家思想的烙印。这些作品描写细腻,也更讲究理趣。当时的诗学情形如何呢?下边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二、叶梦得主自然:从感情上与自然结合
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提出:“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1](P431)所谓“缘情体物”,即抒情状物, 也就是带着感情对现实事物进行具体的描绘。在叶梦得之前,陆机《文赋》曾发表过精彩的言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论文体均意与辞并重,缘情指意,绮靡指辞。诗缘情而绮靡,意思是说,因为讲究感情,诗歌的语言更加精妙了。也就是说,诗情的贯注不仅没有防碍,反而引起诗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这也适合与诗歌关系密切的辞赋一类文体。诗歌本来是讲究感情的,那么,感情的成分重了好不好呢?有人认为不好,认为诗歌注重感情,会使诗歌显得不够庄重,即影响诗言志的传统,重蹈六朝文学绮靡不振的旧习。在宋代也有人这样看。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叶梦得引用陆机的话而加以肯定,显然是反对那种误解的。叶梦得论诗,认为诗歌首先要抒情状物。诗歌既要抒情状物,就必然涉及到诗歌的语言形式方面。一般说来,抒情诗的语言,其形式往往比较华美。语言形式华美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要来得自然,不能过分做作。抒情成分比较重的诗歌,其形式既要华巧美丽,又不要失去其天然妙趣,不著刻削之痕,这样才能收到惟妙惟肖、形神俱备的效果。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叶梦得举了一系列例子。它们是:一、杜甫《水槛遣心二首》诗之一,载《杜工部集》卷第十二,又载《全唐诗》卷二二七。二、杜甫《春归》诗,载《杜工部集》卷第十三。三、杜甫《曲江二首》诗之二,载《杜工部集》卷第十。四、杜甫《登楼》诗,载《杜工部集》卷第十三。五、杜甫《阁夜》诗,载《杜工部集》卷第十四。六、韩愈《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系省称,全称为《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载《韩愈全集·诗集》卷十。[2](P96)又载《全唐诗》卷三四四。七、检刘禹锡集,不见《贺晋公留守东都》诗。叶梦得引用时较为疏略,不尽准确。他所引用的那一首诗,当为刘禹锡《郡内书情献裴侍中留守》诗:“功成频献乞身章,摆落襄阳镇洛阳。万乘旌旗分一半,八方凤雨会中央。兵符今奉黄公略,书殿曾随翠凤翔。心寄华亭一双鹤,日陪高步绕池塘。”此诗载《全唐诗》卷三六零。
为了讲清诗情的表达问题,叶梦得一共举了七个例子,谈如何表现才自然,谈如何表现才有气象。在以上七个例子中,叶梦得认为,前三个例子就都做到了“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如果我们运用诗歌来抒情状物,就应当像那样做。这三个例子,均属于杜甫的名篇,它们的语言都是极讲究的,相当“绮靡”,但是却并未“用巧太过”,因而虽然工稳、巧妙,却并未留下刻削的痕迹。因此,诗歌的语言技巧十分讲究,却一点也没有伤害作品的“气格”。“气格”,其基本的含义就是风格。说“气格”,更侧重于指较为宏大、雄壮、有力的风格,即西方诗歌所谓阳性的(masculine)风格。可是到了晚唐时期, 诗歌的风格就开始卑弱了,较多地呈现出阴性的(feminine)风格。过分的讲究语言技巧便会伤害作品的气格,使它缺少气势。犹如女孩子,打扮过分就失去真美。宋初的西昆派系紧接着晚唐而出现的诗歌流派,他们也同样具有过分讲究诗歌的语言技巧以至于伤害诗歌的气格的毛病。“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这两句并不是出于某一位诗认的诗句,也不是一种诗歌的体类,而是叶梦得自己依据晚唐和宋初西昆派的诗歌风格而拟作的两句诗,意在批评和讽刺。这两句诗对仗极工,语言技巧太过,显得做作,不够自然,也就是犯了我们平时所说的“甜熟”的毛病。
叶梦得举出后面四个例子,旨在说明七言诗怎样才能写得有气象。气象是诗歌凤格的一个侧面,对气象的表现也须自然。在后四个例子中,叶梦得肯定了牡甫的两首诗和刘禹锡的一首诗,他认为韩愈的那一首诗写得不够好。韩愈诗的缺点在哪里呢?叶梦得认为在于“言与语俱尽”,即不够含蓄。一般说来,叶梦得是赞赏韩愈的诗的,觉得韩愈的诗笔力杰出,气势磅礴。从诗行的结构上看,七言诗比五言诗多一个句节。由于古汉语中单音节词较多,多一个句节就至少多出一个词来,往往还会多出两个词来。在古汉语中,两个词有时候甚至可以构成一个分句。因此对于初学做诗者来说,七言诗比较容易入门。但是就诗歌的句式来说,容量一旦扩大,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七言诗不容易写得含蓄有力。把话说尽了,对于诗歌来说,那也是一种缺陷。因为这样一来,作者和读者想象的空间就都变小了。诗歌毕竟是主情的文体,对于作者和读者,都需要一个让感情得以酝酿回环的空间。总之,叶梦得结合诗歌创作史的实际,对诗歌中的感情表达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提出了具有个人独到之见的诗情学说。
三、苏辙主自见:从养气上与自然合一
苏辙的诗情表达理论主自见,侧重从养气上与自然合一。青年时代的苏辙不仅诗做得好,文章也写得条理清晰、论证严密而又有悠长的文气贯注其间。还在青年时代,苏辙就提出了“气充文见”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的主张。(栾城集,四部从刊影明活字本,卷二二)
苏辙是主张以委婉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诗情的,而《上枢密韩太尉书》则可以看成是苏辙这一主张的理论表达。在我们今天看来,三苏之中,以苏轼名气最大。不过在古代也有人认为苏辙水平最高。苏轼《答张文潜书》:“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惊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3](P376 )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集中观诗难为诗,犹群姝中观色难为色也。吾友陆务现,当今诗人之冠冕,劝予哦苏黄门诗。退取《栾城集》观之,殊未识其旨趣,甲申闰月辛未,郊居无事,天寒踞炉,如饿鸱。刘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读数过,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于此道真先觉也。”(周益国文忠集,卷十六)此外如刘攽、秦观等也有类似的说法。苏辙的情思之所以难为初读者所觉察,是因为它以文气的形态隐约地存在于字里行间,与作者的生命融合为一了。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这样概括苏轼和苏辙的性格特点:“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4](P414)知子莫若父,苏洵的话基本上预料了他的两个儿子的一生。苏轼的性格较为外露,其旷达豪放,毫无拘束。其文如此,其诗亦然。苏辙的性格较为内向,其诗歌创作实践如此,其诗学理论亦然:诗情可以而且应该极其充沛,然而其表现则应当尽量委婉含蓄。
苏辙认为,作者有充实的思想感情就会在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由于散文与诗歌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性,“气充文见”也可以转化为“气充诗见”。从苏辙对自己经历的叙述来看,可知他的养气的功夫,主要不在于书本知识,也不纯粹在于德行修养,而在于丰富的生活积累。苏辙强调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体验、观察和积累,以培养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够写出第一流的诗文来。由于苏辙讲究诗情的充足性,他后来的诗做得更好。甚至在北方的契丹国里,苏辙的不少诗篇也家喻户晓。他的诗篇还被北方人民刻在石壁上,以表示他们发自内心的尊崇和喜爱,而这一点苏辙本人并不知道。比如《使契丹题寺璧》诗“”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长傍溪。仿佛梦中寻蜀道,兴州东谷凤州西。”[4](P395 )《宋诗纪事》卷二十一引《池北偶谈》:“谷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苏颖滨诗云云。盖公元祐间奉使契丹时所题,而辽人刻石者。”[5](P525)检《栾城集》, 此诗即《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的《绝句二首》之一。苏辙之诗为北方人民所爱如此。又如《奉使契丹寄子瞻》诗:“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4](P398 )《宋诗纪事》卷二十一引《苕溪渔隐丛话》:“此《栾城集》中诗也。《渑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于璧间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集》。芸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此二句与子由之诗全相类,疑好事者改之,而为此说也。”[5](P525)检《栾城集》,此即《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的《神水馆寄予瞻兄四绝,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风》之三。可见其古文与诗歌的确很高明。
四、姜夔主自鸣:从音律上回归自然
姜夔精通音律,能自度曲。胡云翼《宋诗研究》认为,在南宋有两种诗人,他们的诗歌作风完全与江西诗相反。一种是理学家的诗,另一种是词人的诗。姜夔便属于词人而为诗者,他把姜夔归入“反江西派的诗人”之一。[6](P128)这种看法颇有见地。 姜夔的诗不仅具有词的意境,而且具有词的音律特征,因而富于歌唱性。在理学家们的诗作大为得势的时候,词学家们的诗作响亮地登场,客观上起到了调节当时诗坛的总体诗风的作用。姜夔有功于时代。其组诗《除夜自石湖归笤溪》[5](P1491)由十首绝句组成,作于绍熙二年(1191)除夕,写诗人在风雪中于船上过新年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并回忆了十年来的生活经历。除夕那一天,雪满篷舱,小船缓缓行于江上。诗人悠悠闲闲,从容构思着自己的诗篇,早已沉醉于如诗如画的意境之中。《文献通考》卷二四五《经籍》七二:“《白石道人集》三卷。陈氏曰:鄱阳姜夔尧章撰。千岩萧东夫识之于年少客游,以其兄之子妻之。石湖范至能尤爱其诗。杨诚斋亦爱之,赏其《岁除舟行十绝》,以为有裁云缝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7](P1939)姜夔这种独特的诗风既来自他的生活,也来自他的诗学。
姜夔有自己的诗情表达理论,即“诗本无体,天籁自鸣。”(《白石道人诗集自序》)这是姜夔提出来的论诗口号,讲的是诗情的表达原理。“天籁自鸣”上承庄子的文学思想。姜夔不是简单地向庄子回归,而是通过庄子来强调诗情表达的自然美。《庄子·齐物论》认为,地籁、天籁、人籁是三种质不同的音响。地籁,指风吹孔穴发出来的声音。人籁,指古代竹制乐器即排萧,因为需要借助人的口去吹才能够发出声音,故称为人籁。天籁,泛指自然界的音响,但不是指令人毛骨悚然的狂风怒号。从逻辑上说,地籁也应当包括在天籁之内,广义的天籁指风吹过大地时发出的音响。庄子所以用“地籁’二字,目的在于将不和谐的音响区别出来。庄子所以用“天籁’二字,是要强调音响的和谐、美妙、天然、自发的一面。从庄子之后,“天籁”就具有文章学的意义,专门用来指文章流畅而具有自然情趣,而广义的文章也包括诗歌在内。在北宋,欧阳修和苏轼都大力提倡文章和诗歌的自然天成。生活在南宋的姜夔,提出“文本无体,天籁自鸣”,是在南宋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欧阳修和苏轼倡导的优良传统的继承。
姜夔主张诗歌创作须自然天成,反对模拟前人和过分雕琢。姜夔考察了中国诗歌的流变史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诗歌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体制。《诗经》是人们公认的优秀诗歌的典范。《诗经》何以优秀呢?这是因为里面的作品都是出于自然天成。不过到了后来,虽然诗歌代有人作,诗歌的体貌却与《诗经》时代的诗歌不同了。大约从黄初年代起情况就有了变化。从魏晋开始到南宋时期,由于诗人内在蕴藏亦即思想基础的不同,因而写出的作品也就有了较大的差别。有些人由于没有看到时代的变迁,便难以理解这种种的变化,枉然在那里羡慕追求诗歌固定不变的体制,渴求有某种简便易行的法子让自己当上大诗人。姜夔的这一段议论是合乎中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实际的。接着,姜夔回顾了他自己学写诗歌的经历。他曾系统深入地学习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诗歌。后来姜夔对江西诗派不满意,便弃而不学了。姜夔转而走自己的道路,终于造就出具有个性的诗歌风格。顺便指出,姜夔不满意于江西诗派的地方主要是雕饰过头,并非完全不讲雕饰。在《白石道人诗说》中,他曾明白地指出,雕刻伤气则不可取,但是若鄙而不精巧,则是不雕刻之过。可知,姜夔所谓“天籁自鸣”实际上是追求诗情表达的最高境界。
姜夔认为,在南宋诗坛范成大、杨万里、陆游和萧德藻才是优秀诗人。萧德藻的诗歌以高古、奇峭、清新、小巧、工致为特征。《采莲曲二首》是萧德藻诗中清新、小巧的典型例子。萧德藻《古梅二首》:“湘妃危立冻蛟脊,海月冷挂珊瑚。丑怪惊人能妩媚,断魂只有晓寒知。百千年鲜著枯树,三两点春供老枝。绝壁笛声那得到,只悉斜日冻蜂知。”[5](P1293)以上是萧德藻诗中奇峭的典型例子。奇峭的风格来源何在?这大致相当于英国十七世纪玄学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笔下的奇思异想(conceit)。它来源于奇特的比喻。一般的比喻,主要由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构成,固然也能够丰富诗歌的表现力,但是难于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故难于构造出奇峭的风格。一般说来,那些由对立事物构造出来的比喻较为容易收到奇特的效果,较为容易形成奇思异想,较为容易构造出奇峭的风格来。在例一中,湘妃竟然斜立在蛟龙的背脊上,“湘妃’与“蛟脊”对立。丑八怪惊人的美丽,“丑怪”和“妩媚”又是矛盾对立。在例二中,“斜日”与“冻蜂”对立,斜日怎么说来也还是有一丝暖意的,然而暴露在斜日落晖中的蜂儿还是冻得要死!这样的比喻,在古今中外几千年的诗歌历史长河中确实不多见。又如《次韵傅惟肖》诗:“竹根蟋蟀太多事,唤得秋来篱落间。又过暑天如许久,未偿诗债若为颜。肝肠与世苦相反,岩壑嗔人不早还。八月放船飞样去,芦花丛外数青山。”[5](P1263)以上是萧德藻诗中工致的典型例子。此诗以虚词作对仗,以“又过”对“未尝”。又如《登岳阳楼》诗,这是萧德藻诗中高古的典型例子。在萧德藻诗的诸多特征之中,姜夔最喜欢的是他的工致。为什么大力提倡“自然天成”的姜夔会欣赏萧德藻的“工致”呢?原来,真正的天籁离不开人工。如果抹煞人工,那么最终导致取消艺术家们对天籁境界的不懈追求。如果抹煞天籁,那么就会抹煞检验诗歌艺术造诣的客观实践环节。
诗歌创作实践上,姜夔也做到了“天籁自鸣”。最典型的例子是《过垂虹桥》:“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萧。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在中国诗歌中有的作品可以让人过目不忘,读一遍即终生记得。此诗便属于这样的佳作。人们未必能够明白其深意,但是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美。此诗的音乐性是十分突出的。它的平仄完全合乎格律。《玉钥匙门法歌诀》说:“去声分明哀远道。”由于仄声中去声多于上声,因此听起来特别分明。去声字有:自、韵、最、唱、过、尽、路、四,共八字,占全部十四个仄声字的57%。平声属于舒声之一,发音可以拉长。阴平由古代的清声母字变化而来,其声清晰。由于平声字中阴平多于阳平,因此听起来特别澄明、清婉、亲切、恬静。阴平声字有:新、矫、低、吹、箫、中、松、烟、波,共九字,占全部十四个平声字的64%。而且,在第二句中,小与萧,低与吹,分别押中韵,从而构成同一诗行中的内部协和。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实为全诗关键。因为它体现了诗人与小红的爱情。而且诗人与小红共同的艺术爱好还使得他们之间的爱情长长久久不断升华。关于该诗的本事,《宋时纪事》卷五九引《砚北杂志》:“小红,顺阳公青衣也,有艺色。顺阳公之请老,美尧章诣之。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二曲。公使二妓习之,音节清婉。公寻以小红赐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云云。顺阳公即范石湖。”[5](P1492)显然,该诗的本事与前引《除夜自石湖归苕溪》组诗绝句十首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言姜夔两首词是《暗香》和《疏影》,[8](P2181)其曲调均为仙吕宫。仙吕宫在乐律上,为宫声七调之一,生于黄钟宫。宫声为五声音阶的起始音,其“声情”给人的听觉感受较为响亮。姜夔诗词音乐性较高,这是他对诗情表达学说的实际贡献。
五、王若虚主自得:从内心抒发自然
“诗贵自得”,语出王若虚《论诗诗》。《论诗诗》系今人为研究的而拟的名称,并非原来的标题。原诗有两组共八首。第一组含四首诗。第二组本来含三首诗,后来又增加一首。第一组诗《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云》:“骏步由来不可追,汗流余子费奔驰。谁言直待南迁后,始是江西不幸时?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衮衮笔头倾。莫将险语夸劲敌,公自无劳与若争。戏论谁知是至公,蝤蛑信美巩生风。脱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文章自得方为费,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第二组诗《王子端云:“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予亦尝和为四绝》:“功夫费尽漫穷年,病入膏肓不可镌。寄语雪溪王处士,恐君犹是管窥天。东涂西抹斗新妍,时世梳妆亦可怜。人物世衰如鼠尾,后生未可议前贤。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鞭。世间笔墨成何事,此老兄中具一天。百斛明珠一一圆,丝毫无恨彻中边。徒渠屡受群儿谤,不害三光万古悬。”(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卷四五)第一组诗,一本题作《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有言文首东坡,论诗右山谷之语。今之学者亦多以为然,漫赋四诗为商略之云》。第二组诗,元好问编《中州集》题作《王内翰子端诗,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漫赋三诗,为白傅解嘲》。[9](P146 )王若虚学有根底而专攻学问多门,是金元之际的大学者。有人认为王若虚的诗文创作平平,实际上也有颇为可观的作品。比如《贫士叹》、《白发叹》、《失子》、《病中二首》就是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佳作。《贫士叹》诗:“甑生尘,瓶乏粟,北风萧萧吹破屋。入门两眼何悲凉,稚子低眉老妻哭。世无鲁子敬、蔡明远之真丈夫,故应饿死填沟谷。苍天生我亦何意?盖世功名实不足!试将短刺谒朱门,甲第纷纷厌梁肉。”[9](P144)“自得”是王若虚论诗的主旨。“自得”指真实的思想感情在诗歌中的表达犹如从肺腑中流出。王若虚认为真正的诗人须有自己的真感情、真怀抱,而不依傍别人。只有这样的诗人,其作品才具有独创性。他从正面的肯定性论述和负面的谴责性批评两个角度出发,建立了他的“自得”说。
首先研究王若虚的正面论述。王若虚崇尚白居易和苏轼,以他们为正面的例子而加以褒扬和肯定。王若虚认为他们都是感情极其充沛的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能够“情志曲尽”,“随物赋形”。苏轼的诗歌宛如“万斛泉源,不随地皆可出。”其所以如此,都是首先得之于内,然后才形之于诗的。他们的诗篇大都是情感与智慧交互作用的产物,决非刻意求工的苦吟者所能企及。白居易和苏轼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主要是由于他们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感情。至于具体的创作过程,王若虚反对“经营过深”,“雕琢太甚”,这是因为他认为“哀乐之真,发乎性情”。他赞扬苏轼的诗歌如三江滚滚,笔底翻涌着波澜。他赞扬白居易的诗歌如明珠颗颗,晶莹圆彻落入玉盘。白居易和苏轼,在具体写作的时候,似乎都是不假思索,信手便拈来一首首诗的。实际上他们在诗歌中表达的事物早就在心中酝酿许久了,他们做诗时的那种挥洒自如的景象,不过是灵感迸发时的外在状态罢了。王若虚论诗宗白居易和苏轼,那么他是怎样评价他们的呢?这个问题值得细论,而且十分有趣。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是这样评价白居易的:“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卷三九)王若虚的《文辨》是这样评价苏轼的:“东坡自言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滔滔汩汩,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所知者当行于所知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论者或讥其太夸,予谓惟坡可以当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势,随物赋性之能,而理尽辄止,未尝以驰骋自喜,此其横放超迈而不失为精纯也邪?”(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卷三六)比较这两段评价,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点:“随物赋形”。这就是白居易和苏轼的共同特征。随,依据;物,客观事物。这里特指有待于诗人来表现的现实生活。赋,给予;形,形式。这里特指诗歌的表现形式。“随物赋形”,作为一个成语,为了便于以四字构成定格,未明确说出主体。“随物赋形”,系对外而言。既然有外,则必然有内。于是我们看到了内外的对立统一。作为一个命题,尚需具有主题的一方。那么,这个命题的主题是什么呢?显然,在这个命题中,主题与主体是一致的。主体就是诗人的真实感情。真实感情从何而来呢?只能“自得”于诗人的内心。
其次研究王若虚的反面批评。作为对比,王若虚以前辈诗人黄庭坚为负面的例子,《滹南诗话》写道:“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卷三六)本来苏轼和黄庭坚开宋朝一代诗风,黄庭坚虽然是苏轼的学生,由于其自成体系功勋卓著,苏、黄并称也是史上的定论。苏、黄于宋诗均有变新的意义,然而苏、黄二人的风格又大不相同。苏轼和黄庭坚,与历史上的任何伟大诗人一样,其伟大就其总体而言,就其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而言,至于他们的部分作品,并非完全毫无疵瑕。江西派诗人宗法黄庭坚而无取于苏轼,这种做法已经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了。至于江西派的末流,则只学到了黄庭坚的某些缺点。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王若虚的《论诗诗》时需要注意的。
王若虚还举出了他的同时代人王廷筠(1151—1202)为例,认为王庭筠之所以苦苦吟诗而不得佳篇,原因在于他在“诗贵自得”方面还做得不够。《金史》卷一二六有王庭筠传:“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晋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律诗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金史,卷一二六)从王庭筠传可知,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王若虚把“功夫费尽漫穷年”的王庭筠比作以管窥天,认为他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两个岂不是矛盾么?而且,就一般而言,王庭筠的诗歌创作,其水准远在王若虚之上。王若虚与王庭筠大体是同时代的人,应当了解所论对象的真实情形。他们俱为高官,俱以学问见称于世,又不见有个人怨恨之记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矛盾呢?这种矛盾只能说明,王若虚的本意在于强调“文章自得方为贵”,在于强调诗情表达的真实性。王若虚欲立其论,有时不免偏颇,这是可以谅解的。
六、宋金时期的天人对话
10至15世纪,中国的科技文化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01—)称有宋一代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63)。按照中国古典的研究惯例,广义的宋代文学也包括辽、金、元文学。在宋金两朝,虽然时有战争,但是科学、技术、文化、文学、文艺理论均在发展。就诗学领域而论,它的各个分支都在发展。叶梦得论诗情的主天然,侧重从情感上与自然结合。苏辙论诗情的表达主自见,侧重从养气上与自然合一。姜夔论诗情的表达主自鸣,侧重从音律上体现自然。王若虚论诗情的表达主自得,侧重从内心抒发自然。这四大板块构成了宋金时期诗情表达理论学说的主流。如果我们将中国诗学放在世界思想体系中加以考察,就会得到新的理论整合。宋金元时期,大致相当于西方各国的中世纪后期,当时的世界思想依然是以宗教为总论纲的体系。在中国,由唐至宋,佛教逐渐衰萎下去,道教愈发兴盛起来。道教这一中国本土宗教是十分重视天人关系的。在唐代,作为基督教一支的景教曾一度十分兴盛,并且由唐太宗立为国教之一,从而出现过儒、道、释、景四教并立的局面。会昌灭佛,景教也连带受到冲击,在中国内地消失了。人们常说的唐代三教并立,实际忽略了景教曾经在中国有过辉煌存在。到了宋代,道教极度兴盛,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天人对话关系、对自然的回归、天人合一、对人的终极关怀等问题依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在宋代,思想界的另一种动向则是理学的勃兴。理学的勃兴暗示着人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关注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即逻辑思辨维度的发展。如果我们从诗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唐代和元代,诗情表达理论中都不存在向自然回归的大趋势;在宋金时期,中国的诗情表达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向自然回归的大趋势。这一趋势在宋金时期的出现犹如波峰凸现,而唐代和元代则如波谷低回,对比是明显的。基督教在宋代的消失,并不能说明基督教思想在该时期的消失。天人对话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之一,它与人的基本生命期待紧密地契合着。任何一个民族,一旦接受了基督教思想,那是很难消除的。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民族的先进的、敏感的、优秀的组成部分,其情形更是如此。宋金时期中国诗学中诗情表达理论的特别发达、细致和深入,可以看作天人对话思想借助诗歌理论形态而隐含地存在着。换句话说,在宋金时期,逻各斯(Logos)、话语(Word)和道(Way)还是存在着的。到了元代,也里可温教兴盛起来了,它是基督教的另外一种形态。天人关系的表达多了一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比诗学更为广阔和开放。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诗学领域中相应的理论和学说也就少了。
[收稿日期]2000—08—24
标签:诗歌论文; 叶梦得论文; 王若虚论文; 姜夔论文; 语言风格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杜工部集论文; 全唐诗论文; 栾城集论文; 苏轼论文; 萧德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