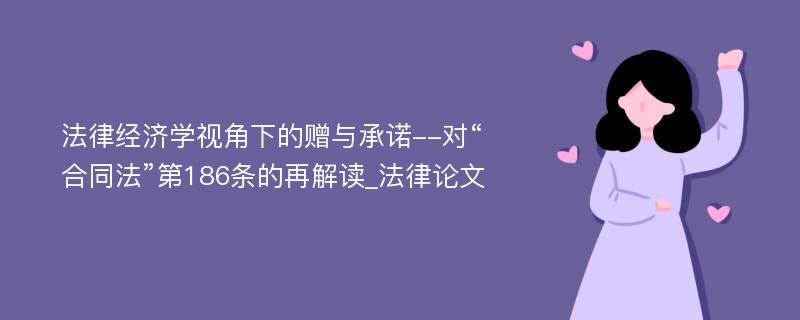
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赠与承诺——重解《合同法》第186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同法论文,经济学论文,视野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205(2014)04-0051-(008) 假定我口头答应两个月后赠送给你一条牧羊犬,事后却反悔了;你不幸地相信了我的承诺,并因此失去了一次低价购买同种牧羊犬的机会。但是,你若为此起诉我,则即使证据确凿,你也打不赢这场官司,法院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合同法》第186条关于赠与合同有明确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相对于“契约必须遵守”的一般合同法原则,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算是个例外情形。但是,为什么法律区别对待赠与承诺和交易性承诺?这个问题迄今未被国内民法学界认真思考,相关讨论虽有所涉及,但大都一笔带过,千篇一律的解释是: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由于赠与人承担的义务是单向的,所以要赋予其撤销权以允许其反悔,否则对赠与人未免过分苛刻,并因此有失公平①。 然而上述解释很快就会遇到麻烦。假定我答应赠送你牧羊犬的事情发生了一点变化,我和你签订了一份书面赠与合同并且做了公证。此时,如果你起诉我,你就会打赢官司,法院也会强制执行我的承诺。根据《合同法》第186条关于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一旦赠与合同经过公证,赠与人就无权撤销承诺。但令人迷惑的是,为什么赠与承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沿用“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说辞很难回应这一诘问。 虽然司法实践中的赠与纠纷并不多见,但由此引发的理论问题却非同小可。只需将两个假设的案例稍作对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大陆合同法的“合意”理论,还是英美合同法的“对价”理论,在对关于赠与承诺可否被强制执行的解释上,都难以自圆其说。按照“合意”理论,倘将赠与合同定性为“实践性合同”(合同在赠与财产权利交付时成立),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赠与合同经过公证却能摇身一变成了“诺成性合同”;按照“对价”理论,倘说法院不会强制执行没有“对价”的承诺,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公证程序可令对价无中生有,以致竟能凭空虚构一个“名义对价”。更何况,诸如“实践性合同”以及“没有对价”之类的说辞,都只是关于赠与合同的一个描述,而不构成其无法被强制执行的一个解释。 本文试图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主要是《合同法》第186条)做出一种理论解释,以弥补传统合同法理论在赠与合同解释上的深刻裂痕。在美国,关于“无偿承诺(gratuitous promise)”的经济分析文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积累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知识区,它是“利他主义法律经济学”这一更为广阔论域的组成部分②。尽管如此,在吸收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我仍期望本文的分析能够有所突破。不同于以往经济分析文献对赠与承诺一概而论,本文将赠与承诺按当事人赠与意图的强弱分为三类(即“真心承诺”、“假意承诺”及“试探性承诺”),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合乎实质正义(即追求决策零误差)的法律方案,继而引入法律实施成本的变量,以最终发现司法实践中可操作的法律方案。与追求实质正义不同,追求法律方案的可操作性,是通过合理牺牲法律实施精确性来换取法律实施效率(降低实施成本)的努力。 法律术语的不精确会导致思维上的混乱。按大陆法系的传统,合同的订立被描述为从“要约(offer)”到“承诺(acceptance)”的过程,但若用这两个概念描述赠与合同的订立,却至少在汉语语境中显得十分别扭——将赠与人称为“要约人”,而将受赠人称为“承诺人”显然不合乎汉语习惯。交易性合同在英美合同法理论中被更为恰当地描述为一组“双向承诺(bilateral promises)”,它包含了彼此对应且可被分解的两个承诺③;与之不同,赠与合同只是赠与人向受赠人做出的一个“单向承诺(unilateral promise)”。鉴于这种表述更为清晰,下文将用“赠与承诺”的概念取代“赠与合同”④,做出承诺的一方是“承诺人(promisor)”,接受承诺的一方是“受诺人(promisee)”;通常情况下,他们就是“赠与人(donor)”和“受赠人(donee)”。 一、赠与和赠与承诺的功能 赠与通常被认定为一种利他主义行为⑤。理论上,当他人的满足成为自我满足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利他主义赠与就会发生⑥。但绝大多数赠与不是纯粹利他主义的,我之所以今天赠送你一瓶酒,目的是激励你明天回赠我一条烟,这种具有互惠性质的相互赠与其实是一种替代性交易;如果恰好你酷爱喝酒而我又喜欢抽烟,那么我们互赠礼物的行为就会创造“交易剩余”。正如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发现的,在市场交易不发达的社会,礼物交换就是赤裸裸的交易⑦。 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礼物交换的商业性功能已基本不复存在,赠送礼物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信号,以表明赠与人试图和受赠人建立、保持或加深人际交往。我精心挑选了一份礼物赠送给你,如果你不想辜负我这番好意,你就应该收下它以表示“领情”。接受礼物的行为意味着你愿意在一段时间内将自己置于我的“债务人”地位,同时表明你同意我将要向你施加某种影响力(所以,不难理解许多行贿是以礼物赠送的方式来完成的)⑧。按照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拒绝接受礼物,或者在接受礼物之后又立刻回赠一份价值相当的礼物,都可能被理解为不友好的举动(有时甚至被视为冒犯),这两种行为都表明你拒绝我的好意,因为你不想成为我的“债务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传递信号为目的的赠与具有明显的互惠性质,但它仍需要被一层利他主义面纱遮掩起来,以区别于赤裸裸的交易,否则,赠与行为传递的友好信号就会被削弱。[1]50-55 赠与行为还可以让赠与人向除受赠人之外的更为广泛的群体发出信号,以表明其拥有慷慨大方或乐善好施的美德(这可以让赠与人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或升迁机会)。当赠与人的信号目标从受赠人扩展到一个广泛群体的时候,赠与就变成了捐赠。捐赠并非纯粹的利他主义行为,在很多时候,捐赠是一种花钱买声誉的交易。对企业而言,捐赠类似于打广告。事实上,绝大多数企业把捐赠任务分派给销售部门并将捐赠支出列入企业的促销成本之中。声誉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它既可以用金钱来购买,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兑现成金钱。[1]50 但令人迷惑的是,为什么人们会为赠与做出承诺呢?既然我已打定主意两个月后赠送你一条牧羊犬,为什么我会事先做出承诺?行动不是比语言更响亮吗?上述提问让我们发现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赠与是一回事,为赠与做出承诺是另一回事。传递信息无疑是赠与承诺的功能之一,如果你事先得知我将要赠送你一条牧羊犬,你就不再忙着去市场上寻找同种牧羊犬了,你还会提前建造狗窝,准备狗粮,学习养狗知识;这意味着,只要承诺确定兑现,则即使在赠与物不变的条件下,仅仅一个承诺就能额外地改善你的境况;换言之,赠与承诺能在赠与财产之外创造额外的价值。通过事先做出承诺,赠与人可以提高受赠人对赠与财产的效用评估值,并因此给赠与人自己也带来一个效用增值。[2]412此外,在互惠性质的赠与中,承诺的另一个功能是可以让赠与人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影响受赠人的行动。尽管牧羊犬在两个月之后才会送到你家里,但如果我现在做出承诺,就能提前收获你的感激。在以上两种意义上,赠与承诺都可以创造与交易性承诺同样的价值。 二、赠与承诺的主观分类 与交易性承诺不同,赠与承诺往往不能清晰表达承诺人的真实意图。你出价100万元要购买我的一套房产,我要么同意,要么拒绝,其中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事实上,模棱两可被推定为拒绝)。而赠与承诺则不然,我答应赠送你一套房产,这在形式上表现为承诺,但我的承诺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假意的,还可能是试探性的;且在严格意义上,这几种承诺都不违背公序良俗。法律如何对待赠与承诺,按照实质正义的标准,自然要考虑当事人(主要是赠与人)的真实意图。为了能够细致描述赠与人的真实意图,下文根据赠与意图的强弱把承诺分为三类,即“真心实意”的承诺、“虚情假意”的承诺以及“试探性”的承诺。当然,分类只是为了描述的方便,相邻类型之间的界限只是逻辑上的;而事实上,从一种类型到相邻的另一种类型,是过渡的而非跳跃的。此外,在下文的讨论中,受赠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假定为“无差别的接受”,因此不予考虑。 (一)真心实意的赠与承诺 大量关于赠与合同的讨论都隐含着一种不假思索的观念:强制执行赠与承诺,对受赠人有利,对赠与人不利⑨。这种观念忽略了强制执行给赠与人带来的利益。假定我打定主意要在两年之后赠送你10000元,并且做出了明确的承诺。尽管这笔礼金数额不菲,但在你眼里,我承诺赠送的礼金其实远不值10000元,因为它只是“期货”,而不是“现货”。撇开通胀因素不谈,你至少会想到两年间的变数很大,我可能随时改变主意,甚至承诺本身就是信口开河。尽管我的承诺出自真心实意,但你猜不透我的心思,看不到我的真诚,你我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只要你认为我兑现承诺的概率达不到100%,你就会根据这个概率的评估值对我赠送的礼金打个折扣。假定你认为兑现概率只有50%,那么10000元礼金的预期价值在你眼里就缩水成5000元了。这显然对我不利,因为你低估了我承诺赠送礼金的价值。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我还想获得赠送你10000元礼金的预期效用,就不得不提前兑现承诺(甚至立即兑现),或者被迫增加承诺赠送的金额(甚至翻倍)。这两种选择都会给我造成效用损失。若要避免或减少这项损失,就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换言之,必须设法增加你对承诺的信任度。致力于此,提高我违背承诺的成本是可行的途径——如果你发现,我违背承诺是得不偿失的,你自然会更加信任我的承诺。然而,如何提高我违背承诺的成本呢?最现实的选项莫过于让法院强制执行我的承诺。 由此可见,只要承诺出自真心实意,则强制执行既能保护受赠人的利益,又能提高赠与人的预期效用;这意味着,强制执行赠与承诺,如同强制执行商业性承诺一样,结局都是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2]411[3]404真心实意的赠与人只会期望而不会惧怕强制执行,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二)虚情假意的赠与承诺 与真心实意的赠与人不同,“虚情假意”的赠与人不会期望其承诺被强制执行。社会上有很多人喜欢信口开河,随意许诺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古人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君子毕竟是少数,何况,即使是君子,也难以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言出必践”。“假意承诺”是一种温和的欺骗,虽并不构成欺诈,也难说违背公序良俗,但毕竟对社会有害无益。倘若“假意承诺”被强制执行,理论上可以减少“假意承诺”的数量,进而减少鱼目混珠,提高人们对“真心承诺”的信任度。但这个设想行不通。 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虚假承诺,法院的最佳态度是置之不理,否则,难以计数且琐屑无聊的空头许诺会让法院难以招架。更何况,许多“假意”的承诺人并无邪恶企图,他们随意许诺往往只图个一时痛快,或只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说者无心,听者也无意,很少有人把大话当真。可是,一旦“假意承诺”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就会激发许多机会主义诉讼,原本没有当真的受诺人会谎称自己确实当真了,还可能编造出各种“信赖损失(reliance loss)”以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如此,强制执行所带来的少量社会收益(减少“假意承诺”数量)就可能被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增加机会主义诉讼的数量)所淹没。 然而,虚假的承诺确实会导致真实的“信赖损失”。假定我答应半年后送你一辆二手车,我只是随口一说,事后全然没放在心上;但你却把我的“假意”当成了“真心”,随后,你盖了个车库,还专门学习了驾驶技术,半年后你才发现我的承诺其实只是个谎言。期待中二手车彻底泡汤了,可是你的“信赖损失”找谁去算账?我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我随口一说,你就信以为真了,你对我的信任是天真的、草率的、孩子气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理应由你自己来承担。合同法只鼓励人们对他人的承诺投入“合理的信任(reasonable reliance)”,而不是“过度的信任(overreliance)”。[4]167-171进一步说,你我之间的“合意”有名无实,你的“信赖损失”源于一场“误会”⑩。倘把这场“误会”看做一种事故,就可以根据侵权法的经济学逻辑去思考——谁能以较低的成本避免这个事故(11)?尽管你我双方避免事故的预期成本在个案中无法比较,但法院却会推定:让你提高些警惕要比让我改变自己随意许诺的生活习性更容易一些(因而,由你来承担损失就比让我去赔偿损失更可能减少“误会”的数量)。这一推定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上像我一样随意许诺的人数量众多,而像你一样粗心大意的人却很罕见,将责任分配给粗心大意者可以使法律“树敌较少”,由此降低法律的管理成本。显然,相对于个案的合理性,法院更注重判决在未来产生的社会激励。毕竟,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欺骗的世界,这是法律无力改变的既定社会条件。尽管一律执行赠与承诺,可以减少谎言和欺骗的数量,但由此产生的少量社会收益补偿不了极度攀升的执行成本;相反,拒绝粗心大意者的索赔请求却可以抑制诉讼的动机,减少诉讼的数量,降低法律的实施成本。[2]416更何况,如果法律应该鼓励人们去成长,就不应过分保护那些天真无邪的人们。 (三)试探性的赠与承诺 有许多赠与承诺既非“真心”,亦非“假意”,而是“试探性”的;试探性的赠与承诺处于“真心承诺”和“假意承诺”之间的过渡地带。可以稳妥地打赌说,当学者们论及强制执行赠与承诺对赠与人有失公平的时候,他们脑子所想到的主要是试探性的赠与承诺,而非真心实意的赠与承诺(12)。在社会交往中,试探性的赠与承诺很常见。我之所以答应以后每年帮你购买春运期间的火车票,目的是想和你建立更为密切的人际关系,但由于我不清楚这份好意是否只是一厢情愿,所以我会在未来观察你的行动。如果你的所作所为让我满意,我自然会兑现承诺;但如果你让我失望了,那么对不起,我的承诺也就不了了之。这种试探性承诺实际上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承诺,只是按照社会交往的习惯,赠与条件不便说到明处,更不便写在纸面上,它相当于赠与合同中的一个“默示条款”。试探性承诺中的另一种默示条款类似于“情势变更”,例如,我答应明年赠送你一副名人字画,正常情况下我愿意兑现承诺,但若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端(诸如,我的生活突然拮据了,或者字画的价格猛然飙升了,或者有位我得罪不起的朋友也看中了这幅字画,等等),我就会改变主意。 尽管试探性承诺一般不会采用书面形式,但无论是承诺人,还是受诺人,对承诺的性质、目的以及何种情况下承诺作废等事项均彼此心照不宣。强制执行试探性的赠与承诺一般不会产生社会收益。最重要的原因是,法院难以判断承诺所隐含的那些应该兑现的条件以及可以撤销的情势,更难以判断条件是否确已具备以及情势是否确已变更。尽管,在试探性承诺的情形中,强制执行也会增加受诺人对赠与财产的评估值,并由此给承诺人带来一个效用增值,但对于承诺人来说,这个效用增值通常补偿不了因丧失撤销权而产生的效用损失。由此可以推定,在试探性的赠与承诺中,绝大多数承诺人的真实意图是不希望其承诺被法院强制执行。倘若试探性承诺被受诺人误解为真心承诺,则其“信赖损失”(如果有的话)仍由自己来埋单,其中的道理与受诺人误把“假意”当作“真心”是一样的(13)。 三、法律方案的比较 前文的分析暗示了一个如何处理赠与承诺的立法思路:法院应当强制执行真心实意的赠与承诺,而不去理会虚情假意的或试探性的赠与承诺。换言之,法律决策者应将“真心实意”作为强制执行赠与承诺的条件。然而,即使这个思路对头,也只是纸上谈兵,其操作性障碍显而易见:法院难以辨别承诺人的真实意图——谁知道承诺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两者皆非?根据承诺人的主观意图来决定承诺是否应被法院强制执行,虽然理想,但并不现实。实质上合理是一回事,形式上合理是另一回事。要设计出可实施的法律方案,必须将可观察的“标识”作为强制执行的条件。标识还应具备实现“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的功能,即让那些真心实意的承诺人努力获得这些标识,以区别于那些虚情假意或试探性的承诺人,如此设计出的法律方案才能在拥有了合理形式的前提下,又不至于在实质正义上偏离太远。 可观察的标识无非是书面记录(包括赠与合同文本、承诺人单方立下的字据以及其他文字记录)和公证手续。赠与承诺由此可被分为三类:即口头承诺、未经公证的书面承诺以及经过公证的书面承诺。同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法律方案:(1)仅将书面记录作为强制执行的条件,拒绝执行口头承诺;(2)将书面记录和公证手续共同作为强制执行的条件,拒绝执行口头承诺和未经公证的书面承诺。显然,与方案(1)相比,方案(2)规定的强制执行的门坎更高,因而,下文把方案(1)称作“宽松方案”,把方案(2)称作“苛刻方案”。 (一)宽松方案Vs.苛刻方案 倘若满足强制执行的条件是无成本的(交易成本为零),则无论采取哪种法律方案都会出现最优结果。真诚的承诺人会通过满足强制执行的条件向受诺人发出信号,以表明自己的承诺确实出自真心实意;而虚情假意的承诺人和试探性的承诺人则恰恰相反,为了避免其承诺被法院强制执行,他们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此,“宽容方案”与“苛刻方案”在结果上没有分别,最终都会实现“分离均衡”。实际上,如果满足强制执行条件的成本为零,也无所谓“苛刻”与“宽容”。 然而,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毕竟不现实,满足强制执行的条件是有成本的。倘若法律决策者选择“宽松方案”,则满足强制执行条件所要耗费的成本十分低廉,只需把承诺写成文字而已。但若要满足“苛刻方案”的强制执行条件,成本就高昂得多。倘以耗费时间作为评估指标,粗略地说,口头承诺可以以秒计算,书面承诺至多用分钟计算,而公证则正常要耗费双方当事人的半个工作日。公证费更是一笔可观的支出,并且与赠与财产的价值正相关(14)。 要求当事人满足强制执行的条件,类似于就赠与事项向当事人双方征税。理论上,当强制执行给承诺人带来的收益被“税务负担”所淹没的时候,承诺人就会放弃满足强制执行的条件,最终的结果就会背离完美的分离均衡。如此,出于“避税”的考虑,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真诚的承诺人将会放弃被强制执行的机会。相比之下,“宽松方案”的“税务负担”要轻得多,出于“避税”考虑而放弃强制执行收益的承诺人也会少得多。如果“宽松方案”比“苛刻方案”更容易接近完美的分离均衡,那么实质正义就会要求《合同法》降低强制执行的门坎,从而将强制执行的范围扩展到未经公证的书面承诺。 然而,上述结论忽略了“苛刻方案”相对于“宽松方案”的巨大优势——前者可以抑制当事人的诉讼动机,减少诉讼和强制执行的数量;相反,如果立法采取“宽松方案”,就势必会有大量琐屑的赠与纠纷因执行门坎太低而涌向法院。但是,这一看似强有力的质疑其实站不住脚,如果立法者试图通过“征税”减少赠与诉讼的数量,那么最合理的安排应该是提高案件受理的诉讼费,而不是要求当事人在缴纳诉讼费之前先去缴一笔公证费。显然,较之将“征税权”分散到公证机构和法院,由后者独享“征税权”不仅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包括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也有利于灵活调控赠与诉讼的数量。按照庇古的经济学逻辑,仅仅通过调整诉讼费,法律决策者就可以将赠与诉讼的数量控制在任意一个期望值。 “苛刻方案”的另一个相对优势是它可以降低诉讼中的证明成本,使判决结果更容易预测,从而减少诉讼的数量。但是,公证在强化证据效力方面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十分有限,因为书面承诺足以提供高强度的证据效力。更何况,一般说来,较之交易性承诺,赠与承诺要简单得多。如果越是简单的事项对公证的依赖越弱,那么,不要求交易性承诺去做公证而要求赠与承诺去做公证,就是法院在提供公共服务(强制执行)方面的一种不合理歧视(15)。尽管如此,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歧视仍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被正当化。 首先,经济分析并不能完全捕获法律的复杂性。尽管在理论上,法院可以通过收取诉讼费来调控诉讼的数量,但诉讼费的多少并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确定诉讼费的标准和额度常常会遭遇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16)。受阻于政治压力,即使在诉讼数量极度膨胀的时候,法院通过提高诉讼费来减少案件数量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尽管,与提高其他纠纷案件的诉讼费相比,提高赠与纠纷案件的诉讼费政治阻力最小,但由于合同纠纷案件传统上会采取统一的收费标准,单纯提高某一类案件的诉讼费会让人们感觉莫名其妙。考虑到上述因素,通过某种隐蔽的歧视措施以减少赠与诉讼数量的做法,即使缺乏明显的经济学理由,也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合理性。 其次,在市场交易发达的现代社会,赠与的社会功能已经今非昔比,因此,较之交易性承诺,赠与承诺所获得的法律保护也应相对减弱。[5]567-609并且,强制执行在一个方面强化赠与动机的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会削弱赠与的动机。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赠与行为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环境中所传递的信号尤为强烈;而一旦法律介入,信号就会被稀释,人们会认为赠与人之所以兑现承诺是因为害怕被其承诺被法院强制执行,而非出于利他主义动机。如果赠与人的利他主义动机受到怀疑,赠与的动机就会被削弱。在这个意义上,前文的分析夸大了强制执行所产生的社会收益。 不仅如此,关于合同法的经济分析也许在整体上夸大了违约的法律救济(作为国家提供一种公共物品)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尽管法律救济能够强有力地阻止合同履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同时也抑制了信誉机制在激励当事人遵守合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倘若没有法律救济,当事人就会通过其他方式来提升其承诺的可信度——他会更加注重积累自己的信誉,也更担心信誉受损所造成的损失。但如果当事人对法律救济产生了“依赖性”,就会出现“供给创造需求”的局面。正如,尽管毒品能够暂时解决成瘾者的痛苦,但却不能由此认定毒品供货商立下了功劳。许多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都表明了,就阻止合同履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言,法律救济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重要,因为社会还存在替代法律救济的信誉机制(17)。就赠与承诺而言,替代强制执行的信誉机制更容易发挥作用。绝大多数赠与是隐蔽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5]567-609我之所以承诺赠送你一条牧羊犬,目的是为了协调或促进与你的人际交往。同时我也很清楚,一旦我违背承诺而没有合适的理由,结果就比单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更加糟糕,因为你会拥有足够的机会和手段对我实施惩罚。对于相当数量的赠与人而言,恪守承诺主要动机不是害怕法院的强制执行,而是担心与受诺人的人际关系遭到破坏。而在利他主义赠与中,信誉机制更容易发挥作用,因为受赠人若想对赠与人实施惩罚,甚至无需付诸行动,比如消费者对商家的“用脚投票”。上述事实都强化了合同法应采取“苛刻方案”的理由。 (二)强制执行Vs.赔偿损失 前文一直在讨论强制执行,这似乎暗示了强制执行是法院处理赠与纠纷时所采用的主要救济方式。事实的确如此(18),但多少还是令人迷惑。合同纠纷的主要救济方式是赔偿损失,法院很少发出强制执行令(19)。可是,为什么在赠与纠纷中强制执行却取代了赔偿损失的核心地位?当赠与人违背承诺时,法院为什么会强制执行他的承诺,而不是仅仅责令他赔偿受赠人的违约损失? 合同法之所以会允许违约方在继续履行合同和赔偿被违约方损失之间做出选择,目的是不想阻止一些有效率的违约。[6]违背赠与承诺同样可能是有效率的,赠与人在做出承诺之后可能发现另外一个人(包括他自己)比受赠人更适合拥有该项赠与财产,以致将赠与财产改赠他人(或留给自己)所产生的效用增加值在补偿了受赠人的损失之后还有盈余。在这种条件下,法院强制执行赠与承诺就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然而,受赠人损失是难以确定的。确定受赠人的损失有两种依据:一是受赠人丧失的预期收益,二是受赠人因信赖承诺而产生的“信赖损失”。倘若按“预期衡量法(expectation measure)”评估受赠人的损失,那么,在纯粹利他主义赠与中,受赠人丧失的预期收益就相当于赠与财产的价值,此时,强制执行与赔偿损失的结果是一样的;而在互惠性质的赠与中,受赠人丧失的预期收益仅相当于赠与财产的“利润”,它是受赠人应该分享的“交易剩余”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互惠性质的赠与总是以利他主义的面目出现,所以,在法院无法确定赠与性质的条件下,只能将所有的赠与都推定为利他主义赠与,其结果就是强制执行吸收了赔偿损失。按照“信赖衡量法(reliance measure)”评估受赠人的损失会造成更多的麻烦,除了同样存在损失难以确定的问题之外,还会导致受赠人对承诺的过度依赖。 四、公益性的捐赠承诺 捐赠承诺几乎无条件地会被法院强制执行。根据《合同法》第186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无权撤销承诺。对此,不少学者解释说,救灾、扶贫事关重大,因违背捐赠承诺所产生的“信赖损失”非同一般,出于保护社会弱者的需要,法律应对捐赠人提出比一般赠与人更为苛刻的要求。[7]但上述逻辑依赖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强制执行捐赠承诺必须从整体上对社会是有益的,即可以改善捐赠人的境况。若非如此,结果就会事与愿违。倘若捐赠人觉得强制执行过分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此造成的效用损失超过了强制执行给他们带来的收益(这项收益来自于受赠人以及其他人对捐赠财产的评估增值),那么,强制执行就会削弱捐赠动机,减少捐赠数量,结果反倒不利于受赠人。 幸好,强制执行确实可以让绝大多数捐赠人受益。倘若捐赠承诺可以随意撤销,承诺本身就贬值了,这将导致承诺人花同样的价钱却只能买到较少的声誉。而强制执行则可以提高捐赠承诺的可信度,并提高人们(包括受赠人)对捐赠财产的评估值,从而让捐赠更具吸引力。对于捐赠人来说,承诺的挑战性越高,它能换取的声誉就越多。 强制执行捐赠承诺的另一个理由是阻止捐赠行动中的“搭便车”。以救灾或扶贫为目的的捐赠大多是一种集体行动,捐赠人的集体声誉是靠那些认真兑现承诺的人们积累起来的。然而糟糕的是,只承诺不兑现的少数人却可以免费捞取同样的声誉,这种“搭便车”的行为被大陆媒体指责为“诈捐”。“诈捐”不仅欺骗了受赠人,而且贬损了捐赠活动的集体声誉,并因此给那些真诚的捐赠人造成连带损失。长远看,一旦“诈捐”泛滥,鱼目混珠,真诚的捐赠人就会被迫退出捐赠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强制执行捐赠承诺可以防止捐赠活动蜕变成“柠檬市场”。不仅如此,捐赠承诺的执行成本相对低廉。公益性的捐赠承诺大都有文字记录,或者采取公开的方式。保存完好的证据可以大大降低法律的实施成本和错误成本。 《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该条法律规定包含三个要点:(1)通过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法律区别对待赠与承诺与交易性承诺;(2)对于强制执行赠与承诺,法律采用了“苛刻方案”,强制执行的形式条件是赠与承诺经过公证;(3)对于强制执行捐赠承诺,法律没有规定任何形式要求。前文的分析为该条法律规定提供了一种远比传统合同法理论更为坚实的理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一个认为经济分析只能用以解释英美合同法而不能用于解释大陆合同法的荒诞符咒。然而,由于本文并未提出关于修改法律的任何批评性建议,所以难免让人怀疑经济分析的价值——既然经济分析的结论和人们的直觉性判断基本吻合,那么,经济分析又有何用?这个质疑正是国内法学界针对法律经济学的许多固执偏见之一。 没错,绝大多数时候,法律决策者做出正确判断可以独立于深谋远虑的经济学思考。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制度文明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其中包含了无数次试错、检验和淘汰的过程,能够有效增进社会福利的制度很少来自于某个强大心智的精心设计,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积淀,是一代代人们的经验积累,以至于生活于制度之中的人们竟可以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20);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已经获得了借助直觉来完成决策的能力(据说这种能力集中于大脑的前额叶和顶叶皮质),[8]尽管直觉性的判断难免会犯错误,但其相对于深思熟虑的巨大优势是可以减轻思考的负担,在这个意义上,“难得糊涂”的人们反倒会在生态竞争中获得优势。 然而,以上两个事实都不能否定经济分析的价值,经济分析的解释力可以独立于法律决策者的清醒意识。因为,倘若经济分析可以深化人们的思考,它就能有效降低法律决策者犯错误的概率,从而使制度的进化更容易捕捉正确的方向。并且,只有在深思熟虑的检验中,直觉才会变得更加敏锐,彻头彻尾的直觉只意味着莽撞。更何况,学术研究是个服务行业,其价值就在于研究者通过写作去节省别人的思考,进而帮助别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倘若研究者只用“公平正义”或者“权利义务相一致”之类的说辞去泛泛而论,研究者的思考也就泯然众人矣,其结果将导致学术研究的职业尊严岌岌可危。 收稿日期:2013-08-13 注释: ①这种观点散见于许多著述之中。如,韩世远:《合同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431页;崔建远等:《债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0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0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1-662页;王利明等:《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30页。 ②参见一个较新的综述,Susan Rose-Ackerman,Altruism,Nonprofits,and Economic Theory,34 J.Econ.Literature,701-728(1996). ③假定你同意用10万元买我一辆二手车,那么我们签订的合同就包含了两个相互之间的承诺。一个是我对你的承诺:只要你同意付给我10万元,我就给你这辆二手车;另一个你对我的承诺:一旦我同意给你这辆车,你就会付给我10万元。 ④绝大多数英文文献习惯于“无偿承诺”这一更加宽泛的概念。 ⑤绝大多数关于赠与承诺的法律经济学文献都把利他主义当做赠与行为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动机。例如可参见,Michael J.Trebilcock,The Limits of Freedom of Contract,170-87(1993); Charles J.Goetz & Robert E.Scott,Enforcing Promises:An Examination of the Basis of Contract,89 Yale L.J.1261(1980); Richard A.Posner,Gratuitous Promises in Economics and Law,6 J.Legal Stud.411(1977); Steven Shavell,An Economic Analysis of Altruism and Deferred Gifts,20 J.Legal Stud.401(1991). ⑥假定你我之间有交情,你的快乐会带给我一些快乐,假定二者的相关度是15%,这意味着,给你增加100个单位的效用,就会给我增加15个单位的效用。如果我手头的一瓶酒只能给我带来10个单位的效用,但却恰好能给你带去100个单位的效用,那么我就愿意把这瓶酒赠送给你。在这里,赠与给我创造了5个单位的效用增值。 ⑦互赠礼物的交易性质在下列人类学和社会学文献中早已形成共识,参见[法]马塞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余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版,第111页;Marcel Mauss,The Gift: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trans.W.D.Halls,London:Routledge,1999; Peters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New York:J.Wiley,1994.少数法学文献也有很精彩的讨论,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74页;以及Eric A.Posner,Law and Social Norm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50-55.(2000). ⑧并且,在受赠人回赠之前,赠与人会获得某种相对于赠与人的影响力。参见Robert B.Cialdini,Influence 34-35(1984).See,e.g.,Jon Elster,The Cement of Society:A Study of Social Order 111-14(1989); William Miller,Humiliation 115-52(1993). ⑨参见韩世远:《合同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431页;崔建远等:《债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0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0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1-662页;王利明等:《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30页。另外国外学者也广泛存在这种误解,例如George K.Gardner,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Contracts,46 Harv.L.Rev.1,7-8(1932). ⑩这种情形类似于“重大误解”,按传统合同法理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是可被变更或撤销的。参见《合同法》第54条。 (11)参见Guido Calabresi & Jon T.Hirschoff,Toward a Test for Strict Liability in Torts,81 Yale L.J.,Vol.,1060.(1972).波斯纳发现,关于“信赖损失”的责任分配,与侵权法的逻辑是一致的,参见Richard A.Posner,supra note 5,at 416. (12)否则,学者们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强制执行有利于受赠人,而不利于赠与人。例如唐明:《试论赠与合同的立法及司法实践》,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第68-69页。 (13)在英美法上,单边承诺不被视为交易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单边承诺都不能强制执行。例如,某个年轻人根据某个富人的承诺(为他提供完成大学学业经费)而决定放弃他的业余工作。尽管这里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交换,但法律仍将违背承诺看作违约。作为判决基础的假设是:“不利信赖(detrimental reliance)”也是一种对价。尽管只是一种假设,但它至今仍被采用。参见Richard A.Posner,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Little,Brown and Company,96(1992). (14)赠与合同的公证费,按收益额的2%收取,最低不低于200元。参见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司法部《关于调整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15)波斯纳就认为:“因而,从效率观点看,许多国家通过制定法废除以盖印方式使无偿承诺可强制执行的做法是个令人迷惑的进展。”参见Richard A.Posner,supra note 5,420. (16)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开始实施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将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费降至每件10元,这显然是个政治性的决定。 (17)关于这个主题的实证研究数量很多,例如,Stewart Macaulay,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A Preliminary Study,28 Am.Soc.Rev.1963; H.Laurence Ross,Settled Out of Court:The Social Process of Insurance Claims Adjustment,New York:Aldine Publishing Co.,(rev.ed.) 1980.; William L.F.Felstiner,Influen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on Dispute Process,9 Law & Society Review 1,Autumn,1974.另参见一个很有传统风格的理论研究,Dori Kimel,Neutrality,Autonomy,and Freedom of Contract,21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73(2001). (18)《合同法》第188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该条规定表明,赠与合同的主要救济方式是强制执行赠与承诺,而非赔偿损失。 (19)大陆合同纠纷中大量属于欠款纠纷,司法实践中常把欠款纠纷从合同纠纷中单列出来。除欠款纠纷以外的合同纠纷,法院一般不会强制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而是判决违约方赔偿违约损失。 (20)哈耶克认为,我们对许多制度性知识(包括绝大多数伦理规范和法律)是“知其然(know that)”而不“知其所以然(know how)”,我们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识到他们,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相适应,但却对这些知识的发生原因和一般效用茫然无知。哈耶克的这种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实际上,这一思想是其自由主义立场的基础。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2页。标签:法律论文; 契约法论文; 赠与合同论文; 赠与公证论文; 强制执行公证论文; 公证论文; 民法论文; 诉讼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