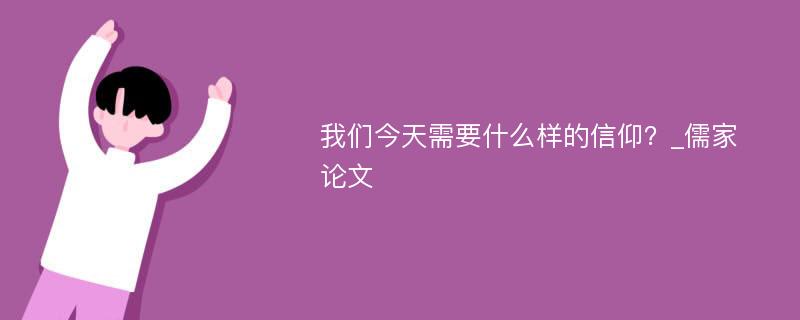
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信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要什么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第8期《上海文化》发表了潘知常教授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上篇),在近几年国内讨论信仰问题的文章中,该文令人耳目一新,它将信仰问题与“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联系起来,把信仰之有无视为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视角颇为独特。在潘知常教授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信仰的维度,真正的信仰是由基督教来代表或由基督教所孕育的,为此,该文用了大量文字分析了基督教所孕育的真正的信仰。一般而论,对于潘文呼吁中国人要“信仰起来”这个诉求,笔者并无异议,非但无异议,而且认为这是今天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但中国人要如何信仰起来呢?潘文出示的途径,乃是“重新回到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只要能够从后期儒家、后期道家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并且再次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出发,去加以创造性的转换,就不难走出‘信仰困局’。”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按照潘文的逻辑,如果中国从来并无真正的信仰,而西方基督教才代表了或孕育了真正的信仰,那么引进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回到儒、道,这才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潘知常教授“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取向,在思路上与整篇文章是矛盾的,而且此一取向恐怕也未能使中国走出“信仰困局”。本文以潘文为引线,浅谈“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仰”,以就教于潘教授及学界方家。 一、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信仰?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似乎是当今学界的一个共识。前几年中国曾流行一句话:“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就是信仰金钱。”这是“寓沉痛于悠闲”,是无奈的调侃,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中国人根本没有信仰。为什么信仰金钱并不是信仰?有一种观点认为,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据此,信仰金钱也是一种信仰。改革开放以来,不是有很多中国人“以宗教家的热忱”去追求金钱吗?法国哲学家阿兰说:“金钱和别的好处一样,必须对它忠贞不渝才能得到它。”①这里的“忠贞不渝”岂非正是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可以有这些辩解,我们仍然断定信仰金钱不是信仰,这就像以色列人崇拜金牛犊不是信仰一样。崇拜金牛犊,是偶像崇拜,也是迷信。信仰不是迷信,而是正信。迷信与正信的区别,显然跟信仰的对象有关,由信仰的对象决定。崇拜金牛犊不是信仰,崇拜上帝就是信仰。可见“信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信什么”的“什么”,未必便是金钱、金牛犊之类实体性的对象,它也可以是一种精神向度,一种意识指向性。这种指向性基本上有两大类:指向现实和指向超现实。对金钱、权力的信仰,充其量是实用信仰,它并没有超越现实。日常生活中的信念如相信“太阳照常升起”,实用信仰如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种种迷信,这些中国人都有,但这些都只是现实关怀。真正的信仰是终极关怀,其根本标志是超越性。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信仰,那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终极关怀。 中国人没有真信仰,这是一个全称判断。根据这一判断,原始儒家也是没有真信仰的。这个观点需要加以论证。1947年,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中指出:“中国人素缺乏高尚的宗教生活。”②1949年,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断言,中国文化的“两大古怪点”之一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中国文化内宗教之缺乏,中国人之远于宗教,自来为许多学者所同看到的”。③并明确指出,孔子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以道德代宗教”。自梁漱溟和贺麟以来,学界大多认可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教。但从中国没有宗教的事实,不能推断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结论。宗教信仰是信仰的原初形态,也是信仰的主要形式,然而宗教信仰并不是信仰的全部。在宗教之外,仍有信仰。因此,尽管中国“几乎没有宗教”,但仍然可以有信仰。例如宋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看到这四句话,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儒家也有某种信仰。 然而严格地说,“横渠四句”仍然不是真信仰。理由有二。首先,“横渠四句”具有虚妄性。这是说它大而无当,华而不实。人不是造物主,不可能“为天地立心”。人也不是救世主,不能侈谈“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口气也大得离谱,跟秦始皇似的。纵然是秦始皇,也只是希望万世保有权势,并不曾为万世开太平。现在如能开数十年的太平,就已是不折不扣的伟人了。至于“为往圣继绝学”,虽然也狂妄,但毕竟不全是夸夸其谈,不是飘在空中的无根的浮云。“为往圣继绝学”,大致就是传承文化,传承学术。然而儒家“为往圣继绝学”,隐含着把“往圣之学”等同于终极真理的意思。事实上,“往圣之学”可能早已不合时宜,也可能谬误百出;“为往圣继绝学”,很可能是抱残守缺。把“往圣之学”当作终极真理,也就是崇拜以往的圣人,这也不能算是真信仰。因为,(1)在中国文化中,“圣人”的宗教意味少、政治意味多。君王几乎就是天然的圣人,如杜甫诗句“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非君王的圣人,也往往是后世帝王追封的。(2)在中国文化中,推崇“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这种文化信念不仅缺乏谦卑,还使得圣人缺乏超越的维度。 其次,“横渠四句”缺乏超越性。这表现在它囿于现实之域。“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不过是一种政治诉求。所谓“往圣之学”,也就是早期儒家的学问,其核心是“经世济民”之学,是伦理与政治合一的学问,因此,“为往圣继绝学”与“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是同一层次的追求。“横渠四句”中唯一看似有超越性的是“为天地立心”。对“天”的信仰,近乎宗教信仰。但是,(1)儒家的“天”不是西方的“上帝”;(2)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天人合一”,“天”要么体现于君,要么体现于民。君是“天子”,代天立言,所以儒家对天的信仰,往往转变为对君的信仰,如杜甫“每饭不忘君”。就连颇有道家气质的李白,也曾写过:“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张炜指出:“中国人没有‘上帝’的概念,常常以一国之君替代。皇帝被看成是上天派来管理地上事务的,于是也叫‘天子’……所以李白、杜甫心系皇帝和朝廷,有一部分当是‘代信仰’的意识在起作用。”④然而张炜并没有指出,“代信仰”并不是真信仰,因为“君”不过是政治人物,而非超越之在。而对君而言,“天”又体现于“民”,此即《尚书》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总之,“为天地立心”,究其实仍不过是“经世济民”的政治伦理关怀。 宋儒如此,原始儒家亦然。原始儒家有一种类宗教的行为,即祭天祀祖。祭天祀祖只是类宗教的行为,其行为中也不包含真信仰。孔子早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⑤一个“如”字,道出了并非真信仰的实质。儒家提倡“慎终追远”。慎重地办理丧事,虔诚地祭祀祖先,儒家以为这就是“终极关怀”了。事实上,“慎终追远”与其说是终极关怀,不如说只是实用原则,甚至只是一种统治术。曾子已然一语道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⑥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到“以孝治天下”,不过一步之遥。显然,较之道家,先秦儒家比较缺乏终极识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⑦这是出自亲传弟子的证言,说明孔子思想的确缺乏终极关怀之维。曾有不少学者为孔子辩护:不说,不等于不懂。然而正如一个艺术家只能将自己表现于作品中,一个思想家除了自己所说出的东西,还剩什么呢?反之,老子明明承认“道可道,非常道”、⑧“知者不言,言者不知”,⑨可是仍然坚持说了“五千言”。此无他,不过是因老子“有话可说”。正是由于有了“道”这一终极识度,老子才可以充满自信地批判儒家的仁义,批判仁义的非终极,不彻底,无根基。 那么原始道家能否突破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恐怕也不能。不错,老子的“道”,是终极关怀的产物,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然而老子之道,并不纯粹,形而上的维度固然有之,形而下的维度也颇为突出,它与“人君南面之术”糅合在一起、与“欲擒故纵”等权谋术掺杂在一起,穷到究竟,与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诉求并没有根本差别,而与基督教“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大相径庭。庄子之道,较老子纯粹些,不过庄子的思想取向,只能说是“超脱”,不能说是“超越”。闻一多认为庄子有宗教精神,他写过一篇《道教的精神》,认定老庄思想的前身是“古道教”,此“古道教”是相对于东汉以来的“新道教”而言的。闻一多指出:“后世的新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但真正接近道教的宗教精神的还是庄子。《庄子》书里实在充满了神秘的思想,这种思想很明显的是一种古宗教的反影。”“我们现在也可就宗教思想的立场,说庄子的神秘色彩最重,与宗教最接近,老子次之,杨朱最切近现实,离宗教也最远。”⑩此说别出心裁,不过有些牵强。牵强者有四:(1)较之道家,注重祭祀和礼仪的儒家,与“古宗教”的连续性更为明显。(2)所谓“古道教”既然以“道”为名,则说明“道”的地位已极为崇高,而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这是不可能的。(3)《庄子》一书固然如闻一多所说,颇有神秘色彩,但在我们看来,“神秘”不过是难以言说或不可言说罢了,就此而言,神秘未必通向宗教。艺术经验是神秘的,爱情也是神秘的,日常生活经验都有几分神秘性。《庄子》之所以富有神秘气息,那是由于庄子的哲学之思触及“前语言”的领域,而这种“前语言”的经验,与其说是宗教经验,不如说是艺术经验。(4)我们知道,宗教赖于信仰,哲学崇尚怀疑,而庄子正是中国哲学史上怀疑主义的宗师。庄子几乎怀疑一切。他怀疑以往的“圣人之言”、“先王之道”,怀疑流俗的价值观,怀疑道德(仁义),怀疑知识,怀疑理性,怀疑语言,甚至怀疑“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11)怀疑精神使庄子有一种远离政治和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的超脱,却未能使庄子拥有超越性的信仰。庄子的处世格言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12)没有超自然、超世俗的精神向度,不可能有真信仰。 中国文化还有一个构成因素,就是佛教文化。佛教本来是印度的宗教,自汉末“白马东来”,佛教在数百年间不断输入中国。有一部海外汉学名著《佛教征服中国》,描述了佛教输入中国的过程,其实事情应当反过来说:“中国征服佛教。”在中国扎根下来的佛教,深受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之影响,已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迥异于印度佛教。举例来说,佛教徒是出家人,“沙门不敬王者”,本来理所当然,但在东晋时期,净土宗的慧远大师就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13)佛教和儒学既然“殊途同归”,此后佛教也逐渐公开标榜儒家的忠、孝了。到了唐朝,佛教已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而这也意味着佛教的完全世俗化。唐朝有“终南捷径”的说法,这是借道家隐士的身份接近朝廷,寻求升官发财;唐朝还有“选官何如选佛”的说法,也是以佛教和尚作为进身之阶,寻求升官发财。史铁生的以下说法,是对今天佛教世俗化的经典描绘: 中国信佛的潮流里,似总有官的影子笼罩。求佛拜佛者,常抱一个极实惠的请求。求儿子,求房子,求票子,求文凭,求户口,求福寿双全……所求之事大抵都是官的职权所辖,大抵都是求官而不得理会,便跑来庙中烧香叩首。佛于这潮流里,那意思无非一个万能的大官,且不见得就是清官,徇私枉法乃至杀人越货者竟也去烧香许物,求佛保佑不致东窗事发抑或锒铛入狱。若去香火浓烈的地方做一次统计,保险:因为灵魂不安而去反省的、因为信心不足而去求教的、因为理想认同而去礼拜的,难得有几个。 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神位,历来少为人的心魂而设置,多是为君的权威而筹谋。(14) 于是我们可以断言,我们曾经有过的儒、道、释,都不曾给中国人提供真信仰。中国的佛教已经“堕落”了,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回到原始佛教?看来不行。原始佛教产生于印度,但在今天的印度,佛教已经式微。佛教早已搬了家,目前主要流行于东南亚一带。但我们显然不必引进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国的佛教,因为我们历来认为,中国的佛教更高明。我们也不能引进日本的佛教,因为日本的佛教本来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在20世纪,我们有过一段向日本学习的历程,但我们学习的并不是日本佛教,而是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文化。那么,我们能否复兴保留在中国的佛教?此路也不通。因为佛教早已被充分吸收,消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国文化有儒、释、道三家,既然无法复兴佛教重振信仰,如此,我们仅有的选择,似乎就是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了。但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并没有提供真信仰,就算我们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也还是走不出“信仰困境”。 然而我们更应该问一个问题:能否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答案当然是回不去了。试以儒家为例,从学理的角度看,按照诠释学,一切历史都是效果史。宋明理学虽然号称“新儒学”,但它不过是将儒家思想中的固有因素或潜在因素显现出来,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原始儒家的新事物。宋明理学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内在发展。于是,有没有一个全然独立于后期儒家的“原始儒家”便成了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由于儒家思想缺乏超越性维度,它始终与现实捆绑在一起。往大里说,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农业社会捆绑在一起,而今天已经是商业社会、工业社会,有着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的运作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往小处说,儒家思想与古代中国特有的乡土社会、家族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代,“家”并不是像今天城市里的三口之家那样的家庭,而是如曹雪芹《红楼梦》和巴金《家》中所描写的家族,“家”与“国”是同构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唯其如此,古代儒家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君王才能呼吁“以孝治天下”。这样的家族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已不复存在。显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孝治天下”之类的儒家基本信念,如今已经没有着落。总之,儒家思想彻底丧失了现实基础。儒家思想中的个别观点放在今天可能仍有价值,但儒家思想在总体上已成为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亚当与夏娃一旦离开伊甸园,就没有了归路,只要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我们便不可能再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去了。 二、我们能否引进基督教信仰? 如果不能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如果中国佛教也不能提供真信仰,那么为了走出“信仰困局”,我们似乎只能引进基督教信仰了。但我们能否引进基督教信仰?这是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正如我们无法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我们也难以直接引进基督教信仰。或者更严谨地说,引进基督教是可能的,引进基督教信仰则是困难的。 基督教被视为普世的宗教,在普世性方面,能与之一较短长的,似乎只有佛教。佛教和基督教都颇有向全世界扩散的趋势,而基督教传播的范围似乎更广些。基督教传入中国,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事实上,早在唐朝,基督教就已正式传入中国,在中国活跃了两百多年才偃旗息鼓。基督教第二次向中国传播是在元朝。第三次传播是在清朝,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下半叶,传播者是以利玛窦为首领的天主教耶稣会信徒。19世纪初,新教传入中国,《新约》也被译为中文。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已然数量不菲。然而综观中国历史,较之佛教,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肌体上打下的烙印可谓若有若无。文化集中地体现于语言,如今汉语中充斥着大量源于佛教的词汇,以至于有人模仿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强调“离开佛教,中国人就不会说话了”。相比之下,基督教的词汇极少甚至几乎没有进入汉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基督教式的叙事也微乎其微,仅有20世纪的许地山、史铁生等寥寥“二三子”,好似空谷足音。如果一种宗教不曾渗透进某种文化的语言,那么可以说,宗教与文化还是相互外在的。因此,正如“佛教征服中国”并没有为中国人带来真信仰,基督教多次在中国传播,基督徒遍布中国,也并没有改变中国“几乎没有宗教”的状况。这里的“几乎没有宗教”,并不是说中国几乎没有基督教的形式,如教堂、信众,而是说,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基督教精神所在,就是信仰。林语堂即是佳例。林语堂是个基督徒,写过自传《信仰之旅》(又译为《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然而我们阅读林语堂的著作,发现与其说他是个基督徒,不如说他是个孔子信徒。 一方面,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在原则上,我们可以直接引进基督教信仰,这正如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一样;但另一方面,宗教与科学又有所不同,宗教的普遍性迥异于科学的普遍性。科学放诸四海而皆准,宗教未必如此。世上并不存在美国的物理学、德国的化学之类的东西,但确实有美国的宗教、德国的宗教之类的东西。比较而言,科学是文明的代表,宗教是文化的形态。宗教是一种文化形式,而文化总有地域性、特殊性。在1000年前,生在中国的人,自然而然地便会亲近佛教,而生在欧洲的人,自然而然地便会信仰基督教。中国也有基督徒,但如果没有环境和家庭的长期熏陶,一个中国人不太可能自动地成为基督徒。林语堂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因此罗素说:“真正使人信仰上帝的根本不是什么理智的论点。大多数人之所以信仰上帝,是因为从小就受到这种信仰的熏陶,这才是主要的原因。”(15)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可想而知,数千年在儒、释、道文化氛围中浸染的中国人,很难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理论上,基督教信仰具有普适性,实际上,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信仰总是会发生变形。林语堂说:“虽然我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牧师,但这绝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家。”(16)这说明林语堂之父信仰的基督教,已是儒家化了的基督教。林语堂之父如此,林语堂自己亦然。 日本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本文化大体上可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我们不妨通过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变形,来推测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日本文化精神与基督教精神也是冲突的。梅原猛指出:“日本的基督徒很少。为什么基督教在日本没有扎下根呢?可以说,这是由于佛教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日本人的精神深处。”(17)日本作家远藤周作曾在《日本人的宗教意识》一文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从小是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懂事以后,我对一件事开始感到迷惑不解,那就是主张一个神的基督教,为什么能被认为大山、森林及其他各处均有神存在即多神的、泛神的日本人所宽容地接受、信仰、理解呢?”他经过长期思考,得出的答案是: “他们信奉的并不是基督教,可以说是变形了的基督教。他们信奉的基督教,是民俗的、土著的宗教。在那里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成分,如佛教、神道教一类的东西,简直如同大杂烩一样,统统被加在一起。”(18) 远藤周作有一部小说名作《沉默》,以17世纪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失败历程为题材,小说借天主教神甫之口说道:“在这个国家,你和我们的宗教终究无法生根。”“这个国家的人那时候信奉的并不是我们的神,而是他们的神。在好长、好长的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实,误以为日本人变成了天主教徒。”“圣·沙勿略神甫所教的上帝,日本人任意把它改变成大日的信仰。对崇拜太阳的日本人来说,上帝和大日的发音几乎一样。”“基督教的神,在日本人心中,不知何时已丧失了神的实体。”“日本人并未具备思考和人类完全隔绝的神的能力。日本人也没有思考超越人类存在的神的能力。”“天主教之所以灭亡,并不是你们认为的是因为受到禁止或迫害的缘故,这个国家存在着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天主教的某种东西。”(19)这些话道尽了基督教在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基督教在日本的失败,根源于文化冲突。由于文化冲突,自16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入日本以来,就多次遭到排斥、禁止、压迫。时至今日,基督教总算在日本取得了一席之地,似乎站稳了脚跟,但仍远不如佛教那般“深入人心”。日本如此,中国大致也是如此。 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如蔡元培、胡适等人,竭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从而导致了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胡适说:“基督教信仰的宣传,在这个新中国看来是不会被许可而有多少光明前途的。恰恰相反,基督教到处都面临反对。基督教占领中国之梦看来很快就破灭了——可能是永远破灭了,这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解释了。”(20)胡适用以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工具,乃是老子和孔子开创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传统”。这个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传统,与基督教是难以共存的。其表现有二:(1)中国文化不可能接受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原罪观念说明人的先天的欠缺、不完善,以此反衬了神的完全。由于基督教的缘故,西方文化甚至被称为“罪感文化”。但中国文化无论是儒还是道都与原罪观念格格不入。按照老子和庄子的倾向,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而自然是无所谓善恶的;不仅如此,自然本身是值得肯定的,生命并不是罪过。按照孔子和孟子的倾向,“人之初,性本善”。有些学者把儒家的性善论解读为“性向善”,性之向善,犹如水之就下。但无论是“性本善”还是“性向善”,都倾向于先天的善,而非先天的“恶”或“罪”。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原罪观念显然毫无立锥之地。(2)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一开始便将上帝的观念排除在外了。从此以后,中国文化中和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上帝的身影。中国的人本主义和欧洲的人本主义不同,欧洲人本主义认为,上帝在根本上不过是人的对象化,如费尔巴哈所言:“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所以,对象所加于他的威力,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的威力。”(21)但上帝作为人的本质的绝对化,是一个超越的存在,并不能被消融于人自身,于是,欧洲人本主义仍有可能保留上帝的观念。 但我们之所以难以直接引进基督教信仰,其原因不只是中国文化,还在基督教自身。或者说,还有欧洲文化自身的原因。自文艺复兴以来,发生在欧洲的一件划时代大事就是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每前进一步,基督教就后退一步。主要是由于科学的兴起,导致了欧洲自身的一场“反对基督教的现代运动”(鲁道夫·欧肯语)。到了19世纪末,这场运动以尼采“上帝死了”的论调而画上句号。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中,科学也是中国学者采取的有力武器,蔡元培在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中说: 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见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此则一种历史上之习惯。譬如前清时代之袍褂,在民国本不适用,然因其存积甚多,毁之可惜,则定为乙种礼服而沿用之,未尝不可。又如祝寿、会葬之仪,在学理上了无价值,然戚友中既以请帖、讣闻相招,势不能不循例参加,藉通情愫。欧人之沿习宗教仪式,亦犹是耳。 所可怪者,我中国既无欧人此种特别之习惯,乃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讨论。(22) 蔡元培的这个说法,源自对19世纪欧洲思想状况的观察。根据他的判断,基督教在欧洲已经衰败了,导致衰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科学。但蔡元培不说“以科学代宗教”,而说“以美育代宗教”,这是由于在他看来,基督教和美育都跟人的情感相关。欧洲思想史上可以追溯至康德、席勒并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的审美主义运动,似乎在学理上证明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如蔡元培和胡适,并没有看到一个事实:尽管早期的宗教也对自然说三道四,但总的来说,宗教与科学属于不同的领域:科学探索自然,宗教安顿人生;科学处理事实,宗教关注价值。以科学反对宗教真理是肤浅的、常常是“错位”的,反之,以科学证明宗教真理也是无效的。蔡元培们也没有发现20世纪欧洲的新动向:在20世纪初,欧洲又掀起了“基督教复兴运动”。哲学家罗素写了一篇《宗教能否解除我们的困惑》,就是针对基督教复兴运动的。尽管罗素认为基督教不能解除我们的困惑,但他比蔡元培和胡适更为睿智之处,表现在他并不处理宗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是处理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个人认为道德并不像宗教徒信仰的那样仅仅依赖宗教。”(23)且不论罗素的观点是否正确,他的文章至少从否定的方面表明,基督教仍然在文化中保有一席之地,并没有在科学的进攻下一蹶不振。 尽管如此,基督教自身确实存在着坚硬的内核,与现代思想构成难以调和的冲突。这个内核有两瓣:(1)一神论;(2)柏拉图主义。一神论被视为高级宗教的标志。基督教的一神论在哲学上表现为“只有一个真理”。然而,“真理只有一个”的传统思想,大约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被西方思想所抛弃,真理的多元论顺时应势,取而代之。威廉·詹姆士的《多元的宇宙》,可视为现代哲学趋于真理多元论的一个路标。基督教被尼采称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事实上,柏拉图主义为基督教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有两个表现:灵肉二分和两个世界。自尼采以来,西方思想家开足了火力,展开对柏拉图主义的猛烈批判,这场思想战争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世纪兴起的身体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其首要目标就是克服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现象学之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如今已被绝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只有一个世界,也就是生活世界,这是今天多数西方思想家的共识。据此看来,基督教确实与今天的思想状况格格不入。由于现代思想的发展,基督教神学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如在黑格尔哲学中那样),继续充当哲学王冠上的明珠。就此而言,基督教确实是衰颓了,但导致基督教衰颓的原因,与其说是自然科学,不如说是现代哲学。 三、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精神与基督教精神构成一定的冲突,现代思想的发展已然背弃了基督教思想,这是我们难以直接引进基督教信仰的两个主要原因。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无法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也难以直接引进基督教信仰,那么,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我们今天需要一种非宗教的信仰。前面说过,宗教信仰只是信仰的主要形式,在古代社会,也许曾是唯一形式,但历史发展到今天,信仰的形式已经多样化了。例如,贺麟在《信仰与生活》中,就把信仰区分为三类:(1)“宗教的或道德的信仰”;(2)“传统的信仰”,如“对于社会的权威和礼教、民族文化的信仰”,前文提到的“横渠四句”中的“为往圣继绝学”,大概也属于贺麟所说的“传统的信仰”;(3)实用的信仰”,如政治军事的信仰,相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即是政治军事上的信仰。(24)在这三类信仰中,传统的信仰和实用的信仰显然并不是本文所说的真信仰。但无论如何,贺麟的说法表明在宗教信仰之外,仍然可以有某些信仰形式。而且我们可以尝试在宗教信仰之外,探索某种真信仰。在当今世界,最具有普世性、最足以代表真信仰的,应当说还是基督教信仰。因此我们需要的信仰,只能从基督教中提取。但我们提取出来的信仰,必须是非宗教的信仰。具体地说,是一种无上帝的信仰。 “非宗教的信仰”有很多优势。我们知道,一旦拥有了某种宗教信仰,也便意味着接受了某种具体的宗教教义、某些具体的宗教实践形式,但接受同时也是束缚,信仰同时也是枷锁。在历史上,宗教与宗教之间始终纷争不断,宗教战争与宗教迫害此起彼伏。即便在世界各大宗教呼吁对话的今天,不同的宗教仍然有不少的龃龉。例如,中国的佛教徒常爱比较佛教与基督教哪一个更“究竟”,答案自然是“佛教更究竟”,这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想法。若是非宗教的信仰,就不存在这样的纷争。“无上帝的信仰”也并不可怕。在基督徒看来,不信上帝根本不是宗教信仰,但我们知道,佛教信仰从来就是一种无上帝的信仰。按照佛教,只要一个人接受了“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他就是佛教徒了。以“三法印”作为佛法的底线,实际上是以某种认识或理论作为是否信仰的尺度,换言之,佛教徒信仰的不是神,甚至不是佛,而是智慧,或曰真理。佛教因而被视为无神论的宗教。如果说基督徒的目标是赢得永生,那么佛教徒的目标就是获得智慧。不过,佛教固然可以是无神论的宗教,而从基督教信仰中提取出来的信仰,可能是“无上帝的信仰”吗? 在基督徒看来,上帝存在是信仰的第一前提。因此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康德之后,这种证明已经很少见了。而在今天,我们已经领悟,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根本毫无必要。这不仅是由于信仰并非理智方面的事,而且是由于上帝已经不被需要了。但这也不是拉普拉斯意义上的不需要。拉普拉斯将《天体力学》献给拿破仑,拿破仑发现其中并没有提及上帝,问他为什么,拉普拉斯答曰:“陛下,我们不需要那个假设!”拉普拉斯用机械论解释自然,在机械论的解释体系中,并没有上帝的立足之地。但我们这里说的不需要上帝,并不是对自然的说明,而是对《新约》的解读。事实上,在《新约》中就已经有了诸多“不需要上帝”的表示,只是由于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的强大影响,使得很少有基督徒领会其中的奥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25)传统基督徒常常把这句话理解为,耶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然而,中介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耶稣本身已是道(路)、真理、生命了,我们不需要越过耶稣,通向别处。所以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26)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与人的合一。耶稣就是上帝。既然如此,我们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在耶稣之外再设定一个上帝了。换言之,我们已经不需要那种实在论的上帝了。上帝体现在耶稣身上,犹如天国就在你的心中: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27) 天国或神的国,也不是一个实在论的概念。天国并不是一个地方,并不是基督徒死后才能到达的某个世界,恰似上帝并不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我们看到,基督教的教义中固然存在着与现代思想对立的成分,但它也潜藏着与现代思想可以契合的因素。将神性与人性合而为一,就是这样的重要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我们就可以在尘世中看见神圣,在人间实现天国,恰如耶稣的祷告词:“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28)有了这个思想,我们就有可能克服传统基督教的两个世界的观念,清除其柏拉图主义的痕迹。 上帝不存在了,柏拉图主义也被清除了,基督教信仰就被转变为我们需要的非宗教的信仰。当然,以上只是本文从《新约》中引申出来的看法。基督徒想必会说,虽然《旧约》被《新约》取代,但上帝并没有被废弃或取代。《新约》并没有提供“无上帝的信仰”,只是改变了上帝的性情和属性,让基督教的普适度大大提高。再则,《新约》的大部分可能有统合两个世界的意思,但《新约》中仍残留有两个世界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必须离开耶稣,才能真正抛弃上帝。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上帝或是耶稣,都不过是真理的象征罢了。非宗教的信仰和无上帝的信仰,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耶稣。我们需要的信仰,不是对上帝的信仰,也不是对耶稣的信仰,而是对真理的信仰。不过,这真理却是耶稣提示出来的。这真理必定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因为科学意义的真理是认识的对象,而且科学真理具有相对性,会过时,会被推翻。作为信仰对象的真理乃是终极真理。耶稣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29)可见,爱,就是终极真理。罗素指出:“基督教有三个构成要素,如果可能我们最好保留住它们,那是崇拜、顺从和爱。崇拜是基督教给予上帝的;顺从是给予一切不可避免的事物,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爱是赋予同胞的,也可以给敌人,事实上是针对全人类的。”(30)这三个构成要素中,前两个都与上帝相关,只有第三个要素爱,并不涉及上帝。当然我们可以说,爱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但这个作为爱的上帝,显然不是基督徒所想象的居于天国,手握权杖发号施令的耶和华了。以爱为对象的信仰,可以是一种非宗教的信仰、无上帝的信仰。 爱也有形形色色。C.S.路易斯写过一本《四种爱》,提到物爱、情爱、友爱、爱情、仁爱诸种爱;弗罗姆在《爱的艺术》中,也提到博爱、母爱、性爱、自爱、神爱诸种爱。但无论是哪一种爱,都须以自由为前提。不自由的爱不是爱。传统儒家的“父慈子孝”,往往出自礼制的硬性规定,并不是出自自由。如果爱并非源于自由意志,缺乏自发性,那它便缺乏生动性,也缺乏持久性;爱会沦为抽象的责任或义务,最终导致爱的消亡。自由是通向真爱的通衢大道,也是爱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正如耶稣是通向上帝的道路,但他本身也代表上帝。自由也是终极价值。举例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科学和民主都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东西,但它们也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就连现代新儒家,也希望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纳入孔孟之道,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中体西用”。但是学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引进并不成功。经过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科学和民主还是没能在中国扎下根来。我们并没有学得真正的科学精神,只是模仿了西方的各种科学技术。我们也没有让民主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生根发芽。这是什么缘故?穷到究竟,无非是忽视了自由。科学和民主是自由的左膀右臂,不能将它们任意地切割下来,嫁接到孔孟之道的躯体上。科学的前提是自由思考、自由探索;而民主不过是自由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实现。科学和民主的依据都是自由。“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31)因此,哪怕只是为了学到科学和民主的精髓,哪怕只是为了让科学和民主深入人心,我们也得召唤自由之降临。而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以自由为信仰,视自由为生命,为自由而奋斗。在西方,自由意志的概念,虽说是斯多葛派率先发现的,但它在基督教中才得以成熟。因此,正如我们可以从基督教提取爱,我们也可以从基督教提取自由。 总之,我们今天需要的信仰,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爱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它是非宗教的信仰,是无上帝的信仰,但它是从基督教信仰中提取或抽绎出来的信仰。在基督教信仰中,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说,而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也不妨说是真理、爱、自由的三位一体。 注释: ①阿兰:《幸福散论》,施康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②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页。 ③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④张炜:《也说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9-30页。 ⑤《论语·八佾》。 ⑥《论语·学而》。 ⑦《论语·公冶长》。 ⑧《道德经》第一章。 ⑨《道德经》第五十六章。 ⑩闻一多:《历史动向:闻一多随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112页。 (11)《庄子·齐物论》。 (12)《庄子·天下》。 (13)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体极不兼应四》。 (14)史铁生:《活着的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13页。 (15)罗素:《宗教能否解除我们的困惑》,黄思源、卓翔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16)林语堂:《信仰之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17)梅原猛:《佛教十二讲》,雷慧英、卞立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94页。 (18)井上靖等:《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周世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19)远藤周作:《沉默》,林水福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第172-178页。 (20)转引自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56页。 (21)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页。 (22)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8页。 (23)罗素:《宗教能否解除我们的困惑》,第76页。 (24)参看贺麟:《文化与人生》,第96-100页。 (25)《约翰福音》14:6。 (26)《约翰福音》14:9。 (27)《路加福音》17:20。 (28)《马太福音》6:9。 (29)《约翰一书》4:16。 (30)罗素:《宗教能否解除我们的困惑》,第24页。 (31)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标签:儒家论文; 基督教论文; 国学论文; 佛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日本佛教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宗教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