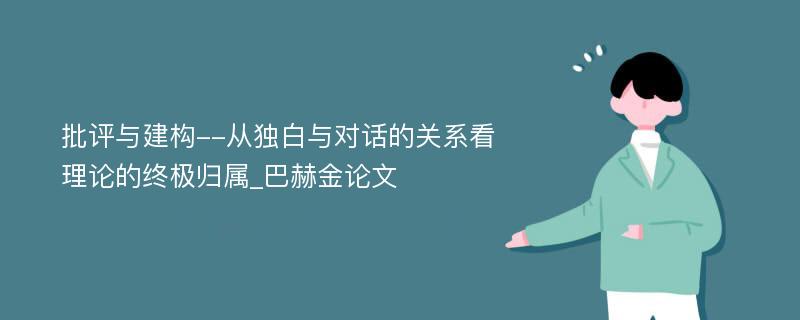
批评与建构——从独白与对话的关系谈理论的终极指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白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3)04-0049-06
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来,占据批评论坛的主要是欧陆理论,但是巴赫金的小说理论却 一直为各路理论所青睐,原因很明显,那就是因为巴赫金的独白、对话和狂欢这类概念 本身就是复调的,它们既是关乎文本技巧的概念,又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因此正如保罗 ·德·曼所说,它们对“众多的批评家可以、并且已经意味着众多不同的内容”。(注 :Paul de Man,The Resisitance to The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107.)而且正是作为后者,它们才具有一种理论的活力,超越了纯形式主义的范畴而 成为思想的模式,高度概括了文化哲学或文化批判所关怀的几种话语形态以及它们之间 的关系,也体现了理论话语的基本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都是元理论概念。
一
从以上角度来理解,所谓独白就是一种对世界的“原则性态度”,按巴赫金的说法, “任何一种原则性的态度都具有创造的、积极的性质。”(注:《巴赫金文论选》,佟 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46页。)因此独白不仅是一种叙事意义上的超 视和越位,更是一种观念上的整合和建构。对于有着救赎理想的早期巴赫金来说,这种 原则性态度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因此前期的巴赫金推崇托尔斯泰那样围绕 自己的理念塑造角色的作家;在后期的巴赫金理论中,这种原则性态度似乎让位于一种 多元化意识,独白精神似乎被对话精神所否定。所谓对话(或复调和多声部),即一种多 元话语空间,在此不存在一个把他者对象化、把对象的精神存在归化在自己的观念范围 内、使之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的绝对主体,而是其中每一个人都是主体,每一个他者 都是一个我,而每一个我都考虑和参照他者的面孔和凝视来定位自己。他者意识是对话 原则的精神实质。任何代言、解释或说明都被看作是独断或思想暴力。
于是乎,独白与对话作为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把巴氏的思想体系分成互相矛盾的两个 阶段,但是如果把巴赫金首先是“人文学科中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然后才是“20世 纪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这一点与独白和对话理论所针对的历史背景做综合考虑,就会 认识到前期的他是以一个有着宗教救赎情结的文化哲人的视角,借文学批评来言说人对 世界的责任,因此必然强调归化、统一,这可以说是俄国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使然 ;而后期的他则是在前苏联30年代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作为一个受迫害的思想者, 从反对独断、一言堂、压制的立场而把自己的情怀隐藏在对小说样式的描绘中,因此必 然把文学语言阐释为一个可以充分释放欲望与压抑、允许多元化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尽情 嬉戏、狂欢的自由空间,以此来呼吁和倡导自由、民主、多元。在此,小说批评理论同 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寓言,复调的、多声部的特征不仅被用来界定小说的完美形 式,也在某种意义上被用来代表多元化的文化生态,与专断和统治相对立,因为多元意 味着未完成和变化,因此蕴涵着生命与活力,而专断和统治则总是已定型和已完成的, 因此是死亡与物化。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后期的理论只是从反题的层面表达了同样的社 会责任意识,这同样是一种“原则性态度”,因此可以说是以对话的面貌而呈现出来的 独白。
这表现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其实并不是在“客观”描绘一种文本样式,同时也在阐发 一种批判精神。细读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会发现他所阐释出来的陀思妥 耶夫斯基几乎就是一个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历了解构主义洗礼的文化批判者,首先他的 主人公就不同于一般小说,不是具有固定性格特征的角色,而是思想和意识,作家如同 一个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在一个平面共时的体系中考察各个意识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又 如同一个知识考古学家,把各个意识与不同背景的角色相关联。思想在他的小说中并不 是用来刻画人物,给小说以思想性,而是思想本身就是被描绘的对象,小说所表现的不 是日常情景,不是城市乡村,甚至也不是人物,而是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最具批 判(对话或他者或解构)意义的是,所有这些争奇斗艳的思想形态并不是一个统一精神的 不同阶段,也不构成黑格尔意义上的正题、反题、合题。事实上,在陀氏的小说中不但 没有整体、合题,而且没有历时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在每一部小说中出现的,都 是没有被辩证地消除的众多意识的相持”,(注:《巴赫金文论选》,第31页。)它们是 平面上的星丛,只有空间共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没有时间先后和主客区分的关系,这 是“一个个营垒,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不是个人的道路(升降沉浮),而是社会的状况。 社会现实的多面性和矛盾性是作为时代的客观事实出现的”。(注:《巴赫金文论选》 ,第33页。)对于巴赫金所理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研究一个世界,就意味着把 这个世界的一切内容都作为同时性的东西加以思考,识破其同一个时间横断面上的相互 关系”,(注:《巴赫金文论选》,第35页。)而不是张扬一方,贬抑另一方。有意味的 是,巴赫金也用“事件”这一概念来指称互相对比和对立的意识,正如索绪尔用“事件 ”指称语言中的言语一样。但是,在巴氏所阐释的陀氏小说中,没有语言,只有言语, 即没有大一统的结构和规范,只有独立自主的行为,它们“作为并列或对立的东西,作 为共鸣而又互不融合或绝对矛盾的东西,作为众多互不融合的声音的永恒的和谐,或这 些声音之间永无休止、永无结果的争论,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注:《巴赫金文论 选》,第37页。)对话精神从这一层面来看,完全如同强调非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 或否定大一统结构观的解构主义哲学。
这种对多样性、多元化的追求在巴赫金对拉伯雷的《巨人传》的解读中,被更为激进 的狂欢化概念所包容和延展,这后一概念不仅更具文化政治色彩,而且同时表明批判的 目的是救赎。在此对对话和共存的追求是通过狂欢与复调,即颠覆与瓦解来实现的,因 为对于身体的、下等的、边缘的、疯狂的话语来说,寻求共存的手段必然是颠覆原有秩 序,所以狂欢就是以“独特的逆向、反向和颠倒的逻辑”,“上下不断换位、面部和臀 部不断换位的逻辑”,用“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渎、打诨式的 加冕和废黜”,(注:《巴赫金文论选》,第104页。)来制造“人人共有、自由、平等 和富裕的乌托邦”(注:《巴赫金文论选》,第104页。)所带来的喜庆。用20世纪60年 代以后的文论术语来说,狂欢化是一种解构与建构的双向运作,正如巴赫金所说:“狂 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又有再生和更新。一般来说,民间文化完全没有单纯的否定 。”(注:《巴赫金文论选》,第106页。)它“既是埋葬,又是播种,置之死地,就是 为了更好更多地重新生育”。(注:《巴赫金文论选》,第119-120页。)这点又如同哈 贝马斯所界定的“拯救性批判”,(注:Jurgen Habermas,“Walter Benjamin:Consciousness-Raising or Rescuing Critique”,in Gray Smith,ed.,On Walter Benjamin(The MIT Press,1988),p.98.)在此,批评家一如一个本雅明式的深海采集珍 珠者,他深入下去,拆毁外壳,为的是拯救生命之精华。由此可见,对话或复调精神发 展到极致便是颠覆,而任何颠覆都是一种政治行为,都是为了清出场地,重新建构。对 此,本雅明在60多年前就有了共识,他说:“建设的前提就是拆毁。”(注:Andrew Benjamin & Peter Osborne,ed.,Walter Benjamin's Philosoph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x.)巴赫金则称这样的策略为“正反同体”。(注:《巴赫金 文论选》,第104页。)这使得真正的对话精神一如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既不是嬉戏 ,也不是技巧,而是一种立场,一种范式,它在抗拒独断、盲从、压制和暴力的同时, 也在催生完美的文化生态或社会秩序。正是从这个层面上,巴赫金的上述概念才能成为 元理论概念而被不断演绎和范化。
二
巴赫金理论的元理论性就在于它是一种最高品位的理论精神,它表明,对话和多元精 神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围着巴别塔的废墟而众说纷纭,而是为了重建这一通天计划, 但是动机已经不是取代上帝,而是在认识到人类的独断与专制所带来的灾难以后,寻求 重新与世界、与一切他者的和谐关系,所以归化与和解才是最终的目的,而这一追求也 正是20世纪以来被冠以“理论”的文学批评或文化批判的共同特征。这些“理论”要么 在政治上经历了革命与失败的体验,要么在思维范式上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洗礼, 因此无论是作为文学批评或是文化批判,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对意义、表征、身份 的重新定义或定位。这意味着它们首先是一种反思,是对那些常识性的、体制化的、从 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上被确立、因而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物的质疑,所以即便它们以 文学批评的面貌出现,其终点也是跨越疆界,进入文化阐释和文化批判,而不可能画地 为牢,停留在描绘文本上,而且无论这类批评从哪个层面上介入,采取何种不同的姿态 ,呈现何种不同的走向,但在其终极层面上都具有“正反同体”的深层的通约性,即它 们都是试图“穿越废墟而寻找回归之路”(注:Walter Benjamin,Reflections(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78),p.302.)的哲学探险。综合来看,可将这样的 理论分成3种大的批评模式:解构、批判理论(或意识形态批判)和救赎(或拯救性)的批 评。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构批评在所有的文本中都发现了狂欢,这全得力于它那“哥 白尼革命”式的阅读方式,这是一种隐藏着政治学动机的、因此而独具犀利和锐气的“ 双重解读”,它将索绪尔在其共时语言学中提出的“在一个横向的体系中只有差异性, 而没有实证条件”的指意原则推向极致,因此在每个文本、每种指意体系中都能发现“ 矛盾和谐”,借此它向人展示,“国王”(结构)实际上全由“奴仆”(事件)制约和界定 ,因此全是幻象。整个意义的王国就是这些“奴仆”们的嬉戏。(注: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Alan Bass(London,Melbourne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p.278-294.)
因此首先被拆解的便是结构这个先在的概念本身。这一批评模式的始祖德里达指出, 一方面,结构主义认为意义来自于关系,即来自于系统内部成分之间的差异性,另一方 面又认为系统或结构是一切的根源,它先于事件而存在,通过统管体系中的所有成分而 保存自身的稳定不变,因此结构被构造为一个中心、一个宏大叙事、一种元语言。它既 在体系中,又高高在上于体系,在一个全由关系的相互制约构成的体系中,它本身却不 受结构原则的限制,而是主导整个体系的运行。它不可以被替代,它的意义也不产生于 差异,不需要参照体系中的其他成分来界定,而是先在的、形而上的、真理的、准则的 东西,总之,它不加入结构的运行而是限定这种运行并衍生事件或言语,作为中心,它 是一个超越体系的所指或意义的终极源泉。在德里达看来,这种矛盾的用意全在于建立 结构的专制性,使它以不变应万变,使得只有它是实质性的存在,而其构成成分则没有 自身的价值、质量或实在性。这首先表现为,体系内部的任何个体成分一旦脱离体系的 制约,便无法被界定,因而便被视为另类或无用之物;其次,个体成分永远受制于结构 原则,即差异关系的运作,其自身的实现永远在于被替代、被交换,因此只有悖论似的 存在状况;第三,个体不具备质疑体系的能力,更没有超越的可能,因为个体存在的本 身就是由体系界定出来的。由此似乎一个奴仆各就各位的井然秩序就确立了,但在德里 达看来,这是一种貌似的实在性和稳定性,按照“在体系中只有差异,没有实证条件” 这一原则,结构的本质在于它是自我封闭的,其指意的机制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 依靠“补充性逻辑”来运作。也就是说,一方总是以另一方为参照、或通过否定另一方 来界定自我,因此它就永远不可能是自身完整的在场,它必须依靠它的对立面才可以成 全自我,因此它竭力要排斥的他者实际上先在于它,并决定着它能否自我实现或存在,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本身变成了它要否定的他者的一个补充。因此中心或结构本身就 是事件,语言本身就是言语,言说本身就是书写。前者均由后者所界定,是后者的一个 案例,并不存在一个实证性的、完全在场的中心或结构,中心或结构与任何权力话语一 样,同样是一种建构,一种幻象,一种愚民的意识形态。
按照这种解读,顷刻间井然的秩序被打乱,稳定的意义被瓦解,如此被解读的文本完 全如同《巨人传》一般充满扭转乾坤,翻天覆地的狂欢。德里达用这种方法读卢梭、读 黑格尔、读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犹如一股势如破竹的威力,拆解了任何结构 的藩篱、语言的牢笼,使中心没有存在的可能。一切都在流动、漂浮、嬉戏,他不仅以 此解构了在他之前的哲学文本,也对他同时代的诸多哲学家和理论家的理论前提穷追不 舍,包括以批判和解构姿态出现在人文学科舞台上的大师们,如罗兰·巴特、拉康和福 柯,使得批评家海扎德·亚当斯称德里达为“解读了所有文本的最后一位哲学家”。( 注: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ed.,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Tallahasse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86),p.17.)但他自己却竭力回避使自己成为这“最 后”的偶像,否定自己在建构一门学科,而自称一种途径,一个方法,他所效仿的是能 够从任何束缚中脱身的魔法大师,以这种姿态提醒人们不断置疑,以便彻底结束用固定 的结构或先在的体系解释一切的强权。在德里达看来,任何强权体系为了保证其稳定性 ,都不允许意义的自由嬉戏或多元狂欢,更不可能自我质疑,因此必然走向僵化和独断 ,要求盲从和驯服,而解构,正如他在刚刚完成的关于他本人的记录片中所说,则是一 枚手榴弹,目的是炸开一切盲从、压抑、控制,所以批判与解构构成了思想家对社会的 伦理责任。而这种责任同时也就是一种立场、一种对世界的态度、一种坚定不移的关怀 ,最终目的是为了真正的和谐与自由。因此,解构向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发难,可 谓一种“实战演习”,为的是向一切自以为是的权威话语挑战,使人们从对任何真理话 语的盲目归顺转向对它的语言构成性的意识,从而保持思想的活力,以便维持健康良好 的社会生态。由此看来,解构的“双重解读”正如上下颠倒的狂欢式颠覆一样也蕴涵着 乌托邦的向往,它既不是80年代英美学界所推出来的“嬉戏”,更不是为了收获被拆解 的“巴别塔”的废墟,而是如同德里达在20世纪90年代和最近刚刚发表的一系列访谈中 所表明的那样,在解构中始终萦绕的同样是一个“马克思的幽灵”,(注:雅克·德里 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一种真正的对社会与人生的关怀,产生于解构的“嬉戏”作为一种策略,是 对解放之潜能的挖掘。
三
相比之下,批判理论则在一切文本中发现了对话,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发现了对对 话、对他者的压抑。这一模式的代表是法兰克福的批评家们,他们是亲身经历了法西斯 专制主义暴行的一代人,对于独断、专制的心理和认知机制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和更为 痛切的体验,所以他们将压迫、同化、独断同整个启蒙传统相联系而批判。如果从辩证 批判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模式,可以说,他们的理论能量都集中在反 题上,其揭批力度毫不亚于解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的最后章节中以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反面教训最为有力地证明,启蒙理性的堕落就在于把一切他者对象化 ,发展到极致,便是权力对一切他者的统治欲望,公平和正义就丧失了存在的基本伦理 环境,因此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灾难性的后果。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的非人 迫害就是这种启蒙精神的极限,这个极限的标志就是对最后的人文底线的践踏。理性之 所以表现为疯狂,文明之所以表现为野蛮,全是由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异化的过程 中,他者意识丧失殆尽的结果,人的思维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客观化或对象化模式,主体 完全以我为核心,把内部强加于外部,把主体强加于客体。这种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征 服和掠夺过程的思维范式,在社会中必然被用来对待一切非同一性的他者群体,而一切 群体的他者性都会使持上述思维模式的主体感到恐慌和危机,因此都会被加以同化和归 化,一切从宗教、文化、政治、经济、习俗等方面被先在的概念体系界定为无法归化者 ,则需被清除出去,成为文明的祭品。对于这种思维来说,多元化因素的平等对话是不 可能的,强制性归化才是它的特性,因此建立在这种理性基础上的文明社会是一个权力 主体无限膨胀的病态社会。无怪乎克里斯蒂娃在寻求解放的事业中,首先要解构的就是 这样的主体意识,因为这种解构是一副解毒剂,它能够保全一个健全的人类社会和一个 平衡发展的世界文化生态。
正如巴赫金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使之成为一种倡导 对话的理论寓言,上述批评方式的杰出代表阿多诺则在“自从有了奥斯维辛后,写诗就 是粗野的了”(注:杨小滨:《否定的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154页。)的时 代选择了充满不谐音的现代音乐和以人类受难为主题意象的现代派文学,使之成为他的 “否定的辩证法”的形象表征。在阿多诺看来,现代派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不认同大 一统的社会价值,不反映虚幻的现实,而是以自身内在的异化、破碎和不协调来模拟外 部世界的异化、腐朽和疯狂,以表面的变形、荒诞、支离破碎、反英雄、甚至反艺术来 揭示一种隐秘的、形而上的社会真实,因此现代艺术永远是一个他者的声音,一种牵制 的力量,它否定、揭秘和批判。但是它并不是为了否定而存在,它的“否定性是忠实于 乌托邦的;它在自身中包容了隐密的协和”,(注:杨小滨:《否定的美学》(上海三联 书店,1999),第154页。)即否定的最终指归是为了未来的社会变革和完善,是为了超 越单向度的社会。所以尽管这种激进的非同一性批评拒绝与任何总体性认同,但是总体 却是蕴涵在其中的乌托邦,因此正如《否定辩证法之缘起》的作者苏珊·伯克-莫斯所 说,“阿多诺是一个不相信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家”,(注:Susan Buck-Morss,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the Free Press,1977),p.67.)这一点高度概括了这 一理论方法的正反同体性。
四
拯救性批评更是一种明确的正反同体性批判,它同样在现代性中看到他者被压抑,只 是这一批评的重点放在拯救传统上,因此在否定与批判的同时挖掘记忆和引入憧憬,让 一个平面维度的社会截面因成为一个纵向传统的片段而具有意义。这一批评的实践者是 瓦尔特·本雅明这样一个写作生涯跨越两次世界大战的自由文人,一个在纳粹开始猖獗 的年代里从弥赛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独特视角批判资产阶级进步神话的犹太血 统知识分子。对于他来说,在现代性中,“光晕”概念的丧失便是人与他者之间主体间 性或对话性丧失的标志,对于光晕的实质,他是如此界定的,即“能够看到一种现象的 光晕意味着赋予它回看我们的能力”,(注: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ed.,Hannah Arendt(Fontana/Collins,1977),p.190.)这意味着一种没有主客体分裂、没有 凝视和被凝视,而只有平等、模仿和同情关系的和谐状态。本雅明称之为传统,其源头 是一种人与世界、与自然、与一切他者和睦共处的、人类尚未堕落时的存在状态,在那 样的世界景观中,不仅人类有语言,一切他者都有语言,人类言说的内容不是指涉,而 是传达,即毫无遗漏地传达自然的精神,那是一种纯天然而友好的对话关系,两者最后 统一在完整和谐的宇宙法则中。这一天堂中的生存状态毁于人类的堕落,人类从永恒进 入历史,靠劳动来谋取生计,与自然日渐异化,与他者关系日渐敌对。因此拯救这个传 统也就是回归本原,找回失去的乐园,建立一种傅立叶意义上的人间天堂,使人类的劳 动将不再是“掠夺自然,而是能够把在自然的腹中沉睡的潜在事物催生出来”。(注:Ibid,p.261.)把人类和解的关系催生出来。
之所以称此为传统,是因为在人类的活动中,这种状态构成了所有奋斗的意义内涵, 作为记忆与憧憬一代代传承。但是在形式逻辑、工具理性、同一性思维的现代社会中, 这一传统在中断、被忘却,四分五裂为零星的碎片,或散在于诗歌、文学以及一切非主 流的文化片段中,或深埋于商品世界的表象内。因此救赎的批评致力于“损毁”表象, 挖掘本质,唤起对这些传统的记忆,力图把隐含在世界表象以下的乌托邦梦想彰显出来 ,把由于人们的遗忘而濒于流逝的本原拯救起来,把传统衔接起来,把一个破碎的世界 整合起来,最终显现救赎的乌托邦远景。因此对于这种批评来说,不仅文学是可读解的 文本,一切文化现象、历史陈迹、过时的商品等等都是批评家从救赎的视角来定位和理 解的文本。这就意味着,它的批评方法是批判和保守、摧毁和挽救同时进行,但是最终 目的是保住与守住那急需被拯救的珍宝,即传统和记忆的碎片。
如何实施这样一种批评?一如在巴赫金所阐释的陀氏的复调小说世界中,对话的各个阵 营须在一个共时的平面上“仿佛凝固的事件似的,形成静态的图形”,(注:《巴赫金 文论选》,第32页。)形成对峙,而决不融合,决不吞并,这时,作者(也许更是批评家 )作为一个局外人、旁观者或另一个阵营的代言人才得以描绘关系,实施“知识考古” ;救赎的批评也同样须在“凝固的事件”或“静态的图形”中开始思索与参悟,才能抓 住流逝的意义。因此它是将时间空间化,让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性直接对话,把它 们并置为一个星丛、一种蒙太奇效果的对照或反衬,在这种安排下,过去和现在形成一 个静止的“辩证法”形象,一个充满张力的构型,一种充满哲理的悖论。在此,现代性 将在传统的反衬下显现为一场不断堆积废墟的盲目进步的风暴,而相比之下,传统才是 真正的新异,因为它把人类带入更合理的生存状态。
这种批评意味着批评必须打断空洞、同质的时间进程,从一个永恒的现在、永远的在 场来重新审视历史,依靠这种审视来激发革命、解放、救赎的欲望,并不断用传统来支 撑、用记忆来强化这种欲望。这种批评自然是解构与建构的双向运作,一方面它打断“ 从前有一次……”的物化历史,另一方面它从被“爆破”的历史连续体中救出饱含意义 的永恒时刻,使之在思想的凝思参悟中结晶为一个“单子”,即一个完整世界的缩影。 哈贝马斯称之为拯救性批评也就是因为它拯救出了那些人类永久记忆的种子,剥去包裹 着种子的历史积层,使人们看到在其内核深处生命尚存,因为这是在大浪淘沙的时间长 河中沉淀下来的金子,是永不泯灭的价值和意义,是人类对于自由、平等,完整、和谐 的生存状态的记忆和向往。批评就是这种淘金意义上的拯救。
这一批评模式的实践者本雅明把这样的批评区别于惯常意义上的评论,他说: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可以说,我们把成长着的(即意义随不同的接受视野而变化着的 ——作者注)作品看作燃烧的葬礼柴堆,评论者就像站在旁边的化学家,而批评者则如 同一个炼金术士,对于前者来说,木头和灰烬是他的主要的分析对象,而对于后者来说 ,只有火焰本身才保有秘密:即那活着的东西。因此,批评家探索真理,真理那生生不 息的火焰在已成为过去的木头上和已被体验过的灰烬上熊熊燃烧下去。(注: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ed.,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Jenning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98.)
对于这样的批评来说,批评不是综述材料和描绘现状,而是一种超越和哲学建构,它 所遵循的认知模式不是来自于康德,而是歌德,即它不会用已有的思维定势去统括,而 是从现象入手,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追索而锁住意义,因此它必然是以解构 支撑建构,以批判支撑终极关怀。这其实总结了上述3种批判模式的共同品质,再次借 用苏珊·伯克-莫斯的话,可以说真正的理论都是不相信形而上学的相信形而上学,即 都是通过批判与否定体制化的意识形态而追求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如此界定的批 评最终是一种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也正是海德格尔所界定的诗人的天职,即还乡,也就 是回归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意义和价值均已被工具理性、商品化思维深深埋没的 语境中,回归之路必以解构为先导,这便是理论所面对的现实任务。
20世纪以来,上述意义上的理论曾经与法西斯主义抗争,作为一个微弱的批判声音, 英勇而悲壮;在工业化、城市化、大众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的理论又不断反思进 步、科技、理性之类的意识形态,在时代的喧嚣声中冷峻思索,大声呼吁。它拆解结构 ,剖析权力,解秘文化,可以说已经在解构、否定、拒绝、批判上倾注了足够的理论能 量。但是借此,它所期待的其实是自我扬弃,最后消解在自由和解的文化生态美景中。 然而,正如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一页第一句话中所说:“哲学之所以还健在 ,是因为实现的机会都错过了。”(注: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ton(Routledge,1990),p.3.)正因为实现的机会尚未来到,所以理论或 哲学还不能消解,还必须健在,而让理论或哲学健在则是批评家在当下所应有的思想品 格和理论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