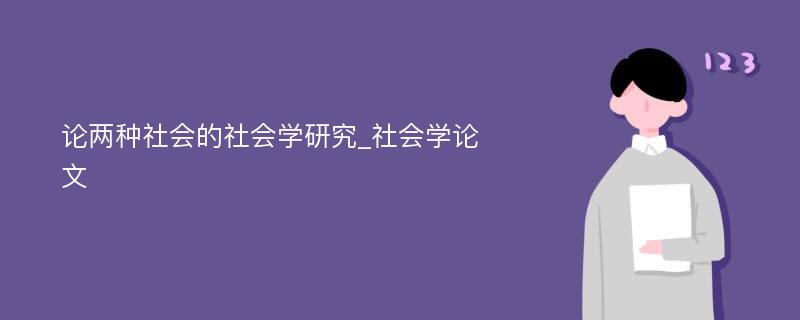
论两种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社会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何担心理论?
其他学科没有人像社会学家那样推崇古典学者。这也许归咎于社会学理论的缺乏。我们的祖先从未建造过经典、完整、跨越历史的理论大厦。他们只是试图理解社会。一些人留下了巨著,但另外一些人已化作尘埃,悄无声息。今天已几乎无人问津莫斯卡。
缺乏理论的学科需要指导,比如经典的问题及其答案,在百年后的今天,仍引人深思。其实,它们只是经验性的问题,通过寻找规律和解释来探讨社会。抽去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成为两个对立阶级的假设。韦伯的官僚主义理论则为经验的总结,其权力社会学实为类型论。杜尔凯姆的劳动分工论对亚当·斯密的学说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变革;而米歇尔的寡头政治论,试图从一个实例研究中得出一般化假设。
启发性的问题、假设和类型学只有建立在稳定统治的社会秩序之上时,才具有永久价值。这种秩序能推动跨越时空的权力集中,能创造反映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制度框架。用默顿(Merton)的话说,19世纪30年代、50年代、甚至70年代的社会学家成绩卓著,是因为他们站在前人的,尤其是巨人的肩膀上的缘故。资本主义制度仍旧沿着杜尔凯姆所预见的轨迹前进,因此,与古典学者的交流仍大有裨益。
新千年即将临世。虽然诞辰往往并不具有历史意义,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不同凡响。尽管无法证明,但许多人相信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正在诞生。社会学正在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之间徘徊。已知世界为“工业社会”,未知世界正在孕育中,暂未定名。如果确是如此,那么一代代社会学家孜孜不倦所创立的古籍遗产,也许会成为一纸空文,毫无价值。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正在发展的社会?下个世纪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学呢?
我不会妄下断语。社会学并非缺乏理论、岌岌可危。我们需要的是锚,是稳定、公认的“社会常数”,利用它们才能测量社会变量的重要性。我认为,前辈们的贡献不在于社会理论、类型学,也不在于他们伟大的问题,而在于他们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法。正如我们一样,他们的问题也是如何在事物发展早期进行预测。他们用的是双重比较法。他们通过对过去进行历时的、跨领域的比较,来认识新事物。当他们做出重大发现,他们便成为经典。新千年呼唤深刻的思想力、敏锐的洞察力和社会学的新发现,但是很遗憾,我承认本文并没有什么新发现。
重大的问题
没有自由选择就无所谓经济学。但有趣的是,经济学家却信奉垄断。他们购物常只买一个品牌。社会学家却相反,喜欢多种多样,是完美的主权消费者。
这种自由产生能量和创造力,但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创造力也难以开花结果。那么,如何引导我们的创造力呢?主要依靠重大的问题,它促成了社会学的诞生。这个问题是民主、平等、团结的社会秩序如何与城市化、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共处,两者之间是保持一致和追求效率的矛盾。
追求效率是经济学家的目标,它来自边际效应理论和均衡论。社会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趋同,并诉诸于科学。有笑话说,经济学家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哲学博士,而为社会正义和团结疾呼的社会学家,则更像一个民主主义者。
然而,现代社会学家似乎已忘却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历史使命。社会学正在向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语义学等方面发展。今天,有更多书是关于性别差异而不是权力或社会阶级,有更多的讨论是关于语言而不是如何进行经验分析。
因此,整个世纪以来困扰社会学的那些重大问题,已不能使今天的社会学家找到灵感。这也许是因为人们感到韦伯和他所忧虑的社会已是昨日黄花。今天,大量“后××”层出不穷。我们所知道的就只能被贴上“后××”的标签。但这行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决裂:现代工业社会已一去不复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做什么?后现代主义、富科(Foucalt)理论和构造学说能在新旧社会间建立桥梁吗?或者我们应另求发展?跨学科研究当然值得褒奖,但是历史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历史,语言学家最擅长研究语言。如果我们是社会学家,我们还是应该做最擅长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回到祖先开创的伟大的问题和经验分析上。研究身份鉴定、品味和语言文字自然有其价值。现在的年轻人过一种他们父辈完全陌生的生活,这毫不奇怪。了解他们的愿望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方向。但是,现代微观社会学研究潮流稍纵即逝,就是因为它没能认识全新的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后现代主义者没有提出划时代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是动力消失的结果。他们认为事物是随机的,因此因果解释毫无道理。
如果重建整个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家的火眼金睛将比语言诡辩更起作用。他们试图发掘新的运动逻辑和基本规律。如果真是如此,我们社会学家也应该把视线转移到新兴经济的作用上。在这一点,经济学家将爱莫能助。正如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经济学一样,经济学家也需要重新认识社会学。
利用“主题”
斯汀库姆(Stinchcombe)认为,摘社会学就是利用该领域的概念去解释一些变量,如权力、合法、平等或离婚等。这个世界没有常数。为做实验,我们需要最大的变量;但当变量太大时,我们又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因此,由于缺少选择,社会学没有遵从斯汀库姆的严格变量标准,成为一门主题学科。
利普塞特(Lipset)的“民主阶级斗争”,贝尔(Bell)的“思想形态的终结”和克斯彻摩(Kirscheimer)的“反对派之衰退”就是这样的主题。“工业主义”理论吸收了城市工业社会巨大的凝聚力。同样,“福利资本主义”和最近的“福特主义”是来自主题理论而非变量学说。主题理论认为在错综复杂的变量下面隐藏着根本的组织和连贯原则。
如果不是重大的问题和主题,战后的社会学不会如此引人入胜。它们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假设和检验,就像任何强劲的理论所能引起的一样。主题替代了理论。
“后××”的社会学
我们的时代跟马克思、杜尔凯姆的时代一样动荡不安。这个世界像我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那样吗?毫无疑问,当今社会万象更新,日新月异。在变革中,如果我们被卷入其中而不是冷眼旁观,我们就会陷入重重迷雾而迷失方向。
社会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我们处在新旧世界的交点。因此我们没有主题,无处抛锚,也不能参透各种变量。这也许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魅力所在。后原子家族、后生产力、后工业化社会总是被我们用来表示与过去的决裂。我们着眼于未来,却仍旧立足于现在。
创造一些“后××”的新词,并不能像早期“主题”那样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社会。“民主阶级斗争”或“福利资本主义”虽然像口号,但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了对当时世界的理解,指引了人们前进的方向。
远离“通常”社会
在“通常”社会中,社会变革沿袭和遵守固定规则。这些制约社会行为的规则稳定不变,延续至今。当然,从18世纪晚期到今天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民主制度和福利政策已在很多国家巩固和发展。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体制——家庭、官僚主义、工会、社会和阶级的基本类别——仍保持着他们的基本特点。面对这样一个遵守规则的社会,我们更关注集中和多样化,研究这些变量需要跨领域比较。
当然,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不同于韦伯时代的德国。但社会学家能发现固定的常量来量度社会进步。“工业化逻辑”是衡量历时凝聚和跨领域变化的基准。但是在体制分裂过程中,凝聚力何时会消失?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持“历史终结说”的人不会痛心基准和规则的消失,因为他们的世界随机而又杂乱无章。如果我们相信历史不是走向终点,而是走向新的起点,我们就需要寻找新规则。
生产力常被用来做基准。但在许多人认为生产已失去生产力的今天,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会不幸被布洛克言中,被一种新重农主义所窒息吗?
为逃离新重农主义,我们必须预见未来。卡尔·马克思在资本主义胜利之前不可能写出《资本论》;利普塞特利用“民主阶级斗争”论分析战后阶级状况,因为他是处在60年代而不是40年代。
大量理念源自“中心论”。韦伯的官僚主义论和马歇尔的“铁幕法”被称作典范,就是因为以德国为中心而被国际上采纳的缘故。现代主义和多元民主也是美国中心的再版,现代福利国家又把瑞士作为他们的中心和楷模。一个国家成为强国,他就可能被当作“中心”。
但当它失去统治地位时,这个理念也就会失去作用。韦伯的关于人与职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一种“福特主义”的效率理念。调查显示,个人性格和社交技能是“高官得坐”的法宝。
现在研究一下关于工作等级的看法。医生与护士的关系,餐馆老板与侍者的关系,与工业社会的等级关系一样吗?当然不同。因为在服务领域,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客户与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生产关系。这样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工作等级制度是否会更像银行、麦当劳或日托中心的制度?还有,顾客所付的价值是否反映服务者的生产力水平?在谢兹·皮埃尔理发店花50美元理发,他的生产力是否是当地理发师的两倍?我的回答是毫无差别,或差别不大。
走近新社会
迷雾茫茫,前途未卜,我们该怎么办?有三种答案。第一种答案,即历史终结说或后现代主义认为,从现在起一切都杂乱无章,没有规律。第二种答案认为,一切变革源于定则,任何事物都会沿其固有轨迹前进。第三种答案认为,我们面临历史的交替,时代的变更。
历史的交替意味着社会正在变革,也许其文字符号保持不变,但其内容已焕然一新。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历史正在被改写。过去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因为出现了新型生产方式,新的诱导机制和新的稀缺资源配置方式。稀缺资源的定义也在改变:以前是土地,后来是资本,现在是社会资本和大脑。新型经济带来新型社会结构、冲突和分流。现有社会走向分裂而非一体,建立新制度已是当务之急。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会层出不穷,行会成为联合组织,国家成为福利政体,社会学到了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时候。如果目前分裂现象仍很严重,社会学该作何解释?我们是否能够提出伟大的问题,看到新的完美典范或主题的出现?对新型社会的趋同,我们是否有挑战性的假设?
被称作“当代马克斯·韦伯”的卡斯特尔(Castell),其关于网络社会的著作引起极大反响。无疑他试图超越“通常”社会研究,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和主题。
卡斯特尔认为,由独立个体追求金钱、权力、幸福或效益而推动的旧秩序,正在被新秩序取而代之。无处不在的网络使决心、行为和积极性都变得空前活跃,已成为新秩序的焦点。21世纪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电脑空间”。如果社会网络开始控制交易和生产,如果网络质量决定人们彼此信任和协作的程度,那么人机结合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论述旧社会样板消失和多样化出现的,不仅仅是卡斯特尔一人。“标准化生产”的日益衰落有目共睹。那么,目前这种变化的动力何在?阶级又该如何划分?将来,几乎人人都会从事与消费同步进行的生产活动,比如牙医、金融顾问或总台接待员、敬老院服务员。服务业需要社交技巧,它改变了权力轴心。医生当然会吩咐护士,领班也会命令侍者。但是,这些吩咐和命令最终还是来自消费者。这条社会关系是建立彼此信任的关键,也是判断服务质量的依据。网络社会帮助我们领会这些主导关系的出现,并提供关于新型社会冲突、分流和组织发展的假设:无论它们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都来自全球网络的外围。但是这些外围事物是否会操纵历史?
可以设想,如果经济和生活依赖于网络运作,那么家庭、社会和阶级间的关系会大为改观。人们会竞相进入网络而不仅仅是找一份好工作。你的声望、收入和权力将更取决于你的交际面和网络价值。这样,社会资本资源和家庭以及教育将造成不平等。社会资本和社会技能正日益挑战常规人力资本,而成为基本稀缺资源。这样,在一个服务性社会里,如何去掌握和量度生产力、需求和稀缺资源,已成为新的障碍。
经济社会的分水岭可能不会使分而治之、追求效率的资本家与整齐划一的工人阶级决一雌雄。实际上,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网络而不是家庭、宗教、社区和社会运动。这对社会学会有何影响?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去理解历史裂变和展望未来社会,就最好从研究家庭开始。家庭是社会学的基础,是巨变发生的地方,并被称作后工业社会的先驱和核心。
家庭,曾是“无情社会中的天堂”,也许正在经历从社会整体的基本细胞到前工业社会的经济细胞的转变。家庭正在脱胎换骨。在服务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家庭正从封闭温情的蜗居走向外面的世界。我们的经验知识和研究策略是否能帮我们认清家庭的真实面目呢?
从经济学方面来说,人口增长和对物质资料的需求推动了工业经济的发展。民主阶级斗争、多元的“中产阶级社会”和“富裕起来的工人”使家庭只用一个劳力就可有足够的购买力,这样妇女就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这样的家庭,不仅可保证人口增长,还可保证其他成员得到关心和照顾,这就是所谓的“后核心”家庭理论。
在当今世界,这种理论已无人喝彩。经济方面已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女性劳动力供给已赶上男性劳动力供给;二是家庭推动了新型服务经济,但方式却与过去大相径庭。确切地说,对服务的需求仍取决于购买力(恩格尔定理),一个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势必会引起服务消费增长。问题是服务业生产力增长放慢,实际收入增长也会随之放慢。因此服务业发展必须另觅出路。
问题症结在于相对价格。在生产消费品的经济中,家庭要么购买该产品要么就不用它。没有哪个家庭能够自行生产冰箱或汽车。在服务业经济中却不然。生产者面临来自家庭的竞争,因为家庭可以自我服务。因此,要发展服务经济,定价必须与自我服务的机会成本竞争。有两种办法:其一,降低服务价格。这可能会造成收入不均和社会分化。其二,提高家庭对服务的需求,比如他们缺少进行自我服务的时间或能力。妇女解放使新型家庭缺少时间,推动了服务经济的发展。
总之,服务经济从人们家庭生活不自觉的改变中获得动力,但这个变革过程却充满矛盾。一方面,家庭缺少时间急需服务;另一方面,只有定价适中,人们负担得起,供需才能平衡。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服务工人挣钱太少,以致于享受不起自己的服务。长此以往,社会分化在所难免。
新型家庭会刺激新型经济,但同时也会对社会一体化进程产生影响。变革使家庭同时处在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之下。它对社会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正在减弱,因为家庭和社区生活的凝聚强度与它们服务消费的水平成反比。家庭办公室会加深有社会资本的人和没有社会资本的人之间的鸿沟,工作场所会成为社会联系和个人满足的网络。如果确是如此,社会聚合和隔绝的动力何在?它又会如何影响效率和统一之间的平衡?
简而言之,社会学的当务之急就是去发现是什么构成了当代家庭、单位、官僚政治或福利国家的完美典型。
未来社会的社会学
对未来社会的研究,我主张有意识、有目的的经验主义。研究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粒子是研究整个社会的捷径。窥一斑可以见全豹,就是这个道理。
有目的经验主义可以从理性选择角度得到大量启示。例如,最近哥德索普(Goldthorpe)指出,个人行为微不足道,社会整体会更具理性,因此人们为某种目标结合成为群体。或者如赫克特(Hechter)所言,理性选择理论致力于社会效果而非个人行为。总之,理性选择理论是目的经验主义的有力指导。
经验主义似乎有悖于先人的指导。但其实他们也在无意识地坚持理性选择方法。他们对新秩序的宏观描述,正是对微观社会研究的结果。
因此,我们的先人对经验主义并非一无所知。他们运用比较法,将历史进行历时比较。他们把工业前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常数,以此来认识他们所处的新时代。对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家来说,“历史”不应是氏族社会或中世纪的英国。因此我们的常数应为“工业主义逻辑”、“福利资本主义”或“民主阶级斗争”。至少这是本人研究家庭和服务经济的途径。研究家庭变革可以阅读帕森斯(Parsons)的著作,研究职业等级关系可以阅读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著作。当代学生似乎更专注于威廉森(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但如果他们致力于组织行为研究,他们也许该读一下瓦特(Whyte)的《组织中人》。
历时比较法也有其缺点。其一是进化不对称,即“裂变”与“因袭旧路”会因为体制不同而有所变化。比如家庭可能正处于巨变之中,但福利政体或工业关系却纹丝不动。不对称的体制变化可导致严重失衡,社会紧张或所谓“危机”。其二是进化雷同,即过去会扰乱视听。社会变革不会一蹴而就,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历时比较应深入历史,从变革的最初发源地开始。
运用历时比较的目的经验主义,必须了解自己的目的。但未来社会,我们的研究目标,仍是云山雾罩,难识其真面目。真正的天才会先想象未来社会,再用自己的研究去印证。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善此道,需要一盏明灯来照亮这迷雾中的世界。
于是,跨领域比较法便乘虚而入。指明灯当然越亮越好,这意味着详尽的目的经验主义研究应致力于寻找变数。我们祖先中的精英识别了未来社会的先兆,并把它转化为未来社会的完美典型,极大地推动了历史进步。当韦伯把德国官僚政治作为先兆时,他是幸运还是伟大并不重要。现在,卡斯特利斯(Castells)把硅谷作为未来社会的先兆。但只有历史才能最终证明社会是否将变成一个“硅谷”。如果成为硅谷6的常数,无疑卡斯特利斯会被作为当代的韦伯。
这样,在没有理论支持或主题作为参考的情况下,如何研究转型过程便有了答案。它包括比较过去的极端状况与未来的征兆,并搜寻和整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项工作仍然是在变化中寻找规律,这正是社会学家的专长,也是社会学的学科优势。
问题是,大多数社会学家是否真正在运用该方法。为求得未来的发展,社会学也许需要重新定向。历时比较要求研究者具有一些历史知识。我们的知识足够使我们进行历时比较吗?我们的学生仍在学习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运作机制吗?对社会、经济和社区略知皮毛决不可能发现未来社会的征兆。有多少比较学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学家?我们怎样才能确保下一代社会学家对进行比较的社会有足够的了解?
如果未来的社会学家仅仅拘泥于自己的社会和时代,那么他决不会有什么建树。因此,我们不应仅仅是鼓励,而应是严格要求未来的社会学家对各种社会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比较。如果美国人研究德国,德国人研究西班牙,西班牙人研究美国,那么社会学回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大为提高。实际上,如果有一天卡斯特利斯击败所有美国社会学家而一跃成为当代的马克斯·韦伯,那么这也是因为他是一个研究美国的西班牙人。
摘自英国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Jan-uary/March 2000
标签:社会学论文; 历史社会学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历史学论文; 家庭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