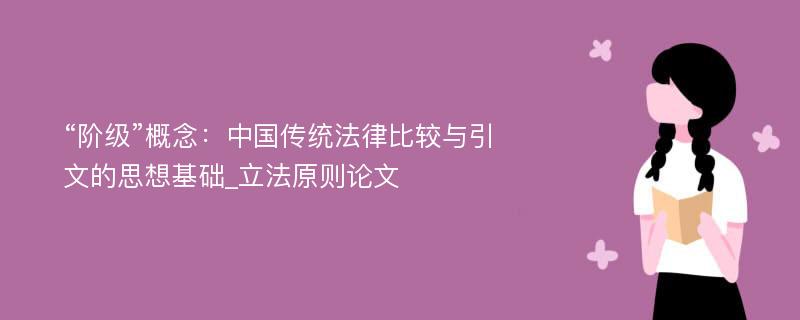
“类”概念:中国传统法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概念论文,思想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9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1710(2012)02-0093-07
我国经过30余年的努力,法治建设的主要问题已经由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转变为司法不公以及由此带来的司法缺失公信力的问题,法学研究也因应由对制度建设的关注转向对制度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关注。另外,由于移植的法律给当下的中国法律和当下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法学界的目光转向了“回采历史”[1]。因此,在从立法实践到司法实践这一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背景下,随着中国传统法的现代意义的不断追问,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日益从探讨律令制度逐步转向对司法实践的关注,以探讨其可能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司法的实质是对荀子的“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的“法、类”思想的贯通,即缘法定罪与比附援引是中国传统司法的核心内容,二者双剑合璧,形成合力,共同保证了司法结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充分注意到了缘法定罪与比附援引之间存在的一定张力,“他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运用智慧和技巧不断追求裁判的合法性与公信力的统一,从而通过纠纷的解决不断接近秩序和谐的目标”[2]。然而,法史学界在以往比附援引的研究中由于考察角度的不适当,产生了很多误解甚至是不恰当的结论,比如把比附援引作为缘法定罪的对立面,并进而认为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由于法史学界对逻辑学界关于比类思维的研究关注很少,以致在中国传统司法运作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在司法领域,比附援引属于法律方法论的范畴,具体而言是指一种法律发现的方法,即:某一法律问题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通过寻找与之有类的对应的规范中的制度事实,将作为小前提的法律问题涵摄于作为大前提的一般法律规范,从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方法。笔者认为,比附援引是中国古代比类思维逻辑在司法领域的运用,其思想基础是古代的“类”概念,以“类”概念为思想基础的比附援引保障了司法判决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一、“类”字考证
中国古代的比类思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被广泛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医、古代科学等领域,在秦朝时已大量进入司法运作中,这从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可以得到证实。比附援引是中国古代推类逻辑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是建立在对类概念的认识之上的。
类是中国古代比类思想的基础,但是类最初的意义并非如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类的内涵和外延经过了多次转换,才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逻辑思维范畴。
“类”字的繁体字写作“類”,这是一个会意字,其左右两部分都是由象形字组成:左侧为“米”和“犬”,右侧为“页”。在殷商时代,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不能科学地解释一些问题,常常求助上天的保佑和庇护,因此在殷商时代祭祀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活动。为了表示对上天的虔诚,用作祭祀的祭品不可或缺,在当时谷物和牲畜是用作祭品的品种之一,而“類”字左侧的“米”和“犬”这两个象形字所表示的客体是殷商时代用作祭祀的祭物。另外,“類”右侧的“页”,在古文中通“首”,如同倒悬的人头。在殷商时代的祭祀活动中,奴隶用作祭品也十分常见。因此,通过分析组成“類”字的三个象形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类”字与古代的祭祀活动有关,这能够在传世文献中得到证实,“凡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宗庙则为位”[3]587,“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五曰攻,六曰说”[3]775。我国古代祭祀活动的名目有多种,而祭祀的仪式随之有不同,“类”就是一种祭祀仪式的称谓,因此,类的最初含义应该是祭名。
到了周朝,“类”具有了“族类”的意义,“族类”之意与类的最初含义“祭名”具有一定的联系。在祭祀活动中,总是有许多人参加,参与祭祀仪式的人员作为一个集体,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参加人员必须是属于“族类”的人员,因为“神不歆(保佑)非类,民不祀(祭祀)非族”[4]416,“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4]539,即是说神不保佑非族类人员,也不受纳异族的祭奉。为什么在西周,类具有“族类”之意?类的含义由“祭名”演变为“族类”,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联系,具体而言,这与周朝的宗法制度有一定的因缘。宗法制度源于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于西周时趋向成熟。在漫漫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这样族权与政权合一,宗族与君主统治合一,政权、族权和王权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概括而言,宗法制度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宗法制度最终形成以嫡长子继承为基础,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的庞大宗族网络。因此,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普遍地受到宗族关系的支配,这种关系对人们有着组织和制约的作用,而统治阶级在利用这种关系维护自己的统治时又使得这种关系进一步强化。对于同一宗族的人,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所谓“同性同德,异性异德”[5]337,“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824。对于同一宗族的社会成员,由于同宗共祭一祖,决定了同宗族的人祭祀活动的同一性,所谓“神不歆(保佑)非类,民不祀(祭祀)非族”,属于同一宗族的就是同类,不属于同一宗族的就是非类。祭祀活动成为表明参与祭祀人员之间亲密关系的方式,而且通过一起参与祭祀活动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类之“族类”之意与类的最初含义“祭名”具有一定的联系。从类之最初含义“祭名”到“族类”概念的出现,这说明随着人们社会实践领域的逐步扩大,人们认识水平和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族类”概念把“类”与人群的分类联系在一起,人们的认识阶段已经由个别发展到特殊。
类之“族类”之意是先人对社会领域人群属性异同的抽象,在自然领域,也产生了对事物类属关系的认识,物类概念随之产生。在“物象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5]95,“方以类聚,物以群分”[6]认识的过程中,赋予了类具有事物相同属性的意义。无论是社会领域的“族类”概念还是自然领域的“物类”概念,都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之间联系的一种认识和抽象,而这种认识和抽象是以把握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为基础的,因此,类自然具有了“同”之意。关于“同”,墨家学派提出四个层次,即“重、体、合、类”[7]480,“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7]480。即,“重同”为全同,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相同;“体同”是种属之同,两个概念的外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合同”,指的是两个概念的外延包含于同一概念的外延之中而彼此之间是互不包含的并立关系;“类同”的判断是“有以同,类同也”,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指两个事物之间有随便的一种联系就是类同,类同必须是事物的本质相同。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类同的事物之间一定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但也一定会具有能够区别彼此的非本质属性,否则就成为“重同”;而非“类同”的事物,一定是彼此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当然还会具有某些相互联系的共同的非本质属性。因此,判断事物之间是否“类同”非常复杂,这是由客观事物之间联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的,简单、随意地将两个事物中的某种相同的属性视为分类的根据,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事物的本质属性并不是仅靠感觉就能准确把握,必须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理性分析过程。
应该说是墨家学派完成了类概念的最终确立,因为其揭示了类概念的真谛所在,即事物的本质相同。从类的最初含义“祭名”到“族类”和“物类”,再到“事物的本质相同”,“类”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多次转换,这说明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思维的内容和范围是不同的,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8]另外,“类”字含义的演化历史也反映出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在不断提高,在社会实践中人们对事物的把握逐渐地接近它的本质,这也反映出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客观规律,即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
二、“类”思想
“纵观类概念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逻辑范畴出现的,只是在经历了社会实践若干阶段性的变化所引起的内容多次转换之后,才逐步地以逻辑思维的规定性的形式在人们的意识中固定下来。”[9]类概念确立后,作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范畴,成为比类思维的基础,因为从已知到未知逻辑推理的正确性,有赖于思维内容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知类”则是对思维内容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的保障。比类思维成为人们由已知到未知的认识手段和思维范式,被广泛运用在中国古代的多个领域,如古代文学、数学、中医,同样,在司法领域,解决“法无正条”下的疑难案件的比类思维是中国古代司法思维的重要内容,将类概念和类思想运用在司法领域的首推后期儒家的伟大代表荀子。
荀子对“类”概念的认识,在继承和吸收墨家“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的关于“类”概念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独到而完善的类思想体系,不仅包括物类,还包括伦类和统类。
关于物类,荀子认为“物各从其类”,“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10]6-7在此,荀子揭示了“类”是事物的本质所在,类本质的不同决定了事物的同异。荀子认为物取自物类,虽然时间久远,同类的事物必然具有同样地规律和事理,所谓“类不悖,虽久同理”[10]82。既然“类”是事物的客观存在,那么人必须要遵循,因为“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10]309-310。那么,人如何获得对“类”的认识呢?人具备辨别事物“类”的能力,能够“所缘以同异”,“然何缘以同异?源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其也……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簿其类然后可知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10]415-418在此,荀子指出,人能够依靠天官(感官)和心智对事物的类(本质)有经验性的体认和抽象的把握。既然人能够依靠其心智把握事物的类本质,那么就可以依凭推类的方法由已知获得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因为“推类不悖”[10]423,即同类相推不会产生悖论。
荀子的类除了物类,还有伦类和统类之意。物类,指的是自然领域的各种事物的类本质,即“物各从其类”;物有类属,情理同样也有类属,伦类指的就是情理的类属,面向的是社会领域中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指的是人际间的伦理规范(或价值取向)的类同,如“伦类以为理”[10]256。荀子的推类以物类或伦类为基础,这说明荀子的推类不仅是逻辑的,而且具有伦理性,因此荀子的类思想的诞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认识论和伦理学上的意义。荀子的类思想之所以比较完善,不仅因为其对墨家的物类的意义阐释的更深刻,提出了社会领域的伦类概念,还在于他阐明了以整体的角度全面把握事物规律性的“举统类以应之”的思想。在荀子的类中,荀子将类与“统”字连用,提出了“统类”这一概念。荀子的统类思想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一贯、一致、统一,如“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变万举,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10]445,“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10]95;其二,统类有普遍原理、根本原则之义,如“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10]140对于尝所未闻、尝所未见的没有经历的事情如何处理呢?则需要“举统类而应之”,统类在这里是普遍原理之义。在法律领域,统类则是根本原则之意,如“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10]407;“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10]94;“举统类而应之,张法而度之”[10]140。那么,作为法律根本原则的统类具体指什么呢?“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10]163,“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也。”[10]11-12由此可知,荀子强调的统类是建立在“礼”这一总纲之下的。
三、类——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
人类步入阶级社会后,法律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因为成文法的制定和颁布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比如一定时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积累、一定的立法水平和技巧以及发达的文字作为基础,这些在人类刚刚步入阶级社会的初期,是根本不具备的,因此不成文的习惯法是人类不可逾越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经过了漫长的不成文的习惯法时期,在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制定法的公布,必然因应产生遇有法律未规定的情形实践中如何操作的问题。因为法律文本是对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的总结和规定,但是社会还在向前发展,法律滞后性的问题应运产生;再者,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与文本本身的有限性,千变万化的实践情形与相对固定的法规则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逾越的客观存在[11]。另外,由于立法者认知的有限性,不能把人们需要解决的所有社会纠纷、社会矛盾的处理方式完全涵摄于法律文本中。因此,进入成文法时代,“定法有常,犯状无常”的矛盾凸显。荀子的“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10]500为这一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中国传统司法的实质是对荀子的“法”、“类”关系的实践,“从法律实践领域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并不是孔子、孟子,而是荀子。他在战国末期为行将出现的封建大一统王朝提供了礼法结合的治国理论,并为未来的立法、司法活动设计了一整套方案。”[12]
(一)“无法者以类举”中“类”之含义
传统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设定的行为类型之间的关系包括两种:法有正条和法无正条。法有正条针对的是简单案件,能够直接适用现有法律规范就能解决纠纷,即作为案件事实的小前提能够直接涵摄于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之下,案件事实的行为类型与法律设定的行为类型之间的关系是墨家学派所总结的“重”或“体”的关系,即完全相同;法无正条针对的是疑难案件,在现有法律中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规范,即案件事实的行为类型与法律规范设定的行为类型具有“类”的相同或相似,没有直接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只能适用具有“类”的相同或相似的法律规范解决纠纷,简而言之就是比附援引。荀子“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成为司法活动中的法有正条和法无正条两种情况下如何适用法律的思想基础,而比附援引就是对“无法者以类举”思想的实践和贯通。比附援引是否准确以致最后能够合理而又合法解决案件的关键是案件事实的行为类型与法律规范设定的行为类型之间是否具有类的相同或相似,换言之,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是“类”,与荀子的“无法者以类举”中的“类”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无法者以类举”中的“类”具体指什么呢?
“由于语词在意义上具有‘开放结构’,加之语词在确定由事物间联系方式所形成的意义上存在必然的偏差(甚至根本无能为力),因此语词的意义依赖语境。”[13]同一语词会因为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语境对于厘清某一语词的确切意义十分重要。关于“类”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荀子的著述中有两处提到“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其一,《荀子·王制》曰:“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10]151;其二,《荀子·大略》曰:“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异理而相守也,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10]500。前者,寥寥数语,“类”的语境不是很清晰,可以通过后者的语境管窥到“无法者以类举”中的“类”为何意。笔者认为,此处的“类”应该包含如下两层含义:其一,统类之意。如果一个法律问题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以在法律根本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处理,即“以其本知其末”,此处的“本”为法律根本原则之意,即统类;其二,物类或伦类之意。“即以其左知其右”,即如果一个案件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以比附案件事实与法律所设定的行为类型相同的规范,这里的“类”是物类或伦类之意。那么,“法”概念与“类”概念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关系呢?首先,类与法具有相同的功能,而且类概念是相对于法概念而相依存;其次,法与类具有各自的适用领域,即有法可依与无法可依;最后,类能弥补法的滞后性与僵硬性,具有法所不具备的应变性,所谓“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10]158。总之,对于无法可依的法律问题,在统类(法律的根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物类”或“伦类”相同的思维判断,从而发现比附援引的法条,这样就能够做到合理、公平的奖赏和刑罚,贯通“类”的要求实现一致和统一,即“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荀子的“无法者以类举”中的统类、物类与伦类之意,作为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对于司法活动中的比附实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物类、伦类与统类——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比附援引的适用正是对荀子的“无法者以类举”思想的贯通,作为比附援引思想基础的“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和外延是有区别的。在秦和汉朝初期,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是物类,而不涉及伦类和统类,因为这一时期奉行的是法家主张,司法裁判中强调严格守文,对于法律真空地带的疑难案件在比附援引时,仅仅强调物类的相同;西汉中期,经过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社会处在转型时代,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在司法转型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化,由先前法家思想指导下的物类的相同,逐渐开始也强调伦类、统类的相同;经过魏晋六朝时期儒家思想的熏陶、浸润,至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唐朝,法律领域实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中华法系的道统与法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缓和,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在比附援引时不仅重视物类的相同,而且非常重视伦类和统类的相同,实现了立法目标与司法目标的一致。之后的宋元明清时期,司法中比附实践的思想基础一如既往地强调物类、伦类和统类的相同。
1.秦与汉初: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强调物类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井田制逐渐瓦解,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进入了大变革时代。曾经维系社会秩序的三代的礼制面临空前的挑战,礼崩乐坏之时,关于治国救世之道的各种药方纷纷出台,粉墨登场,社会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空前活跃时期。在当时的大变革时代,在诸侯争霸的历史背景下,以富强为治国之急。儒家逐渐落伍于时代,其思想与时代要求不能契合,而法家思想适应当时霸主之需要,因此法家应运而生,为国君所重视,法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成为拯救时弊的一剂有效药方,法家理论作为当时的显学,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秦朝及其前身秦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奉行法家的主张,践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4]的奉法齐一的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面对法律不能直接处理的法律问题,当把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涵摄于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时,就要考虑案件事实的行为模式与法律规范所设定的行为模式是否类同,这里主要是涉及物类,而不涉及伦类和统类,如《法律答问》中对法律语词的解释大多采取直接说明的方式,直抒法意,“不过多地阐发某一法律概念背后的意旨,更不从道德伦理方面立论,这与汉以后的儒家注法有很大的差异”[15]。因为法家倡导“法不阿贵”、“刑无等级”,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16],“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7],追求的是绝对的“法治”,而不是天理、国法、人情的整合。正是由于秦朝极端追求“法治”,坚持恪守成文法的语义解释,在无法可依比附援引时,只是注意到物类,而忽视了社会领域客观存在的伦类,抛开天理和人情,只是注意到了司法的合法性,而没有注意到司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过度彰显司法的严酷性使得秦王朝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汉承秦制,汉朝初期的观念和制度与秦代一脉相承①,司法领域中的比附援引只是注重物类的相同,而涉及不到伦类,比如发生在汉高祖10年(公元前197年)的“娶逃亡人为妻”一案,此案发生在汉高祖刘邦颁布疑狱诏②即关于疑难案件审判制度的诏令确定比附援引制度的第三年。按照当时的法律,娶逃亡人为妻,应当“黥为城旦”,但是基层法官认为因为当事人不知道其娶之妻为逃亡人的真实身份,从情理上讲具有可原之处,是否可以比附其他律条进行处理,于是作为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但是廷尉完全不考虑当事人根本不知情的特殊情节,只是呆板、僵硬的根据法条做出裁决:“取(娶)亡人为妻,律白,不当谳。”[18]
2.西汉中期以后、魏晋时期: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开始关注伦类和统类
秦律为法家所制定,以法家理论为指导思想,贯彻的是法家的主张,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司法领域中的比附实践只是以物类为基础,汉初的法律承袭秦制,司法领域中的比附实践同样没有涉及伦类和统类。西汉中期,汉武帝标榜儒术以后,法家逐渐失势,儒家的主张成为的国家正统指导思想。之后,“儒家思想长期支配着汉武帝及其之后的立法、司法活动”[19],法律儒家化运动随之展开进行,但是由于当时国法早已颁布,臣下不能随意更改,法律不可能一旦改弦更张,法律儒家化运动最早开始于司法中的引礼入法。虽然国法已经颁布,臣下不能随便修改法律,但是当时是儒者为官,他们担负着司法的责任,拥有讨论司法的机会,汉时儒家引礼入法大部分的努力在司法领域,因为“司法官是生活中鲜活的、充满个性的人,因为他是社会中的人,所以必须根据对社会的体验来实现对文本的应用。”[20]随着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司法官在判案时开始注入礼的精神,司法领域中的比附实践不仅涉及物类,而且开始逐渐涉及伦类和统类。
3.隋唐以后:物类、伦类和统类成为比附援引的思想基础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引礼入法,至中华法律定鼎时期的唐朝,礼与法的结合臻于成熟与定型,实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法律规范与社会价值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调和。在司法领域,比附的实践完全贯彻了荀子的“无法者以类举”中“类”的内涵,即物类、伦类与统类。之后的宋、元、明、清与唐朝法律一脉相承,司法实践中的比附以物类、伦类和统类为基础,实现了立法精神与司法精神的一致性。宋代,司法实践中非常强调伦类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管窥。比如宋代司法官胡石壁在诉讼判词中明确指出:“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③这里的人情不是指“私情”,而是指人之常情、情理,而人之常情、情理只能从人本身来寻找,而所谓的人,是具有血缘人伦的人,霍存福教授认为:“礼律自然=情理=人伦。”[21]在司法审判中,强调遵守法意,又要强调不违背情理、人伦,对于疑难案件在比附援引时强调伦类的相同,如宋代欧阳修所言:“已有正法则依法,无正法则原情。”④司法活动中的比附实践强调伦类的相同,实现了司法目标与立法目标的一致性,因为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立法实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非常强调立法对人之常情之情理的尊重,如元人柳贯《故〈唐律疏议〉序》所言:“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明人刘惟谦等《进明律表》所言:“陛下圣虑渊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准绳。”清乾隆皇帝御制《大清律例序》所言:“朕……简命大臣取律文及递年奏定成例,详悉参定,重加编辑。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以上都是强调立法中对天理和人情的尊重。那么,在司法中对于疑难案件进行比附援引时强调伦类的相同是与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即司法中“原情以定罪”的必要,来源于先于此的“酌情而立法”。清代,刑部对于发生在光绪10年的“儒师引诱学徒为非”一案的批示中对比附援引的内在机理作出了深刻而又充分的阐释:“如审理案件遇有例无明文原可比附他律定夺,然必所引之条与本案事理切合,即或事理不一而彼此情罪实无二致方可援照定谳,庶不失为平允,如不论其事理,不酌其情罪,徒执一二名相似之文率先爰书,殊失立法本意。……总之此等案件,例内既无明文,历来亦无似此成案,全在司谳者准情酌理折衷心至当,不得意为轩至失情法之平。”⑤可见,在古人的思维中,所谓同类事例意味着“事理切合”和“情理切合”,即是指荀子的物类和伦类的相同,这就是比附的内在机理所在。在律无正文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只有当案件事实与规范内的制度事实“事理切合”或情理切合的情形下,适用比附,才能符合立法原意,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实现统类的一致。
中国古代在“比”的推理思维和“类”的类型化思维下形成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比类”思维形式,而比附援引是比类思维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运用。“类”思想作为比附援引司法实践的哲学基础,保证了比附援引司法判决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司法适用中的比附援引,不能只是简单地将其作为一项司法技术进行研究,而应该从中国长期的农耕文明所决定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对人类思维的影响角度,认识到比附援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再细述,这是下一篇文章要讨论的问题。
①关于汉承秦制,《晋书·刑法志》言之较详:“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始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参见:《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0页。
②汉朝初年,针对“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的法律困境,汉高祖7年(公元前200年)颁布疑狱诏,即颁布关于疑难案件审判制度的诏令:“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参见:《汉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35页。
③《名公书判清明集》是我国宋代一部官府公文和诉讼判词的分类汇编,其绝大部分是诉讼判词。这些书判是现存的关于当时司法实践活动的重要史料,对宋代的法律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反映了当时社会成员的法律情感、法律认知和法律评价,能够帮助我们解读宋代的法律现象的深层文化机理。书名中的“名公”是指当时显赫有名的备受社会尊重推崇的名士;清明,根据明刻本刊印者盛时选在《后序》中所说:“明无一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然后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为哲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1页。
④参见《欧阳文忠公全集·论韩纲弃城乞依法札子》,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文忠集,卷一百三。
⑤参见《刑案汇览三编》卷四十三《儒师引诱学生为非》,沈家本编辑:《刑案汇览三编》(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