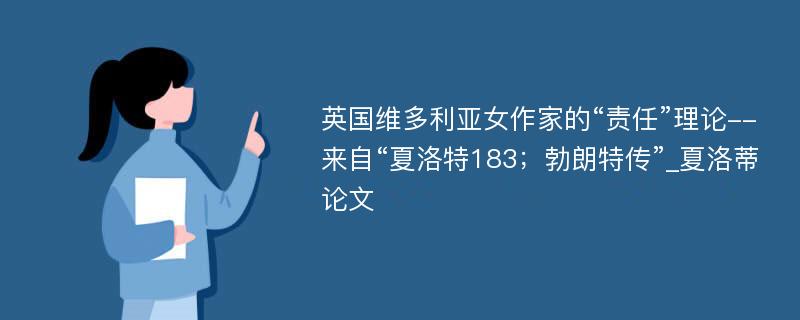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的“责任”之说——从《夏洛蒂#183;勃朗特传》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多利亚论文,英国论文,女作家论文,之说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女性写作空前繁盛的时期。与此前时代相比,更多女作家开始在英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论女性写作的专著《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谈到,18世纪中产阶级女性作家开始写作,可谓是可载入史册的大事,因为始自她们,女性开始可以通过写作获得金钱报酬,这亦即表明女性写作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可。①到了19世纪,女性作者主导了当时各类报刊杂志。女性写作早已褪去时新色彩,她们在文学领域的群像存在已是不容忽视。但是,女性写作依然不会受到多少鼓励。从当时文坛批评名家乔治·刘易斯(G.H.Lewes)那里即可管窥维多利亚社会的普遍看法。刘易斯认为,女性的首要任务是嫁作人妇、生儿育女,这将损耗她们的精力,而体质孱弱的女性尤不适合从事艺术创作,因为艺术事业要求人全身心投入其中。②在许多人看来,女性命定的家庭责任显然有碍她们从事文学创作。不过,因为有了此前时代女作家的先例,对于女性与写作,维多利亚人更为关注的已不是女性能否写作的问题。他们更为关心下述两大问题:女性如何处理文学生涯与家庭责任的矛盾,如何协调女性气质(femininity)与文学的关系。③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气质指向的是“家庭天使”理想——谦卑温顺、纯洁高尚的居家女性,女作家的作品似乎理应展现这般女性形象。因而,当时的女作家不仅要应对家庭责任与文学生涯的矛盾,也可能会因其作品语言、题材风格等不合女性气质规范而招致社会非议。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女作家,她借着撰写《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契机,以夏洛蒂生活中的关键词——“责任感”——为出发点,试图解析女作家的命运曲线,正是应和了维多利亚人的关注焦点。在盖斯凯尔看来,家庭责任既然是全体女性的首要义务,理应也是女作家的第一义务,写作则是其第二义务。因此,女作家要以家庭义务为先,而在写作领域,她们亦另有义务,即有责任再现真相,即使这意味着她们须冲破社会陈规旧习的樊篱。盖斯凯尔实际上是在为女作家争取艺术创作的自由权。盖斯凯尔的这一立场,是在传记中为夏洛蒂辩护时激发出来的,因为《简·爱》暗含“反叛”信息使得夏洛蒂蒙受污名。在传记中,盖斯凯尔选择性地展现夏洛蒂的生平片断,揭示了女作家如何以“责任感”为支点来应对上述的两大难题。女作家在此过程中借用“责任感”这一可为社会接受的话语,拓展了自身的活动领域,从中获得了自我的发展。 一、《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前因后果 盖斯凯尔撰写《夏洛蒂·勃朗特传》与夏洛蒂的小说因僭越女性领域而惹来批判有关。1847年10月《简·爱》的问世轰动英国文坛,大获成功。同年12月《福莱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刊出乔治·刘易斯的文评,对《简·爱》极尽赞誉之词。④但是,批评界某些角落的道德声讨却是敌意甚浓。不少评论给此书贴上“粗俗”(coarseness)的标签,其中以1848年4月《基督醒世报》(Christian Remembrancer)和1848年12月《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的攻击最为猛烈。《基督醒世报》咄咄逼人,批判小说的每一页都充斥着“雅各宾式的道德反叛”。⑤《评论季刊》上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撰稿人伊丽莎白·瑞格比(Elizabeth Rigby)斥责这部小说潜藏的情绪与激发英国宪章运动的情绪无异,简·爱身上满是“邪恶的不满情绪”,她犯下“傲慢”的罪过,是“不受纪律约束”的化身,整本小说都是极为“反基督精神”的。⑥简·爱这样“粗俗透顶”的人物,瑞格比说,“我们不屑与其相识,不应与她为友,不愿跟她沾亲带故,而且还要格外谨慎小心,避免请她做家庭教师。”⑦作者本人的道德名誉也连带严重受损。夏洛蒂虽未以真名示人,采用的是柯勒·贝尔(Currer Bell)的男性化笔名,评论者却也不买账,总也不吝往女性身上涂抹几笔黑墨。《基督醒世报》批判该小说缺乏“女性气质”,难入女作家作品名单之列。⑧瑞格比更是直言,“如果我们认定这是女性写出的作品……她定是早已弃离了女性社会的。”⑨有趣的是,1849年8月,《不列颠北方评论》(North British Review)上詹姆斯·拉瑞蒙先是为《简·爱》洗脱“粗俗”之名,最后却也认定:“如果这是女性的作品,她必定是几乎丧失了女性特征(unsexed)的女性。”⑩1850年,作者的女性身份曝光时,夏洛蒂更是污名难洗。1855年夏洛蒂过世时,各类不实消息不胫而走,辱没她的人品声誉。勃朗特老先生决定托付他人作传,还女儿公道。盖斯凯尔乃夏洛蒂的好友,又是当时文坛一位名气不小的作家,自然是绝佳人选。两年后(1857年)传记出版。盖斯凯尔告诉她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也是夏洛蒂的出版商),她的目的是不再让人们把任何“粗俗”字样的词语与夏洛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1) 盖斯凯尔为夏洛蒂正名,策略之一是突出环境因素对夏洛蒂本人的影响,把“粗俗”这众矢之的归咎于环境。同时代的评论对于《简·爱》的“粗俗”有诸多阐释,包括小说布景、人物言辞及行为举止:女主人公性情激烈、男主人公举止古怪言语不雅、男女主人公如此大胆地表达他们的情感,等等。针对这些诟病,盖斯凯尔公开解释的更多是小说的言语不够文雅以及氛围阴郁问题。盖斯凯尔在传记中反复强调,夏洛蒂一生中接触过的男性屈指可数,他们的谈吐印刻在她的脑海里,而她的良心和强烈的责任感要求她真实地再现一切。这是她为夏洛蒂去除污名的重要立论。传记出版后,原本对夏洛蒂颇有微词的《基督醒世报》在1857年7月的文评中也承认,勃朗特姐妹的兄弟布兰威尔对她们的写作产生了不良影响,让她们熟悉了邪恶的存在。(12) 二、为夏洛蒂正名之路 盖斯凯尔本人意识到,夏洛蒂小说中的不雅语词自是令人震惊,但其女性的激烈性情与反叛倾向更让维多利亚人焦虑不安、夜不能眠。对于后一点,盖斯凯尔没有直接为夏洛蒂作辩解。不少学者对盖斯凯尔的“策略”加以分析。比克(Suzann Bick)认为,盖斯凯尔在传记中试图把美德盈身的夏洛蒂本人与夏洛蒂笔下缺乏女性气质的女主人公区分开来。(13)柯尔比(Robin Colby)指出,盖斯凯尔将夏洛蒂的女性气质(主要是身形小等特征)与智性能力并置展现,拓宽了她所身处的社会文化的“女性气质”的概念。(14)本文则认为,盖斯凯尔主要借刻画夏洛蒂的责任感来强化其女性气质十足的形象。夏洛蒂的责任感中蕴含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的“女性气质”(womanliness)之根本,即在于女性坚持践行自我牺牲精神。(15)盖斯凯尔自始至终都在展现一个相当虔诚孝顺的女儿形象,尽数夏洛蒂克己、悉心承担家庭责任的细节,应是意在消解夏洛蒂小说中映现出来的女性反叛意象。这样的方法确实奏效。传记出版之后,许多评论都认为尽管小说题材“粗俗”,但夏洛蒂本人并不粗俗。(16)但是,盖斯凯尔的《夏洛蒂·勃朗特传》显然不只达到这一样目的。 盖斯凯尔在传记中描述《简·爱》的创作背景一幕,突显出夏洛蒂以及她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的境遇。传记写道,1846年8月,夏洛蒂陪父亲到曼彻斯特做白内障手术,前后大约一个月时间,两人租住在医生提供的寓所中。其间,夏洛蒂在照料术后父亲的空暇,开始动笔写《简·爱》。这个时刻映射出女性边打理家事边创作的境况,极为典型。当时女性写作的场所,大抵是起居室里的桌边一角。她们在书写时亦随时听从家人召唤,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和时间。(17)典型例子有如18世纪末的简·奥斯丁。盖斯凯尔本人也是在敞开着门的客厅里写作,随时打理女儿们和仆人的各种事情。在此意义上,盖斯凯尔不吝笔墨渲染的这一时刻,虽然看似夏洛蒂的个人体验,实是反映了当时女作家们创作时的共同境遇。在传记中,紧随这一幕的是《简·爱》成功出版,夏洛蒂摇身变为职业作家。盖斯凯尔开始把她的存在分解成两个维度,即身为女人(夏洛蒂)和作家(柯勒·贝尔)的存在,强调“两个角色有各自的职责所在——并不互为对抗;二者的矛盾也并非不可调和,但困难重重”(349页)。(18)这是盖斯凯尔在分析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命运时的基本立足点。夏洛蒂以责任感为支点,以家事为先,引得盖斯凯尔赞不绝口。 盖斯凯尔认同夏洛蒂为了家庭乐于奉献自我的精神,两人都认定这是女性最为可贵的品质。坚守孝道一直是夏洛蒂奉行的信条。她在给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的信中,很是强调自己身为牧师的女儿虔诚地履行家庭义务。她亦极力反对女性抛弃自我牺牲的精神。1851年,女性解放的著名倡导者哈丽叶特·泰勒(Harriet Taylor,后为穆勒的妻子)发表《关于女性解放》一文,激起了夏洛蒂的强烈反感。她认为“此文作者忘却了这样的事实,这世界上还有着牺牲自我的爱与无私的奉献”(540页)。她还对盖斯凯尔说道:“你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也说出了我的看法。”(540页)两人在坚守女性的奉献精神这一点上可见是有所契合。盖斯凯尔将家庭义务列为女性的首要任务,也绝非一家之言。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女作家都对此深信不疑。即便是认为上帝、永生之类的概念并不可信的乔治·爱略特,坚守基督教所倡导的职责,深信职责当先,重在践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推崇孝道的缘由可能是“把尽孝道的责任置于自我之上使女性获得了对爱的能力的自信,也使得她们在小说中描写充满爱和同情的女性责任时获得了某种权威性和说服力”。(19)此外,或许还因为,女作家们将尽孝列为自己有别于男作家的优异品质,视为女性特有的一笔精神财富,因而即使在其成为职业作家之后亦不随意放弃。 毫无疑问,盖斯凯尔笔下的夏洛蒂是位对家庭极为尽责的女性。不过,这似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普遍特征,并不能尽显夏洛蒂的独特。玛格丽特·雷恩(Margaret Lane)在20世纪50年AI写作下《勃朗特故事》(The Brontё Story),对盖斯凯尔的《夏洛蒂·勃朗特传》有所回应,其中虽列举盖斯凯尔在细节之处的误笔,但盖斯凯尔对夏洛蒂的责任感强调有加,雷恩却极为认同。雷恩亦认为,夏洛蒂从少女时代就怀有超乎寻常的责任感,这既是她生活中的重负,也是其力量之源泉。(20)透过盖斯凯尔的传记视角,我们看到夏洛蒂的非凡在于:她化解了承担家庭责任过程中潜在的不利因素,推进了自己的写作职业,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夏洛蒂还把责任感延展到写作领域,借此规避当时社会对女性写作的题材等设置的诸多限制。不过,后一要点与其说是夏洛蒂本人所为,其实更是盖斯凯尔在为夏洛蒂辩护的过程中提炼出的女作家责任观。 和许多维多利亚人一样,盖斯凯尔私下里对夏洛蒂的小说也是有看法的。(21)盖斯凯尔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毫不掩饰她对夏洛蒂小说的异见。她认为《简·爱》是本“非同寻常的书”,“不确定自己喜欢或不喜欢它”。(22)她不喜欢《雪莉》(Shirley)的情节,(23)也不喜欢露西·斯诺(Lucy Snowe)。(24)盖斯凯尔甚至认为夏洛蒂把她的“粗俗”(Naughtiness)都写进了小说。(25)“Naughtiness”在当时用语不轻。萨克雷曾对夏洛蒂说,“你和我都写粗俗(naughty)的书”(599页),这让夏洛蒂寝食难安。盖斯凯尔在传记中亦承认,“我自己也不否认她的作品中时有粗俗之处,但其它地方都是绝对高尚的”。(599页)盖斯凯尔如此坦诚,时而惹得批评家们愤慨不已。1857年5月《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威廉·洛斯柯因此质疑盖斯凯尔是否有权批判《评论季刊》上的观点。(26)但是,盖斯凯尔不认同的似乎更是夏洛蒂小说中的某些不雅言辞、阴郁气氛以及不够明快的笔调,因为她希望夏洛蒂的丈夫尼克斯先生(Mr.Nicholls)在《教授》出版前所作的修改也仅限于“删除一些措辞和词汇”。(27)此外,夏洛蒂小说中的主题都是单身女性的爱情,盖斯凯尔认为她若在《教授》(The Professor)中刻画个把“已婚女性”应该会更为有趣。(28)盖斯凯尔可能也觉得夏洛蒂的女主人公的情感都太过浓烈。不可否认,种种迹象表明,两人在写作题材等方面上是存在分歧的。然而,值得留心的是,盖斯凯尔在表达自己对《雪莉》的看法时,先是坦言自己不喜欢其情节,紧接着却说道,“她真诚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却是我极为佩服的。”(29)而且,早在1850年两人相识之初,盖斯凯尔已跟友人表示,夏洛蒂在创作中“对自己的天赋怀有强烈的责任感”,这让她赞叹不已。(30)盖斯凯尔显然欣赏夏洛蒂在写作中展现出的真诚和勇气。她虽不能完全认同夏洛蒂小说的题材,却能够欣赏其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勇气,并竭尽所能为这样难能可贵的勇气辩护。 盖斯凯尔辩护的根基是,写作是上帝赐予夏洛蒂的天分,因而她“不能避离这份额外的责任”(除家庭责任之外),“不应把自己的天赋埋没在尿布中;这天分是用以服务他人的”(349页)。盖斯凯尔亦援引夏洛蒂本人的书信。夏洛蒂说过,“我感激上帝赋予我这样的能力,我的部分信仰是志在保护这份天赋”(419页)。在分析夏洛蒂如何应对文学写作与家庭责任的矛盾时,盖斯凯尔还是采用了“基督式的准则”(Christian formula),指出女性和男性一样也有义务培育自己的天分,且应把这些天分用于建造“上帝的王国”。(31)在此语境下,夏洛蒂的写作欲望被转化成“为他人服务”的行为,披戴上利他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夏洛蒂本人并未如此强调她通过写作来服务公众的理念。紧接着,盖斯凯尔又反复用“责任感”来解释夏洛蒂写作中的“离经叛道”。她认为,夏洛蒂在写作领域也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她坚持自己有“再现真相的责任”(599页)。传记中曾摘选夏洛蒂与刘易斯的通信。夏洛蒂在信中强调自己关注现实,在写作时“坚决把自然与真相作为唯一向导”(343页)。此外,盖斯凯尔还先后列举夏洛蒂亲口提及的《简·爱》中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或见闻的吻合之处,以此证明夏洛蒂是坚持按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作的。例如,夏洛蒂不满当时的文坛“正典”中尽是些美貌女子,认为这是“错误的,甚至是道德过失”,有违现实真相,她决意要写“身形小,虽不够好看,却是有趣”的女性(317页)。盖斯凯尔还补充道,“只描述善良、令人愉悦的人在做着好事、令人愉悦的事也是可能的(但若是这样,她们根本就写不下去)”(350页)。言外之意,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可能总是“善良、令人愉悦的人”在做着“好事、令人愉悦的事”,源于此,夏洛蒂的小说中才会出现不美好的事物。而且,盖斯凯尔又撇清了这些外在事物与夏洛蒂的内在联系,强调道,这些都是外在事物在她头脑的印记,不是她“内在的观念”(349页)。有些评论曾影射《简·爱》的“粗俗”源自夏洛蒂本身,盖斯凯尔这一说显然是有的放矢。那么,夏洛蒂在描写这些外在的不美好的事物时是否会受其影响呢?盖斯凯尔说道,她只是在动笔时“让自己的手在那一时刻受到了污染,只是很浅淡的污损,而且,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在涤荡她的灵魂”(600页)。盖斯凯尔认为跟夏洛蒂相比,“没有另外一位拥有如此神奇天分的人,如她这般负责地运用自己的天分了”(350页)。盖斯凯尔的辩护之辞以夏洛蒂的“责任感”贯穿始终。 盖斯凯尔强调夏洛蒂写作时身怀强烈的再现真相的“责任感”,强调夏洛蒂书写的皆是外在事物给她留下的印象,这似乎淡化了夏洛蒂的个人意志、想象力及勇气在其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夏洛蒂自有很强的主见和勇气,这表现在她不为女性规范所困。盖斯凯尔并非没有意识到,夏洛蒂在写作中一直在努力逃避外在世界的羁绊。夏洛蒂曾向刘易斯坦言,“写作的时候,我没办法总是……想着什么是女性气质中的优雅、迷人魅力……我的作品里不写这些事情……如果公众只能容忍这样的写作,那我就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好了。”(422页)夏洛蒂和盖斯凯尔两人亦曾探讨过在写作过程中能否做到坚持不受外界的影响。夏洛蒂问盖斯凯尔是否能“做只属于自己的女性……不去考虑作品可能会引发怎样的批判或同情?……是否从未受过诱惑,想把自己笔下的角色写得比生活中的人更和蔼可亲……”(615页)虽然传记中无法找到盖斯凯尔的直接应答,但她在自己的书信里曾提及,要是在写作中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或者想到自己会给读者留下怎样的印象,她压根就不能写。(32)而且,她本人在写作中也坚持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1853年她的小说《露丝》因其为失足女正名的主题,出版后毁誉参半,有极端者竟然“烧书”,(33)有的人对她的丧失“名誉”深感遗憾(34)。盖斯凯尔私下对友人说,“我早知这个话题会惹来这样的事,但我决意要说出我的想法。”(35)应该说,是个人意志的坚持和胆识才使得她们超越时代对女作家创作领域的限制。但是,在公开辩护时,盖斯凯尔对这些因素或是暂时抛开或是轻描淡写。盖斯凯尔以贬低勃朗特的想象力为代价,来维护她们的“体面”。(36)此外,前文已说过,盖斯凯尔的另一目的可能是为了把夏洛蒂作品中的“粗俗”归咎于环境的影响。 盖斯凯尔选择用“女作家有责任再现真相”的立论,来为夏洛蒂的“离经叛道”辩护,这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巧妙地为当时的女作家争取写作上的自由权。有评论者指出,盖斯凯尔在传记中本可以如此直言,“夏洛蒂作为艺术家有权利表达她的想法。”(37)上面我们看到,盖斯凯尔在自身的创作中也是执意写出自己的想法。那么,在传记中,她为什么不“直抒胸臆”?盖斯凯尔深知当时社会尚不能宽待这样的“直言”,就像他们不能容忍夏洛蒂小说中的一些语词。因此,盖斯凯尔当时希望尼克斯先生在《教授》出版前多多删除一些不妨碍故事之根本但又“可能导致她(夏洛蒂)被误会”的小细节。(38)她预料到当时的时代尚未能接受夏洛蒂的构思,才据此提出那样的提议。盖斯凯尔在此处也采用了更为巧妙的方法。她的辩词不是女作家有“权利”说出她的想法,而是女作家有“责任”再现真相,因为她亦深知女性的“权利”一说常惹得维多利亚人焦灼不安,甚至会引得他们群起攻之。盖斯凯尔用“责任”的外衣来包裹“自由创作”的内核,部分原因是她真心相信这是女性成为作家时必须担当的责任,同时可能也因为比起“权利”来,将“责任”用在女性身上是更可为维多利亚社会所接受的话语。把“再现真相”上升到“责任”的高度,比“权利”似乎更有力量。她选择这样的辩护之词,显得婉转,但也是更为聪明隐蔽的方式,亦更能达成她的愿望——为多面的夏洛蒂赢得维多利亚人的认可。在辩护的过程中,盖斯凯尔深化了女作家有“责任”再现真相的理念,实际上也等于是在为女作家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利”。 至此,盖斯凯尔用“责任感”诠释了夏洛蒂的生活与写作。这其实亦是当时女性“为自身授权”(self-authorization)的策略的一种。(39)虽然勃朗特与盖斯凯尔的“克己”策略有所不同,但两人都借用了“责任”的概念,将它作为“满足自身的有力策略”。(40)从夏洛蒂的发展轨迹来看确实如此。以家庭义务为先,获得良心的认可,最后求得写作的自由。盖斯凯尔借用“克己”的责任话语来阐释夏洛蒂的写作行为,亦是女性在借用维多利亚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话语,让自身本来“离经叛道”的行为显得“名正言顺”。 三、正名之意义 盖斯凯尔本着为夏洛蒂辩护的目的而刻画出的夏洛蒂是否有所偏颇?盖斯凯尔版本的传记之后又有多部相当有分量的夏洛蒂传记问世,其中包括1967年温妮弗雷德·戈瑞(Winifred Gérin)的《夏洛蒂·勃朗特:天才的演进》(Charlotte Brontё:The Evolution of Genius)、1994年林朵·戈登(Lyndall Gordon)的《夏洛蒂·勃朗特:激情生活》(Charlotte Brontё:A Passionate Life)等,影响不小。后世的传记中,一个更为多面的夏洛蒂渐渐浮出水面。有评论者精辟总结道,勃朗特姐妹对虔诚之人而言是体面虔诚的传统女性,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又是悲剧的女主人公,现实主义者认为她们是自力更生但机会有限的老处女,女权主义者则把她们看作是与父权社会抗争、争取自由的先锋女性。(41)不过,上述传记在解析夏洛蒂这一人物时虽各有偏重,却是一致对夏洛蒂的责任感深表认同。盖斯凯尔笔下这位极具责任感的夏洛蒂更是深得同时代人的认可。盖斯凯尔撰写这部传记的初衷是为了夏洛蒂的声名而辩,但盖斯凯尔同为女作家,对当时女作家的处境感同身受,申辩的过程亦在探索当时女作家的安身之道。盖斯凯尔的这一创作关怀是后世传记中所缺失的。盖斯凯尔为了让夏洛蒂被了解与珍视,呈现了基本上只有一个维度的夏洛蒂。但是,这一维度(夏洛蒂的责任感)却是当时女作家得以僭越社会限制的利器。 盖斯凯尔的创作关怀无疑也决定了她展现夏洛蒂的视角是受限的,但是透过这一视角却能够看到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力争挣脱时代拘限的艰辛过程。盖斯凯尔为夏洛蒂作为作家的维度所做的辩护,有着深远的意义。她间接参与到了女作家拓展写作领域的进程中。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过程中所受的限制,借助伍尔夫的视角则可窥见一斑。伍尔夫曾不无愤怒地抱怨过,她身处的时代的女性在踏入写作领域时,要先拔除一个“幻象”,即“家庭天使”的幻象,她温顺、纯洁,不可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受到很多禁忌的限制;“家庭天使”的“幻象”束缚着女作家的表达,让她们只做规矩顺从的女人,强迫她们展现出符合女性规范的形象,所以女作家须先将其“扼杀”,才能真正写作。(42)伍尔夫所处的20世纪初尚且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更是深受这一“幻象”的羁绊。当时社会默认的规则是,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应以“家庭天使”为典范模板。19世纪40年代,许多女作家都认同她们的“本业”(proper sphere)是通过她们所写的小说来“展示”女性的“本业”。(43)但是,夏洛蒂赋予仅是卑微家庭女教师的简·爱自由表达情感的权利,置女子“本业”于不顾,她显然不是“一般”的女作家。当年,瑞格比对《简·爱》恶语相向,百般攻击。此文虽然不代表公众的普遍看法,却代表着“最恶劣”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是脱离了“本业”的女作家必须抗争的偏见。(44)女作家身处如此艰难的处境,这也促使盖斯凯尔采取婉转的方式为夏洛蒂辩护,让夏洛蒂披戴上“责任感”的外衣。在此意义上,盖斯凯尔为夏洛蒂正名,在辩护中深化女作家“有责任再现真相”的创作理念,无异于是在为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争取更多的艺术自由领地。 女性写作领域的拓展得益于女作家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伍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谈论“妇女与小说”议题时坦言,因为有了女前辈们的努力,她在写作时才可“顺利前行”、“亦步亦趋”。(45)从女作家的族谱来看,身为女性的夏洛蒂之所以能成为职业女作家,不无受益于从18世纪起中产阶级职业女作家所开辟的女作家职业之路。相应地,夏洛蒂所开辟的写作领域的新领地,又使得后来的女作家受益匪浅。维多利亚时代另一著名女作家兼批评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在1855年时即指出,《简·爱》开启了一个新传统,此前小说中绅士对淑女的敬重在这部小说的求爱情节中完全没了踪影,淑女开始要求绅士平等相待,而非屈尊俯就的周全礼待,从某种新角度看这实是“女性权利”的宣言,这部小说引来许多追随者。(46)盖斯凯尔本人就是这一传统热忱的追随者。《简·爱》所开创的先河,在盖斯凯尔的《北方与南方》的求爱情节中也有所体现,这不愧是“《简·爱》扔下的石子”,“在水中荡起的涟漪”。(47)由此可见,一代代的努力促成了女作家之路的不断拓宽、纵深绵延。盖斯凯尔,实如奈斯特(Pauline Nestor)所言,“很乐意用自己的(作家)身份来帮助其他的女作家。”(48)她通过写传记为夏洛蒂正名,亦是在为后世的女作家披荆斩棘,开拓自由之路。 ①(17)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ed.Jenifer Smi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71-72,p.73. ②④G.H.Lewes,"From an unsigned review",The Brontёs:The Critical Heritage,ed.Miriam Alo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95),p.161,p.84. ③June Sturrock,"Literary Women of the 1850s and Charlotte Mary Yonge's Dynevor Terrace",Victori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Woman Question,ed.Nicola Diane Thomp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6-34. ⑤⑧(12)Anonymous,"From an unsigned review",The Brontёs:The Critical Heritage,ed.Miriam Alo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95),p.90,p.89,p.366. ⑥⑦⑨Elizabeth Rigby,"From an unsigned review",The Brantёs:The Critical Heritage,ed.Miriam Alo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zKegan Paul,1995),pp.109-110,p.110,p.111. ⑩James Lorimer,"From an unsigned review",The Brontёs:The Critical Heritage,ed.Miriam Alo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95),p.116. (11)(22)(23)(24)(25)(27)(28)(29)(30)(32)(33)(34)(35)(38)J.A.Chapple and Arthur Pollard ed.,The Letters of Mrs.Gaskell(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417,p.57,p.116,p.249,p.154,p.404,p.417,p.116,p.128,p.503,p.227,p.223,p.220,p.417. (13)比克指出,盖斯凯尔在描述夏洛蒂与丈夫尼克斯的感情时,地似乎暗示,即便夏洛蒂有任何激情澎湃的时刻,那也都是尼克斯引发的,夏洛蒂被刻画成完全被动、顺从的妻子。Suzann Bick,"Clouding the 'Severe Truth':Elizabeth Gaskell's Strategy in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Essays in Arts and Sciences,11(1982),33-47页。 (14)Robin B.Colby,"Some Appointed Work to Do":Women and Vocation in the Fiction of Elizabeth Gaskell(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5),p.77. (15)Carol Dyhouse,"The Role of Women:From Self-Sacrifice to Self-Awareness",The Victorians:The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ed.Laurence Lerner(London:Methuen & Co Ltd.,1982),p.174. (16)例如,1857年5月,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对盖斯凯尔坦言,《雪莉》的开篇他根本读不下去,当时觉得作者是个喜好“粗俗”的人,现在知道自己“误解”了她,觉得“惭愧”,很庆幸那时没有把自己这些“错误的看法”发表出来,因为夏洛蒂对他而言简直是个“在我之上的天堂”(a whole heaven above me)。Charles Kingsley,"letter",The Brontёs:The Critical Heritage,ed.Miriam Alo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95),343页。 (18)Elizabeth Gaskell,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 (London:Smith Elder & Co.,1934).(本文后文引自此书时,不再另注明出处,只在正文中标示页码。) (19)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韩敏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59页。 (20)Margaret Lane,The Brontё Story:A Reconsideration of Mrs.Gaskell's Life of Charlotte Bronё (Melbourne:William Heinemann Ltd.,1953),p.80. (21)有学者对盖斯凯尔的这一反应耿耿于怀。例如,费利西娅·波拿巴特认定,盖斯凯尔也认为勃朗特的小说是“粗俗”的。波拿巴特进而阐释道,盖斯凯尔认为这些粗俗的东西是夏洛蒂身上的“恶魔”的映射。Felicia Bonaparte,The Gypsy-Bachelor of Manchester:The Life of Mrs.Gashell's Demon(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2),241-253页。 (26)W.C.Roscoe,"From an unsigned review",The Brontёs:The Critical Heritage,ed.Miriam Alo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95),p.356. (31)Francoise Basch,Relative Creatures:Victorian Women in Society and the Novel,trans.Anthony Rudolf(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4),p.46. (36)(41)Michael Benton,Literary Biography:An Introduction(Malden:Wiley-Blackwell,2009),p.49,p.51. (37)Felicia Bonaparte,The Gypsy-Bachelor of Manchester:The Life of Mrs.Gaskell's Demon(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2),p.241. (39)(40)Deirdre D'Albertis,"'Bookmaking out of the Remains of the Dead':Elizabeth Gaskell's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Victorian Studies,Vol.39,No.1(Autumn,1995),3页。“满足自身的有力策略”(a strategy of empowerment of gratification),德阿尔伯提斯此处转引的是哈普汉姆(Geoffrey Galt Harpham)的说法。 (42)(45)Virginia Woolf,"Professions for Women",The Virginia Woolf Reader,ed.Mitchell A.Leaska(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84),p.279,p.277. (43)(44)Inga-Stina Ewbank,Their Proper Sphere:A Study of The Brontё Sisters as Early-Victorian Female Novelists(Goteborg:Akademiforlaget-Gumperts,1966),p.41,p.32. (46)Margaret Oliphant,"From an unsigned article",The Brontёs:The Critical Heritage,ed.Miriam Alo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95),p.312. (47)Margaret Oliphant,"On 'sensational' novels",The Brontёs:The Critical Heritage,ed.Miriam Alot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1995),p.390. (48)Pauline Nestor,Female Friendships and Communities:Charlotte Brontё,George Eliot,Elizabeth Gaskel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9.标签:夏洛蒂论文; 简·爱论文; 维多利亚时代论文; 勃朗特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教授论文; 夏洛蒂勃朗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