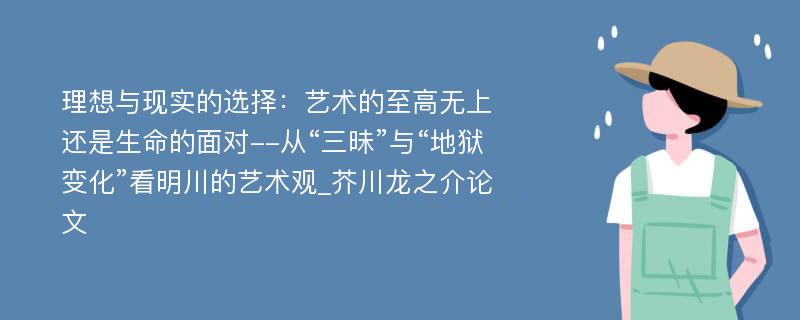
理想与现实的选择:艺术至上还是直面生活——从“戏作三昧”和“地狱变”看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直面论文,地狱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芥川龙之介生于1892年,作为跨越两个时期的日本著名短篇小说家,知识构成和文学修养形成于明治时期,文学创作则集中于大正时期。这位和菊池宽、久米正雄并称为“新思潮三尊”的作家,在日本文坛素有“鬼才”、“大正文学的象征”之称(吉田精一177)。其作品形式以短篇小说为主,兼有诗歌、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评论等。其作品风格虽然受到森鸥外的历史小说及夏目漱石思想的极大影响,但芥川从《今昔物语》、天主教文学等未开发的领域中发现素材,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确立了自己在日本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芥川与其师傅夏目漱石是当时的文学双璧”,“作为作家,芥川是大正时代最华丽的存在”(井上靖395-396)。
从1918年5月1日到22日,分20次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晚刊》上的“地狱变”,是根据日本古籍《宇治拾遗物语》卷三中的“绘佛师良秀喜欢火烧自家记”和《古今著闻集》卷十一中的“弘高的地狱屏风”的故事,加之受罗丹《地狱之门》的影响创作而成,是反映芥川早期艺术观的集大成作品。“地狱变”为佛教专有术语,指为劝善惩恶而描绘各种地狱苦状的图像。“地狱变”主人公良秀是一个孤高桀骜的画师,他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在权倾一时的掘川大公命令下,良秀全神贯注地绘制画作“地狱图”,然而良秀始终无从构思年轻男女被焚死在槟榔毛车中的核心画面。大公老爷倾心于良秀之女,想要占有却不能得逞,于是,大公老爷居心叵测地答应良秀,“槟榔毛车点燃大火,车里坐着一位艳丽女人,还要贵妇装扮”(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49)。谁知,在槟榔毛车上,锁链捆绑的却是良秀之女。眼见自己心爱的女儿任烈火烧遍全身,画师良秀虽也本能地奔向车子,但这种痛苦瞬间被艺术的激情所战胜,他很快从一个父亲的立场转为画师的立场。眼中所见,只有美丽的火焰的颜色,以及在火焰里遭受痛苦的年轻女子。良秀如愿以偿地完成了画作,然后便悬梁自尽了。
对于“地狱变”在芥川文学乃至整个大正文学中的地位,井上靖引用作家正宗白鸟发表在1927年《中央公论社》上的评论说,“在我所读的作品中,毫无疑问,我推荐这一篇是芥川龙之介的最高杰作。即使是在明治以后的文学史上,也是大放异彩的名作”(井上靖400)。“地狱变”在《大阪每日新闻晚刊》上的连载,除了得益于大阪每日新闻社学术艺术部副部长薄田泣堇的推荐外,也得益于前一年10月20日至11月4日在该刊连载的“戏作三昧”所受到的极大好评。
“戏作三昧”以龙泽马琴创作《八犬传》的故事为素材,揭示了芥川自身作为作家的苦恼和烦闷,并宣示了自己今后忠于艺术、为艺术献身的决心。该作品的题目“戏作三昧”中的“三昧”是佛教用语,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称在某方面造诣深湛为“得其三昧”,而在这部小说中是指主人公马琴专注于创作、献身艺术的精神。
“戏作三昧”通过马琴面对生活和艺术时复杂的矛盾心理,入木三分地解释了艺术家在推崇艺术至上时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和生存问题,并表明了自己为了艺术,不惜牺牲亲情、生活甚至生命的决心。而其后的“地狱变”通过极端化的人间悲剧形式,描写了生活中的权利与艺术的冲突。无论是“戏作三昧”还是“地狱变”,都是描写了艺术家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中的种种矛盾以及取舍。在两部作品中,都蕴涵着芥川龙之介一贯探究的问题:为了艺术是否可以牺牲一切?本文通过“戏作三昧”和“地狱变”中创作主体与接受对象的隔阂、创作题材与生活压力的矛盾、文学创作与文学管制的博弈、艺术自律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等内容的分析,认为在芥川龙之介早期文学创作思想中,其艺术观处于推崇艺术至上还是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纠结中。
一、创作主体与接受对象的隔阂
“戏作三昧”一开始就描绘了一个最能反映众生相的场所——日本澡堂中的景象:在“哗哗的浇水声和木桶的碰撞声”中,有“聊大天哼小调的”,“从账房那边还不时传来木铎声”,在此可以看到“洗澡客”、“商贩乞丐之流”的俗众。在一片杂乱中,六十开外的主人公龙泽马琴“斯斯文文挨在角落里,静静地搓着身上的污垢”(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76)。当老人怎么都搓不出什么来的时候,忽然勾起了他的迟暮之感。回想自己“为谋生疲于奔命,几十年来还苦于不停地写作,弄得身心疲惫不堪”(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76)时,有一种期盼“解脱烦恼,安然寂灭之感”(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76)。但马琴即使感到创作的疲惫,也还是看不起和歌、俳句这一类的艺术,“在马琴眼里,那是第二流艺术”(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78)。而“马琴的想象,向来带点浪漫色彩”(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0),但这却被澡堂中的俗众说成“全是抄人家的冷饭”(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1),“马琴写的玩意儿,全靠耍笔头子,肚里没有一点货色”(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1)。俗众喜欢的是描写世俗、猎奇的“了不起”的十返台一九和式亭三马。尽管听到了俗众的这些评论,马琴还是尽量不让自己落入这种迎合潮流的创作,不管俗众怎么评论自己的作品,马琴认为“顶多让我不自在罢了”(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4)。
1915年4月,芥川龙之介与吉田弥生的初恋因受到家人的极力反对而走向失败,芥川也通过这失败的恋爱,认识到了人类的丑恶和自私。11月,根据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罗生门”发表在《帝国文学》上,但没有引起太多反响。12月初,在芥川的大学同学、夏目漱石学生林原耕三的介绍下,和久米正雄一起出席“漱石山房”每周四的文学聚会,投在了漱石门下。1916年2月,同样基于初恋失败经历创作的“鼻”发表在第四次创刊的《新思潮》创刊号上后,由于受到文学大家夏目漱石的赞赏而在杂志《新小说》上再次刊登,迈出了登上文坛的第一步。10月,在当时被称为步入文坛的敲门砖杂志《中央公论》上发表“手巾”后,芥川在对原善一郎的信中称:“这时我也能够向文坛交入场券了”(森本修387)。11月,在畔柳都太郎的介绍下,他作为英语老师进入横须贺的海军机关学校工作。这些成就,让年轻的芥川感到无上光荣,也使他对海军机关学校教师和作家的双重工作做得得心应手。但是,此后的芥川,“也慢慢感觉到了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辛酸”(宫坂觉25)。当然,这种心酸,固然有艺术创作所带来的经济价值难以维系家庭生活的无奈,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作家,作品不被理解更是无比“辛酸”的事。这种作品不被接受的“辛酸”,充分地体现在“戏作三昧”中澡堂内的俗众的评论中。
如果说“俗众”对自己作品不接受还可以理解的话,对芥川来说,更加难以忍受的是从全国选拔来的海军机关学校的优秀学生也对文学不理解,因此芥川感到的不是授课的愉快,而是一种苦恼,在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1919年3月,芥川毅然辞去了海军机关学校教师的职务,转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结束了那段不愉快的双重生活,而专心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戏作三昧”以马琴为媒介,充分表现了芥川为了创作而体验到的生活的“辛酸”,同时也体验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接受主体之间的隔阂。芥川即使面对着不理解真正文学、而以猎奇为文学标准的俗众,也仍然“辛酸”地维持着生活,维护着艺术创作的尊严。
二、创作题材与生活压力的矛盾
“戏作三昧”中澡堂的俗众,直截了当地表示出喜欢世俗的、猎奇的作品,而对马琴散文作品不屑一顾。从澡堂回到家中的马琴,一进门就遇到了“抽一管细细的银烟袋,白脸膛上油光光的,拿捏着一股子劲儿”(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5)的出版社老板和泉市兵卫,他坐在“没有任何像样的装饰”(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5)的马琴书房内,为的是请马琴“赐稿”。市兵卫一方面是向马琴索要适合妇孺阅读的通俗“长篇”,以及像为永春水之流“为赚钱,投读者之所好,写些艳情小说供他们消遣”(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9)的快速制造的作品;一方面是向马琴提供以鸡鸣狗盗为内容的创作素材。市兵卫“凡提到作家名儿,不管对谁,从不加敬称”(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8),而其在马琴面前,“他的表情显得非常下流”(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9)。马琴对出版商市兵卫“心里不仅不痛快,还觉得受了胁逼”(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89),他最终对市兵卫下了逐客令。但是,马琴立即又觉得对市兵卫下逐客令,“不是什么高尚之举”(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0),虽然是被逼的,但“那么做,只能说明自己也变得卑劣起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1)。不仅是出版商,即使是自己的读者,也骂马琴的《八犬传》和《巡岛记》“写得又长又臭”。自己的文学创作,既不符合出版商的要求,又不符合读者的胃口,这“又引发了马琴一种说不出的寂寥之感”(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1)。
马琴为了创作,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甚至在书房中没有任何装饰。但对于文学创作,他反感出版商要求的那种以猎奇为内容、以俗众为对象、以速度为利益的要求,并最终以逐客令的方式表达了对想利用自己发财的出版商的愤怒。对于沉迷于低俗小说而看不起自己作品的读者,马琴也表达着一种讽刺和憎恨。在马琴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中,也始终存在着这种追求艺术和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当马琴在创作中文思枯竭时,“禁不住怀疑起自己的真实实力来,不免忧心忡忡,有种不详之感”,而这种忧心,又“益增他孤独落寂之感”(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8)。在家庭生活中,“阿百和阿路婆媳俩正对着灯,在做针线活”(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02),“身子瘦弱的宗伯,坐在一边,一直忙着搓药丸”(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02),就是在这种艰苦的家庭生活中,马琴一边承受着家人“又赚不了几个钱”(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02)的唠叨,一边进行着创作。这种痛苦,只有在听到孙子告诉自己“观音说用功吧!别发脾气!而且要好好儿忍耐!”(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01)的天真话语时,马琴才有一种恍惚悲壮的感激,也让自己充满了继续创作的激情。芥川借马琴与出版商在创作题材方面的冲突,以及家庭生活困苦的情景描写,表明了自己即使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也会坚持艺术至上的文学创作理念,不屈服于生活压力和出版商的利诱。这种在与现实生活对决中的悲壮创作,达到了“拂去日常性残渣的艺术三昧的境界”(宫坂觉26)。
三、文学创作与文学管制的博弈
在现实生活中,文学创作的内容和主题除了受到出版商的胁逼外,还有一道更难逾越的坎,那就是无论是侧重内容的文学作品,还是侧重形式的书画作品,都遭到愚昧无知的官吏对文学的严格“审查”。“戏作三昧”中提到“书籍审查大人专横到了极点”,不但不能在小说中写“当官的受贿”,而且“只要涉及男女之情,不管什么书,立马就说是淫书”,小说中也不能写“探监人去送吃的和穿的”之类的内容。虽然有关对官吏审查书籍的内容是在和画家华山轻松愉快的对话中描述的,但是两人友好的对话,更加衬托出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管制的矛盾。马琴一句“审查大人横行的世道让我灰心”(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5),表达了马琴对愚昧专横的官吏的愤怒和对现实世界的无奈。但是,面对这种现实,马琴和华山道出了自己的心声,“那咱们还是拼命吧”(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6),“年轻人首先得明白,活下去才是正经。想拼命,什么时候都能拼”(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6)。为了活下去,马琴们不得不一边艰苦地进行着文学创作,一边以随时拼命的态度与官方文学管制抗争。
在“地狱变”中,也始终充斥着艺术创作与官僚统治的博弈。掘川大公老爷在诞生之前,“大威德明王曾在其母枕边显灵”,生后的掘川府邸,“那规模简直难以形容”,但“荣耀华贵”的掘川大公老爷,“更多考虑的是平民百姓”,具有“百鬼夜行,他也不会有太多麻烦”(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29)的“威望”;而画师良秀是一个“身段低矮,瘦骨嶙峋,让人感觉是一个心术不良的老头儿。……良秀举动像个猴子,所以送了他一个诨名——猿秀”(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30)。良秀不但“相貌猥琐”(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33),而且还有一些“吝啬”、“贪婪”、“无耻”、“怠惰”的怪癖,但“良秀在画坛占有很高的地位”(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33)。
就是这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大公,在得不到良秀的女儿时,却以残忍的方式将其烧死在槟榔毛车上,并和“身旁的侍者们诡秘地微笑”(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52)。当这种残酷的方式受到各方的指责时,大公却说“大公的真正意图绝非要烧车杀人,而是要惩治屏风画师良秀的邪恶根性”(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55)。而良秀“一旦涉及到绘画就是一个偏执狂”(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49),看到女儿在槟郎毛车上被烧的景象,虽然“惊吓得几乎昏厥过去”(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53),但当看到那呼啦呼啦地熊熊燃烧的火车时,良秀“那皱纹密布的脸上却浮现出令人费解的光辉,宛若恍惚之中的法悦(佛)光辉。他仿佛忘记了大公的存在,双手紧抱胸前伫立于廊下。那情形似乎令人感觉——美丽的火焰和烈焰中受难的女人身姿,令之产生了无限的喜悦”(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55)。
官僚的统治难以压抑住艺术家对艺术的无限追求,而这种对艺术的无限追求,也会使地位高贵、貌似善良却内心险恶的诸如大公之流的统治者“脸色铁青,嘴角翻沫,面目全非”(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55)。面对艺术,相貌和心灵都“猥琐”的良秀却让人肃然起敬。作品通过这种极端化的人间悲剧,凸显了权利与艺术的对峙。芥川在两篇作品中都融入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管制的博弈内容,暗示了自身的艺术创作,是在与官僚统治斗争的过程中艰难前进。
四、艺术自律与功利主义的冲突
在“戏作三昧”中,马琴承受了俗众、出版商、读者的数落之后,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表现和文学内容,作为道德家和艺术家的马琴,在文学创作方面,始终处在注重道德内容还是文学形式的思想冲突之中。在马琴心里,“‘先王之道’赋予艺术的价值,同他在感情上想赋予艺术的价值,想不到相差甚远”(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2)。面对着马琴的朋友华山所创作的“寒山拾得像”,马琴和华山对艺术是侧重于形式还是内容进行了探讨。两人共同的观点是:不管是侧重艺术的形式还是内容,对艺术要进行不断的探讨,虽然这种努力“充溢着只有他俩才知道的寂寞”(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5),但“与此同时,这寂寞同样又使宾主二人感到一阵强烈的兴奋”(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295)。
马琴一边进行着《八犬传》的创作,一边思考着文学创作是侧重道德说教的内容、还是侧重文学形式——“为艺术而艺术”这个问题,即对文学自律与功利主义如何取舍的思考。
艺术创作在和官僚统治的斗争中尚可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在艺术创作中,感情的天平几乎让人难以把握尺度。“地狱变”中“像似野兽般令人恶心”的良秀,却有一个“乖巧可爱”、“天资聪颖”、“善解人意”、“国色天香”的女儿。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朝画界以“专横”、“傲慢”著称,“刚愎自用”,“却也保留着唯一的人类情爱”画家良秀,对“身为侍女的独养女儿,表现出近似疯狂的怜爱”(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34)。但是,在面对艺术时,“为女儿身心憔悴的良秀一旦开始了绘画,便不再惦记着去见女儿”(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37)。对于自己的弟子不理解自己为了完成“地狱变屏风”而噩梦连连时,他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孤寂之色”(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38)。为了完成“地狱变屏风”,良秀狠毒地用铁链锁缚住心爱的弟子,使弟子“肥壮躯体里的血液循环不畅,以至脸庞和躯体全都憋得通红”(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40)。让猫头鹰“凶猛地冲着弟子的面门扑飞而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42)。但这些残酷的实践,都没有成就艺术品“地狱变屏风”,这使得“老爷子竟莫名其妙地多愁善感起来,时常躲在无人的地方嘤嘤哭泣”(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44)。最终在“为了实现那般描写,就须体验那样的恐怖情景”(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1:348)的创作信念的驱动下,在被大公恶毒私欲的利用之下,良秀以牺牲女儿为代价,完成了那著名的“地狱变屏风”。
虽然良秀完成了“地狱变屏风”,但在与现实社会的抗争和与弟子、女儿的感情纠葛中,最终选择了悬梁自尽。“在艺术上,良秀是成功的,但在现实中,他却失败了”(高慧琴13)。这种艺术与现实的冲突,实际上既是现实生活中始终困扰芥川的问题——选择艺术还是面对现实,也是芥川毕生挣扎的问题。芥川在1919年发表于《新潮》杂志8月号上的论文“艺术及其他”中说道:“为艺术的艺术,一步走错就会掉进艺术的游戏论中。为人生的艺术,一步走错就会掉进艺术的功利论中”(芥川龙之介,“艺术与其他”24)。芥川龙之介在这两篇小说中,在思想上始终充斥着文学自律与功利主义的冲突。从两篇小说内容上看,芥川努力克服艺术为道德服务的功利主义艺术观,维护着艺术自律,但这种冲突却折磨着芥川的内心。
如果说“戏作三昧”反映了芥川在艺术和现实生活的斗争中,以随时准备为艺术拼命的觉悟中,悟得了“艺术三昧的境界”的话,那么“地狱变”中的主人公则以“为了艺术的完美,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女儿的生命”(高慧琴12)的思想超越,把“艺术三昧的境界”推到了极点。但当把艺术推向极致之后,主人公良秀却在与现实社会的抗争和与弟子、女儿的感情纠葛中,最终选择了悬梁自尽。通过两篇小说所反映的艺术创作观演变的历程来看,芥川龙之介在文学创作初期推崇艺术至上,但同时也感受到了难以脱离社会现实而进行艺术创作的生活困境。
五、从“戏作三昧”与“地狱变”看芥川的艺术观:艺术至上还是直面生活
“戏作三昧”中的主人公龙泽马琴,实际上是芥川龙之介自身的写照,“从《戏作三昧》主人公龙泽马琴的背后可以看到龙之介”(宫坂觉25)。而“地狱变”中的良秀,也同样是芥川的写照。如果说龙泽马琴还显示出芥川在面对艺术和现实时处于摇摆不定的心态的话,那么“地狱变”中画家良秀的自杀,则反映了芥川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各种矛盾中无所适从的悲剧境地。推崇艺术至上的浪漫主义者总是“把艺术看作是解决一切矛盾和带来和解的最自然的道路,这样他们的社会理想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陷入悲观主义乃至对死亡的礼赞”(赵宪章391)。因此,芥川虽然毕生都在追求艺术至上,但在各种难以调和的悲剧性矛盾和冲突中,他对艺术至上主义是悲观的,最终走向了自我的毁灭。
对于浪漫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韦勒克和沃伦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相信‘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的出现是因为艺术家感到:他们的目标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艺术家一定是十分憎恶他们的社会,而且一定是认为他们的社会没有改变的希望”(转引自韦勒克沃伦109)。为了艺术,芥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家庭。但芥川龙之介为了艺术,又道出了“艺术家为了创作非凡的作品,在一定的时候或一定的场合下有可能会把灵魂出卖给恶魔”(高慧琴26)的无奈,描绘了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的悲剧。
虽然有学者认为芥川的文学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生活,但从芥川在“艺术及其他”中所说的“当我们奔向艺术完美之路时,有某种东西会妨碍我们的前进”(芥川龙之介,“艺术与其他”25)。由此可以看出,芥川是关心生活的。关口安义也认为,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停留在“认为他是一个多病压抑的青年,是一个对时代和社会不关心的青年,更加强调其厌世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但实际上“通过中国视察之旅和关东大地震,他绝不是对时代和社会不关心”(关口安义18)。芥川不但关心生活,而且深深感受到了生活对于艺术创作的压力,既有外部社会的压力,也有家庭生活的压力,而这种种压力,让芥川感觉到的是“寂灭之感”、“寂寥之感”以及“孤独落寂之感”,最终陷入了“孤独地狱”。“戏作三昧”描绘了艺术家与出版商的买卖关系,这种艺术家和买主的合同关系,虽然能保证艺术家不受市场的冲击而安心创作,但这种合同本身把艺术品变为定做的商品,使艺术家以一定程度的创作自由为代价来进行营生。“地狱变”的文学主题看似是追求纯艺术问题,实际上在更深层次上是反映追求艺术的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为了艺术,甚至不惜牺牲女儿的生命。
一直以来,研究者认为“《戏作三昧》与《地狱变》是阐述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至上主义思想的重要作品”(占才成171)。而丸谷才一认为:“芥川是浪漫主义的,或者难以理解。但是,从他对艺术概念的态度来看,显然说明芥川是浪漫主义的。认为艺术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是浪漫的大正文坛的基本主张,从《地狱变》及其他作品可以看出,他被这种倾向所支配。……但是,我觉得大正文坛最终被引向了人生论式的艺术观,容易迷失方向”(101)。实际上丸谷在这里虽然没有再进一步说明“被引向了人生论式的艺术观”的具体所指,但从芥川一生的创作来看,当芥川开始对社会不满,但又无能为力时,他感到了对现实生活的迷茫,对理想的幻灭,对政治的无能为力,从而开始了自己“人生论式的艺术”,并因此而成为大正时期“私小说”的代表,“为不安和危机感所苦恼的芥川开始转向并维护起私小说来”(柄谷行人170)。从“地狱变”和“戏作三昧”两个作品所反映的芥川的艺术观来看,青年时期的芥川,对于艺术,始终面临着矛盾冲突的苦恼和烦闷:追求艺术至上还是直面生活?芥川后期的文学创作转向私小说,也是其由追求艺术至上主义向描写现实生活转变的软着陆,这种软着陆,源于反映其艺术观的早期作品“戏作三昧”和“地狱变”中,就通过创作主体与接受对象的隔阂、创作题材与生活压力的矛盾、文学创作与文学管制的博弈、艺术自律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等这些内心斗争,曲折地映射出芥川对艺术至上主义的悲观心境。
两部作品,都以佛教术语命名,也充分体现了芥川在种种压力和矛盾的心理下,对于道德与艺术的思考,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面对现实,维护社会固有的道德,亦或是选择虚无的佛教界表达自己的心情。面对这些矛盾,芥川选择了假借历史来表达心情。究其假借历史题材的原因,是“芥川的这些作品,虽然因取材于古典,时间上是古代而被称为历史小说,但却并非直接描写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而是让古典作品中的人物具有近代的自我意识,尝试新的芥川式的解释,在这一点上,虽然穿着历史的衣裳,却和现代小说没有区别”(井上靖401)。“戏作三昧”和“地狱变”就是假借历史,表达了青年时期芥川对自己艺术和现实生活的思考。
“戏作三昧”和“地狱变”在芥川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研究芥川艺术观的宝贵资料,“《戏作三昧》和《地狱变》是表明了以艺术家为人生价值的芥川的真实一面。虽然在这两部作品中也有局限于艺术家生活的狭隘性,但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反映了他的真实生活,所以可以说,与现实对决的残酷性,都集中表现了出来”(和田繁二郎295)。而我们还可以从作品中深刻体会到芥川对艺术和现实生活的矛盾心理:艺术是至上的,真正的艺术家应该用毕生的精力追求完美的艺术。但在现实中,读者、商人、官僚、甚至是家人都不能容忍这种超脱世俗而追求艺术理想的人的存在。在文学创作中,芥川既反对功利主义,又不得不面对文学的功用效果;既拒斥现实,又不得不正视现实。这种文艺思想的驳杂性,始终困扰着芥川:是艺术至上还是直面生活。在这种隔阂、矛盾和冲突中,带着对生活的失望和对艺术创作的苦恼,1927年,芥川匆匆以年轻的生命撒手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