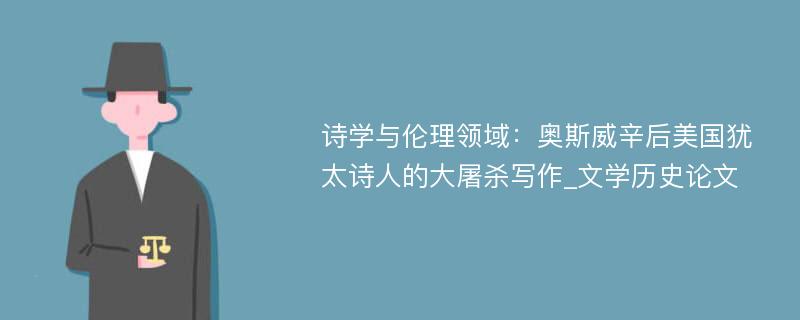
诗学与伦理共筑的场域——后奥斯威辛美国犹太诗人的大屠杀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诗学论文,美国论文,伦理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屠杀是美国犹太小说中一个重要主题,艾·辛格、马拉默德、索尔·贝娄等美国犹太小说家均曾以此为背景或者主题创作过小说。与大屠杀小说引起的热议不同,大屠杀诗歌似乎很少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美国犹太诗人也频频触及这一主题①。但是,这些诗人们并没有亲历过集中营和大屠杀,因此属于典型的后奥斯威辛写作。美国成为他们躲避这场犹太民族灾难的避难所,但他们本身的不在场却成为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并因此使他们产生了复杂的大屠杀书写焦虑心理。大屠杀本身惨绝人寰的特殊性、书写者不在场的心理焦虑、书写者族裔文化身份和政治立场、书写时间与事件本身的距离等等因素,使得后奥斯威辛大屠杀书写变得异常复杂。简言之,美国犹太诗人的后奥斯威辛书写面临着“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忘”还是“不忘”的多重困境。
一、美国犹太诗歌的大屠杀主题
奥斯威辛难以被直接表现的原因在于,这一极端事件本身已经超出了任何道德和伦理底线,“是连施暴者都觉得只能做不能说的行为”②。面对这场根本不能用人们习惯的方式来阐释的历史事件,任何形式的表述似乎都存在着简单化的危险。这场有悖于人性的浩劫带来的是文学表达上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大屠杀和后大屠杀书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的‘基本教养’”③;另一方面,在反复被书写的过程中,大屠杀书写逐渐“散发”出一种麻木不仁,并“把人们的想象力束缚起来,逐渐使之僵化老套”④。其中,对于大屠杀从文字到图片、从声音到图像铺天盖地的表达最不满的是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他说:“文化批评认识到自己面对着文明和野蛮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威辛之后写作诗歌是野蛮的。”⑤这句“极端”的反思性文字在无数次被引用之后,也不幸成为关于奥斯威辛叙述的套话,成为大众文化话语建构出来的又一“陈词滥调”。然而,无论是大众话语对大屠杀疯狂的文化生产,还是有良知的人们对它小心翼翼的接近,它作为一个“存在”而存在着,更作为文学想象而存在着。在这样的文学想象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经历这场灾难,而这场灾难也在文学想象中被重新塑形。正如耶鲁赛尔米所言,在犹太集体想象中,大屠杀形象“不是被历史学家的铁砧,而是在小说家的坩埚”中被塑造的⑥。
与大屠杀在小说中的“热度”相比,这一现代悲剧在诗歌中则显得有些落寞,却也因此包含了更大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诗人们在触及这一主题时颇多踌躇。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奥斯威辛之后写作诗歌是野蛮的”。此后协商和质疑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其中有三个人最具代表性:一是犹太历史学家丹尼尔R.斯沃兹,他说:“事实上不写诗歌是野蛮的”⑦;二是评论家、学者芭芭拉L.艾斯垂恩,他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作同样的诗歌是野蛮的”⑧;三是诗歌评论家克里斯托弗·菲尼斯克,他说:“奥斯威辛之后只有诗歌”。这几种不同的表述代表了人们对诗歌所承载的文化和情感内涵的不同理解。这四种表述看似彼此矛盾,却源自同一个出发点,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对象。总而言之,哲学、历史和文学都转向了诗歌伦理价值和伦理意义的思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表述代表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轨迹:从质疑诗歌该不该触及大屠杀主题,到思考诗歌如何呈现这一主题,再到完全肯定诗歌呈现这一人类灾难的独特价值。美国犹太诗人艾伦·格罗斯曼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我们时代发生的某些事情代表了文化实践的含义和文化的承载。这些事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知识、一种启蒙、一种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经验。这些发生的事情冲击着人类的价值观,也冲击着诗歌。
无论大屠杀文本的表达方式如何不同、风格如何各异,贯穿所有大屠杀书写始终的是对这一极端历史事件本身及其呈现方式的思考和再思考,即对这一人类悲剧所蕴含的人性善恶、社会机制、历史渊源等层面的深度反思,对导致这一悲剧的人类伦理谬误的检视和修正。可以说,大屠杀文本无一例外是作家的写作策略和伦理选择的产物,是在诗学和伦理双向坐标的不断修正和描画中形成的曲线图。对美国犹太诗人来说,“写作成为了祭奠、净化、赎罪、历史和对人类的情感坚持的道德义务”,更是“作为对野蛮和冷漠的抵制”⑨。换句话说,大屠杀书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意义的救赎行动,这是大屠杀书写与众不同的核心内涵。不容忽视的是,美国犹太诗人往往是在这场灾难尘埃落定多年之后才审慎落笔,属于典型的“后大屠杀”诗歌创作。这类诗歌强调其与这一事件本身以及幸存者想象中的自我意识的关系,成为美国诗歌一个若隐若现的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诗学理念的引领下,大屠杀这一现代人类悲剧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轮廓和内涵。在美国犹太诗人的诗歌中,大屠杀不是一幅画,而是一扇窗,从他们不同的打开角度,大屠杀呈现出多元化的表象和内涵。其中,雷兹尼科夫的《大屠杀》、格罗斯曼的《娼妓们的银钱》和卢森伯格的《大屠杀》是后奥斯威辛大屠杀诗性书写的三个代表性文本,而三位诗人恰恰是三种风格迥异的美国犹太诗学——“客体派”诗学、“神之名义”诗学和“民族志”诗学的代表人物。三位美国犹太诗人正是在三种不同诗学理念的引领下,不同角度地打开了这扇窗,并完成了风格各异的大屠杀书写。同时,三位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大屠杀呈现的伦理维度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大屠杀诗性书写的双向坐标。下面即以三位诗人和他们的代表诗作为例,考察后奥斯威辛美国犹太诗人所面对的“沉默”还是“言说”、“言说”还是“过度言说”的悖论以及诗人们应对该悖论的不同诗学策略。
二、美国犹太大屠杀诗歌的诗学策略
后奥斯威辛时期的美国犹太诗人在处理大屠杀问题上明显不同,他们在大屠杀叙事中充当了全然不同的角色:以雷兹尼科夫为代表的“客体派”诗人充当了沉默的见证者,艾伦·格罗斯曼基于他所倡导的“神之名义诗学”,充当了虚无的预言者;而杰诺姆·卢森伯格则出于“民族志”诗学的理念,充当了巫术的萨满、亡者的招魂者。不同的诗学策略在呈现大屠杀主题时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客体派诗学”(Objectivist Poetics)是美国犹太诗人朱可夫斯基首先提出的,但毫无疑问,雷兹尼科夫是最具代表性的“客体派”诗人。事实上,朱可夫斯基提出“客体派”诗学的雏形,正是以雷兹尼科夫为参照对象的。“客体派”诗学观的核心因素是“真实”(sincerity)和“物化”(objectification),而要达到这样的诗歌境界就要摈弃“控制欲更强、更暴力的个体介入”,“避免在诗歌中投射过多的主体性”。⑩比照这一诗学原则,《大屠杀》(Holocaust)应该算是“客体派”诗学证词般的张力发展到极致的代表作。首先,大屠杀是“客体派”诗歌理想的选题和对象,因为这一题材是“即时的、事实的而不是象征性的或者先验性的”(11);其次,雷兹尼科夫呈现这一人类悲剧的方式保留了该事件的完整性和本真面目,使得这一事件没有被“主体的阐释暴力”所侵犯(12)。细读诗歌文本不难发现,诗人的主观意图和在场性似乎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法庭证词的客观和冷静。这个由客观的残骸堆砌的文本越发使得读者面对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类灾难目瞪口呆:“德国人第一天进入/那年轻女人居住的城市/他们把犹太男人带走,/命令他们用手/清理街道上的垃圾。/然后犹太人被迫脱光衣服/每人身后都有一个德国兵用刺刀逼着/命令他奔跑;/如果犹太人停下,/他的后背就会被刺刀刺上。/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流着血回家了——/其中有她的父亲。/……/他们被枪杀/躺在地上/躺成一种图案:/犹太人和波兰人/五个一组/而且犹太人和波兰人是分开的。”(13)这首长诗是根据美国政府出版的《纽伦堡军事法庭罪犯审判》的材料和对战犯艾希曼(Eichmann)审判的26卷本笔录中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写成的。运用法庭审判进程的副本,这首长诗摈弃了修辞性语言和诠释性修辞框架,如法庭证词一般,没有轻率的结论,也没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大屠杀》对传统的诗歌美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读者在阅读这样的客观残骸的时候不得不暂时忘记我们对于文学文本和历史呈现的种种理想期待和审美需求。阅读这样的诗歌,读者不得不以一种宗教祈祷的虔诚和法庭见证人的严肃保持缄默。正如乔治·斯泰纳所言:“当已经说了那么多之后,现在最好的,可能,就是沉默;不再为不可言说的[东西]增加文学和社会学争论的琐事。”(14)
在心理、艺术、真实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雷兹尼科夫的叙述选择了一个既有别于“见证者”叙述又有别于作家叙述的方式,一种“证词”的见证方式。讲述人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见证者和旁观者之间的复杂身份,是雷兹尼科夫作为一个不在场的犹太人特有的心理。从诗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在叙事者身份的二元对立中形成的沉默诗学体现的正是“客体派”诗学理念的精髓。朱可夫斯基曾经高度肯定雷兹尼科夫的诗歌,认为他“以事物的本来存在的方式去思考”事物的细节,并以客观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词语的组合体现的是它们对应的事物的天然组合,没有外界的暴力对它们的天性予以干扰(15)。的确如此,雷兹尼科夫力图以大屠杀“本来存在的方式”,以证词的细节呈现一个尽可能客观的世界。事实上,雷兹尼科夫沉默的“证词”见证悄然传递出的是诗人本人对大屠杀的伦理姿态。“见证者”叙述是个人的、微观的,在一遍又一遍的个人叙述中,大屠杀似乎逐渐汇集成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集体事件,成为一个“单元素集合”(16)。对大屠杀的这种理解使得这场浩劫变成不会再重复的片段和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独一无二的历史谬误。而以这种方式看待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把大屠杀“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而这种简化是十分“危险”的(17)。基于此,雷兹尼科夫为自己选定的介于见证者和旁观者之间的复杂身份则把犹太人的个人微观历史与宏大历史结合起来,从而使大屠杀既呈现出个人性、偶然性、片断性又同时表现为社会性、必然性和连续性。而这也是“客体派”诗学的终极理想。
从美国犹太诗人的家谱来说,艾伦·格罗斯曼应该尊称雷兹尼科夫为前辈。不过,格罗斯曼颇有影响力的以大屠杀为主题的诗集《娼妓们的银钱》的问世却远远早于雷兹尼科夫的《大屠杀》。格罗斯曼认为,犹太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与非犹太诗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世俗诗人要负责的是世界,而犹太诗人要负责的是上帝。基于此,格罗斯曼提出了“犹太诗歌作为神之名义的计划”的论断,并进而形成了他的“神之名义诗学”(Theophoric poetics)(18)。格罗斯曼认为,无论是诗学的还是神学的,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召唤:在前一种情形下,赫西奥德遇到了缪斯,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的女儿;在后一种情形下,亚伯拉罕听到并听从了上帝的两次召唤(19)。在格罗斯曼的世界中,犹太诗歌不是从种族的角度诠释的,而只有当犹太文化被它的神圣历史塑形,犹太诗歌才与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联系起来。可以说,格罗斯曼“神之名义诗学”是诗人对犹太人群体特点的一种无奈的诉求行动。阿伦特曾说:“与其他所有群体相比,……犹太人处于虚空之中。”(20)民族群体性的历史流散状态使得犹太人“外在于社会结构”,处于“国家和社会的虚空之中。”(21)这种状态使得犹太人自然转向宗教,犹太教也因此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宗教意义。格罗斯曼的“神之名义诗学”集中体现的正是犹太教的“一神”思想和“契约观”,(22)是诗人把犹太诗歌作为宗教想象的一种全新尝试。
《娼妓们的银钱》(23)出版于1961年,惊魂未定的人们还没有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犹太人更是还没有来得及把鲜血拭干。此时的人们需要的不是反思,而是灵魂的慰藉。格罗斯曼“神之名义诗学”正是在现实世界的荒漠中诞生的一片心灵的绿洲。基督教的挪用策略使诗人暂时产生了一种浪漫主义诗人般的使命感,仿佛成为世界的命名者和预言者:“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要净化哭声,我将哭泣,/首先为所有人,/用无声的星星的陌生预言,/一个安静的时刻的孩子然而听到了声音,/虚无的预言者和使者。”(24)在人类的巨大灾难、道德维度全面崩溃和神性缺失的重重困境中,诗人及其诗歌的意义在于预言想象的转化力量。格罗斯曼意识到,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写作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诗歌可能是屈指可数的能够帮助人类深入反思大屠杀这一人类悲剧的崇高手段之一。他的诗歌要实现的是崇高的希望,然而,他也意识到,要想实现这一希望,“在西方文化中可供头脑使用的表现体系对于表现历史的重大事实已经不够了,而现在大屠杀就是符号之一。”(25)在格罗斯曼的诗歌中,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鲜明的主题,而是一个解读犹太人苦难历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是一个定位犹太人现代生存状态和预言犹太未来的符号。格罗斯曼似乎从来未曾描写大屠杀血淋淋的场景,甚至连大屠杀这样的字眼也很少提及。
格罗斯曼在这场神学一象征的阐释中,书写的是一种神秘的超验体验,而诗人本人则充当了阿伦特所定义的“虚空”的预言者和使者。格罗斯曼那飞舞着无数犹太宗教符号的诗歌文本与宗教语言有着异曲同工的效应:“是参与的、呼求的,而不是经验的、超脱的”,格罗斯曼用宗教的语汇“这个审视镜头来审视世界,并按照这种传统发布的模型和命令来规制生活。”(26)格罗斯曼是在犹太人理解审判与拯救、原罪、罪与罚的视野中创造他的“神之名义诗学”的,诗歌是他祈祷的方式,也是他对抗奥斯威辛幻象的武器。作为犹太作家,格罗斯曼似乎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呈现出人与上帝的对话的同时,也呈现出了自己对这个对话的解读。作为自我命名的“虚无的预言者和使者”,格罗斯曼宣称,诗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大屠杀的灾难,依旧是能够净化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人的哭声,甚至能通过合适的净化仪式来净化谋杀者。与格罗斯曼的“崇高”诗学理想相伴的是他的“高雅格调的文体”(27),这也与“客体派”诗歌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格罗斯曼很少触及犹太人日常生活的细节,尽管有时他也会在一个当代背景中涉及某一特殊的历史时刻或地点,也总是更加倾向于借助诸如《塔木德》或者《塞西拿》中的先哲作为传统原型人物的象征性修辞的表达。诗人仿佛是犹太先哲附体,在诗歌中阐释着神圣,又在神圣的视野中书写着诗歌。
另一位对大屠杀进行诗性书写的犹太美国诗人是颇具影响力的卢森伯格。他不但是一位诗人,还是行为艺术家、翻译家和人类学家,而他所命名的“民族志”诗学更使他的名字与美国当代诗歌和人类学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格罗斯曼的“神之名义诗学”在卢森伯格眼中恐怕有僭越之嫌了,当然,他也绝不会推崇雷兹尼科夫沉默的见证。作为犹太先锋诗学和“民族志”诗学的代表,大屠杀写作成为卢森伯格全面体现其诗学与文化人类学理念的试验田。卢森伯格的大屠杀书写策略在“第二代目击者”作家中是颇有代表性的。同为“第二代目击者”作家的西恩·罗森鲍姆对自己的定位似乎也道出了卢森伯格的心声:“我自己一直在斗争,一方面我是小说家,像个巫师、魔术师、真实事件的煽动者,另一方面我又是大屠杀记忆的保护者。”(28)换言之,他们的大屠杀写作是为了保护“大屠杀记忆”。在大规模的谋杀行动之后,人们不能指望屈死的亡灵会那么容易就消失,可见,“第二代目击者”作家想要实现的是让死去的亡灵在文本中说话。卢森伯格在印第安部落中长期采风和记录部落诗歌的经历在大屠杀书写中演化为记录死者的呓语,而诗人仿佛化身为部落召唤舞蹈中的萨满,具有了在生死之间游走的禀赋。作为“民族志”诗学的发轫者,卢森伯格的大屠杀书写很自然地带有后现代“民族志”的气质。在这一视角的透视下,民族志话语再现“意味着对表象拥有一种魔幻力量,意味着可以使缺席的东西在场,而这就是为什么书写——再现的最有力的手段——被称作‘巫术’(grammarye),即一种魔法行动的原因”(29)。作为“民族志”诗学的始作俑者,卢森伯格在叙述中充当的角色与雷兹尼科夫和格罗斯曼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就像一名神秘的“魔术师”和“释经者”,“解码讯息”并“作出阐释”(30)。这种身份决定了他采取的是一个游移视角,而他在文本中的位置取决于他对所描绘的事件的总体呈现。他的在场不会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也不会改变它们被观察或者被阐释的方式,因此他既需要建立起一种文本的权威,建立一条与对话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也需要在他自己与他所目击的陌生事件之间营造出一个合适的距离。卢森伯格以“阐释技巧”建构起民族志呈现的有效性。
卢森伯格热衷于各种形式的诗学试验,但无论其诗歌形式多么特立独行,其犹太内核却是其诗歌中永恒不变的声音:“如果有人乘火车去罗兹/就还有犹太人/就像还有桔子和/罐子一样/就还有人写犹太诗歌/另外一些人用光书写他们母亲的名字”(31)。犹太身份对于卢森伯格来说就像“桔子”或“罐子”的自然属性一样来得自然、没有半点扭捏,而书写犹太诗歌对他来说更像“书写母亲的名字”一样来得自然和顺畅。然而即便对于这样的诗人来说,大屠杀的书写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极端事件。事实上,卢森伯格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并没有直接触及大屠杀主题。在十几年的沉淀之后,卢森伯格终于开始直接从大屠杀的记忆深处搜寻诗歌情绪的推动力量,并最终堆积成为令人震撼的诗集《大屠杀》。这部诗集是一部犹太人的挽歌,带有传记性的真实感,因为其中涉及到诗人的多位亲人在位于纳粹德国的主要集中营——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附近的奥斯特鲁夫马佐夫舍(Ostrow Mazowiecka)大屠杀中的死难经历。多年后,诗人故地重游,冥冥之中仿佛听到那些死难的冤魂低低的泣语,而正是这仿佛来自天堂抑或是地狱的声音唤起了诗人埋藏已久的大屠杀记忆并为诗人写作这段历史提供了理由,同时也对阿多诺的断言以他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应。诗人曾对此作过如下阐释:“我最初在特雷布林卡听到的诗歌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我为什么写诗歌的最清楚的信息。他们也是对那个论述——阿多诺和其他人的——奥斯威辛之后不能也不应该写诗歌的回答。”(32)
与雷兹尼科夫似乎不动声色的“客观见证”和格罗斯曼赋予诗歌具有拯救历史灾难的“神之名义”的诗学理念相比,卢森伯格的“民族志”书写似乎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卢森伯格把他的诗歌创作本身当成了一场又一场部落巫术典仪,而他本人就是巫术仪式的萨满。作为氏族与部落的精神领袖,萨满拥有与灵魂沟通的魔力,并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诗人如游走在生死两界的萨满,在这诗歌的典仪中,一方面充当着诗歌的使者,一方面充当着在大屠杀中死难的冤魂的代言人。如果没有诗人,死者将永远被剥夺了话语权。并将永远沉默下去。诗集的标题“Khurbn”是“大屠杀”的意第绪语的表达,这是波兰犹太人的母语,它随着犹太人生命的消逝而几乎成为“死去”的语言。而卢森伯格正是在这个死亡的生命和同样“死亡”的语言之域创造出了诗歌的语义场。经历了屠城之灾的人们生活在永恒的空无之中:曾经鲜活的生命已经消逝,曾经跳跃的生活永远停滞,曾经丰富的语言现已死去。活着的人们只剩下了空空的躯壳,比死者更不幸地生活在永远无法抹去、又永远不可复得的记忆之中。作为诗人,卢森伯格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本人作为讲述人的特殊身份和视角。他既不是身临其境的在场者,也不是有着明确距离感的旁观者,更不是看不见的缺席者。他仿佛是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到的那位“森林之王”,人身合一的巫术的大祭司(33),召唤着死难者的灵魂。
三、美国犹太大屠杀诗歌的伦理意义
“伦理从来也没有真的被忘记,只不过好像有一段时间让位于语言、政治、社会和文化了。”(34)而对于美国诗歌和诗学来说,当代评论界的“伦理转向”与美国诗歌的发展又正好契合。评论家哈劳(Geoffrey Galt Harpham)对伦理、理论和文学三者之间关系的总结颇有代表性:“叙事与理论咬合在一个相互探究和强化的过程之中,……这种相互激发的理论与例证的名字,这种意识与生命之联系的基本例证,就是伦理:正是‘在伦理’中,理论转化成了文学的,而文学转化成为理论的。”(35)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极端事件虽然不是文学和伦理之间关系进行思考的起点,却恰巧成为这场漫长的人类思考的终点。为了让奥斯威辛不会重复自己,为了让相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这场浩劫迫使人们重新安排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在文学书写中,这次思考的结果就是诗歌重新回归了对生命本身的关注,以及诗歌作为见证和伦理思考的使命的回归。阿多诺关于奥斯威辛之后写作诗歌是野蛮的论断,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唤起了人们对诗歌伦理的关注,因此,他悖论地帮助重建了诗歌所承载的伦理责任。这次伦理转向的结果就是重新审视了诗歌作为见证和记忆的伦理律令的责任。
三位诗人从相同的主题出发,经历了不同的诗学选择和构建过程,却殊途同归地转向了诗学伦理的轨道。当代伦理学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的紧张,而三位诗人的诗学呈现的也正是“是”与“应该是”之间的伦理抉择。换言之,他们的诗学从各自对大屠杀迥异的“是什么”的诠释出发,最终共同完成了大屠杀书写“应该是什么”的伦理构建。而三位诗人的伦理选择也正是从大屠杀书写“应该是什么”中呈现出来的。
首先,三位诗人以各自的方式赋予了大屠杀沉寂的生命以声音,让死难者自己开口说话。芬克尔斯坦曾经说,如果没有诗人,死者将永远无语(36)。雷兹尼科夫采取的是比较直接的方式,让幸存者的证词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事件本身,并给奥斯威辛的那段历史带来了强烈的在场感,使读者直接进入了“语言所‘澄明’的场域中”,并使得这场浩劫转化为一个“现时在场”。(37)死难者的声音就在这个瞬间的“现时在场”回荡在读者的耳畔。这印证了恩格戴尔对证词的力量的定义:“[证词]在两个决定性的冲动上显示了与众不同:给沉默者以声音,并保留了殉难者的名字。”(38)当然,雷兹尼科夫尽管执着地把证词作为诗歌的来源,也并没有牺牲情感和道德的权威,更没有牺牲见证者的人性去迎合一种趋向历史或政治事件的中性的姿态。雷兹尼科夫并非如艾兹拉伊(Sidra DeKoven Ezrahi)所言,没有任何修辞的包装,只是留下了一具事实的光秃秃的骨架(39)。事实上,雷兹尼科夫在不动声色的修辞操作中,为光秃秃的事实注入了他精心准备的“修饰”。在他的笔下,法律证词转化为诗歌的过程经历了选择、编辑、改写等颇为复杂的再创作过程。对于“选择”,雷兹尼科夫曾经谈到自己的操作:“我可能浏览上千页的一卷本,从中只找到一个案例并重新排列让它们更有趣。”(40)雷兹尼科夫“编辑”所选择证词让其更有诗学价值,而且为了清晰和直接,他不但总是毫不留情地对原始的证词材料刀砍斧凿,而且刀刀精准、天衣无缝。既然选择和组合的过程都是阐释性的行为,那么就没有一个文本可以免除阐释。雷兹尼科夫通过诗行断裂、数字编号、对证词的副标题设置等方式微妙地注入了主观的阐释。长诗按照松散的时间顺序,从“驱逐”、“入侵”、到“屠杀”、“毒气室”再到“儿童”、“逃亡”等,最后以犹太聚居区起义结束,体现的正是诗人对这场历史浩劫的素材进行有效选择和重新编码并引领读者穿越历史的悲剧,在苦难挣扎之后到达希望终点的过程。可以说,雷兹尼科夫的诗歌把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维度融进了一个“客体派”先驱的诗歌文本之中,从而发展了一种散文体的、文献式的史诗。
在格罗斯曼的眼中,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是苟活于世的偷生者。犹太诗人更是“一位不能十分确定他事实上没有死的人”。换言之,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赋予死亡以神圣的意义。在格罗斯曼由诗歌、死亡、人和生命组成的等式中,诗歌依赖于死亡,而死亡通过诗歌把意义投射于生命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斯曼的大屠杀诗歌很少直接触动大屠杀本身,更从不直接描写大屠杀。此种写作策略正在于诗人的伦理趋向。这一点我们从格罗斯曼于2009年出版的专著《真爱:诗歌和评价文论》(True Love:Essays on Poetry and Valuing)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诗人在第一章“诗歌与启蒙”(Poetry and Enlightenment)之前加了两段“题铭”分别是前文提到的阿多诺的“奥斯威辛之后没有诗歌”和克里斯托弗·菲尼斯克的“奥斯威辛之后只有诗歌”。可见,从1961年诗人出版《娼妓的银钱》到2009年,诗人跨越世纪的思考始终聚焦于诗歌的伦理维度。格罗斯曼的“神之名义诗学”把在大屠杀中熄灭的生命之火重新点燃,并让沉寂的生命在诗歌中实现了对神的质疑和谴责。如果说雷兹尼科夫的大屠杀书写是对着事件本身和事件发生的当下述说,那么格罗斯曼则是对着未来述说,因为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合法性只有从未来才能获得。这是一种颇具本雅明的弥赛亚救赎时间观的精神气质。投身于民族志诗学的卢森伯格如部落文化中的萨满,向死者敞开心扉,并让他们通过他讲话。诗人成为死者的传声筒,而浩劫之后人烟稀少的奥斯威辛则成为一个死者的游魂自由讲话的真空地带。与对着当下述说的雷兹尼科夫和与对着虚无的未来述说的格雷斯曼不同,卢森伯格对着过去述说,对着被屠杀的犹太人的前世述说,为那冤死的灵魂寻找一个可以鸣冤的管道。当然,其目的不仅仅是慰藉冤魂,也是疗治心灵受到重创的幸存者。卢森伯格的“民族志”书写在唤起一种参与性的现实当中能够起着治疗性的作用,而这正是大屠杀书写最重要的伦理功能之一。
其次,三位诗人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共同建构了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里柯曾经说,陈述记忆是找回历史事件的重要方法。人对痛苦的记忆有时会滥用,有时则会过多遗忘,人有责任去记忆,说出故事,透过故事才能展开记忆的教育(41)。耶鲁赛尔米曾警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建大屠杀话语的人们:“神话和记忆支配了行动”(42),但是没有神话和记忆又何来“行动”呢?雷兹尼科夫的沉默的见证使他把大屠杀从犹太人的个人悲剧记忆变成了人类共同的悲剧记忆;格罗斯曼通过对古老的神祇的不断诉求来神化并舒缓大屠杀的记忆,从而避开了直接书写大屠杀经历,并慰藉人性和心灵的创伤;卢森伯格则在与幽灵的对话中,使大屠杀的记忆成为永恒,并用自己的诗性呼唤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幽冥世界,从而使大屠杀永远避开了被人们的记忆和历史的轨迹遗忘的可能。可以说,三位诗人共同实现了欧文·豪所诉求的“外在的奥斯威辛”和“内在的奥斯威辛”的表达(43)。这就意味着,后奥斯威辛的美国犹太诗人的诗性书写不是一种“简单的披露的行为”,而是一种缔造的行动,并因此充分显示了言语行为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讲,三位美国犹太诗人的书写倒是共同地回应了耶鲁赛尔米的担忧,因为他们的大屠杀书写既是“神话的”、“记忆的”,又是“行动的”。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后奥斯威辛的美国诗人从各自的诗学理念出发,用迥异的方式操演了犹太大屠杀这个共同的主题,并最终归结到了一个深层次的共同思索:大屠杀在记忆的消费中,在一代又一代流散的犹太人的灵魂中,如何生发出越来越深刻的伦理意义,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塑后奥斯威辛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可以说,这是一次殊途同归的诗学建构和诗歌创作之旅,而这一旅程的终点就是大屠杀书写的伦理维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雷兹尼科夫的“客体派”的沉默见证,还是格罗斯曼的“神之名义”的虚无预言,抑或是卢森伯格的“民族志”的巫术招魂,都不约而同地对在记忆和语言的双重加工下生产的大屠杀疑虑重重。在文学的叙述中被反复“复原”的历史注定是千差万别的,这对于那场无可比拟、无法估量、“绝对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的浩劫来说,是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其所需要的真实的本质的。(44)这是语言的不幸,是诗学的不幸,也是历史的不幸。这恐怕也是大屠杀书写永远摆脱不了困境重重的根本原因。
收稿日期:2013-01-20
注释:
①例如卢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格罗斯曼(Allen Grossman)、雷兹尼科夫(Charles Reznikoff)、海耶恩(William Heyen)、鲁斯·惠特曼(Ruth Whitman)、斯特恩(Gerald Stern)、海瑞森(Tony Harrison)、黑尔(Geoffrey Hill)等美国犹太诗人均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对大屠杀的诗性表达。
②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国外文学》2008年第4期。
③王焱:《奥斯威辛之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0-11页。
④[德]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钱定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⑤Theodor W.Adorno,"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Prisms,trans.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Mit Press,1981,p.34.
⑥Yosef Hayyim Yerushalmi,Zakhor: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p.98.
⑦Daniel R.Schwarz,Imagining the Holocaus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p.22.
⑧Barbara L.Estrin,The American Love Lyric after Auschwitz and Hiroshima,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1,p.9.
⑨Harriet L.Parmet,"Selected American Poets Respond to the Holocaust:The Terror of Our Days",Modern Language Studies,24:4,1994,p.78.
⑩桑翠林:《路易·祖科夫斯基的客体派诗歌观》,《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
(11)Hennessy Michael,"Louis Zukofsky,Charles Tomlinson,and the 'Objective Tradition'",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7:2,1996,pp.333-351.
(12)Tim Woods,The Poetics of the Limit:Ethic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10.
(13)转引自[美]埃利奥特·温伯格编:《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马永波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0-62页。
(14)George Steiner,Language and Silence:Essays on Language,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New York:Atheneum,1982,p.163.
(15)Louis Zukofsky,"Program:'Objectivists' 1931",Milton Hindus,ed.Charles Reznikoff:Man and Poet,Orono:National Poetry Foundation,1984,p.381.
(16)[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17)[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3页。
(18)1990年,葛斯曼撰写了“犹太诗歌作为以神的名义的计划”(Jewish Poetry Considered as Theophoric Project)一文,发表在Tikkun杂志,这标志着他的“神之名义诗学”(Theophoric poetics)的形成。
(19)参见Norman Finkelstein,Not One of Them in Place:Modern Poetry and Jewish American Identit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1,p.65.
(20)Hannah Arendt,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London:Allen & Unwin,1962,p.14.
(21)[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页。
(22)参见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2-88页。
(23)诗集的标题意蕴深远,其出处是《圣经·申命记23:18》,记录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娼妓们所得的钱,或娈童们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恨的。”
(24)Allen Grossman.Harlot's Hire,Cambridge,Ma:Walker-de Berry,1961,p.14.
(25)Allen Grossman,Sighted Singer:Two Works on Poetry for Readers and Writers,Baltimore:John Hopkins UP,1992,p.55.
(26)[美]W.E.佩顿:《阐释神圣——多视角的宗教研究》,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1页。
(27)Allen Grossman,Sighted Singer:Two Works on Poetry for Readers and Writers,Baltimore:John Hopkins UP,1992,p.60.
(28)[美]德雷克·帕克·罗尔:《西恩·罗森鲍姆访谈录》,舒程、朱云译,《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
(29)[美]斯蒂芬·A.泰勒:《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李荣荣译,见[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72页。
(30)[美]温森特·克拉潘扎诺:《赫耳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杨春宇译,见[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第81页。
(31)Jerome Rothenberg,Poland/1931,New York:New Directions,1974,p.12.
(32)Jerome Rothenberg,Khurbn and Other Poems,New York:New Directions,1989,p.4.
(33)[英]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关于《金枝》中“森林之王”的神话参见该书第一章“森林之王”、第二章“祭司兼国王”,第1-10、12-14页。
(34)Robert Kaufman,"Poetry's Ethics? Theodor W.Adorno and Robert Duncan on Aesthetic Illusion and Sociopolitical Delusion",New German Critique,33:1,2006,p.97.
(35)Geoffrey Galt Harpham,Shadows of Ethics:Criticism and the Just Society,Durham,NC:Duke Univerisity Press,1999,p.35.
(36)Norman Finkelstein,Not One of Them in Place:Modern Poetry and Jewish American Identit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1,p.31.
(37)王焱:《奥斯威辛之后》,第47页。
(38)Horace Engdahl,"Philomela's Tongue:Introductory Remarks on Witness Literature",Horace Engdahl,ed.Witness Literature:Proceedings of the Nobel Centennial Symposium.trans.Tim Crosfield,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02,p.4.
(39)Robert Franciosi,"'Detailing the Facts':Charles Reznikoff's Response to the Holocaust",Contemporary Literature,29:2,1988,p.241.
(40)转引自Robert Franciosi,"'Detailing the Facts':Charles Reznikoff's Response to the Holocaust",Contemporary Literature,29:2,1988,p.260.
(41)Paul Ricoeur,"Memory and Forgetting",Richard Kearney and Mark Dooley,eds.,Questioning Ethics: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99,pp.6-8.
(42)Yosef Hayyim Yerushalmi,Zakhor: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p.99.
(43)转引自Alan L.Berger & Gloria L.Cronin,Jewish American and Holocaust Literatur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Introduction,2004,p.6.
(44)王焱:《奥斯威辛之后》,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