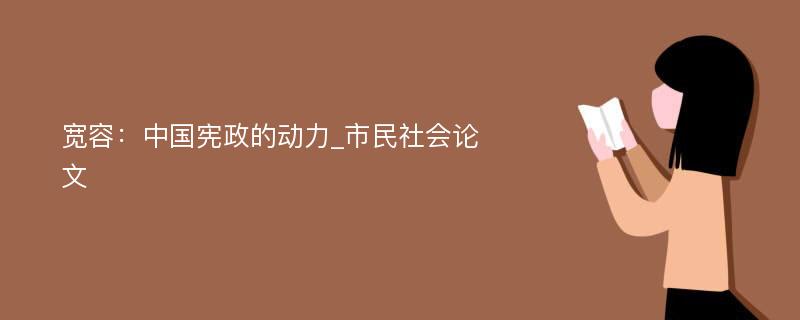
宽容:中国宪政的推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推动力论文,中国论文,宽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宽容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其在宪法文本的表述中以间接性的权利和义务方式得到宣示和固化。藉此,仰赖于宪法制度本身的高位和权威,柔性的宽容得以楔入宪政并在宪政生活中加以实施,进而构建出饱含宽容品格的宪政秩序。上述这个进程的揭示,回答了宽容实现的制度性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宣扬德法并治的今日之中国,更是找到了德法契合的有效中介体。首要理由在于宽容本身蕴涵作为工具价值判断的弹性,即允许多元性的实体抑或程序以及价值的共融,这就意味着宽容能够有特殊的质体将内在道德体现——“恕和”以及外在的法律载体——“权义”完美展示并适用于具体宪政生活中。由此,在构建法律秩序时,善于借助民间的道德认同惯性,以及业已存在的宪法文本样态的先进表达性制度的优势,使宽容有了极大的效用价值,这势必对于宪政秩序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
一、一种警惕:儒教和精神的吸纳
在进行中国制度建构之前,一个不容回避的前提就是中国的既有信仰财产的传承问题,这也是确立宪政精神内髓的基本步骤。面对中国制度氛围下强大的儒教思维惯性,如何应对是制度建构必须考量的核心。中国的儒教中也饱含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等内容,似乎在文本的直接意义上,上述内容可以与宽容等同。但这种宽容思想和现代宪政秩序并不合拍。
首先,儒家的“宽容”思想是确定等级式的前提之后的宽容,即先将人划分为君子与小人之后的宽容,是君子对小人的宽容,而这与现代宪政张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圭臬相悖。所谓“君子不计小人之过”即是其真实说明。宪政秩序内社会主体都是平等的。
其次,强化教化,体现上位阶层对于下位阶层的掌控。在宪政意义上,教化更多会遭遇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范畴的冲突,宽容本应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是双向的,是互相空间的给予而非单方的单项给予,这会将宽容在情感层面异化为恩赐,异化为中国报偿性心理的温床,实不利于建构强化法治的制度基础。
第三,儒家思想中的纲常思想也是一种极大的对宪政价值的背叛。因为儒家的宽容皆有价值底线(或者说有限度),亦即在三纲核心伦理下的宽容,这种核心确立昭示着在儒家思想层面的精神皈依或者权威崇拜的树立。而其崇尚皇权、父权和夫权的取向,直接对抗了人民主权、民法家事平等原则。以皇权为例,其恕道实质则从属于“忠”,是一种“忠”压制下的恕道,是以谋大逆者不可因“亲亲相隐”而获得国法之宽恕。宽恕的内容仅为“过”,惟有出言不逊而无伤大雅的“过”,才有可能得到宽谅与容忍,然而凡是涉及“忠”的问题则另当别论。这种传统的宽容观不能为我们的宪政建设提供太多的建设资源。
最后,儒家强化礼先而非法先。孔子所提倡的周“礼”能够“经国家,序民人,礼后嗣”“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成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往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注:《礼记·曲礼上》。),亦即礼法冲突,则礼先而法后,这就是前述的“非礼不决”的本质。而这一观点放诸宪政则大为有害,盖因“礼决”在现代社会更多是非强制治理手段,以引导为其效力体现;而“法治”则以国家强权为后盾,更具实效性和控制力。
当然,上述讨论实际上已经回归到学者们论述法家和儒教之争的传统路径了。(注:参见刘绍云:《儒家思想对唐律的影响》,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55~56页。)不过,马丁·克里杰在《礼仪的品质》(注:Martin Krygier," The Quality of Civility:Post-Anti-Communist Thoughts on Civil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A.Sajo,ed.,From and To Authoritarianis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pp.9; 14.)更加深刻地指出:礼仪以它的宽容和社会信任为“在陌生人中建立一种非弱肉强食性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现代意义上的“礼”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别于“忠诚”的社会维系力量,礼仪就是“治理多元,保护独立和坚持宽容”的道德联邦(The Moral Commonwealth)。(注:Philip Selznick," The Moral Commonwealth:Soci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Communit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391.)礼,这一古老儒家思维,将在宽容的基调之下,展现新的品质内涵。
似乎可以额外提及这样的一个延续话题——“什么教派是中国宪政的精神皈依”,有学者指出:“单就法律理论而言,从老子的无为学说,经过自发的法律秩序概念的中介,即可以绕开法家的陷阱——在那里法律完全成为君王控制臣民的工具——而形成一种与自由兼容的法律学说。”(注:秋风:《寻找普通法的精神》,载《万科周刊》2005年3月25日号,http://www.vankeweekly.com/main/Web/Article/2005/03/25/1723484849C19529.aspx,下载日期2005年6月24日)在这个论断下,自由兼容将成为宽容精神最直接的表达。这个判定也将成为中国宪政推进中对于宽容的有效解读。
二、宪政实然:二元领域的宽容脉络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存在一种基本的观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契约关系”(注:【英】戴维·赫尔德,燕继荣等译:《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圣托马斯也“暗示王权起源于人民,并把它解释为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注:【英】戴维·赫尔德,燕继荣等译:《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由此孕育了社会契约论的学说。依据社会契约论的基本论断,在现代西方的宪政理论和制度结构存在着一种两极对立的格局,即“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状态。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为了避免“人总是与它的邻人处于战争状态”,而彼此同意让渡某些自然权利,结成社会,建立统治机构,确定统治者。而上述机构一经产生,即独立于公民个体。公民只能通过复杂的投票程序,对统治机构和统治者施加间接的影响。美国学者阿兰·S·罗森鲍姆据此认定,“西方民主社会的近代宪政主义通常都包含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注:【美】阿兰·S·罗森鲍姆著,郑戈,刘茂林译:《宪政的哲学之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席尔斯(Edward Shils)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公民社会的要义有两条,美德和共和政府。(注:Quoted by John Bendix,The Re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ed.,Zbigniew Rau(book review).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1(March 1993),p.248.)遵循这一学术路径,本文在进行中国宪政建构的讨论时也提出宽容对于上述二元对立结构的具体设定作用。
首先,就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层面而言,有学者指出中国在近代以来是一个为“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注:【美】孔飞力著,陈兼等译:《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0页。)人们只能就有限的资源进行残酷的竞争,也因此社会成员之间充满着不宽容的敌意,“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这显然脱离了市民社会所赖以维系的信任基础——即契约合意的形成。而呼唤宽容,恰恰能够有效破解这个合意信任的基础。通过宽容的设定,制度上可以引导社会成员先行性地给予信任,使得成员间不会因为彼此的敌意和所谓资源稀缺而进行零和博弈,施行恶化竞争与对抗。这样一来,中国社会就可以形成“第一波”的信任基础,因此推动式的形成持续的信任传统,从而优化上述信任基础。
我们还注意到,关注中国是否存在构建社会契约的场域,也是一个呼应上述讨论的前提。学者季卫东指出:“中国的‘集众立约’活动能不能与社会契约的观念相通?……中国传统的制度设计原理基本上是以二者关系、二者契约的彻底化为出发点,缺乏社会契约论里的那种公共人格和普遍意志的契机。这样的思路最终能否超越“小宪法”的局限性而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宪政的目标,颇令人怀疑。现代民主宪政既要求合意论构成,同时又要求必须超越具体的契约关系,这样的交涉和议论与互惠性讨价还价的泛化完全是两回事。”(注:季卫东:《从农村的法律话语场看中国宪政的合意论基础及其缺陷》,载《法律人》2004年9月号。)由此,宽容的道德内髓和法律文本属性的表达,将能够成为消解局部利益,锻造共同意志的极好平台,最终“小宪法”可以有效被过渡到“大宪法”,实现宪政的合意基础。
在具体适用层面,宽容的品格还可以借助“小文字法”的运行来有效达到宪政施行的共同意志和个体自由的匹配。(注:【日】棚赖孝雄著,王亚新译:《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51页。)借助棚赖的体系:国民与法分为两种,一种是规定在成文法律中、作为共同体整体来加以考量的“大文字的国民”。与之对照,那种将大文字的国民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的法就是“大文字的法”。另一种国民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存在于社会中实实在在的“小文字的国民”,与之对照,用以解决小文字国民之纠纷的法就是“小文字的法”。在这两种国民与法的互动中,存在着一种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互动与演化。由此,宽容可以得以用民主和自由两个关键词深化并具体展现。
其次,就国家意义的建构而言,现代的宪政在于如何准确厘定国家权力范围及其运行。但是抽象地讨论上述命题是缺乏设定的坐标的,必须回应到宪政本身的实质上。有学者指出:宪政本质是一种平衡性,包含了行为的规范性、利益的兼容性和文化的通融性。(注:参见谢维雁:《论宪政平衡性》,载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 no=1147,浏览日期:2005年6月24日。)那么,据此演化的一个逻辑结论,就是宪政本身体现出的多元性(无论是利益或者文化)平衡之后的一种折冲,并最后经由规范确立。那么国家权力范围和运行在这个逻辑路径下,也同样可以说系一个平衡体系。即包含有内生性的权力范围静态界定平衡和外延性的权力运作的动态平衡获得。那么,多元性的这种平衡,在宽容的表达语境下,则可以自然过渡到采用简单民主机制下获得的代议制度的决策机制。宽容,意味着获得多数支持的代表被授予代议决策的权利,并由此来构筑和修正社会契约的宏观(宪法)和微观(法律)表达,少数人的则引用宽容去认同由此间接体现的多数意志,这是宽容在国家层面运作的体现。在国家具体权力运作上,宽容将被引用为容忍某些权力执行人(主要是行政和司法人员)的违法用权行为。因为即使在权力运作架构上可以形成一定的事前防范体系,但是权利的施行也不可避免会有违法过错的状态存在。在这个角度上,作为授权人的个体并没有权力藉此对抗或者要求重构上述国家权力运作架构,因为这种违法用权必须被计入授权代理成本而由授权人以宽容吸纳或者淡化,否则,国家只能进入被个体意愿分割的孤立体集合而失却任何运作的基础和价值。
三、互动视野下的宪政架构
回顾宪政历史,传统的宪政理论过分关注防止和遏制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膨胀问题,但由此并不必然导致合理行政和积极行政的效果。在中国宪政的本土环境下,控制国家权力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架构下显得很有现实价值,因为传统的国家职权的惯性和民众的心理基础,使得国家权力长期以来形成对公民权利更多的控制和干预。因此,中国宪政的建构,遵循传统宪政理论并不为过。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权力的放弃是化解这个问题的要结所在,虽然在一个阶段内他们会显得多么不情愿甚至反抗。化解这个心结和利结,可以宽容为基调。借助正派的社会的理论,(注:关于正派社会的理论,See Avishai Margalit," Decent Equality and Freedom:Postscript." Social Research 64:1(Spring 1997):147—161,p.147.)人们会重视一切制度伤害的严重性。制度伤害的起因是不能把每一个人当作人来对待,无法真正与群体认同。(注:徐贲:《公共真实中的社会和谐: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载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 id=6310,下载日期:2005年6月26日。)而既得利益集团恰恰就是忘却了这种全体意义上的群体认同。宽容除了可以契合这种利益失却的心理痛楚,可以通过呼唤群体认同来感召既得利益者的合法性“弃权”过程得以顺畅,当然也可以在彼此适度的让步中寻求渐进式的折中和妥协。当然,我们说这是提倡的宽容,绝对不是一种你好我好的乡愿,这也不可能凭空就使得双方得以自动遵循,它需要的是制度体系架构下,利和义、责和权的有效平衡和扎实推进。唯有如此,才能够使得宽容过后的和谐,遍撒宪政架构中带来的社会阵痛,抚平变革中引发的伤楚。因此,国家和市民社会互动是在一个宽容的氛围中平和渐进实现的。
上述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互动有一个潜在前提——已经承认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同生共存状态。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发育进程,以及城市化这个物理阶段下对于市民精神的培育,则并不是上述这个前提所蕴涵其中的。换言之,中国并没有已经出现一个市民社会来匹配上述国家以及国家背后的权力运行及其控制。事实上,中国目前的乡土社会状态,并存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即体现为当前法律适用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域(即使是同一法域)下的实效性问题。在中国大农村背景下,诸多的乡规民约体现出的民间法力量实际主导了大多数乡土社会,而不是国家立法在施行并产生秩序。(注:有学者以民间收债为个案,提出了“无需法律的秩序”这样的命题,也在一定层面表现了农村私力救济对于法律建构的公力救济体系的脱离。参见徐昕著:《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以下。)伯尔曼指出:“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法律有助于以上这两者的整合。”(注:参见【美】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4页。)因此,市民社会精神的养成,首先就是一种法律对于民间法的改造。解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不能把国家法简单地向乡土农村无限制地进行强力扩展或者单向控制,更不能把国家法简单地送入乡土社会,无情地消灭与压制民间法,当然更不能将国家法与民间法进行地理上的疆界划分,强调两者在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平起平坐,各自为阵。而确立这种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共容状态,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首先要建构我们精神层面的宽容。
由于中国不曾有过全国性的市民社会,对于这一思潮和态势的回应就转化为另外一个问题——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以及在宪政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构建什么样的关系框架。有了宽容的基础,就有了吸纳民间法民间文明进入市民社会的可能,就有了扩张市民的素质基础和精神脉络源泉,也就能够真正锻造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和公民品格,从更深的层次上也就意味着宪政精神有了更加深厚的基础。由此而言,“新宪政论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新的研究视角和启迪,而且是其所提出的社会自治和参与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尝试思路,比如发展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以及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民主,让他们在未来的宪政民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注:参见张军:《从宪政国家到市民社会—〈新宪政论〉之述评与思考》,《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第123页。)
再到政治领域,这一市民和国家博弈的大舞台。中国的宪政建设习惯于也正在走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它是通过政治高层的自制逐步推行的。在宪政建设过程中,当权者的政治人物是否具备宽容的品质尤其显得重要。在过去,不宽容的传统,残酷的政治斗争,一直妨碍着中国走向民主化,影响着宪政秩序的构建。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注:参见秦前红、叶海波:《宽容: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载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5/5/ma996218165132550025472.html,下载日期2005年6月25日。)无论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理解和建立的都是一种不同于宪政民主观的“革命”民主观,民主主体与专政对象的划分是“革命”民主观的理论前提。社会中存在一个潜在的身份划分:即民主的人民和专政的敌人。并一次确定了“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界限。在这种逻辑下,国家权力的功能之一是维护人民所代表的真理和善行,限制甚至消除错误和恶的持有者。因此,“革命”民主观将一种观点和行为方式能否成为宽容的对象,直接与一个抽象的“人民”划上等号,而不去关注人民背后的人权或者是权利本身。而这样的一个理论误区,恰恰成为国家权高涨而市民权低落的最好催化剂。
正视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以来的能够让我们享有的宽容和宪政的资源太少,但这不会使得我们退却。因为每一个宪政教化的成功个案,必将产生于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的宽容互动中,而每一份宽容品质,则必将会发轫于心存善意的市民内心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在宪政秩序中提倡宽容,在宽容宣扬中强化宪政建设。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建构和谐的宪政秩序,建设和谐市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