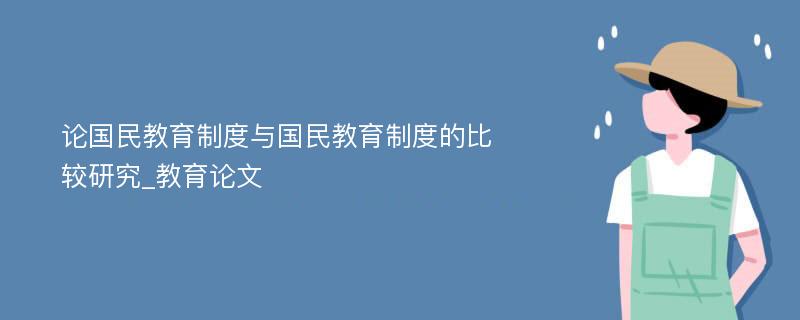
试论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教育体系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8)08-0001-06
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具有无边界特征,这种无边界的研究可能带来的危害是比较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变得无所不包,这并不利于这个学科自身的确立和发展,事实上,已经因为研究的无边界而导致了比较教育研究危机、身份危机等问题。显然,为了有效地解决比较教育研究的边界问题,就需要解决边界是什么的问题。笔者在此提出比较教育研究本体论概念,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概念中涉及到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之一是民族—国家教育体系,① 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比较研究是边界之一,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本文所要提出的问题是,比较教育研究是如何认识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研究的?何谓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它与学校体系有何关系?其根源是什么?在比较教育研究历史上有哪些学者对民族—国家教育体系进行了研究?本文将利用文献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一、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研究概述
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上已经被众多的比较教育学家所认识。在谈到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问题时,顾明远教授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是极其广阔的,许多领域是别的学科难以替代的。例如,教育制度的比较……对教育制度本身的比较,对它产生的经济、政治特别是文化背景的比较分析以及各国教育制度对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哪门学科从事这种研究,除非将来再建立一门教育制度学。”[1] 他所指的“教育制度”在本文理解为“教育体系”,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研究教育体系的基本问题域。即,对教育体系本身的比较;对教育体系产生、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的比较分析;对教育体系对于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作用的比较。
在西方,教育体系的研究在康德尔的认识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比较教育的研究是从组织和管理、课程和教学方法、公众参与以及教师地位等方面涉入教育体系研究(the study of system of education)的。与教育史的研究一样,比较教育试图发现根本的理由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彼此之间如此不同,阐明什么是教育体系的激励目标和目的,其根源又是什么,什么是它的普遍原则。”[2] 诺亚(Noah)和埃克斯坦(Eckstein)更是指出,这个领域首先是在19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与民族—国家教育的产生是同步的,而且它把民族—国家教育体系作为其探究的主要对象(object)。[3] 显然他们是从发生学意义上把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与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产生联系起来,表明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一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教育体系。
1988年出版的《比较教育和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Systems of Education)在“前言”中指出:“严格地说,‘比较’意味着观察两个或更多实体(entities),把它们并列摆放并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在教育领域,这能够应用于两种教育体系之间和两种以上教育体系之间的比较。”“‘教育’这个词通常包含所有计划了的从学前到大学的正规教育形态,还有非正规和成人教育。”[4] 显然,把“比较”和“教育”两个词合在一起,意味着观察两种教育体系或两种以上教育体系并把它们摆放,从而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就是比较教育。问题是从哪些方面去找出教育体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呢?可以从目标、结构、财政机制、年龄组学术成绩等方面找出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当然也可以分析体系的各部分(subparts)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梅斯曼(Masemann)认为,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比较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石。[5] “比较教育始于对其他国家教育体系的描述,而此领域第一批教材是卷本‘教育’。此领域要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组织模式,描述教育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此领域从一开始既是实践的,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要求(desire)。”[6] 沙哈(Saha)认为:“教育体系的比较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7] 当代英国比较教育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评价道:“20世纪的比较学者包括萨德勒、康德尔和汉斯,都把它巩固成一门学术学科,继续强调不同民族—国家体系的分类和对其特征的解释。”“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这个概念构成了比较教育整个精神体系结构的基石。如果没有它就很难思考比较。”[8]
由此可以认为,比较教育研究首先确定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因此从学理分析,比较教育研究首先是探究和生成有关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知识,比较教育研究在形成这种知识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二、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概念和历史起源
民族—国家教育体系是比较教育学者们普遍认可的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何谓教育体系以及它的历史起源。
(一)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概念
这里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谓教育体系”,因为“英语国家方案支持者的出发点是,比较的客体正是教育体系,但是比较应当以教育的科学性分析为基础,把属于教育问题的现象和过程进行对比,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教育学这一名称更好”。[9] 可见,教育体系与比较教育学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通常,体系是指一套相互关联的实体结合而成的系统,譬如一个家庭或一盘棋。而结构更侧重系统内部的整套关系,这套关系既可用抽象逻辑形式予以概括,也能在系统运用中得到象征性的体现。那么何谓教育体系呢?在《教育大百科全书》描述各国“教育体系”的基本内容中是这样来规定的:基本背景、教育政策与目标、正规教育体系(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第三级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技术或商业教育,成人和非正规教育体系)、行政管理的结构与运行、教育财政、师资、课程开发与教学方法、考试和升级以及证书体系、教育评价和评估以及教育研究、主要改革、主要问题。[10] 显然,构成一个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应该是正规教育体系。
在英语当中民族—国家教育体系还有另一种表述,即“national school system”,之所以用这种表述,是因为“学校已经成为所有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服务领域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学校起到了现代化和公民教育的国家控制工具的功能。与所有其他一代又一代生存下来的机构一样,它们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自主体,永远充满活力。因此跨国视角研究民族—国家学校体系一直并仍将成为比较教育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议题。这个议题在我们的学科内部的核心地位是不容置疑的”。[11]
另外,与教育体系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教育体系建构(system- building)。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之所以重视教育体系建构,是因为教育体系本身具有的历史根源,共同的文化理想,致力于国家的、经济的、公民的现代化以及作为一种教育理想的现代性。教育体系本身也是不断地扩展(expansion)和分层(differentiation)的,之所以产生教育体系的扩展和分层,是因为共同的根源与特定的历史、国家传统以及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共同的文化理想实现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因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不同而导致了文化的差异。
从文化和社会化的视角研究教育体系,学校不仅具有自主性,而且是人类和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但它们代表的只是老一代向年轻一代传递文化的工具之一,它们致力于年轻人的教育,这些年轻人不仅在学校中,而且也在复杂的环境中成长,而这种复杂环境又影响着学校,因此学校体系内外的文化和社会化的域境(context)应当成为比较教育研究教育体系或学校体系的一个基本视角。[12] 而比较教育研究把被建构的教育体系作为其探讨对象。
(二)教育体系与学校体系之间的关系
通常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向是以学校体系来界定教育体系,根据课堂教学、教师和训练来界定教育,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时把教育体系等同于学校体系。曾有学者警告:“比较教育的范围实际上缩小为学校体系、与学校和课程相关的决策以及学校体系与社会(主要是经济和行政管理)的其他亚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比较教育的理论倾向主要由社会体系、社会变革、现代化和功能分化的理论所主导;这种倾向被视为一种框架,它能够最有效地应用于学校体系(它们的结构、功能等)的研究。”[13] 学校是一个国家教育生活的最显性的表达,它们具有一种“体系”的特征,它们有一定的结构,可以实现明确的功能,与社会亚体系相互联系,它们是理性规划、行政控制的目标,遵循自我管制的某些规则,还有持续性。更重要的是,教育体系建构(主要指学校体系)事实上是人和社会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儿童和青年人以他们的权利和责任进入到社会地位层级中的决定因素。
(三)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起源
比较教育研究,甚至教育研究中民族—国家教育体系观念不是先验的,而是历史的产物,比较教育学科体系也是随着民族—国家教育的发展而逐步建构起来的,同样,民族—国家教育体系不是自人类以来就有的一种事物,它是随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因此从起源上来看,民族—国家教育体系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现代民族—国家教育体系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先决条件的。不可想象的是,各民族—国家的《义务教育法》不是由主权民族—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正如很难相信美国19世纪各州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可以用于英国19世纪的义务教育实施中,殊不知19世纪英国还没有义务教育观念。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作为人类基本的制度安排条件下,教育体系成为了民族—国家在形塑现代公民和致力于人的生活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的重要制度,它成为比较教育研究首先要探讨的对象之一是历史地决定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人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取代了以朝代国家的生存格局,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现代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每走过一个艰苦的里程,都要通过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框架来制定为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展”。[14] 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也正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框架来制定教育体系的规则的。当然,在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建立的时间表上各民族—国家存在很大差异,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在各国呈现着不同的形态。而比较教育研究被视为民族—国家教育知识的研究,第一对象是民族—国家教育体系,那么比较教育研究就是探讨有关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历史、形态、类型的知识。
三、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研究的谱系
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欧洲现象。因此比较教育研究首先依据欧洲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历史展开。“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和构成体系的制度与成分已经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传统语境……比较教育领域的学术著作主要通过采纳民族—国家构成的,民族—国家成为民族—国家教育体系比较的基础,总体上或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研究的核心。”[15] 在西方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研究中也呈现出富有特点的历史过程。
首先对教育体系进行研究的学者是萨德勒,他在1900年著名的吉尔福德(Guildford)演讲中说:“在研究外国教育体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学校外的事情比学校内的事情更紧要,而且学校外的事情控制和解释(govern and interpret)学校内的事情。我们不能悠闲地漫步在世界的教育体系中,正如一个在花园中游荡的孩子,从一个树丛上摘一朵花,从另一个树丛上摘几片叶子,然后盼望着如果我们把已经采集到的插入家里的泥土里,我们就会有存活的植物了。一种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就是一种生物,是很久以前被遗忘了的斗争和困难的成果,是战斗的结果。它反射出对纠正民族性缺陷的探求……如果我们以一种有共鸣的精神尽力地理解外国教育体系的真实运行,那么我们反过来应当发现我们自己更能够进入到自己民族—国家教育的精神和传统,更敏感于未记载的思想。更迅速地捕捉到标志其成长或影响衰落的符号……以公正的精神和学术的精确性研究外国教育体系的运行的实践价值就在于会使我们更贴切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16] 这段话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1)要意识到学校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和非系统的教育借鉴的危险性;2)比较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可选择借鉴的可能性,不如说在于能够更有效地分析本国体系的洞察力(insights);3)提出了“民族性”概念成为一种分析工具。这就是萨德勒原则(Sadlerian principles),它已经成为20世纪比较教育理论方向的基石。
20世纪前半叶,比较教育研究主要遵循着萨斯勒提出的道路展开。像康德尔热衷于若干社会的教育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影响(effects)和对国际主义的期望。弗里德利希·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和汉斯试图把社会动力和其他动力分开以研究不同教育体系形成的原因;马林森利用民族性概念作为解释教育体系之间的差异的手段;罗伯特·乌利希(Robert Ulich)的研究假设是,如果人们希望理解学校和学校体系,那么必须把它们与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力量联系起来。
在格林看来,第一代比较教育学家热衷于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和国家地位(nationhood)的研究。他们围绕着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对教育进行了分类,收集国家层面的数据,探求民族—国家的特征以解释体系之间的变量。他们都认为国家是塑造教育体系的重要力量,因此他们分析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来理解体系之间的差异,当然也包括语言、气候和宗教等其他民族—国家因素。朱利安是第一位试图分类不同教育体系特征的比较教育学家,但他侧重于制度的模式和过程。爱弥尔·拉瓦瑟(Emile Levasseur)是一位法国的统计学家,他利用人学的数据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定量比较研究,还力图根据宗教、种族气候和民主水平的程度来解释国家教育体系,并发现清教北欧国家比南部天主教国家拥有更高的入学率。跨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研究在早期比较教育学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前半叶重要的比较教育学者,从萨德勒到康德尔,再到汉斯,均关注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特征化,并对其进行解释,虽然比起前辈来在研究中更严格一些,更关注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萨德勒尤其关注制度外部的社会域境。社会域境对于理解教育过程在每个国家的运行比内部制度动力更重要。康德尔也探讨了体系变化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动力和因素”(forces and factors),包括国家和教会的角色以及阶级、种族和社会与经济组织。他们视教育为民族—国家的折射。对于康德尔而言,“一切良好和有生命的教育都是民族—国家生活和特性的表达。它深植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并且满足其需要”。[17] 康德尔在他的《比较教育》的前言中指出,他的著作“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上的,即教育体系是由民族—国家的目的所控制的,教育者和教师的职责就是理解民族主义的含义和对它起作用的所有动力”。[18] “康德尔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19] 他也意识到,民族主义会走向邪恶的方向,不过他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他对危险性缺乏警惕。尽管如此,他的路径依赖仍然是民族—国家视角。在他那里,没有讨论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族裔或者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这些早期先驱者是从历史的视角来对待民族—国家的文化和制度的,强调长时段的模式和连续性,也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这是典型的民族—国家文化决定论。他们不注重历史的非连续性和阶级与族群的结构分裂。这种历史人文主义遗产在20世纪60年代被一种社会科学路径所取代,也就是诺亚与埃克斯坦的新科学主义和布莱恩·霍姆斯(Brian Holmes)的实用主义的问题解决法。这些研究试图要把比较教育牵引进社会科学,尽管它是以牺牲历史深度为代价的。新一代的比较教育学者许多都停留在狭隘的经验主义上,无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政策改革导向。这种比较教育研究更接近于比较社会科学学科。但是视角仍然是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教育体系仍然是比较的重要单位,尽管侧重点已经在因果上。
随着政府被民族—国家的绩效测量所困扰,国际教育成就研究协会(IEA)和其他一些组织致力于学业成绩的国际调查,比较教育也被拖进了某种跨国的奥林匹克——根据有效性对教育体系进行排名。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职业培训开发中心(CEDEFOP)及其他团体的无数专题论文也重视对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描述和分类。显然,“教育研究越国际化,它就越重视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比较”。[20]
在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上,对学校和学校教育及其与社会或外部世界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视,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观察和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关注点更是从早期的影响学校的文化、历史、民族性等因素的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学校与教育结果的关系,学校与受教育者教育成就的关系,学校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学校教育自身的教育结果,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对学生在学校中的表现的影响等的研究。
例如,20世纪70年代比较教育学家关注学校所具有的教育的结果研究,而这是以往被比较教育研究完全忽视的,但这恰恰是决策者和教育者关注的核心。核心主要围绕着“谁上学”的问题展开,这个问题与差异机会、妇女、族群和种族少数族裔以及社会分层的结果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联。在这样的视角下的比较教育研究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比较,它是妇女、少数民族以及不同社会分层在学校的经历的比较研究。当然,“谁上学”是受教育权利的问题,“学校教什么”是教育质量和教育内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不同背景的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于是这个时期研究者们又深入研究学校应该教什么的问题,教育的质量和内容如何影响不同背景的学生的问题。当然,之所以会转向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是与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微观层次上的教育“输入”并不一定会带来教育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比较教育研究从教育的过程追溯到更广泛的教育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结果上,于是大量的、有创新的研究策略开始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出现。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教育成就的研究。由IEA发起的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它促使比较教育研究转向对学校教育的教育结果的理解上,而这是长期以来比较教育研究所忽视的领域,以往一般是关注社会和经济结果。
由于比较教育研究在教育的成绩结果上更深入了,于是比较教育研究开始提出问题,如,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对学生在学校中的表现的方式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另外这也引起了教育成就数据的跨国比较的意义是什么等讨论。
此外在学校教育成就的国际比较研究中还提出了体系差异(system differentials)概念。教育体系的差异是从教育体系的效率(efficiency)和教育体系的生产力(productivity)的差异中体现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IEA选择了12个国家的教育研究机构的代表,开始了一系列的教育体系效率的国际研究,主要是通过某一学科领域的学生成绩进行比较研究。对此,胡森(Husen)认为:“我们越是认识到教育是人力资源的一种工具,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就越强烈地要求研究教育体系的根源,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显示了太强烈的差异性。在研究教育体系发展和‘生产力’背后的因果因素中有一种实证数据的需求,一种与它们真正发挥功能的那些体系相关的跨国性有效变量的需求。”[21]
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研究的谱系表明,比较教育研究中对体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也体现了比较教育研究在体系研究上的进展。
四、结语
如果比较教育研究是具有确证身份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在遵照教育的比较研究的共性原则下对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的教育进行跨国性、跨民族性、跨文化性、跨学科性的学科逻辑的研究,那么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比较研究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进行跨国性、跨民族性、跨文化性和跨学科性的研究。笔者把民族国家教育体系视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一研究对象,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首先,比较教育研究应该确立教育体系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构成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石。任何一个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学科概念,教育体系应该是比较教育学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概念之一。其次,比较教育研究要确立民族—国家教育体系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边界之一。现代民族—国家在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和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民族国家教育体系推动和促进民族国家建设,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教育体系本身就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比较教育研究必须清楚各民族—国家是如何建构教育体系的,以及教育体系是如何促进和推动民族—国家发展的,如具体到义务教育体系,要清楚免费性、强迫性、世俗性、普及性、公共性、无党派性等体现教育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再者,比较教育研究需要深入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跨学科性比较研究,这意味着要加强对比较教育研究历史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的梳理,从而构建出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一门学科的发展是需要理论作为支撑的,没有理论的学科是没有生命力的,比较教育学的理论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历史地展现的,基于历史建构比较教育理论才是科学的方向。事实上,在比较教育研究历史上,针对民族国家教育体系的理论是很多的,如民族主义的教育体系理论、教育体系的冲突论、教育体系的依附论等,不一而足,这些同样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注释:
① 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在英文里是“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本文为什么不理解为“制度”,而理解为“体系”?原因是中文的“制度”可以用很多英文来表达,如institution、regulation、system,而按照英文的system的解释,如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的第一个意思是an assemblage or combination of things or parts forming a complex or unitary whole,显然这个意思离汉语的“制度”有一定语义上的距离,因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是这样解释的:“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当然它还被理解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后一个解释与英语中的system有相同的意思,《英华大词典》中有以下许多翻译,即“体系、系统、分类法、组织、设备、方式、方法、制度、主义、次序、规律、世界、宇宙、(the)身体、全身、机体”等,如a system of philosophy是哲学体系,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用的“世界体系”是world- system,如此有理由把system理解成为“体系”,这样更容易把握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事实,确实,英语《教育大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的第五、六卷是“system of education”,在阐释各国教育的时候使用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文版《教育大百科全书》翻译成“教育制度”按本文的理解似乎不妥,建议修订版时翻译成“体系”,这符合英文原意。
[收稿日期]2008-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