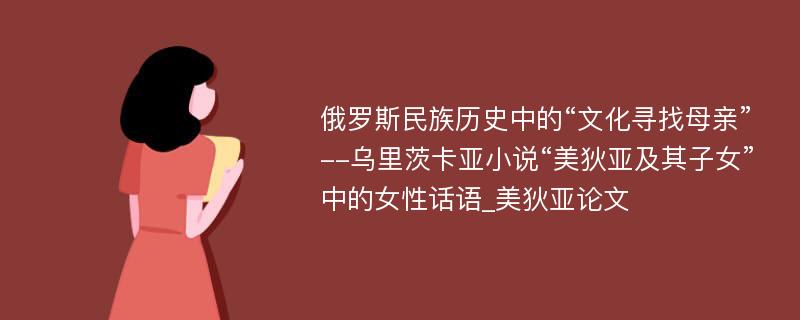
俄罗斯民族历史的“文化寻母”——乌利茨卡雅长篇小说《美狄亚与她的孩子们》中的女性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孩子们论文,长篇小说论文,话语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6)05-0054-08
进入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群的形成与女性文学的崛起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亮点。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部分女性作家创作的共同特征。她们希冀用女性独特的视点,女性独特的文化立场来赢得女性在历史言说中的权力,书写几百年来未被揭示的女性生命体验。俄国 1997年莫斯科—彭内奖①与2001年布克文学奖②得主、当代俄罗斯女作家柳德米拉·叶甫盖尼耶芙娜·乌利茨卡雅就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女作家之一。
乌利茨卡雅是写女性生活状态的作家。她始终以一种温和善意的个性笔法,关注普通女人的生活遭遇与生活状态。这些遭遇与状态无不与生命进程中女性自我生存的基本问题及她们的自然需求有关。在《美狄亚与她的孩子们》中女作家继续以往气质化的个人写作风格,但在延续一贯的生动写实与道德寓意相辅相成的叙说的同时,凸显了强烈的文化思绪,表现出强烈的俄罗斯民族历史的“文化寻母”意识——即在女性生命史中寻觅民族历史文化源头的审美追求。乌利茨卡雅通过对古希腊神话原型文化历史意蕴的当代言说,对俄罗斯民族生存历史中女性本源的探寻,对民族生存伦理中女性道德自主理念的揭示,实现了女性形象由“他者”叙说向自主自为的女性当代创作意识和创作实践的转换。
神话模式的重构及女性主义的文化意蕴
长篇小说的故事叙述与主题表达都借用了古老的希腊神话模式。小说中集聚着像美狄亚、奥林波斯山、酒神狄奥尼索斯、奥德修斯、鸟身美人头的哈尔皮厄斯、忠实的佩涅罗帕等这样一些神话原型形象。乌利茨卡雅以美狄亚为核心张扬了一种独特的女性意识与女性精神,它的多种意蕴使小说获得了丰厚的文化魅力。
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是一个妖魔形象。这个善巫术的女神因为爱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并把尸体切成碎块扔进河中。美狄亚在成就了爱人伊阿宋的英雄伟业之后,却遭到他的抛弃。美狄亚气愤之极,在伊阿宋新婚的时候,送给新娘一件毒衣,新娘穿上后立即毙命。为了不给丈夫留下一点儿盼头,美狄亚还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古老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是一个依附男性,视爱情为生命唯一的女性。她因被情欲折磨而丧失理智,不惜残害兄弟以及女性同类,还杀死亲生儿子,背叛祖国。作为自身情欲的受害者,美狄亚不相信世界有恒久的感情,更不相信会有最终的理智。这是个绝望的情人,恣肆情感而泯灭理性,逃避责任,弃绝义务,犯了背叛祖国、违父杀子、忤逆道德之罪。神话说明人在自身价值的失落中会丧失任何道德价值的支撑。
在《美狄亚与她的孩子们》中,乌利茨卡雅对传统的神话模式进行了重构并进行了新的文化诠释。女主人公美狄亚·西诺普里是一个居住在俄罗斯克里米亚海岸的希腊族后裔。少女时她在情场上一无所获,圣像一般的面容,胸平体瘦的形象,没能吸引任何的追求者。婚后26年的夫妻生活也没有给她带来后代,从丈夫去世起,她便开始了漫长的寡居生活。她的人生中弥漫着女人的痛苦、惆怅、悲哀与无奈。但这一切,包括最为让她痛心的丈夫的背叛也没有使美狄亚的心灵变得焦躁不安,她的情感世界丝毫没有因此变得孤寂、凶恶与残酷。过往的痛苦与怨艾都因最终历史尘埃的落定而消解,曾经沉重的身心也在和谐宁静的心灵中得到了缓释。
小说中的美狄亚在情感和意志的强烈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古老神话中的美狄亚,却拥有后者所不具备的正义、责任感和母性情怀。小说中的美狄亚与神话中的美狄亚都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前者是生理使然,后者是自己杀害了孩子。两个人都经受了丈夫的背叛。神话中的美狄亚残酷地报复自己的丈夫,用自己孩子的生命为代价,显现出人物性格内在的巨大悲剧性。而小说中的美狄亚受到的打击更是双重的,因为丈夫与之一起背叛的女性竟然是她的亲妹妹山德拉。这不仅仅是背叛,更是对上天伦理的伤害。但美狄亚却把自己的初恋,自己的心,一切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给了丈夫。她始终都是一人之妻,一人之孀,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安宁、静谧与和谐。
“美狄亚”不仅是女主人公的名字,还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黑海岸克里米亚古老的费奥多西亚镇的名字。作为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主人公,它如同生活着奥林匹斯诸神的奥林波斯山一样,在整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神话象征意义。它不仅是美狄亚生活的地方,更是“宇宙、星球、白云、羊群等万物为之运转的稳固的中心”,是大地中心的一块“圣地”,是一个伟大的、充满世纪沧桑的历史文化框架。在这个有声有色、充满生命和谐的大自然世界中,早先居住着西徐亚人、希腊人、鞑靼人、犹太人,后来又有了亚美尼亚人、哈萨克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这里有来自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移民,有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第比利斯、维尔纽斯、塔什干以及不知地球上什么地方的客人,这里有清真寺与耶稣教堂,还有犹太教与天主教堂,从这里离去的人们遍布俄罗斯和世界各地。黑海岸的克里米亚是人类生存地域的一种象征,是俄罗斯大地上的一颗古老希腊文化之种,一个离上帝最近的神圣的地方。它远离政治的漩涡,躲避着都市的喧嚣,清净、安宁,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政治斗争的峥嵘岁月,曾经拯救、庇护过无数俄罗斯的子孙后代。它在20世纪尽管得不到人们的爱护而充满忧愁,但历史的神灵却不愿离它而去,春色满园的景物中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会触动人们古老的历史记忆。
“美狄亚”其人、其地成了一种人类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美狄亚地域的美色令人心醉,但更让人心醉的是那未经尘世浸染的尽善尽美的美狄亚的魂魄。那个多年守寡、始终没有改嫁的希腊族人西诺普里和她的后裔成了当地风景和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狄亚”不仅仅是静止的人名、地名,而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的标志,成为女主人公人生萍踪浪迹的极见情味的景观,它浸染着她的品格情愫,被赋予了她的灵魂和性格。乌利茨卡雅用充满诗情的笔触,叙述了克里米亚“美狄亚文化”的融合、重塑、构造、完善的发展历程。它是古希腊文化与现代俄罗斯文化、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的融合,是苏维埃时代意识形态化与反意识形态化碰撞后的重塑与再造。
女作家没有拘泥于对精神文化的揭示,而是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这种精神文化的血肉——使它保持常新、常鲜的物质文化征象。美狄亚的一切都被赋予了重要的自然与物质特征:用天然石头砌成的厨房,用泥土铺成的地,小小的窗棂,挂在墙顶的干草,安放在木架上的铜制用具,陶制的罐,煮饭的生铁锅,腌渍茄子的大木桶,房顶上晒制的水果,三脚桶里煮着的衣被,美狄亚十九岁当姑娘时捡到的、三十年来始终戴在手上的一只金戒指,祖父哈尔兰皮的老式烟斗,不同历史时期的邮票,用香烟锡纸包着的30缕周岁儿童出生后剃下的各种颜色的胎发……作家通过对这些琐细零碎的物件的叙说,道出了质朴而又崇高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的物质支撑:对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永恒的记忆。
西诺普里家族的女人们生活健康、明朗而又自然,没有那么多人为藩篱的约束,她们善于与异性相处,崇尚古老的抒发自由情感的方式。小说中的山德拉、尼卡、玛莎、犹太女骑手罗莎等众多女性是古希腊神话中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的现代版。狄奥尼索斯的欢乐精神让生活在克里米亚岛屿上的女人们获得身心的彻底解放。美狄亚的妹妹山德拉和犹太女骑手罗莎,一生都在变换着职业与男人,多情的尼卡与玛莎始终把诱惑男人当作生命的重要精神食粮。美狄亚深藏着不可外扬的两个家庭秘密之一就是母亲年轻时与一对兄弟的恋情,她是带着身孕从格鲁吉亚的巴统嫁给她的父亲格奥尔吉的。乌利茨卡雅笔下的这些“奥林匹斯女神”决不接受“父式爱情”的霸道与悖谬,她们绝对是女性个体自我存在的典范。她们都不是传统性别模式中“沉默的他者”,而是传统文化生态中以男性为表象的文化本体的叛逆者。作家以直觉、细腻的体验和毫无顾忌的表述,充分展现了女性本来被遮蔽的欲望、狂浪放纵的生活方式和鲜活炫目的生存状态。
即使是死亡也像新生命的诞生一样充满了崇高的色彩。美狄亚丈夫萨穆伊尔的死是被作为一种崇高的,体验了人间爱的幸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结局来描写的。越接近死亡,他的精神与灵魂通过他的那张安详的脸也就越发显得崇高与美好。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美狄亚静静地享受着丈夫的存在,享受着安谧。玛莎的死是小说最具浪漫色彩的片断,临自杀前她在梦幻中与在车祸中丧生的父母相遇,与天使邂逅,在雪绒花汇成的乐曲中从阳台上跳下,宛若张开双手穿过飘落的白雪的飞行。美狄亚在漫长的人生中也已经习惯于忍受死亡,一次又一次地平静而又庄严地守着尸身生活,伴着喃喃诵读的慰灵圣诗,伴着毕剥作响的摇曳的烛光。
神话原型从来就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文化结晶,精神力量的一种源泉,但随着历史的进展它们需要不断予以重新审视与评价。乌利茨卡雅剔除了古老神话中美狄亚施恶作孽的妖魔成分,张扬了她源于生命本源的爱的神力,赋予她纯洁、忠诚的品格,慈善、宽大无比的圣母般的胸怀。这个处于小说审美时空中心的艺术形象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庄重与神圣感。乌利茨卡雅似乎在用女主人公崇高的圣母玛丽亚精神、无比的同情心和善良与传统的美狄亚神话进行论争,女作家在对世界与生活新的理解的基础上创造了20世纪关于美狄亚的新的多元神话:她既在用女性心灵中的宁静、和谐与爱来战胜世界的喧嚣、混乱与罪恶,还在用古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精神针砭压迫女性的流弊,昂扬女性身心的自由。她用20世纪的美狄亚比喻俄罗斯女性,让微弱的、非主流的、被淹没、被忽视、甚至被恶俗的声音响亮起来,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历史学的意味。
俄罗斯多民族的文化史也是一部女性史
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情节的主线是美狄亚及其西诺普里家族的生命史,同时还是黑海流域俄罗斯多民族的生存史,充满动荡的20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变迁史。这部生命史、生存史和变迁史同时也是一部女性的生命遗传史、生活苦难史、人生奉献史。乌利茨卡雅从传统的社会主流和男性中心价值判断中独立出来,高度肯定女性在延续生命,拯救家族,承继民族文化中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长篇小说中女性话语的另一个重要构成。
美狄亚的老祖父哈尔兰皮·西诺普里早先的妻子们六次生育,竟然没有一个存活的孩子,只是因为第二个妻子的吃斋行善,向上帝许愿,到基辅朝圣,西诺普里家族才有了一根独苗——美狄亚的父亲格奥尔吉。而在格奥尔吉迎娶了虔诚的耶稣教徒、美狄亚的母亲玛蒂尔达之后,西诺普里才开始了他们家族的兴旺史。祖母把她的小耳垂和夜视的特异功能留给了美狄亚和她的后代们,玛蒂尔达不仅把红色的头发遗传给了所有孩子,还给了他们坚强的性格与杰出的才干。西诺普里家族强大的生命遗传使得他们没有被其他血缘融合,其子孙后代没有被残酷的年代所吞噬。小说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说明,哈尔兰皮·西诺普里后代五光十色的生命与人性光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来自女性的遗传因子。
女性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女性的苦难和女人的独立都是俄罗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女性的历史在本质上也是人民的历史。女人的声音必定是历史的回声,不可能超越时代与历史。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在整个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女性的苦难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她们背负了太多原来不该由她们背负的苦难。女性的生存真实是不容忽视与忘却的,她们伟大的生命光辉是无法遮蔽的。
小说中女主人公美狄亚似乎没有进入社会生活,但她的个人经历,幸福与不幸,所承受的苦难程度,不同地都与社会与历史勾连。十六岁上,美狄亚的父亲、皇家军舰机械师格奥尔吉·西诺普里因有人蓄意制造的“玛丽亚皇后”号军舰的炸弹爆炸而身亡,九天后母亲去世。父母双亡后,西诺普里一家剩下了十三个孩子:五个哥哥姐姐,七个弟弟妹妹,美狄亚排行第六。她从此便担当起关照兄姐抚育弟妹的重任。国内战争期间,她的大哥被红军打死,二哥被白军杀害,从此家人天各一方。她的丈夫萨穆伊尔·门德斯曾经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却因为20年代初无法容忍余粮征集队枪杀妇女、儿童的血腥手段,而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二战期间,她的一个弟弟被法西斯枪杀,另一个弟弟被苏维埃政权迫害致死。正如为山德拉的孙女玛莎治病的一位犹太医生所言:“苦难会毁掉一些人,但也会造就另一些人。”(乌利茨卡雅:185)苦难造就了美狄亚伟大的人格,一生中她始终挚爱着故土、祖国、亲人,尽职尽责地做好镇上医院医士的工作。她的这种没有福乐荣耀作引诱的人格是高度含蓄内敛的,是以一种深藏着的生命潜流的方式默默地散发其魅力与馨香的。承载这种伟大母性品格的是一种蕴藏在俄罗斯民族心理中圣洁的宗教信念。
尽管在革命胜利后的新世界宗教精神已经消散殆尽,美狄亚却自始至终仍然保留着对上帝的虔诚,始终怀着与先人一样的真诚与上帝交流。永恒的宗教信念战胜了世俗生命中的怠惰劳碌,信仰缺失,不和谐和残酷。每天早晨,她都会默默地祷告自编的“清晨规则”,乞求神灵的保护,接受一天所有的劳累、烦恼、无聊的闲谈与晚间的疲惫,高高兴兴从早到晚,不会发火,不会生气。每天临睡前,她都要念叨自编的祷告词语,接受新的一天将带来的所有劳累、烦恼,不生气不焦躁。去教堂的时候她总是遵守各种教规与戒律,虔诚地祈祷。这个“像白痴一样”的圣徒从小就被生活赋予了一种责任感,做事无论大小态度总是严肃认真,始终如一。星期天,她天不亮就起床,步行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教堂做礼拜,傍晚才回家。一生中只有两次离开过克里米亚,加起来总共只有六个星期。女作家似乎在说,俄罗斯民族浓重的宗教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女性传承的。
淡泊自守、严格简朴的生活方式使她得以与家人安然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剧烈动荡的日子,无情批判的岁月。她善待三十多个第二代亲人,接待过无数来自祖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远亲、朋友。连邻居诺拉,一位勤劳善良、爱女如命的女性,也会在晚间将女儿放在别的地方,好在美狄亚的厨房里享受母性的温馨。每年美狄亚所有的亲戚们都要来到克里米亚,美狄亚的家仿佛成了人们争相朝圣的精神圣地。小说最后,连她的亲人们都不明白,美狄亚怎么会把门德斯家的房子留给了他们谁都不认识的名叫拉维利·尤素波夫的鞑靼族青年。其实,她留给外族青年的与其说是房产,莫如说是留下了让后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权力和可能。小说没有描写老妪美狄亚之死,她仿佛消融在人类永恒的时空中,成为历史的往事,留在了所有后代人的记忆中。
与美狄亚同样经受了人生沧桑并延续着族类生命的还有她的嫂子叶莲娜·西诺普里,一个来自斯捷帕尼扬家族亚美尼亚贵族的后裔。1918年,当国内战争开始,城市遭到炮轰,人们大批仓皇逃亡国外的时候,克里米亚旧政府成员的父亲斯捷帕尼扬也带着全家在撤离。叶莲娜带着中风的母亲留在了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镇。从那时起,克里米亚又多了亚美尼亚的家族血统。叶莲娜娘家几代人曾在亚美尼亚修建了许多教堂,她也承袭了家族信奉宗教的这一传统。她教育儿子格奥尔吉恪守治家之道,鄙视社会上的轻浮与世俗之风。格奥尔吉在母亲的影响下不顾朋友们的嘲笑,始终保持着对妻子胖卓娅的忠实。30年代,鞑靼人拉维尔·尤素波夫的母亲连同她的四个孩子被强行迁徙到哈萨克的卡拉干达,他们用叶莲娜送给他们的最心爱的蓝宝石戒指换了一普特白面,从而使孩子们度过饥荒存活下来。即使是对任何欢乐都不会嫌弃的女子山德拉也被赋予了善良豁达、乐观大度的美好品格。她真诚地将爱给予了每一个她所喜欢的人,质朴地将对上帝的信仰与自己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结合了起来。“她涂口红,喜欢打扮,开心作乐”,但也祈祷叹息,大方地帮助他人,为他人的痛苦哭泣。在玛莎的父母因车祸去世之后,她完全承担起抚育她的责任。她那望着圣像的深沉的目光,还有那对上帝的小声叹息,都使她的第三个丈夫、细木工伊凡·伊萨耶维奇把她看得至高无上、完美无比,对她的崇高品质深信不疑。来自第比利斯的姐姐阿涅莉也和妹妹美狄亚一样,没有孩子,但在战争期间丈夫死了之后,独自将来自夫家的孩子们养大成人。
俄罗斯多民族的历史之路是美狄亚和所有在克里米亚岛屿上的女性的爱之路的拓展与延伸,“母性”灵魂始终呵护着俄罗斯各民族的子孙。母性精神也为下一代女性所传承。山德拉的小女儿尼卡把母亲的全部原始之情都献给了侄女玛莎,生活在山德拉家的几年中玛莎感受到了如同春日般温暖的爱。尼卡内心对另外一个生命的完全接受是她对自己的子女从来没有过的,她会整夜整夜地守候在侄女身边,拉着她的手,天天早晨给她梳辫子,领着她在林阴道散步。阿涅莉的养女尼娜一心一意地照料退休后生病的美狄亚,二十年如一日地照料她那发了疯的亲生母亲。母性突破了家族的局囿,经得住时空的流转,在克里米亚大地上构造出一条又一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情感的虹桥。
战争、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大情势”下的“庸常”、“琐碎”的生活方式使女性始终扮演着社会细胞——家庭(社会实际是一个大的家庭)中的主角,成为男人生命依托的基石、生命快乐与希望的源泉、社会发展的根本。在女作家看来,动荡的社会与充满变革的历史属于无奈的现实存在,因此常常会被她忽略过去,她着意的是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小说中强势的女性心绪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小说似乎在告示读者,无论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还是政治生活动荡的阴影,其实都不重要,任何人的命运都不得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法则:新生命的诞生、爱情的纠葛、人与人的相遇与分离、亲人的死亡,而创造人类最基本生命法则与生命历史的正是伟大的女性。乌利茨卡雅从当前后现代主义泛滥的先锋潮中撤退到了女性丰盈的生活、充沛的人生经验上去。读者在小说中感受到的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体验,看到的是真正的血肉。小说作者以一种淳厚而又不张扬的美学情调,用其纤细韵味的诗意写出了由女人性灵精髓所决定的一部俄罗斯多民族的文化史。
女性生存道德伦理的箴言
——心灵的自由
“珍惜生活中种种可爱的细节,又拒绝他人干预自己的内心世界。”(乌利茨卡雅: 80)——这是乌利茨卡雅在小说中反复强调的美狄亚心灵自由的话题,它传达了作家对女性生存道德伦理的思考,也是她提供给读者的另一种女性话语的启示。
美狄亚作为女性的重要的精神特征是追求心灵的自由。她比任何一个克里米亚的居民更远离社会政治,她的人生家园就是她与她的亲人们自己,即使在战争、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重要时刻,也在坚守着属于她和她们自己的、不可能被任何人夺走的物质与精神的自由家园。一切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事件对于她来说只是“某种格格不入的来自远方的生活的喧嚣”。对她来说,所有的政权都一样,她的侄子格奥尔吉说,她并不在乎当局,她是虔诚的信徒,所服从的完全是“另一种权势”。她不像姐姐阿涅莉的养女尼娜的亲生母亲,后者如同希腊神话中鸟身美人头的哈尔皮厄斯,刁蛮凶狠,却对领袖竭尽愚忠。她对斯大林的逝世漠然置之,此时更为关切的却是亲人妹妹山德拉的命运。人有生老病死,社会有改朝换代,只要这个个体心中的家园自己不弃之,就无人能夺走;只要不辍地劳作耕耘,就会有丰收、繁荣、兴旺;只要把这块家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就能为之献出一切。热爱大自然,用法文写信,阅读赞美诗,遵守斋戒,祈祷诵经,缝制衣裙,采集草药,养育他人的孩子——这一切都是她自由心灵抉择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成为她生命中有机的构成。
美狄亚人生中短暂的婚姻与长久的孤独并非男性社会封建道德理念的产物,而是她对幸福、美好、和谐人生理念的独特理解后的自觉选择。乌利茨卡雅说: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对幸福的一套构想,而我并不重视幸福本身,因为幸福总是瞬间,人生中这样的瞬间寥若晨星。我重视的是我是否行为正确,是否能够处理好和别人的关系,达到一种生活的和谐。(侯玮红:19)
美狄亚关于幸福、和谐的理念是建立在对作为女性存在的独立自尊,即不依赖、不依附,同时又不厌弃、不支配基础上的自由意志、自由情感、自由思想以及对这种意志、情感、思想的捍卫上的。其实,她一生中尽管有众多“儿女们”的敬重爱戴,但总是孤独的时光更多,常与她相伴的是物质的拮据、疾病的折磨、精神上的挫折与打击,间或的快乐、幸福都是稍纵即逝,一大缸苦水,一小勺蜜糖。但她心灵上始终是快乐、幸福、和谐的,因为她深感身心的独立与自由。女主人公的这种道德抉择既是高度理性的,更源于对日常生活朴素的认识与理解,对先辈民族文化传统的自然自觉的继承。二十九岁上才有了爱情的美狄亚之所以看上那个不无放浪的犹太丈夫、牙医萨穆伊尔,是因为她发现了他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上帝的精神——无私的爱、绝对的真诚、伟大的仁慈。这既是她女性的择偶标准,也是她明辨是非,判断真伪,区分善恶的一种生存原则。“临走回首反省,良心是否干净”,这是美狄亚丈夫写在山上厕所硬纸板上的使用规则,实际上是美狄亚人生行为准则对每一个来人的告示。
女作家关于女性心灵自由的思想还表现在美狄亚自我心灵安顿、宁静和幸福的自我体验上。在家中的地位和角色,使美狄亚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她体会到为他人服务的辛劳,更看到平凡却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对自我潜能的开掘和由此带来的身心愉悦。妹妹山德拉婚前的第一个儿子谢廖沙就是在姨妈美狄亚的照料下出生的。她心系外甥,为他做了洗礼,成了他的教母,并帮助妹妹在莫斯科新的地方安顿下来。谢廖沙生命的第一个月恰是美狄亚充分感受到她所或缺的为人之母的体验。美狄亚母亲在为他们踩踏坎坷崎岖的生活之路,构筑充满爱与温馨的生命之巢,铺展广博美好的未来,美狄亚成为克里米亚俄罗斯多民族生命和谐之家的核心,与此同时,她自己也得到了心灵的和谐与宁静。美狄亚不仅让投奔她的人得到一种照耀与沐浴,自己也得到对自身、家、生活和世界的新鲜的理解。这种体验的循环所带来的诱惑和力量远远超过了她追求自身幸福的吸引力。美狄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家族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人,是因为她感受到自己从来就不是社会、家庭中被统治的对象而存在于文化的边缘,不是作为男人的“他者”存在,她是真正的主体,自我的真正的主体,与男人一并彻底融入了民族的文化之中。
美狄亚深为那些年轻的生命、女人们的欢乐感到幸福。虽然她坚信轻浮会导致不幸,但她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轻浮也会成功地造就女人的幸福,妹妹山德拉,外甥女尼卡和山德拉的大孙女玛莎的人生经验却证实了这一点。玛莎与她的丈夫有着与美狄亚截然不同的婚姻原则,他们夫妻的爱首先体现在一种共同的情趣、共同的话语中,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有着类似“兄弟姐妹”的亲情。他们并不恪守忠贞,因为他们的结合是自由人的结合,每个人都保持着独立自主的人格与权力。尽管在美狄亚看来,战后的一代人,尤其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有些像儿戏,她们的爱情、婚姻、母爱中缺乏最重要的责任感和忠贞如一的品格。但她仍被这种人间的欢乐所陶醉,从不对别人乱加评判,更不要说去谴责她们,躺在自己当姑娘时睡的小床上,她常常由此回忆起自己美好的人生时光。小说中关于离婚、婚外恋、多角恋和情爱细节的叙述仅仅是故事表相的叙事层面,深层的却是美狄亚对女性地位、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一种反省,是一种对女性身心自由的尊重与理解。女作家用具体精微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叙说淹没了传统道德的“理性之核”,使读者对女性人物的生活方式作简单机械的道德评判成为不可能。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人们只要与美狄亚在一起,就能感到温暖、可靠,就能体会到一种完全的身心自由。
正是这种稀有的自由精神成就了小说中众多女性的独立性,直面人生,张扬并依靠自己。山德拉在心灵自由的情与理的抉择中,选取了她所喜爱的重情的生活方式,她走的是一条用自己的是非判断的放纵情感的道德之路。生活的历练使长寿的她终于在暮年意识到了她与姐姐选择的差异。人的一生中难免有过失,但即使有过失,也需要自我规约。小说潜在的教诲是:人的软弱、过失在所难免,重要的是自己作为人的道德选择权,相信自己可以去除软弱,走上一条自我拯救、自我完善之路。作品中大多数女性的命运表明,妇女受压抑的原因不仅仅是其处于劣势的社会地位,更在于妇女自我的精神世界,因此女性精神解放的根本在于她的心灵的自由。女性生存道德伦理的原则不应该是男性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种种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而在于女性心灵自由主导下的生存抉择。女人在自身的行为中要能够行使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女人的权利,是对女人的尊重,也是荡涤罪恶、抗拒堕落的唯一途径。
美狄亚对自己情感和角色的清醒把握,透出一个现代女性聪慧的智性和独立的意识。尽管世事艰难,尽管没有浪漫,她还是活得自由洒脱。她的身上洋溢着独立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她用她女性顽强的生命通过深切的柔情传递出了社会关怀、人性关怀和人文关怀。女主人公赢得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价值,还赢得了家族中男性和其他女性真正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的尊重、理解和爱戴。美狄亚独立的性情与品格,没有随着历史时代的流转,人情世故的变化而钝化,相反,像陈年的佳酿,滋味醇厚,芳香四溢,显示出种种世俗女性难得的感人魅力。
“俄罗斯是一个充满不幸女人的国家,所以我们这些发声者天生就爱抱怨”,(侯玮红:17)“有两点绝对没有妨碍过我,一个是我是个犹太人,一个是我是个女人”。(周启超:281)这是乌利茨卡雅关于文学创作的朴素的女性话语。女性主义是多元的。乌利茨卡雅从“细微的家庭叙事”中剥离出了女性的人生体验,看到了女人在时代巨大变迁中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重建等问题做出的历史回应,找回了女人的历史。她的女性主义未必是对男权主义的颠覆,女作家也未必是想通过对女性人性美的赞美与讴歌分享男权主义制度下专属男性的权力,从而倡导一种女性中心主义,确立一种以女权取代男权的叙事话语,而是力图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以重新认识当下俄罗斯人生活的,及至由两性构成的人类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篇小说《美狄亚与她的孩子们》为我们更好地全面了解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女性话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注释:
①1996年由俄罗斯作家协会与意大利地区性的文化团体共同设立,由专家与读者共同提名推选的文学奖项。
②1991年由英国公司设立,专门奖励长篇小说创作的有广泛和重大影响的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