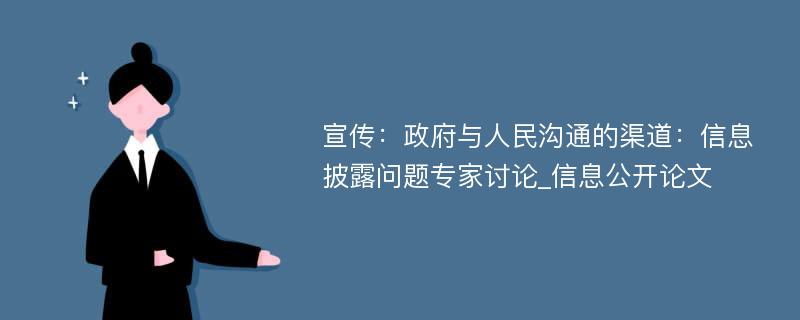
公开:沟通政府与人民的渠道——信息公开专家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渠道论文,政府论文,专家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与主体
提到信息公开,作为占有社会整体信息总量90%以上的政府自然是首当其冲,那么政府信息公开就成了焦点。何为信息公开?政府应当公开些什么?就这个问题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李步云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周汉华博士如是说:
李步云:什么是信息?很难下一个定义,因为它的内涵十分广泛。一般来说,信息与信息载体分不开。也许是考虑到这一点。台湾在立法上使用了“资料档案自由法”的称谓。信息公开、信息自由和知情权这三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但不宜在它们之间划等号。例如,政务是否公开,公开哪些,用什么形式公开,是行政机关的事情,不是公民说了算。公民有要求政务公开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知情权。信息自由也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包括获取信息自由和传播信息自由两个基本方面。知情权主要指公民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可能不包括传播信息的自由,但知情权是传播信息自由的理论依据。只有信息传播自由,公民才能更好地实现知情权。各国家机关实行信息公开,既是一项职权,更是一项职责。这同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有严格区别的。同时,这种信息公开,也不包含有获取信息自由的内容。
周汉华:根据各国的法律,其实政府公开的并不是信息,而是信息的载体,即能够反映信息存在的各种文件或者电子形式的载体。之所以作这种区分,是因为纯粹的信息是不可触摸的,也无法验证,如传言与小道消息等等。对于这种信息,政府机关无法掌握,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外公开。只有信息附着一定的载体之上,如书面材料、电子材料等,才可以为政府机关所拥有和对外公开。例如,1999年制定的日本信息公开法所规定的作为公开对象的行政文件是指“行政机关的职员在职务活动中制作或获得的,供组织性使用的,且由该行政机关拥有的文书、图画以及电磁性记录”。在美国,当事人可以根据信息自由法申请公开联邦政府机关的所有材料。材料的保存方式并不影响其是否应该公开,书面的、录音的、地图、照片、计算机输出的材料、计算机软盘等等都是申请的对象。
作为信息公开对象的载体主要是书面形式的文件或者档案,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形式的载体也越来越常见。然而,不论信息的载体发生什么变化,政府机关都有义务公开其所掌握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信息公开的提法应该说比材料公开或者档案公开等的提法要科学得多,也便于司法机关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
信息公开的主体即谁有权公开信息,它是信息公开的一个基本话题,它使信息公开行为具体化,政府信息公开,当然政府是公开的主体,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成为公开的主体呢?《岳麓法学评论》主编郭道晖教授和李步云教授认为:
郭道晖:谁有权或有义务公开信息?谁有权要求公开信息?这就是信息公开所关联的两个主体。前者是掌握信息而又有权力或义务公开信息的主体;后者是享有“知情权”的有关社会成员。
在民主国家,“信息公开”的主体主要是指受人民委托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亦即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其所需公开的是与社会成员利益相关的政务。这种政务公开,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
现代社会,随着国家——社会二元化,许多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事业组织,多元化的社会团体,都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和信息,从而也就有了可以支配他人的社会权力。它们对于其所属的内部成员,和与其利益相关的外部社会成员,也都有应予公开的社会公共行政事务、校务、商务、社团和社区公共事务等等。即使是医疗卫生机关团体,也有医务公开的义务。这些社会主体的社务信息公开,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信息公开的主体,已不限于国家权力机关,还有社会权力组织和社会公共团体。
此外,在互联网时代,公民个人也掌握大量信息。他们公开传播有益于社会人群的信息,也应属于公民信息自由、表达自由的权利;而且公民掌握的信息,有时还可以成为影响、支配他人的社会文化权力。现在在因特网上,网民们事实上已在行使这一权利与自由;有的黑客则进一步把这种信息自由权利转化成个人的信息权力,在因特网上显示其破坏力。这些表明,在现代化社会,公民不仅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也可以是信息公开的权力主体。
可见,在现代化的民主和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相对于政府,既享有知情权,又有信息公开的权力或权利。总之,信息公开与信息自由的权力和权利都应当掌握在人民手里。这应当看作是民主、自由的一大进步。
李步云:信息公开的主体,依据信息公开、信息自由和知情权这三个概念的区别,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权利主体是公民个人。其义务主体首先是国家机关,因为他们有保障公民个人享有获取与传播信息的自由和知情权的职责。其义务主体也包括其他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因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妨碍、压制和破坏公民个人享有获取与传播信息的自由。在西方,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国家机关,但也有不少国家包括国营企业,这当然是针对广大公民而言。今天,我们讲信息公开,主要是指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机关;同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实行信息公开也很重要。
二、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
学界一般把知情权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但是知情权是一个法理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宪法上的概念,我国的宪法并没有对知情权有过明文规定,那么知情权在我国是不是有法律依据呢?它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又在哪里呢?李步云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作翔教授是这样认为的:
李步云: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不可剥夺的性质。在实践中,它同时也具有请求权的性质,即有权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公布它们应当公布的某些信息。信息自由是一项“消极权利”,即国家机关不得侵害公民那些合法与合理的获取与传播信息的自由。知情权和信息自由是属于个人人权的范畴,它的享有和行使方式主要是公民个人。信息公开是现代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它也具有制度性特点,即哪些信息应公开,以什么途径和形式公开,都要有具体的详细的规定。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制度是基于公民享有知情权和信息自由权而建立的,但它本身并非人权,而是属于民主与法治的范畴。信息公开作为一项原则和制度,应当体现在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发展水平上,是现代民主与法治是否建立与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制度问题上,充分表现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职权与职责)的相互关系:是公民的权利产生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相反;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权力是手段;国家权力容易腐败(失职、越权、权力异化等)需要公民权利予以监督和制约。关于加强信息公开的法律保护,重要的是加强宪法对知情权的保护。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宪法虽然没有对知情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知情权是一项宪法权利,可以通过“权利推定”予以肯定。因为仿照“人民主权”的原理与原则,人民理应享有知情权。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加强宪法对知情权保护的重要一环。
刘作翔: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首先应在宪法层面得到确认,这是知情权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当然,这一论点首先是建立在对知情权和权利性质的认识基础上的。知情权究竟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还是一项基本权利的派生权,或引伸权,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引伸权,它可由言论自由权引伸出来,言论自由权就内含了知情权。因此,没有必要专门确认一项知情权。而我认为,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有联系,但不属同一性质的权利。首先,言论自由权是一种“输出”权,即由主体向外“发送信息”“发表信息”的一种权利;而知情权是一种“输入”权,即主体从外部接受信息、索取信息、获得信息的权利。因此,这两种权利的实现途径是不一样的。其次,言论自由权没有特定的义务人,只要在法定范围内,权利人就可以行使此项权利;而知情权的行使一般要有相对的义务人,即要有相对的“知情”的“人”,这种“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如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委会等等,也即凡需要知情的事项所涉及到的“人”,都是知情权的相对义务人。而相对义务人履行义务,是知情权行使和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此一点正好可以解决有关“哪些主体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的争论。法律不好用一一列举的方式来标明哪些主体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因为这种列举是难以周全、难以穷尽的,法律拟用一种概括的语言,来标明不特定的主体,当所涉事项涉及到某一相对主体时,相对的主体便得以显现。因此,法律应该是概括式的,而不应该是列举式的,这恰好是法律的特点,至少在知情权义务主体和“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上是如此)。再次,如果说,从言论自由权引伸、推导出知情权,会使知情权处在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很难使知情权成为一种重要的基本权利。第四,我们不可把宪法基本权利看得太过“神秘”,基本权利作为一种主观权利和客观权利的结合体,它本来就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及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总的发展趋势是,社会越发展,权利种类便越丰富、越增加,由应然权利变为法定权利,再变为现实权利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就越大。这也正是法治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将知情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确认到宪法的基本权利之中,是解决知情权问题首要和关键的环节。
信息公开究竟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义务,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一样,结果可能也会迥然不同。
郭道晖:信息公开是权力还是权利,或者义务与职责?对享有知情权的权利者而言,当然是权利;对权力者而言,公开信息则不应是他的权力,也不是权利,而是义务或职责。因为,权力者(此处主要指国家权力)所以能掌握有关信息,是凭借其掌握的权力;而这权力最终都是权利人(公民)赋予的,因而其信息不得据为权力者私有;公开其权力活动的信息,是权力者为权利者服务和接受权利者监督所应履行的义务。
但是,长期以来,权力者,特别是国家权力者,往往运用其权力,垄断信息,拒绝公开;或者把公开相关信息,看作是他们对相对人的恩赐;公开多少,也只是由政府“钦定”。这是权力与义务的脱节,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颠倒。
政府情报是多样复杂的。有些属于国家机密,不应或一定时期内不应公开。但决定是否公开和公开多少以及公开时限的权力,也不应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即由立法机关(在我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运用立法权,制定情报公开法和保密法。政府是依法执行,亦即依法履行其情报公开的职责。当然,在法定范围内,行政机关在具体执行中,在掌握公开与保密的界限与量度上,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
在我国,一些行政机关之所以往往把信息公开看成是由自己决定的权力,而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还由于受中国几千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
知情权与信息自由更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关系宪政的实施和国家与人民事业的兴衰。它是公民行使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结社、出版等表达自己和选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基础,也是由这些基本权利衍生的,不得剥夺。公民的知情权和信息自由不是洪水猛兽。试图完全遏制和封杀,是不明智的(当然适当加以法制的规范也是必要的)。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实行情报垄断和新闻封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信息公开的意义和价值
人们呼唤政府信息公开,对政府信息公开寄予厚望,但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它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和社会价值又是什么?这也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步云教授和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的温晓莉教授的观点会给我们以更大的启示。
李步云:信息公开的价值主要有:第一,信息公开是主权在民的体现。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办事情,主人应当知道,否则人民怎么当家作主?第二,信息公开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前提。立法、执法、司法的透明度愈高,公民实行监督的可能性就愈大。第三,信息公开是政府科学决策的条件。什么事情都“暗箱操作”,公民想政治参与也是很难的。第四,信息公开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保障。公开性是预防不正当竞争和欺诈行为的良药。第五,信息公开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好途径。公民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怎样才能保护,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实际做了什么,他们才能有效地为维护自身权利而斗争。第六,信息公开也是防止国家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杰佛逊所言,“阳光能够杀病菌,路灯可以防小偷”是颇富哲理的。政府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一切腐败行为就难以滋生与蔓延,也较易发现与整治。
温晓莉:“政务公开”是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1、政务公开是国家政治权力现代化的必然发展。
国家政治权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公共理性”的不断增强。所谓“公共理性”,指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具有程序上的公开性、正当性,从而以程序上的正义保证政治权力的实质正义的实现。
政治权力在现代国家的发展中,除了仍然具有阶级统治的职能外,它的社会公共职能正日益扩展。伴随政治权力“公共性”的增加,“公开性”也必然成为权力行使的一个显著特征。
2、政务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得以实现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前面已有人说过,这里不详谈。
3、政务公开是防止权力腐败和权力不当行使的重要机制。
历史和现实表明,任何政治权力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实现权力主体所追求的利益和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复杂性和权力本身的特性,它又极容易导致腐败。因此,政治权力的行使不仅需要物质性的强制力和知识、智慧,更需要抗腐蚀的能力。而政治权力这种抗腐蚀的能力,只有在权力的公开行使中,在社会的公开知晓、评判和讨论、协商中,即在一种民主的监督中才能获得。仅靠政治精英和贤人政府的自律、自省来避免腐败,只能是幻想。
4、政务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使然。
政务公开在我国当前实行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还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其上层建筑必须自觉适应它的发展。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实行,使得政治权力的行使再也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任意、专断和暗箱操作。为了增加政府在市场管理中的信誉,降低市场交易的风险,就必须把政府的服务成本降下来,减少政务管理的中间环节,变“黑箱”为明示,使政府管理行为规范、公开、明确、高效。其次,为了适应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也需要增加政治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经济自由度”,而“政治管理水平”则是“经济自由度”评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政治权力行使中充满了“暗箱操作”,则意味着政府花费、审批等行为不受制约和监督,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很高,那么其经济的自由度自然也就低。这不仅会延缓和降低社会财富的运转速度和效益,而且会大大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
5、政务公开还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到来之际的势所必然。
信息社会与知识社会到来对现代国家权力最明显的冲击之一,就是由政务信息的重要性引起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行使方式的深刻变革。
政务信息已成为现代国家权力决策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不够,政务信息量严重不足,信息沟通渠道受阻,信息不真实等,都将导致政务的不正常和社会管理的低效,甚至失控。这就迫使政府更主动地寻求公民和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反馈,更重视保持政治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各种信息渠道的联系与沟通,这也必然要实行更直接、快捷、广泛、低成本的“政务公开”方式。
6、政务公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法治实行的标志之一,就是程序的公开、透明。因此,法治与政务公开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同时,“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法治国家权力,而法治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必然要求权力公开、规范、明确地行使。法治的另一作用就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法治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了解权、政治参与权等基本人权实现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国家政治权力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行使。
(原载《法制日报》)
标签:信息公开论文; 知情权论文; 政务公开论文; 政府信息公开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沟通管理论文; 法律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