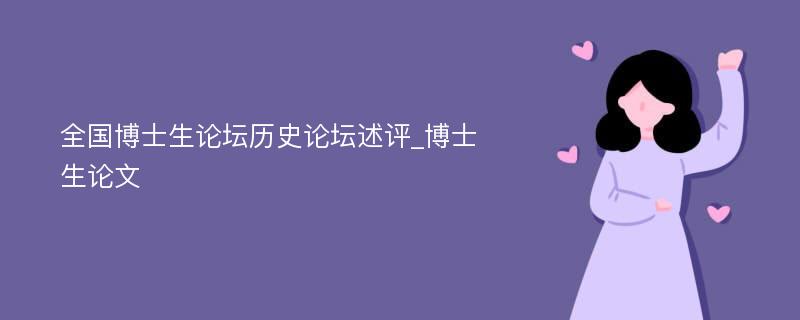
点斑窥豹 滴水探海——“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历史分坛”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博士生论文,学术论文,全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671-881X(2005)02-0254-03
2004年10月18日—21日,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历史分坛在武汉大学顺利举办。本次学 术交流共收到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28个博士生培养单位的121篇学术论文,经过论 坛组委会的匿名评审,共有78人取得了参会资格。其中武汉大学参会27人,占参会总人 数的34.6%;外单位51人,占参会总人数的65.4%。
博士生是我国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它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水平。从参加本次论坛的博士生的学术经历分析,既有在相关的学科领域小有 名气的专家,也有应届博士生。本次学术论坛的参会论文所涉及的学科门类非常广泛, 不仅涵盖了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法律史,而且新的社会史学、心 态史学、后现代史学等等也均在论述之列。本次论坛参会论文的新颖选题“基本上反映 了当前史学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当今史学欣欣向荣的局面”[1](第18页)。通过这些论 文,我们可以看出博士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热点与优势。因 而,通过这些论文反观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思路。就笔者的浅见,本次论坛 有4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史学的发展趋向,值得关注。
一、重视学科建设,关注史学理论
众所周知,在“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史学界出现了轻视理论的倾向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指出了史学界所存在的“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人少了”[2](第13页),后来有学者将这种治史倾向和史学研究潮流称之为“回到乾 嘉去”的史学思潮[3](第118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还有学者认为史学界对理论的 兴趣不大,“从80年代以来理论稍显沉寂”[4](第138页)。今天,这种理论缺失的局面 终于迎来了改观的良好征兆。
本次论坛参会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出各高校研究的传统优势领域,……其间 亦可以看出部分高校在维持传统领域研究的同时,不断加以拓深而产生的新的研究领域 及课题。”[1](第18页)这种拓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学科建设理论的关注和探索 。段天璟在《解析陶器——从实践到理论的尝试》一文中,在分析考古学界在陶器分析、研究方面的典型范例,将前辈学者研究中所包含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概括,总结出以“通过分割、拼合陶器器形以找到其基本特征的”“解析陶器法”[5](第37页)。在环境史学和城市史学领域,钟年在对费孝通的《乡村中国》、《江村经济》等著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田野实地调查的经验,提出了“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应该坚持假设与验证循环推进的学术路向”的观点,指出“‘实地调查’的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携起手来,将是中国文化研究获得进步的重要保证”[5](第275页)。
本次论坛尽管来自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很少,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其 它专业的博士生对史学理论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他们纷纷选取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结合 自己的专业写出了质量较高的文章。于展的《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以 美国学术界对民权运动的研究为例》、方秋梅的《清末民国时期“近代”、“近世”词 义的演化及其史学影响》、张仲民的《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评》等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所有这些迹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当代博士生所具有的自觉的理论探讨兴趣与鲜明的 学术创新勇气。本次论坛对学科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重视,相对于上个世纪末有的学者所 批评的“一些史学家中间,尤其是年轻的史学家中间,似乎对理论的兴趣有所削弱”[6 ](第20,21页)的局面来说,是一个很大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史学界对 理论认识的深化。
二、探索研究模式,致力新社会史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总结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道路时,曾指出:“直到20世 纪中叶,社会学理论才逐渐取代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945年,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 已成为研究的重要模式。”[7](第86页)本次论坛对这一研究视角和创新思路也给予了 广泛的关注。其中区域经济史、民俗个案、特定制度职业的研究分析最具有典型性。这 种以小见大的新社会史的研究理路已经为史学界相当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并且已经取 得了可观的成果,昭示着历史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趋势。
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这一研究思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一些值得进一步 商榷和完善的地方。有人说时下新社会史研究的缺点就和它取得的成绩一样多,这是有 一定的道理的。首先,新社会史的研究路数曾批评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 的弊端,但尽管新社会史研究的选题和研究的视野都大大地缩小了,也尽可能地关注下 层民众的生活,可是仍然很难摆脱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可见,这种弊端的产生 并不完全是以往社会史研究所固有的缺陷所致。其次,新社会史的研究小选题倾向极容 易导致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经济史、制度史研究的狭隘化,造成历史研究的碎化、专 业化的程度的加深。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充斥的公式、图表、模型和数据不仅让一般的读 者望而却步,而且即使是不同研究方向的历史研究者也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历史学由此也极可能更加脱离大众,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再次,新社会 史的研究路数往往是注重对个案的分析、调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增加了造成历史研 究中“孤证不信”现象出现的可能性。社会的有机性决定了众多个体的研究成果的简单 相加并不一定得出对特定时期社会的整体看法。个案真相的求索、考证得出的只是历史 研究过程中的“历史知识之真”(历史事实),而要想真正求得“历史发展之真”(历史 规律)[8](第79页),还是必须在宏观研究上下一番苦功夫。在这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作为 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进行新的探索恐怕还不失为一个理智的选择。最后,新的社会史研 究过多地注重个案的考索,而很少涉及到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正如现代化研究很难避 免造成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历史研究过多地关注地方、民众以及基层政权很有可能造成 基层与中央、民众与政府、局部与整体的对立趋向。过多地强调历史文化中的异质因素 ,恐怕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民族精神的培养等工作的开展带来负面效应。因 而这也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的。
三、注重总结旧法,探讨尝试新技
理论与方法很难截然分开。本次论坛除了对理论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外,还表现出了自 觉的方法论意识。参会博士生的文章透析出,他们除了勇于探索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之外 ,还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范式相结合赋予其新的内涵。首先 ,数学分析法在本次论坛参会论文中的运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本次论坛的论文集所 收录的23篇全文中有11篇不同学科门类的学术论文使用了相当专业的图表和数学分析数 据,占收录全文的47.8%。蒋刚的《盘龙城遗址群出土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樊如森 的《天津——近代北方经济的龙头》、范立君的《“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关内移民》 以及郭爱民的《从土地产权的变革看英国农业革命》等文章是这一方法运用的典范。数 学分析法在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当中所占有的分量和认可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因而,这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史学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趋势。
其次,大力倡导并切实实践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田野调查法。钟年不仅在文中大力倡导 和阐述田野调查法的重要意义,而且还主张把田野调查法与现实研究结合起来。他认为 :“有了实地调查的基础,形成的看法就会比较接近社会文化的真实面貌,再把这看法 拿到更广阔的田野中去验证,由此得出更加符合社会文化真实面貌的结论。”[5](第27 5页)作者并没有于此止步,而是更进一步提升田野调查和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概括 出“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应坚持假设与验证循环推进的学术路向”的大胆设想。
再次,对比较方法的重视。比较是一种古老的史学研究方法,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 野中的比较则具有一种凸显个性、发掘规律的独特功能。南京大学闵凡祥的《国家社会 保障职能的缺位与社会发展——以18、19世纪中国清帮和英国友谊会为案例的分析》一 文,则对起初性质基本相同的中国清帮和英国友谊会进行了深入的比较。作者得出了如 下的结论:“当时的中英两国政府对二者的不同政策决策及所采取的措施对它们的后来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清政府的摧毁镇压政策最终将清帮‘逼’为一支势力庞大、 为害一时的黑社会力量”而英国政府则成功地把友谊会“‘驯化’为广大社会下层成员 的社会福利组织”[5](第249页)。作者的高明就在于,在具有共同本质的事物中比较其 “同中之异”,而最后又能够不止于比较,在高度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抽绎出命题中所 蕴含的“异中之同”来。
四、聚集深层动因,关注现实变迁
从参会论文的选题来看,本次论坛聚焦于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的深层次原因的探讨,关注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历史现象研究。这也恰是对20世纪90年代 以来史学界所存在的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第5页)学风的纠正。在这一点上 表现出了与以往史学研究注重重大事件本身的研究不同的思路和视角。
同时,这种大历史的研究理念还表现在对客观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与研究上。 这种良好的选题意识和初步尝试,为历史研究进一步向更深入、辩证的方向发展奠定了 基础,提供了可能。
此外,本次参会论文的选题还表现出紧密贴近现实,关注现实社会运动发展变化的倾 向。透过论作,人们可以洞悉时代发展变化的脉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的社会 运动变化对史学研究的诉求以及当代的历史研究者所作出的无愧于时代的回应。而此外 ,对于工商业问题、移民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险等问题的关注 也较为充分地体现出历史研究的关注现实、瞩目民生。
无庸讳言,本次论坛在学术方面也存在着缺憾和不足。首先是对史学遗产的继承研究 重视不够。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历史的继承与创新”,但真正从这一角度出发的作文就 入选的文章来看是甚为寥落的。其次是缺乏开阔的世界眼光和全球化的学术视野。对国 际史学研究中的热点关注不够。再次是具体到论文的写作方面,参会论文对史料的处理 、论点的锤炼、论证的逻辑性等方面也都存在着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之处。
总起来看,本次历史论坛是一次成功的博士生的学术盛会。它不仅使每一个参与者都 受到了锻炼,而且对于会议的举办者来说似乎也找到一条优化博士生教育、提高博士生 培养质量的好途径,而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也是一次交流、展示和发展的好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