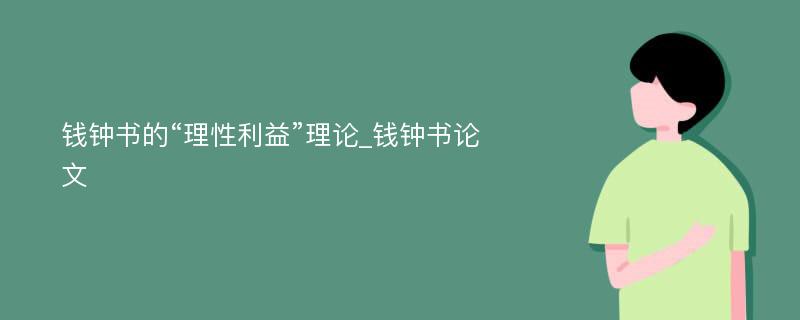
钱钟书的“理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钱钟书论文,理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钟书先生曾指出:“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事实上,古今中外众多文人学士,都曾在“打通”或“融汇”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中国古代的“理趣”诗,就是追求文理兼得的结晶,它将哲理融合于形象情感之中,使思考充满信手拈来的鲜活的情趣,力求在悟道识趣上高人一筹、深入一境。钱钟书先生对此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他说:“窃谓理趣之旨,极为精微,前人仅引其端,未竟厥绪”。(《谈艺录》P224、下引不注)为此,他从30年代的《谈艺录》到70年代的《管锥编》及其以后的补订,对理趣诗问题作了许多精彩的论述。《钱钟书论学文选》(舒展编)曾以“论理趣”为小目类集,但脱漏太多,不足以见钱先生的析辩之心,故有必要再下一番梳理的功夫。或许由此也可窥见其治学方法之一斑。
一、“理”字辩析
钱先生的文艺批评反对只讲抽象概念而不务艺术分析的风气,讨厌“以虚夺实”的诡辩家。他说:“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可以此考史,可以说教、然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毛诗》卷论《狡童》);“以文论为专门之学者,往往仅究召号之空言,不往词翰之实事、遂滋囫囵吞、胡芦提之弊”。“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笔之实事”(P572)“盖勤读诗话,广究文论,而于诗文乏真实解会,则评鉴终不免有以言白墨,无以知白墨矣”(P481)。钱正是从具体的诗歌分析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理”最初指玉石的纹路,后逐渐扩展引申为“文理”“法理”“万物之理”(义理)。而许多人却把“理”作道德解会,袁枚、贺裳就是其中二位,钱钟书也正是以辩析“理”字开始,展开他的理趣论的。袁枚《随园诗话》卷三驳沈德潜“诗无理语”的说法:“或曰: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见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何尝非诗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语,便令人闻而生厌矣”。其实《诗·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是说明文王的光明敬慎。《诗·大雅·思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指文王不闻善言,也自敬慎;不听见谏劝,也入于道德。这两句都不是凭空说理。袁枚下面举的《文选》,唐人、宋人的句子,也“既非诗家妙句,且胥言世道人情,并不研几穷理,高者只是劝善之箴铭格言,非道理也,乃道德耳”(《谈》P222)。而袁枚“闻而生厌”的“月窟天根”,出自邵雍《击壤集》卷十六、十七:“月窟与天根,中间来往频”“困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钱认为这些诗句“固亦不佳,然自是说物理,与随园所举人伦之规诫不同。……抑随园既言尧夫此等语‘闻而生厌’,则明认理语为不可入诗矣,何以又谓不然”。所以“子才所称‘诗中理悟’皆属人事中箴规”。无独有偶,清人贺黄公(裳)也把“理”作道德解,并举元结、孟郊、韩愈、李绅属于教化类的诗,意在说明“理”不能废,驳严沧浪的:“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清人黄白山不同意贺裳的看法,认为:“沧浪理字原说得轻泛,只当作实事二字看,后人误将此字太煞认真,全失沧浪本意(《载酒园诗评》卷上)并举陆龟蒙的《自谴》七律三十首为例,这三十首诗各有各的意思,相互不连贯,亦不如题目所云非“自谴”不可,而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如“五年重别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更感六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多情多感自难忘,只有风流共古长。座上不遗金带枕、陈王词赋为谁伤”。黄白山认为这类诗是属于“无理而有趣者”,不一定“非以鼓吹经史,裨补风化为理”。钱认为黄白山驳贺裳(黄公)解“理”字太隘,驳得有理,但未必合乎严羽本意,严羽的原话是:“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钱认为严羽“所谓‘非理’之‘理’,正指南宋道学之‘性理’;曰‘非书’,针砭江西诗病也;曰‘非理’针砭濂洛风雅也,皆时弊也。于‘理’语言而不详明者,慑于显学之威也;苟冒大不韪而指斥之,将得罪名教,‘招拳惹踢’”。钱在《宋诗选注序》中说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所以,严羽提出“非关理”,正是反对将诗变成押韵的公文和“语录讲义”,但严羽并不笼统地反对“理”,他在提出非关“性理”之“理”后,紧接着就提出了“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明刻本作“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于是针对这一情况,一些主“理”而又反对“理路”“理语”者,便创造出了一个与之相对待的诗学概念——理趣。通过对“理趣”之“理”的辩析,我们已约略可见钱对诗与理的基本看法:作为诗的意理内容之“理”,可有哲学玄思、人生智慧、修齐格言、箴铭警句等诸多含义,概括面极广,于诗不可或缺。作为“理趣”之“理”,当指“道理”而非“道德”;指“性理”而非“人事之箴规”;指“万物之理”“说物理语”而非“修齐格言”。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从钱总结的“以诗言理”史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二、从“以诗言理”到以“理趣”论诗
钱为辩析理趣的精微之旨,还对“以诗言理”的诗歌发展史作了细致的考察,他先把“以诗言理”放在历史发展中分为二大宗:一则为晋宋之玄学,一则为宋明之道学,后来他又在附说、补订中追论了道士之诗和释氏之诗、诗人为道诗和词章家为禅诗。为了叙述方便,根据“理”的内容,且分作玄学诗、佛理诗、道学诗三类来论。
正始时期诗歌中的哲思倾向可看作后来玄学诗的滥觞,过江后的东晋是玄学诗的兴盛期。从现存玄学诗中诗人对宇宙人生规律的体悟玄思来看,确实反映出当时人的思想的成熟,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精神反思水平的提高。然而从诗艺的角度而言,却是干瘪苍白、了无兴象、未达理趣之境,被《诗品序》讥之曰:“贵黄老,尚虚谈,理过其词、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亦称之曰:“诗骚体尽”。唐以前释氏所作之诗,“或则喻空求本,或则观化决疑,虽涉句文,了无藻韵”;居士林中为此体者,若王融、梁武帝、简文帝所作,亦“语套意陈,无当理趣”。佛理诗的面貌在初唐以后稍变。这里所言佛理诗,乃就广义而言,它通常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佛家禅师的诗体佛学和佛典中的偈颂,理胜于词,质而不韵,虽同诗法,或寡诗趣。二是诗僧佛徒用以宣讲佛理教义的通俗佛理诗,梵志、寒山、拾得诸家可为代表。钱评曰:“梵志之句,乃禅和子筋斗样子之佻滑者,虽亦有理,不得为诗”,“初唐寒山、拾得二集,能不搬弄翻译名义,自出手眼;而意在砭俗警顽,反复譬释,言俚而旨亦浅”。三是在俗诗人表现佛禅意理的作品,唐宋诗人多有所作。诗人之佛理诗有直接用佛语明禅理的。如王维的《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白居易的《读禅经》等;也有寓佛理绘禅境而富于禅意理趣的,如王维、刘长卿、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在这方面都有杰作。但这类诗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入宋以后,道学诗大盛,它也包括诗人所作与道学家所作两大部分,以后者为主。宋末金履祥编道学诗选《濂洛风雅》,列48家,清代张伯行再编《濂洛风雅》, 选17家。钱认为:“《濂洛风雅》所载理学家诗,意境即庸, 词句尤不讲究。即诗家长于组织如陆放翁、刘后村集中以理学语成篇,虽免于《击壤集》之体,而不脱山谷《次韵郭右曹》、《去贤斋》等诗窠臼,亦宽腐不见工巧”。但是,钱钟书对道学诗人并不是简单否定,他说:“宋之理学家,未尝不略悟斯旨。《河南程氏外书》时氏本《拾遗》记明道曰:“石曼卿诗云‘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此诗形容得浩然之气”。又说《汴京纪事》的作者刘子辉“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宋诗选注》),还极力推重鲜为人知的林肃翁:“自宋以来,能运使义理语,作为精致诗者,其惟林肃翁希逸之《竹溪十一稿》乎。”(P234)
“以诗言理”虽备受责难,但终究有大量优美诗篇和散联警句经久传世。如何评价这一现象呢?以诗言理不同于言志缘情,因此不能以传统的言志论和缘情论作为取舍的尺度,审美特性不同的作品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于是以“理趣”论诗便应运而生了。对此,钱钟书也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考查:“理趣”一词初见于唐代释典,初与文艺无涉,如《成唯识论》卷四论“第八识”:“证此识有理趣无边,恐有繁文,略述纲要”;又卷五论“第七识”“证有此识,理趣甚多”。“理趣”一词由禅学转化为诗学,当始自两宋(按,唐王昌龄《诗中密旨》有“理得其趣”之说,此“理”泛旨诗的情感内容,而非“理趣”之理的玄思哲理)。吕南公《与王梦锡书》、包恢《答曾了华论诗》、袁燮《跋魏丞相诗》、李涂《文章精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论·论妇人形相》等都曾用“理趣”论文评诗析画;(后李耆卿《文章精义》称朱熹称“音节从陶、韦、柳中来,而理趣过之”;明李东明《空同子集》卷五二《缶音序》斥宋人诗“专作理语”;故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讥宋道学家诗有“理障”)。而以“理趣”和“理语”连类辩似,则始于清代的沈德潜。“理趣”在沈德潜的诗歌评论中成为最基本的范畴之一,他在《古诗源》、《息影斋诗钞序》、《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唐诗别裁集》等一系列重要诗选、诗话、诗论中,对“理趣”多有阐述。但钱认为:“归愚标‘理趣’之名,或取《沦浪诗辩》‘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语,未必本诸耆卿”。这一推测是有一定根据的。从诗评史看,理趣说的形成过程,是古代诗评家对言理诗的艺术地位和审美特征认识不断深化提高的过程。继刘勰、钟嵘对“理过其辞”的玄言诗的批评之后,严羽又对“以议论为诗”“尚理而病于意兴”的宋代理学诗提出了批评,并倡“别趣非理”之说。此后数百年,围绕诗与理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争论,有人反对以诗言理。明七子的“宋无诗”论可为代表。有人认为理不碍诗,如刘仕义《新知录》认为:“杜子美诗所以为唐诗冠冕者以理胜也。”贺裳《载酒园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冯班《严氏纠谬》和方贞观《辍锻录》等也持同调。有人认为诗可以有理,但不能以理语入诗。李梦阳《缶音序》:“宋之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胡应麟亦持同调。应当说,此论颇合沧浪论诗宗旨。严羽并非要人写诗排斥任何哲理,除了那句“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或“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外,他在《诗评》中还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可见严羽毫无排斥“理”的意思,他所不满者,是宋诗中“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破坏诗美的倾向,心所向往者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的唐诗的丰韵之美,以及“词、理、意兴,俱在其中”的汉、魏诗的浑朴之美。不过,反对“别趣”说,强调理不碍诗的人,也同样反对以理语入诗。冯班《严氏纠谬》指出,诗中有理,“但其理玄,或在文外,与寻常文笔言理者不同。”因此,诗不废理,但必须理得其趣,妙合而凝,实际上是诗论家们的共识。郭绍虞先生指出:“后人由于这两方都有理由,于是又创为理趣之说,以作调停之论。”(《沧浪诗话校释》P34)确实, 清代理趣说的流行推广正是这场理论的结果。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这既可视为由“别趣”说引发的争论的总结,也概括了古典诗学对哲理诗审美特征的基本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在《管锥编·全晋文卷六一》中对沈德潜“理趣”论的产生还补充了一种说法,与上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同样是钱先生从具体的艺术分析中悟出来的,录此备忘。“余观《国朝诗别裁》卷之三二僧宗渭诗,沈氏记其尝谓门弟子曰:‘诗贵有禅理,勿入禅语,《弘秀集》虽唐人诗,实诗中野狐禅也’;岂沈氏闻此僧语而大悟欤?王应奎《柳南文钞》卷一亦有《〈息影斋诗集〉序》,略云:‘不为偈、颂之言,而有偈、颂之理,此所以尤工也。予闻佛氏之论,谓应以何身而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素公即以诗为说法,而勾引吾党之士胥入佛智。即谓素公之诗,是即素公之偈,颂也可’;沈德潜评:‘僧’诗无禅语,有禅理,乃佳。近代方外人纯以偈、颂为诗,入目可憎矣。篇中持论,与鄙趣合’。盖‘理趣’之旨,初以针砭僧诗,本曰‘禅趣’后遂充类旁通,泛指说理。禅人云:‘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参观《五灯会元》卷三慧海章次);衲子赋诗,于文词之抽黄妃白,启华披秀,如是作翠竹黄花观,即所谓‘禅趣’矣。纪昀批点《瀛奎律髓》卷四七《释梵类》卢纶、郑谷两作,皆评‘诗宜参禅味,不宜作禅语’,而《唐人试律说》于卢肇《澄心如水》诗则评:‘诗本性情,可以含理趣,而不能作理语,故理题最难’,即征‘禅味’之即‘理趣’,复征沈氏说之流传。”
三、“理趣之旨,极为精微”
“理趣”作为一个重要的诗文评范畴,其独特性在哪里呢?通观钱论,其结论性描述,不出二端:一是“举例以概”,二是“妙合而凝”。直捷言此二端,结论未免简单明了,难以见出钱钟书的辩析之心,也难以体现理趣的“精微”,我们只能从钱探究理趣特征的圆转思辩过程中,方能体会出理趣的精微。
钱通过对袁子才诘难“诗无理语”的反诘难,首先明确了:“理趣”之“理”的所指。在此基础上,他征引了沈归愚收集的“理趣”“理语”(“禅趣”、“禅语”)的一些诗例,使人们在感性上认识到二者的区别。但沈认为:理语、理趣的区别在于是否“意尽句中,言外索然矣”“言外有余味耶”。这就与言情写景诗的审美标准混而难分,那么,理趣的精微就难以体现了,为此,著者并没急于从理论上进行辩析,而是转而“竟厥绪”(见前)。通过对“以诗言理”流变的追溯,使读者逐渐明了:“理趣作用”与言情写景一样“亦不出举一反三”。但言情写景之所以举一反三,是因为“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挂一漏万,何如举一反三”(P227)还因为“言情写景欲说不尽,如可言外隐涵”(P228)例如《诗经·小雅·车攻》中只写了“萧萧马鸣,悠悠旗旆”二个细节,其军容之整肃就可如在目前。《诗经·小雅·采薇》中只写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便由景写情,征役之况、岁月之感,胥在言外。而元微之只以排比铺陈,推重杜甫并未真正认识到子美的好处,而说理之所以也要举一反三,是因为道理“散为万殊,聚则一贯;执简而御繁,观博以取约,故妙道可以要言,著语不多,而至理全赅。顾人心道心之危微,天一地一之清宁,虽是名言,无当诗妙,以其为直说之理,无烘衬而洋溢以出之趣也”。说理易尽,故应不使篇中显见。否则,就无当诗妙沦为:“坦直说理之韵语”了。如苏轼“两手欲遮瓶里雀,四条深怕井中蛇”,邵子的“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王维的“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孟浩然的:“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卢纶的“空门不易启,初地本无程”,刘禹锡的“法为因缘立,心从次第修”顾况的“定中观有漏,言外证无声”等等只是理语,无当风雅,难得理趣。
对于言情写景诗来说:“其所言情也,所写者景也,所言之不足,写之不尽,而余味深蕴者,亦情也,景也”“见点面知嫣红姹紫正无限也”。而对于理趣诗来说:“所举者事物,所反者道理,寓意视言情写景不同”“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例如石曼卿诗云:“乐意相关禽对话,生香不断树交花”此诗形容得浩然之气,鸟语花香即秉天地浩然之气,而天地浩然之气,亦流露于花香鸟语之中。这才是理趣诗举一反三,举例以概的特点与方法。诗中言理需别具手眼,因为“有形之外,无兆可求,不落迹象,难著文字;必须冥漠冲虚者结为风云变态,缩虚入实,即小见大,具此手眼,方许诗中言理”。诗可以“徒方情”,如:“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也可以“专写景”,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但“唯一味说理,则于兴观群怨之旨,背道而驰”,那么,以诗明理言道就要另立方法,那就是:“乃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如见。譬之无极太极,结而为两仪四象;鸟语花香,而浩然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传焉。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万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P228)。
《管锥编·全晋文卷六一》中说:“盖谓词章异乎义理,敷陈形而上者,必以形而下者拟示之,取譬拈例,行空而复点地,庶堪接引读者”。实则不仅说理载道之文为尔,写情言志,亦贵比兴,皆须“事物当对”在文学作品中,言情、写景、明理,并非水火不容,写景语未尝不可借用以说理,说理语也可以烹炼以抒情(参见《管》P628—629、 《谈》P545)理趣诗的精微之处还在于:理与诗的“冥合圆显”,心与物的“妙合而凝”,事与理的融洽无间。
关于理与诗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柏拉图认为:理无迹无象、超于事外,而诗文侔色绘声,狃于耳目,去理远而甚失真。而亚理士多德认为:括事(可)见事,殊(能)得共,史仅记事,而诗可见道,事殊而道共。黑格尔则认为:事托理成,理因事著,虚实相生,共殊交发,道理融贯迹道,色相流露义理。黑格尔的所谓“实理”(Idee)与僧达观撰惠洪《石门文字禅序》中的观点相类,只是后者不是说理与诗,而是言禅与文字,他认为:“禅如春,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钱钟书认为以僧达观与黑格尔的意旨来说诗家理趣,“尤为凑泊”,“大似天造地设”。因为:“理在于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这就是理趣诗的“冥合圆显”。理与诗的“冥合圆显”既非“香艳之篇什,淆于美刺之史论的”“比兴之旧解”,又与“穿凿如商度隐语”的所谓“内外意”貌同而心异。既非常州词派比附景物、推求寄托的“意内言外”“文微事著”,又与西方文学中“以事喻道”“比拟附会”“异术而必曰同梦”“仍二而强谓之一”的“寓托(AIIegory)”不同。英国十七世纪玄学诗派以巧于取比著名,但巧于取譬、罕譬而喻多是以事拟理,而非理趣的即事即理。例如约翰·唐以蜗牛戴壳喻人随遇自足,著处为家、无往而不自适,万物皆备于身,比喻虽新妙贴切,但是“取足于身,可以蜗牛戴壳为比譬,而蜗牛戴壳,未是取足于身之例证”我国诗人曾以蜗牛戴屋行喻“曲谨庸懦之象”;英国古小说以蜗牛顶屋言埃及妇女足不出户;法、意诗家以蜗牛讽宴安墨守之自了汉,恋家鬼(P551—2),这都是以事拟理,而非即事即理,而真正的理趣, 乃是“目击道存,惟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即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例如:杜少陵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吾心不竞,故随云水以流迟;而云水流迟,亦得吾心之不竞”与“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一样,就做到了内外胥融、心物两契,即所谓“凝合”,故沈德潜认为“俱入理趣”。又如《五灯会元》十三龙光谭禅师云:“千江同一月,万户迟逢春”“以明法身之分而不减,散而仍一”;“法身现此世界,而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千江也,万户也,月也,春也,观感所著,莫非法身之显相也”。这正是《五灯会元》卷三慧海所谓:“应物见形,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再如叶水心诗:“包容花竹春留巷,谢遗荷蒲雪满涯”包容花竹,自是阳舒,谢遗荷蒲,正为阴惨。所以,理趣之即事即理与以事拟理的区别在于:“其在世也,则是物本为是理之表见;其入诗也,则是物可为是理之举隅焉”。而以事拟理则是“每牵合漠不相涉之事,强配为语言眷属也”。
另外,理趣诗的“举例以概”又不同于说理陈义者的“取譬于近”。钱钟书在《管锥编·乾》中论及《易》之象与《诗》之喻的区别时曾谈到这一点。他指出了古今中外说理陈义者对“取譬于近、假象于实”的重视,“理赜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释氏所谓权宜方便也。古今说理,比比皆然。甚或张皇幽眇,云义理之博大创群者,每生于新喻妙譬,至以譬喻为致知之具、穷理之阶”。钱钟书认为:“《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心喻道,而非道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可也”。例如,王弼就认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只要能喻道明理,以羊易牛、以凫当鹜,也无不可。王之所以提出“得意而忘象”就是恐怕读《易》者拘泥于象而妨碍喻道明理。但是“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例如:“取《车攻》之‘马鸣萧萧’《无羊》之‘牛耳湿湿’易之曰‘鸡鸣喔喔’,‘象耳扇扇’,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着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之变换,将别开面目,另成章什”。所以“《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管锥编·狡童》有关于含蓄与寄托的比较也可资辩析理趣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