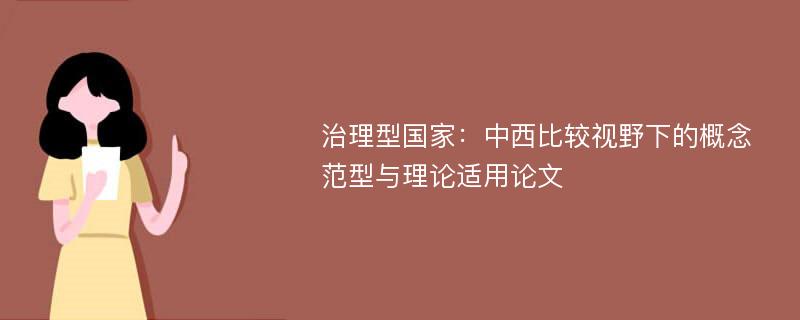
治理型国家: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概念范型与理论适用
申剑敏
(上海政法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上海 200333)
【摘 要】 近年来,国家建设已经取代政治发展成为政治现代化研究的主要解释路径。然而,当前基于西欧早期国家形成经验的“财政-军事国家”解释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必须发展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概念范型来认识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国家建设进程。“治理型国家”正是这样的概念范型。在“治理型国家”的概念框架下,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由于西欧国家不独占治理权,通过选举式民主来驯化国家权力不必然带来良好的治理。中国存在悠久的国家治理传统,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如何解决国家集权与分化治理的矛盾。当代中国的实践表明,“治理型国家”建设的重点,就在于国家如何有序且有效地推动社会成长,最终形成国家与社会共生共治。
【关键词】 治理型国家;国家建设;国家治理
国家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之后,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成为政治现代化研究中时而交锋、时而互补的两条理论主线。查尔斯·蒂利更是直言不讳自己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用意即在挑战政治发展理论。[1]近二十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目标,被亨廷顿倡导的“第三波民主”带入一个按西方标准模式预设的理论陷阱之中,致使政治发展逐渐失去感召力。相形之下,国家建设更专注于具体国家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比较,顾及不同国家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其解释优势日益彰显。依国家建设的解释路径,有望摆脱基于西方国家成长经验而形成的理论桎梏,发展出新的概念范型。随着政治从业者和学者越来越将国家当做治理机构而非战争机器,以及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吁求近年来对作为西式政治现代化范型的民主化所产生的质疑,“治理型国家”这个新概念范型的提出,可谓适逢其时。[2]
一、反思“财政-军事国家”
从查尔斯·蒂利迄今,国家建设的理论侧重点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现代国家的“财政-军事”集中化特征,转向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与19到20世纪国家建设的历史趋势是一致的。将西欧早期国家形成置于“财政-军事国家”模式之下加以解释,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若以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仅有违初衷,更可能犯张冠李戴之大错。
诚然,历经数十年反复咀嚼,“财政-军事国家”理论已是蔚为大观。不过研究者应了解,这一理论并非查尔斯·蒂利的发明,实来自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启发,这一解释可见诸《共产党宣言》: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3]
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指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集中”。集中包括了两个齐头并进的进程,即资本的集中化与政治的集中化。他们分别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组织化后果,前者是生产性企业的蓬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兴起,中介是城市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一重要发现,被查尔斯·蒂利全盘接受,且奉若圭臬,发展为资本集中和强制集中两种国家形成模式。[4]
这个解释模式之所以具有感召力,在于它概括了现代国家作为权力拥有者的两个基本形象。首先,现代国家是一个掠夺者,借助强制力向社会强行提取资源来壮大自己;其次,现代国家还是一个控制者。它通过财政集中和强制集中来强化自己的能力,将权力不断向基层社会渗透,直至对其臣民形成完全监控,使后者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埃利亚斯、安东尼·吉登斯等“莱斯特城学者”眼中,现代化进程就是国家这一“权力容器”对臣民监控能力提高的进程。[5][6]
当然,财政集中与强制集中并非一致的过程。那些片面依赖商业税的城市国家,或者片面横征暴敛的土地-官僚国家,都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有那些将两个进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成为追赶者竞相效仿的对象。在蒂利的众多追随者看来,正是对“财政-军事国家”模式的摹仿,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世界图景。
然而,“财政-军事国家”并非轻易习得,否则将无法解释现代化进程中的分岔。比如拉克曼就发现,由于精英斗争的存在,诸如西班牙、荷兰这些早期国家,在维持高水平财政收入的条件下,仍然出现军事能力衰退的非线性回归现象。[7]这表明“财政-军事国家”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身存在复杂的机制。
在没有试验资料时,混凝土的含气量参照《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352-2006)有关规定,根据抗冻等级和骨料最大粒径选用,本工程混凝土的含气量4%~6%控制。
“财政-军事国家”解释模式的局限性,在它囿于早期西欧国家的历史经验。下文将提及,脱胎于中世纪的早期国家,当时并非公认的社会治理主体,更多是充当战争机器。社会治理功能更多是由教会、商业联盟、行会这些组织来承担。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国家”一词没有明确的治理含义,当时的政治,也是争权夺利的代名词。[8]“财政-军事国家”完美地阐释了这段历史,但它既未离开西欧,也未走出早期,无法解释此后一百多年国家形态和功能的进化,尤其是国家权力“公共性”的起源。
早期西欧国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威”,而只是“宫廷权力”的放大。这些国家的“公共性”,不可能来自于“财政-军事国家”本身,更多是来自“财政-军事国家”之外的压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身份政治和社会抗争两者。
首先是身份政治。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随着王权铲除土地贵族而告一段落,此时对原属领主之臣民的征召,便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成功的民族建设,把领土内居住的人口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内,赋予其共同的政治身份,即所谓国民身份。国家俨然成为这种“民族国家”的代表。马克思提出“虚幻共同体”一说,指出现代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在于从“真实的共同体”转化为“虚幻的共同体”,[9]换言之,民族国家的实质,就是将自己装扮为各社会阶级的共同体,以“公共性”争取合法性。从历史经验上,随着欧洲政教分离不断彻底化,诉诸于血缘、历史叙述、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来构筑“想象的共同体”,[10]重塑民众生活意义秩序,成为现代国家越来越迫切且不可或缺的政治功能。
对于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治理传统的国家而言,其优势在于,只要国家权力足够强固,就可以成功避免治理失控,因为国家治理在精神上和制度上始终处于一种基于“公共性”的大众监管条件下。与西欧中世纪相比,那些把持了主要社会资源的教会、领主、行会、贸易联盟,他们的权力基本不受约束,各种对人身的残酷伤害、生杀予夺,都是基于社会组织内部团契、规则来进行,只有跨组织的来往,才有所谓契约也就是法律的用武之地。[30]治理是高度“封建化”的,也是无序的。但在中国传统帝制下,国家权力始终是受各种因素制约,从来没有达到过任性妄为的程度。这些制约因素,既包括礼制、律法等制度因素,也包括道德伦理等精神因素,更重要的是来自官僚集团与君权的相互制约。那种基于“隐私”、由特殊利益所构成的社会权力形式,固然可以在私人领域里任意妄为,但在中国却很难有一席之地,因为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少有独立于“公共性”的正当“隐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连具体的君主,也概莫能外受制于“公”。政治作为天下之“公器”,绝非君王一家一人之事;对于士大夫政治而言,“先天下之忧而忧”亦是基本准则。对于政治权力,不仅有延绵的礼制来规范,历代严刑峻法亦从未中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不幸的是,无论身份政治还是社会抗争,都是“财政-军事国家”解释模式力有所不逮的空档。也许正因为如此,蒂利才在学术生涯中期放弃了对“财政-军事国家”的解释,转而投身于社会抗争研究,因为后者才蕴含了国家“公共性”的秘密。
缺乏对“财政-军事国家”模式的反思,导致我们对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研究走上弯路。此前的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沿用“财政-军事国家”模式。[12]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它与近代以来中国上下一致倡导的“富国强兵”目标看起来十分一致;第二,它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采取的一些应对手法似乎也相当吻合: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是从失败中向更先进的“财政-军事国家”学习,开始其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对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建设的研究,基本逃不出“国家提取”和“军事化”两个主题。[13]这种对中国国家建设的研究,要么是以西欧早期经验为普遍准则,要么是把中国当作是西方的单纯摹仿者和追随者,如今已经难以令人满意。
中国国家形态是原生的,远早于西欧,期间还经受了内亚政治传统的深刻影响,[14]形成了自身的演化逻辑。即便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冲击,国家建设进程也并非片面专注于财政和军事的集中,事实上这两个集中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富国强兵”背后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寄厚望予国家,勠力建设之,使之承担民族复兴之大任。换言之,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从来就不是目标,而仅仅是手段。就此种种反思而言,将中国国家建设纳入“治理型国家”范畴来加以解释,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6)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缺失。我国涉农企业中,国有企业或者规模较大的民营涉农企业,建立党的组织结构,实行党的领导。如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的组织结构,成立党委,切实发挥党的模范带头作用。但部分企业中党组织不健全,未能切实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组织虚化和党员边缘化问题较为严重,党员出现“游离”现象。国企中党组织职责定位不清,党领导作用的发挥缺乏保障等问题严重存在。我国涉农企业民营性质且中小规模的企业数量众多,家族式管理特征明显,党组织缺失,企业的发展方向偏离国家整体发展思路,难以实现既定的战略发展目标。
我这时意识到,在这个叫老四的人身边小心点是明智的,尽管他之前在平台上救我时满面和气,但这种平静的外表下好像暗藏危险。
二、“治理型国家”的演化机制
不论是“财政-军事国家”还是“治理型国家”,都是我们理解国家建设的一个概念范型而已,不能将其绝对化。从历史经验上,即便最典型的“财政-军事国家”也不可能绝对不提供公共品;“治理型国家”若是忽视了财政与军事能力建设,则一切无从谈起。仅仅作为概念范型,“治理型国家”至少应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是否具备一整套“公共性”的政治伦理系统,以此作为合法性基础;第二,是否形成分工合理、相互约束、权责对称的组织结构,来确保权力运作和政策目标的实施;第三,是否以提供公共品作为主要政策目标,着眼于整体社会的长远发展来制定战略规划。与“财政-军事国家”相比,“治理型国家”概念主张国家是公共政策制定的责任主体,而不是单纯的“权力容器”、政治场所。借用美国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及后来功能主义者的理论,“财政-军事国家”的成败,取决于“输入”侧的资源提取功能;反观“治理型国家”的成败,则取决于“输出”侧的公共政策功能,它正是以公共政策实施的反馈结果来获取支持。就此而言,伊斯顿本人将“国家”当做单纯的政治场所加以“悬置”,绝对是败笔。
天葬是云浮对神明的献祭,是最圣洁的事情,自己为了满足私欲,竟用这种龌龊的方式,来为神明祭献一具并无信仰的外族尸体。天葬刀将在自己的手中受到玷污,神明兴许会因愤怒而降下灾祸。而之后祈神时的异象,更加地证明了,云浮确实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一般认为,城市共和国对财税的依赖程度,较之君主制国家更大,相对而言,城市共和国更倾向于提供公共品来“回馈”纳税市民,也就是更有可能成为“治理型国家”。而君主制国家更多依赖于直接税,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不必听从社会力量的诉求,更像是一个单纯的提取者。但是西欧的历史证据表明,两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想象般大。原因正在于西欧的小国政治模式。由于周边小国林立,无论君主制国家还是城市国家,都面临风险巨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而国土规模小又使得竞争失败的后果很可能直接就是国家崩溃。如此一来,这些早期国家不得不将财政支出的大部分用于战争和战争准备。战争也是这些统治者向市民和农民索取的主要借口之一。可以说,西欧不是没有公共品,而是把战争当成主要的公共品;如此便没有多少剩余价值来提供攸关治理的公共品。[15]
现代国家从社会权力中脱颖而出,“凌驾于社会之上”,使国家权力仿佛成为社会中惟一具有宰制性质的权力。这样的国家形象,只有置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工具性和自主性双重属性的框架下才能解释。对国家作用的夸大,甚至认为只要通过扩大普选权等民主政治方式,将国家权力驯化,就可以永久消除权力的宰制,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或者说是一种障眼法,让人们忽视国家之外的社会权力。从久远时代流传下来的各种国家之外的权力形式,并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被消除。他们在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惟一的不同之处,就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并且向社会各个角落蔓延。用福柯的话来说,只有在权力的基层,才能发现权力的真相。[25]
然而,即使国家开始对那些传统上具有独立性的社会权力发起了挑战,在治理中扮演越来越吃重的作用,总的来说还不足以引发革命性变化。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对多元社会权力主体的挑战是有限度的。后者的因应,就是通过法律、民主、普选等手段来约束国家权力,力图使国家权力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至于对自己的权力构成致命威胁。西方选举式民主的发展,是在欧洲传统多元主权的历史逻辑下发生的。这种选举式民主自有其限度,表面上对国家权力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却为社会权力横行留下大量剩余空间,后者是选举式民主不可及之地。反过来,迄今选举式民主依然是现代社会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权势集团控制国家政权最有效也最简便的手段。这就是选举式民主与治理有效之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实质:选举式民主只能让特殊利益更加有效地控制政权,而克服不了特殊利益的权力滥用本身。因此不难发现,在那些缺乏强大而自主社会力量的地区,民主化更有可能取得治理效果;而在那些社会力量我行我素、不受约束的地区,民主化带来更多是灾难性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味追求选举式民主来企图制约国家权力,而不考虑如何通过“治理型国家”建设去加强社会治理的做法,不能不说是缘木求鱼。正如福山痛定思痛之后所称:“软弱无能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29]他已经隐约意识到,二十一世纪世界现代化进程更取决于“治理型国家”建设的成败。
“治理型国家”的这些特征,对于今天世界的政府而言,似乎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原理,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早期西欧国家远远及不上这些标准。在政策目标上他们充其量也只能达到类似于亚当·斯密笔下的“守夜人国家”。从“财政-军事国家”到“治理型国家”的演化,意味着西欧国家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形势的变化。
反观中国从历史上就是一个经典的“治理型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典国家形成的时间远较西欧要早。原始社会晚期,中原文化载体就已经从“农耕聚落”转化为“都邑国家”,[18]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职官行政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在整个东亚处于独大地位,不存在致命的地缘政治竞争,除了应付北方的游牧民族之外,没有更多的战争负担。近年来,加州学派通过中西比较,以公共品供给比例来测量国家的治理水平,发现中国传统王权治下的公共品供给比例更高,[19]国家财政支出的相当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河道疏浚、灌溉工程、城市网络、驿站交通,等等,足以说明中国古典国家相比西欧近代早期国家,更接近“治理型国家”特征。
更有一例可供佐证。尽管中国古典国家向来奉行“皇权不下县”原则,而底层社会亦有“帝力于我何有哉”之惯习,仿佛王权推卸其治理责任,悉数交由基层社区自我调节。但是一叶便可知秋。例如攸关民生的食物供应问题,向来是中国王朝的文治之一,自秦以来便形成了系统的民食政策。[20]更有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之戏言流传至今。在欧洲,民众的生老病死,从来不入王权法眼,只在借现代国家缔造的契机,西欧才形成了第一套由国家控制的食物供应系统,蒂利以此为西欧国家形成之标志,[21]即便如此,食物供应较之财政、军事两个集中,还是黯然失色。相比之下,中国的“治理型国家”传统显然久远、稳固得多。
首先,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通过提高自身实力,与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合作关系[10]。
然而,中国的“治理型国家”因晚清帝国的衰落,失去了“财政-军事”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财政-军事国家”建设,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段弯路,但又不得不走。但若在理论上想当然地把“财政-军事国家”当作中国国家建设的原型,甚或目标,那就是食洋不化、生搬硬套了。
中国遭逢严重财政—军事危机的条件下,依然走上“治理型国家”建设道路,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民族战争与革命。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引发了最广泛、最彻底的社会动员,用查默斯·约翰逊的说法,日本人对中国农村的扫荡,使中国农民形成了民族主义。[22]以民族政权名义抗击日本侵略,使中国国家建设进程完成了身份政治的转变。革命的成功,既是历史使然,也是“治理型国家”模式对国民党所迷恋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的胜利。战争结束之后,我国一手抓“财政-军事国家”建设,一手抓“治理型国家”建设,两手并重,从根本上逆转近代以来国家建设困局,从此一往无前走上“治理型国家”建设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治理型国家”建设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其理论意义与政策意义都非同凡响。
美国存在类似情况。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立国,其建国历程适逢欧洲“治理型国家”建设的长和平时期,相互影响在所难免。相比欧洲,美国拥有一个巨大优势,那就是不存在战争威胁。但是美国“治理型国家”建设相对比较迟缓,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作为中央权力的联邦政府不存在巨大的社会治理压力,缺乏紧迫性。但是情况在美国内战之后发生了变化。南北战争同样是一场大规模、势均力敌的内战,北方和南方都需要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战争结束之后履行承诺,正是美国走上“治理型国家”建设快车道的缘起。“进步主义”时期的治理改革,实际上是美国“治理型国家”建设的重大转折。
总而言之,“财政-军事国家”解释模型,是建立在早期西欧小国政治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这些国家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面临残酷的地缘竞争,而不得不将集中化的财政用于更加集中化的军事强制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中美俄印这些大国的政治已经成为主要模式,大国的国内治理问题相比地缘竞争毫不逊色,建设一个“治理型国家”更加迫切。在深刻反思早期“财政-军事国家”解释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更容易发现“治理型国家”概念范型的适用性。潘基文指出:“在之前的世纪,联合国的中心任务是制止国与国(country)之间互相厮杀。在新的世纪,根本的使命是加强国际体系,这样才能应对新的挑战,更好地服务于人。我们需要有能力、负责任的国家(state)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要,联合国正是为他们而创建。”[23]
三、“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
若以“治理型国家”来考察国家建设进程,将是另一番风景。对于“治理型国家”而言,“国家治理”是应有之义,但在西欧历史经验中却长期缺席。“国家治理”与西方学者主张的那种“治理”存在根本区别。后者所提出的“治理”旨在“去国家化”,倡导所谓“多中心主义”。这种“治理”概念有其合理性,在于指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之必要性,但是它拒斥国家在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则基于对西欧历史经验做了形而上学的理解。
在西欧,国家向来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应该说,作为政治权力原型的王权本来是一种高度自主的权力。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将王权长期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欧洲的王政传统则中断了。罗马之后是一片黑暗,那是王政被摧毁之后的秩序混乱。但欧洲出现了新的权力形态,那就是教权。教权的兴起,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意味着后来重建的世俗国家权力,无论多么强大,都始终面临教权的制衡。更何况,中世纪以降,欧洲那些重建的王政一直羸弱不堪,他们为了争权夺利甚少关心公共品输出,并且在这些争斗中不断被消耗、摧毁。总的来说欧洲那些前现代政治体的“权力”本身并不像中国的王权那么强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并非惟一的权力形式。除了高高在上的教权,领主、行会、贸易联盟都以“超经济强制”各据一方,形成自己的“政府”。这种政府权力的多元化,是欧洲中世纪之后新的政治传统。
国家形成之后貌似获得统一的权力,形成了中央集权,但是一方面国家权力在进入现代的时候先天不足,另一方面那些在社会上掌握了各种权力的集团,都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权力独立化,并且不受制约。欧洲新兴的现代国家所摧毁的,只是那些与之竞争的政治体,对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各种权力形式,依然显得无能为力。除此之外,国家权力还面对一个新的竞争权力的力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来就是在中世纪庄园制之外产生的势力,相对于国家具有独立性,而其后的发展,是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支配了政治权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议会制。
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原本是欧洲旧制度下“超经济强制”的现代翻版。资产阶级支配了社会经济,同时也控制了国家权力,使国家沦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国家作为一种自主的统治力量兴起,始于第二个波拿巴执政时期,前提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分离,中世纪“超经济强制”的政治传统消退。由于资产阶级更注重于自己在市场上的经济权力支配,而不得不放弃了直接统治,将国家权力交给自己的代理人,国家便有可能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24]
但是反过来说,促使西欧国家从“财政-军事国家”向“治理型国家”转型的主要动力,同样是战争动员的扩大,以及因之提取过度引发的社会抗争。[16]战争频仍、动员规模的扩大,无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要求国家提供对等的公共品。这种诉求在战争状态下并不显著,一旦战争结束,如果国家不能及时给予社会精英和民众相应补偿,就会引发政治危机。[17]
因此,相比“找回国家”学派主张国家权力在某些领域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的批评者米格达尔的“社会中的国家”,[26]可能更接近真相,那就是波比奥在他的国家与社会权力二元对立框架[27]中阐释的问题:国家权力随社会力量的强弱而变化。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因其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赋予了所谓“公共性”,而不得不置身于社会公众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之下。相反,那些从中世纪乃至于之前就已经流传下来的各种权力形式,因其一直处于独立、封闭发展的地位,实际上是不受约束、任性和专制的,这种专制的权力形式被认为是天然的、不容质疑的,也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加以监督和控制。马克思早期就通过对林木盗窃法的批判揭露了这种天然专制的不合理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弱化而只是不断强化这种权力的专断性质。
对于欧洲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模式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摧毁和削弱了很多旧权力,特别是那些与国家长期颉颃的旧社会势力集团。按照奥尔森的观点,摧毁得越彻底的国家,特别是德国日本这样的战败国,其战后经济社会发展越迅速。[28]可以说,战后西方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事实上国家通过大规模战争强化了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种变化是以“福利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美国这样的非福利国家,都不得不面临“大政府的兴起”。
从历史上看,拿破仑征服之后的百年和平,是西欧国家走向“治理型国家”的关键转折。在这一百年的时间内,有几个因素促成了向“治理型国家”的转型,包括国家间战争的减少、社会抗争的反复、普选权的扩大、议会制度以及财税体系的完善,等等。即便经历如此漫长的演化,“治理型国家”也没有真正成型,因为欧洲不久就迎来了长和平的终结,两次世界大战横跨半个世纪,中断了西欧的“治理型国家”建设进程。直到战后西欧在美国的军事安全保护卵翼下,才有机会重拾“治理型国家”建设的努力。迄今不过半个多世纪,这些欧洲国家已经无力应对经济衰退、基础设施老化、难民潮等社会危机,疲态尽露。整个“治理型国家”建设进程在西欧可谓一波三折,道阻且长。
《上海护理》杂志是伴随白衣天使成长的良师益友,一路走来,我们与天使们许下了最好的承诺:携手同行,并肩齐驱,相约在岁岁年年的好时光里,相聚在字字句句的好文章里,相知在卷卷期期的好杂志里。一年的光景,六期的承载,三千篇的希望,透过我们的细致编撰,终结成一卷墨香的书页。我们与天使相识于字里行间,感受着真诚的心扉,充溢着坚定的信念;我们与天使相惜于点点滴滴,积淀着微小的进步,体悟着彼此的成长。正是广大天使姐妹不懈支持,才有了《上海护理》丰足的内容;也正是因为《上海护理》扎实的编校质量,更有力地回馈着广大天使姐妹的厚爱。
四、“治理型国家”的有效性
与西欧的经验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从未缺席。但从传统帝制到现代国家,中国同样存在国家转型的挑战,所不同的是,这一挑战更多在于“治理型国家”的自我调适,而不是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权争夺。
小兹维列夫今年21岁。在2018网球男单年终总决赛中,他以2-0的分数力压强手,夺取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一个冠军,他不仅是继1995年名将鲍里斯·贝克尔之后又一位拿到总决赛冠军的德国选手,同时也是继2008年德约科维奇之后最年轻的总决赛冠军。
从早期国家形成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期间历经北方游牧部落入主中原、佛教延播,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亦未中断过。一方面,从中原地区发源的农业社会结构,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虽然经历了王朝更迭和制度革新,但是王政传统一直没有被摧毁。传统中国社会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从来没有产生出与国家权力平起平坐的社会权力。
其次是社会抗争。“财政-军事国家”单向的集中化提取,必将引起民众抗争。“财政-军事国家”过分偏重于国家作为权力主体的提取能力,而忽视它相应所承担的治理责任,这恰是早期西欧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治危机的来源:国家向社会索求无度,反而导致社会力量走出狭隘的地方性,直接对国家提出诉求。为了缓解这些危机,国家不得不开始提供一些公共品,使自己的政策目标一定程度独立于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表面上具有了“公共性”。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驾于社会之上”,要扮演“缓和社会矛盾”的“调解者”。[11]
但是,这种由国家独占治理权的模式,本身也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一再被历史所证明。首先是中央集权体制的财政负荷和治理责任太重,既造成官僚体制僵化,也使社会丧失活力,中国古代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此。其次,中国历史上未曾经历“财政-军事国家”建设,使之有别于西欧小国政治模式,同时也恰恰构成了国家建设两个致命软肋,财政的集中化与军事的集中化从未真正在中国王朝政治中实现过,财政体系崩溃,或者军事体系的瓦解,构成了明清两代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31][32]这些现象都源于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国家集权与分化治理的矛盾。
长期以来,学者对这一矛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形成了“压力型体制”、“选择性执行”、“地方性国家”、“条块分割”、“预算软约束”等分析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周雪光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提炼指出:“一统体制的核心是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紧张和不兼容集中体现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33]平心而论,国家集权与分化治理的矛盾,并非中国所独有,只是在很多中国研究者眼中显得比较典型。一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治理型国家”,各种矛盾比较集中,暴露得也比较充分;二来中国的国土和人口规模大、社会结构复杂,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大规模国家”,集权与分化的冲突当然十分典型。
总体看来,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超大规模国家,国家治理一定不可能是一马平川、不打折扣的。除了考虑要因地制宜,保持地方治理的弹性之外,更重要的是权力本身依循科层化组织路径,在传递过程中会因时空因素而呈现非均质的分布和流变,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可以确保国家提供的公共品足够“好”呢?为了将权力流变的负效果减至最低,科层制下的正-负激励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而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就是分权,通俗地说,一是给钱(财权)、一是给权(事权)。类似的情况,哪怕联邦制的美国也存在,所以才有尼克松、里根时代两次“还权于州”,先给钱,后给权。
在中国,“给钱”的制度刚性远大于“给权”,而这正是“治理型国家”的有效性问题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最大治理难题,就是财力不足,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如此。财力不足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共识,财政激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样一来,要确保政策执行的效率,达到有效的治理,必须创造出一种辅助性、或者说是补偿性的激励机制。众所周知,这种在中国社会中非常独特的激励机制,就是建立在精神层面的思想动员。相当长时间内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仰赖于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思想动员。从经验数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收入增长水平一直低于GDP、识字率等客观治理指标的增长水平。换言之,中国是以低财政来支持高增长,[34]除了工资维持在长期低水平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通过思想动员形成了中国式的“勤劳革命”。这在其他国家几乎难以想象。以高度组织化的思想动员为核心的政策执行机制,形成一种“内敛型”治理,[35]具体而言,就是权力集中化和集约化程度都比较高,政策执行效率高,但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组织体系,创新能力较弱,容易达到增长瓶颈。
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对此也有经典阐述,在201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表示,中国的各个行业都过于分散,行业重组势在必行。行业重组目的是使我们公司、我们国内企业的市场集中率能够提高。许小年举例说,汽车行业中国有70多家生产厂家,70多家整机生产厂家。美国只有3家,1家福特,1家通用,还有1家特斯拉。这意味着中国汽车生产厂家的规模效益远远低于美国,意味着中国汽车生产厂家能够投入到研发中去的资源远远低于美国。我们的企业太分散了,没有力量集中资源进行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的研发,导致中国的企业在基础技术方面现在和美欧日的差距依然是非常的显著。如果谁能抓住行业重组的历史机会,就有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难题,但是整体财政收入水平依然是吃紧的,因为中央财政收入弹性下降。[36]在激励机制上,对组织化思想动员的依赖程度降低,而更多依赖于分权,以为分权更能激发创造性。彼时财权、事权都给足,激励机制一次到位,形成“财政联邦主义”,[37]甚至部分地方一把手宁可留在地方,也不愿意晋升到上一层级担任职能部门领导,与“晋升锦标赛”[38]的解释可谓格格不入,后者其实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激励弱化、责任机制强化其中一个产物。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纳入到刑法处罚的范围是必然的,而且必须实现对该行为的全面监督,不能仅仅是以危险结果的发生为依据。我国目前已经在刑法中加入了危险驾驶罪,其中包括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具体的规定中,不需要考虑醉酒驾驶所造成的具体后果和情节,只要行为人存在醉酒驾驶的客观事实就构成该类犯罪,需要处以拘役以及罚金,因此需要对该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研究,明确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构成该类犯罪,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并在实践中实现对社会安全的保护。
激励机制的形成,目的是为了缓解国家集权与分化治理的矛盾,但是客观上导致地方治理的吃重,弱化中央权威,事实上也同样影响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就表现出来了:执政党的集中化组织领导。由于存在一个全国性的、自上而下、高度组织化的政党系统,可以强化责任体系,成功纾解分化可能造成的治理失控。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家治理各种“双轨”过渡现象中的矛盾,最后都通过党的组织运作来克服。这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从总体上始终保持有效性的根本原因,但也会导致社会治理的矛盾被引入到党内组织建设之中,影响党自身的发展和建设。总而言之,光靠国家体制内部激励机制来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并不足够,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由党来领导、国家主导来推动社会建设,向社会有序、稳步放权,形成国家与社会共生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
随着出行游玩方式的多元化,人们已经打破传统的游玩模式,开始了新的出行旅游。中国作为当前最受游客欢迎的国家之一,也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旅游行业的发展水平,增加出入境旅游业务的数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航空事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还要以市场为导向,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有效地促进航空业的发展。
根轨迹法是分析和设计线性控制系统的图解方法。根轨迹不仅可以指出系统某一参数变化时所有的闭环极点在S平面上的位置和动态性能,而且可以指明开环零极点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
据此,1949年后中国国家建设的路径就可以得到理解了。这是一个从集中到分化的过程,而且是一种以集中为基础的分化。第一步就是通过各种努力,实现财政集中和军事集中,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基本条件。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汲取了历史经验,成功避免了传统“治理型国家”在“财政-军事国家”建设方面不足的问题。第二步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让国家向市场社会放权,培育社会力量,形成国家主导下的多方共治模式。向社会放权与原有的国家体制内部分权是不一样的,放权意味着国家将一部分社会治理权力下放给社会,释放社会的自主性。当然,向社会放权也不是为了建立西欧历史上那种竞争治理权的格局,而是形成一种由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国家治理模式。
相信经过上述一系列层次分明的教学指标设置之后,学生学习体育的激情和自信心势必会大增,能够为日后这类群体体育水平快速提升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
从分权走向放权,是国家治理模式自我调适的结果。通过向社会放权,不仅能够激发社会创造力,形成社会力量对国家治理的支持;同时,由于市场社会这一参照体系的存在,也有利于国家体制内部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这一个过程注定是非常艰难、复杂的,特别是两点:第一要避免国家权力原本的自主性受到侵害,使国家治理的“公共权威性”被弱化;第二是要确保“治理型国家”建设,不至于对新兴市场力量构成威胁。这都需要一种“微妙平衡”,这个平衡者,从实践经验来看,就是强而有力的党组织。正是党高度组织化的运作,确保了国家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相对于新兴的市场力量,仍然保持高度的自主性。同样,党的坚强领导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
五、结论
总体而言,只要依循由国家主导来发展社会的路径,国家与社会共生共治的“治理型国家”模式就是可欲的。一方面,由于市场力量是国家有意识、有计划培养出来的,即使市场力量反过来对国家权力有所约束,这些约束已经是国家所预期的,国家更不可能因为市场的存在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公共目标。另一方面,国家培育市场的过程,会要求新的社会治理主体强化公共治理责任,这是中国在放权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治理主体,与西方那种原生的社会治理主体所不同的地方。一些食洋不化的中国研究者,习惯以西方标准来要求中国那些与之名实不副的社会治理主体,或者反过来,以西方治理责任有限的政府来对照中国政府,这些都给人强烈的时空错置之感。
在当代中国,国家培植社会力量的目的,不是损害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和公共权威性,而是由社会分担相应的治理功能,形成结构上复合的(央地、跨域等)、内容上立体的(阶级、基层等)、手段上多中心的“治理型国家”。“治理型国家”强调治理的整体性而不是单纯的原子化社会契约,主张政治权力运作的协商性而不主张非合作性的竞争,其政策目标是达到充分的社会包容而不是社会排斥。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近代化以来的国家建设模式,找到中国自己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cene of arts changed in Europe.
参考文献:
[1][21]Charles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4.
[2][35]陈周旺.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J].学海,2019,(1).
[3][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676.
[4]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M].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6]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二卷)[M].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7]Richard Lachmann,“Mismeasure of the State”,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2004.
[8]肯尼思·米诺格.政治的历史与边界[M].龚人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8:3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0-503.
[10]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12]斯蒂芬·哈尔西.追寻富强[M].赵莹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13][32]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4]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15]理查德·邦尼.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M].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286.
[16]布赖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M].赵信敏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7]西达·斯卡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M].何俊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8]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4.
[19]王国斌,让·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M].周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204.
[20]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2]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23]申剑敏,陈周旺.现代国家的治理内涵辨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6).
[25]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6.
[26]乔尔·米格达尔.社会中的国家[M].李杨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27]诺伯特·波比奥.民主与独裁[M].梁晓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28]曼瑟·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M].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9]福山.国家构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0]迈克尔·泰格,玛德琳·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纪琨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31]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阿凤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33]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2017:19.
[34]陈周旺,韩星梅: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中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的着力点[J].探索,2019,(3).
[36]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37]钱颖一.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A].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C].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3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中图分类号】 D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997(2019)03-0118-08
收稿日期: 2019-05-23
作者简介: 申剑敏,管理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家治理、跨域治理。
(编辑:刘晖霞)
标签:治理型国家论文; 国家建设论文; 国家治理论文;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