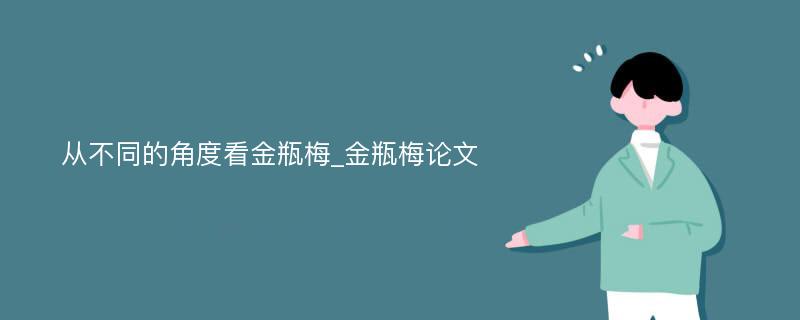
换个视角去观照《金瓶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换个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人必要的品格是应当不断地反思自己学术思维的缺失和学养的不足。而一旦发现了这种缺失和不足,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充实自己,修正自己的观点,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转换自己审视文本的视角。记得十几年前我为自己所写的《说不尽的〈金瓶梅〉》(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版)那本小册子的“后记”中就说过:《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和研究者中间,它仍然是一部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我虽然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我也仍然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读我现在所写的这部书稿时,我就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
时过境迁,现在一旦检点这部旧作就真的发现,我确实对《金瓶梅》有过偌多的误读和并非全面正确的诠释。当然我也发现一些精神同道和我一样,对它有过“过度诠释”的毛病。当然,这也是文艺研究与批评的正常现象。我信奉歌德的那句名言:“人们已经说了那么多的话,以致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精神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的作用。”歌德这段评价莎士比亚不朽的话也可以移用来看待《金瓶梅》,并用之于调整我们的阅读心态。因为作为一部伟大的精神产品的《金瓶梅》,也必将对我们的精神和思维空间起着拓展的作用,回过头来,又是对它的新解读。
引发我重新打量《金瓶梅》的文化精神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对吴存存的《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阅读所受的启发;一个是去年我去新加坡参加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逼得我去重读《金瓶梅词话》,并重新思考《金瓶梅》在小说审美意识演变中的地位与价值。
吴著中的一段话对我最有震撼力。她在对张竹坡领悟的那个“真义”进行批评的同时说:“对于一部反传统(着重点是引者所加)的作品,竭力从中找出合乎正统观念的因素,把这视为一大优点借以抬高这部作品,是我们小说批评中一个卑陋而自以为是的传统。”(见该书第95页)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了。仅就这一点来说确实值得我们部分“金学”研究者进行深思。
在多种原因的引发下,我对《金瓶梅》的理解多少也有了一些转变,也想试着换个视角去重新观照《金瓶梅》这部伟构具有原创性的价值。
中国的小说发展史有它自己繁荣的季节、自己的风景,有自己的起伏波动的节奏。明代小说无疑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高峰期、成熟期,是一个出大家的时期。要研究这段历史上的小说审美意识,除视野必须开阔、资料储备充分以外,最主要的是如何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和中国小说自身的内在逻辑。比如从一个时段来看小说创作很繁荣,其实是小说观念显得陈旧而且浮在表层,有时看似萧条、不景气,也可能地火在运行,一种新“写法”在酝酿着,所谓蓄势待发也。如果从《三国演义》最早刊本的嘉靖壬午(1552)年算起,《金瓶梅》最早刊本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止,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小说的变革与其说是观念、趣味、形式、手法的变迁,不如说这个时期“人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人群”的差异是根本的差异,它会带动一系列的变革。这里的人群,当然就是城镇市民阶层的激增和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市民的审美趣味大异于以往的英雄时代的审美趣味。而世代累积型的写作在逐渐地消歇,随着人群和审美意识的变化,小说领域越来越趋向于个人化写作。而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在失去意识形态性的宏伟叙事功能以后,积极关注个人生存方式的结果。在已经显得多元的明中后期的历史语境中,笑笑生特异的审美体验应属于一种超前的意识。
这里所说的“超前意识”全然不是从技术层面考虑,而是指《金瓶梅》颇富现代小说思维的意味。比如作者为小说写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它不断地在模糊着文学与现实的界限;它不求助于既定的符号秩序;它关注有质感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追问已经无法从道德上加以直接的判断,因为这种生活的道德意义不是唯一重要的,更重要的倒是那个仿真时代的有质感的生活。于是它给中国长篇小说带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原始冲动力,一种从未有过的审美体验。这就是《金瓶梅》特殊的文化价值。
任何文学潮流,其中总是有极少数的先行者,《金瓶梅》就是最早地使人感受到了非传统的异样。它没有复杂的情节,甚至连一般章回小说的悬念都很少。它充其量写的是二十几个重点人物和这些人物的一些生活片段。但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片段都有棱有角。因为《金瓶梅》最突出的叙事就是要保持原始的粗糙特征。至于这些人物,在最准确意义上说,几乎没有一个是正面性的,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个个都是“坏人”。他们就是一些活的生命个体,凭着欲念和本能生活,这些生活就是一些日常性,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令人崇敬的行为,这些生活都是个人生活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但这里的生活和人物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作者毫不掩饰的叙述中,这些没有多少精神追求的人,他们的灵魂并没有隐蔽在一个不可知的深度,而是完全呈现出来。所以,当你一个个地分析书里面的人物,反而是困难的,而且很难分析出他们的深刻,你的阐释也很难深刻。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没有深刻性,只有一些最本真的事实和过程,要理解这些人和这些生活,不是阐释、分析,只能是“阅读”和阅读后对俗世况味的咀嚼。
《金瓶梅》的叙事学是不靠故事来制造氛围,它更没有三部经典奇书那样具有极纯度的浪漫情怀。对于叙述人来说,生活是一些随意涌现又可以随意消失的片段,然而一个个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和最微小的元素,被自由地安排在一切可以想象的生活轨迹中。这些元素的聚合体,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影响:它使我们悲,使我们忧,使我们愤,也使我们笑,更使我们沉思与品位。这就是笑笑生为我们创造的另一种特异的境界。于是这里显现出小说美学的一条极重要的规律:孤立的生活元素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但系列的元素所产生的聚合体被用来解释生活,便产生了审美价值。《金瓶梅》正是通过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认识了生活中注定要发生的那些事件,也认识了那些俗世故事产生的原因。笑笑生的腕底功力就在于他能“贴着”自己的人物,逼真地刻画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又始终与他们保持着根本的审美距离。细致的观察与精致的描绘,都体现着传统美学中“静观”的审美态度,这些都说明《金瓶梅》的创作精神、旨趣和艺术立场的确发生了一种转捩。
《金瓶梅》审美意识的早熟还表现在事实意义上的反讽模式的运用,请注意,笔者是说作者事实意义上的反讽而不是有意识地运用反讽形式。反讽乃是现代文学观念给小说的审美与叙事带来的一种新色素(我从来反对流行于中国的“古已有之”的说法),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在艺术实践上的反讽的可能,虽然它还不可能在艺术理论上提出和有意识地运用。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金瓶梅》研究界很看中它的讽刺艺术,并认为,作为一种艺术传统,它对《儒林外史》有着明显的影响。但依笔者的浅见,与其说《金瓶梅》有着成功的讽刺笔法,不如说笑笑生在《金瓶梅》中有了事实意义上的反讽。一般地说,讽刺主要是一种言语方式和修辞方法,它把不合理的事象通过曲折、隐蔽的方式(利用反语、双关、变形等手法)暴露突出出来,让明眼人看见表象与本质的差异。而反讽则体现了一种变化了的小说思维方式:叙述者并不把自己搁在明确的权威地位上,虽然他也发现了认识上的差异、矛盾,并把它们呈现出来,然而在常规认识背景与框架中还显得合情合理的事象,一旦认识背景扩大,观念集合体瓦解而且重组了,原来秩序中确定的因果联系便现出了令人不愉快的悖逆或漏洞。因此反讽的意义不是由叙事者讲出来的,而是由文本的内在结构呈现,是自我意识出现矛盾的产物。或者可以更明快地说,反讽乃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出现了自身解构、瓦解的因素。
事实上,当我们阅读《金瓶梅》时,已经能觉察出几分反讽意味。所以对《金瓶梅》的意蕴似应报之以反讽的玩味。在小说中,种种俗人俗事既逍遥又挣扎着,表面上看小说是在陈述一种事实、表现一种世态,自身却又在随着行动的展开而转向一种向往、一种解脱,这里面似乎包含了作者对认识处境的自我解嘲,以庄子的“知止乎(其)所不(能)知”的态度掩盖与填补着思考与现实间的鸿沟。实际上我们不妨从反讽的角度去解释《金瓶梅》中那种入世近俗、与物推移、随物赋形的思维形态与他对审美材料的关心与清赏。其中存在着自身知与不知的双向运动,由此构成了这部小说反讽式的差异和亦庄亦谐的调子,使人品味到人类文化的矛盾情境。
面对人生的乖戾与悖论,承受着由人及己的震动,这种用生命咀嚼出的人生况味,不要求作者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而是以一颗心灵去体察生活中各种滋味。于是,《金瓶梅》不再简单地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和是非善恶的简单评判,而是倾心于人生的生命况味的执着品尝。在作品中作者倾心于展示的是主人公和各色人等人生道路行进中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和小看了这个视角和视位的重新把握和精彩的选择的价值。小说从写历史、写社会、写风俗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这就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这就是《金瓶梅》迥异于它以前小说的地方。
《金瓶梅》中的反讽好像一面棱镜,可以在新的水平上扩展我们的视界与视度。当然,《金瓶梅》反讽形式的艺术把握也有待于进一步思考与评说。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归结一句话,就是它突破了过去小说的审美意识和一般的写作风格,绽露出近代小说的胚芽,它影响了两三个世纪几代人的小说创作,它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