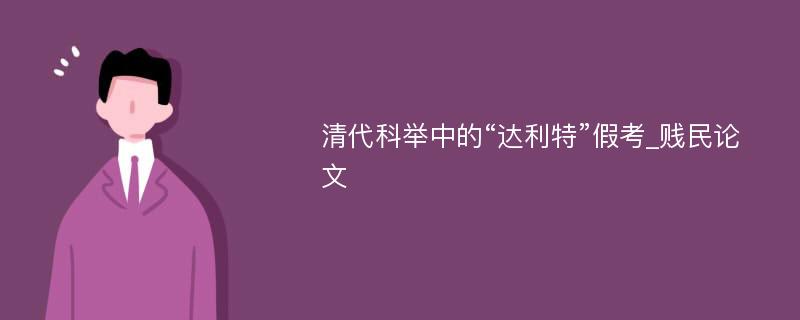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贱民论文,科举论文,清代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3-0072-08
在隋唐以迄清末1300年的历史中,科举制总体而言越来越走向开放,但历代均有某些所谓的“贱民”群体被排除在外。终清一代,由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贱民等级的应举资格被严格限制,从而无法直接以合法身份进入科场。至雍正时,朝廷先后出台针对某些贱民群体的“除豁令”,但一方面其规定本身十分严苛,另一方面“人以役贱”,社会总需一定人群从事所谓的“贱役”,因此,这一松绑政策的实质意义相当有限。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贱民冒考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清代贱民等级的应举资格与冒考问题,为全面、深入审视科举制的开放性、公平性以及社会等级与社会身份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参照点,对其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价值。学界对清代贱民等级的应举资格及相关的冒考问题已有较多关注,但这一问题牵涉面广、情节多有复杂,尚有许多值得拓展与深入之处。
一、清代社会贱民等级的构成
传统中国社会历来都是一个“良贱有别”的等级社会。不同朝代“贱民”名目具有一定的差异,而其等级范围也不尽一致。到明清时代,良贱律成了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君健曾指出,在明律中“贱”主要指“奴婢”,杂户中大约除了乐户、倡优以外,其余杂户的法律地位都不是贱民,与一般凡人没有差别。《大清律例》继承了明律中的良贱律,除奴婢之外,同时又明确地将其他一些人群纳入了贱民等级范围内,“贱民”这一概念被正式法律化了。[1]
那么,在清代何为“贱民”?“贱民”范围包括哪些社会群体?《清史稿》称,“且必区其良贱,如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2]清代的贱民首先是指奴婢和倡优,长随跟奴仆等同。为政府服役的皂隶等因其所从为“贱役”,因此被划定进了贱民的范围。所谓“人以役贱”,无论之前是属于良籍的平民等级,还是某些特权等级的子弟,只要承担了皂隶、马快、步快等政府杂职,便立即被划进了贱民的范畴。此外,尚有一些生活在某些地区的特殊人群,在《大清律例》中虽没有将之列为贱民的明文规定,但无论在各地方民间社会还是地方政府,却又都将之视为贱民。这些类别的贱民包括生活在某些地区的丐户、乐户、蜑户、九姓渔户等。雍正年间,政府先后宣布豁除丐户、乐户的贱籍,蜑户、九姓渔户亦照此办理。但是,这些贱民的子孙必须在其报官改业“从良”几代之后,且须本族亲支内并无操持贱业者为必要条件,方可获得应试出仕的资格。同时,豁除贱籍者子弟即便是达到了这些苛刻的条件,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也时常遭到来自其他考生以及廪保的歧视与阻碍。因此可以说,这些贱民在豁除令发布之前属于贱民,而在豁除令发布之后且改从“良业”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仍被视作贱民。
经君健认为,清代社会贱民等级主要包括奴婢类贱民、隶卒类贱民、佃户类贱民以及堕户、丐户、九姓渔户、蜑户等类别。[3]冯尔康与常建华持论也大致如此。[4]由于“人以役贱”,还有某些从业者也在应试出仕上受到一定限制,如身为屠户者、厨师者、修脚者等均是如此。因此,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此类人群也同样带有一定贱民身份色彩,或姑且可以称之为“半贱民”身份者。以下将主要就奴仆类、隶卒类、倡优及乐户、堕户类贱民与其他具有一定贱民身份色彩者的应试权益以及相关的冒考问题展开探讨。
二、清代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从“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
关于清代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一方面可以说是基本缺失的;另一方面,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也为贱民应试权益的获得提供了一种制度层面上的“可能性”。
(一)奴仆类贱民的应试权益①
按清律规定,奴仆类贱民不得应试出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其应试权益基本上是缺失的。但是庄头却存在例外情况。八旗户下投充庄头,“无论旗档有名无名,均不准应试出仕”,而其子弟则可参加考试。[5]投充庄头子弟考试,系由满洲都统咨送,所以常在满洲额内入学、中式。雍正十一年(1733年),经吏部奏准改属汉军额。乾隆三年(1738年),重申雍正十一年定例,要求严格执行投充庄头子弟“注名另册咨送,归入汉军额内考试”的规定。[6]内务府各司所属大粮庄头、园头、投充庄头、蜜户等亲丁内有情愿考试者,查核丁档有名者,准予报考。[7]另外,由内务府拨出到王公宗室户下管庄的庄头与一般八旗户下的庄头也不同,自嘉庆十一年(1806年)后开始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旗档有名者,归入汉军考试,旗档无名者,归入民籍考试。”[8]
奴仆开户后,亦曾有参加科举考试者。据“嗣后八旗远年开户人等,除从前奉有谕旨准其考试之举监生员仍准其考试外”,[9]可以断定曾经有开户者读书入学而成为举监生员者,甚至还曾有获准参加会试的情形存在。但总体上而言,放出奴仆的身份仍然低于旧主,因此,清代主要还是采取限制其应试出仕的政策。乾隆三年明确规定,“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买,作为印契之人,令在本主佐领下选补步军。俟三代后,著有劳绩,本主情愿放出为民者,具呈本旗,咨报户部,查明祖父姓名籍贯,准其为民。仍行文该地方官注册,止许耕作谋生,不准考试。”[10]又如乾隆六年(1741年)规定,“从前契买家奴,将本身及子孙考试之处永远禁止”;投充、掳掠人等未经开户以前,“曾在伊主家身供役使,今若准令考试,究与名分有乖。应将本身及子孙考试之处,永远禁止。”[11]不过,虽然乾隆六年出台了永远禁止开户人应试出仕的规定,但至少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奴仆开户后有的仍可应试,而通过考试或捐纳也可成为在京或在外的文武官员。[12]
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颁布了如下谕旨:向来满汉官员人等家奴,在本主家服务三代实在出力者,原有准其放出之例。此项人等既经伊主放出,作为旗、民正身,未便绝其上进之阶。但须明立章程,于录用之中,仍令有所限制。嗣后,此等旗民家奴,合例后经该家主放出者,满洲则令该家主于本旗报名,咨部存案,汉人则令家主于本籍地方官报名,咨部存案,经部覆准后,准其与平民一例应考出仕。但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至三品,以示限制。著为令。[13]嘉庆十一年(1806年)进一步确定为放出家奴“只许耕作营生,不许考试出仕”;“其放出入籍三代后所生之子孙,准其与平民一例应试出仕,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至三品。”[14]因此,放出家奴本身不允许应试出仕,而子孙虽然可以但也必须为放出、入籍三代后所生,同时在出仕官品上仍有所限制。之后,对于放出奴仆应试出仕资格的限制,一直至光绪时期皆大致如此。
(二)隶卒类贱民的应试权益
前引《清史稿》中的资料称,凡衙署应役之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而长随的地位则与奴仆等同。这些衙门当差者既被列为贱民,则无法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
一般说来,在衙门应役的库丁、民壮一类,因列于齐民,因此享有应试出仕的权益。但道光十九年(1839年)又规定,“户部库丁,自属贱役,不准捐考。其子孙照小马、隶卒之例办理。”[15]因此,库丁者也并非都可以应试出仕。嘉庆二十年(1815年)覆准,“民壮例得捐考,如系承缉案件,总催钱粮,与粮差、皂快无异,其子孙不准考试。”[16]可见,民壮是否具有应试资格,还需要看其具体从业形态。又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覆准,“江西赣南道衙门舍差,专司关饷,并无拘犯行杖之事,原择身家清白之人承充,嗣后准其捐考。”[17]道光四年(1824年)覆准,“安徽省长淮卫粮差,系轮派催粮,并不兼充他役,亦非支领工食,与湖南省专设粮差不同,其子孙仍准其捐考。”[18]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覆准,“承催卫粮民粮,名为粮长,其子孙准其捐考。如由贱役改充及兼充贱役者,仍不准借粮长名目,蒙混捐考。”[19]由于隶卒人等在承差之前“原身份”不尽相同,而承差具体形态也有差异,因此,是否具有应试权益也不尽一致。再如,道光七年(1827年)覆准,江苏徐州道衙门直堂吏一项,均系招募清白农民,自备资斧,办理河工事件,并不勾摄公事,嗣后准其捐考;[20]道光十三年(1833年)覆准,江苏省浒关渡夫,系摇载书役巡税,即与在官人役无异,照在官轿夫之例,不准捐考;[21]道光十九年覆准,良民充当船头纤夫,本非卑污贱役,向无额设卯簿,嗣后准其捐考;[22]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覆准,民人曾充军牢,虽无卯簿结状可稽,究系贱役,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23]据此,贱役身份的判定相当复杂,承差之前是否为良民、是否为“在官应役”及是否列名于“卯簿”、是否勾摄公事、是否拘犯行杖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于隶卒类贱民而言,郑定、闵冬方认为,“关于同为贱民的隶卒的解放,虽未有明令,但根据除豁的精神,似乎应该也如其他贱民一样一体解放。”但二人又认为,隶卒的解放被拖延到了民国时期。[24]清末法学家薛允升认为,若隶卒有改业为民已逾三代,似应准其报捐。[25]而根据上引道光二十八年关于民人曾充军牢者,“究系贱役,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似乎可以认为此种规定同样适用于隶卒类贱民。
(三)倡优、乐户、蜑户与九姓渔户的应试权益
在清代,倡优类贱民并不具有应举资格。至雍正时,朝廷先后出台了关于乐户、堕民、蜑户、丐户贱籍身份的“除豁令”。[26]不过,“除豁令”的发布并不意味着贱民可以立即获得应举资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议准:“山陕之乐户、江浙之丐户,虽编籍由来无可确据,而其相仍托业,实属卑污。雍正元年,因御史年熙、噶尔泰先后条奏,准令除籍改业,得为良民。正所以杜其邪僻之路,非即许其厕身衣冠之林也。嗣后应酌定限制,以清冒滥。如削籍之乐户、丐户原系改业为良,报官存案,祓濯旧污,阅时久远,为里党所共知者,自不便阻其向上之路。应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系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若系本身脱籍,或仅一、二世,及亲伯叔姑姊尚习猥业者,一概不许侥幸出身。其广东之蜑户、浙江之九姓渔户及各省凡有似此者,悉令该地方官照此办理。所有从前冒滥报捐各生,均行斥革。……”[27]清人王庆云在论及此一规定时称,“旧染污俗,咸与维新,而必以四世为限,盖宽大之中尤极爱惜名器云。”[28]可见,被豁除贱籍的乐户、堕民、丐户、蜑户等在应试出仕上仍受到诸多限制。这些限制条件主要包括:一是报官改业。实际上,对于这些贱民而言,由于为生计所迫,令其改从“良业”并不容易。二是年限限制。在报官改业之后,需要在四世之后方可应试,时间相当漫长。三是在“四世”的期限内,还须以“亲支无习贱业者”为必要条件。如果这一条件不能满足,则报官改业四世之后仍无法获得应试资格。以此来看,雍正朝对于乐户、堕民、蜑户、丐户所出台的“除豁令”的实质意义仍是相当有限的。
(四)“半贱民”身份者的应试权益
“半贱民”身份所涉及的具体“贱业”形态比较广泛、复杂,而应举权益所受限制也不尽一致。例如,厨行、屠户等“半贱民”身份者,均在应试出仕方面受到一定限制,而收生妇女之子孙是否可以应试需要看其是否“承差服役,传验奸情”。道光四年覆准,“厨行一项,除本身不准捐考外,酌照捆工及在官轿夫之例,于报官止业后,扣满十年,子孙方准捐考。退业后复朦混承充,即将捐考之人,一并斥革。至本系家奴充当厨行者,仍照例不准捐考。”[29]道光七年议定,“民间收生妇女,地方官概不准勒派验奸,果无别项身家不清,其子孙应准其捐考。如系承差服役,传验奸情,迹类仵作,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查系身家清白,方准捐考。”[30]光绪元年(1875年)覆准,“屠户一项,执业近于残忍,未便遽列士林,俟报官改业后,准其捐考。”[31]厨行、屠户以及收生妇女如果报官改业,则十年之后其子孙便可应试,这与一般的奴仆、隶卒、倡优以及乐户等类贱民需要报官改业三代之后所生子孙方可应试是不同的,在应试出仕上所受限制明显较轻。此外,棚民与畲民也经常遭到社会歧视,在应试出仕上受到地方社会的阻挠。但棚民子弟应试受阻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贱民”身份的问题,[32]而畲民应试受阻也与本文所探讨的各类贱民有很大差异,此不赘述。
从以上探讨可以看到,奴仆类、隶卒类、倡优、乐户、堕民类贱民的社会身份具有相当强的“纵向遗传性”,甚至也有一定的“横向扩散性”,这些贱民及其子孙在应试出仕上均受到相当严格的限制。相比较而言,厨行、屠户等“半贱民”身份的“纵向遗传性”无疑要弱得多。另一方面,既然规定了放出奴仆若干代之后以及乐户、丐户、隶卒等报官改业若干代之后可以应试出仕,则从制度上说贱民等级的应试出仕权益终究有了一定改良。因此可以认为,清代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
三、清代科举制下的贱民冒考现象
清代对于贱民应试出仕进行了极大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贱民都能够遵行这些规定。实际上,清代的贱民冒考现象并不鲜见。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对于各种情形的贱民冒考案例进行一一列举,在此仅通过某些案例来管窥不同类别贱民的冒考问题。
(一)奴仆类贱民的冒考
嘉庆年间,广东赎身奴仆洪兆龙之子在应试时被判定为冒考情形而加以禁止。[33]广东巡抚陈若霖在给户部的意见中认为,洪兆龙曾经其父洪显明卖与郑龄之父郑希大为仆,后又赎出为民,而且洪兆龙娶妻生子也均在赎身以后,并未受郑姓豢养之恩,因此,若照放出世奴俟入籍三代后始准子孙应试似乎未有区别。但在究竟应否允许洪兆龙之子应试上也难以断定,因此向户部呈请批示。户部根据“其放出入籍三代后所生之子孙准其与平民一例应试出仕,京官不得至京堂,外官不得至三品。其虽经放出,未经呈报者,应俟报官存案之日起限”这一规定,将洪兆龙之子应试判定为冒考现象。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江苏放出奴仆张聚恒之孙张绍华应试时,也被判定为冒考情形而加以禁止。[34]当时的江苏巡抚认为放出奴仆张聚恒之孙张绍华即是属于“放出奴仆三代后所生子孙”,而刑部则认为张绍华并非“放出奴仆三代后所生子孙”,张绍华之孙即张聚恒之玄孙方为“放出奴仆三代后所生子孙”。这一案例反映出了不同司法部门对于“入籍三代后所生之子孙”理解的差异。按照刑部的解释,放出奴仆张聚恒之孙张绍华应试因尚非“入籍三代后所生之子孙”,因此属于冒考。
(二)隶卒类贱民的冒考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安徽盱眙县一位皂隶的子孙参加武科乡试,遭到攻讦。知县杨松渠认为,该武童的父亲早在其祖父充当衙役之前就已出继他人,故该皂隶的贱民身份与武童无关,应准其参加考试。两江总督书麟对之进行了批驳,认为即使情况如此,该武童参加考试也“究属违例”,将知县杨松渠咨参。经礼部议,杨松渠被“降一级调用”。[35]又如光绪三年(1877年),曾在广西怀集、灵川、贺县等县衙门当过门丁的牛升,冒入桂林县籍,使其子牛光斗考试中式举人。被查出后,牛光斗举人头衔被革斥并按律惩办。[36]
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在应考童试时,也曾由于“身家不清”而遭阻考。关于这一问题,王清平与王德彰认为“皂的子孙后代允许参加考试,而隶的子孙才不允许考试”,而“刘春霖的父亲在保定府衙门当差,是属于‘皂’,母亲给知府家当女仆”,因此并不在应试出仕限制之列。[37]但实际上,所谓皂役之子可以应试出仕的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在清代,皂役之子“冒考”的案例并不鲜见。既然被判定为“冒考”,则说明其本身并不具有应试资格。从嘉庆七年(1802年)恩治所称“查各项皂役人等例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向有成例遵行在案”,[38]亦可清楚地得知皂役子孙并不具有应试出仕的资格。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清代科举考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刘春霖并不具有应试资格,其参加科举考试等于是一种冒考行为。
(三)倡优类贱民的冒考
关于倡优类贱民冒考,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戊午科乡试大案最广为人知。该科乡试,旗籍满洲人平龄中式在前十名内,但因被认定为属于“优伶”中式而被革去举人,并且遭到弃市的悲惨下场。薛福成认为,平龄并非真正的优伶,只是偶尔登台表演而已。“平龄素娴曲调,曾在戏院登台演戏。盖北方风俗,凡善唱二黄曲者,虽良家子弟,每喜登台自炫所长,与终岁人斑演戏者稍有不同。然京师议论哗然,谓优伶亦得中高魁矣。”[39]由于这一科场案中夹杂着激烈的政治斗争,除了平龄以外,主考官柏葰及同考官浦安等均被一同弃市。从贱民冒考的角度来看,则是平龄的“偶尔登台表演”使其被沾惹上了“贱民”身份,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直接被判定为贱民冒考行为。
乾嘉时期安徽六安州捐职州同畲蟠赴部呈控廪生周合等阻考一案,[40]作为贱民冒考的案例也相当值得关注。此案中的畲蟠原籍为安徽省凤阳府定远县,其曾祖畲汉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迁居六安州,生子畲通海(即畲蟠之祖父)、孙畲光前(即畲蟠之父),并且置有田房产业。不过,当时仅仅是居住在六安州,包括畲汉功、畲通海以及畲光前在内均未真正入籍此地。这意味着畲氏在六安州还无法获得以户籍为载体的诸如应试、报捐等资格与权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畲光前呈请入籍应试,“当有绅士李杰等数十人以畲光前之祖母缪氏在州花鼓唱歌,其父畲通海抬轿营生,其母单氏受雇与人服役,事业卑贱,请饬回原籍,以杜朦考等情,赴州讦告”。其后,畲光前随以“将相无种,人贵自立,古有屠狗赌奕即身卿相”等词具诉。正当六安州申饬查办期间,畲光前又呈明愿归定远县原籍。但实际上,之后其并未回定远原籍。在畲光前故后,畲虬与其弟畲步蟾分别于嘉庆三年及十五年间先后呈请入籍六安州,并请生员吴麟标等具结投呈,由于畲光前之前被讦原案情节而未获准。于是,畲步蟾便赴藩司及学政衙门进行控告。当时参与处理该案的候补知县赵墫与知州吴永绥认为,畲步蟾迁居已在六十年之外,该州某些绅士控其身家不清并无证据,因此应准其入籍捐考。正当时任巡抚的胡克家下令进一步调查取证时,畲步蟾又与畲蟠先后赴部报捐职监,且虽经饬催取具族邻供结但最终并未送呈。其中的重要原因便在于畲光前之前曾有被讦前案,而且讦控人数众多,因此基本上没有人愿意为之出结。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畲步蟾子弟应考州试,该州童生以其出身卑贱不愿与之互结,而廪生周合等亦不敢承保,于是畲步蟾再以违例阻考上控。代理知州吴篪鉴于“与考生童及合学廪生,佥称畲缪氏花鼓卖唱属实”,因此议请不准捐考。畲蟠未甘罢休,并赴巡抚衙门控告。在控告无果的情况下,又以周合等阻考赴礼部具控。在律无正条而又无成例可引的情况下,礼部只得依据“相近原则”进行比照办理。由于花鼓卖唱与乐户、丐户“事属相类”,因此最终判决结果为:第一,畲蟠请照削籍之乐户、丐户例,以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准予报捐应试。第二,畲蟠系畲缪氏曾孙,其祖畲通海即经改业,现在本族亲支亦俱清白自守,但逮至畲蟠尚止三世,其与畲步蟾等均不准捐考。第三,畲蟠之子侄已逮四世,寄籍六安又在六十年以外,应准其在该州入籍捐考。至此,这一时间跨度久远,案情曲折、复杂,前后曾引发了多次争讼而且诉讼层次不断升级的贱民冒考案才得以完全平息。
此外,还有其他某些从业不够体面的“半贱民”身份者子弟应举的现象。例如,钟毓龙在《科场回忆录》中提到其幼时同学、祖母为喜娘的童增奎应试入学的问题。[41]按钟氏说法,童增奎身家并非十分清白。如果严格按照清代“清流品而重名器”的传统规则,则亦可认为其存在着冒考嫌疑。
终清一代,在“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下,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乐户、堕民等贱民的应试资格被严格限制,而其他一些如厨行、屠户等“半贱民”身份者也同样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使贱民报官改业从良,也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可取得应举的资格。由于被限制了应试资格,因此即使具有真才实学的贱民身份者,也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不过,由于科名的强大诱惑,又可以看到不少贱民身份者冒考甚至出仕的现象。从相关的史料来看,衙门隶卒类贱民冒考现象在清代贱民冒考的总体中所占比例尤重。这与此类贱民在地方社会的实际“操纵力”不无关系。以上所列贱民冒考的各案例中,畲光前以“将相无种,人贵自立,古有屠狗赌奕即身卿相”进行自辩,虽在当时属于社会的某种“异类”,但这一“呐喊”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震撼之处。相对于畲光前而言,刘春霖虽也属于贱民冒考,但有力廪保为其担保,因此能够得以应试并最终成为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此外,由于有的贱民身份者本身便十分清楚其在应举方面所受限制,因此选择以跨区域冒充户籍的方式达到应试的目的。例如,前引牛升之子冒考一案便是属于此类情形。而对于“半贱民”身份者,能否顺利与考,很大程度上在于是否能够寻得有力廪生为之作保。如果有廪生为之出结,则往往可以参加考试。上引钟毓龙之幼时同学童应奎即是属于此种情形。此亦为探讨贱民冒考问题时所应特别关注的方面。
四、结语
传统社会贱民等级的真正解放是在清末中西文化发生碰撞之后,基本上是从20世纪初才真正开启的。但作为传统社会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在中西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于1905年已被停废。
那么,贱民冒考与一般意义上的冒籍应试有何关系?贱民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对科举制的开放性、公平性又有何影响?对于贱民冒考,杨方益认为这也是一种“冒籍”。在他看来,清代科举冒籍之“籍”包括两个方面:一为籍贯之籍,一为家庭成分或者说阶级性质之籍。[42]后者实际上便是说贱民冒考属于一种冒籍问题。的确,若从“贱籍”与“良籍”的二元划分来看,贱民冒考无疑等于在事实上由“贱籍”冒充“良籍”。就此而言,似亦可将之视为一种特别意义上的“冒籍”。不过,清代科举冒籍主要还是指跨区域性的冒充户籍应试,对贱民违反规定应考的现象主要还是以“冒考”来指称。贱民只有在冒考的同时又存在跨区域冒充户籍的情形,才可能被称之以“冒籍”问题。
以往有论者认为,科举考试并不具有真正的平等精神,其原因之一便在于这一制度将整个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张仲礼便称“有一个社会集团是完全排斥在外的。凡奴、仆、娼、优、隶和其他属‘贱民’出身者,均不得参加科举考试”。[43]若就开放性而言,不可否认科举制因将贱民限制在外而降低了其开放程度。不过,我们应理性看待科举制将贱民等级限制在外这一问题。这是因为,首先,其根源并不在于科举制自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即使不采行科举制而采用另外的选才方式,贱民也同样将被排除在外。其次,虽然由于“人以役贱”,良人因为选择了某些“下贱”的职业便被严格限制应举资格,但贱民等级群体无疑只是平民以上社会等级总体的一小部分。再次,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新陈代谢”功能,是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封建社会、印度种姓社会以及日本的藩封制度等其他相对封闭的社会形态所不具备的。[44]因此,以同时代横向比较视野来看,科举制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开放性与公平性。
在清代,对于并不知其是否为贱民子弟的“路边遗弃儿”应否准许应试出仕甚至都存在争议。[45]在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下,我们不应苛求科举制百分之百的开放性。因此,尽管贱民等级的应试资格被加以严格限制,但其对科举制的开放性、公平性并无根本性的影响。总体上看,科举制仍不失为一种开放、公平的选才制度,[46]亦仍堪称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项重大制度文明。[47]
注释:
①关于奴仆类贱民应试出仕的权益问题,经君健在《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中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里仅作一简单介绍。参见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