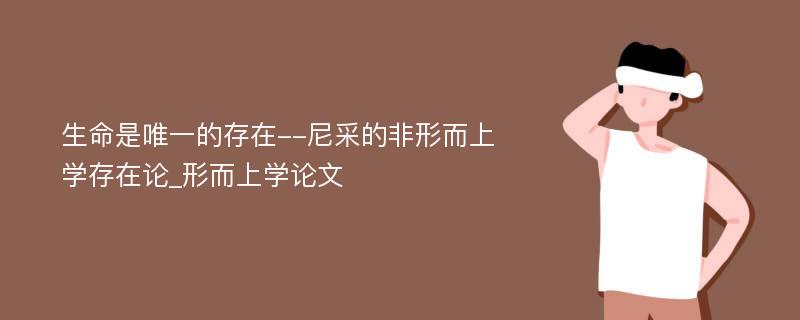
生命是唯一的存在——尼采的非形而上学存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形而上学论文,生命论文,是唯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4)02-0034-08
一、尼采是谁?形而上学家抑或非形而上学家
尼采的言述大多是断章和格言,没有什么形式上的逻辑,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语义限定 ,同一个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味,且往往是相反的意味,比如“真理/谬误 ”、“好/坏”、“善/恶”等等。初读尼采真有点琢磨疯子呓语的感觉,但细细嚼来又 感到别有意味,一种充满思性反讽的意味。因为,上述语词不是可以互换的吗?换一个 角度“真理”不就是“谬误”,“好”不就是“坏”吗?但人们还是习惯了以传统的眼 光看尼采,这个疯子,真让人眼花缭乱!
人们想看清尼采。“尼采是谁?”这是海德格尔在《尼采》中提出的问题。在海德格尔 看来,造就“真正尼采”的是形而上学的传统,尼采是“完成形而上学的思想家”或“ 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将尼采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并在这一关系中谈论尼采及其思 想,也许是海氏尼采研究中最有价值和启示性的东西,非此我们不能走近尼采也不能走 近形而上学。但是,海氏的研究方式和结论却可以商榷,比如德里达的质疑。
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以他预设的形而上学阐释框架将尼采思想整理成了形而上学 ,从而将尼采思想的非形而上学性掩盖起来了。在《阐释签名(尼采/海德格尔):两个 问题》一文中,德里达指出:海德格尔以“尼采”作为洋洋百万言的《尼采》之书名, 仿佛“尼采”只有一个,“尼采思想”只有一种。海德格尔的预设是“尼采思想即便不 是古典意义上的体系,但仍具有统一性”。[1](P235)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对尼采其人 其思之单一性和统一性的预设只是海氏一厢情愿的形而上学独断,尼采的透视主义和自 觉的面具意识使签名的单一尼采具有潜在的复数性,尼采言述的碎片性是不可整合的, 不存在一种言述背后的统一的尼采思想。但海德格尔却固执地要挖掘出那碎片下的统一 的尼采思想,拯救被碎片掩盖的尼采。“海德格尔清楚提出的一个论题是:凡是伟大的 思想家都只有一种思想”。[2](P235)看来,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 在尼采光怪陆离的“风格”背后没有统一的思想,统一思想的信念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 东西,我们要学会接受破碎的思想才能走近尼采;后者却认为在尼采表面风格之“多” 的背后有思想之“一”,只有发掘出被掩盖的统一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尼采的多样风格。
细察尼采言述,德里达与海德格尔二人的断言都叫人生疑。德里达被尼采的透视主义 、面具意识和言述表面的破碎所迷惑,以为尼采思想正中其解构主义的下怀。不错,尼 采讲透视主义旨在破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尼采本人的视角是不确定的, 至少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有了自己独特而确定的视角,这便是所谓“ 强者”、“健康者”、“高贵者”的视角。如果说在尼采言述中有视角混乱的话,那也 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的事,即尼采思想的准备期。至于“面具”,尼采是说 过“每一思想深邃的人都需要戴面具”,[2](P44)尼采也的确戴过“查拉图斯特拉”这 种有形的面具和别的无形面具,但戴面具不一定是为了将自己藏起来,也可以是为了更 好地表达自己的意图。显然,以查拉图斯特拉这个波斯先知的身份来宣布上帝之死和超 人的来临,比尼采本人出面说要好得多。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尼采是不屑 于戴什么面具的。
尼采曾骄傲地说:“我身上没有任何病态的特征,即使重病缠身,我也从不是病态的 。”[3](P39)作为健康者、高贵者和强者,尼采从来就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至 于表面风格的混乱多样要么是问题没想清楚(比如早期),要么是一种表达的技巧和策略 ,要么是与传统语言之间不得已的反讽、戏拟等游戏。尼采绝不是一个没有自己一贯之 思想的德里达式的“风格主义者”,也绝不是刘小枫所说那种处在“说与不说的”内心 紧张之中,好“微言”而玩“大义”的智者。[4]
就此而言,我倾向于海德格尔的判断,在碎片式的尼采言述下有一种统一的尼采思想 ,虽然它不是一种古典式的体系。不过,海德格尔的发掘方式令人难以接受,其如德里 达所言,他把尼采装进了他预先制作的一个名叫形而上学的套子。
海德格尔不同意狄尔泰等人对尼采的浪漫化,而认为尼采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海德 格尔相信:凡伟大的思者都思考同一个问题,即“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思考是人的 天命,人类在对存在的思考中开启自己的存在,伟大的思想家之伟大就在于他被天命所 召而行进在思考存在的途中,或者说,所有伟大思者的思想都聚集在(统一在)“存在” 这一问题之中,尼采也不例外。
海氏认为对存在的思考可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特征)是什么?一是 存在本身是什么?前者是所谓“主导问题”,后者是所谓“基本问题”。在西方思想史 上,思考存在问题的主要样式是哲学—形而上学。
在尼采的思想碎片中,海德格尔发掘出两个表述来说明尼采思想的哲学—形而上学性 ,那就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和“一切事物的永恒回复”(the eternal recurrence of all things)。海德格尔说: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态度可以通过两个句 子来规定:其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是“权力意志”;其二,存在是“一切 事物的永恒回复”。[5](P25)也就是说,“权力意志”学说回答了主导问题,“一切事 物的永恒回复”学说回答了基本问题。据此,海氏断言:尼采思想行进在西方形而上学 追问的轨道之上,只有将尼采思想带入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领域才能拯救出真正的尼采 思想并确定其意义。
海德格尔的这一论断叫人莫名。海氏在批评形而上学时不是说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是 以思考“存在者”的方式遗忘了“存在”吗?不是说形而上学只思考了“一切存在者之 存在是什么”这个“主导问题”,而从来就没有思考“什么是存在本身”这个“基本问 题”吗?海德格尔的著名推断是:由于看不到“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形而上学 误以为它所思考的主导问题(“存在者”的问题)就是基本问题(“存在”本身的问题), 从而导致了它对“存在”的遗忘。叫人纳闷的是:海德格尔一边说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 上学家,一边又说尼采不仅以“权力意志”的论述思考了主导问题,也以“一切事物的 永恒回复”的论述追问了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尼采并没有像形而上学家那样遗忘存在本 身的问题。显然,海德格尔有关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论断与他通常的形而上学 论是矛盾的。
更叫人难以苟同的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问题框架中对尼采思想之形而上学性的论断 。德里达就对海德格尔这套拯救尼采的计划表示怀疑,“在所有的问题中,我们必须首 先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这一计划是否是根本的和必要的。”[6](P157 )“海德格尔在拯救尼采时又失去了他;他想救他,同时又让他走掉。他在肯定尼采思 想的独特性的同时,又竭尽所能地想表明尼采的思想完成了形而上学的最伟大的(因此 也是最一般的)计划。”[6](P159)
德里达的这一提醒很重要,海德格尔的确是在自己的存在论问题结构中将尼采思想模 铸成了最后的形而上学,并宣称这就是“真正的尼采思想”。在此的问题是:尼采思想 是否真如海氏所言归属于他所谓的形而上学?能否将他理解的尼采思想说成是真正的尼 采思想?
第二个问题在今天的学术背景下似乎不用多说了,任何人都无权这样独断,这已是常 识。须深究的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等于问:“权力意志”真是对“一切存在者之存 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吗?还有,“一切事物的永恒回复”回答了“存在本身是什 么”这一问题吗?更重要的是,这种回答真的是在形而上学的轨道上吗?
二、尼采的生命存在论
要恰当地回答尼采思想是否真如海氏所言归属于他的形而上学这一问题必须与海德格 尔的提问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摆脱他预定的眼界与思路。我想从海德格尔不太重视也 被人们念烦了的大白话“上帝死了”开始。尼采笔下的一个疯子向世人宣告:“上帝死 了”。人们很愕然,心想:上帝之为上帝,就在于他的不死性,说话的人一定是“疯子 ”。尼采当然不这么想,他宁愿相信疯子也不相信人们。其实,尼采本人就是这个“疯 子”。
“上帝死了”不是说原来有上帝,现在他死了,而是说上帝本来就不存在。“上帝死 了”不过是上帝本来就不存在的一个迟早要出现的见证。不过,“上帝死了”也不是说 以前没有上帝,而是说以前活着现在死了的上帝是人们虚构的上帝。“上帝之死”的双 重义涵必须注意。
此外,还须留意的是,尼采所谓“上帝死了”不单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之死,而是指整 个形而上学的上帝之死。尼采曾将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和耶稣式的神学都称之为“形而上 学”,(注: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称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是“木乃伊形而上学”,称 耶稣式的神学是“刽子手形而上学”。)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虚构一个形而上的与“这 一世界”对立的“另一世界”,并将其全部思想建立在这一虚构之上。“上帝”作为“ 另一世界”的象征就是哲学和神学的形而上学虚构。
形而上学的“上帝”之死将尼采逼向了后形而上学之思,即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处境中 重新思考一切。因此“上帝之死”是我们进入尼采思想的首要路标。
虚构的“上帝”死了,我们面对的唯一真实是什么?“生命”!从“生命”出发重新思 考一切和估价一切是尼采思想的基本路向。于是,生命是什么?如何排除上帝的阴影以 重新思考生命本身?从生命本身出发思考到什么?如何清除形而上学的妄念,从生命出发 重估一切思想文化、社会秩序的价值并重建价值?“权力意志”、“一切事物的永恒回 复”、“超人”、“价值重估”、“虚无主义”等尼采式的言述如何聚集在生命之思的 路上并发出独特的声响?这些问题将是我们思考尼采思想的具体路标。
生命是什么?尼采用五个表述回答了这个问题。1.生命是唯一的存在;2.生命是肉体; 3.生命是权力意志;4.生命是力的差异运动;5.生命是一切事物的永恒回复。这五个表 述相互关联,其潜在批判指向就是形而上学的存在论。
“存在——除‘生命’而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3](P186)有生有死的 生命运动就是全部的“存在”,此外,别无其他存在。尼采的这一存在论思想显然是针 对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无论是哲学形而上学还是神学形而上学都相信存在是二元的, 俗常所谓的生命存在不过是一种过眼烟云的存在,一种有死的存在,这样一种存在在终 极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存在,终极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是不死的恒在(柏拉图的理式和基督 教的上帝)。然而,不死的恒在(上帝)终于死了,我们被抛给了唯一的存在:有生有死 的生命存在。
唯一存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存在?生命是肉体。尼采的这一思想叫人难以接受。其实几 乎全部尼采思想乍一看都叫人头疼,因为我们已习惯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并在形而上学 铸造的语言中面对尼采。在形而上学的二元世界中,生命是一分为二的,即灵魂生命和 肉体生命(或感性生命和理性生命)。前者是不死的,后者是有死的;前者是上帝之城的 居民,后者是地上之城的居民,形而上学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尼采说生命是肉体也就 是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中以极端的方式强调纯粹的灵魂生命(理性上面)是不存在的,存在 的只是被形而上学贬责的肉体生命。
尼采说:“‘灵魂’、‘精神’,最后还有‘不死的灵魂’,这些都是发明来蔑视肉 体的,使肉体患病——‘成仙’。”[7](P106)“根本的问题: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 且以肉体为线索。肉体是更为丰富的现象,肉体可以仔细观察。肯定对肉体的信仰,胜 于对精神的信仰。”[3](P178)因为,肉体是生命唯一的居所。
肉体化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纯粹灵魂(纯粹理性)的生命是不存在的,因此,尼采说 应把这些信念从科学中驱逐出去!不过,尼采也并没有断然否定“灵魂”、“理性”和 “精神”的存在。他建议我们不要简单地放弃这些古老而受人崇敬的假设,而要将它们 从形而上学的语境中拯救出来,从肉体出发去改写这些字眼的语义,提出一些新的理性 假设和灵魂假设。“今后诸如‘终有一死的灵魂’、‘主观多样性的灵魂’、‘作为本 能与感情的社会结构的灵魂’等等概念,应该在科学中享有合法权利。”[2](P13)这样 的“灵魂”(理性、精神)显然已肉体化了。
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之外,说生命是肉体也就是说俗常所谓的感性/理性、灵魂/肉体 都不过是同一生命的现象。查拉图斯特拉就说:“感官(sense)和精神(spirit)是工具 和玩物:它们后面还站着自己(the Self),自己用感官的眼睛寻找,也用精神的耳朵聆 听。自己总是在听、在找,它比较、支配、征服、破坏、它统治着,也是我(ego)的统 治者。我的兄弟呀,在你的思想和感觉后面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人,一个不知名的智者, 它叫自己。它住在你的肉体内,它就是你的肉体。”[7](P50)
那么,作为肉体的生命是什么?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超越自我”的一节,尼 采说他发现了生命的秘密:“生命就是权力意志。”在这一节,查拉图斯特拉提出并回 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最智慧的人”所面临的危险何在?查氏从一个古老的哲学信念说 起,即“最智慧的人”(哲学家)的根本动力是“求真的意志”,(Will to Truth)但查 拉图斯特拉告诉“最智慧的人”一个秘密:“求真的意志”就是“求权力的意志”(
Wille zur Macht,the Will to Power)。智者(统治者)的根本危险不是俗常所说的来于 “不智者”(民众)的造反,而是来自求真意志所掩盖的求权力的意志或统治民众的意志 。通常人们认为,智者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但查拉图斯特拉说:“你们,最智慧的 人啊,你们的危险以及善恶的结局不是这河流,而是意志本身,即求权力的意志——永 不枯竭的创造生命之意志。”[7](P125)
智者(统治者)的危险不在于一般的政治关系,而在于使人们进入非此不可的政治关系 的求权力的意志。何以如此?查氏自称他紧随生物之后,走了一条最伟大也最渺小的道 路,看到了生物的本质或生命的秘密。那就是一切生物既是服从者又是命令者,他不服 从他者的命令就要服从自己的命令,他不向别人施令就要向自己施令。是什么东西劝说 生物听从、命令,甚至在命令时也听从,在听从时也命令呢?回答:“权力意志。”换 句话说,追求权力是一切生物不得不服从的绝对命令,所有的生物都追求对他者和对自 己发号施令,即支配、控制和统治他者与自己。“我在哪里发现生物,就在哪里发现权 力意志,甚至在奴仆的意志里也发现了要做主子的意志。”[7](P126)“权力意志”即 “做主子的意志”。
如此这般的求权力的意志注定了生存关系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即命令与服从、支配 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人与物之 间,甚至发生在人与自我之间。生存关系的政治性无所不在,现实政治只是它的表现形 式之一,因此,泛政治性是尼采权力意志论的根本特点。
具有政治性的权力意志是一种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的意志,尼采曾多次强调“权力意 志”之“意志”不是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即一种受到外在刺激而作出被动反应的 心理机制,也不是叔本华所谓的“求生存的意志”,“因为:不存在者也不可能有什么 意愿;而已存在者还追求什么存在呢!”[7](P127)求权力的意志(Wille zur Macht)是 一种无须刺激而自发创造的意志(德语名词“Macht”——“权力”与动词“Machen”— —“做”有关,故“权力意志”也是“创造意志”),同时它又是生命之自我毁灭的意 志。
创新必毁旧,创造必冒险。自我创造的权力意志是一种绝对的生命意志,是不容抗拒 的生命意志,即使生命本身也抗拒不了这种内在于生命的意志。一旦生命(无论他者的 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阻碍了求权力的意志,权力意志也会毫不怜惜地从自己的生命上 面踏过去。“我宁愿屈从也不愿否认这唯一的事情;真的,哪里有屈从,哪里有树叶飘 落,瞧,哪里就有生命自身的牺牲——为了权力!”[8](P126)
既然这样,为了生命的安全是否可以放弃追求权力的意志?尼采说不行。生命就是追求 权力的意志,放弃追求权力的意志就是放弃生命。因此“‘生命’的定义应该这样来下 ,即它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斗争着的力增长不匀。无 论是处于服从地位的反抗力有多大,它绝不放弃固有的权力。在命令中也同样存在着承 认对手的绝对力未被战胜、未被同化、未被消解的问题”。[7](P158)因此,“生命就 是权力意志。”[3](P128)
作为权力意志的生命之“力”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它有强弱之分,但无论是强者还是 弱者都想支配他者,因此而有彼此间的斗争,因此而有了生生灭灭的生命运动。就此而 言,生命中没有任何实体性的支配者,只有变化万端的求权力的力与力之间的差异运动 ,或者说,权力意志的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就表现为这种强弱力量的差异运动,这一运 动就是“一切事物的永恒回复”。[8](P8-11)“一切事物的永恒回复”指的就是力与力 之间的差异运动,即作为权力意志之生命的自我运动,这种运动就存在的世界。
尼采以差异创世说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创世说吗?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差异的确是造 物主,说不是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造物主。形而上学的造物主(柏拉图的“理 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基督教的“上帝”等等)既先于一切个别存在者而存在( 它是创造、派生一切个别存在者的终极因),又在一切个别的存在者中存在(它在一切个 别存在者中并支配着它们的存在),并在一切个别存在者消失之后存在(它是永恒的)。 这个造物主就像德里达说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怪物,一个逻各斯中心,这个中心既在结构 之中,又在结构之外,它支配着结构,却不被结构所约束。德里达认为这样的“中心” 是形而上学的虚构,它根本就子虚乌有。差异不像这个形而上学的造物主,存在于生命 世界之外,差异就是生命世界,差异运动的创造与毁灭就是生命本身的创造与毁灭,差 异与生命同生死。
生命之外没有给予生命者,世界之外没有创世者,这就是尼采的“一切事物的永恒回 复”。生命(世界)的生成与毁灭是生命(世界)自身的事情,与任何生命(世界)之外的东 西无关,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生命之外的东西。对此,洛维特解说道:“世界既不可能作 为上帝的造物而存在,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而存在;世界只能作为一切循环中的循环而 存在,并如其所是地存在。”[9](P90)尼采对他的这一想法十分得意,他说:“给生成 打上存在性的烙印——这是最高的权力意志。……认为一切都是回复的,这使一个生成 的世界极其接近于存在的世界——观察认识的顶峰。”[3](P674-675)
作为生命自身差异运动的“一切事物的永恒回复”是不可思议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可 思议呢?也许正是这种不可思议透露了尼采思想的非形而上学性。根据这一解释,一切 生命(世界)都是生命的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没有它之外的另一造物主,也就没有原初 的开端和目标性的终结,生命(世界)总已在着。生命(世界)的恒在(没有开端和结束)不 可思议,但它恒在着,这是唯一的真实。生命(世界)的恒在又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永 恒”,即非时间性的不变,这个生命(世界)恰恰是时间性的,它变换万端。生生灭灭的 生命(世界)时间也不是变相的形而上学的时间,即有开端(起源)和终结(目的)的时间, 一种有神意安排的时间,而是无始无终的盲目的时间(尼采反对任何形式的预定论和终 极因果论)。“原来的生命是无目的、无意义的,但却是无可避免地回复着,没有终结 ,直至虚无,即‘永恒的回复’”。[3](P622)“变易乃是幻想、意愿、自我否定、自 我克服:没有主体,而是行为、设定、创造性的、没有‘因果’。……代替了‘因果’ 的是变易之物的相互斗争,时常伴随着咀嚼对象的轧轧之声;变易没有恒定的常数。” [7](P622)这盲目而恒在的生命世界犹如潮起潮落,永不停息的力的海洋,那波涛就是 作为权力意志的生命本身。
这样,我们从“生命即唯一的存在”开始,经由尼采有关“肉体”、“权力意志”、 “力的差异”、“一切事物的永恒回复”的论述,又回到了开始的命题:“生命即唯一 的存在”,这就是尼采的生命论与存在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生命论与存在论。
三、海德格尔的洞见与盲视
有了以上概说,再来看海德格尔有关尼采思想的论断就能见出其洞见与盲视了。海德 格尔认为尼采思想归属于存在论,因而行进在伟大思想的轨道上,这一判断原则上不错 ,因为尼采的生命论就是存在论,但海德格尔断言尼采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思考存在问题 则有误。
海德格尔断言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其主要理由是:尼采虽然颠倒了柏拉图主 义的二元等级结构却没有放弃这一结构,因此是一个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者。在海德格尔 看来,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的根本特征是预设了“超感性领域”和“感性领域”二元 对立的存在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居于高位”的超感性领域是赋予尺度的东西,是用来 度量和解释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终极存在者,因而是“真实世界”;相反感性领域作为 “虚假世界”而“居于低位”。所谓“倒转的柏拉图主义”就是倒转了超感性领域和感 性领域的位置,让前者居于低位而让后者居于高位。海德格尔说:“所谓感性领域位居 高位,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感性领域是真实的东西,是真正的存在者。如果我 们仅仅以这种方式来看倒转,那就可以说,高层和低层的空位还是保留着的,仅仅作了 不同的分配而已。而只要这种高层与低层决定了柏拉图主义的结构形态,则柏拉图主义 在其本质上就依然持存着。这种倒转并没有完成它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须完成的东西, 亦即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克服。只有当高层本身根本上被清除掉,先前对一个真实的 和值得追求的东西的设定已经终止,理想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已经被取消掉,这时候,对 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克服才能取得成功。”[5](P222)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只是倒转了其“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 之高低真假的位置分配,而没有从这种倒转中走出,即彻底放弃这种二元模式。“当尼 采认识到对柏拉图主义的倒转就是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的过程时,他已经精神错乱 了。”[5](P223)因此,海德格尔断言尼采并不是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的克服者,而 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即他以倒转的方式完成了形而上学内部的另一种可能。
海德格尔的上述论断影响深远,但却是一种误断。事实上,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以来,尼采便摆脱了柏拉图主义。这其后的著述长达数年,并是他的丰产期,因此, 说他刚刚要从柏拉图主义中转变出来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实在有些冤枉。
尼采在批判哲学、宗教和道德时的确高度肯定了感性存在,但是尼采并没有将他所肯 定的感性存在(肉体、欲望、激情、生理等等)看作取代理性存在(精神、灵魂、理式、 上帝等等)的终极本体或终极存在而放在“高位”。尼采曾明确断言:“双料的伪造, 从感性出发和从精神出发,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一个存在物的世界,即僵化的和等值的世 界。”[3](P675)在尼采看来,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感性的名义构造一个僵化等值 的存在物世界,都是“伪造”,因为这样的世界是超越此世的彼世,而任何彼世都不存 在。
尼采曾这样谈到形而上学对二元世界的虚构:“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这个世界 是表面的。因此,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有条件的。因此,一定有一 个绝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矛盾重重的。因此,一定有一个无矛盾的世界;——这 个世界是变易的。因此,一定有一个存在的世界。——这都是十分错误的推论(对理性 的盲目信仰:假如A存在,那么它的对立概念B也应存在)。这种结论是痛苦激发的结果 。根本说来,这些推论都是愿望,它们想要这样的世界;同样,对一个制造痛苦的世界 的仇恨也表现在对另一世界的幻想上,一个更可贵的世界。这里形而上学家对现实的怨 恨真是创造性的!”[3](P659)
形而上学对现实的怨恨创造了两个世界的幻象,因而它注定要幻灭。在《偶像的黄昏 》中,尼采概说了形而上学之两个世界幻灭的历史。尼采将这一历史分为六个阶段:“ 一、真实的世界是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可以达到的,——他生活在其中,他就是它。 (理念的最古老形式,比较明白、易懂、有说服力。换一种说法:‘我,柏拉图,就是 真理。’)二、真实的世界是现在不可达到的,但许诺给智者、虔信者、有德者(‘给悔 过的罪人’)(理念的进步:它更精巧、更难懂、更不可捉摸,——它变成女人,它变成 基督教式的……)三、真实的世界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被看作一个安慰 、一个义务、一个命令。(本质上仍是旧太阳,但被雾霭和怀疑论所笼罩着:理念变得 崇高、苍白、北方味儿、哥尼斯堡味儿。)四、真正瞬时速度世界——不可达到吗?反正 未达到。为达到也就未知道。所以也就不能安慰、拯救、赋予义务:未知的东西怎么能 让我们承担义务呢?……(拂晓。理性的第一个呵欠。实证主义的鸡鸣。)五、‘真实的 世界’是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理念,也不再使人承担义务,——是一个已经变得无用 、多余的理念,所以是一个已经被驳倒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天明;早餐;健康的感 觉和愉快心境的恢复;柏拉图羞愧脸红;一切自由的灵魂起哄。)六、我们业已废除了 真实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假象的世界?但不!随同真实的世界一起,我们 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久远的错误的终结;人类的顶峰;《 查拉图斯特拉》的开头词。)”[10](P26-27)
当“真实世界”和“假象世界”这种形而上学的幻象都被废除之后,我们便面对着一 个唯一的世界,一个没有超越者的世界,一个在正午的太阳照耀下明明白白的世界,一 个没有神秘的超越“深度”和“灵魂”的肉体生命的世界。
由此可见,尼采并不是简单地颠倒而是根本地否定了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颠倒只是策 略,彻底否定才是目的,通过颠倒和否定,尼采得以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框架之外谈论 存在—生命。看来,海德格尔误解尼采的关键在于:他没有充分注意到“上帝死了”这 一事件对尼采思想的决定性作用,即尼采拒绝任何形式的“上帝”的复活,而坚持在没 有上帝的处境中思考,在形而上学的轨道之外思考。因此,海德格尔在拯救尼采的过程 中又毁了尼采(不仅仅是失去了尼采)。不过,以上论述也让我们看到了尼采思想的内在 一致性,它并不像德里达说的那样在“尼采们的宴会”上我们只看到思想的碎片。
收稿日期:2003-12-02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尼采论文; 德里达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存在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权力意志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