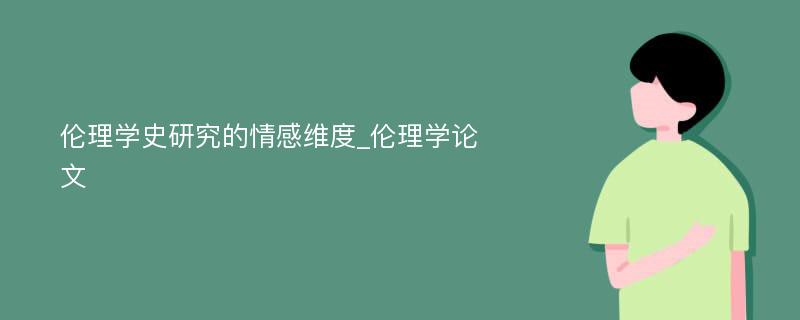
伦理学史研究的情感之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5-0010-05
在当代,国内学术界对伦理学史的研究可谓贡献多多,如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陈少峰著《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多卷本),陈瑛著《中国伦理思想史》,沈善洪、王风贤著《中国伦理思想史》,朱贻庭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章海山著《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宋希仁著《西方伦理思想史》,万俊人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周辅成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等。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伦理学史从情感维度做出的研究却少之又少。
然而,情感维度是研究伦理学史不可缺失的重要维度,这是因为伦理学与心理学之间有着深刻和必然的联系。“如果说道德的根本在于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根本上不是对必然的认识,而只是一种自由感,那么,伦理学就不能脱离与心理学的干系。如果伦理学还讲道德良心、道德同情、道德意识、道德情感的话,那么,伦理学也就完全不能没有心理学的基础”[1]。正是从伦理学与心理学之间特有的关联出发,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伦理学史研究中情感缺失问题,并对伦理学研究中的情感回归做出尝试性的探索。
一、伦理学史研究缺乏情感维度之表征
在学术界,伦理学史研究情感维度的缺乏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没有对伦理学史上关注了道德情感问题的伦理学家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一点在西方伦理学史研究中尤其突出。比如在西方伦理学中,情感往往被当作是与理性相对立的概念而只能在道德论证中扮演附属的角色。因而在西方伦理学史研究中,少数对于情感问题给予了特别注意的伦理学家也在这种偏见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比如,在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中,夏夫兹博里(Shaftesbury)和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等人确立了“一种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道德观”[2]299。然而,由于国内习惯将他们学说中最关键的概念“moral sense”翻译为“道德感”,而不是“道德感官”,这种译名用汉语语境中的某种道德情感或道德直觉代替了西方道德情感学说的中的人性论与先验心理学基础。“sense”在英文中的多义现象以及这种偏离原文旨意的译名或多或少地帮助读者误读了道德情感学说,从而导致西方伦理学研究者大多认为夏夫兹博里、哈奇森等人的伦理学只是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而建立在经验心理学基础上,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对他们在近代道德哲学中的作用视而不见,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学说恰好坚决地反对了霍布斯等人创立的以“自爱”为核心的经验主义伦理学,也没有注意到哈奇森所创作的“曾在整个18世纪的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得到广泛翻译,并产生很大影响……的道德哲学著作”[3]9所应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相反,要么有研究者误解了他们而认为他们“把感情的地位与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4]179,要么有研究者忽略了他们而认为:“近代哲学在认识人的道德本性方面分为两个流派:一派(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的出发点是:人的本性从来就是坏的、恶的;另一派(莫尔、卢梭)则认为人的本性从来就是善的。”[5]297显然,在这种把握中根本就没有夏夫兹博里、哈奇森等人的位置。在为数不少的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专著中对夏夫兹博里、哈奇森只字不提的却是大多数。似乎夏夫兹博里、哈奇森根本就是与西方伦理学没有关联、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人物。麦金泰尔在他的《伦理学简史》提到了哈奇森,但认为哈奇森“的观点仅仅建立在无根据的断言上”[6]221。国内竟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夏夫兹博里、哈奇森的伦理学著作的译本。
休谟在近代建立了情感主义的伦理学。他说:“只要说明快乐或不快乐的理由,我们就充分地说明了恶和德。”[7]511休谟把道德建立在快乐和痛苦的情感上,把德性归结为一种主观性的情感。他说:“道德这一概念蕴涵着某种为人类所共通的情感。”[8]124但只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休谟关于“道德的区分不是来自于理性”[9]245和“道德感是道德的根源和道德评价的标准”[9]253的观点。其实,正是觉察到情感在道德中的极端重要性,休谟在伦理学史上才首次做出了“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的分离,这是休谟对伦理学史的最特殊贡献。伦理学史研究由于缺乏情感之维的考察,有人反而认为休谟伦理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仅是“对幸福问题的看法”[10]427以及“包含若干辩证法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10]429,这种评价是不得要领的。在相同思路的范导下,学界对于亚当·斯密的研究重点则主要集中于《国富论》和经济自由思想,对其经济思想的伦理基础即道德情感学说,以及《道德情操论》却研究不够。人们几乎从不愿意承认亚当·斯密是一位成绩卓著的伦理学家,实际上,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出现于20世纪的元伦理学认为伦理学应该把善是什么当作伦理学应该解决的初始问题即元问题。元伦理学的创始人摩尔认为,善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定义的东西,因而我们只能依靠直觉来对其进行判断。因此,善的问题是一个自明的问题,它能最为有效地带来个人感情上的快乐和由美好事物而产生的喜悦行为。元伦理学之情感主义代表罗素认为,伦理命题属于价值而非事实领域,因而只能表达情感却不表达任何知识,所以没有任何意义。斯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深入研究人们在现实生活情境中进行的道德争论的性质、意义和功能,从而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被批评家称为是继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之后,元伦理学中最富于创造性的著作,是对伦理学的情感理论的最彻底最精确的系统阐述和研究。斯蒂文森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制定或论证道德规范,而是分析伦理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具体来说就是从情感意义上分析道德语言,指出道德判断之所以与科学判断不同就在于它具有科学判断所不具有的情感意义。然而,国内伦理学界对这种从情感维度切入道德问题的伦理学至今感到特别陌生。元伦理学当然也不能在伦理学史研究中扮演主流伦理学的角色。
其二,没有对伦理学史上忽视了道德情感问题的伦理学家给予足够的批判。
这一点在中国伦理学史研究中尤其突出。比如中国伦理学史提倡的是一种典型的理性道德。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一种强制规定和外在规范,是他律的而不是自律的。中国传统道德条目大多是僵死而冰冷的理性法则,是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对抗的道德玄谈,是哲学上的一种抽象而体面的思辨表达。
梁漱溟指出:“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11]98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作是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11]118这种理性化了的道德与人的情感具有严重对抗性。
事实上,情感本来就是中国历史极力回避和鄙视的字眼。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那种对于爱情的自由的、饱满的、酣畅的描写。《三国演义》里的人物不谈爱情。《西游记》里的爱情是妖精和猪八戒的专利。《水浒传》里的爱情与淫妇是同义词,而其中的英雄豪杰(如武松、杨雄、宋江)大多有手刃淫妇的“先进事迹”。《红楼梦》里林黛玉和贾宝玉带着青春的萌动,共鸣于爱情的诗文,但又害怕爱情的语言。所以,中国的古典文艺作品反倒更像是道德教科书。即使偶尔谈及情感,也要将它定位于理性名下。因此,中国艺术素来强调抒情,但总是止于“思无邪”的道德规范。
儒家对待情感的态度,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理性原则,对不符合理性的情感,向来不予以肯定。由于疏远了情感之维,历史上中国伦理学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真正的道德家园,相反却导致了道德乌托邦的营造,而在这个道德的乌托邦里人们往往在道德的幌子下干不道德的勾当。对此,很少有人从情感维度做出批判性分析。相反,当前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者们更愿意陶醉于道德乌托邦的营造之中。如果说伦理学史研究还有一点批判色彩的话,批判者至多也只是将伦理学史置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审视和批判之下,去发现伦理学史上伦理学家的唯物主义特征和唯心主义特征,去深化对历史上某一派伦理思想的理解,尤其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解。有学者就指出,学习中国伦理学史是为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解”[12]397,而学习西方伦理学史是为了“丰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2]获。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对伦理学史上忽视了情感问题的伦理学家给予足够的批判与反思。
二、伦理学史研究缺乏情感维度之原因
当今伦理学史的研究以及教材编订都缺乏情感维度,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主要缘于人们对道德与情感的双重误解,似乎道德一定是远离情感的,情感也一定是远离道德的,道德与情感处于严重的分离之中。伦理学史上对道德的误解主要体现在把道德等同于理性和知识,这一点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尤其突出;而对情感的误解主要体现在把情感等同于自然血缘之情,这一点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尤其突出。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把道德等同于理性知识的做法源远流长。在古希腊人看来,善之所以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就是真或者说真的知识。道德依赖于理性知识,没有理性知识就没有德性,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人只有具备了有关道德的知识才能做善事,而且人具备了有关道德的知识就必然做善事。所以苏格拉底强调,伦理学必须寻求关于善的永恒的、普遍的概念和定义。而“美德即知识”就是他关于美德(善)的一般知识。它表明理性知识是美德的“充分”“必要”条件。“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经过亚里士多德之形而上学的提升,成为西方伦理学普遍认同的命题。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说:“把美德视为知识的见解是一种本质上的希腊的思维方式。”[13]45只要理性被夸大,情感就没有生长的空间。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差不多完全没有可以称之为仁爱或慈爱的东西。人类的苦难——就他所察觉到的而论——并没有能在感情上打动他;他在理智上把这些认为是罪恶,但是并没有证据说这些曾使得他不幸福,除非受难者恰好是他的朋友。更一般地来说,《伦理学》一书中有着一种感情的贫乏”[14]238。
近代伦理学是在自然科学方法的荫庇下成长起来的,具有明显的科学化、认识论倾向。近代伦理学认为美德可以借助某种逻辑的工具而得以获得,善恶可以借助理性的手段而得以认识。洛克就说:“道德学和数学是一样可以解证的。因为伦理学所常用的各种观念,既是实在的本质,而且它们相互之间又有可发现出的联系和契合,因此,我们只要能发现其相互的常性和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到确实的、真正的、概括的真理。我相信,我们如果能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则大部分道德学一定会成了很明白的,而且任何有思想的人亦不会再怀疑它,正如他不会怀疑给他解证出的数学中的命题的真理似的。”[15]640
在现代,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无批判地使用各种自然科学材料和自然科学方法,甚至寄希望于借助自然科学如遗传工程、行为技术学的成就来解决道德难题,达到道德的完善和伦理学的成熟。实用主义伦理学从生物进化论和彻底经验论出发,认为一切自然科学都可以成为道德研究和伦理科学的用具。当伦理学把道德贴上理性知识的标签时,就必然会用普遍的知识来否定特殊的情感,走向情感与理性的二分。事实上,情感问题在西方理性哲学中是不入流的,被遗忘在阴冷的角落。张世英指出:“西方传统道德观,受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主要地是一种轻视感情欲望的道德观。”[16]343人的情感生命受到理性的排斥,道德之学最终会成为远离情感“知识之学”。用有序的理性来排斥无序的情感,甚至最终会导致道德的不可能。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如果这些知识不在人的感性体验、偏爱、和需要的烈火中溶化,任何的道德规范、义务、禁令等的知识都不能保证个人道德上的可靠性”,“没有道德感,真正的人道和集体主义不可能得到发展”[17]16。
对情感的误解体现在,人们用狭隘而有限的自然血缘亲情来代替道德情感,并认为自然血缘亲情就是道德的出发点。这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伦理学中。以自然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仁”是儒家伦理思想建立的基础。“仁”是从自然的“亲亲之爱”辐射出去的一种伦常之情。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纵的方面表现为父子关系(孝),在横的方面表现为兄弟关系(悌)。然而,“为仁之方”在于推己及人。因此《孟子》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而“仁民”,由“孝悌”而“泛爱众”,中国历史因此而建立起一种以血缘亲情为根基的差序结构,这是一种“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8]28。显然,这种具有相对色彩、经验成分的自然血缘亲情明显地与道德的普遍原则相背离。为了使其具有一种先验的普遍心理结构,自孔子开始,中国人就试图给这种最自然的“亲情”做出礼仪性的规定。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正因为中国自然人伦之情与礼制、礼法直接相联,因此,随着礼制礼法的日益僵化,自然人伦之情很快失去了直接的感受性,走向了图式化即非情感化。“情感”一旦成为一种礼仪规范、一项义务,它就不再是情感,而只剩下一副假面具,成为图解道德观念的脸谱。中国传统道德温情脉脉的面纱恰好遮蔽了个体最深层、最自由的情感。僵化的礼法与礼制使得传统道德归根结底是一种理性的设计而不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所以,中国伦理学史最后竟是排斥情感而独讲礼法,并且是越讲礼法就越排斥情感。所以,与西方伦理学史以理性压制情感不同,中国伦理学史以礼法压制情感。
三、伦理学史研究情感维度之归正
一方面是对道德的理性化解读导致了伦理学史研究中情感维度的缺失,另一方面没有情感维度的伦理学史研究又直接支持了道德的理性化解读。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情感生命越来越泯灭。“如果一门伦理学拒绝与生命接触,不屑于去触动心灵中的那根游丝;如果一门伦理学不注重对良知的唤醒,不张扬人的反省精神,那么这门伦理学不是在开启道德之途,而是在堵塞道德之源”[19]293。为了唤醒人的道德情感,伦理学史研究必须归正情感维度。归正情感维度有两点特别重要:
第一,确立道德的非科学性。
西方伦理学几乎把伦理精神与理性精神相等同,科学知识在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其基本倾向是寻求道德的科学性。然而,伦理学与科学不同,伦理学中的道德公理既不能经验证明也不能逻辑证明。科学涉及“是”的问题,而伦理学涉及“应该”的问题。所以道德的真正领域是意志的领域也仅仅是意志的领域。而意志产生于情感而不是逻辑。只要伦理学涉及“应该”的问题,那么伦理学史研究就必须认同情感维度。而认同情感维度的伦理学史研究就必须坚决超越伦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立场。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科学主义立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但由于伦理学直接面对的是道德,而道德行为的发生与人的内在情感紧密相连,“道德不是口头语言和规则、不是威逼和教训,道德是心灵的感发,是生命的行动……道德只存在于道德主体的心里”[19]211。因此,科学主义立场因其特有的客观性在伦理学研究中恰好是需要被超越的。
第二,确立情感的非自然性。
中国传统伦理学所理解的情感是自然天定的亲情。如果把情感界定为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上的交往和心理上的共鸣,我们就会发现最讲亲情的中国人缺少的是真正的情感。这不是指中国人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络,而是指情感联络超不出亲情的范围。
有学者认为:“在儒家看来,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是情感的动物,就其最本始的意义而言,人首先是情感的动物,特别是道德情感,是人类道德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价值的重要标志。道德情感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爱亲敬兄之情是从发生学上所说的道德情感的最初表现,也是道德行为的基础,有其先天的根据,即自然界的生命创造。情感是与生俱来的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命意识,在后天的生活境遇中‘随感而应’,表现出种种情态,如同见‘孺子入井’,人人皆有恻隐之心一样,有其普遍必然性。”[20]这里,该学者显然没有注意到自然亲情与道德情感的不同。自然亲情立足于血缘,是浅层次的、相对的;道德情感立足于自由,是深层次的、普遍的。并且道德的普遍视野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消解掉亲情的相对立场。这就是哈奇森所说的:“最令人厌恶的激情和情绪——固执、愤怒和害人的欲望——是有限而‘褊狭观点’的后果,它们来自对私人利益的强调以及对公共善的误解。因此,它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不怎么出现,并会消失在道德体系的普遍视野中。”[3]16局限于自然亲情,很容易把人降格为自然物,把人的道德理解为自然本能,而道德情感恰好可以把人从自然物提升出来,因为道德情感凸现的是人的感性生命和自由创造。
自由的情感既实现了人生的崇高又高扬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如果说有无自由情感是人与非人的界线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有无自由情感是真道德与假道德的界线。实现从非人向人的跨越,从非道德向道德的跨越,都要求我们对情感实现从自然性向自由性的跨越。在这里,如果说超越科学理性是归正情感维度的第一步,那么超越自然情感是归正情感维度的第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