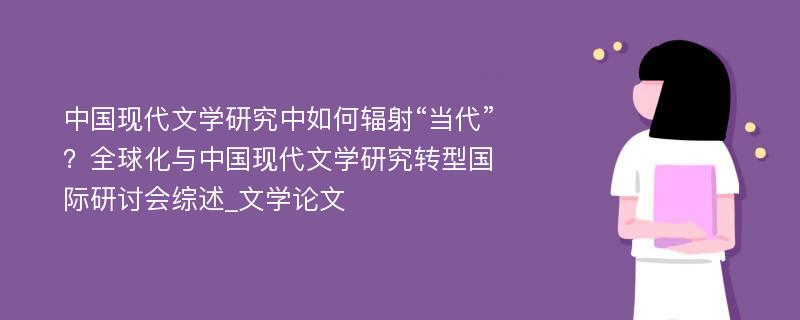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焕发“当代性”?——“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1月18日至20日,“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 海大学举行,主办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在研讨会期间,来自国内外的 百余名专家学者纷纷就相关议题发表见解,并展开热烈讨论。其中,钱谷融(华东师范 大学)、李欧梵(美国哈佛大学)、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王 晓明、袁进(上海大学)、尾崎文昭(日本东京大学)、张新颖、倪伟(复旦大学)、夏中义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陈美兰(武汉大学)、蔡翔(《上海文学》)、薛毅(上海师范大 学)、吴晓东(北京大学)、包亚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卫威(河南大学)等 二、三十位学者先后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陈思和(复旦大学)、胡志德(T·Huters,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此外,钱理群(北京大学)所作的“特 邀评论”,以其深刻的反思与饱满的激情,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共鸣。
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困境出发,王晓明在发言中率先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 的‘当代性’问题”,意在重新恢复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的互动关系,以应答社会 和文化现实,特别是融于其间的重大精神问题。他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包括过 去通常称之为“近代”的文学,更包括当下的文学,故其研究范围的时间下限不断延伸 ;它的研究对象也不限于文学文本,而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和社会文本。在此定义 之下,现代文学研究显示出与研究者所处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或精神现实的直接联系 ,这就使它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性”。其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接受国家意识形态 的渗透和控制;二是对研究者所处的当下重大的社会、精神和文化问题的敏感,对尚未 被主流接纳的思想萌芽的呼应,以及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至少到80年 代中期为止,许多学者相信正是这后一种“当代性”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使之 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科之一。但进入90年代后,当学界开始检讨80年代的“激 进主义”、呼吁建立学术规范时,现代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地提出要安守本位,不应过执 “当代性”而背离“学术性”。受这一主流倾向的影响,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 一大批在搜罗细节、体现学术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 却日渐淡薄。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研究愈益疏远这后一种“当代性”、愈益“专业化”、 “学科化”的现象?是在目前社会普遍“失范”的情况下鼓励这一趋势,或者听其自然? 还是将上述现象视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萎顿现象,且和目前更大范围的精神迷惘和逃 避相联系,故而觉得有必要展开深入的讨论和反省,以促成整个学科的“转变”?
基于上述思考,他进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努力直面现实、但又绝不重蹈过去 那种将文学研究仅仅当作社会批判工具的覆辙,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发展对当代重大问题 的敏感和回应?如何理解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与所谓“思想锋芒”、“艺术敏 感”的关系?在充分意识到“现代中国”及其文化所内含的外来或“世界”因素,意识 到当代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各个方面的愈益紧密的互动关系,现代文学研究者该如何 努力拓展真正的全球视野?与此同时,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处理文学中所凝聚、所体现的 “本土”经验?如何通过对此种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的思想 资源?如何把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关系?……上述问题,引发 了与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向上进行的回应、争议和探讨。
一、如何看待“学术规范”与“思想锋芒”、“艺术敏感”的关系?
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化趋势,以及有人判定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论 断,夏中义从学术积累和传承的角度出发,强调建立学术规范原是为了精神和思想价值 的强化、而非淡出,且不应将“思想”狭义地理解为仅仅是对社会现实和公共问题的 应答。因而就广义的思想发展而言,他认为目前所谓的专业化趋势看似有所“失落”, 实则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进展”。陈思和更呼吁要回归专业研究领域,强 化“岗位意识”,并在具体研究中带入对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他看来,80年代的那批 优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正是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却又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回应了许多 重大问题,从而复兴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更何况,时代和现实问题往往充满困惑、解 释不清,难以当下把握它,然而却可以经由审美的、精神的层面而得以充分展现(他举 王安忆为例),越是复杂的问题越需要做具体的专业研究。所以,他热切地希望大家都 能回到文学中去、回到自己真正喜欢的感性中去。钱理群则对当下学术的生存环境和学 院派研究的利弊作了清理。在学术界所面临的体制化和商业化这两大危机面前,他既赞 成提倡学术规范,因为真正的学院派研究有利于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同时他 又警示出其陷阱所在,即或者是沦为智力游戏、惯于对材料作技术性操作而丧失学术生 命力,或者形成限制和压抑性机制而导致学术霸权的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他表示,自 己的学术研究要尽力跟当代生活保持息息相关的联系:一是要高度重视中国本土文化及 其实践经验,二是尽力做到使问题意识产生于当代,但研究与思考本身要有距离,富于 超越性,让现实关怀与超越关怀结合起来。对此,吴晓东也提醒大家:在提倡关注“当 代性”的同时,也要避免因当下立场的过于明显,而可能丧失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感。
二、如何分析和理解“全球化”趋势,进而拓展真正的“全球视野”?
关于“全球化”自身所蕴含的某种悖论,不少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有所意识。一方面 ,各地域特有的文化符码正逐渐被某种“标准文化”所整合,致使各民族、各区域的文 化认同普遍陷入困境;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所施加的种种影响和压力,也在不断地提醒 并强化着人们对自身所处的民族、地域、宗教、性别、阶级、语言等问题的深度理解, 从而有可能以更复杂的眼光、更理智的态度面对这一切。
李欧梵对全球化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及文化的多样性等前景表示怀疑,他指出,在无 法阻挡的全球化趋势中,所谓“多元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取代现象已经无所不在 ,这往往也得到了民族国家力量的支持,并在进入“一体化”的同时表现出微妙的地域 性差异。包亚明进一步阐明,某些地域性现象不仅可以与全球化链条相关联,而且成为 全球化渗透到地区性日常生活所必须化身的手段。我们当然不应忽视全球性(Globaliza tion)与地域性(Localization)在当代中国的某种内在紧张,即地域性知识往往通过强 调日常生活的权利来对抗资本与民族国家等等的抽象要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须认识 到这两者之间有冲突也有互补,特别是与国家资本之间交织着彼此制造、抵抗的关系, 因此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作二元论的理解。
王晓明认为,所谓全球化,抽象说来是指原本互相隔绝的地区逐渐联为一体的进程, 而从具体来看就是指各地区如何联结起来的方式问题。因此,他提出:既然人类不可避 免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联结为一个整体,那么能否在目前情况下,共同来争取一个不同 于西方主导模式的、相对较为合理而公正的联结方式?
三、如何发掘和处理“本土经验”,藉此提供多样的思想资源?
至于如何寻找和整理本土经验、并以此作为当下的思想资源,不少学者提请人们要更 多地关注和研究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 问题。蔡翔指出,中国在1949年后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脱离现代化想象,譬如说到,革 命、诗意与日常生活的对立,革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整个社 会的动员组织方式(如城市街道、工厂的结构),等等。此间,文学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宣 传和推动作用。然而,究竟何谓社会主义运动?其整体的文化想象方式是什么?有无值得 借鉴的经验?……这一切都还有待于更为深入而充分的探讨。倘能全面考察社会主 义运动的文化想象方式,就有可能提取出某些经验,成为我们新的想象资源。
钱理群也强调: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化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又拥有多种不同 的实践模式。如果寻找本土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最主要、也最特别的中 国经验。他相信,在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研究中,若能吸收文化研究的方法, 通过具体而细致的文学研究阐发出本土和当下经验,必将为世界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反思 和当下实践作出特殊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要处理好“当下性”和“历史性 ”之间的关系,既有同情的理解,又须正视其后果。而对于国内目前存在从西方进口理 论、据此对本土材料作加工、最后再出口到西方世界的这一再现于学术领域的国际分工 现象,他深感忧虑和不满。与此相关,薛毅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对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专 制主义的批判,应该纳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知识分子应该反思在西方和民众之间 的“主体性”位置,改变自己的臣服于西方而指责民众的所谓启蒙主义角色;应重新思 考个人、集体、民族、阶级和世界、和人类的关系,而不是排斥民族和阶级,不是简单 地建立一个超社会、超地区的个人和世界、人类的关系;重新定义“文学”现代性,重 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以西方为标准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现代文学进程,而是从中国 现代文学内部寻找标准和方法。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活力不在于向西方臣服 ,而在于一个由抵抗和学习所组成的悖论性空间之中,这里有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经验 ,而这也是无法被全球化所整合的本土经验。
另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分期的上下限拓宽、延伸之后,原有学科框架中的某 些重要缺失,如忽略了对近代以来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的研究等问题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袁进为此提出,要加强对旧体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旧体诗词、散曲,文言散文、小 说和章回小说,创作或改编的传奇、杂剧、京剧及其它地方戏曲的剧本,以及对上述各 种旧体文学的批评等),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增长点,以此探究中国文学 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本土)特征。在他看来,中国旧体文学的存在和衰亡,恰恰是中 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民族特色。针对着历 来的正统文学史观对于通俗文学所表现出的排斥和贬抑倾向,尾崎文昭从雅、俗角度出 发,重新打通并阐释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结构。他认为80年代末以来对精英立场 的放弃,才导致了中西通俗文化观念的合流。
四、如何理解和把握“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
为使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重现生气和活力,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当引进 新思路,扩大学科领域,调整研究视野,而“文化研究”在此给人以很多启发。
罗岗首先廓清了目前对文化研究的种种误解,指出将文化研究当作与国际接轨的学术 新潮,甚至视之为用学术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藉口,这恰恰有悖于文化研究的精神。追 溯文学研究的源头,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还是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尽管 思路和言路迥异,但其研究的出发点都不在于纯粹学术和知识的趣味,而更多的是对所 处时代的重大问题的敏感与回应,并且这种精神在文化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 。因此,与其将文化研究当作一套固定的理论家法和知识谱系,不如视之为某种批判的 实践精神、开阔的理论视野、灵活的分析方法和权宜的介入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 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介入,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
倪伟进一步分析了“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的其它优势,诸如和当下社会实践 紧密结合,能够精细地剖析社会生活的肌理,等等。他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应当确立这样 一个目标,即研究意义是如何在文学这个场域中生产出来的,这个动态的意义生产过程 当然会牵涉进许多文学之外的因素,文学生产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实践之间由许多中介环 节衔接而成的复杂的互动过程正应是现代文学研究着意的对象。他建议,现代文学研究 至少可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开拓。一是文本政治分析:文学写作是一个多种意义卷入、 斗争、协商、生成的过程,倘在更大的背景中拆解文本,使之语境化、历史化,包括从 中质询写作者的主体位置,也许就能发现制约文学写作的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因素。二是 对日常生活形式的关注:构成社会生活肌理的毕竟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是抽象 得多的观念形态,从有关的文本分析中,可以探讨日常生活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 的认知,又是怎样嵌入到他们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之中。三是对文学的流通和消费过程 的研究:文学的意义只有在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或是增值,而在这个意义增 值的生产过程中,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介入理应成为文学作品接受研究的主要目标。换 言之,这种研究指向的并非作品本身,而应该是各种力量彼此交织、冲突、协商的社会 历史场域。
上述观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而在所有这些学者的实践和表述中,依然隐含 着这个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极为难得的审慎与激情。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国际文化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