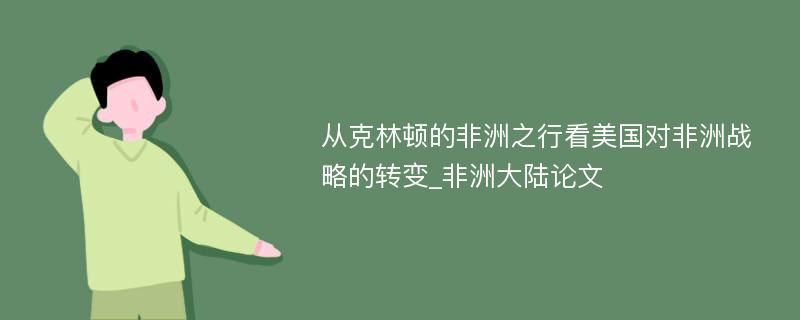
从克林顿访非看美国对非洲战略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非洲论文,美国论文,战略论文,访非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80年代后,非洲经济停滞不前,政局动荡不安,国际地位有所下降,非洲似乎成了“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但是,近几年非洲形势开始好转,一些“热点”问题逐渐降温;经济走出低谷,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大国纷纷关注非洲,调整对非政策。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更是不甘落后,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马,访问非洲。克林顿总统的非洲之行是美国对非重大的外交行动,反映了美国对非洲战略的变化。
一、克林顿的非洲之行
1998年3月22日至4月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对非洲的加纳、 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博茨瓦纳和塞内加尔6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访问。 克林顿对所访问的非洲国家显然经过了从地缘政治到实力版图的精心挑选。6国中既有位于大陆南端的非洲经济第一强国,又有居于西部、 中部和东部非洲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突出的国家;既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又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整个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起始于作为17至18世纪贩卖奴隶集散地的加纳的阿克拉王宫遗址,终止于将拍板成交的奴隶转运到美洲去的塞内加尔的戈雷岛。白宫到很晚才在克林顿非洲之行的日程表中加上卢旺达,以显示美国对1994年在那个国家发生种族灭绝行为的关注。不过,出于安全考虑,克林顿只在卢旺达的国际机场作短暂停留。
这次访问的高潮是克林顿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共同主持召开的由民主刚果、肯尼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四国总统及埃塞俄比亚总理参加的小型“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1998年3月25 日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召开的。会议发表了旨在推进非洲民主和贸易的“恩德培宣言”,双方表示,愿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非洲与美国的新型伙伴关系。
克林顿的此次非洲之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是美国在职总统对非洲大陆时间最长的一次访问。克林顿访非是继1978年卡特访问非洲之后美国在职总统首次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克林顿在非洲逗留了12天,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在非洲呆过这么长时间。1909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了写一部有关猛兽的书,在非洲呆了很长时间以获取灵感(注:法国《费加罗报》,1998年3月23日,转引自《世界知识》1998年第8期,第10页),不过,他当时已经卸任了。
第二,访问团人数众多。此次访非规模庞大,克林顿的随行人员多达800名。其中有总统的妻子女儿、他的两名黑人内阁部长、 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及其他美国黑人知名人士,还有大批企业家和记者。
第三,在访问途中,克林顿接连向非洲人民致歉,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1998年3月24日, 克林顿在乌干达的一所小学演讲时向非洲人民公开承认错误(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26日)。他说, 早在建国前,美国就从奴隶贸易中获利,“我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他还承认“美国对非洲不总是公平对待的”,因为在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争霸,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过一些非洲国家,导致大量武器运入非洲,引发了长期的武装冲突,有的至今还未得到解决。美国在历史上曾经支持过实行种族主义统治的南非白人政府。访非途中,克林顿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作了短暂停留,会见了6名1994 年“部族屠杀”的幸存者。克林顿再一次向非洲人民道歉,他说:“屠杀开始后,我们行动太慢”,国际社会对于未能制止那次大屠杀是有责任的。克林顿表示,此次来非洲就是为了“听取你们的意见,并向你们学习”;就是要用“新眼光”看待非洲,以建立“跨世纪的美非伙伴关系”。对照美国过去对非洲国家动辄进行粗暴干涉、强加于人的一些言论和做法,克林顿连连向非洲人民致歉,这其中意味深长。它反映出非洲在美国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以往对非政策的深刻反省。
二、美国对非洲战略的转变
尽管非洲舆论对克林顿此次访问提出许多批评,对美国的动机表示怀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克林顿此行是无足轻重的。从美国调整对非战略的角度看,克林顿的非洲之行是历史性的转折。
美国调整对非战略需要一个过程,它开始于90年代中期,到克林顿访非宣告完成。美国对非战略转变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疏远非洲到重视非洲。
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政策的核心是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渗透扩张,与苏联争霸。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加上海湾、波黑、中东等热点不断出现,使得美国在战略上无暇顾及非洲。美国随之对非洲有所忽视,援助逐年减少。尤其在1993年美国快速反应部队干涉索马里内战失败后,对非洲更趋冷落。但是,随着近年来非洲的形势出现好转,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政府的对非政策,呼吁克林顿政府重新认识非洲。
1996年2月和10 月美国商业部长布朗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先后访问非洲,明确提出了对非洲的关注。今年克林顿总统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非洲6国,其本身表明美国政府对非洲的关注和重视。 克林顿在访非途中公开承认,美国对非洲所犯的最大错误,也许是对非洲的忽视和无知。这表明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自己以往对非政策的失误,感到非洲的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所以对非洲逐渐重视起来。
2、从“以苏划线”到强调“民主”。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把非洲国家或政治力量是否“反苏”作为其支持与否的标准,因而长期同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利比里亚的多伊政权、安哥拉的安盟等保持密切关系。蒙博托在冷战时期实行亲西方的政策,因而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全力支持他,把他作为在非洲抵制苏联影响的重要人物。从1965年到1991年,蒙博托从美国得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超过15亿美元。扎伊尔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之一(注:《西亚非洲》,1997年第5期,第27页)。 美国历届政府多次帮助蒙博托摆脱内外困境,维持其独裁、腐败的统治。但是,冷战格局结束以后,美国在非洲的政策目标由原来的同苏联争霸改为推广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所以,在这个时候对美国来说,蒙博托已失去了使用价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直言不讳:“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同蒙博托的友谊也就结束了。”(注:新华社1997年4月10日电讯) 美国政府放弃支持蒙博托, 转而支持他的对手卡比拉。 失去支持的蒙博托政权于1997年5 月垮台。蒙博托曾经哀叹:“我是冷战最后的牺牲品,美国已不再需要我。”(注:《西亚非洲》,1998年第1期,第17页) 冷战结束后, 在安哥拉问题上美国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1993年5月,美国正式承认安哥拉政府。这一行动标志着美国对安哥拉政策的重大转变。因为安哥拉政府得到前苏联和古巴的支持,美国过去对它一直不予承认而支持安盟。
美国在非洲结束“以苏划线”后,打出“民主”旗号,指出促进民主是其对非洲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克里斯托弗说,非洲的未来“不由扎伊尔总统蒙博托之类的腐败独裁者决定,而由非洲大陆每个地方的勇敢的民主人士来决定。我们的新政策的中心是对民主与人权作出持久的承诺。”(注:《西亚非洲》,1998年第1期,第17页) 克林顿在此次访非过程中,也一再呼吁“加强民主和尊重人权”。看来,美国在非洲推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利用“民主”、“人权”向非洲国家施压的做法将继续进行下去。
3、从直接干预到幕后操纵。
1993年美国快速反应部队在干预索马里内战失败后仓皇撤退。此后,美国吸取这次维和行动失败的教训,被迫放弃直接军事卷入非洲国家冲突的方针,转而主张采取所谓“多边主义”和“预防性外交”的做法,努力推动联合国、非统组织等国际组织出面组建维持和平的力量,并且强调非洲问题应该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尽量避免直接卷入,而只是躲在幕后操纵。
1996年10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非洲,提出了一个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出钱、非洲国家出人来组建“非洲危机反应部队”的计划,即由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等国出人组成一支7000到10000 人的“非洲危机反应部队”,其使命是对非洲的各种冲突进行人道主义的干预,为平民建立安全区并实行保护。这支部队受联合国管辖。美国负责这支部队的训练并向它提供武器装备。在该计划遭到冷遇后,美国又于1997年提出了“对付非洲危机计划”,并准备在1998年投入2000万美元加以实施。同时实行的还有“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计划和代号为“J7”的培训计划,这些计划都是为了训练非洲国家军队,提高其干预冲突、维持和平的能力。目前,非洲国家中已有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塞内加尔、马拉维、马里和加纳同意接受美国的训练。
4、从侧重政治到关注经济。
冷战期间,美国在非洲主要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同苏联对抗。冷战结束后,美国伙同其他西方国家在非洲掀起“多党民主化”浪潮,结果造成了不少非洲国家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衰退,也损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近几年来,随着非洲政局趋稳和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对非洲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经济方面,并从经济援助转向贸易和投资。这一变化集中反映在作为克林顿访非见面礼的《非洲经济增长与机会法案》(简称“美非贸易法案”)之中。
早在1996年2月美国商业部长布朗访问非洲时, 他就明确表示美国不能拱手让出具有强大潜力的非洲市场。为了发展同非洲的经贸关系,1997 年4月,美国政府提出了《非洲经济增长与机会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增加非洲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最致力于改革的非洲国家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增加技术援助以便使非洲国家能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努力增加在非洲的私人投资;继续努力对从事经济改革的非洲最贫困国家取消双边和多边债务;每年同所有从事改革的非洲国家举行部长级经济会议。”( 注: 《西亚非洲》,1998年第1 期,第19页)这一法案的实施将使非洲对美国的出口商品从4000种增至5800种,价值增加50%,并增加美国对非洲私人投资1.5 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5亿美元。1997年6月,美国宣布1783种产品——其中多半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可以免税进入美国。1998年 3月,克林顿访非前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非洲经济增长与机会法案》。
克林顿访问非洲时,竭力推行美国对非洲的新政策,重申《非洲经济增长与机会法案》的精神,将发展经贸关系作为美国对非政策的重点。3月25日,克林顿与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 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六国首脑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强调必须采取措施,加速非洲经济改革,扩大互惠互利贸易和投资机会,以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并使其尽快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克林顿在会上表示,要加快实施《非洲经济增长与机会法案》,让更多的非洲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27日)。显然, 美国对非洲战略重心已从政治和军事转向经济,从援助转向双边贸易。
三、美国调整对非洲战略的原因
1、近年来,非洲总体形势趋向好转, 美国从非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中看到了新的商业机会。
非洲在取得民族独立后,经济一度发展较快。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非洲经济面临重重困难,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在整个80年代,非洲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仅增长0.4%,而它的人口年增长率却超过2.5%。所以,人们常说80年代是非洲发展“失去的十年”。90年代初,在多党民主浪潮引发的剧烈动荡的冲击下,非洲经济仍然步履艰难,1990—1994年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9%(注: 《 人民日报 》,1998年4月20日)。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 非洲总体形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热点”逐渐降温,冲突减少,政治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努力发展经济,非洲经济开始复苏。最近几年,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一直保持在年均4 %以上的增长势头,有的国家甚至超过6%。其中,1996 年非洲经济增长率达到4.6%;这一年有11个非洲国家达到或超过6%;1997年非洲经济增长率为5%(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18日),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
随着非洲经济的复苏,其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在日益显现。据专家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5年,非洲的进口总额将达4800亿美元。此外,非洲资源丰富, 素有“世界原料库”之称, 在世界最重要的50种矿产中,非洲至少有17种占世界储量的第一位,如铀、钴、锰、铬等均储量很大。这对既需要原料又急欲开拓海外市场的美国来说,无疑是有很大吸引力的。然而目前美非贸易额不高。1996年美国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为210亿美元,在西方国家中只占第五位。1997 年“对非洲的贸易只占美国全部贸易的1%,非洲的进口品只有7%是美国产品”(注: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98年3月22日)。 所以,美国从它的经济利益出发要重视非洲,要扩大与非洲的经贸关系,将其对非政策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由援助转向贸易和投资。
2、为了同法国在非洲争夺势力范围和市场。
法国与非洲有着密切的传统关系。它在结束对非洲的殖民统治时并没有完全撤出,而是改变了方式,继续维持同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系。因此,法国历届政府都重视非洲,把加强同非洲国家特别是法语非洲国家的关系,作为维护其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为了巩固和发展在非洲的传统利益,希拉克总统自1995年5 月上台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三次访问非洲。他在访非时明确表示:法国永远是非洲的朋友,“帮助非洲就是帮助法国自己”,法国将一如既往地把非洲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优先地区,与非洲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法国也在加紧调整对非政策。它一方面削减其在非洲地区的驻军,不再直接插手非洲国家的事务,另一方面同非洲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并且推行“援助”与“投资”并举的方针。目前,法国每年向非洲援款260 亿法朗,为美、英、德、日四国援助的总和。
美国在非洲争夺势力范围和市场的最大挑战来自法国。据统计,欧盟目前占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的40%,对非投资占其全球总投资额的32%,其中仅法国一国的非洲市场占有率就达21%。相比之下美国的非洲市场占有率仅为7.7%,对非投资仅占其全球投资总额的8%(注:《瞭望》周刊,1998年第13期,第40页)。美国不能满足于这种现状,为谋取在非洲更大的利益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而美国这种进攻态势,自然与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发生冲突。所以,今天法美在非洲的激烈角逐取代了冷战时期美苏在非洲的争霸。1993年,美国公司向前法属西非等地进军。美国石油公司遍布安哥拉、喀麦隆、刚果、几内亚湾和尼日利亚,受到打击的都是法国埃勒夫·阿基坦石油公司。在政治上,法国支持喀麦隆的保罗·比亚政权,美国就支持它的反对派。1996年10月,围绕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非,双方摩擦进一步公开化。克里斯托弗访非的第一站是西非法语国家马里,这被认为是美国明确向法国的势力范围挑战。法国讥讽克里斯托弗此行是为克林顿“捞取美国黑人的选票”,美国“并不真心关注非洲发展”。美国则反击说,“法国把它过去的殖民地看成它的领地”,“法国应该允许这些非洲国家有更多的独立性”。在1997年的扎伊尔内战中,法国支持蒙博托,而美国支持卡比拉。对于今年克林顿的非洲之行,法国媒体也颇有微词。法国舆论认为,克林顿访非是一次“公关行动”,一种“商业行为”,“美国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患难之交”。
实际上,在同法国的角逐中美国已占上风。近年来,美国在非洲“大湖地区”连连得手,法国的影响正在减弱。美国以此为契机,企图建立一个北起埃及,中经民主刚果、乌干达等中部非洲国家,南至南非共和国的“美非轴心”,以确保21世纪美国在非洲的霸主地位。
3、试图向非洲渗透美国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
最近几年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冷战结束初期动辄对非洲国家粗暴施压和直接干预的做法,采取了比较灵活务实的态度。但是,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总方针出发,企图在非洲发挥主导作用,将非洲纳入西方体系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利用“民主”、“人权”对非洲国家施压的基本做法也不可能完全放弃。所以美国仍然千方百计地向非洲渗透其价值观和经济模式。美国提出,非洲国家如果想同它在经贸方面结成伙伴关系,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非洲经济增长与机会法案》明确要求非洲国家在得到任何经济实惠之前必须按美国所主张的方式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美国免除部分非洲国家的债务也是有条件的。克林顿在访非期间宣布,美国将免除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而享受这一待遇的,必须是“最积极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不论它们是最富的还是最穷的”(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30日)。
4、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战略转变也是它国内政治的需要。
长达400多年的黑奴贸易给今天的美国留下了3400 万(约占美国人口的12%)非洲人的后裔。他们是美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的选票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渴求的。近年来,美国黑人后裔要求美国政府“赔偿”他们人身和精神损失并敦促美国向非洲国家“道歉”。所以,克林顿访非期间,到塞内加尔的“奴隶岛”上对贩卖奴隶的历史表示忏悔以及在乌干达的小学发表演讲时向非洲人民致歉,这些“道歉”与其说是给非洲人听的,还不如说是给美国的黑人听的。
克林顿的访非行动标志着美国为推行其对非新战略在非洲大陆摆开了全方位推进的外交态势。但是,美国对非洲新战略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非洲国家对此存在怀疑和警惕。南非总统曼德拉明确表示,南非拒绝“美非贸易法案”。曼德拉说:“南非不能接受这个法案,美国不能用贸易代替援助。”(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29日) 南非副总统姆贝基同样直言不讳地批评“美非贸易法案”。他说,这一法案提出的美非相互开放市场的方案不现实,因为非洲国家同美国相比经济实力悬殊,不能在同一水平上竞争。针对“美非伙伴关系”,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提出警告,“非洲大陆既不是法国的,也不是美国的”;“非洲受外国控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注:《人民日报》,1998年3月 22日)。既然美国不能消除非洲对它的疑虑,那么“新型的美非伙伴关系”只能是水中的月亮,美国对非洲新战略的前景也就不容乐观了,因为政治上已取得独立的非洲大陆再不允许有任何枷锁强加于他们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