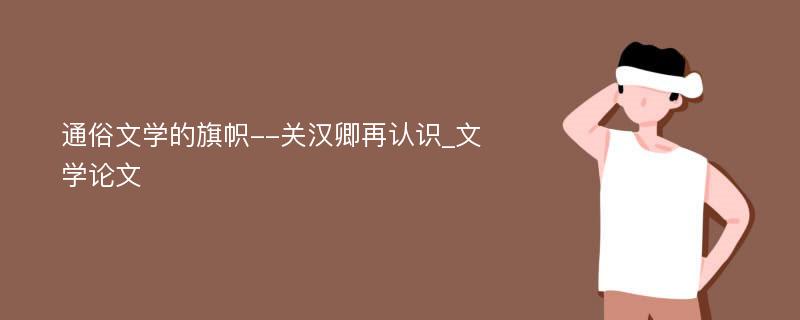
俗文学的一面旗帜——对关汉卿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旗帜论文,关汉卿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有两个转折时期特别令人瞩目。一是魏晋时期,标志着文学挣脱政治的束缚而走向“自觉”,“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①]展示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和文学的审美特性。二是元代,文学经历了由“雅”变“俗”的伟大变革,文学由贵族文人的专用品,变为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的精神食粮,文学从题材、思想、体制、语言诸多方面全方位的俗化,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元代俗文学的崛起,昭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扭转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方向,而向近、现代文学过渡,比起魏晋时代的文学转折来意义更加伟大。而关汉卿正是这一文学转折时代的一面旗帜。深入分析这一文学转折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正确估价关汉卿在这一文学转折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俗文学崛起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开始走下坡路,从北宋的衰亡,南宋屈辱的偏安而最终被一个少数民族所完全征服,清楚地显示出历史已不同于昔日的衰落特征。在政治、军事不能恢复汉唐旧观的同时,宋代经济、尤其是随着城市经济繁荣而兴起的商业、手工业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人、手工业者、江湖流浪汉、艺人(以文艺为职业者,区别于士大夫文人)、艺妓等市民阶层随之增多。这些人脱离了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四海谋生,充满着惊险与竞争,同时也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市民阶层新的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崇尚济危扶困和患难互助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一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行为无疑是对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是一股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元末明初的《水浒》作者曾用诗句明确地揭示了这一历史转折:“昏朝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第四十二回),“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第二回)。随着社会的衰颓,衣冠上层失去了上升期的勃勃生气,既缺乏治国安民之术,又大都是贪官污吏。衣冠上层的腐败更加速了社会的衰落。他们已失去了作为统治者的优势而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而属于“微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反抗暴政的江湖英雄、与统治者分道扬镳的落魄文人等市民阶层逐渐走向历史舞台。蒙古贵族的入主中原,加速了这一历史转折的进程。一方面,强权政治和公开的民族歧视使以蒙古贵族为中心的衣冠上层完全撕下了仁义道德的虚假面纱,公开抢劫搜刮。忽必烈的平章政事阿合马抢人妻女,卖官鬻爵,被他霸占的妇女竟多达133人,而向他行贿买官的官员竟有五百八十一人。权奸桑哥的党羽纳速刺丁灭里“恣为不法,理算江南钱谷,极其酷虐,无故死者五百余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②]。“赋役不均,官吏并缘为奸,赋一征十年”[③]。这简直是一帮残暴野蛮的豺狼!统治者丧尽民心,而不断激起人民的反抗,正如元散曲中所说:“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这些起义者成了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真正英雄。元代现存的六种水浒戏,写的都是当人民遭受恶势力的残害时,由水浒英雄出来主持正义的故事。可见人民对上层的极度失望,和把反抗社会黑暗、救民水火的希望寄托到起义英雄身上的愿望。另一方面,元代的城市经济却畸型繁荣。蒙古贵族要开疆拓土,东征西讨,需要大量的军需品和生活用品,特别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把大批工匠拘略到大城市,窝阔台和忽必烈都曾集中七十多万户工匠,聚集于各大城市,设立军器制造、染织、陶瓷等作坊和商肆,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再加上元朝疆域辽阔,横跨欧亚大陆,国内、经济文化商业交流频繁,更刺激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当时的大都,每天仅生丝就有上千车入城,店铺林立,人烟稠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手工业者、商贩、下层文人、士兵、艺妓等市民阶层随着增多,他们迫切需要反映其生活、思想愿望和审美趣味的俗文学出现,来歌颂他们理想的英雄人物,抨击压迫他们的黑暗势力和社会制度,反映他们悲欢离合的生活境遇、道德风尚和人生追求。很显然,用“雅”言来“载道”“言志”、辅翼教化的诗文,和他们是多么格格不入。可以说,俗文学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
(二)文学原因。社会对俗文学的需求,这只是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它还必须通过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而起作用。宋金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由盛转衰,以及市民阶层的出现和文化的发展,文学已不再是上层社会垄断的宠儿而开始蜕变。在诗文等雅文学统治的领地里,开始萌生俗文学的幼芽,南宋时期的说话艺术和杂剧,金代的诸宫调与院本,便带着勃勃生机悄然兴起。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封建朝廷对文人学士还有一定的吸引力,因而,传统作家仍然卑视俗文学而自守雅文学的阵地,只有民间作家投身俗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创作虽不乏新鲜感和生气,但艺术上难免呈现出稚拙粗朴的特征,宋杂剧和金院本没有流传下来完整的剧本,就与此有关。元代是俗文学勃兴的千载良机。在文学繁荣的外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创作主体——作家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代文学的成就大小。元代作家的主体是“书会才人”,这是一批从上层分离出来而走向下层的特殊群体。一方面,元蒙贵族的强权政治与他们信奉的道德治国的仁政理想格格不入,因而他们不愿向上层靠拢;另一方面元蒙贵族尚武功而轻文士,长期废除科举,拆除了文士向上层靠拢的阶梯。这两个原因相互作用,形成了元代作家“离心”倾向的合力。他们一方面出于谋生的目的,适应市民阶层对俗文学的需求,投身于杂剧、散曲的创作,成为“书会才人”;另一方面,他们沦入市井,和草民百姓一起身受上层社会的压榨,对社会黑暗有切肤之痛,对贱夫小民的生活、遭遇和抗争,由熟悉而理解,由理解而同情、支持。他们对俗文学的创作由不自觉到自觉,最终成为平民阶层的代言人。正如钟嗣成所说,他们自甘“得罪于圣门”,与“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分庭抗礼。[④]同时他们也在俗文学创作中寄托自己的哀乐、爱憎与理想。明代胡侍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中州人……每沉郁下僚,志不得伸……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乎声歌之末,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⑤]这些时代的“弃儿”,却是艺术的骄子。他们和以前的作家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中国封建社会的作家大致分为士大夫作家和民间作家两部分。“书会才人”虽出身士大夫家庭,但沦入下层,与士大夫作家不同。比如杜甫、白居易,与人民有相通之处,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却决不赞成人民反抗,从维护封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角度来揭露时弊,关心民瘼,主张社会改良。“书会才人”从上层社会分离出来而融入芸芸众生之中,和下层民众同生活共命运,必然会突破士大夫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是非观念,从下层人的角度来审视社会人生,为民众,也即为自己鸣不平。另一方面,“书会才人”与以前的民间作家也有所不同。民间作家未能受系统的文化教育,文学素养较差,作品比较稚拙粗朴,因而也较难产生影响深远的巨著。而“书会才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沦入下层。他们吸收了士大夫作家和民间作家的优点——高度的文学修养和下层人的立场、是非观念和反抗精神,成为一种新型作家。在他们身上体现了雅、俗两大文学潮流的汇合,而这种汇合又是以雅文学因素被俗文学所同化为归宿的。这些“书会才人”投入俗文学创作,是俗文学能够崛起并取代雅文学的决定性因素,无怪乎钟嗣成在《录鬼簿》中称他们是“不死之鬼”而炳彪青史。
二、关汉卿在俗文学兴起中的作用
俗文学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大致应包括三个方面:即题材的平民化,思想倾向的平民化和文学形式的通俗化。在这三方面,关汉卿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元代形成了俗文学崛起的“气候”,但还必须有敢为天下先的杰出人物乘时而起,把这种历史进程中的“可能”变为“现实”。正如李大钊所说:“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⑥]。这种“闻风兴起”的先驱,无疑是某一新思潮、新文艺兴盛的一面旗帜。
关汉卿是一个把自己的描写视角对准平民的杰出作家。在关汉卿现存的十八本剧作中,除七种历史剧受题材原型的限制外,其它十一种几乎都是以平民生活为题材。从勾栏卖笑、婢女悲欢、弱者蒙冤、寡妇血泪,到债务纠葛、日常生计、婚丧嫁娶、人命官司,这些过去士大夫作家很少涉及的题材,关汉卿却以极大的热情给予关注和多侧面的描写。尤其是被当时社会压在最底层的妇女,更成为关汉卿描写的中心。在现存的十八本关剧中,有十二本是以妇女为主角的“旦本戏”。其中有被流氓恶棍、残暴官府推向断头台的年轻寡妇窦娥;有被迫卖身为奴、弃子荒郊的王嫂,精神肉体遭受凌辱的婢女燕燕;更有丈夫被害又不得不献出亲子的王婆婆,婚姻家庭受到恶势力威胁的谭记儿;以及挣扎在妓女制度、封建家长制下的赵盼儿、宋引章、杜蕊娘、谢天香、王瑞兰、王闰香等众多女性。毫不夸张地说,关汉卿描写出了元代下层人民生活的悲惨世界。
大量地全方位地描写平民生活,这只是关汉卿创作平民化的基础,而关汉卿创作平民化的精髓还在于他代平民立言的思想倾向和对平民生活题材开掘的深度。
关汉卿描写平民生活,总是把他们置于元代民族压迫、阶级矛盾的现实土壤上,揭示出他们苦难生活的社会根源,多侧面抨击元代的罪恶制度。《蝴蝶梦》中的葛彪公开宣称:“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无故打死王老汉后,竟毫无畏惧地说:“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王老汉的三个儿子忍无可忍打死了葛彪,清正如包拯,也不得不按法律判决王三为葛彪抵命。这种极度的不平等正是元代民族歧视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作者借王婆婆之口大声疾呼:“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本在呼唤“法平等”的同时,有力地抨击元代民族歧视制度。元代法律明文规定:“诸杀人者死,”而“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⑦]或按“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夫,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⑧]。剧本把故事发生的背景写成宋代不过是借宋比元而已。“杀人夺妻”的杨衙内,抢人妻女的鲁斋郎,都是元代享有特权的野蛮蒙古贵族的化身。吏治大坏,无官不贪,冤狱成山,这是元代社会的突出特征。仅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就有“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⑨]。《窦娥冤》中的桃杌正是贪赃卖法、残害民命的贪暴官吏的典型代表。他认钱作父,严刑逼供,一直把一个无辜的年轻妇女推向了断头台。这样的贪官酷吏竟然升迁了,通过他的形象,艺术地总结了元代冤狱成山的社会原因。
元代的私奴制度,是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元蒙贵族把掳掠来的人口变为私奴,也有因生活无着自卖为奴者。他们被称为“驱口”,成为被主人奴役、压榨、凌辱的“活”工具。关汉卿勇敢地揭开这社会最黑暗的一角,为这些“非人”的生灵鸣不平。《五侯宴》中的王屠之妻李氏,因夫亡家贫,只好卖子葬夫,后被地主赵太公典身三年,乳养己子。赵太公竟把典身文书改为卖身契约,迫使李氏终身为奴。赵太公为了让李氏只乳养自己的儿子,竟要摔死李氏亲子,逼得李氏只好忍痛弃子荒郊。这悲惨的一幕,不禁使人想起柔石的《为奴隶底母亲》。私奴的另一典型是《调风月》中的婢女燕燕,她聪明美丽,渴望爱情和自由人的生活,却被主人的贵客“小千户”诱奸,还要被逼去为“小千户”说亲,为新娘梳妆,在“吃人”者洞房花烛的喜庆中,去体味自己身体、灵魂被践踏的双重痛苦,谁能不为这个地狱中的灵魂洒一掬同情之泪呢?
罪恶的妓女制度是元代社会的另一“毒瘤”,关汉卿用艺术的解剖刀剜出了这一“毒瘤”的根子。《金线池》中的艺妓杜蕊娘是李氏“亲生的女”,但这位母亲却逼迫女儿卖身赚钱,要女儿“只待夜夜留人夜夜新,”“淡妆浓抹倚市门,积下金银囤”。为此甚至不准女儿嫁人,要嫁人就是“生忿忤逆”的不孝,就要“筋都敲断你的”。深刻揭示出母亲(老鸨)与女儿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妓女就是供人玩弄、替人赚钱的“活”工具。元代的妓女制度就是奴隶制残存的人身依附关系和随着商业繁荣出现的金钱关系畸型结合的产物。
横暴的家长制则是关汉卿抨击的另一对象。《拜月亭》中的兵部尚书王镇生生拆散女儿与穷秀才蒋世隆的婚姻,而当蒋世隆中状元后,对这一被抛弃的女婿前倨后恭,揭示出这一封建家长专横、虚伪、势利的嘴脸。总之,关汉卿不是把平民的苦难生活当做偶然现象来写,而是把它当做元代各种罪恶制度的必然产物来写,透过平民苦难生活这个窗口,让人看到元代黑暗社会的五脏六腑,认识这个罪恶社会的本质,达到了写平民题材前所未有的高度。
代平民立言的关汉卿,不只是写出平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把他们写成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挖掘出平民阶层灵魂中的闪光点和蕴藏的力量,歌颂他们道德的高尚和为争取生活的权利、向恶势力机智勇敢抗争的斗争精神。《蝴蝶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公案戏,它的主角不是包公,而是一个农村老婆婆。不敢秉公断案、为民伸冤的包待制,被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王婆婆高尚的道德风范所感动。《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救人危难,机密智勇敢地击败了奸诈残暴的官僚子弟周舍,体现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遇蠢”的真理。关剧中的平民大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年轻寡妇窦娥面对封建官府和整个黑暗势力敢于以死抗争;被小千户诱骗失身的婢女燕燕,在小千户与贵族小姐的婚礼上大闹婚宴,表现出泼辣恣肆的“野山椒”性格。谭记儿、赵盼儿、杜蕊娘、王婆婆都是为争取生活的权利,敢于“捋虎须”的斗士。关汉卿正是在这些平民身上寄托自己美好的生活理想、崇高的审美情感和对社会黑暗的抗争精神,是关剧平民化思想倾向的集中体现。
文学形式的通俗化是文学平民化倾向在文学形式上的体现。在这方面关汉卿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首先,为平民喜闻乐见的杂剧体制是关汉卿最早完备的。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杂剧)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关、白、郑、马,一制新作”。而《录鬼簿》又列关汉卿于元代杂剧作家之首,就连贬低关汉卿的皇族朱权,也不得不承认:“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⑩]。从关汉卿流传下来的剧作看,除《五侯宴》是五折外,其他均为四折。这些材料就清楚地说明关汉卿对杂剧体制的首创之功。其次,关汉卿在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起到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关汉卿是元杂剧“本色派”语言风格的典型代表。王国维对此中肯评价说:“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元人第一”(11)。其语言通俗自然,入耳消融,声口毕肖,与反映平民生活的内容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而倍受平民观众欢迎。李渔就说:“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不问而知,为今曲,非元曲也(12)。关剧语言正是让人入耳消融的“绝妙好词”,而更适合舞台演出的需要,代表着文学语言健康发展的方向。
三、关汉卿代表的俗文学传统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俗文学的一面旗帜,关汉卿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关汉卿抨击上流社会的罪恶、代平民立言的创作倾向影响了一代代作家。元曲中的反抗精神和平民化色彩直接导源于关剧,而明代《水浒传》歌颂“微族”英雄除暴安良、济危扶困的道德情操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也与关剧的平民化倾向一脉相承。《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全面批判和对众多女性高尚不屈的灵魂的刻画,也与关汉卿的创作倾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关汉卿通俗化的文学形式,也成为后代文学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元明清三代,以通俗生动的白话取代典雅雕琢的文言,以叙事写人的戏剧小说取代抒情写意的诗文,正是俗文学传统战胜雅文学的标志。这一俗文学传统甚至对“五四”文学革命都有着启示作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在答胡适的信中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人物郭沫若也说:“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产生出来的。”(13)“五四”文学革命内容上的平民化倾向、创作方法上的“写实”精神、语言上的平易通俗都与关汉卿开创的俗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革命是对俗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关汉卿代表的俗文学传统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向近、现代文学过渡的桥梁。
注释:
①曹丕《典论·论文》
②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七《阿合马、桑、卢之奸》
③《元史》卷一百八十四《王都中传》
④钟嗣成《录鬼簿·序》
⑤胡侍《真珠船》卷四《元曲》
⑥李大钊《晨钟之使命》
⑦《元史》卷一百零五《刑法志》四
⑧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引窝阔台语
⑨《元史》卷二十一《成宗本纪》四
⑩朱权《太和正音谱》
(1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12)李渔《闲情偶记》
(13)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