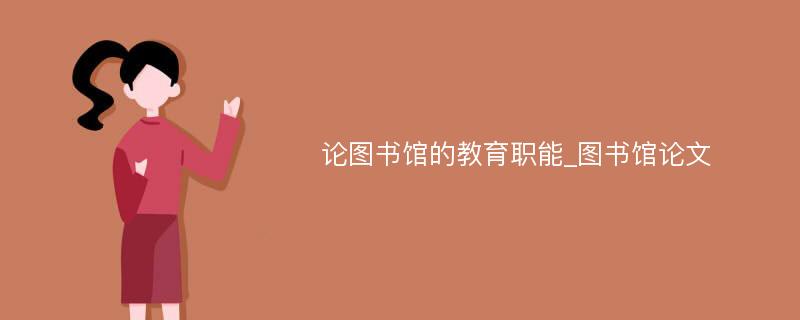
图书馆教育职能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职能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图书馆只是学校、研究单位或政府文化部门的一种附属机构。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一机构的教育职能,但更多的人往往只从它对学校教育、专业研究或意识导向所可能起的辅助作用上去理解。本文拟从探讨图书馆的独立教育价值入手,对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及其应有的人文品位作一简要的阐说。这阐说倘不全然落于偏颇,也许多少有助于人们从教育的向度上获得一个近于正确的关于图书馆的整体观念。
1 图书馆的独立教育价值
图书馆因其设在学校而有附属于学校的一面,因其设在研究单位而有附属于研究单位的一面,因其为政府文化部门所设立而有附属于政府文化部门的一面,但图书馆,无论是学校的、研究单位的还是社会性质的图书馆,成其为图书馆,毕竟有其独立的理由或独立的价值。所谓图书馆的独立教育价值即是这独立的理由或独立的价值在教育方面的体现。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一民族有着古今略可通解的一套文化符号系统,这相对稳定却又并非一成不变的符号系统构成每一代人的生活背景,也构成每一代人对真、善、美、圣诸人生价值的创造性追寻的背景。它除了展示于前后相续的可感的生活境遇和一定风俗习惯乃至社会心理外,也更大程度地保留在以文字为表意方式的图书典籍中。图书典籍诚然为智识之士所述作,但却常常是留下这些典籍的民族在某一时代的价值取向的记录或趣真、审美、致善、希圣的文化成就的结晶。因此,珍藏民族的图书典籍,也是珍藏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灵魂。有了这些珍藏,后人的心灵才可能同前人的心灵接续得上;有了这些珍藏,后人的新的文化创造或文化批判才有可能获得一个相对高的起点。默无声息的图书典籍储藏着难以量计的精神资源,收藏这些资源是古代的藏书处与今天的图书馆的独特的使命,这使命使藏书处或图书馆的存在有了一种背负历史而指向未来的神圣感。所以,藏书处或图书馆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一个教育的维度,它以“藏”这一文化行为本身对人们所作的是别具一格的历史教育和对人文创发的神圣感、敬畏感的启迪。倘借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前一重教育即是所谓“通古今之变”,后一重教育则将人们的可能深刻的反省引向“究天人之际”。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持续存在是需有一种历史认同和民族或国家的神圣感的确立的。一旦这种历史认同或人文神圣感动摇了,这个民族或这个国家的衰亡也就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至少可上溯到距今已4000余年的夏朝,而设官置室以藏书的历史也可上溯到与此一样久远的时代。藏书丰瘠的起落多少相应于朝代的兴替,典籍的命运往往系于文脉或国运。《史记·肖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吕氏春秋·先识览》则记:“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图书、图法的去、归,在这里恰同一朝一国的衰、兴相印合,肖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终古、向挚、屠黍——夏、商、晋藏守图书的官史——分别“载其图法”而“如商”、“之周”、“归周”,固然不无对“图法”的实用价值的看重,但也未始不是出于对“图法”所具有的那种人文神圣感的尊崇。
今人多以为图书馆的职能在于由“藏”而“用”,但“用”却更大程度地被赋予了实用的内涵。其实“藏”本身即是一种“用”,或所谓“不用之用”。这“不用之用”在于,藏本身即对于启示人们的历史感或人文神圣感受有着莫大作用。它作为一种教育价值是藏书处或图书馆所独具的,是学校教育或专业性的成人教育所不能替代的。
2 图书馆的依存教育价值
诚然,图书馆的“藏”的价值总是由“用”体现出来的,尽管“用”并不就能尽其所“藏”。这“用”或限于学校,或限于研究机构,或限于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图书馆服务于学校、研究机构或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使图书馆的价值带上了某种依存性。因此,图书馆在教育上的价值遂成为一种依存价值,即所谓依存教育价值。
一部《道德经》(《老子》)在军事院校的图书馆里可能更多地是作为“兵书”而起教育作用的,一部《论语》在大学教育系的图书馆里则可能作为古代贤哲论说教育的著作而起教育作用,但无论是《道德经》,还是《论语》,其思想对形上世界和形下世界的精神覆盖显然要大得多。图书馆所藏的《道德经》和《论语》,是完整地“藏”了老子和孔子阐发于其中的思想的,所“用”不免于是“藏”的价值在“用”中的赋有依存性的实现。对“用”的偏向性的发现与矫正当然在于新的“用”,但这“用”的新新不已所以成为可能则是因为“藏”。就是说,图书馆在现实的“用”中所以能发挥其不竭的依存教育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因为它有着体现于“藏”的独立教育价值。
“文革”中的图书馆,其所“藏”儒家、法家的著述和《水浒》等书曾为“评法批儒”、“批《水浒》”所用,“文革”后纠正“评法批儒”、“批《水浒》”等错误意识形态导向依然要“用”到同样的所“藏”著述。这是“藏”对于“用”所具有的本体地位最直观的说明,也是图书馆的独立价值不能为其依存价值所取代的最直观的说明。“文革”是政治功利一元化的时代,那时图书馆事业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只是被看作当下政治需要的一种工具。图书馆被政治工具化是图书馆在人文意义上的独立价值的丧失,由此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许多图书馆所“藏”图书在“文革”中被毁或被禁。其实,图书馆在任何一种实用意义上的工具化,都会导致图书馆的独立人文价值的相当程度的丧失,只是沦为政治实用的工具,其问题更突出些罢了。
图书馆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的所“用”都会产生一定的教育作用,因而都会显现图书馆所可能有的教育价值,但将任何一个方面的所“用”夸大为图书馆的唯一之“用”,也都会妨碍它的更全面的教育功能——包括“用”的自我纠正功能——的发挥,因而也都会因着图书馆的独特的人文价值的被否定而导致其独立的教育价值的被否定。图书馆的正常教育价值的实现是一种有着多层次的教育的过程。这个施教过程的最浅层次当然是知识性的,图书馆在这一层次上也可说是一个知识库。就知识的确定性——如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或《道德经》分“道”经与“德”经两部分——不随任何一种人文实用的需要以发生改变而言,实施知识层次的教育也许是最没有狭隘的依存性的,但停留在知识教育上,图书馆的价值充其量不过相当于一本待查的百科知识词典。图书馆教育职能的第二个层次是方法的层次,这是较知识层次深进了的一个层次。其所藏的典籍中“藏”了知识,也“藏”了方法,读者掌握其中的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产生自己的方法,这要比掌握其中的知识更困难些,但也更重要些。此外,图书馆所藏典籍也还“藏”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种种价值观念,这些观念藏在更深的地方,有待于读者以敏感的心灵去感应、反省和批判地汲取。现实中的人们可以接受这一或那一方法和观念的引导,也可以拒绝这一或那一方法和观念的引导,图书馆以其对群典群籍的博藏所施于人们的教育不仅仅是要人们去领略、理解因而把握这一或那一方法和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让人们以更宽容的态度、更开阔的胸襟去同情理会种种可汲取的方法和观念,在于让人们学会懂得自己的“无知”相对于更多“知”,一个真正求知的人总会觉得自己是“无知”的,同时,也懂得自己的眼光和胸怀总会是受限制的,因而启示人们不断陶冶自己的兼收并蓄而又自有存主的心灵。
3 图书馆应有的人文品位
图书馆既然担当着如此重要的教育职能,它便应当具有与这一职能相称的人文品位。一个好的图书馆应当给人以一种儒雅、文静和肃穆感,应当是同喧闹、匆忙、充满功利之急切的市井或社交世界全然异趣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心灵可望得到一份官场、商场、游艺、娱乐,乃至消闲场合无从得到的那种恬淡和宁静。它所诱发的唯一欲望是人的求知之欲,所带给人的唯一乐趣是读书明理之乐。它让人暂时脱开功利的奔竞和浮名流誉之累,使人在学以致思所引出的可能的反省中,获得灵魂的纯化。单是图书馆的气氛便有着一种教育作用,这教育的方式主要是感染和陶冶。图书馆的建筑与设备无论简陋与否,都不妨碍这种人文氛围的营造。孔子说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问题不在于屋宇或陈设的丰俭,而在于所谓“君子”之风的养成。
一个好的图书馆应当以它的所藏图典带给人一种亲切的民族认同感和深沉的人文历史感,应当给予在现实生活中奔竞的人们以一种人生的厚度和历史的眼界。一般说来,越是切近于实用而带有技术性的图书,其借阅率越高,图书馆以相当的资金购买并储存这一类书是完全必要的。但也应看到,越是实用性、可操作性强的知识,越容易随着时间和时潮的推移而被淘汰。因此,在图书馆必要的藏书剔除工作中,这一类书的剔除率便很高。一个照顾到功利所需而又不被急近的功利潮流牵着跑的图书馆,无论是专业性很强的图书馆,还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图书馆,一定应当有自己的经典藏书。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曾产生过许多哲人、贤达、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以文字形式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历史风雨的剥蚀和淘汰,这份文化遗产愈来愈去粗取精而经典化。一个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哪怕是某一专业研究机构的图书馆,都应当藏有这样的经典。这些经典稳定而有生命力,图书馆可能因此而有一个藏书重心,也会因此而更好地履行民族认同感和人文历史感方向的教育职能。诚然,所谓经典图书,愈是历史久远的,愈有一个为更多的人所认可的标准,而愈是现代的,则愈需要选购者有较深的人文教养和图书知识,也需要选择者对诸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经心关注。
一个好的图书馆还应当具有开放时代的精神,不仅能提供最必要的与时代相称的科学、人文信息,而且能给予人一个深广得多的世界视野。它应当藏有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诸多文化领域的经典图书,也应当有一定数量的、堪有经典相称的日文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图书。购藏这类书的中译本固然很重要,但亦应有外文原版书。外文原版书较昂贵,在资金并不充足的情形下,通过专家、学者的推荐对书籍作精心选择便十分必要。
图书馆对图书作科学编目并在条件允许时尽可能诉诸最新手段的管理,这固然是不可忽略的事,但图书馆的人文品位的提高最重要的还在于图书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人文素养的提高。正像教育领域要将自己作一个重心自在的人文领域肯定下来,必须树立教育家的理念那样,图书管理作为一个有着相对独立性的人文领域也有必要树立图书管理家的理念。图书管理意义上的敬业精神可以从多方面说起,但这些精神无不关联着所谓图书管理家的理念。这理念同行政职务的高低不相关涉,它的内涵在于图书管理者对图书管理这一有着神圣教育职能的人文事业的神圣感的体会认识,也在于图书管理者的业务能力和自身的人文品格的充分提高。中国古代著名的图书守藏者终古、向挚、屠黍……被称为“有道者”,这“有道”二字的评价在古代是极高的,它当然包括了对相当高的学识教养者的肯定,但其最重要的所指则在于一种虚灵的高尚的人文境界。今天的图书管理者应当在图书管理家的理念的感召下努力提高自己,以成为新时代的“有道者”。一个图书馆的人文品位其实就取决于这个图书馆的图书管理者自身的人文品位。肩负教育使命的图书管理领域同其它领域一样,人是决定一切的。培根在《人类求知的进展》一文中对图书馆作了如下的描绘:
“在这座圣祠里安息着所有先贤圣哲的流芳遗韵,洋溢着纯真的美德,没有令人迷妄和欺世盗名之处。”
一个高品位的图书馆应该具有这种“没有令人迷妄和欺世盗名之处”的“纯真的美德”,一个高品位的图书管理者当然应该具备与此美德相应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