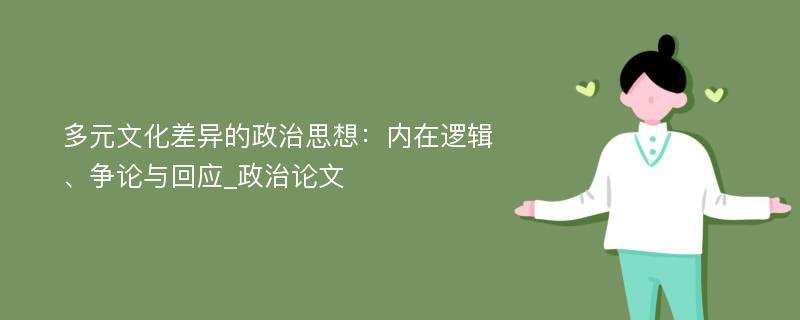
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内在逻辑、论争与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思想论文,逻辑论文,差异论文,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在二战后西方国家族裔文化多样性不断形成、发展和凸显的背景下,于20世纪50~60年代产生的关注族裔文化多样性,主张承认并尊重族裔文化差异的重要政治思潮。这一思潮强调通过寻求保护少数族裔群体权利以实现族裔群体公正,多元文化平等共存和共同繁荣。
国内学者把这一思潮主要分为四个流派,即:以威尔·金里卡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以玛丽恩·杨和詹姆斯·塔利为代表的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以亚瑟·施莱辛格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以查尔斯·泰勒和迈克尔·沃尔泽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①
尽管流派各异,多元文化主义却拥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思想是多元文化主义者面对“文化差异”的事实和“文化平等”的诉求而提出的一系列应对方案及其理论论证,多元文化主义的嬗变与论争多源于对差异政治的理解及其应对方案的分歧。本文力图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政治思想及其论争作一概述、分析和讨论:文章将首先探讨差异政治思想的思想渊源和内在逻辑,然后重点分析多元文化主义内部对差异政治思想的论争,以及来自外部的批评与回应,最后对差异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强调特殊认同,主张所有的独特性都应该得到普遍平等的尊重和承认,认为所有文化都值得平等尊重。这种差异政治思想源于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之普遍主义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思想的反思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女权主义、黑人政治、后现代主义思潮、“权力话语批判”,以及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兴起,“弱势”、“少数”、“身份”、“特殊性”等话语逐渐成为解构普遍主义模式中同一性支配下的霸权话语和主流体制的“另类之声”。“差异”作为这些思潮的基本范畴,与族裔文化相结合,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建构,包括差异政治思想的阐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差异政治的起源:对普遍主义政治的反思与改进
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是在反思传统自由主义之普遍主义政治的缺陷过程中产生的。传统自由主义以重视道德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建构其理论,但传统自由主义对待差异的方式,却遭到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反对。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传统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政治强调所有公民均享有平等的尊严,主张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平等化是以牺牲差异、少数和多元化为代价的,“无视差异原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首先,传统自由主义建立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论哲学基础之上,主张普遍的公民观念。这就把个人与其所在的群体和文化割裂开来,不去关注个人背后的文化,忽略了公民的独特性和不同团体间的文化差异。传统自由主义还认为,个人选择了文化,因而个人的文化选择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都是私人领域的事情。
其次,正是这种普遍人性论和普遍公民观促使传统自由主义主张普遍主义的公正理论,认为正义是超越历史和时空的原则,是评判一切的标准。对此,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在实践意义上,普遍公正理论把道德主体的多元性简化为单一性,试图以相同的原则适用于所有人,没有顾及社会中存在的多样化需要和不平等。
再次,为保证公平,传统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正理论要求对所有公民平等对待。多元文化主义者批评这种平等观不仅忽视了公民的差异,而且无视族裔少数群体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普遍主义政治所谓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并不能消除社会差异。文化族群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忽视文化差异的做法最终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最后,传统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政治是主流文化群体主导的政治,本质上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同化主义的政治。因而,多元文化主义者要求真正的文化平等,主张“去中心化”。
(二)差异政治的基础: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
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评基于族裔群体间的文化差异这一客观事实,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又是差异政治思想发生的基础。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者并没有赋予“差异”一致的界定。桑德斯认为,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解释这一概念:(1)“差异”是“同质性”的副产品;(2)差异是一种实现平等权利的方式;(3)差异因其所处的政治情境而具有政治特色;(4)差异的载体是共同体。② 这种抽象解释论及了差异概念的关键之处,即差异的政治意义和共同体意义,但是并没有论及差异的文化意义,也没有限定什么类型的共同体。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主要是指族群文化的独特性,尤其是族裔少数群体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差异需要通过政治的途径来取得平等地位。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差异?多元文化主义接纳了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个信念:对于不同的群体,甚至对于同一群体内不同的个体而言,“相同的符号对象承载着不同的语义学的涵义……而且这种差异影响着实践的同时也受实践的影响”。③ 这表明,文化差异一方面产生于语义学上的理解差异,另一方面受不同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影响。金里卡在讨论文化的内涵时指出,文化必然是指“社会性文化”,即一种能够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中为其成员提供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它不仅包括共有的记忆和价值,而且也包括共同的制度和实践。④ 由此可见,记忆和实践的不同必然导致文化的差异。
(三)差异政治的必然要求:文化差异的认同
不同群体之间会产生差异性的文化,假如这种差异容易消除,那差异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但问题在于,“对许多群体……而言,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公民资格,但仍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共同文化’之外……这些群体的成员之所以感到被排斥,不仅仅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因为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即他们的‘差异性’”。⑤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文化之间的转化是非常困难的,消除文化差异的做法将付出巨大代价。因为:(1)族裔文化为成员的自我认同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和安全的归属感,其他文化很难满足自我认同的这种心理需求。(2)对族裔文化的熟悉性为其成员提供了可想象的界限和选择的范围,如果一种文化遭到歧视或受到限制,其成员的选择和机会也将减少;而如果一种文化的成员被迫置于陌生的文化环境中,他将无所适从。因此,文化的多元并不能减弱人们以其自身文化来生活和工作的渴望。为保证共同体成员不因自身文化的消失而损害有意义的生活选择,必须保存和发展差异性的族裔文化。
(四)差异政治的价值支撑:文化差异的重要意义
对于个人而言,首先,文化塑造了个人的内在特性。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任何个人都是特定文化共同体中的个人,他的个性和认同必然受共同体文化的深刻影响。文化规定了“此人是谁”,它甚至是“人之为其人的组成部分”。⑥ 其次,共同体文化是个人进行有意义选择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共同体的文化结构为个人界定了可供选择的范围,而且使其选择更有意义;另一方面,共同体文化培养了个人的认知和选择能力。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的习惯性态度和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这些态度和理解力形成了他的观念,并指导着他的认知、判断和选择。按照自由多元主义的论点,“差异性被视为人类昌盛的必要条件,它向个人,不论男女提供各种选择权,使他们的自主权富有意义”。⑦
对于群体和社会而言,文化的意义在于,它规定着共同体成员的信仰和价值观,规定着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方向,因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一些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文化差异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差异性为世界的丰富多彩、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提供了可能性。至于文化差异是否会影响到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这是存在争议的。不过,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恰如罗蒂所言,多元文化及其道德差异的存在对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是极为有益的。⑧
(五)差异政治的实现:文化差异的应对
既然文化差异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而且消除文化差异十分困难,那如何应对这种差异呢?
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首先,“差异只是‘不同’,而不是‘劣等’”,⑨ 因而必须承认并尊重这种差异,对不同族裔文化群体给予平等的地位。其次,如果仅仅把文化看做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差异性的文化根本无法获得平等地位,因而必须把文化平等的诉求纳入到公共领域。可是在公共领域如何实现文化平等呢?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由于不同文化对于其成员具有差异性的价值,而且个人只有通过介入一种文化,才能使其选择具有意义,因而需要根据不同族裔群体的特点区别对待,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平等。也就是说,这种平等不是同化主义的平等,而是文化差异之间的平等。最后,所谓区别对待,根本上就是要赋予族裔少数群体特殊的团体权利。
因此,所谓差异的政治,“即承认少数群体的文化身份与多数文化具有相同的意义和地位,珍惜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将它视为国家的共同资产和力量,并根据差异原则和少数群体的文化特点区别对待,赋予少数群体以更多的文化权利,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同时也能发展和享用自己的文化传统”。⑩ 差异政治的本质是弘扬多样性和异质性,拒斥同一性与同质性。
二、多元文化主义内部对差异政治的论争
尽管差异政治思想拥有共同的逻辑起点——文化差异,也诉求共同的现实目标——文化平等,但在通过什么途径达到目标的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者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泰勒提出平等承认的政治观,沃尔泽要求对差异采取宽容态度,玛丽恩·杨诉诸群体代表权,而金里卡则试图调和公民个人权利和族裔少数群体权利。
(一)平等承认的政治
查尔斯·泰勒是社群主义的杰出代表,针对如何应对差异的问题提出了“平等承认的政治”。他分析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扭曲的承认”和“等级制的承认”。认为前者把人置于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中,后者则与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相关。泰勒主张的“平等的承认”是建立在平等原则上对差异的承认。但是,在他看来,即使是同样的平等原则,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传统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政治”(11) 和激进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政治”。泰勒论述的重心就在于分析和比较这两种模式。
所谓普遍主义政治,就是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它所要求的是公民身份的平等。而差异政治要求承认个人或群体的独特认同,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性;这种政治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泰勒看来,这两种模式虽然有其共通之处——都接受普遍平等的原则,(12) 但二者的分歧和冲突是很清楚的:普遍主义政治要求承认的是某些普遍的权利,是一种无视差异的平等;差异政治要求承认的是某种特殊的认同,是承认差异的平等。“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到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的认同”。(13) 差异政治指责普遍主义政治的无歧视原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反映,其结果是只有少数民族文化或受压抑的文化被迫采取异化的形式。所以,表面上公正和无视差异的社会不仅是违背人性的,而且其本身是高度歧视性的……‘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是某种特殊文化的反映”。(14)
泰勒认为,这两种思想各执一端,都有偏颇。对于激进的差异政治,泰勒部分地接受了来自传统自由主义的指责,认为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在呼吁特殊性的同时,忽视甚至违背了普遍主义的平等原则,他们的做法实际上不过是“把歧视性措施颠倒过来”,让原先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获得某种特权。按照传统自由主义观点,激进多元文化主义似乎是一种倒退和背叛,是对普遍平等原则的彻底否定。对于普遍主义政治,泰勒批评了其程序自由主义,认为他们在文化领域坚持程序性承诺,而放弃实质性观点,完全无视公民间的差异。如果把源自卢梭的平等自由与无视差异相结合(这正是一些传统自由主义者所偏爱的),那么族裔群体的文化差异就会被普遍主义程序所掩盖、同化和抹杀,承认差异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泰勒试图在传统自由主义和激进多元文化主义的冲突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即“温和的自由主义”。(15) 这条道路的原则是既要承认差异,又要坚持平等。不过他对这条道路的具体图景语焉不详。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描绘出他所持的主张:第一,必须承认族裔文化差异,但它只是平等原则的补充。第二,自由主义不应主张完全的文化中立性,但具体该采取何种措施,泰勒没有明确的回答。
(二)对差异的宽容与尊重
泰勒的平等承认政治不仅没有提出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且在对待差异的态度上,也仅仅停留在承认的层面上。他的平等承认,被视为一种简单的平等。美国多元主义正义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迈克尔·沃尔泽的观点则往前推进了一步,他主张宽容差异并为复合平等论进行辩护。
在多元和差异成为客观事实的背景下,沃尔泽指出,“宽容使差异成为可能,而差异使宽容成为必要”。(16) 他所说的宽容是为实现不同文化群体和平共处而实行的宽容,而不是传统自由主义历史上对不好或错误之事物的宽容;其宽容所针对的主体是具有各自历史文化传统的群体,而不是传统自由主义所偏爱的个体;其宽容是多样化的文化心态和政治实践,而不是传统自由主义讨论宽容问题时的单一的抽象原则。
沃尔泽认为,宽容可以带来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和平共处,不过这需要某种政治上稳定、道德上合理的宽容体制。一种宽容体制就是一种政治形式,而和平共处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治形式,每种政治形式都不是普遍有效的,最佳的政治安排总是相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历史和文化而言的。(17) 为说明宽容体制的多元性及其与族裔文化的紧密相关性,沃尔泽分析了五种不同政治体制(多民族帝国、国际社会、联盟制政权、民族国家和移民社会)在处理族裔共存问题上的政治实践。他还据此总结了四种宽容心态:一是“无恶意的冷淡”,即兼收并蓄成一统;二是道义容忍,即对少数族群拥有各种权利予以原则上的认可;三是倾听交流的心态;四是积极拥护差异的心态。(18) 沃尔泽认为,后两种通过沟通而获得对方承认的心态更易于达到对差异的宽容。
法国的阿兰·图海纳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互相沟通’意味着对他者、对多样性和多元性的承认。”(19) 不过图海纳的分析不像沃尔泽那样侧重于主观态度,而是立足于历史的社会现实。他认为欧洲国家最初是出于停止宗教战争之目的而提出宽容问题,宗教战争之后,宽容问题则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今天,由于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远胜于阶级冲突关系,宽容已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共存的问题。
由于存在不同的宽容心态,特别是被动冷漠的宽容同样暗藏着危机,所以简单的宽容是不够的,必须对差异采取尊重的心态;而要尊重差异,就要了解不同族裔群体背后的文化与认同,并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三)多元正义与复合平等
无论是承认、宽容,还是尊重,都是态度问题。虽然这些态度对于目前处于劣势的族裔少数群体而言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体制建设和政策实践来促进这种态度并切实保障少数群体的权利。为实现多元文化的平等共存,沃尔泽在论证其多元主义正义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复合平等观。
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一样,沃尔泽也讨论了分配的正义问题,不过他对正义的理解不是基于抽象的个人权利,而是基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共同体成员对社会物品的多元理解。由于不同物品在各种共同体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因而正义的内容是多样的,这决定了“正义原则本身在形式上就是多元的;社会不同善应当基于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程序、通过不同的机构来分配”。(20) 也就是说,所有分配公正与否不由物品本身决定,而是与物品的社会意义直接相关。而且,任何一种物品都不应具备对其他物品的统治或支配权,各个领域的分配应相对自主。据此,“物品的社会意义”和“各领域的相对自主”是决定正义与否的根本要素。
沃尔泽从这两个正义要素出发,进一步推导出复合平等观。这种复合平等是相对于简单平等而言的。简单平等观假设存在支配性的善,(21) 这种善通常被特定群体所垄断,因而简单平等论者要求打破或限制这种垄断,试图使所有人都同等地享有这些善。沃尔泽不同意这种追求均质化的简单平等观。他认为,真正的平等意味着减少一种领域之善支配其他领域之善的可能性,而不主要是打破或限制垄断。也就是说,即使一个领域的善被某人垄断,他也不能凭借这种善去支配其他领域物品的分配。因此,复合平等要求:(1)各领域分配自主;(2)尽量使各种善不能普遍转换。据此,沃尔泽设想了复合平等的社会:“其中不同的社会物品被垄断性地持有……但其中,没有特定物品能够普遍转换……[在这种社会中]尽管会存在许多小的不平等,但不平等不会通过转换过程而增加。”(22) 这种社会为差异和多元文化留有了空间,它不是抹杀差异而是要捍卫差异,它不是对多元文化进行整合,而是区别对待,它虽然允许小的不平等,但在总体上是平等的。
沃尔泽为设计区别对待差异的体制提供了重要的原则,即相对自主与减少支配,但他的复合平等观产生了以下问题:如果一种社会物品被几个(而不是所有)族裔群体赋予同样重要的意义,但该物品仅为那个力量强势的族裔群体所垄断(按沃尔泽的观点,这是允许的),其他弱势的族裔群体忍受不平等,这难道是小的不平等吗?在垄断某种社会物品的族裔群体内部,如果垄断者仅是该群体的少数几个人,那么其他族裔成员也该忍受不平等吗?一个处处充满垄断和不平等的社会,真能实现更大的平等吗?
(四)差异的政治:赋予族裔少数群体特殊权利
显然,沃尔泽的设想并没有为族裔少数群体提供切实的保护,激进多元文化主义者是不满足于此的,他们要求通过赋予少数群体特殊的权利来保护差异,这就是激进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的政治”。
作为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美国的玛丽恩·杨是真正主张并强烈要求实行差异政治的学者。她批判了分配正义理论,认为正义不能只关注社会物品的分配,还应该关注参与、协商与决策的制度正义和程序正义问题。在她看来,“正义的社会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满足他们的需要并实现他们的自由,因此,正义就要使所有的人都能表达他们的需要”。(23) 因此,必须为少数群体提供畅通的参与和表达渠道。她还进一步批判了传统自由主义有关普遍公正的理想,指责这种理想全然不顾公民的独特性与差异,认为造成压迫的不是群体差异,而是普遍公正理想所要求的同质化。在杨看来,传统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政治要求以相同标准对待所有人,这种形式平等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带来同化,反而强化了群体内聚力和团体间的分化;不仅没有消除差异,反而扩大了差异。如果继续坚持忽视差异的形式平等,那将导致少数群体的严重压抑,这样,普遍公正的理想不过成了压抑弱势群体的借口,最终带来的只能是对少数群体的排斥、隔离和压制以及权威主义等级制的合法化。
针对这些危险,杨提出用“差异政治”来取代普遍主义政治。她强调,不能再把族裔群体的认同与差异看做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是要将族裔差异纳入公共政治领域。一方面,要承认少数群体的文化身份与多数群体具有相同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根据族裔群体的文化特点进行区别对待,赋予少数群体差异的公民身份和特殊的文化权利,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政治经济生活。为保证少数群体权利的实现,杨在具体政策领域提出了“群体代表权”的主张,要求“一个民主的公共制度应该为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有效的承认机制和独特的代表制度……群体对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策有最后投票权”。(24)
杨的差异政治观得到了不少人的欢呼和支持,然而即使在多元文化主义内部,特殊权利的主张也受到了担心和质疑。有人认为,这种特殊权利使得少数群体无法确认:他们取得的成功究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能力还是因为他们特殊的族裔身份?有人则担心,给少数群体更多的代表权是否会导致一种反向的歧视,即对多数群体的歧视?还有人甚至尖锐地指出,赋予少数群体特殊权利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就肯定了少数群体的低劣?对于这些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内部一直争论不休。大体上,赋予特殊权利的支持者回应道:少数群体的劣势地位是历史造成的,赋予其特殊权利是为了弥补历史上遭遇的不公正,并为他们提供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五)应对差异的“后帝国主义”宪政构想
正因为特殊权利的政策主张似乎过于尖锐,遇到了不同方面的质疑甚至极力抵制,一些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开始另寻出路。作为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加拿大政治理论家詹姆斯·塔利从杨的差异政治回归到泰勒的平等承认的政治。但与泰勒不同的是,塔利不是关注为什么要承认文化差异这个态度问题,而是试图把“文化承认之政治”运动中提出的要求纳入到宪政框架中,通过一种“后帝国主义”的宪政制度来承认和调适文化差异。
塔利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论批判了现代宪政主义,(25) 认为现代宪政主义试图打造“一致性之帝国”,具有浓厚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由于它过度强调普遍性与一致性,一味用所谓的进步标准来同化其他规范,扼杀了少数民族及原住民的文化尊严。(26) 因此,现代宪政主义并不能调适和包容文化差异。
那么,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宪政安排呢?塔利并不打算重构一个全新的宪政体制,而是试图恢复“古宪法”传统,即普通法宪政主义。与现代宪政主义预设一致性文化不同,普通法宪政主义尊重文化差异,愿意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尤其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古宪法中三项弥足珍贵的常规:相互承认、文化延续以及同意。(27) 其中相互承认意味着尊重文化差异;文化延续是指重视各种文化传统及惯例的延续性;而同意是指所有涉及当事人利益的规定都应通过协商对话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塔利认为,普通法宪政主义及其三项常规完全可以用来指引后帝国主义时代(塔利也称之为“文化歧异性时代”)的宪政主义。(28)
在后帝国主义宪政构想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在三项常规的引导下展开以相互承认为主题的宪政对话并形成宪法,随着时间推移,宪政上的承认与结社形式也相应改变。在这种宪政主义中,宪法是某种承认和调适文化差异的形式,它“理应被理解为一种行动,一种跨越文化藩篱的对话,在对话之中,当代社会中文化背景不同的主权公民们遵循着相互承认、同意与延续等三项常规进行长期的协商,试图对宪政结合体的方式达成协议”。(29) 据此,宪法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连串的持续协商与协议。这种宪政主义的主要目标除了承认和调适文化差异之外,也要调解表面矛盾的两种基本善:自由与归属。前者是“企求从自身文化及地域之生活中解放出来,将自己从自身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后者是“企求归根于某个文化及某块土地,企求能在这世间找到一个归宿”的愿望。(30)
塔利并不是诉求特殊权利,而是在诉求族裔群体间平等的、持续性的宪政对话,他的宪政构想预设了族裔群体的平等。可以说,这种构想是未来多元文化并存的一种理想形式。这种宪政理想的问题在于,没有回答如何使当前处于劣势的族裔少数群体获得平等对话的机会。塔利似乎解决了未来的问题而不是当前的问题,并没有化解杨的特殊权利方案所带来的危机。
(六)政治一体内的文化多元:协调公民权利与少数群体权利
试图既保护杨所提出的特殊权利又遵循当前的宪政结构(而不是塔利那种宪政构想)的杰出代表,是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作为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者,金里卡努力在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进行调和,致力于在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实现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
在金里卡看来,首先,族裔少数群体在国家制度中遭遇的不平等是保护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现实要求。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制度总会促进某个族裔群体的文化认同,导致其他族裔群体文化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影响到这些群体的机会和利益。要在族裔群体间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公正,必须赋予少数群体特定的权利以弥补其在制度上遭受的不平等环境。也就是说,“真正平等的要求不是相同的对待,而是差异的对待以便于调和这些差异的需求”。(31)
其次,个人在文化团体中的双重身份为保护族裔少数群体权利提供了一致性基础。(32) 在金里卡看来,传统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人权利至上。要在自由主义的宪政框架内实现族裔少数群体权利,就不能将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团体权利对立起来,而必须寻找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存在于个人的双重身份当中。个人既是民族国家的公民(公民身份),又是特定文化团体中的成员(文化成员身份)。团体文化对个人至关重要,要实现个人权利,就必须承认其文化成员身份,尊重和保护他所熟知的团体文化。
再次,族裔少数群体权利存在边界,必然要求处理好个人、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金里卡看来,存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团体权利:一种是内在限制,意指团体以保持文化纯洁性为由限制成员的自由,这对个人自由是一种威胁;另一种是外部保护,意指为了保护团体免遭由国家制度造成的破坏而赋予其更多平等的机会。(33) 族裔少数群体权利应该是一种外部保护,它既要促进族裔群体间的公正,阻止一个群体压迫另一个群体,又要保护族裔群体内部的个人自由,防止以团体名义压制个人。此外,保护族裔少数群体权利还应以维护国家一体为前提。简言之,个人权利优先于群体权利,群体权利是个人权利的重要补充,它可以防止来自国家层面的破坏,同时又不能对国家统一造成冲击。
最后,在如何实现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上,金里卡主张“要把少数群体权利的诉求放在民族国家构建政策这样一种环境中来考虑,把它看作是对国家式民族国家构建的反应”。(34) 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实行的政策对少数群体造成了威胁和冲击,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为使少数群体免遭现实的或潜在的不公正待遇,应将少数群体权利理解为一种保护机制,这是应对国家对少数群体施压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由于不同的少数群体面临不同的威胁,且他们的权利诉求是多样化的,因此,少数群体权利不能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权利内容,而应理解为一项权利原理,它根据不同族裔群体的文化特点而赋予其相应的特殊权利。金里卡进一步分析了把民族国家构建与少数群体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现实方法,包括一些国家正在实行的移民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民族联邦制,这些实践是在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进行的,采纳了有助于少数群体参与的更为开放的包容性民主。
由此可见,金里卡一直是在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与社群主义和激进派的结果平等之间进行调和,主张在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实现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在国家一体的前提下实现文化多元。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他的主张既触及主流群体的利益,又能有效地对少数群体的诉求作出回应,而且,这些理论主张符合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的当前实践,因而在西方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受到的批评与回应
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不仅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保守派的质疑和批评,(35) 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批判与挑战。
(一)保守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出的批评
针对上述多元文化主义者为应对差异而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尤其是针对少数群体权利问题,有些保守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表面上承认文化多元,也表示应该给少数群体一些关照,但实际上仍然秉持白人优越论和等级论观点,有的保守派则公开表示不满和批判。
阿尔文·施密勒从“揭露”多元文化主义的“虚假面孔”出发,从理论内涵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36) 在理论内涵方面,首先,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有关文化平等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将导致无法拒绝一些低劣的文化;其次,多元文化主义误将文化运用到所有社会群体中,因而无法区分国家的文化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亚文化与反文化;再者,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不同的肤色代表不同的文化也是错误的,因为文化是靠相互交往而不是靠生物遗传来传承的。他据此指责多元文化主义歪曲历史,鼓吹非洲中心主义,否定西方文明,主张双语运动和肯定性计划,诉求文化相对主义并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如同特洛伊木马,已经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如果不加阻止,美国将遭致更为深重的灾难。施密勒的分析无疑看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内部缺陷,不过他不是要弥补这些缺陷,而是完全加以排斥。他对多元文化主义所揭示的当前西方社会中的紧迫问题不仅未加以重视,反而视多元文化主义如洪水猛兽。
阿瑟·施莱辛格从维护国家一体和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可能助长国家分裂表示了极度的忧虑和激烈的批判。他认为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以美国信条为模板重铸了各族裔群体,因而具有惊人的化解力。可是,美国熔炉正面临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一方面,他认为这种挑战是以历史为武器,从败坏美国的历史开始的;另一方面,他指责多元文化主义有关差异政治和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主张过分彰显了族裔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个性,这将极大地影响美国的国家认同与凝聚力。施莱辛格坚决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认为它是依赖于“对种族的狂热崇拜”,这种崇拜“夸大了人种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别,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恨与对抗,并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已经宽得吓人的裂痕。而结局是自怜和自我同族聚居”。(37) 因此,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并担心它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和部落化。为避免这种危险,他认为必须要有一种超越族属认同的认同,即塑造美国国家认同的美国信条。
笔者认为,施莱辛格对国家认同、政治稳定和政治一体的强调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认为只有坚持美国信条才能确保政治一体的观点,不仅具有强烈的美国中心论色彩和狭隘的白人优越论情感,而且对影响政治一体的因素作了过于简单的分析。此外,他也误解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夸大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危险。
(二)来自多元文化主义外部的批判与回应
在多元文化主义外部,一些保守主义者对差异政治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艾伦·布卢姆的批判是从作为差异政治思想之基础的文化相对主义开始的。在他看来,文化相对主义鼓吹一种文化并不比另一种文化优越,不应有“民族中心论”观点,对所有文化要一视同仁。他认为这种观点是美国教育灌输的一种道德要求,它不过是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他指责道:文化相对主义意味着,“不应当让人们去寻找人类的本然之善,就算找到了也不应当加以推崇,因为这种发现也伴随着对恶和相应的鄙视态度的发现”。(38) 他认为相对主义已经用一种“开放”思想战胜了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然权利”思想,并着重批判了这种“开放”,指责这种开放是一种冷漠的开放,(39) 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别人。这种大开放的结果是大封闭,它在事实上也导致了美国精神的封闭。
针对文化相对主义保存少数群体的文化个性并尊重“少数”群体的观点,布卢姆批判其颠倒了美国立国原则中尊重少数的意图(在他看来,立国原则中少数是宗派,并不是好事),(40) 把立国原则视为障碍,试图推翻民主政治中的多数原则,鼓吹由少数派和族群组成的国家,其最终目标是企图削弱占统治地位的优势派。
弗朗西斯·福山响应了布卢姆的批判,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41) 他极力为自由民主制国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辩护,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恰恰是作为自由民主制的基石——自由和平等的原理——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而不是原理本身的内在缺陷。在福山看来,美国正是因为其白种人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才得以称霸世界,所以这种文化比任何其他族裔文化都更为优越。这种西方中心论和民族中心论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强烈批判和回应。
塞缪尔·亨廷顿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有力批判者,他担忧其他文明的复兴会导致西方文明的衰弱,认为界定美国国家特性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正面临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必须立即解决美国国内的国家认同问题,否则美国无法与其他文明展开竞争。(42)
四、分析与讨论
从上述差异政治思想的论争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主要缘于如何处理“公共性”与“差异性”(或者说“一元”与“多元”)之关系的问题而产生的。以公共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为主线,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以下四对关系:
(一)共同文化与差异文化的关系
多元文化主义者强调文化多样性并要求给予每一种文化同等的意义和地位,尤其在激进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比另一种文化优越;与之相反,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者强调主流文化的价值与规范。前者陷入了相对主义的陷阱;而后者把多数群体的主流文化等同于共同文化和共同价值,忽视了其他积极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种自我封闭的态度阻碍了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因此,必须妥善处理好共同文化与差异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政治共同体需要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这种共同规范并不等同于多数群体的主流规范,也不是通过将主流规范强加给少数群体所形成,它应该来自于不同族裔群体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交流和对话,达成共识并沉淀为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对此,多元文化主义者拉兹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在承认一种政治生活中永远都会存在着若干文化群体的同时,也要求确立一种共同的文化……所有文化群体的成员将不得不接受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和公约,因为它们可以有效地促使人们参与资源竞争,参与保护集体和个体的政治利益。”③另一方面,所有族裔文化(包括多数群体文化)在法律意义上都应该是平等的。
(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
多元文化主义者要求把对待文化差异的问题纳入公共领域,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文化是个人的选择,应该是私人领域的事情,把个人与其背后的文化割裂开来,忽视了团体文化对个人及其选择的影响和意义;在事实上助长了主流群体的文化,贬抑了少数群体的文化。在此意义上,前者对后者的批评是合理的。以多元文化主义而言,虽然诉诸公共领域是正确的选择,不过他们在究竟该把哪些文化差异纳入公共领域的问题上是含糊不清的。并非所有“群体”间的文化差异都应该成为政治问题,也并不是所有文化差异问题都要诉诸政治手段。多元文化主义所指涉的“群体”文化差异应该限定在以种族、民族、宗教、移民和土著居民等为基础的、具有族性特征的族群上,至于其他文化团体(协会、社团)之间的差异,通常不必纳入政治领域。同时,对这些族群的各种要求也应区别对待:对于诉求族裔文化承认与宽容,平等对待或“差别对待”,以及少数群体特殊权利的问题,理应是公共领域的问题。
(三)公民权利与少数群体权利的关系
多元文化主义者大多要求赋予少数群体以特殊权利,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个人权利至上,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对特殊权利的主张大加鞭挞,认为这是一种反向的歧视(对多数群体的歧视),甚至是一种倒退。
在处理公民权利与少数群体权利之关系的问题上,需要从个人的双重身份出发。一方面,个人是国家公民,应该具有基本一致的公民权,这种公民权塑造了国家认同。正如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言:“民主国家需要有一个公分母,一种超越种族的忠诚,这种忠诚将各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集团混合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超越了族属认同的认同。”(44) 另一方面,少数群体权利是保证少数群体平等机会的条件。大部分多元文化主义者之所以诉诸特殊权利,不仅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为少数群体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生活提供条件。当然,也有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将特殊权利进一步上升为自治权(一定程度的自治也是合理的),甚至自决权,这对国家一体造成了冲击。对此,金里卡的论述对公民权利与少数群体权利的调适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四)政治一体与多元共存的关系
一些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不仅要求特殊权利,而且以族裔差异为理由要求民族自决权,甚至提出分离主义要求,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团结统一造成了威胁。这种主张不仅为大部分多元文化主义者所拒斥,更被外部批评者视为拒绝多元文化主义的理由。尽管存在这种激进派,多元文化主义内部仍有许多人把他们的文化多元要求限定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公共秩序的范围之内。因此,不能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一概都不强调政治一体,实际上他们也在努力调和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矛盾。
当然,文化多元必须是政治一体前提下的多元:国家为族裔群体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保障,国家认同是族属认同的基础;没有国家认同的族属认同是脆弱的,同样,没有统一公共秩序的文化多元将是混乱的多元。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仍需处理好国家认同与族属认同的关系,以及公共利益与团体利益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国家政治一体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和平共存与共同繁荣。
注释:
① 多元文化主义流派划分问题,参见常士訚主编:《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本文采纳了该书的流派划分方法。
② 参见Barbara Saunders and David Haljan eds.,Whither Multiculturalism,Brussels: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03,p.24。
③ [英]C·W·沃特森著、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④ 参见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76—77。
⑤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Return of the Citizen: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in Ronald Beiner,ed.,Theorizing Citizenship,Alba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302.
⑥ Will Kymlicka,Liberalism,Community and Cul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75.
⑦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袁建华译:《论宽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⑧ 参见Amélie Oksengerg Rorty,“The Advangtage of Moral Diversity,”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Volume 9,No.2(1992)。
⑨ C.West,“The New 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in Simon During 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utledge,p.203.
⑩ 这是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玛丽恩·杨的观点,引自常士訚主编:《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第344页。
(11) 泰勒将“普遍主义政治”称之为“尊严政治”,强调这种政治是从与荣誉相关的等级制政治向人人享有同等尊严的政治转化而来的。
(12) 泰勒认为,差异政治有机地脱胎于普遍主义政治,是从普遍主义政治中派生出来的,但差异政治把普遍平等的原则应用到对独特性的承认问题上,要求所有的独特性都应得到平等的尊重和承认。
(13)(14) [加]查尔斯·泰勒著,董之林、陈燕谷译:《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5页。
(15) [加]查尔斯·泰勒著,董之林、陈燕谷译:《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321页。
(16)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袁建华译:《论宽容》,第3页。
(17) 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袁建华译:《论宽容》,第2—5页。
(18) 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袁建华译:《论宽容》,第10—11页。
(19) [法]阿兰·图海纳著,狄玉明、李平沤译:《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2页。
(20)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褚松燕译:《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1) 支配性的善是指:一种善在所有分配领域都具有支配和决定性作用。如果一个人拥有这种善,他就可以凭借这种善去支配大量其他物品。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褚松燕译:《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第4页。
(22)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褚松燕译:《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第20页。
(23) 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34.
(24) 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184.
(25) 参见[加]詹姆斯·塔利著,黄俊龙译:《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16页。
(26) 参见[加]詹姆斯·塔利著,黄俊龙译:《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第43、63—71页。
(27) 参见[加]詹姆斯·塔利著,黄俊龙译:《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第121页。
(28) 参见[加]詹姆斯·塔利著,黄俊龙译:《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第192—193页。
(29) [加]詹姆斯·塔利著、黄俊龙译:《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第192页。
(30) [加]詹姆斯·塔利著、黄俊龙译:《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第33页。
(31) 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p.113.
(32) 有关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建构逻辑,参见吕普生:《多元文化主义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理论建构》,《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33) 参见Will Kymlicka,Finding Our Way:Rethinking Ethnocultural Relation in Canad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70。
(34) [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5) 保守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虽然也可看做是多元文化主义内部的分支流派,但从根本上讲,这个流派是虚假的多元文化主义,他们的主张大都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因此,本文把他们与多元文化主义外部的批评者放在一起。
(36) 参见Alvin J.Schmidt,The Menace of Multiculturalism:Trojan Horse in America,Westport,Conn.:Praeger,1997。
(37) [美]阿瑟·施莱辛格著、马晓宏译:《美国的分裂》,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17页。
(38) [美]艾伦·布卢姆著、战旭英译:《美国精神的封闭》,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39) 在布卢姆看来,开放有两种形式:一是冷漠的开放,二是激励探索欲望的开放。参见[美]艾伦·布卢姆著、战旭英译:《美国精神的封闭》,第6页。
(40) 布卢姆解释了立国原则中指称的“少数”:在美国缔造者的立国原则中,“少数一般来说不是好事,他们跟宗派差不多,是不顾公益的自私团体。”尽管如此,美国缔造者并不打算压制宗派,对于通过教育形成统一的、同质性的公民社会也不抱希望,所以他们建立了一种精巧的机制,包容宗派但让他们相互抵消,使人们能够追求共同的利益。参见[美]艾伦·布卢姆著,战旭英译:《美国精神的封闭》,第6页。
(41)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42)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43) J.Raz,“Multiculturalism:A Liberal Perspective”,Dissent,Winter 1994,pp.67—69.
(44)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译:《公民与国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标签:政治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文化差异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