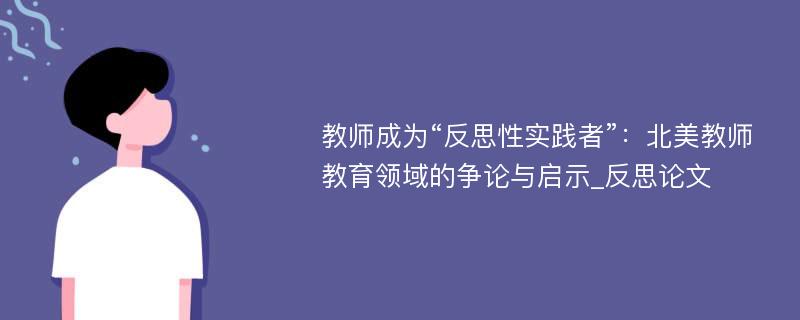
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北美教师教育界的争议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师论文,北美论文,教育界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前哲学教授唐纳德·A·舍恩(Donald A.Schon)在批评技术理性的基础上阐述了他的“反思性实践”思想及“反思性实践者”概念。舍恩主张包括教师在内的实践者要从技术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实践中反思和探究,树立“反思性实践者”的专业形象。之后,在行动科学和教师教育领域相关研究(尤其是对教师反思的研究)的推动下,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培养教师的反思意识与能力、提升教师实践品质,成为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北美教师教育界围绕舍恩的“反思性实践”理念及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这一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也一直在延续。我国学者洪明曾对舍恩的“反思性实践”思想及其相关争议进行评述。[1]本文集中讨论围绕教师专业形象——“反思性实践者”的相关争论,以期对重构我国教师形象、改革教师教育提供参考。
一、舍恩: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
1983年,舍恩在分析建筑师、设计师、管理者等专业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对技术理性视野下的“理论——实践”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技术理性过于关注技术的有效性,忽视了实践的情境性,最终造成了技术与实践之间的裂缝。舍恩把真实的实践情境分为两类:一是“坚硬的高地”,这里可以直接用外在的理论、技术来解决问题;另一是充满着“复杂性、模糊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的“湿软的低地”。其中,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不起作用,实践者借助的是“行动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和“行动中认识”(knowing-in-action),实践者的实践是“以一种不确定性和艺术的方式努力探究的过程”。[2]舍恩指出,绝大部分实践都是处于“湿软的低地”中的“反思性实践”。舍恩先后出版了《反思性实践者——专家如何在行动中思考》(1983)以及《培养反思性实践者》(1987)两本著作,明确了“反思性实践者”的概念。
(一)舍恩对“反思性实践者”的界定
1、“反思性实践者”的典型特征是“行动中反思”
舍恩指出,在复杂的实践情境中,实践者不是依赖现存的理论与技术去采取行动,而是努力去理解情境、主动建构问题。实践者总是一边行动一边思考目标和方法,这便是“行动中反思”,其基本结构是“反思性对话”。所谓“反思性对话”,即实践者不断地根据问题情境及行动结果调整自身的思路和行动。正是借助于反思性对话,实践者得以不断探究问题情境和解决办法,从而创造出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实践工作者重新框定问题、解决问题的努力,将会衍生出新的行动中反思。这个过程即评估、行动、再评估的依次循环,动态发展。[3]舍恩认为,“行动中反思”使实践者在一些情境中能够相当好地处理不确定、不稳定、独特的价值冲突,使实践者在实践中变成研究者,并从固定的理论和技巧中解脱出来,构建一种新的适用于特定情境的理论。因此,他说:“对反思性实践者而言,‘行动中反思’是实践的核心。”[4]
2、“反思性实践者”是实践情境的研究者和实践知识的创生者
舍恩认为,当实践者进行“行动中反思”时,就会成为实际情境中的研究者,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行动中的知识”(实践性知识),这种知识不是普遍的技术、原理,而是“处于专业能力的传统边界之外的”[5]、直觉的、“默会的”“知识”。“行动中的知识”是实践者在专业实践活动中对活动进行反思而形成的,是由“反思性实践”活动来澄清、验证和发展的,同时又通过实践者的“反思性实践”活动来体现的。“行动中的知识”是一种案例性知识。由于实践情境及对象的不确定性,实践者所做的工作及对象就成为一个个独特的“个案”。当实践者经历了为数众多的个案及其差异时,他建立出一个囊括了各种实例、形象、理解和行动的全面性“资料库”。每一次行动中反思的经验都让他的资料库更丰富。随着实践者处理的同类型案例越来越多,他的实践性知识也就不断丰富。
舍恩的观点确认了实践者是实践情境的研究者,他们有能力改进自身的实践和生产自己的实践性知识。由于顺应了“教育界最近20多年所追求的不脱离现实情境、在持续的实践中改进的需要”,[6]舍恩的观点很快为教育界所接受,大大推进了教育界对反思的重视。舍恩的著作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理念在教学与教师教育领域广泛传播。
(二)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意义
1、消解教育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分离
舍恩关于实践者在“行动中反思”的阐述重新解释了反思与行动的关系,并进而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强调以整体的方式把握真实教育情境中教师的思维和行动,强调教师内在力量(反思、意识、经验、信念等)对于改善自身教育实践的价值。反思作为实践的限定词,凸现了教师的主体性,突出了教师的个人经验和反思能力在沟通公共知识与个人实践性知识方面的功能。以“反思性实践者”来概括教师的形象,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理解教育实践性质的基本态度:摆脱那些二元对立的无休止争论,突出教师的主体性,依靠教师自身的力量来融通教育实践中长期分离的两个领域——“理论”与“实践”。
2、打破教育知识的精英主义和专家权威
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概念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教师有能力对自己的教育行动加以省思、研究和改进,有能力创生自己的教育知识。它摒弃了技术理性视野中对“知识”、“实践”的看法,认可教师经验及反思的价值。而且,在表达“思与行合一”这一基本含义上,舍恩倡导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反思性实践者”概念:凡是实践者,都应该是反思性实践者。[7]如果说杜威的“反思性思维阶段说”为反思披上了科学化的外衣,那么,20世纪下半叶舍恩提出的“反思性实践者”概念,则使反思具备了一种“平民化”的特质:教育反思、教育研究既不是专家的专业,也不是教师的专业,而是所有实践者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反思被看成一种植根于教师内心的、致力于不断丰富与完善教学实践的力量。它彰显了实践者的主体价值,弘扬了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
二、舒尔曼、范梅南等学者对舍恩观点的质疑
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教学和教师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许多实践者和研究者迅速聚集到它旗下,阐发它的内涵并据此改革教师教育;而另一方面,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也随之出现。试举两例:
(一)舒尔曼等学者:“技术理性”立场的批判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学和教师教育专家舒尔曼(Shulman,L.S.)和亚利桑那大学教育哲学家范斯特马切尔(Fenstermacher,G.D.)等学者对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及其蕴含的“行动中反思”的实践认识论持批判态度。1987年4月,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加拿大教师教育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eacher Education)、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eacher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合举办名为“21世纪的教学指导和教师教育:培养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研讨会。会上,舍恩作了“促进反思性教学(Coaching Reflective Teaching)”的主题发言,其中,他对实证主义的学校知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阐发了“行动中反思”与专业实践及教师教育的关系。他的发言立即引发了舒尔曼、范斯特马切尔以及来自加拿大教师协会(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的吉里斯(Gilliss,G.)等人的质疑。[8]其中,舒尔曼和范氏的质疑颇具代表性。归纳起来,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客观知识、技术是教师行动的基础和前提
在会上,舒尔曼以“教育中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危险”(the Dangers of Dichotomous Thinking in Education)为题,对舍恩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9]他认为,舍恩的思想充满了“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体现在舍恩对“学校知识(客观知识)”和“行动中反思”、“技术理性”和“艺术性”、“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等的二元划分上。他颇带讽刺地说,这种二分法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方式,目的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在学术争论中划清界限。他指责舍恩将客观的理论、技术与实践性知识对立起来,将实践性知识看成是构成专业判断核心之基础,从而夸大和过分强调了实践性知识在教师实践和教师培养中的作用。他认为,实践性知识是教师教学所具有的“特征”,而不是舍恩所说的“专业实践的核心”;对专业教师的培养来说,实践性知识并不充分。他主张要将实践经验的反思和理论理解的反思融合起来。
在强调教师掌握确定性知识这一点上,范斯特马切尔与舒尔曼的观点是一致的。范氏认为,教学的前提是教师拥有相应的知识,“教学必然始于教师对所要教的东西以及如何教的理解。然后,教师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为学生提供具体的学习机会,教学以教师和学生达成新的理解而告终。”[10]范氏坚信教师教学行为背后有一个确定的知识基础,教师依此而行动。“教师必须学会使用知识基础来提供选择和行动的基础。”[11]因此,教师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教师根据事实、原则和经验来合理地推理他们的教学并且熟练地履行教学任务。这与舒尔曼在《知识与教学:新的改革的基础》一文中所表达的“教学法推理”的观点颇为一致。[12]范氏也指责舍恩对“科学”在“反思性实践”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他认为,离开科学和理论的实践者是注定要处于奴役状态的。
2、研究者是教育知识的生产者,教师是知识消费者
范斯特马切尔对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概念的质疑主要针对的是这样的问题:教师的反思是研究吗?教师能生产教育知识吗?他针对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概念所表达的“教师有能力对自己的教育行动加以省思、研究和改进”的观点,认为舍恩对“研究”一词的理解过于宽松。他认为“研究”与“实践”是两回事,研究者是运用科学原则生产经受得起检验的科学知识的人,而实践者则是在实践中运用或使用这种知识的人。[13]对舍恩提出的实践者也能在实践过程中生产知识,范氏认为不能把这类知识看成是科学的知识,教师或许会运用科学的成果或“洞见”,但不会生产新的科学知识。
可见,在范氏看来,研究指的是生产科学知识的活动,是专家们的事,教师的任务是从事教育实践,他们与研究无缘。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是教育科学知识的生产者,而教师则是这些知识的消费者;教师的“反思”不是研究,教师经由实践和反思产生的知识缺乏科学性。范氏关于研究和知识生产的精英主义和权威立场,与舍恩的观点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此不难看出,舒尔曼和范斯特马切尔在为“技术理性”辩护。他们从技术理性下的二元论思维来看待舍恩所阐述的“行动中反思”和“实践性知识”,坚持确定性的公共知识、技术及其生产过程的权威性,认为这些知识经专业研究者生产出来以后,就成为教师行动的基础和依据;教师在实践中产生的诸如“实践性知识”、“洞见”、“艺术性”、“行动中反思”等,是建立在既定理论和技术的确定性之上的、对教学起“点缀”和“辅助”作用的东西,是教学的润滑剂,它们不具有科学性,也不能登上教育科学知识的大雅之堂。教师归根结底只能是使用专家生产的知识来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技术员”。
(二)范梅南:现象学视角的质疑
作为现象学教育学的代表人物,加拿大学者范梅南与舍恩一样尖锐批判“技术理性”,认为“技术理性”将实践者看成“工具性问题解决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不赞同舍恩对“反思性实践者”在“行动中反思”的阐述。
1、真实教学情境中教师无法做到“行动中反思”
范梅南认为,舍恩所提出的“行动中反思”与教学的真实情境不符。他从具体的教育场景出发,认为反思是在行动前或行动后完成的,在真实的课堂情境中,教师无法“分身”,没有时间或并不会真正反思实践中的问题,而只能“不假思索地”、“直觉性地行动”。他根据杜威对反思的定义,认为“思维就是在行动和行动后果之间准精而谨慎地建立联系的机制”,“在教育学领域,反思含有对行动方案进行深思熟虑、选择和做出抉择的意味。”[14]因此,他认为“行动中反思”是“暂时停止参与”、“从课堂情境中撤身出来对下一步需要做什么进行反思……,是将所发生事情的所有可能性解释、对意义的各种可能性模式的理解、对其他行动途径的考虑、各种后果的权衡、必须要做什么的选择以及后来真正所做的事情都考虑进来”,[15]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面”、“深入”、“系统”地分析。根据这一理解,他强调:教师在课堂上只能是“非反思的”,“行动中反思”是难以做到的。他说:“教学作为一种实践行为的繁忙性质和紧迫处境使得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活动或交往活动中,教师在严格意义上只能是‘非反思的’,教师在课堂上一定总是在现场行动,他们无法撤身推迟行动,无法先反思这种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及每一种可能的后果……”。[16]
2、实践中的教师采取的是“直觉性行动”
范梅南认为,反思在具有紧迫性、偶然性的实践情境中是难以实现的,造成行动中反思的真正困难在于课堂生活具有偶然性、动态性、不断变化的特征,每一时刻、每一秒钟都有其特殊的情形。他说:“在我们与孩子们的教育生活中,我们以一种下意识的方式主动地立刻参与,只是到后来才进行真正的反思。当我们在一种情境中遇到一个孩子需要我们采取行动时,通常的经验是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做了什么之前我们就已经行动了。”[17]“如果教师总是想要批判性地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做这些事情,那么必然会变得矫揉造作和优柔寡断。”[18]在质疑舍恩的“行动中反思”的认识论的基础上,范梅南提议建构一种新的实践认识论,那就是“作为行动的教育敏感性和教育机智的实践认识论”。他认为,与“理论优先”或“实践优先”的选择相比,教育敏感性和教育机智是一种瞬间行动的智慧,它“在教学的行动中实现自身”。[19]
实际上,范梅南之所以认为“行动中反思”不可能,主要源于他的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视角和对反思的理解。范梅南将现象学思想用于教育研究,尤其关注具体的教育情境本身的意义。用他的话说,就是探讨“运用现象学这一追溯人的最原初体验的方法,寻求教育生活本身的意义。”[20]他的现象学研究起始于具体情境,是“对嵌入在这个情境中的一个典型意识节点的分析、阐释和说明”。[21]研究是为了获得对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本质或意义的深刻理解(而舍恩的重点在阐述思与行的关系);另外,在对反思的理解上,范梅南参照杜威对反省思维的论述,认为反思就是系统化的、全面的思考,“行动中反思”就是要“停下来思考”,这样便导致范梅南夸大了“直觉行动”和“行动中反思”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由此认为舍恩的“行动中反思”是站不住脚的。
三、比较与启示
在各种观点的交锋激荡中去理解和思考教师教育理论,是我们重构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不可回避的重要路径。[22]虽然由于理论基础不同、研究视角各异,上述学者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但他们的争论对重构我国教师专业形象仍然有重要启示。
(一)弘扬教师的主体性,关注教师改进教育实践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教育和教师培训把教师看成是理论的接收者,教师教育就是让教师掌握教育理论或新的教学模式、方法,然后到实践中去应用。教师是专家生产的教育知识的消费者,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被漠视。舍恩和范梅南对技术理性视野下将教师看成“工具性的问题解决者”持反对态度,主张弘扬教师的主体性、关注教师改进自身教育实践的能力,强调教师教学实践行为中内隐的、动态的、能动性的方面,强调教师对自身实践的把握与洞察能力。从理解教师工作的“临床”和现场的特点来把握教师职业的内涵,就会发现,教师就是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不断建构和提升自身经验的“反思性实践者”。虽然对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的具体内涵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但是肯定教师经验的价值、认可教师自身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成为教学和教师教育领域中的共识。这是我们在重构教师专业形象时必须要考虑的。
(二)强调实践性知识的同时不能忽视教育理论的价值
目前,在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性正得到广泛强调,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教师在实践情境中形成的、内隐于行动中的“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但研究者们在强调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对其教学行为的“决定性”、“支配性”作用的同时,教育理论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作用却被严重忽视。在当前对教师专业发展热火朝天的研究中,教育理论处于一种受批判和失语的状态。在上述争论中,舒尔曼、范斯特马切尔从技术理性的立场出发,认为教师掌握教育的原理、技术是首要的,教学实践是对这些原理与技术的应用,是一种技术性、操作性的活动,在这样一种技术性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洞见”只不过是一种点缀。这种观点无疑有很大局限。但是,舒尔曼及范斯特马切尔的质疑至少提醒我们:教学和教师教育在建构教师专业形象、改革教师教育时,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他们实践中动态的、艺术性的方面固然重要,公共的教育知识——教育理论与技术也应该被考虑在内,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