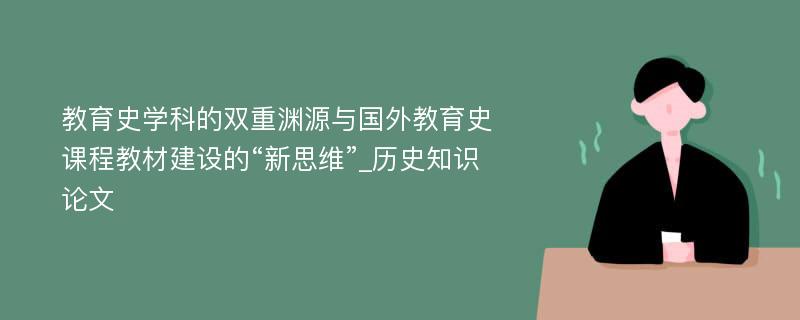
教育史学科的双重起源与外国教育史课程教材建设的“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史论文,新思维论文,起源论文,学科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8)01-0013-05
在我国,自有师范院校以来,外国教育史与教育学、中国教育史、心理学以及教学法一样,一直是教师培养的重要科目。在师范院校本科教育专业的培养计划中,外国教育史则更是作为一门重要的科目而占有特殊的地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也因为教师教育体系的剧烈变革所产生的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以及教育知识的增长和教育学科的分化,外国教育史课程建设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相形之下,外国教育史在课程定位、教学目标以及教材建设等方面还缺乏相应的改革,这种状况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今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一
我国自有高等师范院校至今,不过百余年。在其中的50多年中,由于高等师范院校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因此,教育史(包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一直是高等师范院校各专业的修习科目。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不仅把教育理论与应用教育史作为优级师范学堂各专业“一概通习”的科目[1](P692-699),而且把中外教育史列为经学科大学的选修科目[2](P585)。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以前,教育史既是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的重要课程,也是其他各专业的必修科目。[3](P838-890)。
在高等师范院校内部,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教育系科则主要承担为中等师范学校培养教育学师资的职能。为了履行这个职能,在教育系科的教学计划中,通常都把包括教育学、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在内的基础科目置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教育学原理、教育史与心理学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教育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的主干。
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剧烈变化,中等师范学校在相当广泛的区域急剧萎缩,实行多年的由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院校构成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变为由师范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院校构成的二级体系。中等师范学校的快速消亡,使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科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也由此对教育系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一方面,同样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高校学生就业的基本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实行多年的学生“分配”变成了学生“就业”,学生从过去被动地接受高校或用人单位的安排,变成了学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过去曾经实行的对师范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一些限制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明令撤销或者在实践中名存实亡。在这样的情势下,教师职业就不再是师范院校毕业生的唯一或主要的就业选择。学生就业结构的多元化,使师范院校教育系科原有的培养目标以及课程设置同样面临着危机。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各师范院校教育系科先后对原有的培养计划进行了修订。总体的方向是:第一,增加新知识和新科目,特别是增加了与教育实践关系更为密切的知识内容;第二,扩大一些已有知识内容在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比重;第三,不同幅度地压缩了包括教育史在内的基础课在教学计划中所占的比重。在相当多的师范院校教育系科的教学计划中,外国教育史的课时数一减再减,甚至已经减少到了难以进行系统讲授的地步。
面对外国教育史课程在师范院校教育系科本科教学计划和教学实践中的“境遇”,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外国教育史教学科研人员不断著文,分析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科研面临的形势,分析外国教育史学科面临困境的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方略。① 从现有文献看,尽管论者力求客观分析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现状,但或者是情绪化地指责外界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的轻视,或者仅仅从外国教育史课程安排和课程教学的实践着眼,而缺乏从总体背景出发对外国教育史课程教学进行系统的深层次的反思。
二
学者们在梳理教育史学科的变革历程时,通常都非常强调它与近代教师教育发展的关系。确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教育史学科的兴起都是与教师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法国和美国,早期较有影响的教育史著作包括孔佩雷(又译作康帕亚,G.Compayré)的《教育史》(1883年)、孟禄(P.Monroe)的《教育史教科书》(1905年)、克伯莱(E.P.Cubberley)的《教育史》(1920年)也都是师范院校的教材或者是根据讲义编写而成的著作。但当学者们关注到教育史学科与教师教育之间的相关时,却容易陷入到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区。这就是,就教育史学科的起源而言,尽管在中国和在国外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在共性之外,还存在基本的差异。
1902年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例如李提摩太等)曾向中国介绍国外教育,我国学者也偶有关于国外教育的翻译文字②,但作为一个知识系统的移植,外国教育史是与现代高等师范院校的兴起直接相关的。这也就是说,在我国,包括外国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学知识之所以从国外引进,直接的和主要的动因是由于教师培养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国教育史(也包括其他教育学科)是作为一个教学科目而在中国立足、并开始其发展历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的教育史著作大多都是教科书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教育史课程主要在师范院校教育专业开设的基本原因。
在我国,师范院校最初使用的教育史教材主要是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例如,由中岛半次郎编写,周焕文、韩定生翻译的《中外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先后出版了由我国学者独立编写的教材和著作。有学者认为,最早由我国学者独立编撰的外国教育史著作是姜琦先生于1921年出版的《西洋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4](P190)。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授课的讲义编写而成的。此后,一系列的著作和教材先后出版,包括:瞿世英先生的《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林汉达先生的《西洋教育史》(世界书局,1933年)、蒋径三先生的《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雷通群先生的《西洋教育通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姜琦先生的《现代西洋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王克仁先生的《西洋教育史》(中华书局,1939年)等等。这些著作多为师范院校相关课程的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间,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尽管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总体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直接从苏联引进了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三联书店,1950年)、康斯坦丁诺夫的《世界教育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然后由曹孚先生在苏联教材的基础上编写了《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出版了我国学者独立编写的教材,包括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先生的《外国教育史》(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吴式颖先生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戴本博先生主编的《外国教育史》(上中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吴式颖先生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此外,围绕着教学的需要,一系列专门史、断代史的教材也相继编写出版,包括曹孚、滕大春等先生的《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滕大春先生主编的《外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赵祥麟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天一先生主编的《西方教育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
如果进一步深入地追溯教育史学科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事实上,包括外国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史学科具有双重起源。一重起源是作为师范院校的课程,另一重起源则是作为人类理智探索的一个新领域。而从发生的过程看,教育史最初是作为人类理智探索的一个新领域而出现的,然后才成为师范院校培养教师的教学科目。在西方世界,希罗多德之后的历史研究主要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研究。从19世纪起,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学家的视野突破了原有的框架,逐步开始关注长期被忽视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这才先后出现了包括经济史、文化史和教育史在内的其他专门史研究。早期的教育史著作例如劳默尔(K.von Raumer)的《教育学史》、施密特(K.A.Schimidt)的《教育通史》以及鲍尔生(F.Paulsen)的《德国教育史》、《德国的大学与大学学习》等都是这个时期“新史学”的产物。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的教育史著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而这些著作也主要出之于历史学家、哲学家等学者之手的基本原因。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教育史研究尽管是一个新兴的历史研究领域,但这个领域的研究还主要是学者的“业余兴趣”,因而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的知识领域。
教育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的出现,是与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直接相关的。由于作为师范院校培养教师的重要教学科目,并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占据了相应的地位,教育史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知识内容、知识范围和知识体系(尽管这种体系主要来自于历史学),逐渐形成为一个“学科”。这也就是说,教育史学科的双重起源是“交叉”的。它作为人类理智探究的领域而萌芽,作为师范院校的教学科目而成型。
这种学科起源的“交叉”现象,首先表明教育史知识系统的不同功能。作为一个教学科目,教育史之所以一直被认为是教师培养和培训的重要科目,其原因就在于,一般认为,通过了解教育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教育家的思想、精神和业绩,掌握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总体过程,理解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提高未来教师的教育素养,开阔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创造才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有充分的依据的。所以,直到今天,在很多国家的教师培养和培训中,教育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科目[5]。而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教育史研究的功能在于以科学的方法,系统梳理人类教育变迁的历史过程,探索教育变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以便更为深入地理解作为人类重要社会活动的教育活动的性质,并为从整体上认识人类、社会、文明提供支持,为当代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史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史学科是历史学科的重要分支,因而也是人文学科的重要领域。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内容,教育史学科的功能还在于它的陶冶作用。
学科起源的“交叉”现象还表明了,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轨迹是不完全相同的。作为教学科目,教育史学科直接取决于教师教育课程结构的变化,间接地取决于教师教育体制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对教师素养需求的变化。只有在相对静止的环境和教育知识尚未充分分化的条件下,作为教学科目的教育史学科才可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地位(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由于师范教育的发展,教育史作为一个教学科目得到重大发展。而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教育史在美国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这也恰恰是我国教育史学科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境遇)。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教育史学科则主要受到现实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从历史的经验看,教育变革日益剧烈的时期,正是教育史学科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同样是在美国,20世纪50-60年代后,一方面是教育史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则由于修正派等“新”教育史学的兴起,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教育史却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认识误区,即不能把教育史单纯看作是一个教学科目,不能只在教学的范畴中思考教育史学科的建设。教育既是一个教学科目,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领域。如果仅仅把教育史作为教师培养和培训的教学科目,不仅无助于提高它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反而会导致其学术性的削弱。而这将从根本上消解教育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三
在我国,教育史学科当前面临的危机主要来之于它作为教学科目所面临的困境。而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局限于课程的设置、教学时数、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安排等相对具体的环节。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但绝不是首要的。我以为,从师范院校教育系科外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来说,目前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应当教什么和怎么教,还在于为什么教?由于教育系科本科层次人才培养的目标处于“虚置”状态[6],所以,包括外国教育史在内的一些原来一直主要为培养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师资而设立的基础科目,事实上存在着教学目标游移不定的状况。而人才培养目标的“虚置”,实际上意味着相关教学科目失去了明确的教学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基于本科教育专业(特别是教育学专业、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基于本科教育专业课程教学的走向,主动地重新确定教学目标。而要真正厘清这个问题,首先要进一步深入把握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基本特性和功能。
对于我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来说,当前及今后面临的一个根本任务是,“回归”教育史学科的传统,完成从单纯的教学科目向同时作为教学科目和研究领域的转变。
这种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把外国教育史从过去的教师职业的训练科目转变成为更具通才教育特征的基础科目。作为基础课,外国教育史的定位是学生学习和理解其他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知识的前提之一。没有这个前提,学生在学习其他课程时,或者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而难以深入理解,或者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为重要的是,外国教育史还是一门具有通才教育功能的基础科目。
在我国,高等教育历来被确定为专业教育或专门教育,学生在学期间除了学习那些具有点缀作用和名不副实的所谓“通识课程”外,很难有完整的时间接受哪怕是初步的普通教育。就教育专业而言,由于外国教育史课程本身更接近于历史学科、从而更接近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因此,它的教学能为学生提供基本的历史意识和人文素养的陶冶,使学生不仅具有历史的视野,而且通过了解世界各主要国家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具有世界和全球的眼光。
为了适应这种定位的转变,外国教育史课程教学的目的也应当适时进行调整。首先,作为一门教育专业本科阶段的基础课,外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主要的教育史实,了解教育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教育历史演化的基本特征。尤其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历史知识的传授,使学生具有广阔的视野,认识和理解教育活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性质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展开。
其次,作为具有一门具有精神陶冶功能的教学科目,外国教育史的目的应当有助于学生通过认识其他国家和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更好地理解人、思想、文化和传统等,从而为形成一种广阔的全球和世界视野提供帮助。就此而言,外国教育史的教材一定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本身,更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本身,而应当努力阐释教育发展与社会、文化等人类生活领域变革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认识教育历史演化的特征,才能真正使学生形成一种广阔的眼界和深厚的理解力。
从上述思考出发,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基本方面有所探索,以便更好地实现上述教学目标。第一,探索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的有机结合。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的分离(行内戏称“两张皮”),是外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外国教育史界的前辈和同仁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迄今为止,应当说这个问题仍未很好地解决。应当力图把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之间的联系具体地呈现出来,既注重说明教育制度变革的社会基础,又努力分析它的思想根据;而在叙述和分析某种教育思想时,也注意它与教育实践或教育制度的相关,以便使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有机地结合。
第二,探索学校教育史与社会教育史的结合。在过去,由于教育专业本科教学目的的局限,外国教育史教材一般都更为侧重于学校教育史(尤其是普通学校教育史)。但在人类教育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学校教育都只是社会少数成员的“特权”。如果只关注学校教育,那么,一部教育史就只是少数人群受教育的历史,而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教育史。另一方面,就个体而言,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学校教育都只是其一生教育经历的一个部分。如果只关注学校教育,那么,一部教育史就只能反映少数人的一部分教育经历。只有把学校教育史与社会教育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为全面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整体状况,同时也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
第三,探索国别史与整体历史的结合。从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教育的发展和变革大多是在民族国家的版图中进行的,教育的历史因而具有明显的国别史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以来的教育史等同于国别教育史之“和”。由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趋势(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等),因此,在强调教育发展的国家特色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总体的趋势。而且,也只有在明确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的前提下,不同国家教育发展的特点才会更有意义。
第四,探索教育历史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结合。并未着意强调以往同类教材经常关注的教育史的分期(这在以往的教材中通常是以分“编”的形式反映出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漠视历史分期的价值。事实上,历史分期对于学生了解人类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各个重要阶段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强调人类教育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阶段性。这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在整个人类教育的历史进程中,教育发展的连续性远比突变性(这是强调教育历史阶段性的重要依据)更为普遍和更为重要。除了非常个别的实例之外,通常所强调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之间的差异并不像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社会生活领域中所存在的差异那样显著。具体说来,通常所认为的教育中的“革命性变革”(例如被认为是近代教育开端的人文主义教育),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和“准备”阶段,而“革命”的完成同样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由于这种状况,就使得教育中的质变不仅在外在形式上更像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本质上也因为其本质属性的逐渐显现而成为一种渐变。
收稿日期:2007-08-23
注释:
① 张斌贤:“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贺国庆:“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贺国庆:《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新科:“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回溯与新世纪展望”,李爱萍、单中惠:“外国教育史学科在中国的百年嬗变”,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收入杨孔炽主编:《百年跨越——教育史学科的中国历程》,福州:鹭江出版社,2005年。
② 1901年,《教育世界》刊登卢梭《爱弥儿》(当时译作《爱美耳钞》)和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当时译作《醉人妻》)的节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