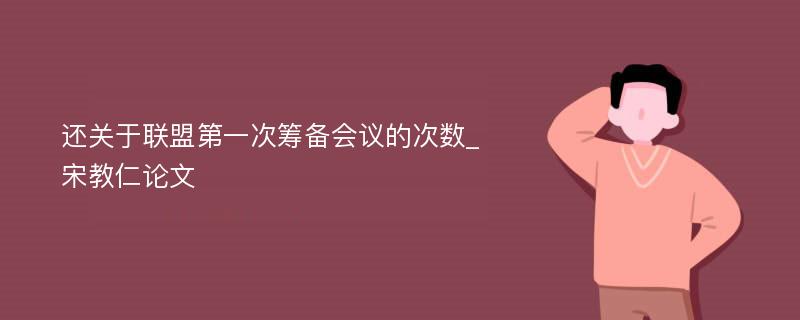
也谈同盟会第一次筹备会议人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会论文,也谈论文,人数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正式成立,由于同盟会成立在当时极为秘密,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以致后来在回忆同盟会筹备会议以及成立大会的日期上产生分歧,仅据当时参与者日后的回忆就有多种说法。如冯自由回忆第一次筹备会是乙巳年(1905年)六月下旬,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人说是二十六日,也有人讲是二十九日①,但并没有说明这个日期是阳历还是阴历。据另一位与会者田桐的回忆,召开筹备会的时间是旧历乙巳年六月二十四日,亦即阳历1905年7月26日②。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载:(7月30日)“未初,到赤版区桧町三番黑龙会,赴孙逸仙会也。既至,则已开会,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讫。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布告此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③。冯、田的说法都是在事隔20多年后才凭记忆而提出的,自然不一定准确,而宋教仁则是当时(或事后不久)的日记所记载,相对来讲就可靠得多,而且宋教仁使用的是黄帝纪年,日期为阳历,所以目前有关涉及同盟会的成立、辛亥革命的爆发乃至于孙中山生平的论述大都将中国同盟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的时间确定为1905年7月30日(即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而成立大会的日期则为同年的8月20日(阴历七月二十日)④。
至于有多少人参加了筹备会亦说法各异。仍参考前引各人的回忆,宋教仁回忆说有70余人参加,冯自由则称出席会议的有60余人,又说第一日加盟的有50余人,而田桐说到会的只有40余人,而另一位参加者曹亚伯亦称到会者有40余人⑤。同样出于前面所提出的理由,目前绝大部分论著均认同宋教仁的说法,即认定出席筹备会的人员大约有70余人。然而到底有哪些人出席呢,早期的回忆以及相关论著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单⑥。
早期提及与会人员名单最详细的是当事人冯自由,据他回忆说:“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兴中会孙总理、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各省同志之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通知到会者,有张继、陈天华、田桐、董修武、邓家彦、吴春旸、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孙元、权道涵、于德坤诸人;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楠、古应芬、金章、杜之杕、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⑦冯自由的回忆共列出了39名中国人和3名日本人出席会议的名单。但是根据宋教仁日记的记载,当天应有70余人参加筹备会,那么还有30人是谁呢?
台湾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原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典藏大量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兴中会、同盟会的档案,其中藏有一份《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即1905、1906两年)之会员名册》(以下简称《名册》)⑧,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它不仅记载了入盟者的籍贯、主盟人以及介绍人等方面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还记录了绝大多数成员入盟的时间,尽管记录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了解同盟会早期成员及其活动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后来就有学者根据这一《名册》推算出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中国人成员的名单。
台湾著名民国史学者蒋永敬教授曾长期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接触到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他最先提出参加同盟会第一次筹备会议的名单⑨,共有70名中国人,他们是:孙中山、程家柽、吴春旸、蒋尊簋、康宝[保]忠、陈荣恪、张华飞、谭鸶翰、马君武、卢汝翼、朱金钟、蓝德中、曾龙章、邓家彦、时功玖、耿觐文、涂宗武、金[余]仲勉、曹亚伯、周斌、陶凤集、叶佩熏、蒋作宾、李仲逵、刘通、李叶干、范熙绩、许纬、刘树湘、田桐、匡一、但焘、陈天华、曾继梧、余范传[傅]、郭先本、黄兴、姚越、张夷、刘道一、陶镕、李峻、宋教仁、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奎、柳扬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凤游、郭家伟、王孝缜、张继、黎勇、朱少穆、谢延誉、黄超如、冯自由、姚东若、金章、汪兆铭、古应芬、杜之杕、李文范、胡毅生、朱大符、张树枬[柟]、何天炯、吴鼎昌(方括号内是《名册》中原字)。另外还有3名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和末永节。
何泽福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份参加筹备会议68名中国人的名单⑩,其中绝大部分雷同,只是在上述名单中减去了但焘和吴鼎昌2人。
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则在何泽福名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人,他们是:安徽人王天培、孙綮、吴春生、王善达,湖北人王家驹、刘一清、陶德瑶和广东人区金钧(11),这样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中国人就有76人。
这份《名册》成员入盟日期大多标明的是“乙巳”或“丙午”某月某日,并无确切说明是阳历还是阴历。若细加分析,这个日期中其实既有阳历,也有阴历。证据一:册中很多成员入盟的时间是乙巳年七月三十日,但该年的阴历七月是小月,只有二十九日,所以这个日期肯定是阳历1905年7月30日;证据二:据《名册》记载,四川籍的谢奉琦、张邦杰、周炯伯、胡树文等4人分别于乙巳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入盟,主盟人为黄兴,然而黄兴本人却是7月30日才首批入盟的(《名册》上填写的也是这个日期),不可能他还没入盟就替别人主盟,因此这个日期就一定是阴历,亦即阳历的8月22日或24日。同样道理,经首批入盟者安徽人吴春旸主盟入会的同乡裴豫祥、夏道沛和吴延世,《名册》上记载其入盟的时间乙巳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九日也应该是阴历,即阳历的8月25、26和29日。然而困难的是,尽管我们可以证明《名册》中的时间既有阳历又有阴历,但却无法确定绝大多数人的入盟日期究竟是阳历还是阴历。
《名册》中记录会员最早入盟的时间是乙巳年六月(没有明确日期),按《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孙中山于1905年7月19日(阴历六月十七日)方抵达日本横滨(12),因此筹备会一定是在其到达日本之后才召开的,亦即阴历六月下旬。《名册》中记录入盟时间较多集中于两个日期,一个是“六月二十八日”,包括前述冯自由回忆名单中的汪兆铭、蒋尊簋、时功玖等人,而乙巳年阴历六月二十八日也正是阳历的7月30日,《名册》中记录于该日入盟但未被上述回忆文章提及的人物还有:张华飞、谭鸶翰、卢汝翼、朱金钟、蓝德中、曾龙章、耿觐文、余仲勉、周斌、陶凤集、蒋作宾、王孝缜等12人。另一个时间是“乙巳七月三十日”,这更是入盟最集中的日期,譬如前述各人回忆中提到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马君武、邓家彦、曹亚伯、匡一、张继、黎勇锡、朱少穆、谢良牧、冯自由、金章、古应芬、杜之杕、李文范、胡毅生、朱执信、张树楠、何天炯等21人。前文已经分析,这肯定是阳历的7月30日,而且这也正和宋教仁在日记中所记载的在东京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的时间相符。《名册》中记载于该日入盟却不在上述名单的还有陈荣恪、涂宗武、叶佩熏、李仲逵、刘通、李叶干、范熙绩、许纬、刘树湘、曾继梧、余范传、郭先本、姚越、张夷、陶镕、李峻、周咏曾、邹毓奇、高兆奎、柳扬谷、柳刚、宋式善、范治焕、林凤游、郭家伟、黄超如、姚东若等27人。
蒋永敬、何泽福等人提出的名单虽然没有解释是如何计算参加会议人数的,但可以肯定他们的这个名单就是用这个方法统计,最后再加上孙中山、吴春旸、程家柽、田桐、康宝忠 5人(蒋永敬再增加但焘和吴鼎昌2人)而得出来的,这一名单虽然不一定完备,但却是有史实依据的。而《孙中山年谱长编》所增加的8人除了陶德瑶《名册》中记录入盟时间为乙巳六月外,其他人均没有登记入盟时间,编者对此并没有加以任何解释。其实《名册》中没有记载入盟日期的并不止上述几位,还有不少人的入盟时间也早于七月三十日,如秋瑾(七月二十七日),俞为民(七月十四日),张仲文(七月十三日),张光黄、成巍、熊兆周、杨杰(七月十四日)等。由于这个日期到底是阳历还是阴历无法确定,而且他们既未出现于前面所提及的回忆名单之内,又不能肯定是筹备会议的召开日入盟的,不能因为《名册》中没有记录入盟时间或是入盟时间早于七月三十日就肯定他们是参加了第一次筹备会议。所以笔者认为,在尚未发现新的证据之前,这个增加8个人的名单根据尚不充分。
除了冯自由的回忆,笔者又参阅了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和一些文献,譬如国民党元老邹鲁早在1924年就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开始广为收集史料,编撰《中国国民党史稿》,并于1929年正式出版。他对冯自由的名单在人数上有所增删,略去了朱炳麟等10多人,却增加了居正、黄复生、张我华、姚粟若4人(13);同盟会的另一位元老邓家彦的回忆亦肯定黄复生参加了会议,同时还增加了吴鼎昌、刘鼎彝、李肇甫3人(14)。在这个基础上,笔者参阅《名册》再结合有关当事人回忆,最后提出另一个名单:
安徽:程家柽 吴春旸 孙竹丹(元) 张我华 权道涵
贵州:于德坤
浙江:蒋尊簋
陕西:康宝忠
江西:陈荣恪 张华飞
广西:谭鸶翰 马君武 卢汝翼 朱金钟 蓝德中 曾龙章 邓家彦
湖北:时功玖 耿觐文 涂宗武 余仲勉 鲁鱼 但焘 曹亚伯
周斌 陶凤集 叶佩熏 蒋作宾 李仲逵 刘通 李叶干
范熙绩 许纬 刘树湘 田桐 匡一 居正
湖南:陈天华 曾继梧 余范传 郭先本 黄兴 姚越 张明夷
刘道一 陶镕 李峻 宋教仁 周咏曾 邹毓奇 高兆奎
柳扬谷 柳刚 宋式善 范治焕 林凤游 郭家伟
福建:王孝缜
直隶:张继
广东:孙中山 黎勇 朱少穆 谢延誉 黄超如 冯自由 梁慕光
姚东若 金章 汪兆铭 古应芬 杜之杕 李文范 胡毅生
朱大符 张树楠 何天炯
四川:黄复生 吴鼎昌 刘紫骏(鼎彝) 李肇甫 董修武
籍贯不清者:朱炳麟 姚礼修 张树棠
这个名单的总人数为84人,来自12个省(3人籍贯不清),较蒋永敬提出的人数多14人(名单下划线者为新增加的人),增加的依据主要是源自前文所提到的几位当事人的回忆。
根据冯自由等人的回忆名单,首批与会成员在《名册》中除了绝大部分注明入盟时间是7月30日,包括阴历六月二十八日之外(这也就是蒋永敬和何泽福提出的名单),有些人并没有标明入盟日期,如程家柽、吴春旸、但焘、田桐、吴鼎昌等人;有人只写下入盟的月份,如康宝忠(乙巳六月),黄复生、刘紫骏2人入盟时间写的则是乙巳七月十四日;还有几个人填写入盟的时间则是在7月30日之后,如梁慕光(8月6日)、鲁鱼、李肇甫(8月7日)、董修武(8月20日)、于德坤(8月21日)、孙竹丹(9月29日)、权道涵(10月5日);甚至还有几位在《名册》中并无其入盟的记载,如居正、张我华、朱炳麟、姚礼修、张树棠等。
以上统计的名单数字超过了宋教仁、冯自由等人所说的人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宋教仁等人的回忆不够准确,当天来了多少人其实并没有经过仔细点算,70多人或 80多人聚在一起也很难辨明到底来了多少人,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同盟会成立的日期后来不就是有各种说法吗?另外的一种可能是,由于冯自由等人回忆的人名与《名册》中的名字不同以致引起混淆或者出现重复,譬如回忆与《名册》名字不同的有康保(宝)忠、鲁鱼 (禺)、吴春旸(阳)、杜之杖(杕)、姚东(粟)若、张树楠(枬)等;有的则是其名与其字号(或原名)不同,如孙元(竹丹)、谢延誉(良牧)、胡毅(毅生)、朱大符(执信)、黄复生(树中)、黎勇(勇锡)、柳扬谷(聘农)等等,相对来讲这些还比较容易核对。有一些人则较难查核,譬如田桐在回忆中曾特别提到会议中有一位湖南人张明夷因同盟会的名称而公开提出意见(15),但《名册》中并无张明夷却有张夷(籍贯湖南南州厅,7月30日入盟);邓家彦回忆说有一位四川彭县人刘鼎彝参加了会议,但在《名册》中籍贯是四川彭县者只有一位,他与黄复生同天入盟,也姓刘,但叫刘紫骏,这样看来他们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因而我将他们也列入名单。再根据这一推理,未出现在《名册》中的几个人,或许是其字号与姓名不同未能查明而重复计算,也可能是《名册》虽未予记载,却不能证明他没参加。因为据编者在公布《名册》时称,《名册》所列会员共计960人,“凡在东京加盟者,十九皆在册内”(16),亦承认还是有些人未能登记,譬如朱炳麟的名字就不在《名册》之中,但据冯自由、田桐等人的回忆,同盟会筹备会刚刚成立他就负责内务部的事务,后来更曾接替黄兴,代理庶务部总干事。这就说明虽然《名册》的记录已相当全面,但还是会有遗漏的可能。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根据宋教仁、冯自由等多位当事人回忆,当天与会者入盟时必须是本人当面宣誓签字,并由孙中山于隔壁房间单独与各盟员交代握手暗号和联络口号,因此他们都是亲自参加,不可能由旁人代表而加入的。
综上所述,笔者补充的这个名单所依据的原则有两个,一是《名册》中所填7月30日 (包括乙巳六月二十八日)入盟的所有成员,二是主要当事人的回忆。
这里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回忆录的问题。前而已经说过,由于时间久远,事过境迁,回忆时对时间、地点、人物出现误差是常有的事,更何况有时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上述各人的回忆是否完全可靠还是值得讨论的。譬如邓家彦的回忆就说胡汉民好像也出席了当天的筹备会,但根据胡汉民(当时名衍鸿)本人的回忆,当年暑假他与廖仲恺因事同行返回广东,“途次闻孙先生已至日本,组织革命党,余与仲恺乃急返东京,至则中国同盟会已成立”(17)。而根据《名册》记载,胡、廖二人是当年九月一日(不知是阳历还是阴历,如果是阴历就是9月29日)入盟的,这与胡汉民本人的回忆时间相符,但与邓家彦的回忆就有出入了,可见回忆录的内容并不一定全是真实的。然而尽管如此,笔者以为在没有其他证据辩驳的前提之下,也不可轻易地去否定当事人的回忆。
注释:
①⑦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原载《大风半月刊》第60-61期(1940年1月20日、2月5日),后收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二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年版,第7页。
②田桐《同盟会成立记》,原载《太平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后收录于《革命文献》第二辑,第2页。
③宋教仁《我之历史》,此书记载了宋教仁1904-1907年从事革命活动的日记,1919年在宋之故乡湖南桃源石印刊行,后全书影印,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一辑《建立民国》,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当日记载见该书第70页。
④如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第一版,第46页;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增订,第196页;金冲及、胡绳武主编《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388页;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42页;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⑤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15-16页。作者自序写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初版印于民国十八年,但出版不到一年因书中有触犯当局忌讳之处(据说是指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父亲当年曾镇压革命之事)而被禁,本书为重印本,但未注出版地及出版时间。
⑥有的论著虽然也说参加筹备会的成员有70余人,但所提到的人名却有误。如蒋纬国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一部《建立民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称浙江光复会的章炳麟、徐锡麟也参加了筹备会就是错误的。此说见该书第一卷,第51页。
⑧该名册最初刊布于《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8-77页。后相继转载于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辑第十一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163-225页;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55页。
⑨蒋永敬《从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探讨几个问题》,《新知杂志》第一年第四期;又见氏着《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48页。
⑩名单见何泽福《同盟会成立新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275页。
(11)(1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42-343、338-339页。
(13)《中国国民党史稿》1944年的增订本略去了汪兆铭、朱炳麟、匡一、鲁鱼、孙元、权道涵、于德坤、李文范、金章、姚礼修、张树棠等11人(见该书第46页),但该书在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时又将汪兆铭的名字补了上去(见该书第36页)。
(14)居正修记录《访问邓家彦先生第一讲》(1942年5月21日),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辑第十一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版,第344页。
(15)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第二辑,第2页。
(16)参见《编者说明》,《革命文献》第二辑,第18页。
(17)《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三辑,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