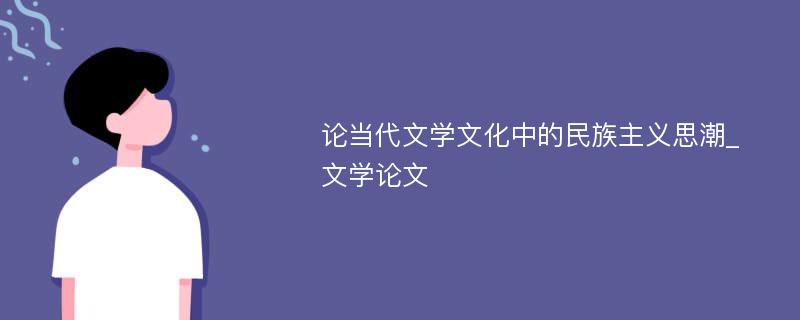
论当代文学和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文学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长期极左政策统治下,受阶级斗争理论和现实政治的困扰,中国当代文学民族主义匮乏。从文化专制中解放出来,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实现自觉的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兴起。陈祖芬的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1980)表现了极左政策对于民族主义的困扰,以及民族主义对于阶级斗争的超越。
“浩劫”过后,面对百孔千疮的现实,中国同先进工业国家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加上改革开放后,西方世界价值观念涌入,在相当一部分国人中,民族自信心减弱,甚至丧失。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大地滋生、泛滥。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生成是回应西方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国内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王蒙的《相见时难》(1982)描写了上述两种价值体系、两种社会思潮的冲突。小说以美籍华人蓝佩玉回国治丧为中心事件描写了发生在1979年里的一出喜剧。领导层里的风派人物孙润成,文革期间曾挥拳痛斥翁式含和蓝佩玉相互“勾结”,而现在却又随风倒,竟要翁式含出面帮忙巴结蓝佩玉这样的“海外关系”;比蓝佩玉年龄尚小并且在她父亲去世后又改嫁他人的杜艳,千方百计地要拉上这个海外关系,以挤进“美眷”行列,甚至希望能跟上蓝佩玉“到美国腐朽上一年半载再回来”。杜艳是王蒙笔下的一个虚无主义者,对内的民族虚无衍生出对外的殖民地性格。杜艳是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在“新时期”的再现,是精神上的“沦陷者”。王蒙较早地揭示了建国30年之后滋生于中国大地的后殖民地意识,并且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忧虑。
《相见时难》描写了蓝佩玉在美国生活30来年,却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保留着“东方人的无法解脱的执拗的痛苦”,回到中国到处寻找东方文化精神。她一直相信:有一种光明,一种力量,一种希望,那是在中国。翁式含体现着蓝佩玉所向往的光明、力量和希望。他是执政党中的务实派。他所经受的“相见时难”发生在“劫难”——作品由于存在致命局限,将此称之为“挫折、失误”——刚刚渡过的历史时刻。它是务实派在中国同世界经济先进国家之间出现的巨大落差面前的窘迫和痛苦,是一种清醒的落后感。这种感情包含着自觉的主人翁精神。他既自觉又自豪地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他认定自己的位置是“在中国干”。翁式含身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人在“大灾难”过后强烈的自强、自信精神。《相见时难》是王蒙反思小说中的“民族篇”。小说以蓝佩玉登机回国开头,又以她坐着飞机离开中国结尾。经过一番寻觅,她找到了中国。她觉得中国“伟大,深邃,痛苦!”“真是深不见底!”她在飞机上安然地睡了。睡梦中喃喃地说:“中国!”两年后,王蒙在报告文学《访苏心潮》中将这首“中国”畅想曲全部唱出,并且凸现了它的动态特征:
我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划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1980),从它的二元标记,到作品所展现的两种生存状态、价值体系,都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差异。这里的许灵均的父亲时隔30年回国与《相见时难》中的蓝佩玉回国有着相同的意义,都属于抱着“另一个世界的价值标准”走进了我们的国门。许灵均同翁式含、蓝佩玉一样,自由地选择了“土地”、“家园”。这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选择。许灵均与父亲的一段对话,集中地表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许灵均所作选择的历史感: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惟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许灵均的选择表现了“大灾难”过后中国人精神的伟岸。
张洁的“访美散记”系列,表现了对于20世纪重要文化现象的关注,其中有敏感而重大的关于“自由”的问题。针对美国一家杂志社负责人向中国作家代表团阐述的“反政府=创作自由”的逻辑,张洁表达了她所理解的文学自由原则、真实性原则,它是富于民族主义的,通向民族复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张洁和张贤亮、王蒙等中年作家表现为对于有历史感的“土地”思想的坚守,而张承志、阿城、王安忆、郑义等青年作家则表现为对于东方文化的坚守,对于“精神家园”的寻觅, 从而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寻根思潮。 《黑骏马》(1982)、《棋王》(1984)、《小鲍庄》(1985)、《老井》(1985)的问世,标志着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寻根文学”旨在寻找民族文化源流,开掘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的内核,将其引入现代。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将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根基上的现代化。
80年代里,国门打开,日货大量涌入,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不少政要总是不时地翻当年侵略战争的案,美化当年的军国主义侵略。这些,引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国内某些势力的不满。198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40周年之际,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以政府公职人员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此背景下得到发展。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一阶段,题材、主题主要集中在表现当年的抗日战争上:揭露日本侵略者当年犯下的罪行,描写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战,以回答当今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其主调是悲愤。
老舍40年代创作的抗战史诗《四世同堂》在中国大陆被冷落了30年后,第一次得到出版, 并且随后拍成电视连续剧, 正值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播出,广大观众踊跃观看,满城争说。人们随着当年沦陷区北平普通百姓的遭遇、觉醒、抗争而悲愤、痛苦、憎恨、振奋,爱国主义热情徐徐燃烧。
莫言的《红高梁》(1986)响彻着“高梁红了,高梁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的抗战主调,疏导了中国人民心中的悲愤。余司令领导的抗日队伍与日本侵略者的冲突处处表现为“红高梁”和“非高梁”的冲突。爷爷、奶奶们奋起保卫的是“红高梁”。“红高梁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
徐志耕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1987)饱蘸同胞的血泪,感情激荡,以详尽的事实和资料,较为完整地记述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力驳了日本某些势力散布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同时也警示我国人民要世世代代牢记这一惨痛历史。
这期间,还出现了以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与人》为代表的一批新抗战小说。这批小说大多采用编年体,描写上下几十年,纵横几千里的战争岁月,透露出强烈的记载历史,警示后人的创作意图。
《新战争与和平》追求的是《战争与和平》的史诗品格。小说描写了从“9·18”到“8·15”14年间中国大地灾难深重而又如火如荼的历史场景,以及贯穿于这段历史时期的主人公刘本生和川岛芳子的不同命运。描写之中揉进了对于战争本质的思考,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华文化精神。
《长城万里图》将驱动历史事件的内在动因及外在的历史人物尽收笔下,表现出师承《三国演义》的意向。
《战争与人》表现主人公在民族存亡面前选择人生道路的艰难、痛苦及其严肃意义,思考战争中人的命运,近似于《静静的顿河》的主题。
这批新抗战小说,以及包括电影文学《血战台儿庄》(1987)在内的新抗战文学,比起1958年前后问世的“革命历史小说”模式下的那批抗战小说,在真实性、独立性上前进了一大步。新抗战文学以民族视角客观地描写并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贡献,热情地讴歌了国民党中的爱国将领、抗日官兵。这表明阶级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逐渐消弭,民族主义在不断加强。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在90年代形成高潮。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已由两极转为多极。而美国妄图独霸世界的想法却在加强,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的情绪也在加强。他们一再在中国的台湾、西藏、贸易、人权等问题上插手,明里遏制,暗里颠覆,不让中国发展,以防止出现“美国将来的敌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遏制”下日趋高涨。它是对于“遏制”的“反遏制”。
藏族作家益希单增的长篇小说《雪剑残阳》(1996)再现了本世纪初西藏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的英勇斗争。面对武器精良的侵略者,藏族广大军民,顶着腐败的清廷代言人的压力,凭借原始的火炮弓箭,甚至石头,浴血奋战,在西藏大地上,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爱国主义的丰碑。
根据《雪剑残阳》改编的电影《红河谷》(1997)在原作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及其主题的基础之上,增强了艺术幻想并对主题作了深化。《红河谷》描写两个外部落难者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西藏雪域文化之中。汉族姑娘雪儿被一家纯朴的藏民搭救后,与他们一起生活,并与老阿婆的孙子格桑两心相属。格桑剽悍、倔强、专情,富有自尊心。艳丽、高贵的丹珠超越等级观念,暗恋上了格桑,对格桑发出咄咄逼人挑逗的同时,也对雪儿摆出头人千金的专横。面对骄横的丹珠,格桑不卑不亢,雪儿达瓦也不失平民的自傲。雪域高原的生活以它的灿烂多姿在和平地向前行进着。
英国人罗克曼来西藏“探险”,无视西藏的神秘而遭到大自然的报应,落入死难之中。被搭救后,他送给了格桑一个打火机。打火机在作品中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象征。
以罗克曼为代表的英国侵略者想用西方的另一文明——洋枪大炮征服西藏,这是他们又一次的、在整体意义上无视西藏的神秘。宁静的生活被破坏,神圣的土地被践踏,整个西藏都怒吼了。无论是上层,还是平民,无论是骄横任性的丹珠,还是不卑不亢的格桑,和温柔自尊的雪儿达瓦,结合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同侵略者展开了殊死卓绝的抗争。丹珠面对侵略者凌辱,高声唱起富有雪域文化底蕴的民歌《在那草地上》,青春和爱情获得了更加壮丽的勃发。雪儿达瓦两次被搭救,感知了以老阿婆为代表的藏族人民的恩和格桑赤诚的爱。西藏不仅给她以生命,还给她以灵魂。她已与藏族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格桑英勇不屈,敢爱敢恨,在更高的意义上不卑不亢,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他最后一次拿起打火机,面对这种“文明”的主人的恩将仇报,他的性格美升华了,他用它点然了洋油,复仇的烈焰轰然而起,引爆了炸药,他与恩将仇报者同归于尽。英国侵略者受到了中华民族的惩罚。
《红河谷》远远地超越了它的“时间面”——“1904年”。它是在一百多年的大时间跨度里表现东方,在动态中表现东方——“永远征服不了的东方”。《红河谷》是东方复兴的征兆,中华民族精神复兴的征兆。
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而上表现,凝聚为一句话则是“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的政治杂文集《中国可以说不》(1996)表达了世纪之交中国人民激越的情绪。
《红河谷》重温世纪之初的一场悲壮,表现不可征服的东方。《中国可以说不》则立足于世纪之末中国已经崛起,来表现中国人的激情:
如果说中国10多亿人口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能够过上现在的生活是一种奇迹的话,那么中国人也同样有能力实现下一个奇迹……
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渡过新世纪的太阳升起之前的必然要经历的一段艰难时光?对此,《中国可以说不》的鲜明观点是:“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取,但民族主义还是要的。”
如果说此前出现的新抗战文学是再现“昨天”来回答日本,那么《中国可以说不》则是立足“今天”同美国对话。
《中国可以说不》是针对美国所谓“遏制”的。“说不”的艺术是“反遏制”的艺术。对于美国霸权主义在中国的表演,作品以哲理性的幽默写出它的变形、可笑,从而显得并不可怕:“美国的表演,再加上追随者的表演,已经让人看够了。毫无新意。美国得不到它想象中的喝彩。如果它听到什么动静,那只能是倒彩。”
在压倒一切的倒彩中,有一个更短促更有力的声音,那就是一个单音字——
“不!”
“不!”这个单音节否定性副词是一雪百年耻辱,历史已经发展到现在——中华民族不可欺不可辱的现在,12亿中国人对于美国霸权主义的一个响亮回答:
中国可以说不。
现在说正是时候。
全书都在透露“说不”的意义: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这是发自全体中国人的和平、自主的声音。正如何蓓琳为该书所作“前言”中写的: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
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
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老子说“自胜者强”。一个结束了屈辱的历史,结束了阶级斗争的纷乱,而专心致力于建设的中国,奉行和平、自主外交政策的中国,体现着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主潮,她必将带着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特色去融于世界。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意义所在。《中国可以说不》发出了民族主义的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