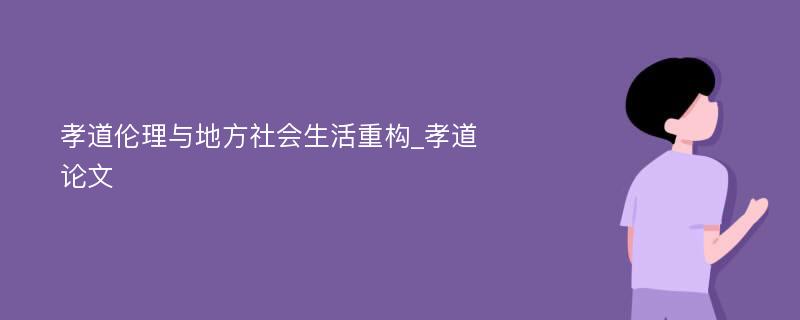
孝道伦理与乡土社会生活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道论文,乡土论文,社会生活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5)02-0005-07 一、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与伦理困境 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伴生现象,是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看,日益增长的庞大的老龄人口的存在,给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家庭结构、伦理关系、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人们的情感体验都造成了诸多困境。面对这些难题和挑战,无论是市场的自发秩序,还是福利国家都难以将其化解。 在资本和利润的逻辑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老年人作为非就业人口和几乎纯粹的消费者,对于资本是一个巨大的投资获利的“市场”;与此同时,养老对于整个社会、家庭和老年人个人,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难题的渊薮。这是一个悖论:现代市场和资本能够从老年人口的存在中获取利润,但是资本的介入非但未能解决养老的问题,反而使养老变成愈来愈棘手的难题。我们能看到,资本从养老市场中攫取的利润的上升趋势与养老问题的恶化程度似乎适成正比。事实上,由于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依据的基础是理性“经济人”意识形态、单一的交换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伦理学,老龄化社会的相关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内部成为一个在根本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种困境迫使我们必须反思现存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伦理范式本身,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家庭制度在价值观和道德上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伦理范式,来替代现存的以个人主义和交换价值观为内核的伦理范式,这意味着需要思考超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家庭制度的可能性。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传统中国的孝道与乡土社会时,我们发现了一种可以为现代老龄化社会提供普遍性的伦理智慧的资源。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及其家庭生活,非但没有被老龄人口的存在所困扰,反而因为老龄人口的存在而受到祝福,充满天伦之乐。 二、孝悌之俗与乡土社会:“父子相隐”的伦理意蕴 从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中国古代的孝悌之道是乡土社会的一种伦理习俗。我们在《论语·子路》篇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关于乡土社会生活的故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个故事当然可以从父子之间互爱的感情——孝和慈之“心”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孔子的评论中无疑还包含这样一个重点:对赋予父子相“隐”以道德肯定的“吾党”的强调。吾党是何党?作为乡土社会的“吾党”显然已经发展出了一套视孝心和慈爱为理所当然的伦理习俗——礼。它包容和鼓励明显“违法”,然而却含有真诚的孝心和慈爱的行为——一孝之行。 孝之行超越法理正义——叶公所谓“直”。孝之行内涵更高的正义品质,即道德上的正义——孔子所谓“直”。如果说“父子不隐”体现了某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理上的正义,那么,“父子相隐”则强调对于父子之间的生命关联和身份关联的认同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父子作为家庭共同体的成员,惟有无条件地(哪怕违犯法律)认同父子命运与共的一体性,才是道德的;而不认同这种命运关联性和整体性,则是不道德的。个体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从个体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来衡量的,而是从个体是否认同并维护家庭共同体(父子命运与共是其典型体现)来衡量的。 “父子相隐”作为孝行的道德正当性,甚至被孟子推到了一个极端。孟子提供了一个更为尖锐的法理与道德冲突的例子:舜父杀人被捕,舜竟然弃天子之位如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诉然,乐而忘天下”[1](《孟子·尽心上》)。这个说法颇耐人寻味,孟子的解释是:“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1](《孟子·离娄上》) 不仅父子关系,而且整个家庭即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乡土社会生活正是以家庭这种自然主义的血缘命运共同体为“细胞”组织起来的,其通行的道德习俗之正义与否的价值标准,不是以个体而是以家庭为基本尺度的。正是在这种尺度下,乡土社会中的人们理所当然地将“父子相隐”视为“直”而不曲。很显然,这种孝行礼义(伦理制度与道德价值)与个体主义的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 孝行礼义赋予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体以乡土生活的道德意义与道德尊严。在“父子相隐”的例子中,个体的道德“责任”与“权利”都是从家庭整体的角度出发来定义的,而不是从个体的法律正义感和所谓个人自由来定义的。在这里,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体,必须克服或超越其法律上的“责任”和“权利”,通过明显违法的“隐”瞒行为,才能成就乡土社会所认可的道德意义和道德尊严。 “吾党直躬”之“直”,意味着“父子相隐”含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仁”,从行为和情感上看,即是父慈子孝。这意味着作为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个体皆认同父子命运与共,皆视家庭为一命运共同体。“直躬”意味着身行此行即为“义”,而不如此行恰为不义。这种道德上的“义”与个体的家庭责任感及亲情“良知”的安宁有关。“父子相隐”被孔子推崇和肯定,而孔子的推崇和肯定本身反映的正是乡土社会的一种伦理共识和默契。由此可见,“父子相隐”本来就被“吾党”普遍地理解和接受为合乎“礼”的正直行为,是乡土社会生活之“礼”的一个核心内容。“父子相隐”所涵之“智”,主要表现为个人具有超越法理理性的道德智慧。“信”的实质是自己的真诚与他人的信任。从值得亲人信赖和性命相托的意义上讲,“父子相隐”本身是具有互相信赖的本质的;而且,“父子相隐”出于自然亲情的孝慈之诚,为“吾党”所推尊,当然亦可以名之为“信”。 通过以上对“父子相隐”的孝行伦理内涵的分析,我们发现,孝道是以“家”庭这一自然的血缘生命共同体为基本主体和价值尺度的。此外,从孔子所强调的“吾党”本身来看,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古代讲究孝心,盛行孝行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孝道社会。这种作为孝道社会的乡土社会,赋予孝慈的自然表现以社会习俗(礼)的形式,从普遍道德规范的意义上予以肯定,使之成为一种社会生活品质的必须,社会生活内容的必须,以及个体身份的必须。 在孝道的道德思维中,个体的身份是家族身份的载体。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共生的关系,父亲的生命和生活与儿子的生命和生活有一个高度交织与重合的共同部分,而所有现世的家族成员都与祖先以及未来的家族世代成员之间有着一种共通的家族身份的“内核”或“基因”。 三、孝悌之义:“家庭”的伦常 传统中国的孝道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基于家庭角色和生命历程的人的概念、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生命共同体伦理学,和一种全面的价值体系与价值秩序。《论语·为政》篇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孔子对于“孝”的理解:“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从字面上看,孔子对“孝”的理解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孝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爱关系。第二,孝的实现和表达,是真诚的爱敬情感与合乎礼俗的奉献行为的统一。徒有其表的奉养行为,以及表面的礼仪形式等都是违背孝的本质的。第三,孝既涉及生之事又涉及死之事,体现为家族生命共同体内部代际关系的无限连续性。 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们作为共同体在一起生活,同时每个人又作为个体有其相对独立的生活。儒家在理解个体的人时,总是将这个事实的两面作整体的观照。儒家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定义具体的个人,而不是将人理解为抽象的、具有某种空洞的“自由”、“平等”的原子化的“个人”。儒家所持的人的概念将具体的人视为具体的社会共同体中的参与者和成员。个人在多层次的社会共同体中多重的具体角色,与个人所属的多层次的特定社会共同体本身,对于界定和理解一个具体的人是缺一不可的。儒家关注到人群中与他人互动共生的人,适为人之真实存在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儒家不承认单独的个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 儒家的人首先是在家庭中定义的。《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孝慈互动关系是任何人作为一个人的根本关系。因此,《论语·学而》有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而且,儒家也用一种扩大了的广义的“家庭”观来理解乡土社会、国家和天下。基于这种眼光,儒家将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都视为某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论语·颜渊》) 这种狭义或广义的“家庭”关系整体中的具体的人的观念,是儒家乃至整个古典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核心“密码”。这意味着,以家庭为典型和基础的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与个体的存在,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古人在描述个人时,总是追溯至其先祖之德,个人生命的意义在家族生命延续中定义。如果利用儒家惯用的隐喻——“树”的本末来看,家庭是个体生命的根本,个体生命是家庭的枝叶。从这个意义上讲,父子之间的孝慈互动,关乎父和子个人与其自然性的家族生命根源之间的联系,于是,这种互动行为具有某种养护个体之生命根源的宗教性的意义和功能。 现代的个人主义对个体的理解与儒家的“共同体主义”不同,它首先将共同体的生活与个人的生活分为两个生活,将一个整体事实的两面,拆分为两个事实。其次,它将抽象的个人生活视为首要的和根本性的,而共同体的生活只不过是这种个人生活派生出来的“契约性”的组合形式。这种理解当然不符合自然的人类生活经验实际。 孝道的根基是家人之间自然的血缘依存关系。虽然这种自然关系的确定性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的支撑,但是,它却不是不可以包含某种宗教精神的:祖宗神崇拜渗透在中国古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家庭实际上成为一种圣俗两面兼备的统一体。 儒家认为,家庭这一生命共同体中包含父子、兄弟和夫妇三种伦理关系;其基本伦理原则就是互爱——仁,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家庭中的人际互动,是依据具体成员的具体角色,依据亲子男女长幼的秩序与关系,而适用不同的行为法则。家庭成员之间依孝慈恩爱相互关怀的情感而互动,这些情感互动将家庭连接为一个和谐的生命共同体。可见,支撑家庭生活的伦理秩序是一种自然的长幼秩序,它是不符合自由主义抽象的“人人平等”原则的。家庭成员之间生命的相互依托,也不是基于契约式的权利和责任的锁链,而是互爱和感恩的自然结果。 孝道的基础是人与人生命的自然亲情网络与连环:一种由家庭血缘纽带和互爱之情所维系的自然的代际生命历程的连环。在这里,人被理解为家庭生命共同体的参与者,而乡土社会则是这种家庭生命共同体的地方性扩展之物,或者说是一种地方性扩展了的“泛家庭”生命共同体。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无名”的“原子”个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成员,一个个具有完整的生命历程的人。他们有名有姓,为人子女,为人兄弟(姊妹),为人父母;出生、长大、成年、结婚成家、生育下一代、享受晚年,然后心满意足地寿终正寝,而且在死后能得到亲人的怀念与子孙的祭祀。 儒家对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生命的根源有一种宗教性的理解:个人所属的家庭生命具有无限延续性,并且与宇宙性的自然主义的本体、万物的总根源“天”相通。逝去的祖宗作为神灵与“天”处于同一精神世界,甚至祖宗神和天地万物的神灵乃至天本身,是浑然一体的,神秘而玄妙地作为一个相互贯通的整体而存在着。于是,人们通过祭祀礼仪与祖宗神的沟通,一方面是报本返始的人神沟通,另一方面也往往意味着以祖宗神为中介而实现的人天沟通。殷商之际,中国古人尚有对人格化的天帝或上帝的信仰,祖先如非被视同天帝,即被视为传达讯息于天帝的中介。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叶,但最后却逐渐由超越的精神实体——“天”的概念所取代[2](P20)。可见在儒家的观念中,个人与祖先和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整体。 就生命而言,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之间,乃至祖先和未来世代的后人之间,在肉体、心灵和德性上都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天然渗透与连锁关系。由于个人处在家庭生命共同体的生命链条之中,家庭对于个体的人格和人生意义具有建构性的作用。家庭赋予个人以多重角色,这些角色会随着个人生命历程的渐次展开,并且依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逐渐变化而具体地呈现出来。虽然,个人的多重角色是家庭赋予的,但是个人扮演这些角色的道德价值,却需要个人自己躬行孝悌而获得。“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1](《大学》),惟其如此,才能成就父子角色应有的道德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个人实践道德修养,在道德人格上逐渐成长,并实现自我道德价值的历程。 孝道所依托的“人”的观念,是具体的具有完整生命历程的人。其生命历程根源于生生不息之“天”,最终又回归大化流行之“天”。孝道将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包容在家庭代际生命延续的无尽链条中,不仅为个体提供了肉身所居的家园,也为个体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孝道的基本伦理精神在于:家庭是人的生命历程相互交织的生命共同体;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生活追求一种生命交响的和谐。这种内在的和谐,不仅渗透在家庭之中,而且也遍布家庭之外的国家,乃至天下。 正是出于某种天下一家的情怀,孔子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将孝悌之道与仁德相贯通。于是,仁成为孝道的伦理准则。它始于自然亲情的人人身心连接,可以推至天地万物。《论语·学而》篇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在孔子看来,本于小家庭内部的孝悌,可以推展到国家和天下大家庭,从而体现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的一体之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论语·学而》)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论语·公冶长》) 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论语·雍也》) 这种孝悌普遍化为仁爱的思想与实践,在孔子看来古已有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其原始可以追溯至唐虞之际。 孝悌之道在家庭之外的推展,使孝悌扩展为普遍的尊老爱幼的仁爱之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民间的实践来看,孝道在乡土社会中的盛行,为乡土社会建设了一种人与人相互关怀,相互信任的特殊的“社会资本”。这就是孔子所强调的“里仁为美”,一种良风美俗的社会氛围,和家庭般温暖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孝道之用:养老与尊长 孝悌之道本为百姓日用之道,其本天然,其体仁爱,其用在亲人之间的命运与共,家庭生命共同体命脉之永恒绵延。其主要表现为养老以尽人之伦,尊长以成人之德。孝道之用如此重要,以致古代的字典直接从孝道之用来定义孝道:《说文解字》曰:“孝,善事父母也。”《尔雅》亦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道的功能从家庭内部来说,包括一个和睦健全的家庭的全部功能:尊老爱幼、生儿育女、互敬互爱,相互关怀,生事丧祭等等。本来,儒家也强调,孝慈相通。如《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但是,古典儒家主要从养老的意义上来强调孝道的社会功能。儒家的所谓养老,是子女或后辈对长辈既有内心尊敬又有周到奉养的行为。孔子认为若对长辈不存恭敬之心,则与养狗马无别,不能名之为养老之养。 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在感情上也是非常丰富细腻的——既喜又忧。由于父母年长,喜其健康长寿,忧其年事日高:“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1](《论语·里仁》) 儒家对养老要求极高,非常细致周到,不仅要恭敬有礼,情感真挚,而且要始终和颜悦色。和颜悦色所体现的敬爱父母的真情是孝的实质所在,如果只有饮食和服侍,那还不足以成其为孝:“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论语·为政》)“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论语·里仁》) 养老不仅是孝道社会的乡土风俗,也是国家的礼法制度。《礼记·王制》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又有:“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3](P187-189) 虞、夏、殷、周四代的养老燕飨制度和礼仪与当时的教育制度结合在一起,其目的在于推行尊长养老的人伦教化:“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1](《孟子·滕文公上》)“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1](《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还以文王之例说明,文王“善养老者”而天下归心的人伦教化之效应:“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1](《孟子·离娄上》) 养老的效用一方面在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这种亲情自然洋溢的生命的欢愉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之一。孟子称其为君子三乐之一。另一方面,养老的行为作为一种生活内容直接构成了家庭中年轻一代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修养内容与功德。儒家视养老为“成人”的核心道德实践。是人所载所弘之道最切近日用,最根本,最紧要的实践活动。亲亲行于家庭之内,亲人之间;长长或尊尊则通行于全社会。孝养父母的普遍流行就会形成尊老爱幼的社会习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论语·乡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片段:“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孔子的形象被如此记录下来,不能不说《论语》的作者很大程度上是有意将孔子作为乡土社会中个人角色的一个典范来描绘的。从孔子的“乡党”形象来看,个人在乡土社会中的角色是谦恭与和悦的,因此,可以说,和乐恭敬是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在乡饮酒礼中,孔子对“杖者”的礼让,则透露出尊老是“乡党”的基本伦理规范。 但是,尊长非惟年长者是尊,尊有德而寿者也:“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1](《论语·宪问》) 一个老人必须具备值得尊敬的德行才会令人尊敬。这种德行实际上是一种长期修养的结果,是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生命成长的成就。这就是:自幼年时起即躬行孝悌之道,在成年时有值得称道的言行,老年时乐天知命,自尊自重。 五、孝道之治:“孝悌”的乌托邦精神 儒家对于孝治抱有一种乌托邦主义式的执着。《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即托孔子之口,将孝道界定为先王治国平天下的“至德要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儒家虽有孝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古典儒家所推崇的孝治实践典范似乎只限于“先王”——黄帝、尧、舜、禹、文王、武王和周公。 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大教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先圣与后圣,考后而甄先,教民大顺之道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4](P30)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礼、褅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1](《中庸》) 对于古之圣王以后的孝治历史,儒家明显表现出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的确,“先王”之后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封建君主利用孝道巩固皇权的历史。古典儒家思想中的这种“厚古薄今”的态度,在孟子那里有极为典型的体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1](《孟子·告子下》)同时他又认为:“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1](《孟子·滕文公下》) 其实,在儒家之外,也一直都存在着破斥历史中上演的政治化的礼教“孝道”的声音。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庄子·盗跖》直斥孔子为“鲁之巧伪人”,“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他们都是针对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孝悌精神的“异化”状况来作出批判的。也许老庄都会赞同,孝悌乃“为仁之本”,然而,他们都看到了,当孝悌被利用为博取封侯富贵之工具时,则仁之本失,民之朴善,性淫德败,所谓孝悌,名不符实,确乎乱天下之具。 在儒家关于孝治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表面上相似,实际上大相径庭的思想路径:其一是“仁孝”的逻辑;其二是“忠孝”的逻辑。前者强调孝悌为仁之本,仁是孝悌之推展;后者则论证孝悌——亲亲为忠君之基,孝亦是忠,而忠君乃孝之至。按照这种忠孝的逻辑,孝悌之道欲贯通于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必须要将君臣关系转化为某种特殊的“父子”关系。《大学》欲证君为民之父母,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又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孝经》借孔子之口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从历史上看,孝道的实践形态及其命运在庙堂与乡党之间颇有不同:孝悌之道被朝廷利用而为君主专制礼教服务的历史,实为孝道被皇权玩弄和扭曲之相,而民间乡土社会依然保有孝道的纯真表现样式。在漫长的民众生活史中孝道虽受诸多污染,却仍有真实的乡土社会生活的实践。 尽管古典儒家思想家看到了在仁孝与忠孝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的裂缝;尽管他们也深知存在着君主扭曲仁孝,并利用忠孝的逻辑为皇权的利益服务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主张,一种孝治的乌托邦是很有意义并且是可能的。因此,儒家仍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愿望而强调:孝悌之道,切近而平易,值得遵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在先秦的儒家政治哲学中,“家”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单位。“家”的观念,也是中国古典政治理念的一个基本范式。这种政治思想以家庭生活的经验为基础,来理解作为家庭成员的具体的个人及其多重角色——父子、夫妇、兄弟,同时也以家庭为模型来理解“(邦)国”和万邦共处的“天下”,即把国家和天下视为更大的家庭。很显然,在这种政治思维中,不存在一种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国家也不是这些原子化的个人们所订立的“契约”。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政治思维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家庭,因为,具体的个人是根据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和相互关系来定义的,而国家和作为国际共同体的天下,只不过是外延扩大了的家庭。正如孟子所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孟子·离娄上》) 《大学》认为,齐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无非就是孝、悌、慈。更进一步讲,齐家之道同时也是平天下之道:“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这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于“家”的政治属性和作为基本政治单位的重要性的界定。从具体的政治实践来看,首要的政治事务和核心内容就是治理家庭,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睦有序,使家庭生活幸福安康。孔子甚至认为,政治之至平凡而至显著者,即是在个人日常生活中躬行孝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论语·为政》) 六、孝道与乡土社会的重建:一个现代议题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孝道伦理及乡土社会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传统孝道的自然基础是家庭,一种以血缘关系将长幼代与代之间的生命历程连接起来的生命共同体。这种作为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原型”。在儒家的观念中,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整个天下,都可以理解为某种扩大了的家庭。基于这种“家庭”共同体主义的理解,儒家所理解的个人也不同于现代个人主义所昭示的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儒家的伦理思维从具体的个人出发,这种具体的个人具有自然的生命历程和血缘关系;随着其生活的展开,这种具体的个人在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中扮演着一系列角色。除了包含这种独特的关于共同体与个人的理解之外,传统孝道与乡土社会生活方式也昭示了一种超越“交换价值”主宰的全面的价值观体系,它以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和关怀,共同体的和谐与幸福为核心价值。 现代老龄社会从中国传统孝道伦理及乡土社会生活方式中能够获得多方面的启示,其中最主要者有三:一是孝道伦理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地反思个人主义伦理的参照系;二是展示了一种关爱与尊重生命的价值的生活方式复兴的希望。从而使我们能够重建被交换价值观的僭越(殖民)所扭曲了的价值世界;三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复兴孝道与乡土社会的养老习俗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找到现代养老问题的化解之道。 首先我们从诊断的角度为现代的老龄化问题及其根源略作观察:现代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往往伴随着成年人的两性关系的“灵活性”、单亲家庭、青少年犯罪问题、教育的功利主义(培养生产者与消费者,重技术轻德行)等一系列问题。它们彼此关联,不可孤立看待。然而,上述众多问题产生的根源皆与家庭及社区共同体的衰落有关。 现代社会流行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念,强调个人是构成世界的原子,而且这种原子是彼此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几乎绝对的自由。个人主义的这种观念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社会方面表现为家庭的岌岌可危、代际关系的扭曲;经济上则是市场交易关系的盛行,以及作为市场“保姆”的福利国家制度的膨胀;政治上则导致片面强调个人权利的乌合之众加政客的“民主”游戏的出现;意识形态上则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道德观念、过度膨胀了的交换价值观,以及拜金主义的宗教精神。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契约化了的世界,个人契约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成功统治,也恰是现代社会分崩离析、认同危机、人情冷漠、人性扭曲、人的价值贬损的根源。由此看来,老龄化问题牵涉到观念、制度与伦理等多个层面,其化解之道也就在于在这些层面做出相应的变革。 现代老龄化社会的困境,暴露出现代社会从个体出发组织共同体的悖论:现代家庭人际关系的“扁平性”的“平等”对正常的代际伦理秩序的破坏,现代家庭中的“个人契约”夫妇关系的脆弱,现代生活方式对民间“社会资本”的破坏,以及“福利国家”与市场体系之间的自相矛盾。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向是:通过复兴儒家“理想主义”意义上的孝道和乡土社会生活方式来改造现代社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一种创造性的智慧恢复和重建信仰上的祖先崇拜、敬老习俗和礼仪;以及重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关系与伦理原则;重建老人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方式;重建由这种健全的家庭所扩展而成的乡土社会。 这种变革涉及到:第一,自我意识从个人主义转向共同体主义,这意味着家庭及其孝悌伦理的恢复,以及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这种特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第二,孝道礼仪和乡土习俗,如乡射礼、乡校、乡饮酒礼、家礼等礼俗,经过创造性的转换而在现代社会“复活”。这将既是对这些礼仪传统的继承,又是因时因地制宜有所“损益”的创新。第三,教育上的相应变革,以教导和传播根源于孝道伦理智慧和乡土社会生活传统的新的价值观、伦理原则、道德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这种变革所期望的目标,是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主义与合理的个人主义的互补,是人性的自然体现与自由发展的有机统一。 收稿日期:2014-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