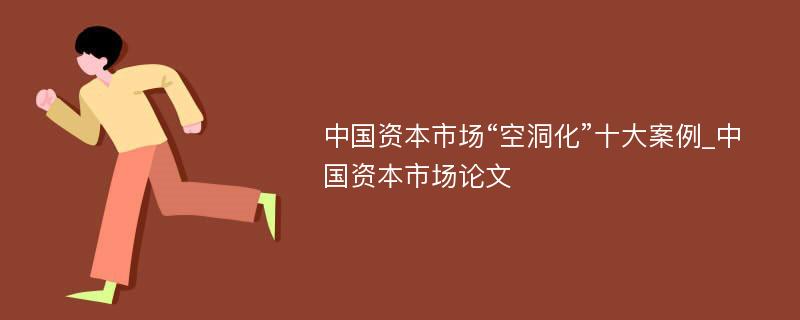
中国资本市场十大“掏空”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中国资本市场论文,案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触目惊心的十大案例
由于缺乏一定的定性定量标准,同时,由于情况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我们至今无法对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所说的
“一批实际上被掏空了的上市公司”的全貌作出全面的客观的数量反映,但从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掏空了的上市公司十大典型案例来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确实是十分令人触目惊心的。
(一)济南轻骑的大股东轻骑集团居然以其高达25.8亿元的巨额欠款,创下了中国证券市场“拖欠”之最。1993年公司改制上市时,轻骑集团作为发起人投入的部分资产至今未过户。公司首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就有3亿元被三大银行强行扣下替轻骑集团还债。1999年11月15日,因违规炒作股票,轻骑集团
董事长张家岭等三名有关责任人员被认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一枝动,百枝摇。禁入令迫使张家岭交出所兼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职务,上市公司与集团公司的“三分开”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令一向讳莫如深的大股东欠款问题浮出水面。尽管轻骑集团先后多次以房产、股权等资产来冲减对济南轻骑的应付款,但截至2000年12月31日,公司对轻骑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的应收款项总额同比反而增加了66858万元,增长幅度达33.06%,应收关联单位欠款高达25.59亿元。这种近乎于竭泽而渔的做法,导致一家曾被誉为绩优股的上市公司,最终沦落为“亏损大户”。
(二)2001年8月28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三九医药正式立案稽查。经查,截至2001年5月31日,三九医药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96%,严重地侵占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直接威胁到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三九医药于2000年3月9日上市,实际募集资金16.7亿元。据该公司一份公告披露,早在1999年12月8日,公司就与第一大股东三九药业签订资金借用协议,根据该协议,1999年公司累计向三九药业提供借款本息共计2.79亿元,2000年度为4.16亿元。在2000年年报中,三九医药对三九药业的其他应收款为6.9亿元,2001年中报显示公司期末应收账款8.28亿元,无应收大股东款项,仅有一笔应收关联单位三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货款1300多万元;期末其他应收款9.49亿元,其中大股东欠款5.63亿元。大股东占用的资金藏哪儿去了呢?2000年年报的注释给出了答案,原来在15.8亿元的其他货币资金中,主要是一笔11.4亿元的定期存款,公司把它存在关联单位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这笔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没有放在银行存款科目而列入其他货币资金,说明公司对这11.4亿元资金拥有直接支配权,这个支配权其实是属于三九集团的。三九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深圳三九药业100%股权,直接和间接持有三九医药73.39%的股份。
(三)1993年上市的猴王股份是全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也是焊材行业迄今为止惟一一家上市公司。可是,这家曾经创出焊材年产销量达7万吨、综合经济效益连续几年居全国同行业第一的上市公司,却因为上市以来一直处在母公司猴王集团的完全控制之下而深受拖累,猴王对集团的应收款至少有8.9亿元,外加担保3亿元,尤其令人称奇的是,集团甚至可以随便用上市公司的名义为自己贷款,并且一贷就是3个亿。1999年猴王股份终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达6770.20万元的亏损,每股收益为-0.22元,净资产收益率-20.32%,每净资产仅1.10元,调整后只有0.96元。2000年亏损额由上一个会计年度的9523万元,增加到6.8亿多元,每股收益也由-0.31元增加到-2.28元。2001年2月27日,它的母公司猴王集团突然被宣布破产,猴王集团欠下猴王股份的近11亿债务付诸东流,猴王股份还因为集团承担的逾2亿元的担保及自身的上亿债务而被三大债权人申请破产。
(四)东海股份第二大股东农工商东海总公司欠了上市公司5.21亿元,其下属的万隆房地产公司更欠了6.97亿元。这些巨款的来龙去脉同样令人称奇。至1999年12月31日,公司当期净资产仅为4.45亿元。原来,东海股份从银行贷款,转手再借给大股东和关联企业,然后一手向银行支付利息,一手向大股东收资金占用费。在东海股份的身上,充分显示了上市公司对大股东的某种“融资”价值。而东海股份居然一度以这种奇特的“融资”为生,靠利息差拼凑利润。然而,到1998年,大股东再也交不出所谓的资金占用费,也还不出钱。这条“融资链”断掉了,留下12亿元巨债压在东海股份身上,成了东海股份的“噩梦”。据2001年中报披露,在大股东占用的资金中,还有一部分是1996年和1997年发行B股和A股募集资金。其中被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占用9069万元,海南大东海旅业股份有限公司占用1350万元,占公司这两年募集资金净额12405万元的83.99%。
(五)2001年6月13日,PT粤金曼被终止上市。这家曾经享有过“世界鳗王”盛誉的上市公司盛极而衰的历史应从那笔10亿元的欠款说起。从1996年开始,粤金曼被它的控股股东金曼控股集团长期挤用资金达10.1253亿元。控股公司多次利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向外投资,最多的时候投资的企业达到了20多家,其操作办法更是匪夷所思:先以集团的名义投资,但用的却是粤金曼的钱,等项目成熟了再由上市公司收购,列在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关联企业,每年都在增加。一个与台商合资建立的微电子厂,开工不到一年,就停止了运转,两亿元就这样打了水漂。当一个个项目纷纷落马时,金曼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粤金曼已经对大股东和关联企业的欠款计提了近10亿元坏账准备,比其总资产还要高。该公司也因此成了两市资不抵债最严重的公司之一。而当粤金曼踏入PT行列之际,金曼集团却已悄然从上市公司退出,其留给上市公司10多亿元已逾期的短期借款,令欲对公司重组的新股东束手无策。“世界鳗王”的血是被大股东抽干的。
(六)2001年6月上旬,交通银行长春分行因怀疑吉发股份贷款可能形成巨大风险而提起诉讼。实际上,吉发股份资产空心化的现象已是事实。据2000年报,吉发股份第一大股东———吉林省开发建设投资公司欠吉发股份款项达3.16亿元;同时吉发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担保合计4.57亿元,公司自身有息负债合计6.34亿元。由于第一大股东财务状况恶化,公司对第一大股东的3.16亿元账面债权与4.57亿元账外潜在债权,合计7.73亿元债权已发生重大危机。即使抛开吉发股份自身的6.34亿元债务不说,一旦其第一股东宣布破产,吉发股份势必受连带影响,难以逃脱资不抵债的厄运。
(七)大庆联谊1999年报披露,其第一大股东大庆联谊石油化工总厂欠上市公司应收账款2429万元,其它应收账款高达5.96亿元。2000年报显示,该大股东所欠公司债务仍达6.02亿元。中国证监会在对大庆联谊欺诈上市案的处理决定中,责令其大股东在6个月内将所占有的募集资金4.8亿元归还上市公司。然而,时限已过,大庆联谊石油化工总厂依然故我,认账不赖,还钱没有,要还就拿一大堆破烂资产来顶债。2001年5月29日,大庆联谊披露,联谊总厂拟以资产和现金总计2.9亿元偿还欠款,偿还后尚欠大庆联谊应收款3.12亿元。而据此前的另一则公告披露,拟用以抵债的资产总计3.6亿元。大庆联谊失去的是白花花的现金,得到的却是天知道效益怎么样的宾馆、酒店、沥青厂,还有写字楼。
(八)棱光实业是被担保拖入泥沼的。截至2000年中期,棱光实业为大股东恒通集团担保达4.17亿元,而棱光实业自身的净资产不过1.47亿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谁也不知道棱光的担保到底有多少。棱光董事长一职长期由恒通集团的总裁兼任,这使棱光为大股东担保变得十分随意。直到1999年2月棱光董事会开始清理这一切时,清理者才惊讶地发现,担保像山洪暴发一般不断涌现出来,而绝大多数担保不要说没经过董事会讨论,甚至董事会根本就不知道。截至2000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恒通集团及其子公司金额高达34857.64万元,其数额已超过公司的净资产。截止到2001年6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已核定的总额为人民币53773.1589万元、美元159.8万元,起诉涉及金额人民币44627.1589万元、美元159.8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系前期遗留的为大股东及其子公司所作担保。
(九)幸福实业冒出了这样的咄咄怪事:上市公司的2.5亿元资产被集团私自拿去抵押,三年来公司居然不知情。被抵押的这部分资产几乎是幸福实业目前全部的经营性资产。ST幸福2001年2月7日公告称,称查出幸福集团用公司24978.51万元的资产作抵押从中国农业银行潜江市支行获取最高贷款限额19050万元的问题。被抵押的资产包括:幸福实业服装厂的部分财产和部分房地产;公司全资企业幸福实业铝材厂的机械设备与房地产;公司子公司幸福电力公司的输、供电设备等。另外,幸福集团还将公司参股企业幸福包装制品厂和幸福大酒店进行了抵押。幸福集团在掏空上市公司后,自己也早已运转不下去了,甚至在1997年以后就再没到工商登记机关进行企业年检,丧失了继续经营的资格,并在2000年被迫将第一大股东拱手相让,自己退居第二。刚刚易主的幸福实业眼看收款无望,只好将对幸福集团的1.66亿元应收款全部提了坏账准备,公司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亏损。这次被私自抵押的2.5亿元资产如追讨不回来,将更是雪上加霜。
(十)由于大股东长期占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不还,春都股份将春都集团告上了法庭。1998年12月,春都募集资金4.098亿元。但由于春都集团在把春都股份推上市之前贪大求全,四处出击,已经背上了不少债务。尽快上市募集资金成为春都集团解决债务问题的首选办法。作为独家发起人,春都集团迫不及待地把募集资金抽走。春都股份上市仅3个月,春都集团就提走募股资金1.8亿元左右,以后又陆续占用数笔资金。2年多时间下来,大股东占用资金达到2.5亿元。如果再算上其他关联企业占用的资金,春都被占资金高达3.3亿元。这意味着,拥有62.50%股份的大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所占用的募股资金和生产资金,相当于全部募集资金的80%,致使春都股份募股时所承诺的十大肉制品投资项目,九个不见踪影,仅有的一个低温肉制品项目,计划年产量3万吨,而实际生产还不到3000吨。被大量“抽血”的春都股份在力不能支的情况下,2000年跌入亏损行列。而春都集团占用的募集资金除了填补过去的资金窟窿以外,其余的又盲目投入到茶饮料等非主业项目,新建的项目也无一盈利,旧账未了新债又添。春都股份和春都集团双双陷入困境。
易如反掌的八字绝招
大股东是如何掏空上市公司的?说起来令人吃惊,做起来不过八字诀而已,竟然如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一样容易。其一,“截”字诀。作为发起人,大股东在截留募集资金上占有先天优势。事实上,许多上市公司在上市前不要说没有独立的管理,甚至根本就没有独立的财务,募集资金到位后,实际上完全由控股大股东在支派,在那些为上市而改制分拆出来的上市公司更是如此。大股东
利用代为管理募集资金之便,截留募集资金以为已用。春都集团就是这样,由于贪大求全,四处出击,春都集团在把春都股份推上市之前已经背上了不少债务,尽快上市募集资金成为春都集团解决债务问题的首选办法。作为独家发起人,春都股份上市仅3个月,春都集团就提走募股资金1.8亿元左右,以后又陆续占用数笔资金,累计高达3.3亿元,相当于全部募集资金的80%。春都的情况或许还算不上最严重的。东海股份1996年和1997年发行B股和A股募集资金,被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大东海旅业股份有限公司占用10419万元,占公司这两年募集资金净额12405万元的83.99%。而2000年3月才上市的三九医药,实际募集资金16.7亿元,而被大股东截留占用25.8亿元,占用比例竟然超过154%。
其二,“挪”字诀。大庆联谊上市时募集资金4.81亿元,计划投向四个项目。当年年报中,公司谎称这些项目进展顺利。1998年报中,这些项目有的被取消,有的被改建,有的交给了大股东却并未按计划投入。而在1999年报的“投资”一栏中,再也没了募资项目的踪影,公司索性“坦言”相告:“前次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挪为他用!”在常人想来,上市公司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条件下将资金委托集团母公司代为实施是很正常的事,如果集团母公司尽到责任,倒也无可厚非。可惜的是事情的结果非但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不是像大庆联谊那样资金被挪作他用,就是被擅自变更资金投向。曾以36.68元的破纪录价格发行了核准制下第一股的用友软件公司近日宣布,其筹集到的9亿多元资金中,有3亿元投资国债。今年4月底用友的董事长王文京在谈到用友刚刚以天价融得的巨资时,信誓旦旦表示,公司早在两年前就进行了投资项目论证,已通过政府审批的项目资金缺口是8.03亿元,此外还有正在谈判的项目和拟议中的软件厂商收购等,9亿多筹资有明确的去处。言犹在耳,巨额资金已用作他途。
其三,“垫”字诀。我办事,你付款,甚至比从自家口袋掏钱还要容易。北大青鸟入主北京天桥以后,青鸟天桥成了大股东的付款机,大股东负责设计开发投资项目,上市公司负责付款。据2001年中报披露,两年多来,青鸟天桥作为长期股权投资付出的资金达66456.63万元,大大超过了公司在1999年股权重组前6年的投资总和。实际上,这个数字尚未包括上半年已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四项投资,如果加上这四项投资,青鸟天桥的长期股权投资总额将近8亿元。在上述投资中,一部分属于北大青鸟置入资产业务的延伸,如北大青鸟商用信息系统;一部分是为了配合北大青鸟投资10个省100个市广电网络系统的扩张目标,据统计,到目前为止,青鸟天桥对广电系统的投资约3.2亿元;还有的是为了配合大股东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本运作,最突出的是2000年6月15日收购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和2000年3月份参股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7.89%股份,从而使北大青鸟控制的上市公司由一家扩展到三家。
其四,“借”字诀。早在1999年12月8日,三九医药还没上市,公司就与第一大股东三九药业签订资金借用协议,根据该协议,1999年公司累计向三九药业提供借款本息共计2.79亿元,上市后,账面反映出来的2000年度借款为4.16亿元。实际“借用”数当然远不止此数。东海股份的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从银行贷款,然后再转手借给大股东和关联企业。就这样,第二大股东农工商东海总公司欠了上市公司5.21亿元,其下属的万隆房地产公司更欠了6.97亿元,12亿元巨债压在东海股份身上,成了东海股份的“噩梦”。有的大股东表面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连续不断的短期借款只是为了使账面上无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而已,这并不能掩盖大股东占有上市公司资金的本质。根据托普软件与托普集团公司签订的资金使用合同,托普集团公司使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金按月末平均占用额及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年6%利息支付资金使用费,2000年公司共计收取占用资金利息1281.60万元;2001年1~6月共计收取利息760万元。换言之,托普集团这两年所占用资金大约为21360万元和25333万元。可是,在历年的年报中,托普软件均以一句无持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欠款搪塞了过去,未予披露。
其五,“套”字诀。关联交易是大股东套取上市公司资金最为常用的手法。上市公司及其关联股东出于利益的驱动,使得关联交易不断升级,而关联交易是抽血机。棱光实业自1994年由恒通集团入主以来,几乎每年都是靠跟大股东的关联交易粉饰财务报表,尤其是其花了1.6亿从恒通收购的电能仪表公司,通过托管每年保证不低于2193万元利润,成为棱光实业收入的一大重要支柱。可是1998年1~11月该公司税后利润仅1102万元,远低于原先双方约定的协议底线,于是恒通又以经评估后净资产2.21亿元的价格回购该公司全部股权,使棱光不仅获得一笔投资收益,还能享受该公司当年1~11月的净利润,从而又占了一个大便宜。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事实上恒通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几年来从棱光套走了8亿多元的资金,还留下了一大堆官司。资产置换是又一种套取资金的绝招。ST粤海发1998年一项重大资产置换,获得投资收益3537.7万元,其实是大股东深圳粤海玩弄的“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其置换给粤海发展的苏州一物业是个并不拥有产权的“空壳”,而这一“空壳”及另一笔实际未拥有的债权合计算了7000万元,一来二去,粤海发展还欠其3000余万元。不仅如此,ST粤海发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还借此拖欠各项借款1.2亿元,并为它们提供各项担保2.6亿元,截至2000年底,该控股公司在已经退出以后,还有拖欠款7000余万元挂账未还。比资产置换更为直接的套钱手法是以物易钱。五粮液通过向大股东购买无形资产商标使用权,一次就付给大股东9780万
元。这是其继2000年花16.57亿元现金支付置换大股东窖池等酿酒资产的差额之后,又一次向大股东贡献巨额资金。
其六,“赖”字诀。1993年济南轻骑改制上市时,轻骑集团作为发起人投入的部分资产至今未过户。公司首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又有3亿元被三大银行强行扣下替轻骑集团还债。但长期以来,在轻骑集团铁腕统治下,对大股东赖账不还谁敢说个“不”字?ST港澳、PT网点、西藏圣地、渤海集团等发起人股东的发起人股打白条,闽福发、活力28配股打白条等,无不如此。渤海集团大股东当初以土地使用权出的资,大股东却未支付土地转让金,令渤海集团至今未能取得土地开发权和转让权,大股东等于向上市公司打了白条,然而,这个官司竟至今没法打赢。
其七,“蛀”字诀。由于大股东内部人控制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不少上市公司被公司内部少数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了他们肆意侵占公司资产财物的乐土。在1997年以前每年尚有几千万元净利润的琼华侨,自1998年起突然出现了巨额亏损,并连亏三年,进入了PT行列。近期披露的由北京科企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李士祥的离任审计报告证实,李士祥在担任琼华侨总裁期间,“大肆挥霍损害国有利益和股东利益”,个人侵吞资财达4000多万元。前任董事长赵锴在任职期间也存在违规炒股和非法侵吞公司资财等严重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琼华侨的问题不只是出在公司高层个人身上,它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病的综合反映。公司高管不是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而主要是对各自代表的股权单位负责,这就造成了四面八方的大股东分割蚕食公司利益的严重局面,也给某些个人侵吞公司财富提供了可趁之机。近期,个别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由于对当事人收购资金来源,收购定价方式和付款方式等关键问题不够明晰,存在暗箱操作嫌疑,客观上有可能为内部人蚕食上市公司资产和侵占其他股东权益提供方便。
其八,“卸”字诀。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做担保,好比两手提篮,左也是篮(难),右也是篮(难),一旦借方无法偿付债务的时候,作为提供担保的保证人或第三方就负有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这是《合同法》和《担保法》所规定的无法推卸的一种法律责任。近年来,棱光实业、ST金帝、国嘉实业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所持法人股一度成为拍卖对象,而且都是由于大股东以股权质押向银行贷款逾期未还而引起的。虽然在法院判决并委托强制拍买变现时均告流产,但其中种种复杂的内幕足以表明,由于大股东事实上存在推卸责任的故意,事情远未结束。棱光实业和ST金帝的有关巨额担保、贷款都没有严格按规范进行运作,或者仅由董事长签字确认,或者仅由原公司负责人私自将巨额转让款返贷,不言而喻,其中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至于担保如果涉及到欺诈蒙骗,那更是坠落黑洞,风险难测了。成都联益第一大股东广东飞龙持有5474.56万股法人股,占总股本40%,其股份现已全部冻结。据第二大股东、原第一大股东成都联益集团控告,这些股份是广东飞龙向其诈欺所得。广东飞龙窃得第一大股东地位以后,伪造公司董事会决议,私刻公司法人公章,为广东飞龙高速客轮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海珠广场支行贷款100万美元提供虚假担保,导致其所持成都联益法人股险遭拍卖。
如出一辙的四大症结
为什么会出现掏空现象?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具体的案例告诉我们,种种掏空现象所反映的四大症结,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股独大”的机制。
(一)“一股独大”造成治理结构形同虚设
截至2001年4月底,沪深共有上市公司1124家,其中发行A股的公司1102家,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占公司总股本50%的有890家,约占全部公司总数的79%。第一股东为国家持股的公司,占全部公司总数的65%。以目前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含国有法人股)2500多亿股计算,所占的股东权益值达7000多亿元,国有经营性资产(国有股权益总值)更高达6万亿元以上,这是决定上市公司行为易受国有控股股东的价值取向所左右的最基本的现实。在现有的制度下,国有股和国家利益混淆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使得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企业行为和国家行为混为一谈,使得控股股东得以拉大旗作虎皮,包装自己,吓唬别人。其实,我国国家所有权的虚化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目前,大多数国有控股公司在以国家所有者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同时,又以所在地区、部门等利益集团的独立利益作为自己的具体目标和价值取向,其所作所为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所有者全权代表的内部人离开委托人,追求小集体甚至少数领导人的利益,而作为最终所有者的国家的利益却不能得到体现。”
在上市公司的全部董事中,有73.3%的董事具有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的背景,其中前者占27.9%,后者占45.4%。股权高度集中,使得第一大股东利用控股地位几乎完全支配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平衡。由大股东掌控的董事会常常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控股大股东提名的董事、经理无不认为向提名股东负责是天经地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规范的三会制度,即使有独立董事的参与,即使有从外部聘请的空降兵———职业经理人,也无法改变大股东一手遮天的局面。吉发股份一年多以前就设立了独立董事,但是,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拖欠债务的行为依然故我,一直没有受到触动。据年报披露,截至2000年末欠公司款项计3.16亿元,比1999年年末增加了1.02亿元。同时,公司为该大股东提供巨额担保,总计26016万元人民币、1325万美元;为该大股东的所属企业贷款担保445万美元;为该大股东发行债券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2002年9月到期)。这为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以及财产安全留下了严重隐患。
(二)“一股独大”是“三不分开”的病根
PT粤金曼上市伊始,公司与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金曼控股一直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金曼控股的主要管理决策人员亦同时为PT粤金曼的主要管理决策人员,两者之间“资金统筹安排”,实际上是股份公司粤金曼的资金由母公司金曼控股“统筹安排”。从此,粤金曼便成了大股东的“提款机”。据披露,在近几年中,金曼控股占用PT粤金曼资金1998年末为7.10亿元,到1999年末9.95亿元,2000年末10.12亿。至2000年末,PT粤金曼在金曼控股控制下,为福建福曼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水产发展公司等单位的银行借款人民币54997万元、日元732003万元、美元42.24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大股东的侵权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其它股东的权益,也把PT金曼拖向了资不抵债的深渊。至2000年末,PT金曼三年累计亏损额为13.70亿元,每股净资产为-7.91元,股东权益为-10.62元,已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在上市公司的队伍里,由于“三不分开”而造成的类似这样的提款机何其之多!
“三不分开”的病根在于“一股独大”。为了约束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在关联交易和资金运用上的不正常行为,上市公司普遍强制实行了人员、资产、财务“三分开”。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上市公司采取资产置换的方式解除了大股东的债务。假如这种资产置换与公司的资源配置要求是一致的,并且是按照公平交易原则进行的,自然无可非议。但是,实际上,在大股东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指望通过形式上的“三分开”和资产置换来保障上市公司的独立权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以济南轻骑为例,轻骑集团先后多次以房产、股权等资产来冲减对济南轻骑的应付款。这些资产均没有经过评估,短期内也不能为济南轻骑带来效益,长期而言更没有保障,这意味着即使在所谓“三分开”的条件下,只要“一股独大”的情况未改变,济南轻骑依然不免成为大股东“丢卒保车”的牺牲品。
(三)“一股独大”使关联交易变了味
近年来,上市公司与关联股东主要是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盛行不衰。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4月21日,沪深两市共有1018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2000年报,其中发生各类关联交易行为的有949家,占样本总数的93.22%。此外,关联交易的形式各异,花样不断翻新,但总体上关联交易的利益天平总是倾向于关联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即使有时候似乎表现为对上市公司有利,那也是为了通过与大股东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掩盖经营上的问题,以保持再融资能力,归根结底也还是为了让大股东更
多地圈钱而已。
大量的关联交易,造成上市公司几乎丧失了独立经营的能力,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也不断下降。一些上市公司原本就是控股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或加工厂,而控股公司则成为上市公司的原料采购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一方面,上市公司向控股公司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形成的关联交易成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来源。统计结果显示,在公布2000年报的1018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47%的关联销售交易是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而且少数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销售收入来源于与其控股股东的关联销售交易。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向控股公司购买原材料、劳务及其他服务形成的关联购买交易构成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结果表明,在1018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34%的原材料、劳务等关联购买交易是发生在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还有一些上市公司同时存在着销售和采购两方面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神马实业等13家上市公司,其销售收入和原材料采购的50%以上都来自关联交易。
由于上市公司业务经营上独立性很差,对关联方存在过分的依赖性,导致其市场竞争力下降,而且造成上市公司与控股公司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方面不分彼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分开”根本无从谈起。控股大股东正是利用其控股权,在重大关联交易中以牺牲广大中小股东的正当利益为代价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广大中小股东又显得无可奈何。
关联交易给上市公司带来的只能是一次性、不稳定的非经常性收益,对企业的业绩增长贡献也只能是短暂的,难以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常性收益只能给上市公司带来一时的“痛快”,并不能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更有些上市公司为了保住配股的再融资资格,多年来不是在生产经营上下功夫,而是利用每年年底与大股东之间“突击重组”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来粉饰财务报表,勉强保住配股资格。
(四)“一股独大”导致资产重组迷失方向
在某些“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存在着非等价交易、自我交易、内部交易等问题,使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我国上市公司的重组,有着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同的特点。我国上市公司起源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存在于国有股“一股独大”,上市公司同政府的关系、企业的融资偏好以及上市公司重组的动因都有着相当的特殊性,这些因素无不在上市公司重组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为了利用上市公司这个壳从证券市场获取低成本、低责任的资金,“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重组中总是伴随着大量的自我交易。自我交易也被称为关联交易,即公司同自己的控股人、参股人、子公司或它们的下属企业进行交易,这种交易极易出现非等价交易和资产、利益转移的现象,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交易中的纠纷乃至欺诈。其中有一些优势企业通过这种“先予后取”的方法来搞欺诈性的重组,即先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然后通过配股或获得贷款,最后将资金转移或挪用。协议转让使小股东利益得不到保证。协议转让很容易使小股东失去选择和参与的机会,臭名昭著的郑百文重组就是这样,大债主和大股东凭着所占有的股份优势,竟然操纵股东大会,以决议形式确认默示原则,实质上连小股东的流通股份交易权也要彻底剥夺掉。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不利于以建立规范有效的治理结构和转换经营机制为目的的重组本身的规范进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重组大多数是围绕资产质量差、财务困难的企业来进行的,特别是ST板块的公司重组活动更是频繁,有些重组虽然暂时使股东权益有所改善,但由于重组的不规范,新入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可能会因此从股市欺骗性地获取更多资金并转移资金,使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受到更大的损害。收购四砂股份控股权的通辽艾思迪就是这样,它勾结作为原第一大股东的国有股东,在其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下,先行入主上市公司,甚至让上市公司出资购买其下属不良资产,然后将其拖欠和占用上市公司巨额债务转让给别的企业,巧妙地使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导致上市公司整整动荡了一年多,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
在一些重组案例中,“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常常将净值为负的“不良资产”以一定价格或者零价格转让给控股母公司,从而咸鱼翻身,而有的控股母公司在本身没有偿债能力的情况下充当劣质资产大仓库,无非是钻债权保障法律不完善的空子,以此废逃银行债务。截至2001年中报结束,老PT公司全部中期扭亏盈利实现“胜利大逃亡”———获得宽限期暂缓退市。即使撇开其业绩的真实性不谈,值得注意的是,仅仅靠非经常性损益收入和降低费用来“苟延残喘”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老PT公司基本上由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债台高筑,巨大的财务费用将吞噬掉利润,在重组后的主业盈利没有根本解决的前提下,如果一味依靠降低费用和非经常性损益来获得宽限期,那么,最后将由谁来为其买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