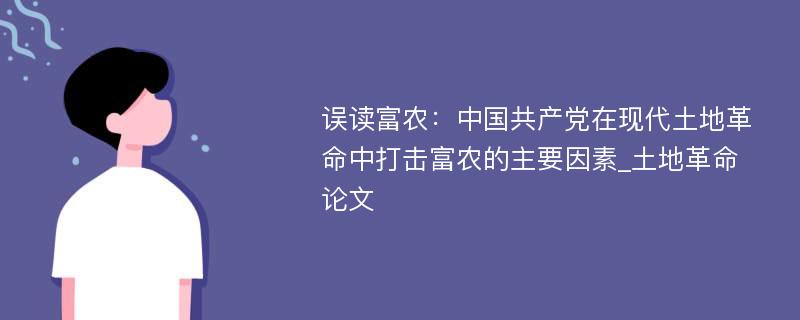
误读富农:中共在近代土地革命中打击富农的主要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农论文,土地革命论文,误读论文,近代论文,主要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鼓励和扶持农村家庭农场,努力提高农户的集约经营水平。近代的富农经济即是家庭农场经济。富农是近代乡村家庭经营集约化程度高、生产能力强的社会阶层①,是农业现代化的最早发起人②。富农经济虽然仍旧采用家庭经营方式,也不是完全以满足市场需要而生产,但是,它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成分和进步的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是应该予以保护的③。但是,在近代土地革命中,由于中共对富农认识和富农政策的失误,导致富农阶层在土地革命中屡遭打击。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富农问题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富农的界定、阶级性质、富农经济的发展及富农与乡村社会关系等问题④。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对富农问题的反思,比如杨奎松针对过去学术界总是把地主和富农问题放在一起研究,他主张把地主和富农区分开来,探讨“富农”的由来、富农由“资产阶级”变成“半封建半地主”等问题。这种反思对认识近代中国富农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⑤,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深入思考富农生产经营特点及中共富农政策逐步趋向激进的基本动因,因此,很难挖掘出近代中共打击富农的深层次原因。而学术界过去在解释富农遭受打击的原因时,往往以党内的“左”倾错误作为理由。本文认为,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屡遭打击的主要因素,用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因此,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反思了富农遭受打击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其主要因素在于中共的误读,而这种误读恰恰是近代乡村土地关系和中共土地革命的必然结果。
一 富农生产经营的主要特征
要研究中共在土地革命中对近代富农的误读问题,首先需要分析富农所占的比重及其生产经营的基本特征。关于富农在近代乡村社会各阶层中所占比重问题,过去人们常常把地主和富农放在一起,因而无从知晓近代富农所占的比重到底有多少。根据相关研究可知,近代中国除少数地方没有富农外,其比重大体在0.6%~20%之间⑥。
在为数不多的富农中,到底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呢?根据相关材料可知,农业生产是富农的主要经营事业,而部分富农家庭还采取主副兼业方式。农业生产作为主业,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方式,即全部耕种自己土地的自耕富农、耕种自有土地外还需要租入部分土地的半自耕富农和全部耕种租入土地的佃富农⑦。富农在乡村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其生产经营规模却比较大。1933年广西22县48村富农经营占农户经营总数6.4%,所使用土地面积达全部面积9.8%;1933年广东番禺10村富农经营占经营总数12%~13%,使用农田占33.9%;1933年河南省辉县4村富农使用土地占全部土地42%、镇平6村使用土地占26.5%、许昌5村富农使用土地占全部土地20%,据估计近代富农使用土地大概占全部土地的20%⑧。与乡村其他阶层相比,富农生产经营规模大尤为明显。1933年广西省22县48村共有2705户,其中,92户地主平均每户占有土地75.1亩,使用土地28.3亩;173户富农平均每户占有土地30.9亩,平均每户使用耕地30.9亩;557户中农平均占有土地12.1亩,每户平均使用土地16.6亩;1883户贫农平均每户占有土地2.7 亩,平均每户使用土地5.6亩⑨。由于富农经营土地面积大,需要人工较多,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有时雇佣少量的长工,在农忙时节还会雇佣一些短工。苏北萧县9村富农大多雇佣2~3个长工,农忙时再雇佣大批短工⑩。黑龙江省拜泉县时中区126户富农,平均每户耕种土地30晌,需要雇佣长工3~4人,在农忙时节还需雇佣大量短工(11)。而且富农还是农村各阶层中拥有耕畜最多的阶层。在广西省22县24 村中,37 户地主平均每户拥有耕牛2.30头,83户富农平均每户拥有耕牛2.75头,280户中农平均每户拥有耕牛1.74头,912户贫农平均每户拥有耕牛0.82头(12)。富农家庭不仅耕畜数量多,而且质量和品质较好。辽宁农村主要有牛、马、骡、驴四种耕畜,其中富农拥有牲口主要是骡和马,它们不仅喂养得很好,长得也膘肥体壮,干起活来顶事;而中农贫农的耕畜则以牛、驴为多,不少牲口是瞎、跛和瘦弱的(13)。
富农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外,有些还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兼业。如近代苏北启东大多数富农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还兼做商人,甚至有的还兼营高利贷(14)。苏南富农在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在农闲时则多转向家庭副业,包括栽蚕养桑、捕鱼、务工、编织竹器、土产贩卖、土布纺织、家庭饲养业等(15)。华北富农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经营手工业、副业和商业,其中手工业主要是榨油、酿酒、制粉、米店、棉行;家庭副业主要包括小买卖、猪毛加工、熬硝盐、食品加工、工匠手工业、家庭纺织业、编织、家禽家畜饲养等(16)。成汉昌在总结近代富农生产经营特点时指出,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也有的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或者自己完全没有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他们大多数拥有较好的生产工具和一定数量的资金,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雇工劳动(请长工)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此外,富农采用兼做农产品加工、销售及其他副业或商业(17)。
二 中共对富农认识及富农政策的演变
随着中共土地革命的兴起,富农常常与地主纠结在一起,成为土地革命打击的主要对象。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提出,农民分为佃农、自耕农和半佃农三种,它们还可以分为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富农虽然很少,但在农村中颇有势力,一部分富农与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土豪劣绅一样是农村中的剥削者(18)。
1928年中共六大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农民根据经济状态及土地占有情况,可以分为富农、中农、小农和最小农等几个阶级,富农有许多是半地主。中共中央又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富农在反对军阀、地主和豪绅等一切封建剥削的斗争中,还可以结成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当农村斗争深入到土地革命之时,富农常表现为消极、中立或仇视的态度,最后滑入反革命的阵营。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之际,中共应吸收富农加入到农民反军阀、反地主和反豪绅的斗争中;凡是富农已经成为反动力量的地方,反富农斗争应该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19)。同时,中共中央又认为,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贫农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因此,在革命斗争对象还是军阀、地主、豪绅的时候,不要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20)。1929年2月《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指出,富农在反对地主阶级斗争中常常可以参加革命,而当农村实行土地革命时候,富农就会发生动摇,形成同情革命、反革命和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三种不同的态度。对于同情革命的富农,必须吸引到反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已经反革命的必须在反地主反军阀斗争中同时反对富农;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就不必故意加紧斗争,但要特别同时准备反富农的斗争(21)。同年8月《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使农民急剧破产,促进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大多数农民日益贫困,而少数农民成为了富农。富农有了资本便土地出租和投资高利贷,而不是扩大农业经营,因此,富农一般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半封建半地主性的富农,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往往是动摇妥协的,甚至会成为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是坚决地反对富农(22)。反对富农“是没收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即取消富农的高利贷没收出租部分的土地,其余富农的土地财产不没收”(23)。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共认为富农有半地主性、资本主义性和初期性三种形式,反对富农的策略不仅可以应用到“半地主的富农”身上,还可以应用到“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和“初期性的富农”身上(24)。中共执行反对富农政策,而地方政府和一般民众很难分清富农与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非封建剥削成分的区别,因而他们在反对富农斗争过程中,把富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一概没收。“凡属地主阶级、公共祠堂、庙宇以及富农的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房屋、山林、如竹山、茶山,凡可分而为贫农群众要分的,一概平均分配。”(25) 反富农斗争的过火行为使中共意识到必须对反对富农做出明确限制,反对富农是在经济上限制富农各种方式的剥削,不是“打”富农,更不是反对某一个富农。我们只有限制富农剥削,才可以限制富农私人资本的发展。如果只“打”某一个富农,而未打击新生的富农,这样是不能达到限制私人资本的目的,反而失了反富农的意义(26)。而“过去各地政府都采取打土豪方式去打击富农,如派款、罚款、逮捕等,甚至看人家买猪肚子而指为富农,这样只打击富农个人的方法,结果不独富农恐慌,一般中农因受富农煽动,也同样发生恐慌,以为苏维埃政府不容许农民有一点存积,这样是会使苏维埃脱离群众,而且妨碍社会生产”(27)。
1935年12月15日,中共开始改变富农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部分之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种的,均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28)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还认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战争和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是,富农有一部分是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和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候,对富农的租息也要照减不误,同时要求人们交租交息,保障富农的人权、地权、政权和财权(29)。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调整抗战时期相对温和的富农政策,改变为更激进的政策。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能打击得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即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30)中共中央要求一般不动富农土地,有些地方干部在土改中强调照顾地主富农,要给他多留土地,要保证地主过富农生活,等等(31)。由于地方政府和干部要照顾地主和富农,土地改革很难推动,1947年7~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平分土地时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32)。但是,许多地方已经不是按照《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是“对富农和地主用一样的方法去斗,甚至要打死一些人,对地主甚至对富农一律用扫地出门的办法”(33)。不仅富农土地要拿出来进行分配,而且他们的牲畜、工具同样要拿出来分配(34)。不仅老富农土地财产可以清算,而且佃富农土地也是可以清算的,清算出来的土地由农会统筹分配。但是,中共对新富农还是主张保障其产权,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35)。然而,随着解放区土地革命向深度发展,中共保护新富农的政策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松动。华中局和华东局规定,平分土地时对新富农要“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36)。而实际上有些地方“新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都拿出来”(37)。由于各解放区存在着平分新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的要求,1947年11月任弼时在《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可否规定新式富农多余的土地,应当劝说他们自动拿出平分;对他们多余的房屋、粮食、财产、耕牛和农具,除自愿献出分给贫苦农民外,其他原则上不动,或者规定不准分配新富农除土地以外的多余财产(38)。尽管尽力维护富农这一农民阶层,但在革命浪潮下富农这个阶级还是要被“革掉”的。
三 中共对富农的误读
杨奎松认为,当年那些地主和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借权势盘剥欺诈而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却是经营生产能手。后来,台湾有不少地主富农被迫转向工商业,他们大都取得了成功;大陆那些因成分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在改革开放后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9)。杨奎松的反思是耐人寻味的。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产生许多可以重新思考的问题。其中,中共在土地革命中打击富农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在中共领导近代土地革命中,富农常常成为中国革命打击的对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过去常用中共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加以解释。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是富农受到打击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实则中共的误读才是富农在土地革命中屡次遭受打击的主要因素。
(一)阶级属性的误读。对近代中国富农阶级属性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富农虽然富裕,但仍属农民的范围;一种观点认为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一种观点认为富农比较接近于地主,属于半封建剥削阶级;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富农是介于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一个阶级(40)。中共在进行农村革命时,已经注意到富农的阶级属性问题。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41)。1928年中共六大开始改变富农是属于农民的认识,一方面认为富农是农民中的一个阶层,另一方面又强调富农雇佣工人(雇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42)。富农在农村中雇佣工人是否就是农村资产阶级呢?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富农雇工经营,不是利用土地进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剥削雇工,而是为了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因此,近代中国富农不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43)。1929年6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指出:“中国的富农,却少采用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而多是封建剥削制度的代表人。中国的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小地主,他们用更加残酷的剥削形式剥削中国农民基本群众。”(44)同年8月《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马上改变了富农是中国农村资产阶级的认识,并认为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阻碍着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富农有了资本就去购买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而不愿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因此,中国富农兼具半地主半封建性(45)。1930年,中共党内提出了富农有三种不同形式:第一种是半地主性富农,就是自己耕种一部分土地同时出租一部分土地;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他们自己不出租土地,有时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工耕种;第三种是初期性富农,就是不出租土地,也不雇佣工人,但土地和劳动力充足,每年出卖多余的粮食和借出部分金钱。但他们对贫苦群众有三种共同的剥削方式,第一种是放高利贷和商业性出卖粮食;第二种是半地主性富农的地租剥削和资本主义性富农的雇佣劳动剥削;第三种是兼营商业,开设商店及贩卖产品,用商业资本剥削贫苦群众(46)。1942年7月张闻天在《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中认为,富农经济是农村资本主义(47),这无形之中又承认了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1943年春,薛暮桥在中共山东分局干部会议上所做的《中国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研究》报告中指出,农民在与地主对立的时候还有共同的利益,构成了一个阶级,但他们内部已经分化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富农耕种田地较多而劳动力又不够,必须雇佣长工和短工,所以他们的生产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富农是农村小资本家,不是小资产阶级;但因资本主义发展困难,有些富农让一部分土地出租,此时他们已经不是农民而是兼有小地主性质;有些富农还利用高利贷来剥削贫苦农民,或者进行其他各种封建性的剥削,这种富农不能够与一般富农(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同样看待(48)。由此可见,中共在分析富农性质时,强调了富农“资本主义性”和“半封建性”,由此完成富农从农民阶级——农村资产阶级(资本家)——半封建性半地主的理论建构。然而,中共在对富农阶级属性的理论建构中,对农民性、资本主义性和半封建性的强调是不同的。在抗战时期,中共突出富农的资本主义性,而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强调富农的半封建性,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提出初期性富农而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反而不再提及。中共对富农阶级属性的这种理论建构,其实就是一种主动性误读。
(二)对富农经济的误读。中共对富农阶级属性的误读,主要还是来自其对富农经济特点的误读造成的。在土地革命中,中共认为富农对贫苦农民剥削主要有土地出租、雇工剥削、放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剥削,我们认为富农四种“剥削”其实就是中共对富农经济的误读。
1.土地出租问题。“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49)中共认为富农出租一部分土地是为了剥削贫苦农民,收取封建地租。那么,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1933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发现,江苏省邳县6村富农租进土地596亩,无出租土地;盐城7村富农租进土地353亩,租出土地6亩;启东8村富农租进土地576.708亩,租出土地10亩;常熟7村富农无租进土地,租出土地20亩。除常熟富农有少量土地出租外,江苏省邳县富农使用的土地有50%是租来的;盐城富农使用的土地有17.5%是租来的;启东富农使用土地也有35%是租来的(50)。1933年浙江龙游8村富农租进土地93.2亩,无租出土地;东阳8村富农租进土地24.3亩,租出土地3亩;崇德9村富农无租进土地,租出土地53.0亩;永嘉6村富农无租进土地,租出土地21.0亩。浙江省龙游富农使用的土地中有16%是租来的;东阳8村富农使用土地约30%是租来的;崇德9村和永嘉6村富农多为自耕农,只有少量土地出租(51)。20世纪30年代,江苏、浙江两省富农除少数村富农出租土地外,多数村庄富农使用的土地都是自有和租进的。
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在山东农村调查发现,抗战以后莒南、赣榆县3区11个村富农,户均租入土地4.68亩;莒南大店、筵宾、沟头三区11个村富农户均租进土地17.9亩;沭水县石河区、临沭县蛟龙和大兴区9个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2.85亩;兰陵县台儿庄富农无出租土地,租进土地810.5亩,户均租进土地90亩(52)。山东富农抗战后租进土地比租出土地要多。
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在江苏农村调查发现,苏南16县964乡富农,户均出租土地2.4亩;青浦县朱家角薛间车乡车路村富农,户均租进土地18.4亩;江阴县长径镇新民1个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3.1亩;江阴县长泾区潼南乡4个村富农户均租进土地1.1亩;武进县戚墅区政成乡富农出租土地252.48亩,租入土地13.80亩;武进县湖塘区马杭乡富农出租土地213.92亩,租进土地1.90亩;无锡9个乡富农出租土地505.76亩,租进土地468.89亩;奉贤县第一区六墩乡和砂蹟乡2村富农出租土地77.420亩,租进土地212.425亩;嘉定县唐西乡富农出租土地237.48亩,租入土地212.50亩,户均出租土地0.42亩;嘉定县娄塘区塘东乡1个村富农出租土地3亩,租进土地17亩,户均租进土地2.3亩;无锡县张村区6乡富农出租土地163.6亩,无租入土地;无锡云林乡富农户均出租土地1.24亩;武进县梅港乡富农户均出租土地5.19亩;松江县新农乡富农户均租进土地10.9亩(53)。江苏富农户均出租或租进土地数不大,有少量富农大量租进。
1950年《新湖南报》社在湖南省农村情况调查中发现,湘潭县黄龙乡4保、宁乡县洋泉乡第8保、邵阳县震中乡第17保、衡阳市6区第6保富农户均出租土地5.19亩、1.1亩、8.9亩、3.4亩(54)。
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在福建农村调查发现,古田县七保村富农户均租入土地10.55亩(55)。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在安徽农村调查发现,皖南6个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12.15亩;南陵县戴镇村富农户均租进土地0.22亩;芜湖杨埠村富农户均租进土地14.49亩;岳西县北山村户均出租土地4.42亩;宣城县东里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22.23亩;宣城周王区金象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27.54亩;贵池县齐山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7.25亩;屯溪市隆新乡徐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18.79亩;当涂连云保富农户均出租土地5.00亩;贵池杏花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0.75亩;贵池馈口保富农户均租进土地14.8亩;滁县大王营乡富农户均出租土地20.59亩;滁县关山乡富农户均出租土地8.60亩;无为县百马乡富农户均出租土地15.68亩;霍山县诸佛庵乡3个村富农户均出租土地14.88亩;宿松县柳坪乡富农户均出租土地9.54亩;肥西县上派河乡富农户均出租土地8.88亩(56)。湖南、福建、安徽三省富农户均租出或租进土地数量有所提高,而少数富农大量租进并无变化。
根据20世纪上半期农村调查统计,一半左右的富农租进了土地,他们不但没有“剥削”贫农,自己反而遭受了地租“剥削”;还有一半左右富农出租土地比佃入的土地多,他们是否剥削了贫苦农民呢?当时有人认为,富农出租土地主要是为了解决那些远地、土质不好的土地(57),或者是为了处理家庭劳动力不足而无法耕种的土地,甚至是被拨出的土地(58)。还有富农大量出租土地可能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如安徽省屯溪市徐村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多,因为该村各阶层土地大部分是用于出租的,其中地主土地83.55%、富农土地85.14%、中贫农土地50%左右用于出租(59)。我们认为,不排除少数富农出租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收取高额的地租,但富农作为一个整体,其出租土地的主要目的却不是为了收取封建地租,而是为了解决耕种不便或家庭劳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与地主纯粹为了收取地租而出租土地的目的和性质是有区别的。因此,笼统地认为富农出租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剥削”贫苦农民,似乎有点名实不符。
2.雇工剥削问题。近代乡村自耕富农的比例超过雇工经营富农的比例,即使富农雇工经营,家庭自耕成分也比佃耕的比重大(60)。但是,那些雇请少数长工和短工的富农却被认为是农村资产阶级(资本家),其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雇请长工或短工真的就是剥削了雇工劳动吗?
(1)雇工独立性和主雇平等关系问题。清朝时期,雇主和雇工没有主仆名分之分,雇工和雇主可以同坐共食,双方关系趋向平等(61)。民国时期农业雇工市场的发展更为完善、成熟,雇工到市场求职,雇主到市场寻求雇工;雇工出力,雇主付资,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惯例和制度,这种习惯性规范是在雇工市场中的雇主和雇主、雇工与雇工、雇主和雇工之间的交互博弈而产生的,而且雇主和雇工之间形成雇佣保障性机制(62)。受这种习惯性规范的约束,富农和雇工之间,处于平等关系。“雇主待遇雇农,极为平等,与奴仆绝异。”(63)王先明教授认为,雇主和雇工之间阶级关系的判别既不分明,虽然不免有当时乡村调查者主观认识的误失,但其阶级鸿沟尚未出现明晰分野,恐怕也是一个客观存在(64)。由于近代乡村富农和雇工没有阶级区别,他们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主体,因此,富农和雇工之间的关系不像传统观点所说的那样,“除了工资少以外,雇主还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剥削雇工,降低雇工的生活待遇,加重雇工的工作量,使雇工过着非人的生活”(65)。相反,雇工尤其是长工“雇工和雇主从事同样的工作,都是在田间工作”(66),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亲近。有些长期受雇的长工,“曾换得了主人家的微薄优待,吃饭和家人一样,不另外做”,以至于“老长工的心意曾和主人的心意一样无二致”(67)。“雇工有戚谊者,论戚谊,无戚谊者,家长对雇工称名,雇工对家长或叔或伯或兄之,视年岁为定,衡无贫富阶级,亦无主仆名分,故相交以诚”(68)。主雇之间“有理由或双方感情不和时,可以随时解退”(69)
(2)雇主和雇工互惠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富农雇工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种地10亩左右的农民,自己喂不起牲口而给那些牲口有余而劳力不足的富农做帮手,以自己的人力换取畜力来进行生产。雇主和帮手是合作关系,双方承担各自的义务,雇主对帮手的土地和耕种自己的土地一样,从耕耘到收获都是由雇主的牲口来承担;帮手则需要给雇主工作,在工作时在雇主家吃饭,雇主不付帮手工资,在合作期间有些只在耕耘和收获时给雇主做工,有些还兼做雇主家的事情。第二种在江浙和华南地区的预卖劳动方式。比如江苏萧县富农种田很多,每到耕种或收获季节需要大量劳力,由于担心临时雇不到短工,富农大多在春季借给贫农或雇农粮食,到农忙时贫农和雇农给富农做短工,工资待遇与一般短工一样,以工钱抵粮钱,不足部分以劳力偿还,多余部分则由雇主补足欠资。第三种在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等地方的“伙计”制度和河南的“揽活”或“揽庄稼”。地主或富农以借款方式把粮食发给每个雇农,并供给他们牲口、农具、种子等,雇农则带着自己的农具给雇主干活,雇主不供给雇农饭食,收获时由雇主和雇农对半平分,雇主再从雇农中分得的部分扣去借款所抵的粮食。第四种情况农业劳动者、苦力贫农和雇农三位一体。1933年,在河南乡村中无地或少地农民,往往今天在自己田里劳作,明天当人家的雇农,后天又为城里的商店运输商品(70)。从富农雇工形式来看,除了第四种雇工无法判明主雇关系外,其他雇工形式中富农和雇工在雇佣关系中遵循着“互惠准则和生存权利”原则。
(3)雇工解雇问题。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离村,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供应紧张。抗日战争时期农村劳动力锐减,雇工工资步步攀升,各地解雇与退工现象十分严重(71)。“解雇与退工,只要有正当的理由,解雇与退工都是随便的。一般的雇工退工的时候多,雇主解雇的时候少。饭食不好,雇工就退了,俏皮的雇工在作工三个月后夏天到了,为挣大钱也辞退了。雇主则以长工退了仍得雇,但工资既大,人也难雇,所以多不愿意解雇。”(72)可见,雇工在雇佣关系上占据主动权,富农总是想方设法留住雇工,通过雇佣关系“剥削”雇工已非易事。
3.高利贷剥削。“农村债务,除掉贫农与贫农之间少数的友谊的借债外,都带有封建剥削性质。”(73)中共常认为农村高利贷是地主和富农放贷的结果,希望通过废除地主、富农的债务来解决高利贷问题。“乡村借贷资金非常缺乏,它与债务众多的局面形成了尖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放款者奇货可居,养成高利贷之风气’。”(74)农村高利贷现象表明了农村资金需要大于资金的供给,反映了农村资金的短缺,而并非地主和富农放贷造成的。相反,地主和富农很忌讳别人知道他们有钱,所以他们极力回避财富消息外泄,因而往往拒绝向别人放款,即使愿意放款也不愿公开办理(75)。由于农村高利贷盛行,具有强烈经营意识的地主和富农应该趋之若鹜,但与事实不同的是,地主和富农却不愿放贷乡村,这足以说明在农村放高利贷本非地主和富农的主要目的。而且富农是近代农村生产规模最大的阶层,他们在生产中需要资金较其他阶层为多。1933年广东番禺10个代表村,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负债户数比例分别为48.6%、52.8%、58.9%、22.9%,平均每户负债数额为223.4元、102.6元、98.8元、19.2元(76)。近代富农借贷比例比雇农高得多,比中农、贫农略低,但其户均负债额是中农的2.2倍、贫农的2.3倍、雇农的11.6倍。由于富农被认为是农村中的高利贷者,其家庭负债被错误地解读为“高利贷向着资本主义的借贷关系徐徐发展”(77),反而忽视了富农如其他阶层一样必须承受着农村高利贷“剥削”。
4.商业资本剥削。富农在从事农业生产主业外,还经营着各种兼业。“各种富农中有许多兼营商业的——开小商店及贩卖产品,则是用商业资本方式剥削贫苦群众。”(78)近代农村富农开商店和经商者到底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没有全国范围内富农从事经商和开设商店的具体统计,我们兹以河北省磁县120户富农样本家庭为例来分析他们兼营商业的情况。根据材料统计,富农纯粹从事农业生产者占67.5%,从事主副兼业者占32.5%;富农开商店和经商者(包括开花店、经商、贩卖、商业等项)占16.8%(79)。近代经营工商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土地投资的利润率。抗战前苏南农村土地投资年纯利润率只有8.7%左右,而工业投资利润率为30.2%,商业投资平均利润率为31.4%,两者均相当于土地投资利润率的3.5倍(80)。工商业利润远高于土地投资利润,从事商业贸易的富农比例应该比较高。而实际上从事主副兼业的富农家庭只有三分之一强,而真正从事开商店和经商的比例只有四分之一左右,我们还注意到大多数富农家庭从事主副兼业,主要在于家庭人口众多,而土地相对不足,需要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81)。因此,富农从事商业经营,主要目的不在于用商业资本剥削贫苦农民,而是为了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和发家致富。
四 中共对富农误读的原因分析
中共对近代富农认识的误读,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对地主、富农主观主义认识过多,缺乏对客观实际情况的了解(82);而实际上它是近代乡村各阶层土地财产占有和使用状况以及中共土地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土地是农村的中心问题,谁垄断或取得了土地,谁就支配了农村,谁就成了农村经济的主人(83)。中共认为,农村半数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绝大多数的人口是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农村土地关系的基本矛盾就是无地、少地的农民与占有大量土地的大、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是中国农村革命的主要内容(84)。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共提出没收地主、祠堂庙宇和其他公共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但是,实际上近代乡村地主占有土地不如中共预计的那么多。有学者认为,在24 省991县18 544乡中,地主占总户数的4.10%,占土地总数的32.25%(85)。另一方面,在土地革命中贫雇农数量大,需要分配的土地多,如果仅仅是没收地主的土地,难以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因此,中共提出必须没收富农的土地,如果不没收富农土地来进行平均分配,就很难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群众的需要(86);而如果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那么富农最终可能成为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土地革命把豪绅地主赶跑了,高租重利取消了,苛捐杂税没有了,但土地不来一个彻底分配,实际得利最多的,只是富农。”(87)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提出:“中国农村中的富农,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要彻底消灭封建与满足贫农土地要求,对富农就不能不动,就非挤不可。挤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是挤到以解决农民土地为限制,一个要挤到中农不动摇。”(88)
中共最初提出没收富农多余的出租土地,进行平均分配,因为富农占有和使用的土地超过各阶层平均占有和使用的土地量。1933年陕西渭南4村富农户均占有土地53.79亩,人均占有土地8.06亩,各阶层户均占有土地21.09亩、人均占有土地4.44亩(89)。浙江省龙游8村富农户均占有土地25.6亩,人均占有土地3.26亩,各阶层户均占有土地15.87亩,人均占有土地2.85亩(90)。1944年山东莒南筵宾、大店、沟头3区富农户均占有土地22.97亩,人均占有土地3.92亩,各阶层户均占有土地14.26亩,人均占有土地2.84亩(91)。福建古田县七保村富农户均占有土地19.81亩,人均占有土地2.33亩,各阶层户均占有土地3.92亩,人均占有土地0.97亩(92)。1933年浙江龙游8村富农户均使用土地30.54亩,人均使用土地15.25亩,各阶层户均使用土地12.29亩,人均使用土地10.09亩(93)。1944年山东莒南筵宾、大店、沟头3区富农户均使用土地30.78亩,人均使用土地5.25亩,各阶层户均使用土地9.63亩,人均使用土地1.92亩(94)。安徽皖南6村富农户均使用土地17.01亩,人均使用土地2.83亩,各阶层户均使用土地8.16亩,人均使用土地1.85亩。皖北28个乡村富农户均使用土地5.07亩,各阶层户均使用土地2.91亩(95)。可见富农占有使用土地超过当地户均占有和使用土地量。于是,富农平均多出的土地,成为土地革命没收的对象。然而根据上文统计,地主和富农全部占有土地还不到50%(96),当土地革命开展之时,中共发现仅仅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和富农多余土地可能还是不够,因而进一步提出要没收富农自耕土地的问题。“既要使雇贫农得到足够的土地,又要使中农及新富农土地不被侵犯;那么就必须把地主的土地全部拿出来,把富农的出租土地也全部拿出来,此外还必须动富农的自耕土地;不如此就不能满足雇贫农的土地要求。如果又要照顾雇贫农,使他们得到足够土地,同时又要照顾地主富农,使他们多留地,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土地只有这样多,厚此则薄彼,厚彼则薄此,这是两者不可得兼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要消灭封建,不是为了消灭封建而消灭封建,而是为了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而消灭封建。”(97)
通过没收地主和富农土地,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暂时性解决了贫雇农土地问题。但是,近代中国贫雇农不但缺乏土地,而且还缺少必要的生产工具。“除富农和中农外,其他各阶层牲畜全不够用。”(98)而富农拥有耕畜、农具等其他生产资料较多。1944年山东筵宾、大店、沟头3区11个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拥有耕畜分别为0.12、1.57、0.71、0.19头,各阶层平均拥有耕畜0.39头;沭水石河、临沭蛟龙、大兴8个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拥有耕畜0.92、1.35、0.76、0.32、0.18头,各阶层平均拥有耕畜0.58头(99)。富农往往“除自家使用外,还将耕牛出租给贫农耕种,而赚取他们廉价的劳动”(100)。在进行土地分配同时,中共还需要进一步解决贫雇农的其他生产资料问题。有学者认为,富农出租耕畜存在着所谓“剥削”,其实程度很低,尤其是人工畜工交换,代价大体相当(101)。但是,当时认为贫农“向富农借用耕牛,而以人力交换,这是用半封建的雇役劳动的形式来完成的”(102),因此,富农出租耕牛或用人工畜工交换,被认为是富农的半封建剥削。
中共在土地革命中提出要没收富农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时,需要提供没收富农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合法性依据。土地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使群众没有饭吃的有饭吃,没有衣穿的有衣穿,没有事做的有事做,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分做两个步骤,今天先限制以至取消封建剥削,减轻资本主义剥削,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进一步取消资本主义剥削,使人民在经济上完全解放,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10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要消灭封建剥削,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并把它分配给贫雇农,是消灭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但是,如前所说,近代中国大地主数量少,小地主数量多,仅仅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显然是不够的,还必然发展到没收富农的土地财产。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如果富农属于农民则没收富农土地和财产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此中共提出,近代中国农民阶级内部产生了分化,一部分农民分化为富农,成为农村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农民由于贫困变成了贫农和雇农,成为农村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富农经营土地较多,有时需要雇工,他们的雇佣行为,使富农获得了农村资产阶级(农村资本家)的“称号”。如果富农属于农村资产阶级(农村资本家),而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如此,富农在土地革命中还是还缺乏被没收土地和财产的充分理由。所以,当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富农不是农村资产阶级,而是半封建半地主之时,中共很快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主张。当富农出租因缺乏劳动力无法耕种的土地或者因远地和土质不好而收取地租时,少数富农兼从事乡村放贷、商业经营,具有与地主相似的农村经济行为特征,从而使富农被认为是半封建半地主的“封号”性质时,中共没收富农多出的土地才获得了充分合法性的依据。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和买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谁剥削谁(104)。有学者指出,在苏区广大农村,租佃是“剥削”、借贷利息是“剥削”、雇工并参与共同生产是“剥削”、经商投机倒把是“剥削”。这种对剥削与被剥削的理解,便容易简单地体现为家中财富的多寡,财富多、赚钱多者就是“剥削者”,就是革命的对象,而不论导致富裕与贫穷的具体原因(105)。当富农成为“剥削者”之时,富农作为农民本质反而被淡化,相反其作为剥削者的地位得以强化。当然,在近代土地革命中,中共首先强调富农半封建半地主的性质,然后才强调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性质。当土地革命发展到没收富农多余土地和财产时,富农作为半封建半地主更具有必要性。但是,当土地革命深入到要没收富农自耕土地和其他财产时,富农作为半封建半地主的合法性依据就不足了,而此时强调富农作为农村资产阶级或农村资本家具有特别的意义。富农作为剥削雇农的主要对象,它的这种“资本主义”经营剥削同样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当富农具有半封建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身份时,为土地革命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因此,中共必将对富农经济行为产生忽视客观事实的误读,贴上主观主义的标签。
五 结语
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困境:发展生产和动员民众的矛盾选择,如果优先选择发展生产,就必须保护好富农的生产发展愿望;如果优先选择动员民众,就需要没收富农土地和财产,满足大多数贫雇农的利益。但是,在国共两党争夺政权而内战频发的情势下,中共最终作出了动员民众优先的选择,占人口大多数的贫雇农是中共动员的主要对象,重视贫雇农利益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中共这种选择固然反映了其追求社会公平、改变近代乡村社会贫富不均的良好愿望,却恰恰忽视了富农是近代乡村社会中最富有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阶层。当富农在土地革命中遭到打击时,它似乎在提醒或警告其他社会阶层,一旦变成富农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在农民中甚至部分的干部中,怕中农发展成为富农……大家都不赞成使中农成为富农,认为成为富农就‘坏’了。”(106)另一方面,当中共强调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以动员人数众多的贫雇农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时,用分配社会财富方式来改善贫雇农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就变得更加重要和更具有合法性的依据。当时有人指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107)但是,这种理性的思考所释放出来的力量是微弱的。中共在近代土地革命中很难理智地分析富农经济发展的主要特性,最终生成了对富农阶层的非理性误解,这恐怕是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中富农遭受打击的主要因素。
注释:
①对于富农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认识,本文所谓“富农”则以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对富农的认识为基础,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富农家庭经营集约化程度高和生产能力强是指富农使用土地、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较其他阶层多,耕种土地亩产量、人均农业与农副业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比其他阶层高,具体情况参见丁长清、慈鸿飞:《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农业结构、商品经济与农村市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6~132页。
②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之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③丁长清、慈鸿飞:《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农业结构、商品经济与农村市场》,第132页。
④罗朝晖:《近百年来富农问题研究述评》,《安徽史学》2008年第3期。
⑤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37页。
⑥参见苑书义、董丛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7~557页。
⑦(13)李尔重、富振声等:《东北地主富农研究》,东北书店1947年版,第90、109页。
⑧章有义编:《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15页。
⑨⑩(12)冯和法等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下,黎明书局1935年版,第669、694、672页。
(11)东北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印行,1946年,第21页。
(14)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1页。
(15)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49页。
(16)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视角》,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78~214页。
(17)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20世纪前半期》,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0页。
(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492页。
(19)(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56、584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22)《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46~454页。
(23)(24)(25)(26)(27)(2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3、286~287、460、436、435、838页。
(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30)(35)江苏省财政厅等编:《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5~266页。
(31)《从鹅钱乡斗争来研究目前的土地改革运动》(1946年7月7日),江苏省财政厅等编:《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32)(34)中央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194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85~86、57页。
(33)(37)(3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411、411~41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0页。
(39)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08页。
(40)肖铁肩、李慧:《论中国近代的富农不是“农村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1期,第137页。
(41)(4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28页。
(4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43)肖铁肩、李慧:《论中国近代的富农不是“农村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1期,第139~140页。
(44)(4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282、397页。
(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48页。
(47)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48)薛暮桥:《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50)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1~52页。
(51)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4、89、143、188页。
(52)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2 年,第15~16、33~34、55~56、63~64、87页。
(53)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5~7、12~13、29、29、43~46、69~70、76、81、82、97~99、107~108、133~134、141页。
(54)新湖南报社:《湖南省农村情况调查》,新华书店中南分店1950年版,第18、34、68、89、94页。
(55)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72~73页。
(56)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7~8、173~174、167~168、153~156、149~150、139~142、131~136、128~130、112~113、100~102、96~97、92~93、81~82、57~58、46~47页。
(57)李尔重、富振声等:《东北地主富农研究》,第90页。
(58)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1985年,第164页。
(59)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130页
(60)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5页。
(61)周邦君:《清代四川农村雇工问题:一个乡土角度的考察》,《古今农业》2005年第4期,第68页。
(62)尚海涛、龚艳:《民国时期农业雇工市场的制度性解读——以习惯规范为中心》,《山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63)《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安徽当涂》,《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143页。
(64)王先明:《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117页。
(65)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66)陈友鹏:《嘉兴农民状况的调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
(67)《杨家坡雇工调查会记录》,山西省档案馆,A88-3-32-1,转引自王先明:《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第117页。
(68)刘清如主纂:《馆陶县志》卷六《礼俗志·风俗》,1936年铅印本,转引自张佩国:《近代山东农村的土地经营方式:惯行描述与制度分析》,《东方论坛》2000年第2期,第85页。
(69)《晋西北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材料汇集》,山西省档案馆,A—88—3—32—3,转引自王先明:《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第118页。
(70)(71)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第453~454、347页。
(72)《杨家坡村雇工问题》,山西省档案馆,A88—3—32—2。转引自王先明:《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第111页。
(73)《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10月19日,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74)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75)(77)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62~63、68页。
(76)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7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397页。
(79)(81)转引自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视角》,第309~325、309~325页
(80)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46页。
(82)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83)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1937年版,第1页。
(8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29~331页。
(85)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第58页。
(86)(8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56、455页。
(88)谢忠厚等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89)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页。
(90)(9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1、29~30页。
(91)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第9页。
(92)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第69页。
(94)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第9~10页。
(95)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安徽省农村调查》,第7~8、24~25页。
(96)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第58页。
(97)邓子恢:《土地改革的基本任务与要求》(1947年6月25日),江苏省财政厅等编:《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3卷,第16页。
(98)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第23页。
(99)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第23、205页。
(100)(102)刘端生:《嘉兴4312户农业经营的研究》,转引自徐畅:《耕畜借贷与农业经营: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安徽史学》2002年第5期,第69、69页。
(101)徐畅:《耕畜借贷与农业经营: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第70页。
(103)江苏省财政厅等编:《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第57页。
(104)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33页。
(105)杨丽琼:《财富与剥削在苏维埃革命划分阶级中的演变及启示——以中央苏区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第78页。
(106)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第172页。
(107)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