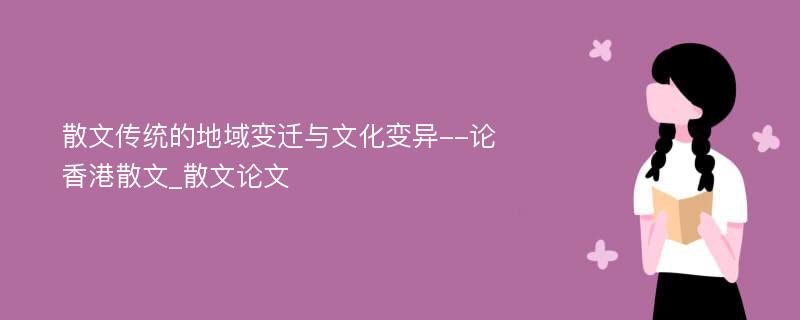
散文传统的地域推移和文化变异——关于香港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香港论文,地域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系《香港文学史》中的一个章节,为散文部分的“绪论”。面对纷繁、驳杂的描述对象,作者采用“散文文体在文化、文学系统中的功能性结构分析的方法”,将香港散文划分为传播完成期和发展成熟期先后两个段落,并从五个侧面论述香港散文的总体风貌:一、(地域推移中)文化传播和文化普及功能;二、香港散文的闲适性和趣味性特征;三、新闻传媒的主导地位和香港散文实用性倾向的关系;四、商业运作机制、“文化消费的一次性”对文学散文创作的制约;五、都市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汇合和多元构成。文章满腔热情地肯定了曹聚仁、叶灵凤、徐訏等在香港延续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五四”现代文学传统的功绩,指出董桥、梁锡华等人为代表的学者散文是香港散文精萃所在。文章对号称香港散文之大宗的“框框杂文”定义为都市“公众空间的个人言说”,在此一背景下充分肯定刘以鬯、梁秉钧、锺晓阳等人在不同时期为散文文体的革新所做的努力。
散文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文体类别,民族文学传统的共性和地域殊性同样在这一文体类别交汇。如前所述,香港地区属华夏文化的岭南文化,与世界上其它殖民地人民不同,连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在殖民统治中被湮灭或遭受极大的损害。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也在香港得到延续和传播。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批第一流的作家如茅盾、许地山、夏衍、萧红、张爱玲等等,或先或后在这块中国人聚居的土地上居住过,从事写作或其它文学活动。他们既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又“现身说法”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本身。从50年代以后,一批由内地留居香港的作家,他们或者在三四十年代的内地就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或文学根基教育在内地已经完成,但其文学事业有成则多半在香港。已在30年代出名的有叶灵凤、曹聚仁、徐訏、以及徐速、刘以鬯、丝韦等;香港本土作家如舒巷城等人,他们薪火承传,理所当然成了“五四”至30年代新文学传统的传播者、继承者,乃至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的开拓者。将他们视为香港散文的奠基者,就非空穴来风的不实之词。在六七十年代从事写作的一批作家,无论是来自内地、欧美留学归来者,还是台湾来的“驿站过客”,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欧美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背景则是共同的。余光中、思果、董桥、梁锡华、黄国彬、陈耀南等人,与同时或稍晚于他们,且因文学生长点的不同,受西方后现代文化和文学濡染的梁秉钧、西西、钟晓阳等人,将作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股独特支系的香港散文推进到了最终成熟的阶段。在七八十年代,内地的“文革”浩劫结束后,国门打开,又一波内地作家到香港定居,他们则带着大陆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把握世界方式加入到香港散文作家的队列之中,以曾敏之为“领队”的一批不同年龄的南下散文作家,同样是今天香港散文繁荣、斑斓、多元化构成的总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因此,从时间上次第登上香港文坛的作家队列的演变,我们即大体上可以将近半个世纪的香港散文、界限不甚分明地划分为奠基完成期和发展成熟期。
有评论家用诗意的语言描述成熟的香港散文的总体风貌,曰:“秋实累累,异彩纷呈”[1]翻译成理论术语,意指繁荣和多元。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共识了,但仍不免有些空泛,因为繁荣和多元,同样适用于描述别的系统和文类。因此,结合香港地方的地缘特征,带有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对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制约,特别是它的商业性和开放性与散文发展的关系是最直接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地缘的政治文化因素,香港散文成为了今天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变异,又仍然是20世纪中国散文总体格局中的一部分,用散文文体在文化、文学系统中的功能性、结构性分析,就同样不失为面对特别驳杂的系统时的方法之一。据此,将香港散文与民族传统母体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诸多殊性特征,作以下互为关涉和连结的几点概说。
一、文化传播和文化普及功能
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度极为短暂的岁月中,香港成为全国文化和文学活动的几个中心之一,在往后半个多世纪中,意识形态的争夺是一种波及造成的,本地却非风穴和源头所在。相反的是,左右之争只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文学的生产力,而在传播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普及中国文化精神方面,却并没有被搁置起来。在殖民化政治、语言背景下,捍卫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是一客观的需要,为将南来北往的外来留居者、“过客”和本港文化人的脚色定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垦殖者,提供了天时地利的可靠依据。散文作为民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载体,换言之,散文作为民族文学体式,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用文学语言传播文化知识,是其显在和深隐的功能。身为“创造社”后期重要成员的叶灵凤,用散文小品的形式传播中外文化艺术,旨在提高和扩大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关注香港方物,考订历史、传说,也说明了用散文普及和传播中国文化知识的巨大作用。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活跃的青年,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旨在当时的香港学术空气相当淡薄的情况下,传播和普及中国民族的文化学术。他的其它作品,均贯穿着一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具有的文化启蒙精神。
二、香港散文的闲适性和趣味性
30年代的中国现代散文小品,原本就存在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两条创作路线:鲁迅的针砭社会痼疾、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匕首和投枪”;周作人的“独抒心灵”的闲适主义。大体上讲,香港的散文小品基本上是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一路发展下来的。周作人讲,现代散文小品的来源,一是明清小品,一是英国小品,是两者的会合(参见《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前言》)。他的这个观点影响了台湾的许多散文作家,连“创造社”出身的叶灵凤也是“名士风度”十足的,更何况曾在上海与林语堂一起创办过《人世间》等推行闲适主义路线小品刊物的徐訏等人,可谓直接把30年代的这一派散文小品带到了香港。虽说,按照周作人的观点,闲适也有大小之分,大闲适为忧患意识,小闲适为一己的趣味、品位,但是由于香港工商社会的性质、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使得以小闲适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小品找到了蓬勃生长的土壤。60年代出版的《五十人集》、《五十又集》,这两部集众多名家谈诗论画,说典故,记游踪,以知识的丰富多彩和趣味的高雅、行文的亲切为总体特色的散文小品总集,被誉为“香港文体活动史页”的一件盛事,可以说正是闲适散文小品的一次群集大展。到了七八十年代,卓越的散文家董桥和香港学院派“才子散文小品”的崛起,同样是这一散文小品路线的继续和延伸。梁锡华的散文小品始终贯穿一种轻喜剧的幽默风格,他推崇梁实秋、王了一等人的散文小品,作品受其影响,他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一定要使它成为所谓投枪与匕首,但总该使它成为一点照亮幽暗的光明。不论是慰藉之光,知识之光,智慧之光。”[2]他还表白过寄沉痛于幽默的艺术追求,而这恰恰是与寓审美于休闲相对应的。相对而言,以行文的洁净、精致,高文化品位和审美品位著称的董桥,他在自嘲时甚至是相当放肆的,但这一切也没有逾越一位绅士和名士的风范,他写得最好的那些篇章,也不是以汪洋恣肆的雄健风格见长,而是以苏州园林那一类精于布局,以小见大,玲珑剔透,雅韵逸致的绵远悠长擅胜。香港学者创作的小品是香港散文的精粹所在。
三、新闻传媒的主导地位和香港散文的实用性倾斜
新闻传媒,确切些说是报纸副刊在推动散文小品的发展繁荣中居功至伟,这也是中国现代散文小品史上的一个传统。香港作为一个大都市,传媒资讯发达,香港散文小品的演变历程,与作为物质载体的新闻传媒休戚相关。许多著名的散文小品作家,本人就具有新闻人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是办副刊出身的;对大多数专业写作者而言,报纸副刊是其笔耕谋食的衣食父母,而学者教授们虽无衣食之虑,报纸副刊却仍是发表散文小品的主要阵地。由于“文学杂志不足,报刊专栏便提供了创作园地”(参见也斯《专栏与新感性》一文)。因此,发端于50年代的报纸框框专栏,到六七十年代渐渐成熟,成为各报必有的部分。报纸副刊在香港散文小品的发展演变中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闻传媒的谋划和面貌差不多就是散文小品的面貌。在作者作为生产者的生产和消费的流程中,社会商业化的程度越高,文化阅读市场的主导性作用就越大。因此,散文作为拥有多种功能,包罗甚广的文体类别,其审美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实用功能就发生种种大小不一的向一边倾斜。但即便如此,散文作家主题的文化价值意识受到磨损和剥弱,却没有也不可能在新闻传媒的推波助澜下被商业功利的大海彻底淹没。有三个前后辉映的报纸专栏文章,就颇堪耐人寻味,一个是1956年10月,由金庸、梁羽生、陈凡三人在《大公报》副刊上开设的《三剑楼随笔》;一个是1974年由柴娃娃、杜良媞、圆圆、小思、陆离、尹怀文、亦舒等七位女性作家轮流执笔,在《星岛日报》上开设的副刊专栏;还有一个专栏则是在各类专栏越分越琐细,文学性和人文精神更趋淡薄的情况下,于90年代由在沙由执教的三位学人:梁锡华、黄维梁、潘铭燊轮流“坐庄”开设的专栏。应该说,第一个专栏的知识性文化品位最为浓郁,陈凡在结集时的后记中说:“有时为写一篇千字的随笔,也常常要翻几本书”,“是甘还是苦,得失寸心知”,足见作者是当做一桩严肃的文学事业来从事的。第二个专栏的文史知识和人文精神已相对稀释,多取材于女作家们在眼下生活中的所感所遇,已显示出“亲切地道,自有香港的特色”,“可见70年代报章专栏特色的一面。”[3]第三个专栏,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叙事策略上的调整,融入中有执持,在文化品位、匠心经营和红尘俗世、柴米油盐之间作了一定的折冲,借用“三驾马车”之一的梁锡华自己的话来说,在一大片“或乱穿衣,或半裸不文,或甚至一丝不挂”的形形色色专栏文字的包围之中,自有一番“临风潇洒”的玉树之风致[4]。
香港工商社会的性质,使得新闻传媒,“除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因素所影响外,几乎是完全顺从市场供求关系而衍生的文化资讯网络”[5]。作家王璞则在《香港散文的生存环境和读者群》一文中说:“香港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功能式教育,它所着重培养的是各行业的实用人才,偏重灌输的是实用性知识。”[6]陈辉扬还说:“香港各大报章与杂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应该是香港数十年来城市文化发展在文字媒介方面一种较全面的纪录,也是反映香港文化生态的一面广角镜。香港虽然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在文化上,却有先天不足及后天失调的特点,而专栏这种文体得以在此大放异采,是因为它同时具备几种重要功能:一、作为文学较浓的专栏,具有欣赏及消闲之用;二、作为资讯性质的专栏,则为提供种种日常生活及专业与非专业性质的实用知识,以致各种有关中国术数的信箱,都是这方面的特产。”[7]按也斯在《公众空间中的个人论说——谈香港专栏的局限与可能》一文中所列举的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专栏,约有“专门谈经济、政治、艺术、医药、教育、投资、移民、甚至优皮、音响、录音、养花、养狗等文化的专栏,”“逐渐增多了电脑使用、办公室政治投资、广告术语、商业策略、酒店公关日记这类专栏。文笔之优美不是必须的条件,内容的多元化和专业性反而是要求。”“直至自然形成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字直销网络,以期把各类读者一网打尽,当然,这也是所有先进社会的共同命运——大家都无所遁于文网之外。”(陈辉扬语。同前)
四、商业运作机制和文化消费的一次性对文学散文创作的制约
刘以鬯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大部分读者只要求作品具有趣味性、消闲性和流行性,不重视作品的艺术、社会教育作用与所含纯度。因此,在香港卖文,必须接受文学被商业观念扭曲的事实,向低级趣味投降。”(参见《香港文丛:刘以鬯卷》)梁锡华则说:“香港人无论上、中、下流,大体上是奋力赚钱加努力享乐,谁有兴趣钻进高妙或创新的文字里头去开展胸襟、扩大视野、抚时感世、增智添识或培德立品?”[8]梁锡华还有一段描述这种文化消费的恶俗趣味的话,他说:
社会爆发之后,金钱和享乐,都要愈抓愈多,愈多愈抓,如此循环不已,没有几个人有时间、心情、兴致和语文程度去咀嚼佳构华章的。浅俗的东西,是文字快餐,匆匆吞噎后扬手一丢了事,还符合时代的节奏和风韵。……香港人在大自由和大‘拼搏’(作者原注1)的环境下,你板起面孔所谴责的无聊事物,还是他们百啖不厌的精神粮食。专栏文章愈有‘八卦’(作者原注2)内涵的,愈受欢迎。
许多作家对香港的文化消费、阅读市场如此不堪的描述,是不能被看成应该推倒的“诬蔑不实”之辞。它对严肃的纯文学散文创作的销蚀作用是一个客观存在。此外,“一次性消费”,“逸乐阅读”还助长了原本就已经存在的某种粗制滥造现象的恶性膨胀,从“戏说”式的文化解码、“文化演义”到后现代文化工业的大量复制和繁殖,香港每天报章杂志上的专栏文字,车载斗量,广种薄收,即是商业空间入侵作家艺术思维空间的一个佐证。
五、城市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汇合和多元构成
作家小思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个性所在”,“香港的文化个性也朦胧”。“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香港,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她只有努力朝向前方,紧紧地追随着世界大流适应急剧的新陈代谢。”[9]许迪锵说:“香港是个多元并存的社会,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于是,与各种内容一并展现的,是各种不同风格的散文。”[10]专栏作家阿浓则说:“香港作家来自五湖四海,所受教育也不同。又因大多业余写作,各依其本身职业而有不同的生活圈子。……没有规定他们要怎样写,写什么,因此,出现了较多的类别和不同的风格。……其派别如下:
传统派:学养极佳,经验丰富,见闻亦广,用字遣词,起承转合,均有规矩法度。
学院派:大多在大学任教,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较深,又受报章框框的限制,着力追求文学价值。
载道派:议论纵横,言必有物,有心人也。
议政派:或诚挚、或造辟、或独到、或尖锐、均见功夫。
绿色派:着重环保和绿色思想的鼓吹。
社会派:对本港社会事物表现出的急切的关注。
温情派:以人情味见长,鼓吹和谐与互援。
活泼风趣派:着重趣味,不戴道学帽子。
清醒派:文字及意念均清醒可人,不落俗套。
绅士派:温文尔雅,以气度见长。
新潮派:文字思想,都以打破观念规范为乐。
其它如:谈书派、旅游派等。”[11]
阿浓先生的结语是“风格多样,类别甚众”。从内容类别和艺术风格的并列加以描述,既是香港散文斑斓驳杂的现状的反映,同样也符合将纵向的历史作平面的罗列概括。
而如果再作进一步的集中化约,并用移动的视点加以概括,则香港散文大体上由三个大小不等,成绩不一的板块构成。这就是:学者散文随笔、通俗专栏杂文、前卫探索型的散文。学者散文随笔。包括五六十年代一批文化播种者,六七十年代同样肩负着文化传播和垦殖的一批“文化过客”的散文作品,以及尔后以沙田为基地的“学院派”散文和非学院的学者散文。香港散文以学者散文成就最大、贡献最为卓著,他们出经入典,含英咀华,融汇中西,薪火承传,可以说在地域空间和时间所许可的条件下,开创了散文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感性和知性相融合的一股新的生面。在他们最杰出的作品中,确如董桥所说的,达到了“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不过,香港学者散文,自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因主要侧重了传播和普及民族文化,上承三四十年代内地传统,难以贴近本港本土的现实生活,而另一方面看,由于散文与新闻写作的快速制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又不免粗疏,这个在后来非常突出的弊端,其实由来已久。作为香港散文重要成就和富有香港特色的学者散文,其“乡愁的理念”(董桥语)不像台湾那样有一个层次分明的深广发展的过程,“生民疮痍,笔底波澜”又难以与大陆内地的散文作家相比拟,即或其思想意境的深邃和广阔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和不足,但其气度的雍容,雅洁,精致,乃至低调沉潜,谐而不谑,则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发展的背景上就显得是绚丽醒目的一支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老一辈的文化传播者们,他们要在这一块大体上荒瘠的土地垦殖,首先要在商业社会中立下脚跟,生存奔忙十分辛苦,有的甚至穷愁一生,赍志以殁,为中国文化事业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70年代又一波南下作家,虽然难以与学贯中西、艺术素养极高的老一辈作家相颉颃,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像老一辈到香港的作家一样对中国文化文学事业矢志不移,初到香港,几乎无不在白天干重活,晚上回到蜗居窄小的空间伏案写作。他们那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现实主义精神,是香港散文整体格局刚健的一部分。
框框杂文(专栏)在量的生产方面是香港散文的大宗,据阿浓先生对1990年11月17日报纸的统计,他发现“各报的专栏一般在三十个左右,而总数约五百个”,“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计算,全年在报章发表的散文篇数,高达十八万个,每篇平均五百字的话,全年的字数是九千万。”[12]量的生产,由此可见一斑。而香港专栏的文化兴致,也斯先生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将之界定为:“公众空间中的个人论说”。他说:“专栏作者就像一个朋友或同事,是每日接触,有共同话题的,谈得来就谈下去,谈不拢就不谈算了。专栏就像‘闲话家常’、‘倾偈’、‘天南地北’、‘信口而谈’,是‘日记’、‘手记’、或是‘私记’。”这是一种“特别的沟通方式”,“说的话不会特别令人吃惊,但也没有什么足以令人深思的地方”,作家“会自觉地把响亮的声线降低,把高蹈的姿态缓和,还是齐白石画上的题字所说‘不欲教人仰首看’”。也斯又说:“散文感性的一面,常常在专栏中发挥到极端”,而“这种世俗亲切的特色,已渗透到香港散文中,成为香港散文与台湾大陆两地散文不同的主要特色。”
香港框框杂文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是特定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悖论”处境下的产物。黎海华在《城市节奏与香港散文”一文中说:“殖民政府的管治,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加速了她现代化的步伐,使她亦无可避免地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和熏陶。香港人在种种历练和变革中,大抵锻炼了一份强烈的求生意识,‘生存’是首要之务。”“香港对各方的文化和艺术,包容性极大,也因此在艺术的观照上、文化的触觉上,对作家制造有利的条件,但她的经济体制、政治气候、社会结构、亦有局限性。她的局限,可能也是挑战之处。”[13]对于香港作家和香港文学来说,中国和外国,古代和现代,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整体和局部,人性和异化,审美和实用,长远和目前,……这诸如此类的矛盾纠葛,一件事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的缠绕牵连,往往不是走向冲突对抗,而是在怀抱着希望和信念的前提下,在低调处理的过程中走向融汇。也斯说:“若城市变得非人化,我们总是希望书本可以令人变得人性化。”(《书和城市》序)。黎海华在分析香港散文对城市价值取向时说:“抗拒有之,接纳有之,亦有处于二者之间者,有疑虑、有反省、有刺痛、也有感激,有热爱、亦有批判。表达方式,重知性有之,重感性有之,或二者兼具。平铺直叙有之,委婉表达有之。如何阅读这个城市,观看这个城市,又与个人成长的背景、际遇、个性、理念、文化嗅觉息息相关。”[14]
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只有自由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边缘”而又“追赶世界大潮”导致文化个性的斑驳和多元,但仍然是中国式的斑驳和多元。香港散文不折不扣是一个现代都市的繁杂的市声,她的多声部,她的世俗化、生活化、亲切感、当下感,同样地影响和渗透到散文的文体变革,大体是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的传播和萌生是同步的。刘以鬯先生是我国最早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若干作品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不妨将他视为将意识流同时引进散文文体变革中来的第一人。那么,以也斯、西西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大体上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相互呼应的。也斯自己所说的“以比较低调的姿态出现”,“却是细微沉潜的”,“我没有故乡的回忆,只想看清楚眼前的事物。我生活其中的城市当时正在逐渐变化,这现代的生活,该用怎样的方法去透视去说出来呢?我只好绕过艳丽的辞藻,寻找定见以外的看法。”“我喜欢城市的现代生活”,“我只好不理会别人习惯的说法,好好看清这个世界,由零开始去重组文字。”[15]因此,以也斯为代表的香港后现代散文创作,不论如何地感到人被物化,为了更真切地传达现代人的那种孤寂,企图以不偏不倚、漠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所谓“情感的零度介入”,其实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始终笃信”书本可以令人变得人性化”。而正是这种低调和对温馨的渴望,使他终究有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原装货。散文在时间的场合中流淌,散文传统也是一条流动的长河;河流流过时间和空间,河床可能会变窄或加宽,迷人的风景线会有所不同,但长河的名字不会改变,长河生生不息。
注释:
[1]潘亚暾《八十年代香港散文掠影》、《香港散文选》序,百花出版社1995年。
[2]梁锡华《香港报章杂文的发展》、《祭坛佳里》,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
[3]转引自《香港文学书目》,青文书屋1996年版59页。
[4]参见台湾《联合文学》第八卷第十期第30页。
[5]陈辉扬《专栏2》同上,第32页。
[6]参见《香港文学》115期。
[7]同[5],31页。
[8]参见台湾《联合文学》第八卷第十期第18页。
[9]小思《香港的故事》,台湾《联合文学》第八卷第十期142页。
[10]许迪锵《散文:2》同上26页。
[11]阿浓《香港散文的香港特色》,1990年11月20日到26日《明报》副刊。
[12]阿浓《香港散文的香港特色》,同前。
[13]参见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宝》,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
[14]同上。
作者原注1,2:“拼搏”和“八卦”都是香港的流行语,前者指尽力而为,特别说到赚钱和求上进方面,即使危险也不怕。后者指一切琐屑新闻,包括名人、艺术生活、秘笈、艳遇、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