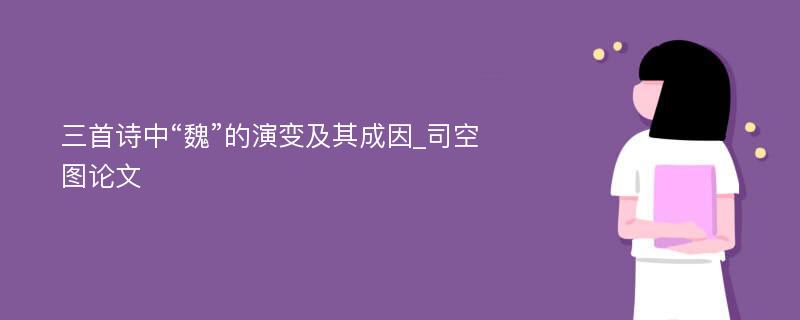
“味”在三部《诗品》中的演变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3)01-0095-06
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样式,论诗和品诗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上产生了以《诗品》为标题的三部论诗著作,即南朝钟嵘的《诗品》、唐朝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清朝袁枚的《续诗品》。钟嵘的《诗品》产生在文学脱离经学开始独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产生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顶峰的唐朝;袁枚的《续诗品》产生在中国古典诗歌走向衰落的清朝。这三部著作从标题到内容都有继承关系,考察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在这三部《诗品》中的表现能够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脉络。本文探寻“味”这一古典美学范畴在三部《诗品》中的演变及其原因。
一
“味”开始与艺术和审美发生联系,最早的记载是《论语》。《论语·述而》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是用“肉味”来衬托《韶》乐的艺术感染力的。到了陆机《文赋》,开始明确地以“味”论诗文:
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1](422页)
此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地用“味”来喻文学之美:
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2](170页)
赞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2](432页)
三部《诗品》里也以“味”论诗,而且把“味”当作诗歌的首要因素。例如,钟嵘在《诗品序》中说:
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3](14页)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3](60页)
钟嵘品诗之所以选五言,是因为他认为五言诗有滋味。由此可见,是否有滋味是钟嵘品诗的重要标准。但滋味如同食物中的味一样,有浓淡之分,有深浅之别,因此,钟嵘按照诗中蕴含滋味的深浅、浓淡将诗分为上、中、下三品,而同一品的诗人的诗歌成就也不尽相同。钟嵘说: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3](14页)
这是钟嵘对“滋味”的内涵最完美的概括。在钟嵘看来,臻于此境的诗人只有曹植。他说: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3](32页)
堂是正厅,室是内室,先入门,次升堂,最后入室,这是比喻治学的几个阶段,刘桢、张协、陆机、潘岳均属上品,但他们或仅入门,或仅登堂,诗歌成就并不相同。而曹植已“入室”,表明他的诗歌成就进入了最高阶段。那么,曹植的诗歌特点究竟是怎样的呢?钟嵘是这样评价的: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3](32页)
风力之干属于“质”的层面,丹采之润属于“文”的层面,曹植的诗“体被文质”,也就是说他的诗既有风力又有丹采。
由此可见,钟嵘的“滋味”从文和质这两个层面论述,诗歌如果兼具文质,滋味就最浓;如果只做到文质中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不足,诗歌的“滋味”就会略逊一筹。比如:
(刘桢)壮气爱奇,动多振绝。……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3](35页)
(王粲)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
……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3](37页)
应该说,刘桢、王粲能位居上品,都是极有成就的诗人,但刘桢终因“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气质有余,文采不足,只能屈居“陈思以下”;王粲“文秀而质羸”,文采秀丽,但气质羸弱,故而也“方陈思不足”。而其他诗人也多是在文或质一方面达到一定高度而使得诗歌具有一定滋味的。如钟嵘评张华:
巧用文字,务为妍冶。……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3](70页)
气质不足,但文词上有一定成就,故而置于中品。而嵇康因为“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过分急烈,才气毕露,使得文采表现不足。所以也只能置于中品。
钟嵘以“滋味”论诗有文与质两个层面,但显然地偏重于“文”这个层面。在他的上品诗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以“文”见长的,如《古诗》“文温以丽”、李陵“文多凄怨”、班婕妤“词旨清捷”、陆机“才高辞瞻,举体华美”、张协“词采葱菁”等。
总之,“滋味”是钟嵘品诗的大标准,因为他论诗的对象都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的五言;滋味的深浅、浓淡是钟嵘品诗的小标准,因为他根据滋味的浓淡、深浅将诗歌分为上中下三品。钟嵘的“滋味”是从文质两个层面论述,文是指有文采,就形式而言,质是指风力,就内容而言,所谓“体被文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
到了晚唐的司空图,他的《二十四诗品》通篇没有一个“味”字,却处处是在以“味”论诗,而且他的“味”不同于钟嵘的“滋味”,这主要是在他的一些杂文里反映出来。例如: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4](47页)
辩别诗味后方可言诗,可见,司空图认为“味”是品诗的首要因素。那么,司空图说的“味”指的是什么呢?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
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合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
表圣论诗,味在咸酸之外。
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4](47-49页)
咸酸是具体可感的味,但“味”不止于咸酸,在咸酸这种本味之外还有另一番味道,正是这另一番味道才使得味“醇美”。诗歌也是如此,除了具体可感的、容易体会到的味道之外,还有隐藏在这种“味”之后的更深层的味,它就是味外之味,后人根据“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将这种味外之味概括为“韵味”。
如果把司空图的杂文看作是对“韵味”的理论论述,那么他的《二十四诗品》就是对韵味说一种生动具体的实践。《二十四诗品》虽是理论著作,但整齐的四字一句好似一首首优美的诗歌,而且每一品都蕴含着味外之味,正是对其韵味说最好的实践。试以“典雅”品为例: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4](12页)
这是说茅屋中的佳士饮酒、赏雨,怡然自得,自得其乐。“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充满了“雅淡”的情趣,从人的雅淡中我们体味到了宇宙自然的空灵、冲淡,人的心灵世界和宇宙自然化为同一。这就是“味外之味”。正如张法在《中国美学史》中所说的:
读《诗品》中的任何一品,除了它本身的景象外,都可以感其景外有景,象外有象,充满了“韵外之致”。[5](206页)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前一个象、景、味是后一个象、景、味的铺垫和基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只有后一个象、景、味才能真正地深入诗心,接近诗歌主旨。处理好两个象、景、味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写好了诗。前一个象、景、味具体可感,后一个象、景、味需要人们高度的想像力,具有虚空、无边无际的特点。具体可感的东西描绘多了,或者太细碎了,给人的感觉太粘滞,那么想像的空间不会大,也就影响到后一个象、景、味的体味。因此,前一个象、景、味不能描绘得太实、太满,后一个象、景、味才能在更大空间呈现出来。由此可见,司空图论诗主要从两个象、景、味的层面论诗,主要突出后一个象、景、味,这完全不同于钟嵘的从文质两个层面论诗。
司空图论诗以王维、韦应物为理想对象,他说:
表圣论诗,味在酸咸之外,因举右丞苏州以示准的,此是诗家高格,不善学之,易落空套。[4](48页)
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4](47页)
司空图先说王、韦的诗有“味在酸咸之外”的特点,后面又说王、韦的诗有“格淡精致”的特点。那么“格淡精致”和“味在酸咸之外”有何关联呢?联系司空图论诗的两个层面就明白了。我们经常说“淡而有味”,这并不是说因为淡而有味,而是说因为前一个象、景、味的淡使得后一个象、景、味的意蕴在更大空间突现出来,从而诗味十足。而“味”一般是就后一个象、景、味而言,不是指如酸咸般具体可感的前一个象、景、味,所以说“味在酸咸之外”。
试以“实境”品为例:
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遇之自天,泠然希音。[4](33-34页)
语直、思浅是就前一个象、景、味而言,由于诗的语言直实,不纡曲,运思也较浅露,不深微,没有钟嵘的“文秀”,从而淡味十足,但正由于淡,才能“忽逢幽人,如见道心”,看到大道之心,使得后一个象、景、味让人最大程度地感受到。
总之,司空图品诗以“韵味”为主,所谓韵味是指味外之味。司空图的韵味从两个景、象、味的层面来论,它超越了钟嵘传统的“文质”两个层面。
到了袁枚,仍将“味”视为品诗的首要因素。例如《续诗品》中的“次韵自系,叠韵无味”“(“择韵”品)、“知味难食,知脉难医”(“知难”品)等,但对味的具体论述见于他的《随园诗话》。他在《随园诗话》(卷一)说道:
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采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6](111页)
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中有“品味”二绝,今取其一首:
平生品味似评诗,别有酸咸世不知,第一要看香色好,明珠仙露上盘时。[6](76页)
评诗似品味,只有知道诗味,才能论诗。那么,袁枚的“味”指的是什么呢?以上两例说熊掌、豹胎虽极珍贵,然而一经生吞活剥,味就不鲜,没有了生气,竟不如一蔬一笋;牡丹、芍药虽极富丽,然而一经剪采,同样味不鲜、色不香,终究连野蓼山葵都不如;明珠仙露刚上盘时,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香色好坏,香色好,自然味就鲜。由此可见,袁枚的“味”指的是鲜味,袁枚的“鲜”包括“新”和“活”两个方面,两者关系密切,但侧重点不同。“新”重在不落俗套,出人意外;“活”重在灵活多变,只有味的新、活,才能保证诗出于性灵,“不关堆垛”。
袁枚还在《续诗品》里有许多关产于诗味要新、活的论述,如“精思”品:
疾行善步,两不能全。暴长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点,兴到语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迈。人居屋中,我来天外。[6](10页)
“人居屋中,我来天外”一句之意可与《随园诗话》(卷七》中的一段话相互印证:
古梅花诗,佳者多矣,冯钝吟云:“羡他清绝西溪水,才得冰开便照君。”余咏芦花诗,颇刻画矣,刘霞裳云:“知否杨花翻羡汝,一生从不识春愁。”余不觉失色。金寿门画杏花一枝,题云:“香骢红雨上林街,墙内枝从墙外开。愉在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咏梅而思至于冰,咏芦花而思至于杨花,咏杏花而思至于状元,皆从天外落想,焉得不佳
咏梅只局限于梅,咏芦只局限于芦,咏杏也只局限于杏,这是“人居屋中”,咏梅能思至于冰,咏芦能思至于杨花,咏杏能思至于状元,这是“我来天外”。从“人居屋中”角度构思,既使将被咏之物刻画得多么生动如画、多么逼真,然一见天外落想句,竟会“不觉失色”,终觉略逊一筹。只有这种从“我来天外”角度的构思,才能出新意,不落俗套,体现出诗味“新鲜”的特点。
又如“即景”品:
混元运物,流而不住。迎之未来,揽之已去。诗如化工,即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无故。因物赋形,随影换步。彼胶柱者,将朝认暮。[6](167页)
“彼胶柱者”取自《史记》“廉颇蔺如相列传”中蔺相如比喻赵括用兵犹如“胶柱而鼓瑟耳”的典故,意思是鼓瑟时,柱是用来调弦的缓急的,如果将柱胶住,弦不得随意调,只能“缓者一于缓,急者一于急,无活法矣”,这是嘲笑赵括只会死背兵书,不能灵活作战,适应新情况。袁枚用来嘲笑那些写文章死守前人法度,不能灵活变化的人。
“因物赋形,随影换步”一句和“即景”小标题直接取自于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一文,原文如下:
天地人物,各有情状。以天时言,一时有一时之情状;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状;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状;以物类言,一类有一类之情状。诗文题目所在,四者凑合,情状不同,移步换形,中有真意。文人笔端有口,能就现前真景,抒写成篇,可见,袁枚认为天地人物不断变化,一时有一时的情状,如果我们死守法度,不会灵活变化、“移步换形”,所描写的就不是“现前真景”,即那一时的天地人物的情状,诗中的真意不会传达,也就没有了诗味。诗人只有处于随事物情状的不断变化而灵活变化之中,才能“即景成趣”,保证诗味的鲜、活。
总之,袁枚的“鲜味”有“新”和“活”两个特点,从“人居屋中,我来天外”的巧妙构思中见出味之新;从“情状不同,移步换形”的灵活笔法中见出味之活。
二
以上具体分析了“味”在三部《诗品》中的不同内涵及其特点,那么这种不同的内涵和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认为,这与三位作者所处的时代及人生阅历有关。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为他们的思想形成提供可能,他们的人生阅历则实现了这种可能。
钟嵘处于南北朝的齐梁时代,宫体诗和永明体开始滋长,形式主义文风泛滥,使得齐梁时代文学的主流随着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方向极端地发展下去。正如袁行霈等在《中国诗学通论》所说:
齐梁时代,随着人们伦理观念的转变,艳情诗赋遂日渐增多。萧纲就毫不隐讳地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段文章且须放荡。”说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读者论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在简文帝萧纲及徐、庾父子的煽炀下,这种淫艳轻靡的宫体诗便日益滋长起来了。这无疑是对“诗缘情而绮靡”的一个片面的发展。[1](237-238页)
永明体也是对“诗缘情而绮靡”的一个片面的发展,张法在《中国美学史》中说:
时至萧梁,萧统、萧纲、萧绎以皇族之尊主导文艺,沈约、谢朓、王融、周颙以士人精英的身分推涛作浪,宫廷和王府成了审美的中心,形式美的追求,一浪高过一浪,讲音韵,比隶事,吊书袋,求对偶。……上上下下共谋了青史留名的六朝“绮丽”之风,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形式美的典范。[5](120页)
“从永明四、五年到永明末,钟嵘与在京邑的文学之士多有过从”,《诗品》就说到“朓极与余论诗”的情况,而京邑是歌舞升平之地,京邑之士的文风多是绮丽淫靡的,因此,钟嵘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六朝“绮丽”文风的影响。他反对沈约永明体的“拘忌声病”,但认为他“长于清怨”,有可取之处,故而置于中品。另外,他自己的作品虽不见流传,但在《梁书·钟嵘传》记载:“元简命嵘作《瑞室颂》以旌表之,辞甚典丽”。钟嵘重文的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南北朝时代,在哲学思想上,儒学开始走向衰微,但是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儒学的衰微打破了“独尊儒术”的束缚,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多元的开放的局面,比如由道家演化而来的玄学对当时的文坛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钟嵘主要还是受到传统的儒家的影响,比如他将最佳的理想诗人曹植比作“人伦之有周孔”。他对道家是排斥的,例如他认为玄理的东西“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钟嵘写《诗品》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辩彰清浊,掎摭病利”,使五言诗归于雅正。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五言诗“会于流俗”,五言诗的“俗”,为当时许多人士认同,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2](50页)
又如挚虞《文章流别论》:
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1](424页)
斥五言为“流调”、“非音之正”,认为四言是正体、雅音是当时普遍现象。而钟嵘将五言诗归入《风》、《骚》二源,力图化俗为雅。正如张伯伟先生所指出的:
自建安以来,五言诗的流行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诗品序》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而钟嵘写作《诗品》的目的,正是为将“会于流俗”的五言诗的发展,沿着“取效《风》《骚》”的途径,走上化俗为雅之路。因此,他将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优秀之作归入《风》、《骚》二源。[7](71页)
钟嵘的化五言之俗为雅正反映了其审美思想受孔子的深重影响。正由于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钟嵘论诗主要从文质两个层面论述,孔子在《论语》中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是孔子诗歌的理想状态,不赞成文胜质,也不赞成质胜文,而要求文质彬彬,即两者相济相用,相辅相成。
总之,儒家思想使得钟嵘论“味”从文质两个层面,而六朝绮丽的文风又使得他偏于“文”这一层面。
唐朝是诗歌繁荣昌盛的时期,思想高度开放,儒、道、佛(禅)三教并行不悖,对当时诗坛有重大影响。司空图生活在唐末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遭遇坎坷,他三次从长安奔走逃窜,归隐在中条山王官谷他家祖传的别墅,心境异党凄凉,他写诗抒发体弱国难时的内心痛苦:
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8](204页)
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从佛老思想上寻求解脱,他在《自诫》一诗中说:
众人皆察察,而我独昏昏。取信于老氏,大辩欲讷言。[8](205页)
渐渐地由痛苦、悲观转向佛老的任其自然、恬淡,在审美理想上对佛老思想也多有吸收。况且唐时的道家哲学不再是钟嵘所说的一味“大谈玄理”,让人感觉“淡乎寡味”,而是将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空”、“自然无为”、“至大至无”、“淡”等结合佛家思想渗透到具体创作中去,使诗歌作品呈现出一种禅道境界,这种境界的典型人物便是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以王维的诗为例: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明月松间照,请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叶维廉在《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的视境》一文中阐述了诗人和事物的三种对应关系,第三种是诗人在创作之前,就已变为事物的本身,从事物的本身出发观事物的本身[9](82页)。王维便是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例子。他的诗完全是从事物本身的角度观照事物的本身,没有人为的因素,没有主观情绪的渲染,诗人的心灵世界转化为事物的宇宙世界,诗家之景从自然现象里纯然倾出,让人不但感受到了恬淡自然的诗家之景,而且从这种诗家之景领悟到自然天机。王维诗歌体现出的这种佛老的精神境界,与司空图的精神内涵是相一致的,所以,司空图论诗会标举王维,以王、韦为理想对象。
前面已说过,司空图论诗以王维、韦应物为理想对象,正是因为他们的诗“味在酸咸之外”,而王维受佛老思想的影响与司空图是一致的,所以,司空图会欣赏他们的诗“澄澹精致”的风格,欣赏他们的诗“味在酸咸之外”,从两个象、景、味的层面上论“味”。
总之,司空图的韵味从两个象、景、味的层面上论述,前一个象、景、味是实的,后一个象、景、味是虚的,就是司空图说的“味外之味”,它的审美空间要由前一个象、景、味来决定。由于司空图受到道家“至大至无”、“道之出言淡然无味……乃用之不可穷极也”等思想和佛家的“空观”的影响,认为前一个象、景、味应尽量地空化、淡化,后一个象、景、味的审美空间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来。所以,司空图的“韵味”崇尚冲淡,认为“淡而有味”。
袁枚处于中国古典诗歌走向衰落的时期。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早已过去,诗也不再是以前惟一的或极其重要的文学样式,它面临着戏曲、小说等新兴崛起的文学样式的挑战,正一步步地走向衰落,但诗歌曾经有过的无限辉煌又在不时地激发着清代诗人们的热情,这使得许多诗人对古代圣贤抱残守缺,亦步亦趋,没有丝毫创新,泥古思潮非常严重,袁枚曾指责他们是“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因此,要求创新、宣扬个性的心声很强烈,但古代圣贤们的诗歌始终如影子般缠绕着他们,使得他们面临着既要学习古人又要如何摆脱古人的矛盾问题。袁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矛盾的困扰,他一面高唱“应将秋水双眼洗,一生不受古人欺”,一面又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为解决这个矛盾,他从新和活两方面提出具有新意的诗味:鲜味。
从明代中叶起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到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虽经曲折,毕竟又有了发展。思想界虽然受到“文字狱”等禁锢人们心灵的高压运动的毒害,但仍出现了反道学、反传统的叛逆精神,体现了某些具有启蒙色彩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因素。和袁枚同时或前后的许多文人都无一例外地对个性解放表现出极大的狂热,如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说:“不但不随世人脚跟,亦不随古人脚跟”、“必言前人怕未言,发前人怕未发,而后为我之诗”,充分展示“我”的个性,“我”的独创性。在小说戏曲创作上更体现出对个性解放的狂热追求,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将人类真正的人性寄托在非人类的精灵狐鬼上,显示出高度的个性解放。因此,可以说,个性解放也是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袁枚深受影响,他在《著我》品中说:“竟似古人,何处著我”,认识到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个性,要与众不同,表现在诗歌作品上,就是要新,他说:“司空表圣论诗,贵得味外味。余谓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6](5页)虽然味外味不可得,但如果能够去陈言、出新意也是诗歌发展的好方向。所谓去陈言、出新意就是要与众不同,高扬个性。为此,袁枚从新和活两方面提出了具有新意的诗味:鲜味。
由以上可见,“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这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论家的生活阅历所决定的。考察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和特征,对于构建我国古代文论史是不无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2-06-08
标签:司空图论文; 诗歌论文; 诗品论文; 二十四诗品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续诗品论文; 袁枚论文; 随园诗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