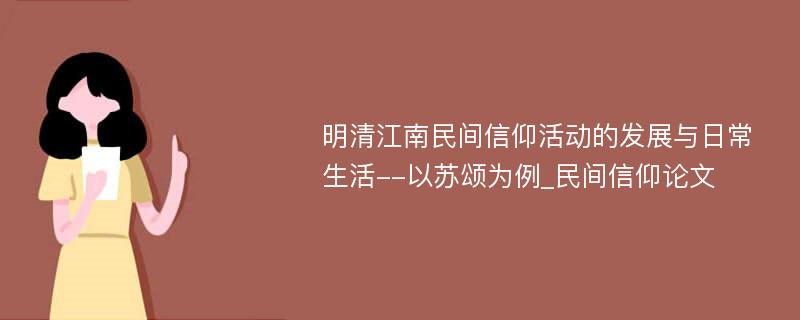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为例论文,日常生活论文,明清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2-0155-08
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从日常生活与民众心态的角度来探讨民间信仰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并已经产生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①。不过,关于民间信仰活动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究竟是如何具体开展的,有哪些主要群体参与其中,对社会民生又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打算以明清苏州、松江地区为例,通过对地方巫觋群体以及组织、参与各类民间信仰活动的人群的考察,进而探讨当我们将民间信仰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时,它对不同的群体有着怎样的意义。
一、地方巫觋:信仰活动的核心群体
民间信仰从本质上而言是体现了民众的一种心理需求,一个神灵越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人们的崇奉。那么,神灵如何取得人们的信任呢?这就必然涉及到所谓灵媒的作用,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主要就表现为各类巫师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仅是神灵的创造者,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们通过对各类仪式的反复操演,更是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神灵的心理认同。因此,当我们研究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时,对于作为信仰中介的地方巫师必须加以关注。明清苏松地区巫风之炽盛在时人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如明初曾任苏州知府的著名文人高启便作有《里巫行》一首描写本地民众信巫之风:“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②这里描写的是民人因病而求巫的事例,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普遍的,如嘉靖《上海县志》中就说,当地民人“疾病杂用巫医”③。而且这种情况也并非仅仅是就下层百姓而言的,即使是诗礼之家,亦在所不免,即所谓“士族间亦有信之者”。而其对此一般也并不讳言,如明初苏州地区的一块碑刻中就公开提及一位“诗礼世家”的女主人因病“巫医莫治,遂革于正寝”④。
除了个体性地与人驱邪除病,作为一个群体,巫师还更多地活跃在各类民间赛会活动中,如清代吴江人袁棠就曾经在《里巫行》一诗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地方庙会期间一个女巫的形象及其作法的过程:
赛神会,庙门开,男和女,杂沓来。焚香各就座,老巫语琐琐。昔我病将危,梦神来救我,命我度世人,许我证善果。惟神最灵,赏罚分明,慢之者死,奉之者生。敢告众善信,各各致诚敬。神能锡福延尔命。排门突入一狗屠,张目向巫大叫呼,妖言惑众千刑诛,妄论祸福尤虚诬,吾毁汝神逐汝去,汝与汝神其奈吾。言未绝,倏僵蹶,面死灰,口流沫,阴风飒然来,灯火翳欲灭。鬼声隐隐人声寂,满堂兀立森毛发,有妇长跪哀老巫,狂夫无知望悯恤,侬愿享神连夜宰猪羊。月米香金不敢缺。援手一救胜念千声佛。巫变色,厉声叱,汝夫触神遭神杀,何与我事相喧阗,况今神怒不可回,岂有死人能再活。回家火急市棺来,净土难容凶秽骨。妇悲啼,众怆凄,环扣巫前共祷祈,巫之一身神所栖,巫能缓颊,神当霁威。恶人死固不足惜,可怜此妇无罪为鬼妻。老巫一笑回阳春,令妇稽颡自诉神。巫传神语,神许自新,戟指书空作符簶。口含法水频频喷。相与待良久,仆者忽微吟,跃起作儿拜。……大众目击心茫然,此有亡灵求荐拔,彼有老病祈祝延,不惜金帛,只论后先。老巫指神对众言,我且不爱钱,神岂贪华筵,止因善男子善女人,借此神前结善缘,慈悲安忍相弃捐。⑤
笔者在讨论明清以来苏松地区的庙界问题时,曾提及苏松地区多数村落之中每年都要做社⑥,那么做社的内容又是如何展开的呢?据民俗学者顾希佳对上海郊区及浙江嘉兴、平湖等地的调查,发现在这些地区,所谓做社实际上是地方巫师参与的主要活动之一,当地人称为太保先生。其程序一般是先由太保先生带领信众至本村庙宇礼拜,在安放筵席、排列神码之后,开始请神、接神、唱书等程序,最后以送神结尾⑦。此活动每年一般举行春秋两次。同样,在更高层次的迎神赛会中,也能听到太保的讴歌声,清末上海文人秦锡田在描绘当地赛会情形的一首竹枝词中就写道:“报赛秋冬礼亦宜,村农集社竞鸠资……筵前太保进歌词,半杂荒唐半笑嘻。”⑧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地方文献就会发现,这样的活动无疑是有其源流可溯的,清初康熙年间汤斌曾在江南地区大兴毁淫祠运动,但其主要对象之一的五通神却屡禁不绝,据乾隆《震泽县志》载,五通神“自康熙中巡抚汤斌檄毁上方山庙宇,沉其像于太湖,而民间门外小庙之设亦遂衰废,然今乡村间犹有所谓侍茶筵者,罗列神马至数十,而巍然中坐,祀之备礼者,则名郡主,云是五通神之母,五通神像并具其旁,是虽不敢公然祀之,而恶习固未能尽革也”⑨。此处提到的侍茶筵者,以五通神为主,并罗列神马,遍祀诸神灵,与顾希佳等在乡间调查所见是比较相似的。
再往上追溯,明末陈继儒在崇祯《松江府志》中曾谈及所谓“巫医之变”:“今巫祷率宰杀为祭品,陈列凡十数桌为叠台,遍禳诸神,歌唱达曙,又用歌童,时侑以曲,鼓乐间之,献花献币,病者小差则以为占卜之验,祷赛之灵,转相愚惑,虽贫家亦勉强事祷。”⑩所谓“遍禳诸神”“时侑以曲”云云,与上文请神、送神、唱书等程序相较,则明显也是有相当大的类似之处的。
我们已经指出,巫师、太保的存在,其重要的意义是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实际效果反而是其次的,正如社会人类学家莫斯所认为的,“巫术是被信仰的,而不是被理解的。如果说现代科学奉行的是一种归纳逻辑的话,那巫术则更多的是遵循一种演绎逻辑,一次巫术的失败并不会影响人们对巫术的整体信仰,最多只是导致对单个巫师的怀疑”(11)。因此,如果单纯地从现代理性角度去考量传统时代的此类现象,恐怕是有欠妥当的。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能否认巫觋群体的行为本身一定是有很强的利益动机的。清代道光年间,江苏巡抚裕谦在任时,采取了很多措施,大力禁毁淫祠,整顿地方风俗,在其当政时留下的文牍中,对当地师巫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揭示了其敛钱的一些手段:
病家求其禳解,伊视其家之肥瘠,必断其赴庙招魂,名曰叫喜。其所指之庙必在冷僻处所,庙门常闭,该巫预串庙祝,多方勒索,始准其入庙叫喜,其实师娘与庙祝朋比分肥;
叫喜之外,视其家之稍有力者,必令其拜太母忏,太母即五通之母,自前抚宪汤除五通而后,太母之像失之未毁,僧人尚私奉上方山,至今赛飨犹盛。其忏非僧道所知,能礼此忏者皆若辈伙党。欲礼此忏,必即托其转为延请,其所索之钱,视寻常僧道不啻数十倍:
凡婚嫁疾病,女巫必怂恿其到上方山赛飨五通……亦有在家设祭者,名曰侍筵,且于卧房秽亵之处供设筵马,名曰立粧。稍知颜面者未便显设神像,暗托巫家,供桌飨祀,名曰寄粧,按季索费。(12)
在此,我们实际上发现了一条围绕地方信仰活动,由巫师、庙祝、太保等等共同参与,分工合作所构筑的利益链条,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利益链的存在,是导致民间信仰活动在江南地区持续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13)。
二、信仰活动的组织及其影响
除了地方巫觋,民间信仰活动在地方社会的具体组织与开展还牵涉到其他许多不同的群体,包括会首、衙役、各类承役者以及借助于信仰活动而维系生计的其他人群等等,通过剖析这些人群的类别及其功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的关系。
(一)会首与衙役
关于民间赛会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明末王稚登在《吴社编》中提到了所谓会首的存在:
会所集处,富人有力者捐金谷,借乘骑,出珍异,倩伎乐,命工徒雕朱刻粉,以主其事,曰会首。里豪市侠,能以力啸召俦侣,醵青钱,率黄金,诱白粟,质锦贷绣,敛翠裒香,各一其务者,亦曰会首。会首之家,先期数月,毕力经营,临期数日,输心会计,及期不过骑马市中,插花鬓畔,执鞭张盖,往来指麾而已。要之皆亡赖为之,亦有夤缘衣食者。(14)
在王看来,明末苏州民间信仰活动中的“会首”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富人有力者”,一是“里豪市侠”与“亡赖”。前者是出资赞助,“主其事”;后者则是出力组织,“各一其务”。
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会首担任者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如清代中期,昆山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也谈到了当地的会首:
其所谓会首者,在城,则府州县署之书吏衙役;在乡,则地方保长及游手好闲之徒。大约稍知礼法而有身家者,不与焉。(15)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特别提到了所谓“书吏衙役”、“地方保长”在民间赛会中担任会首的情况。关于地方保长这类群体在民间信仰活动中作用的凸显,或许是与清代中期以后在地方实行保甲制度相关,比如在常熟“市乡各图地保每届农民收获之际,遍发请贴,美其名曰祀神”(16)。而在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等人对江南民间信仰的调查中,也多次提到地保、甲长等在赛会过程中担当着组织者的角色(17)。可见,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形。
在今天的吴江地区,当地人将某一神灵的管辖范围分为几个坊,赛会活动的举办即由他们轮流管理,每年轮到的坊就叫做“现坊”,“佛会做道场、迎神赛会、做春台戏等等都是现坊的事。现坊中的头头,即是坊里的大阿爹是传代的。如果小辈无能力行事,只好叫有能力的代理,这个代理人便是大阿爹,大家都听他的话。大阿爹的威信高,权力很大,社会上的一切事情脱离不了他”(18)。这里的“大阿爹”似乎也有着当年地方保长的身影。
至于衙役活跃于赛会活动中,在晚明已然如是,据徐树丕《识小录》“吴中巫风”条载:
城隍正神,一年正三出,乃清明、中元、及烧衣节也。旧规至虎丘祭孤魂,府县官必来成礼。迩年来府县官骄蹇,委衙官了事,遂以为常。始惟府城隍出,数年来两县城隍亦出,未几而各乡土地尽出……凡大小衙役是日无不尽来执事。盖衙役平日所作过恶,众多冀以一日受役于神,阴销其罪耳。(19)
此风至清代更盛,如张紫琳在《红兰逸乘》中介绍嘉道年间的情形时说道:
吴俗敬鬼神而尚巫觋,故庙宇无不崇焕。署中衙役争为会首,纠众醵钱,假公济私。募缘不足则勒派之,杜撰之,神诞又造夫人诞,演剧排筵,以畅其醉饱。惟出于衙役,故一衙奉一神。(20)
道光年间裕谦在属地查禁迎神赛会时亦发现“每会均有衙门中人倡首,遂致毫无忌惮”,“如松江之东岳会、杨老爷、方老爷等会,并有男女舍身服役情事,亦用木印出示,有董事、阴阳生串同衙门中人为之倡导”(21)。
可以想象,在当时,此类公门中人,实际上也是地方神灵与巫祝和官员接触的一个纽带,如明代弘治年间常熟县教谕徐朝瀚及其家人屡次患病皆得痊愈,后来徐朝瀚得知“儿辈尝祷于神祠(当地神灵周孝子)”,于是大发感慨:“祷出于下人之口而应在其主之身……此非自祷而卒获良佑,毋乃祷而求之外,别有感极之道耶”,因此而为周孝子庙撰文勒碑(22)。
(二)信仰与生计
上文所引王稚登关于晚明苏州会首的文字中,在最后特别提到了其中有所谓“夤缘衣食者”,也就是说,民间赛会活动的举行不仅仅关乎信仰,其实在另一面更关乎一些人的生计,这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是那些直接参与赛会活动的人群从中可以得利维生,上文所讨论的巫祝、会首等自然可以被归入此列,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赛会活动中存在的其他一些所谓“承役者”。
清代上海县二十六保地区有漕河庙一座,根据附近居民在道光二年(1822)所立《漕河庙事略碑》(上海历史博物馆藏拓片)记载,该庙拥有的田地被分为几类,其中特别提到了有两类田产,被称作是炮手田与轿班田,据称前者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由王维章“买与炮手承种,以充常年工食,其田粮号内众户带完”,后者亦由“十图、十三图众姓捐资买作轿役工食,其田粮由众姓带完”。另外还有三巡乐器田,“昔年吴胜祥经办,众姓完粮,乐工承种,以贴三巡工食”。据此,我们知道围绕漕河庙举行的各类活动中存在着一些职业群体,包括炮手、轿役、乐工等,他们实际上正是通过赛会活动来谋求其生计。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明清松江地区有打钱幡的习俗,崇祯《松江府志》载:“(三月)旧志载歌咢游山(干山,即天马山)迎会,先时巫者舁神偶沿门互唱索钱,结彩成幡胜,以奉岳神为钱幡会,至今有之。”(23)清人丁宜福《申江棹歌》进一步点明了这些人的身份:“东乡有类巫者,世业宫豕术,不与齐民齿,土人呼为‘牡猪’。正月初一为始,挈伴担刘郡王像,以尺许小椎及钢叉迎门舞掷,谓之打钱幡。三月二十八日群会于岳庙,各逞其技以酬神,礼毕而止,谓之钱幡上庙。”(24)在此,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群依靠神偶索钱讨生计的人。
事实上,在明清时代江南各地的赛会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类似的所谓贱民的身影。如常熟“周孝子出会,丐户扮忤逆媳妇,梳牡丹头,穿桃红布高底鞋,插旗背梆”(25)。嘉定“立春日前期县官督委坊甲……选集优人妓女,装扮社夥,教习二日,谓之演春”(26)。清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大江以南多奉刘猛将,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27)。而在笔者看来,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这些群体更加依附于神灵,充役于神前,相信既是为求自身福祉,同时也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正与其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
信仰活动的资生功能当然远不止于此,我们还可以结合赛会活动中的奢侈现象进一步作些分析。明末上海县人陆楫在《蒹葭堂杂著》中论奢侈的著名文字现在已经广为人知(28)。而具体到民间信仰问题上,其实当时也已有些有识文人认识到了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益处。如清代苏州人袁学澜便认为,民间赛会虽然“繁费无度,作为无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顾吴俗华靡,而贫民谋食独易。彼其挥霍纵恣,凡执纤悉之业,待以举炊,而终身无冻馁者比比也。此亦贫富相资之一端,为政者殆不可执迂远之见,以反古而戾俗也”(29)。顾公燮也说:“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也。”(30)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乾隆年间,苏抚陈宏谋曾禁妇女入寺烧香,但在实行不久之后,却因“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而导致“物议哗然,由是弛禁”(31)。
在这方面,苏州虎丘山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明清时代这一带的繁华与每年三次的城隍出会有密切关系,如徐树丕所言,每届出会,“山塘一带,观者如云”,并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中舟船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意。据说每当诸神赛会之前,画船歌舫便已“不可复得,盖一月前多已预订,虽倍许其价,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辞”(32),可见其生意之兴隆,而从业者也有了其固定的崇拜对象(33)。
在乾嘉时的苏州,腊月间各纸马香烛铺也“预印路头财马”以售人,用于接路头财神之用。黎里镇上则“有印神佛纸马者,用油纸雕穿为范,以苏墨汁刷印,谓之‘榻马’。其精者用笔勾清,饰以金采”(34)。另外,各地还有所谓的装佛店,即专门塑造装饰佛像之所(35)。嘉庆《上海县志》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陆洪畴字符九,起龙孙,笃于伦纪,力行善事,舟过汜泾,见浮尸瘗之,又经羊肠河,亦瘗浮尸二。有印神像为生者,贫不能举火,七口几殒,特给其资,适邑中大疫,日事禳祈,神像得售,七口赖以全。”(36)
此外,信仰活动中的奢侈行为还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一些地方产业的发展,如锡箔业。这在相关记载中也多有可见,如宝山县“三月二十八日举行解饷会,万人空巷,金银冥宝与檐齐,白镪朱提盈筐载道,一炬余烬且值百金。故邑虽贫瘠,浙东锡箔之贾得因谣俗所好,列肆操纵,为商业大宗”(37)。根据民国《章蒸风俗述略》的记载,当时“调查全区纸箔店每年销售锡箔,岁出以巨万计”(38)。道光《双凤里志》载:当地“市中小户则以冥镪为营生”(39)。朱小田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也曾以迷信纸的生产及无锡惠山泥人业的发展为例对庙会与当地特色产业的关系作过细致的研究(40)。这实际上在更高层面上表明了民间信仰活动资生功能的重要性。
三、女性:一个重要的信仰群体
关于明清时代女性在民间信仰活动中的活跃程度,学术界已经有过不少的研究,如赵世瑜就指出,与传统文献显示的女性形象不同,在明清时代,“妇女可以借口参加具有宗教色彩的种种活动,以满足她们出外参加娱乐性活动的愿望”(41)。而美国学者曼素恩在其著作《缀珍录》中也认识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在维持佛教势力方面的重要作用(42)。他们的观点在明清时代的江南无疑是部分适用的,女子烧香是明清妇女生活的一大特色,吴地犹甚,“吴中陋习,妇女入寺烧香……每乘佳辰佛月,空城而出,陆舆水舫,新装丽服,殊犯冶容淫秽之戒”,每年七月晦日地藏王诞,“妇女烧香开元寺,脱红裙以忏产,点肉身灯以报母恩”(43)。“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东岳天齐仁圣帝诞辰……二十七日夜,先有妇女宿殿上,谓之坐蒲团,此最近亵。”(44)嘉定黄渡“七月十二日,俗传嘉邑城隍夫人诞时。花田三蓐方毕,女工稍休,烧香婆嫂最盛”(45)。
明人冯梦龙在其所辑《山歌》中便收有《烧香娘娘》一首,详细描摹了赛会期间乡村妇女的心理与活动,惟妙惟肖,读来煞是有趣,兹稍作征引:
初春三月是江南赛会举行的高潮,该山歌所描述的烧香娘娘就是在这个时候打算出门上香,参加庙会:
春二三月暖洋洋,姐儿打扮去烧香。……屋里精无一塌,硬三蛮极要行。便去央求对门知心妈妈,又央求隔壁着意个娘娘:请你来再无别事,有一句知心话替你商量。我从小许子穹隆山香愿,至今还弗曾去了偿。昨夜头偶然得介一梦,三茆菩萨派我灾殃。那间我要还还个心愿,百无一有难行。头上少介两件首饰,身上要介几件衣裳。
正在为出门的行头发愁,不料丈夫又横生阻拦:
家公便道娘呀,目下无柴少米,做生意咦介无赚处个孔方。春季屋钱要紧,米钱又无倽抵当。烧香虽则是个好事,算来要费介二钱个放光。(白银曰放光)姐儿听得子个句说话,心头爆出子个太阳。天灾神祸骂子几句,乌龟王八也骂子千万百声。这时有人出来劝解道:
玉帝也弗离个金殿,闺女也弗出个绣房。官人也是做人家个说话,并无半句派赖个肚肠”。可是娘娘却偏不买这个帐:“听奴说诉,非奴之过。只因亡八无知,致使我心中发怒。把从前细数,从前细数。与他多年夫妇,几见他撑持门户,尽亏奴。若不去还香愿,非为女丈夫。
于是她开始东借西凑,准备行头:
“徐家管娘子有一个金镶玉观音押鬓,陈卖肉新妇有两只摘金桃个凤凰。张大姐有个涂金蝴蝶,李三阿妈借子点翠个螳螂。”第二天终于成行:“娇娘早起拂装台,炭画蛾眉粉弹腮。只愁装不就好身材,尽情把衣饰来穿戴。且喜得人家肯借来”,“时兴衣服乔装扮,粉香脂气,分明是麝兰,娇音细语,分明是凤凰”。
上香完毕,一切又回复到了原来生活的轨道:
夜晚头边有星走失,借别人介多呵物事,教我拿倽陪偿。慌忙赶到屋里,撞着子多呵个婶娘。说弗尽路上个景致,话弗了山上个风光。只听得大门呀生能介一响,再是讨衣裳个阿妈娘娘。慌忙头上除下子首饰,身上卸落子衣裳。两人抬头一看,满身剥个精光。方才金光参殿,像个常熟山上新装塑个尊观音佛,那间破珠挪撒,好像个盘门路里乌龟算命个星臭婆娘。(46)
在这里,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个迥异于传统的农村妇女形象,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她们甚至可以与丈夫分庭抗礼(47)。
这样的现象无疑是引起传统文人士绅反感的,如清代乾隆时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曾经指出,民间迎神赛会有十大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混男女:“凡乡城有盛会,观者如山,妇女焉得不出。妇女既多,则轻薄少年逐队随行,焉得不看。趁游人之如沸,揽芳泽于咫尺,看回头一笑,便错认有情;听娇语数声,则神魂若失。甚至同船唤渡,舟覆人亡;挨跻翻舆,鬓蓬钗堕,伤风败俗,莫此为甚。”(48)乾隆《续外冈志》卷1《风俗》亦说:“闺阃之风向来严肃,不游寺观……近日颇有入寺烧香,垂帘观剧。”可见,在他们的那个时代,男女杂沓参加各类信仰活动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当乾隆年间陈宏谋担任江苏巡抚时,在其所立的《风俗条约》中专门将禁止女性烧香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妇女礼处深闺,坐则垂帘,出必拥面。何乃吴俗习于游荡,少妇艳妆,出行无忌。兜轿游山,灯夕走月,游观寺院,做会烧香,跪听讲经,僧房谈笑。或宿神会为结缘,或翻佛经为求福,或宿山庙而求子,或点肉灯以禳灾,或舍身后宫寝殿,朔望供役,僧道款待,恶少围观,本夫亲属,恬不知羞,深为风俗之玷。”(49)
但是,如果只是笼统地认为,明清时代的江南妇女都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类赛会活动,恐怕也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与下层妇女相比,上层女性外出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空间恐怕要狭小得多:张大纯《吴中风俗论》说赛会期间,“巨室垂帘门外,妇女华妆坐观”,《珠里小志》中也谈到当地“市镇诗礼之家,不观戏,不入寺观,迎神赛会,间有观者,必垂帘于户”(50)。朱泾“八月初一日,东林寺开香市,寺中货卖杂物,列肆而居。至中秋前后,四方男妇填街塞巷,杂沓而来,佛殿几无容足之区,直至九月抄方止,惟里中妇女鲜有入庙烧香者”(51)。清末民初《二十六保志》卷1《风俗》也提到“妇女朴实,庄洁自好,素无游寺登山、烧香念佛之类”。可见,大家闺秀的不自由,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52)。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对民间信仰影响力的减弱,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低估官绅之家中妇女对男性家庭成员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孝道理念的存在,老年妇女在个人信仰方面享有的权力与自由更是值得关注,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所谓佛堂在当时士绅家族中的普遍存在,其用意则大多是在于娱亲。与此同时,这些家庭女性也往往是巫祝突破的对象,正如裕谦指出的,师娘“谬托视鬼,平素勾结不肖婢媪,窃探人家琐事,名曰买春。设其家偶有疾病不安,婢媪则捏造见闻,以耸主妇之听,内言一出,虽读书谈道之士,明知无益,不得不从”(53)。因此,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妇女,她们中的多数人实际上都将民间信仰看作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以其自身的方式对地方信仰活动的发展产生着特有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多个群体密切相关,其中以师娘、太保为代表的地方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而会首、衙役等群体则是信仰活动的具体组织与参与者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推动民间信仰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也是民间赛会活动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评审意见:民间信仰是近年来史学界比较前沿的一个研究领域,这篇论文关注于民间信仰活动在地方社会的具体展开过程及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这是学界较少着墨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却也是研究民间信仰绕不过去的基本问题之一。论文从参与民间赛会的人群着手,结合方志、碑刻、文集等资料分别探讨巫觋、会首、衙役、女性等社会群体在信仰活动中的形象、角色、作用、利益诉求等等,抓住了观察地方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维度,从细微处揭示了民间信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从而也在一个方面解释了其之所以屡禁不绝的原因所在。值得肯定的是,论文还特别提到了民间信仰活动所具有的资生功能,并且将其与明代中后期以来江南地区的奢侈风气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具体地从民间赛会的角度对前人关于江南奢风的研究作了补充论证,这也是很有价值的。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今后加以关注:如普通小农在民间赛会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赛会的经济基础何在,信仰活动的展开在城乡有何差异等等。
评审专家: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
①如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等著作中均有与此相关的精彩论述。
②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
③嘉靖《上海县志》卷1《风俗》。
④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39号碑《故顾宗善妻张硕人墓志铭》,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清诗铎》卷24,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⑥参见王健《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6期。
⑦顾希佳:《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7页。
⑧秦锡田:《享帚录》卷5,民国二十年铅印本。而据笔者在南汇地区的调查,当地太保先生参加的各种仪式中,除了青苗社外,亦有接厂一说。所谓厂,亦即指厂会、厂宴,是当地迎神赛会的别称(根据笔者2007年9月20日对南汇民间文化工作者谈敬德的访谈)。不过,在今天的南汇等地区,太保先生已经基本趋于消亡,其仪式内容的一部分转变为了纯粹娱乐性质的锣鼓书,其余部分亟待发掘抢救。
⑨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
⑩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
(11)参见[法]莫斯等著《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杨渝东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裕谦:《勉益斋偶存稿续存稿》卷7《禁五通淫祠并师巫邪说示》(道光十五年五月),光绪二年刻本。
(13)当然,这些群体之间因利益的存在,也经常会产生冲突,1881年6月27日的《申报》上就曾记录了一则当地女巫因抢夺太保生意而遭到后者斥责,最终不得不加倍赔偿的例子(《巫谋报复》,第2版)。
(14)王稚登:《吴社编》,载《丛书集成初编》第3025册。
(15)钱泳:《履园丛话》卷21,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地保纷纷祀神》,《常熟日日报》(常熟档案馆藏)1916年11月24日。
(17)参见滨岛敦俊、高桥正、片山冈《華中·南デル夕農村実地調查報告書》,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4卷,1994年。在此,会首贪渎的情形当然也是存在的,《申报》1879年的一则记载便表明了这一点(参见《苏台琐录》,《申报》1879年3月25日)。
(18)张振昌:《春台戏杂说》,吴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吴江风情》,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19)徐树丕:《识小录·识小四》吴中巫风条,《丛书集成续编》子部第89册。
(20)张紫琳:《红兰逸乘》卷4《琐载》,《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51册。
(21)裕谦:《勉益斋偶存稿续存稿》卷15《禁各属迎神赛会示》(道光二十年正月)。
(22)徐朝瀚:《敕封周孝子感应记》,载邵松年辑《海虞文征》(光绪三十一年鸿文书局石印本)卷13。
(23)崇祯《松江府志》卷7《风俗》。
(24)丁宜福:《申江棹歌》(姚养怡抄本),收入顾炳权编著《上海历代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5)刘本沛:《虞书》,见丁祖荫辑《虞阳说苑》(民国虞山丁氏初园排印本)乙编。
(26)康熙《嘉定县志》卷4《风俗物产》。
(27)王应奎:《柳南随笔》卷2,中华书局1983年版。
(28)最早关注陆楫“反禁奢”言论的是傅衣凌先生与杨联陞先生。可分别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以及杨联陞《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收入氏著《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此外林丽月则曾对陆楫相关思想的传衍作过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氏著《〈蒹葭堂稿〉与陆楫“反禁奢”思想之传衍》,收入陈国栋、罗彤华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经济脉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29)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0)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丛书集成续编》子部96册。
(31)钱泳:《履园丛话》卷1。
(32)《吴会丛谈》,《申报》1882年4月3日。
(33)《申报》1876年12月3日第2-3版《重建神舟》载:“苏州上塘三乡庙旧有舟船班房,值班者皆歌船画舫中人。”
(34)嘉庆《黎里志》卷4《风俗》。
(35)如清末上海城内就有汪裕盛装佛店。参见《大佛渡海》,《申报》1882年7月30日。
(36)嘉庆《上海县志》卷7《坛庙》。
(37)民国《宝山县续志》卷5《礼俗志·风俗》。
(38)民国《章蒸风俗述略》乙《社会习尚社会迷信》。
(39)道光《双凤里志》卷1《流习》。
(40)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62页。
(41)赵世瑜:《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载氏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
(42)参见曼素恩《缀珍录——18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7章《虔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3)民国《吴县志》卷52《风俗》。
(44)嘉庆《黎里志》卷4《风俗》。
(45)民国《黄渡镇志》卷2《风俗》。
(46)冯梦龙辑:《山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01页。
(47)在吴地,还有不少描写乡村妇女出会烧香情景的歌诗,兹再征引两首:(一)“正月八,腊月八。乡下妈妈要去敬菩萨;东一约,西一约;好大髻,假头发;通草花儿满头插;好白脸,小粉榻就;洋蓝布杉四尺八;青布腰裙一狭狭;花花衬裤稻草扎;东家借裹脚,西家借套袜;大红鞋子绿叶拔,走一走,搭一搭,青皮石上打滑塌;甘蔗荸荠嘴里嚼;肉馒头,怀里揣;路上行人看见都笑煞”(《乡下妈妈要去敬菩萨》,顾颉刚《吴歌》己集第七八首);(二)“二月八,三月八,乡下娘娘出来游惠山;红甘蔗,腰里插;芝麻糖条嘴里塔;一跑跑得口渴煞,要想买碗汤喝喝,没有铜钱活气杀”(《乡下娘娘出来游惠山》,同上七七首)。
(48)钱泳:《履园丛话》卷21。不过,似乎并非所有的士大夫对此都深恶痛绝的,如清代苏州文人袁景澜在《观支硎山香市记》中就有这样的正面描述:“闺房淑秀,帏幕尽开,婢媵后随,山花插髻,芳草绿褥,软衬双跌,臻臻簇簇,联络十里,笑语盈路,众情熙熙,无不各遂其乐。”(《吴郡岁华纪丽》卷2)
(49)光绪《常昭合志稿》卷6《风俗志》。
(50)嘉庆《珠里小志》卷3《风俗》。
(51)嘉庆《朱泾志》卷1《疆域志》。
(52)个中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她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像“烧香娘娘”那样的家庭经济地位吧,他们怎么也不可能发出“与他多年夫妇,几见他撑持门户,尽亏奴。若不去还香愿,非为女丈夫”这样的豪语。
(53)裕谦:《勉益斋偶存稿续存稿》卷7《禁五通淫祠并师巫邪说示》(道光十五年五月)。正是由于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所以在地方志中,那些不信鬼神的女性被大力褒扬,如清代松江张泽镇“府庠生吴时熙妻庄氏,寒圩人。……育遗孤志喜,不事姑息。志喜疾,惟治汤药,不事祷禳,人高其识”(光绪《张泽志·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