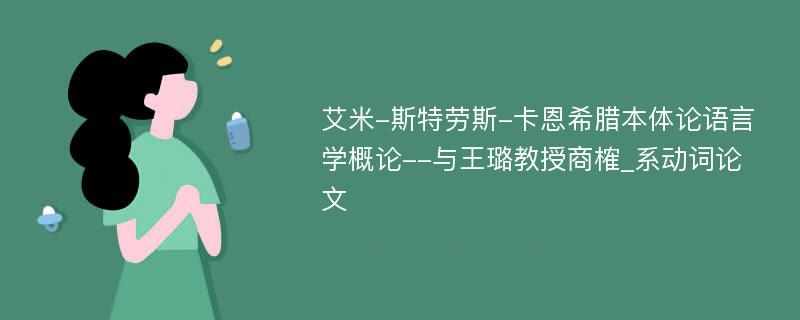
eimi——卡恩的希腊ontology的语言学导论——与王路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语言学论文,导论论文,教授论文,eim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哲学界关于“存在”与“是”的争论时日已久。王路教授于2003年10月发表了他 的新著《“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注:王路:《“是”与“真”——形 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总结了他的立场和观点。在为王路教授这 本书撰写的书评中,我提了两条批评意见:第一,王路教授的思想以西方学者卡恩对古 希腊文“是”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和起点,假如卡恩的观点有问题,那么王路教授的论述 基础也会发生动摇;第二,王路教授对中西思想文化传统的理解着眼于“异”而忽略“ 同”,他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地理解西方哲学,但在跨文化比较研究领域,这种与斯 宾格勒相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注:参见王晓朝:《如何理解西方形而上学史》,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10月31日,第12版。)书评篇幅有限,加之写书评 时我还没有读过卡恩的专著,因此上述批评无法深入展开,是否评得到位心里没有底。 本文则是我读了卡恩专著以后的进一步看法。(注:王路教授在看了我的书评后,将卡 恩的这部专著借给我阅读,在此特致谢意。)
一、关于卡恩的研究目的
王路教授多次建议我们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卡恩的研究成果”(注:王路:《“是”与 “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27页。)。在他的这部新著中,对卡恩研究成果的介 绍和评价占了整整一章。卡恩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论文《动词“to be”与being概念研 究之回顾》(Retrospect on the Verb“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专著《古希 腊语动词to be》(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除了王路教授的介绍和评价外 ,中国学界对卡恩原著做过较为详细考察的还有杨适教授和陈村富教授。(注:杨适: 《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陈村富:《Eimi与卡恩——兼评国内关于 “是”与“存在”的若干论文》;陈村富:《关于希腊语动词eimi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 题》,均载宋继杰编《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卡恩的研究目的是我阅读卡恩首先予以关注的问题。卡恩在其著作前言中说:
本书无心地起始于1964年,当时我试图把哲学产生以前的希腊动词be的用法收集在一 起,以便为解读巴门尼德以来的哲学家对这个动词的比较专业的用法奠定基础。但是这 个任务比我想象得更加艰难和漫长,我逐渐明白过来,如果不直面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 上的许多重大争论,就不可能对这些希腊资料做出恰当的描述。……尽管我已经答应要 处理这些广泛的问题,但作为其后果则可以看到(带着某种沮丧之情)我先前的框架已经 让位于另一范围和维度相当不同的研究,而其焦点则保持在最初的目标上:为这个希腊 语动词的日常的、非专业的用法提供一个解释。当然了,首先推动这一研究的是be的哲 学历程,我始终试图指出,朝着这一方向的分析对研究希腊哲学是有用的。但是本书仍 旧是对希腊语中的动词be的一项研究,而不是对哲学希腊语中的动词be的一项研究。( 注:C.H.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Dordrecht-Holland,1973,Preface,p.Ⅸ.(本文所引卡恩原话均由本文作者自译)。)
卡恩的这段话对他自己的研究目的表述得非常清楚。这一说法也和他在论文中的说法 基本一致。(注:参阅陈村富:《Eimi与卡恩——兼评国内关于“是”与“存在”的若 干论文》,第258—259页。)从中可见,卡恩实际上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起什么作用有 着清醒的认识:他只是要阐明希腊文动词be的日常用法和意义,以便为哲学的分析提供 素材;他不妄求为它的哲学用法和意义提供完整的说明,不想用语言的分析取代哲学的 分析,而只是为解读希腊文动词be的哲学用法奠定语言基础。简言之,他认为自己的研 究是一种“希腊ontology的语言学导论,而不是对此主题的历史性考察”(注:C.H.
Kahn,Retrospect on the Verb“to be”and Concept of Being,S.Knuuttila and
HIntikka ed.,The Logic of Being,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Dordrecht-Holland,1986,p.21.)。
二、关于卡恩研究的基本结论
卡恩这本著作长达519页(正文486页,目录、序言等33页),其主要内容如书名所示, 是对古希腊文be这个动词的研究。该书的取材范围和研究方法在王路教授和陈村富教授 的介绍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概括和阐述,此不赘述。但卡恩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什么,在这 个问题上两位介绍者有争议。
王路教授认为:
卡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古希腊文“是”这个动词进行研究。他的最初成果以论文 的形式发表于60年代下半叶,题目是《“是”这个希腊文动词和“是”这个概念》。… …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多年深入细致的研究,于1973年发表了长达将近500页的 专著《古希腊文中“是”这个动词》。在这本著作中,卡恩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为主要材料,也从荷马以后的希腊文献(包括古典散文和诗)中选择了一些例 句;他以哈里斯的转换语法理论为基础,并且应用了现代逻辑的理论。卡恩抛弃了传统 的“系词—存在”的二分法,提出了自己关于einai这个词的区分方法。他认为,einai 这个动词的主要用法有两种:一种是系词用法,另一种是非系词用法;而在非系词用法 中,主要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存在用法,另一种是断真用法。这样,卡恩就得出了 他研究的重要结论:在古希腊文献中,einai这个动词的用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系词 用法,简单地说,就是“Ν是Φ”;第二,存在用法,这主要是einai这个动词移到句 首,相当于英文的“there is……“有……”或“存在……”);第三,断真用法,比 如“……(这)是真的”。(注: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46 —47页。)
王路教授介绍的准确性如何,还是对比卡恩的原著来说话吧。卡恩在其专著的前言中 说:“本书的核心部分是描述性地解释eimi的各种用法,呈现在第四章,第六章,第七 章。”(注:C.H.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X、85、228.)而 这三章的标题分别是:第四章,对系动词用法的描述(Ⅳ.Description of the Copula
Uses);第六章,表示存在的动词(Ⅵ.The Verb of Existence);第七章,断真用法(Ⅶ .The Veridical Use)。
在第四章第一节开头,卡恩说:
在第三章的最后两节我论证了,对eimi的各种用法所作的唯一令人满意的一般分类, 是将其在形式上划分为系动词结构与非系动词结构,而这个动词的表存在的意义和用法 必须作为一个问题留待澄清。这样一来,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非系动词的用法在意义 上(表示潜能的、表所有的、断真的结构)是否表示存在这一点并不清晰,另一方面我们 又发现,在系动词结构的实例中这个动词同时又带有某些表示存在的价值,或者某些其 他具体的意义。……在本章中我描述形式上是系动词的eimi的用法。在第五章我试图概 括系动词的一般理论(在希腊文中,或在印欧语系中),以便把这些用法置于一个更加宽 广的视域中,并对下述问题的答案提出建议:be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谓语的符号?系动 词纯粹是形式,还是有其自身的意义?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我描述非系动词的用法,而在 结论性的第八章,我讨论这些不同用法之间的联系,并且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单一的语 言符号(印欧语词根es-)既能用作系动词,又能用来表达在与真。(注:C.H.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X、85、228.)
在第六章第一节开头,卡恩说:
剩下来要加以描述的eimi的用法是用一个否定性的标准来区分的:按照第四章第1—2 节所给出的系动词的句法定义,它们代表的是非系动词的结构。人们通常假定这些用法 也可以确定地称作表示存在的。但除了这种表示存在的用法(或多种表示存在的用法)之 外,eimi的非系动词结构包括:
表示所有的:esti moi chremata(I have money.)
表示可能的:esti + 不定式(It is possible,permissible to do so-and-so)
表示断真的:esti tauta,esti outo(That is so.)
出于以后将会说明的理由,在本章中,我在处理这个表示存在的动词的时候也一道处 理表示所有的和表示潜能的结构。而对断真用法的处理则推迟到第七章中。(注:C.H.
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X、85、228.)
在第七章第一节的开头,卡恩说:
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希腊文动词be拥有“是真的”(be true)、“是这样的”(be so )、“是这么回事”(be the case)这种意义(亦即具有这种翻译价值)的一系列用法。这 就是我所谓的eimi的断真意义(the veridical nuance)或断真的词典价值(veridical
lexical value)。“断真用法”(veridical use)这个术语将用于所有eimi拥有这种词 典价值的任何句子。为了能够与本研究的一般方法相一致,我试图尽可能地将这种词典 价值与一种或多种确定的句型联系起来。这些句型中最重要的是类型一,我称之为断真 结构(the veridical construction),一个含有eimi的从句与另一个含有说(不那么频 繁的还有“想”或“感到”)这个动词的从句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具有“事情就 是你所说的那样。”(Things are as you say.)的比较结构。(注:C.H.Kahn,The Verb “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331、371、394、395、397、400.)
卡恩这本书的第八章“希腊文be的系统的统一性”(Ⅷ.The Unity of the System of “Be”in Greek)是全书的结论。他在该章第1节开头处说:“我们对eimi的各种用法的 描述完成了,现在是让关于这个动词的整个系统的各种分析和考虑的线索一致起来的时 候了。一个动词怎么能够发挥如此众多不同的功能?这个动词的哪一种意义或用法我们 应当作最基本的,在何种意义上其他用法是从中演化出来的?”(注:C.H.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331、371、394、395、397、400.)
在该章第6节卡恩综述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
我们首先试图(在第2节)解释eimi的各种用法,视之为源于“在场”(is present)、“ 在某处”(is located somewhere)这个假设性的原初意义的进一步发展。然后我们(在 3 —4节)对这样一种发展性解释的所谓证据再作解释,宁可视之为一般地揭示了在思想 上 对空间—形体(spatial-bodily)的想象的一种心理的或直觉的优先性。在检视和扩张 了 我们这个围绕静态的—变化的—使役的(stative-mutative-factitive)相互关系建立 起 来的语体系统的解释以后(在第5节),我们已经逼近我们讨论的最后阶段,现在我们 要 从哲学概念Being出发,考虑动词eimi的用法的系统的统一性问题。(注:C.H.Kahn,
TheVerb“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331、371、394、395、397、400.)
……
关于印欧语动词to be的传统理论,被存在性用法是其第一位的和原初的用法、系动词 用法是第二位的、派生的用法这样一个假设严重地阻碍了。一旦我们进行了我建议的这 场温和的哥白尼革命,亦即,一旦我们把系动词结构复原到这个系统的中心地位,这个 动词的其他用法就很容易定位了。至于表处所的用法被包括在系词结构中,其相应的词 典价值“在场”、“在某处”显然在这个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对其他许多不仅仅表示 地点的eimi的用法实施某种影响。(注:C.H.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
Preface,p.331、371、394、395、397、400.)
……
我的主张是,如果我们从eimi作为系动词的用法开始解释它与“在某处出现”的观念 的直觉性联系,及其与句子形式更加抽象的联系,视其为谓词的符号和转换的操作者, 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同一个动词用来表达存在与真相的用法。但若我们从存在用法是 原初的,而系动词结构是“派生的”开始,我们就面临一系列无法处理的问题。我们要 把哪一种存在用法当作基本的(因为有几种非常不同的结构)?为什么“第二位的”系动 词用法经常在句法上是基本的,而存在用法则是(始终是或在正常情况下是)语法转换的 结果?为什么这些作为系动词的“第二位的”用法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用法,那怕是 在这种语言发展的早期?(参阅第四章第1节和第五章第4节的统计)我不想再次就这些情 况进行争论。我已经建议了的这种理论上的重新安排之合理必须由它的成果来证明。( 注:C.H.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331、371、394、395、39 7、400.)
卡恩在第7节谈了他的成果对哲学的意义:
与系动词结构一道,断真用法和存在用法(其中最典型的是类型4,5,6)代表着动词
eimi的三种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任何理论或Being这个概念来说都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从哲学的观点看,动词be的问题最终是这样一个问题:词典上的es-的这三种用法是 否共同属于一个具有普遍(或至少非常一般)意义的概念系统,或者它们是否仅仅代表印 欧语言中的独特的语言功能的偶然的群落,是任何一种严格的语言哲学都必须加以搁置 的异质成分的偶发的聚合。(此刻我把不同的存在用法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等一会儿 我们就会分开来谈。)(注:C.H.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33 1、371、394、395、397、400.)
……
在希腊文动词be的系统的统一性问题上我的主张可以用下列三个命题加以清楚的说明 :(1)如果我们把系动词结构当作原初的,那么表示真和在的词典用法就在直觉上变得 清晰与合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观念的天然联系来理解eimi的三重功能这一语言事 实,不仅在心理学上是合理的,而且一定程度在概念上也是合理的;(2)这种基于系动 词结构的用法系统作为印欧语言的特殊性,不仅具有历史的兴趣,而且对于语言理论具 有永久的哲学上的重要性,这只是因为(3)这三种基本用法,就其相互关系确定了一套 问题而言,共同构成了古典本体论的核心,就其也要处理谓词、存在和真而言,它也构 成了当代本体论的核心。(注:C.H.Kahn,The Verb“be”in Ancient Greek,Preface,p .401—402.)
三、对王路教授相关介绍的若干评价
上述摘录虽然没有进入卡恩研究成果的具体层面,但已涵盖了卡恩对自己的研究成果 的基本概括,足以帮助我们对王路教授的介绍下判断了。对照之后,我认为王路教授的 介绍基本准确,但决非“原原本本”,而是有所选择,并部分掺入了他自己的理解在内 。王路教授对卡恩研究成果的介绍与卡恩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表述之间有以下主要差距:
第一,王路教授对卡恩最重要结论(即eimi三种用法)的表述主要取自卡恩的论文,表 述方式是转述,而不是直接引文;而与其相关的具体证明材料取自卡恩的专著。这从王 路教授所加的注释以及他在介绍中喜用einai而不用eimi就可以看出来(尽管这一做法无 可厚非,但容易引起误解)。例如,陈村富教授在读了王教授的论文后,就认为王教授 的介绍与卡恩的原意有出入。陈教授指出,卡恩的专著写作在前,论文写作在后,而发 表时则是论文在前,专著在后。他还指出在这篇论文中,“卡恩论述了希腊动词einai 的三个特征和用法……卡恩讲的是‘语用和意义方面的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是:1. 断真(严格说是包含认识论和逻辑双重意义的真与实,参见第253,260页);2.持续体态 ;3.指称处所—存在,而不是王路所说的‘系词用法、存在用法和断真用法’。”(注 :参见陈村富:《Eimi与卡恩——兼评国内关于“是”与“存在”的若干论文》,第26 0—261页。)
为什么卡恩在专著中用eimi,而在论文中用einai?这是王路教授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而我们知道,“是”的希腊语动词原形是eimi,相当于英文的be,而einai是eimi的不 定式,相当于英文的to be。从卡恩的专著来看,他的目的是要对希腊文动词be作全面 系统的理解,因此eimi及其所有变化形式都属于卡恩的研究范围。而在他提交给古希腊 哲学学会年会的那篇论文中,卡恩意识到eini的不定式einai和eimi的动名词on对于理 解希腊哲学本体论才是最关键的,因此就把论文的取材限定于对esti/einai/on的分析 。王路教授也许认为这一点无关紧要,但在我看来,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卡恩为 什么口口声声说自己的研究目的是阐明希腊文动词be的日常用法和意义,以便为哲学的 分析提供素材,而不是妄求为它的哲学用法和意义提供完整的说明。我认为,卡恩的研 究成果对我们理解作为哲学范畴的on确实有重要启发,但要阐明be动词的哲学历程,则 决非是一个仅靠语言分析或句法分析就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王路教授对卡恩的介绍重点放在那些对他自己的翻译主张(即用中文“是”来翻 译eimi及其各种变形)有利的方面,而对卡恩研究成果中那些不利于他这种主张的成分 着墨较少。他说:“我认为,在卡恩的众多分析和结论中,他的上述三个结论是最重要 的,其中又以第一个结论最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其他两个结论都与这个结论有关,也 因为它们都依赖于这个结论。因此,这个结论应该是我们理解einai这个词的重要线索 和主要依据。我强调这一点,乃是因为由此将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这就是我们 对einai这个词的翻译也应该依据这一点。”(注:王路:《“是”与“真”——形而上 学的基石》,第87页。)他还强调说:“最为重要的是,这不是单纯的翻译,而是对
einai这个词的理解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是根据卡恩的研究而来的。”(注:王路: 《“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89、21页。)王路教授当然完全有权提出 自己的翻译主张(任何人在吸取他人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自己的观点时都会有所取舍) ,但作为对卡恩的介绍,总是全面些好。
读了卡恩的著作,我们对希腊文动词eimi本身含义之复杂以及希腊文分词on作为西方 哲学本体论核心的重要性会有较深的认识。然而,并非eimi的每一个变化形式都是哲学 概念或范畴。称得上是哲学范畴的,是它的动名词或分词形式on。由于on是从eimi演化 过来的,鉴于on在希腊哲学本体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我们可以把eimi称为希腊哲学乃 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文化基因,但它还不是哲学范畴本身。王路教授的介绍有利于我们理 解希腊文动词be,帮助我们去把握希腊哲学范畴on的词源及其含义的多样性,但他对卡 恩研究成果的适用范围讲得不够,而这在卡恩那里却是清楚的。卡恩明确地告诉我们, 他的研究目的是阐明希腊文动词be的日常用法和意义,为解读希腊文动词be的哲学用法 奠定语言基础,所以对西方哲学的ontology的历史性考察不属于他的研究范围。
希腊哲学传入中国以后,从陈康先生开始,中国学者面对这个复杂的eimi和on产生了 种种困惑,这一现象很奇怪吗?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奇怪。不仅是处在 被学者们普遍视为有着根本差异的中西哲学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中国学者会产生这样的 困惑,而且,处在以希腊文明为源头之一的西方现代哲学处境中的西方学者也会有类似 的困惑。当代希腊哲学史专家弗拉斯托在反思on这个希腊哲学的核心范畴时说:
从希腊文的“是”(esti)我们直接得到分词on,得到名词ousia,得到副词ontos。从 英文的“是”(is),我们所能直接得到的是分词being,但得不到名词或副词。我们不 能说“beingness”或“beingly”,而不得不转为“reality”和“really”。但是当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出自同一词干的动词:我们不能说“Socrates reals a
man”或“Socrates reals wise”,除非我们想要开始一场过于热烈的语言游戏,就像 黑格尔主义者或海德格尔主义者那样。如果我们想要说英语,我们将不得不把这四个有 着密切关系的希腊词分成两个词源上互不相关的小组,从第一组中得到我们的动词,而 从第二组中得到我们的名词和副词(还有较为少用的形容词“real”)。这样做并不艰 难 ,但却使在希腊人的眼中视为跳跃的地方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谓“real”和“
reality”只不过是“to be”的形容词和名词形式,而“is”又转过来代表“real”和 “reality”的动词形式。(注:G.Vlastos,Degree of Reality in Plato,N.D.Smith,
ed.,Plato 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Ⅱ,Routledge,New York,1998,p.219.)
西方学者的这种困惑表明,语言分析是哲学思维的前奏,概念反思才是真正的哲学。 仅对概念作反思会显得空洞与抽象,有了语言分析作铺垫,概念的历史性回顾和反思就 会丰满和坚实。
第三,王路教授说他的翻译主张以卡恩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主要来自对einai的理解。 但读了卡恩的著作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我们看到,尽管西方学者也面临着与中国学者相似 的译名问题,但没有人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类似王路教授这样强硬的翻译主张。王路教授 本人在译名上的主张十分明确。针对那种要求对应不同语境使用不同译名的主张,他表 示了反对意见:“我认为其所提倡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别的不说,至少从中文字面上 ,尤其是对于不懂外文的人来说,根本看不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黑格尔论述的 ‘有’和海德格尔谈论的‘存在’根本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实际就会完全割裂了西方关 于本体论问题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讨论和研究,使人们无法看到在这一问题上西方思想 的历史发展和联系。”(注: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第89、2 1页。)
王路教授的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然而在我看来,西方关于本体论的讨论不是一脉相 承,而是一源多流。古希腊哲学家并非个个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理解本体,西方后来的 思想家也并非个个都像黑格尔那样理解本体。弄清eimi的各种用法和多种含义,弄清作 为哲学范畴的to on的源起,并进一步在具体语境中辨析它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用综 述的方式说明西方本体论讨论的历史脉络,并在中国语境中讲清几种译法之间的关联, 就能起到避免割裂西方本体论思想的历史发展和联系的作用。比如王路教授本人的研究 著作就已经告诉我们,西方几位重要的思想家讨论的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都与einai 的断真用法有关。至于译名问题,又何必一定要坚定地主张在各种情况下都要用“是” 来翻译eimi及其各种变化形式呢?难道矫枉一定要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吗?如果我们 注意到了eimi的系词用法,反过来又用eimi的系词用法遮蔽了它的存在用法,那么这样 的译文离开文本的原意不是近了,而是远了。在中文“是”字的含义在现代汉语语境下 都已经系词化了的今天,“是”只与希腊文eimi的系词用法最近,但与希腊文eimi的存 在用法论甚远,远远不如“在”或“存在”更能翻译希腊文eimi的存在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