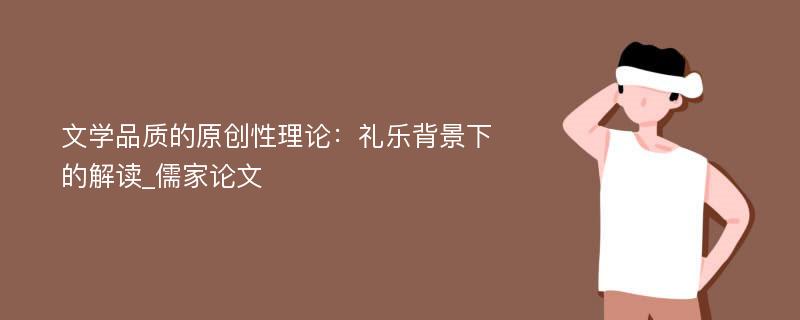
文质原论——礼乐背景下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乐论文,背景下论文,文质原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文学思想发展史而言,产生于先秦两汉的文质范畴以其原创性和无所不包性在意义的实现上通过思想文化的各种形态反复展现,并以衍生出哲学史、文学史和美学史上众多的范畴和命题而贯穿了整个传统时代。它与源于相同知识背景并同生共长的礼乐命题一起,组成了思想史上具有逻辑起点意义的元范畴。探讨礼乐背景下的文质范畴,不仅能使我们对文质生成的历史语境以及包含哲学基础和人文内涵在内的义理有一个本源性的把握,而且有助于我们清理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三代以来由“三才”论和阴阳论所构筑的强大的思想文化传统以及由此生发的自然宇宙观和社会人生价值观等。本文拟从知识谱系和思维模式上对中国思想文化原生时期即先秦两汉时期文质与礼乐的关联作一个审察,希冀以此在文化精神和方法论原则上与古人视界融合,尽可能地体认可靠的思想文化原貌。
一
探讨文学思想的缘起,必然要追溯到文学思想的前身——由各种艺术形态及审美观念所构成的文化思想与时代精神,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该时代占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想。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将礼乐、文质与“三才”、阴阳放在一起言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基本理路。究其根源,成因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其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古人的自然宇宙观和人生价值观,它是由天地人和联系三者终极性的道(天道地道人道),以及贯通其中的阴阳为核心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思维结构,这是古人思想文化视野中最大的解释系统。其中天地人“三才”是核心范畴,统摄一切并搭建了古人思维运行的理论平台。阴阳二元是中介,是贯通天地人之中的两种势力,以对待立义和动态平衡构成天地人结构的内存根据及其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三才”论和阴阳论综合了三代以来的历史文化经验以及诸子各家在辩证智慧上的贡献,是对传统学术的最高概括,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心理的形成并对人文思想的定型起到决定作用,因此是图解古代学术理念、政治文化模式生成的起点。
“三才”思想始于《周易》。虽然《尚书》中多次提到“天”的范畴,但在“天”的基础上增加“地”和“人”,并对此进行最完善、权威阐述的是《周易》。依《易传,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易的符号是根据天地人的关系建立起来的。易每卦六爻,分天、地、人三位,其中初爻二爻为地位,三爻四爻为人位,五爻六爻为天位;其二,“三才”都分而为二,由阴卦阳卦各取一个配合,这就明确了阴阳是贯通天、地、人三道的中介,建构了由阴阳贯通的自然、社会和人事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在“三才”论基础上形成了古人思考人文现象的两个向度:其一,将一切人文现象的源头追溯到天(或天地)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六经”因“与天地准”,反映的是天地的根本道理且其发生和归属都包含在天地之中,因此带有广泛的真理性,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以人文起源为例,《诗纬》云:“诗乃天地之心。”《文心雕龙·原道》云:“言之文也,天地之心。”都是把文的起源回溯到天地这一最高范畴,认为人文与天地并生、与宇宙同源同构,天文、地文和人文以反映“天经地义”之至理而具有贯通一致性。其二,古人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对象,视天地人为一个有机结合的系统:在构造上相同,在精神上共感相通,在表象上互为因果。人处于“三才”之中位,象天法地,阴阳相会而成。从《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的推断中不难看出,古人总是从人与天地同源互感中寻求自身存在的依据,所谓人权天授、人事天设、人文天配等等不过是其具象化而已。我们从汉代《春秋繁露》、《白虎通》、《汉书》到《后汉书》中,亦无时无刻不感到浓厚的因“人参天地”而同类相动、天人感应的文化氛围。可见,源于“三才”论所形成的以人为出发点谈论一切人文现象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
礼乐与文质的缘起也得从“三才”谈起。礼乐的起源,按照《礼记·乐记》的说法有三:本乎天地、生于阴阳、节制人欲。在儒家的一贯理念中,礼乐源自天地,与“三才”之间有着神秘又神圣的关联。《周易·序卦》言先有天地万物,然后有男女夫妇,再有父子君臣,最后是上下礼义,这一个系列浑然天成,和谐统一于“三才”之中,其推论的落脚点旨在证明礼乐所营造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等级秩序因源自天地,所以合理。分而论之,礼乐各有所本,《礼记·乐记》云:“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对于礼乐的起源,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中的论述最为精警:“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在此,董子巧妙地完成了天地人框架中的礼乐建构:礼乐源自天地,人乃礼乐的制作者、宣扬者和体现者,这就为礼乐的存在找到了大本大源,遂成为儒家全部思想合法性存在最根本的依据。文质范畴,从根本上看亦是天地人关系的具象化。在古人看来,物之质文犹如人之内外,属于事物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宇宙万物以及产生的人文现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质内文外即本质与表象的问题。扬雄《太玄·文》云:“天文地质,不易厥位。”《白虎通义·三正》云:“质法天,天法地,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曰文。”《春秋元命苞》亦云:“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天质而地文。”逮至明代湛若水仍云:“物之生也先质而后文,故质也者生乎天地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质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后天而述者也。”(注:湛若水:《唐元次山集序》,《唐元次山集》卷首,四部丛刊本。)可见,古人是将文质视为“三才”的外在表现形态和内在精神品质来言说的。
关于阴阳的起源,古今无有定论,我们根据《周易》中包牺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八卦的说法,亦可以推测是先民从长期的自然、社会、人事观察中得出的关于天地人之生成及发展动因的最直切的推断。阴阳概念,肇端于《国语》。公元前780年,“西周三川”地震,太史伯阳父用阴阳二气是否失序来解释地震原因:“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注:《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因此,阴阳最早是一种自然现象非哲学范畴,“阴阳指寒暖二气,寒气为阴。暖气为阳,认为阴压迫阳气,所以有地震。其所谓阴阳,属于天文学的概念”(注:朱伯惷:《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将阴阳上升为哲学范畴的是春秋末的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注:王弼:《老子注》四十二章,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使之抽象为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并成为解释万物变化的二元原理。成书于战国的《易传》视阴阳以及变化法则为事物的本质,“一阴一阳之谓道”(注:《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将其提高到道的高度,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来言说,建立了“《易》以道阴阳”(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的思想体系。汉代的董仲舒对于阴阳理论的贡献在于将“三才”所体现的自然之道统统纳入阴阳法则中并赋予其鲜明的道德意味。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他根据“天道之常,一阴一阳”的理论,将阴阳对立统一所体现出的尊卑、贵贱、亲疏关系与天地人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贯通起来,并由天地人在阴阳属性上所表现出的同一性推演出“三纲五常”之神圣至上性,在董子这里,“三才”论与二元论真正合一了。
在今人看来,阴阳配列及嬗变是通过一套简易的识别代码建构了一套认知世界的全知全能模式,引导人们自觉地从森罗万象的事物对立面出发去感知、把握天地人组成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从自然现象到人文现象,从生命范畴到道德范畴,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阴阳对举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库。就本文所论及的内容而言,一方面,作为范畴并举,文之于质,礼之于乐,都深受阴阳对待立义结构方式的影响。《礼记》是以阴阳释礼乐的典型例子。《郊特牲》云:“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丧服四制》云:“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论文质也不离二元对举的模式,《朱子语类》所谓“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而是相对立、相比较存在的,因此对事物的认识也必须放在相互关系中去思考。叶燮《原诗》中对这种思维方式归结为:“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另一方面,阴阳作为对立统一的正负两极因互涵、互补和互转而处于一种动态平衡,旁及礼乐、文质亦是如此。以文质为例,古人常常习惯于在文质的递变中寻求天地人的动态和谐。《周书·苏绰传》载《大诰》云:“天地之道,一阳一阴;礼俗之变,一文一质。”《论语·雍也》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判断也表明了夫子对文质作为成人之基本要素的一种价值取向。扬雄《太玄·文》云:“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斑斑,万物粲然。”质是阴气内敛的结果,文是阳气外散的结果,文质结合万物盎然。文质因为具有阴阳变化的普遍意义,遂从历史、道德范畴上升为本体论范畴,这无疑就把传统的文质统一思想上升为自然宇宙的普遍规律了。
综上所论,以今人的逻辑推理,天地人是一个整体结构,是一个网,阴阳是网里的关键要素或联结性范畴,它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范畴系统(注: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对此,古人的直观推断如下:圣人效仿天地之理法(道),创造了与天地相应的人界礼乐秩序(经),然后用经义教化芸芸众生,使人与天地一样处于参赞化育之中和运行秩序中。在此结构中,礼乐与文质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范畴,它们贯通了后世所谓哲学、伦理道德和文化艺术等精神生产的各个领域。总之,“三才”与阴阳结合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浸透到古代学术的一切领域,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最为根本性的思想资源。
二
在大多数关于礼乐对古代思想影响的论述中,一般视礼、乐为一体,且乐是依附于礼的,故重在论礼。实际上,礼乐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乐与礼比较而言,无论从起源意义、宗教文化层面还是从所体现的精神境界上,都要先于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礼。大体而论,先秦两汉时期礼乐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周公“制礼作乐”,西周以具体而复杂的礼乐体制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一统而成为后世诸子追捧的黄金时期,这是礼乐由原始宗教文化演变为政教伦理文化时期,特点是乐主礼辅;第二阶段是春秋“礼坏乐崩”,在此背景下兴起的诸子之学,自然将礼乐作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从他们或肯定或否定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礼乐不仅仅是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更是关涉到人的本质和现实存在的问题。孔子以“仁”为核心对礼乐进行了理论总结,使之进一步人间化、合情合理化,礼乐之间表现出剧烈蜕变的特点;第三阶段是汉代“礼乐复兴”,有汉一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一直在礼乐的兴衰之间反复拉锯,这是对诸子思想重新整合以后形成的新的礼乐传统,学术信仰与政治的高度结合使之最终演变为帝国意识形态,特点是礼主乐辅。礼与乐在这三个阶段的历史地位是不一致的,由此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在先秦两汉思想的发展中,文质不仅仅是一个内容与形式认知上的问题,更是一个充满人文色彩和历史感的范畴。它是古人对人之为人乃至宇宙间一切生命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本质与表现关系所作的反思。文质范畴的三种表现形态以礼乐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和外在必然性为依据,在礼乐发展的三个阶段表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文质是体认三代礼乐形成因革之极为重要的出发点与连接纽带。从文化思想史的两个层面看,在礼乐文化的大传统背景下,文质范畴表现为历史论、道德论,具有描述和价值判断功能;在文学艺术的小传统背景下,文质的表现形态为艺术理论,具有审美的功能。
在“制礼作乐”时期,文质范畴主要体认为以文质论史,其最初兴起是源于对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历史性描述和评价。三代礼乐,夏代渺远,留下的文献很少,殷周礼乐,从春秋战国开始,古人就习惯将“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作为理解二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一把钥匙。关于“亲亲”、“尊尊”,《礼记·乐记》释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散则离。合情饰貌,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也。”在此,“亲亲”的原则在功能上被明确为“同”,被赋予了“乐”的成熟形式;“尊尊”的原则在功能上被明确为“异”,被赋予“礼”的成熟形式。诚如杨向奎先生所言:“尧、舜的‘亲亲’、‘尊贤’与周公所制作的‘礼’、‘乐’在精神与功能上属于同一个系统。”(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三代的社会结构就是在礼乐的维系下以“亲亲”、“尊尊”原则为治而一脉相传的。对于殷周礼乐的实质,金景芳先生认为“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亲亲’、‘尊尊’。用一个字概括是‘质’、‘文’。”(注:金景芳:《金景芳晚年自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其最早的含义是指殷周不同的继承制,殷人超现实重原始血缘故尚质,周人重现实尚政治故文。故“亲亲”、“尊尊”的结合就是文、质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代礼乐的变化也即三代文质的更迭。
以文质论历史的最早记载见于《礼记·表记》,其中有两段文字假孔子之口对三代文化的精神差异进行了洋细的描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蔽,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夏代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巫祭和鬼神,礼乐文化的特点是愚朴鄙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信鬼而轻礼,礼乐制度不够完善;周人尊礼重人,礼乐制度完备但繁缛。具体而言,三代文质,与世推移,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孔子认为“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孔疏认为“此一节总明虞、夏、商、周四代质、文之异。”也即是说,由夏至商,礼乐文化大体是由野到质、文质相间;由商至周,则是由质到文、文胜于质。三代社会由“质”而“文”的演进,伴随着“文”的每一步进化,都会出现相应的弊端。
文质论历史的传统一经形成,文质遂成为一个打通古今历史和不同学科的桥梁,在“尚文”、“尚质”或“文质相半”的追求中寻求传统和进化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从而奠定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基本精神。汉代的董仲舒用文质循环的历史哲学观来解释三代递变的原因,《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主人。”(注:凌曙:《春秋繁露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其“通三统”的循环论,深刻地影响了汉以降的政治思想文化。《白虎通义·三正》引伏胜《尚书·大传》云:“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注: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文镜秘府论·天卷》引隋代刘善经言:“三王异礼,五帝殊乐,质文代变,损益随时。”(注: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天卷》,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宋人王钦若《册府元龟·帝王部四十·文学》中亦云:“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繇其事。”(注:王钦若:《册府元龟·帝王部四十·文学》卷四十,台北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逮至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中对此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在“礼坏乐崩”时期,文质范畴主要体认为以文质论人。从人出发谈论一切人文现象,本质上是对礼乐教化成人的一种反思,属于道德价值的评价。无疑,文质论人的传统肇始于孔子,孔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自觉传承者,他毕生致力于营造一种基于等级秩序的和谐社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孔子在礼乐教化成人中为调和个人情性与道德理性之间的矛盾所设计的一种理想典范,这与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人生三步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均重在强调自然天性与社会规范的相得益彰。《论语,宪问》云:“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对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这样的分析:“成人,犹言全人……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而其为人也亦成矣。”这个分析符合孔子原意,是非常深刻的。所谓“成人”,就必须质内文外,德才兼备。这里的“质”指人的自然本性、内在情性,以真善为特征,体现了乐“不可以为伪”的精神;“文”是指人文活动中必要的规范和文饰,是人内在情性的外在表现,体现为礼,所谓“礼自外作,故文”,其重要特征就是不能失之“野”,以追求美为终极目标。对此,我们从《礼记·文王世子》中亦可得到印证:“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以文质论人之道德的模式形成后,鉴于文质与礼乐、美善等范畴在原初意义共同的价值取向,文质就成为了古代士人成就人格、道德的重要标准,扬雄《法言·先知》云“圣人,文质者也”,可谓一语言中。
从文化思想史的两个层面看,先秦诸子的价值取向表现各异。处于礼乐蜕变转折时期的孔子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文化心态,其“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表明了他对礼乐之“文”的大传统是肯定的,但在小传统上,虽云“文质彬彬”,且“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说法也不乏文质审美思想的萌芽,但孔子对文质范畴的历史描述功能与道德价值评价功能的看重是远胜过其审美功能的,在本质上更重质。处于思想交锋中的诸子思想相因相生,他们所依据的知识背景仍然是三代礼乐传统为主体所构成的信仰系统,支撑其理性革命的知识谱系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他们不同的礼乐观决定了不同的文质观。与儒家相比,墨家、道家、法家在两个层面上的取向各不相同。墨家是礼乐思想最早的反对者,他们基本上由中下层劳动者组成这一结构决定了他们对礼乐制度中所体现的尊卑贵贱之分深恶痛绝,遂标举“非乐”、“先质而后文”向儒家礼乐仪式的繁文缛节弊端正面进攻,但因其功利性强而审美性少矫枉过正,直接导致了墨学思想在秦汉的衰微。道家对西周礼乐传统怀有深刻的怀疑,庄子认为礼乐文化使人丧失天然本性,所谓“文灭质,博溺心”,为了“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就必须“灭文章,散五彩”,表现出他们文质相悖、重质废文的文质观。法家猛烈抨击了儒家所推崇的西周礼乐制度,彻底撕破了儒家人伦情爱中温情脉脉的一面,认为人都是有私利贪欲的即人性是恶的,文质是势不两立的,故主张重质弃文,甚至否定文。《韩非子·解老》云:“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
汉人以“大汉继周”自居,遂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礼乐复兴”。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以文质论史、论人都没有超出孔子所涉及的政治历史与道德的范围,文质是一个关涉到意识形态诸多领域的具有深刻礼乐内涵的原初范畴。西汉后期的扬雄是文质范畴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意义在于:其一赋予文质形上之意义,其“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斑斑,万物粲然”的阐释为文质确立了言说的哲学依据;其二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文质相副的人伦理道德学说,提出“事辞称”的命题,第一次从辞赋创作的角度谈论文质问题。《法言·吾子》云:“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这里的“事”、“辞”指事理和文辞,亦即质与文。扬雄首先肯定了“事”重于“辞”,即质重于文,但同时又要求“事辞称”,文质统一而不失偏颇。他针对汉赋尚辞的倾向,反对淫辞丽说对文的损害,《法言·吾子》云:“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也。”他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危害,极具启发性。从孔子的文质论人发展到扬雄的文质论文,在精神实质上虽无根本差异,但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却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这是后世真正文学意义上文质论的滥觞。其后的刘勰、萧绎、尚衡、姚际恒、姚鼐、章太炎等关于文质统一的说法基本上都沿袭了“事辞称”的思路。清代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中“文以质立,质资文宣”的结论阐述了文质之间乃是文因质立,质为主导与质以文别,文推动质的辩证关系,并指出此乃推动文学发展之重要动力,其论高屋建瓴,可谓文质论文的理论总结。总而论之,就文质范畴的本身发展理路而言,以文质论人格到论文章风格,从道德判断到审美判断也是顺理成章之势。魏晋以后,随着文学观念的自觉,更强化了从纯文学的角度体认文质范畴,以文质论文学遂成为后世文质论的主流。
三
考察中国上古思想文化史,可以发现,礼乐与文质都生成于三代以来的中华原生文化圈,在生成语境、构成形态、话语范式上有着共同的理论背景支撑,是中华本土文化系统中最具混融性和包容性的核心要素。中华文化在其后异质文化的冲击下,能保持自身文化形态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古所形成的礼乐文化传统的浸淫。古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文学内部的传承,另一方面,更受制于思想传统的强大控制力量,尤其在文学观念尚未独立的先秦两汉。先秦两汉是许多重要的文论命题的原生时期,这与后世多元的发展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最初作为文化思想的附庸而发端,历经了由广义到狭义、由素朴到精致、由文学外部到内部、由无意为文到有意为文的发展过程。因为这些文论命题都是适应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而生的,因此,对文论思想所依存的历史文化情境的瞭望,就相当重要了,而这个历史语境,就是礼乐传统。
礼乐作为中国文化原生时期最主要的思想资源和知识背景,上则表现为天道变化,下则为反映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中则体现为人事变迁的法则,涵盖了从典章制度到精神道德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显在的联系与政教的典仪节文,还是内隐的联系与心理的“六艺”之教均为礼乐文化的载体。由此角度,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都是礼乐的产物,文学乃至文论当然也不例外。礼乐文化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学思想的内在精神品质,深刻而内在地影响了古代文化传统以及文论史上众多范畴和命题的形成。文质范畴正是因为在其产生和演变过程中吸收了丰富的礼乐文化因素,因而形成其理论内涵的深厚性和阐释形态的多元化。礼乐传统笼罩下生成的文质范畴,质态表现层面有二:从外部表现的功能看,文质是对三代礼乐的历史性描述、对人的自然情性与道德理性的评价性判断、对语言艺术形象的审美性判断,其原初阶段具有描述、判断和审美等多项功能。从内在发展的理路看,文质在“一文一质”、“文质相半”的动态平衡中获得的质态稳定性,并没有随历史的发展而消失,而是作为思想文化传统中一个独立、核心的联系与中介延续不断,其意义发展的脉络由礼乐的载体最终进入文学这样一个次生领域,并成为此领域最重要最显著的一个元范畴,其间历经了一个漫长而极具启发意义的演变过程。
从文学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文质文论的价值取向大致有二:一是在价值层面上要重振儒家礼乐传统及其衍生的文学观念,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主流,表现为轻视为文的技巧而重道德内涵,尤其强调作品内容与创作主体之道德情性的关系,并衍生出“文以载道”的思想。文学的功能偏向社会政教,儒家的若干正统论点,如“诗言志”、“思无邪”等被后人视为补偏救弊的良方而推崇备至;受此影响,文质范畴在意义的指涉上更倾向于重质轻文的审美标准,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则倡导恢复先秦质朴的文风,反对汉魏以后浮华的风气,这是后人以文质作为批评术语时最平常的一个选择。二是在文学思想发展观上形成以文质代变来描述文学退化史的思维模式。由文及质的历史进程,是文学以及各种文化现象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文质观念在文化传承上自然衍生出“贵古”和“趋新”两种相对的文学史观。综观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在质之“贵古”与文之“趋新”之间反复拉锯展开的一部文学批评退化史。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对文学的变迁发展作价值评价时认为,“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他以质文更迭循环来证明其今不胜古的文学史观,认为一部文学史的发展乃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过程,这与其“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概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刘勰的理论视域里,所谓“通变”,通的就是古今文质、雅俗之变。逮至明代胡应麟更以“格以代降”(注: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来定格《诗经》以后诗歌的发展历史,简明扼要地点出了文论家从古今文质对照中得出文学退化论的共同认识,这也是后世以复古之名行变革之实的重要理论依据。要之,文学退化与整个文化乃至文明进化交错之悖论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特有的书写模式,亦使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文学观念都是现出极其浓郁的向后看的乌托邦倾向。
在发生意义上,文质是对“三才”存在本质及表现形态进行的解答而非针对文学本身而言,以其范畴的原初性和内涵的丰富性闪现在各种人文活动中,尤其在文学领域。文学作为人文化成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以本体结构上内容与形式的区别、语言表现形式之质朴与文饰的异同、创作主体之道德人格与自然情性的矛盾以及文学史进程之古今质文之变,与文质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遂成为文质发展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文学这个次生领域展开的文质范畴,关涉到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家论和接受论各个方面,是古代文学思想史中出现得最早且贯穿始终的范畴,历代文论家对其备加关注。后世古今文质之争,多纠缠于质朴与文饰的争论,对文质的理解,从思想文化本源层面的价值判断外化为语言的表象性描述,使一个具有厚重人文内涵和历史感的范畴单一化、平面化。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论的引进,更强化了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去理解文质的内涵,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从原初混融意义到独立文论范畴的演变历程,从而遮蔽了其本原意义。
惟有对文质发展历史和文化传承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古人之文化处境保持同情之了解,将古代文论中众多孤独的范畴、命题以及方法论的形成从纯粹的理论形态回溯到其生成的原初历史文化语境中,将其从业已不断阐释而形成的传统回复到其原生的批评意识中,才能发现承流会变之轨迹,并重新梳理其由本及未之源流。文质在原初意义上的丰富性和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与后世发展形态的单一化和平面化是完全不能等同的,在思想史建构上所具有的逻辑起点意义也是不相同的。同时,它的发展衍变也昭示出,文质作为一个始终高悬在三代乌托邦想象中的元范畴,一旦脱离了礼乐文化母体的原生意义,离开了先天所混融的诸多意识形态品格,就只能是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差异、没有历时性文化传承和共时性个体差异的停滞的平面范畴,也就无法再现其在思想文化发展上的重要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