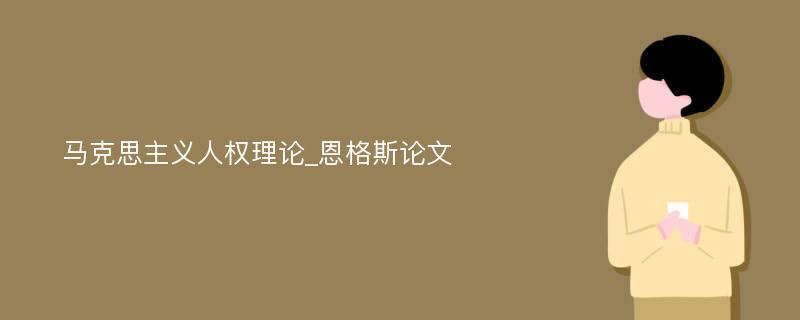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人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人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说过:“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①,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我们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不使用人权概念,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将人权问题视为禁区。特别是“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人权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在实践中也导致了对人权的漠视和侵犯。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重要报刊还以“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等为题,发表过一大批文章,把人权看作资产阶级的专利,强调无产阶级历来对人权口号持批判的态度②。但人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实际上,资产阶级“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③。马克思主义不仅讲人权,认为人权是社会的、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天赋的、抽象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和工人政党在斗争中要善于运用人权武器。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仍不断利用人权发动反华攻势。因此,高举马克思主义人权旗帜,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回击国际敌对势力的人权攻势,对我国顺利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具有本质区别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本质区别,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前者要求普遍的人权,真正的平等。所谓普遍的人权,即:不仅是纳税的白种男人之间要平等,而且要实现男女平等、各民族平等、信这种宗教与信那种宗教的人平等。所谓真正的平等,即:不仅要实现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的平等,而且要争取实现经济地位的平等。因为资产阶级争人权就是反封建特权,争平等,而无产阶级人权要求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实现所有人全面真正的平等。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④ 马克思主义者实现经济地位平等,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实现占有生活资料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各尽所能”,包括两重意思:一方面,每个人都自觉地、自愿地、自由地劳动,尽量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和才能,为社会也为自己谋福利;另一方面,社会要给每个人提供能发挥其体力和聪明才智的条件和机会。在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很高水平,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候,也就是平等问题、人权问题最终解决的时候。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存在着原则的区别。从实际的生活看,各国由于文化传统和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差别,各国发展人权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是不相同的,不能把某种模式强加于别人。但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长期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人权存在着普遍性,当今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可以进行对话与合作。承认这一点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发展人权的坚定信念和宽广胸怀。
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与传统的人权观在许多方面并不矛盾,如马克思主义承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更完整,强调了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受到美国广大下层人民的欢迎。美国人权问题专家约瑟夫·郎卡(Joseph Wronka)在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权政策的影响后,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是现代美国人权思想的来源之一。”⑤
马克思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一项历史权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近代人权学说把人权看成是天赋的、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在马克思看来,人权既非天赋,也不永恒,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他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指出:“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批判’关于人权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比黑格尔更有批判性的言论的。”⑥ 马克思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消除封建障碍而在与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取得的政治权利。用人权代表特权,适应了新兴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⑦
对资产阶级人权的批判,最简明犀利的是邓小平的论断,他说:“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⑧ 可谓一语中的。
二、人权是社会的产物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权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人权是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学者们用“天赋人权”、人类社会早就存在“自然权利法则”等等学说来进行解释,用纯理性观念来作说明,似乎是某些天才人物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了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则。马克思指出:出生只是赋予人以生命,使其成为“自然的个人”,人权作为权利的一般表现形式,则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然人的产物。把自然的个人同作为社会关系的人权看成“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正如马克思所说:“出生只是赋予人以个人的存在,首先只是赋予他以生命,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而国家的规定,如立法权等等,则是社会产物,……所以个人的出生和作为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社会职能等等的个体化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同一,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在这种体系中,自然界就像生出眼睛和鼻子一样直接生出王公贵族等等。”⑨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科学地阐明了为什么从17世纪以来人权和权利平等等理论和口号得到确认,并日益战胜“君权神授”和等级制思想。1858年,马克思用深刻而通俗的语言说明了引发和倡导权利平等和人权理论的最深层次动因。他指出人们在社会生产和需要上的自然差别,“是使这些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动因,是使他们作为交换者发生他们被假定为和被证明为平等的人的那种社会关系的动因,那么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权”是作为封建特权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出现的,“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11),“由于竞争——这个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是平等化的最大创造者,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便成了资产阶级的决战口号。”(12)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与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与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别法令”(13),从此,“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14)。
恩格斯十分明确地阐明了权利平等的经济基础和现实基础。他说:“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15)
恩格斯还深刻地揭示了平等、自由等人权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现代的平等要求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6)
这样,马克思主义论证了人权的社会性,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宣扬的“抽象的超然的天赋人权说”和“契约论”等唯心主义人权理论。
三、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人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有了社会就有人权,只有当社会的经济进步把确立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时,自由和平等才被宣布为人权。人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其内容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丰富。
人权,最初是为反对神权和封建特权提出来的。早期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用人道否定神道,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人权否定神权,呼吁从神学束缚和中世纪黑暗中解放出来。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人性和自然法出发,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核心是“生命”,基石是自由和平等,理论逻辑是每个“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有同样的价值和尊严,都应该享受同样的自由和权利,并认为权利是天赋的、永恒的、普遍的、不可转让和剥夺的。国际人权专家把人权发展划分为“三代”(17)。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第一代人权,以1776年美国发表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发表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标志。美国《独立宣言》所说“人人生而平等”的英文原文“人人”不是person,不是everyone,而是all men,即“所有的男人”。第一代人权不包括妇女、也不包括有色人种,既有性别歧视又有种族歧视。“人人享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是第二代人权,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第二代人权表现的是个人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要求逐步清晰,提出了“集体人权”、“发展权”等要求。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是第三代人权。人权的发展进步,主要是从个人人权发展为集体人权,从政治权利发展为经济、文化权利,从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发展到为全世界人民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服务。这是历史的进步,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很不情愿,又难以阻挡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和一切权利一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总是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总是历史的和相对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8) 针对资产阶级人文学者的所谓“天赋人权”,恩格斯尖锐地指出:“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19) 马克思借黑格尔的话说:“‘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20) 恩格斯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21) 正因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权产生后其内容在不断扩大,并已远远超出了早期人权思想家设想的范畴,并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发展扩大。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不是“自然”“天赋”的而是历史的,其发展只能在社会历史斗争中逐步实现。鉴于西方列强争夺市场发动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保护人权。1948年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国际范围的人权活动的开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取人权的斗争。1955年万隆会议、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1986年通过的《发展人权宣言》等,不断地使人权概念的经济内容得到发展充实,使生存权、发展权和集体人权概念得到不断的认同和发展。
四、人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人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阶级内容的。人权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的反映,但它并不是人们现实利益的直接反映,而是现实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将自己的利益要求普遍化的产物。人权在形式上表现为整个人类的普遍理想,是“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但在内容上却反映着一定时代人们的利益要求及相互关系。人权的这种普遍形式与特殊内容的统一,决定了人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要求,而资本主义社会人权的普遍形式却掩盖了不同利益要求之间的差别。因此,人权是具体的,人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都是具体的,抽象的人权根本不存在。这一点与资产阶级片面强调抽象人权的观点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的经典定义是马克思主义具体人权的核心,是我们研究人权理论的基本指针。恩格斯在1886年很生动地说明了人权的实现不能超越经济结构,他说:“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22)
马克思主义人权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真正的平等。恩格斯阐明无产阶级对平等要求的实质内容时指出:“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23)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和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都不满足于形式平等,而要求实现真实的事实上的平等。列宁也表述过同样的思想:“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24),“‘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25),“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26)。
五、无产阶级和工人政党在斗争中要善于运用人权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和工人政党在斗争中要善于运用人权武器,而不是摒弃它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另一精华。马克思认为,以自由平等为具体内容的资产阶级人权,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只能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反映,并以服务于资本剥削作为其重要的社会功能。资本主义“人权本身就是特权”,“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而“人权只要脱离了作为它们基础的经济的现实,就可以像手套一样地任意翻弄”。这是一个“谜底”。知道这个“谜底”,也就容易看清那些惯用“人权”大棒干预别国内政者的蛛丝马迹。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27) 即工人政党应该尽可能地迫使资产阶级政党“扩大选举权,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取得运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28)。因为“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29)。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等等权利,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夺取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无产阶级和工人政党“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30)。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并升华了无产阶级的人权要求,把无产阶级朴素的人权理论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它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无产阶级人权要求的理论总结和发展,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重要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批判并不是对人权本身的否定,相反,它为社会主义的人权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社会主义运动的每一个发展总是伴随着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也不需要“权利”法则调整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刚刚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仍“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权利”原则来规范社会(31)。列宁也曾经指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32)。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用人权原则来规范社会。但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都曾长期简单地将“人权”概念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排斥。实践表明,人权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它更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面旗帜。正确地认识这一点,为我国的人权理论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起点。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积极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权武器与资产阶级人权作斗争,中国政府1991年至今每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我国人权入宪正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权武器的充分体现。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8-229页。
②董云虎:《“人权”入宪: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人民日报》2004年3月15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⑤Joseph Wronka:Human Rights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 ,P.82.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5-19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17)喻权域:《人权问题的来龙去脉》,载《党建研究》1999年第7期。李林:《人权概念的外延》,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5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8页。
(24)《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25)《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页。
(26)《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6-8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3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