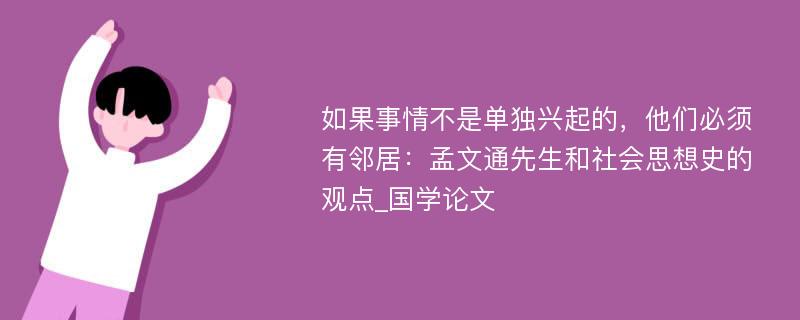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有论文,视角论文,思想史论文,生与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史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普通话”,其余各专门史则有些像各地的“方言”,要保全自身也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近年的趋向则相反,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入其他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在近年中国大陆处于上升地位的各专门史中,思想史是其中之一(注: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现象,因为思想史在西方已呈明显的衰落趋势,海峡对岸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走向;而近年较多致力于“与国际接轨”的大陆学界,却表现出与西方相异的发展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过去政治史独大现象的反作用力所促成。)。而思想史应当怎样研究,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注:大陆学者中葛兆光可为一个代表,其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0年)的长篇“导论”皆着重讨论“思想史的写法”。海外学者中王汎森最近也有连续的论述,参见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北)14卷4期(2003年12月);“思想史研究的反思”,四川大学喜马拉雅讲座,2004年9月15日。)。多数人似乎希望思想史的研究更开放而非更封闭,蒙文通先生对此亦早有论述和实践。
蒙先生治史最重通识,所谓通识,涵盖今人所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由纵的一面言,蒙先生尝据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而史学“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更要能“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总之,“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然后可以做到“言古必及今”而“言今必自古”(注: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1、6页;《中国史学史》,收入《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254—255页。)。
在横的方面,蒙先生的名言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他一向以为,中国历代“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故唐代古文运动之兴起,也因为“有天宝、大历以来之新经学、新史学、新哲学,而后有此新文学”(注:参见蒙文通:《经史抉原·评〈学史散篇〉》,403页;《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222页。)。换言之,同一时代的思想学术是相通的。这里所谓相通,既有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相互支持的一面,也包括其间的对立、冲突和竞争。
或者可以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和“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二语,形象地代表了蒙先生提倡的前后左右治史方法(注:我于1995年秋在四川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以此二语从纵横两面简述蒙先生的治史取向,当时听讲者中似不乏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该文后以《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跨世纪开放型新史学》为题刊发于《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2期),蒙先生曾长期执教于四川大学,然拙文的相关内容似未引起该校历史系学生的关注。)。近人欧阳竟无曾说,他读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后遇沈曾植,指点其“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欧阳氏归而觅俱舍前后左右之书读之,三月乃灿然明俱舍之意。蒙先生尝以此为例,强调读书当“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注: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3页。)。这样的读书方法其实也就是蒙先生治史的一个主要特点,不过其探讨史事的“前后左右”往往远更宽广。
中国治学传统本推重广博,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说法。汉代儒家“定于一尊”后虽有排斥“异学”的倾向,似未从根本上影响到崇尚淹博的学风。王安石便注意到,蜀人扬雄虽曾表示“不好非圣人之书”,其实他对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尤其传世之经书不全,若仅“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王氏自己也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注:按王安石说扬雄“不好非圣人之书”,大概是指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所说的“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1]。
胡适在引用王安石的主张后进而提出:“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他举《墨子》为例说,“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论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故“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胡适以为,读书“不可不博”,即“什么书都要读”,这样才能“加添参考的材料”,知识广博而后“读书时容易得‘暗示’”,可触类旁通[2]。
类似观念在民初学界并不少见,王国维便曾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3]。顾颉刚也指出,“各种学问都是互相关联的,他种学问不能进步到相当程度,一种学问必不会有独特的发展。同样,一种学问里面的许多问题也是互相关联的,他项问题若都没有人去研究,一项问题也决不会研究得圆满”。譬如孟姜女一类传说的故事,各处皆有,若进行广泛搜集,并将各种故事同时整理研究,则可生互助互补之效,“许多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之望了”[4]。
不过,这些关于博览的论述多近于今日所谓“跨学科”的含义,而沈曾植关于“俱舍宗”和“俱舍学”的区分,却不仅意味着广读他书而已,更隐约提示着一个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注:试比较胡适同一文中所说“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论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胡适:《读书》,《胡适文集》,第4册),可知他注重的是“跨学科”知识,而不是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蒙先生将此提升到意识层面,对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有着相当切要的论述。他明确提出:“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比如以黄老和今文学为代表的“老子、孔子之学何以在汉代战胜百家之学”,这一大问题就当从其得势之原因和所起的作用着眼;“从这里看孔、老,似乎比专就孔、老哲学思想看,更有着落”[5](17页)。这是蒙先生治史取向的特点之一,下面试申论之。
内篇:时代精神和学脉渊源
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渊源甚早,孟子已提出“论世知人”的方法,他说:“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就是说,要真正了解古人到可以成为朋友的程度,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更要“知其人”,而“知人”的方式就是“论其世”。推广言之,“论世”不仅可以知人,也可知书、知事。
一、历时性和共时性
傅斯年就特别强调历史上的人与事和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即使是所谓同一学派亦然。他认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所以,如果他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就要“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6]。在钱穆的印象中,北伐后的北大历史系由傅斯年暗中操控,因他“主张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故该系所定课程也以断代史为优先(注:钱穆并说,有一个专治明史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傅斯年甚至“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168—169页。)。
类似的观念在20世纪史学界似相对普遍,法国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就曾引用“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的阿拉伯谚语,来强调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那段时间来了解[7]。傅柯(Michel Foucault)也认为,包括历史叙事在内的任何“话语”,都“不应诉诸于渺不可及的起源之陈述,而是在其发生之时如其发生之状来进行探讨”。(注:据法文本翻译的此书中译本这句话意思相当不同:“不应该把话语推到起源的遥远出场;而是应该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见《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30页。)[8]
这样的取向好像更多提示着共时性的一面,而史学区分于许多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似乎是历时性。陈啸江在区分历史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变迁时说,“历史学所着眼的,乃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变’的法则;而社会学则以现社会发生的现象为其中心,过去的研究,最多亦不过供其为研究现代之参考而已”(注:按该书原文为“通过过去、现在、未来的‘变’的法则”,语不通,疑其中之一“过”字为后之校者所加,故删去。)[9]。
史学的时间性确应予以特别的重视,惟“历时性”和“共时性”在语言学里常常是对立的,在史学中却可以是也应该是相互配合的。晚清官方的新史学对此已有认识,1904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就注意到“通鉴学”和“正史学”的分别,认为两者“纵横各异。正史学精熟一朝之事,而于古今不能贯串;通鉴学贯通古今之大势,而于一朝之事实典章不能精详”。但“若不立正史学一门,则正史无人考究,于讲通史者亦有妨碍,故正史学与通鉴学亦有相资补助之处”(注:该章程并要求,不论是治正史学的还是治通鉴学的,除相互参考外,“并须参考外国史”。可知当年章程制定者的学术眼光不仅通达,且已相当“现代”,确可称为“新史学”。参见《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1904年颁行),收入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4页。)。
蒙先生即认为治史“必须搞通史”,盖“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但他也指出,同时又必须对某一段断代史下“深入功夫。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5](6页)。另一方面,侧重于研究“一段”历史的严耕望也强调专精与博通并重,以为治断代史者应“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因为“断代研究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10]。
论世知人取向最重视立说者所处的时势和环境,实兼顾了“共时性”和“历时性”。若借用佛家的术语,这里的“缘”是与“因”是相关联而伴生的。如陶孟和所说:“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所以要明白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考察他的言行,是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的。然而这个时势环境,也并不是天造地设,乃是人类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经果。一时代的时势环境制度等等,都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了解了那时代的状况,才可以真明白那历史上的人物,才可以评较那些人物的言行”[11]。
且“论世知人”本是双向的,不仅“论世”可以知人,“知人”也有助于“论世”,两者本相辅相成。蒙先生特别提出,“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要通过“突出某些人物”来“论述当时的变化和风气”。如讲晚清今文学,就“应从张惠言、孔广森、庄存与、刘逄禄、宋翔凤以至陈乔枞父子讲起,否则,龚(自珍)、魏(源)的出现将为无源之水”[5](32-33页)。
更重要的是,时代风气的变化并非架空立说,仍要落实在“突出某些人物”之上。蒙先生论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学术界的变化说,那时已“产生了一个反对宋人传统的新风气,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的口号”。这一风气“从文学首先发动,漫衍到经学、理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王阳明正是在这一风气下起而反对朱学的,李贽也是从这一风气接下来”。这样,“纵把李贽写得突出些,也不会显得突然”[5](32页)。
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即是重人,正史被称为纪传体,学史则有学案体(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历史书,所论是理学的“学术”及学脉本身,而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此点前贤早已述及,然今人多不注意,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5页。);在人物基础上重建“学脉渊源”和时代风尚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与某些专论结构、功能却对“人”本身视而不见的社会科学取向颇不相同。而明代士人“反对宋人传统”的风气从文学漫衍到经学、理学等领域的走向再次凸显了蒙先生关于“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论断。既然“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则对任何特定文化现象就“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5](33页),并及“其它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注: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是蒙先生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收入《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巴蜀书社,1999年,253—380页。)。
蒙先生认为,“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该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故“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只有“在排除了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对该史料的歪曲、影响之后,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真象”[12]。故具体史料受其时空社会环境的“制约”是多重的,不“结合”其所出之时代、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进行分析,固不足以认识之;若不“排除”同类因素“对该史料的歪曲、影响”,同样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真象”。
本来同一时代的不同思想学术观念之间,既有相互支持的一面,也有对立、冲突和竞争的一面,两者从不同侧面共同体现着事物的“相通”之处。蒙先生曾说:“先秦诸子号称百家,……就实际论,主要者只儒、道、墨、法四家而已。各家都起自战国时期,在长期并存的岁月里,彼此之间不断的斗争、辨难。及至战国晚期,各家在长期斗争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都改变了其原始的面貌。”[13](201页)这是一个重要的睿见,通常讲到思想斗争,多强调其对立的面相,而辩难冲突过程中竞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并且因斗争的结果而“改变其原始的面貌”,却往往被忽视。
一方面,蒙先生指出,儒家在汉代“能战胜百家而取得独尊地位,当然绝不偶然”,首先“应当到当时儒家——主要是今文学家的思想内容中去找原因”[5](16页)。另一方面,考察特定思想流派对立一方的言论,亦必有所得。如王国维所说:“周秦诸子之说,虽若时与儒家相反对,然欲知儒家之价值,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14]这仍是说,任何一家学说思想都是并存而竞争中的众家之一,要了解特定一家的思想,就需要尽量多读其前后左右之书。研究者具体怎样“论世”可以千差万别,但基本指向一条从作品之外认识作者立意的路径(注:如在研讨近代“国学”之时,如果把“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看作两个“社群”,则从社会角度考察前者怎样因应后者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以及“国学”作为一个类型或门类的学问怎样为社会所认知,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都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国学”的信息,这些信息又反过来增进我们对特定时代所谓“国学”的理解。在看到民初一些本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趋新学人却把相当数量和类型的人排除在“国学”范围之外时,对他们与“国学”相关的复杂心态自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第8章)。另一方面,以西学为蓝本的新学术在中国的成长发展历程中又时时与“国学”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当然也包括相互竞争,导致我们今日学术研究中产生相当一些“中国特色”,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现象。)。
二、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
蒙先生在论及二千多年来孔子在中国社会的尊崇地位时说,在“这二千多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剧烈”。从汉代到清代,学派相当歧异,“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人,所认识的孔子各不相同”。然而他们“却都各认为自己所讲的才得孔子之真”。只有“摆脱一切学派的圈子”,从历史的变化上“寻根溯源,区别出一切学派系统,结合时代深入探讨”,特别注重“在某一时期,什么样人排斥孔子,又是什么样人推尊孔子”,才有助于“对孔子的理解”。这样“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学术演变上来看孔子”,也才可能“真正正确估价孔子”[13](157页)。
这一观念大致可见“古史辨”的影响。《古史辨》第一册刚出来,傅斯年就看到,梳理历史表述的演变,不仅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被表述者的真相,还可从怎样表述及何以如此表述中看到关于表述者本身的历史“真相”(注:关于“古史辨”在这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和影响,我将另文探讨。);所以他建议顾颉刚研究历代孔子形象这一“观念”的演变过程,以成“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并借此了解历代立言者的心态,即“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 Complexes)”[15](448-449页)。顾颉刚对此心领神会,他在1926年收信后即提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16]
故蒙先生关于各学派“所认识的孔子各不相同”并非新说,但他进而有意识地考察特定时期“什么样人排斥孔子,又是什么样人推尊孔子”,便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提升了从作品外认识作者的取向。傅斯年留学期间的笔记中有一条论及汉代经学,认为当时经学的“家法之争,既是饭碗问题,又涉政治”,也体现了类似的思路(注:傅斯年留学期间(1919—1926年)笔记,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Ⅰ:433。承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谨此致谢。)。钱锺书曾据“孔子言道亦有‘命’”之说指出:道之“昌明湮晦,莫非事与迹”[17],无意中也提示着从“哲学思想”之外观察的取径。他们的看法与蒙先生相类,大体皆可说源自孟子的“论世知人”法。
章太炎在清季观察到,一些国人初因己国学问不能退虏、送穷而贱视之,以为不足道;后见外国也有欣赏中国学术者,遂转而以为本国学说可贵。他针对这一现象指出:“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注:按本书是陈平原先生据泰东书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斟酌损益而编成的。)[18]这当然是所谓“学者”应有的基本立场,即学问的价值不因其社会受众的一时多寡而定。但反过来看,任何学说、思想都处于具体的社会之中,某种学说在特定时空之内的社会反响,其是否及怎样为社会(或学界本身)所重或所轻,同样表现出与此学问直接相关的消息。
顾颉刚便认为,把读书人“历来各派冲突的话记出,也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他曾有意就此做一部“文人相非考”(注:参见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368页。)。可惜顾先生太忙,而他想做的事又太多,此文终无暇做出,否则“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当更上层楼。实际上,“古史辨”学派的一个弱点,可能就是轻视了他们中一些人已隐约意识到的从社会视角考察学术的取径;致使他们在疑古之时,常常忽略古代学术的产生方式这一社会背景,而聚讼于某书是否为某人某时所作。
傅斯年较早就提醒顾颉刚,辨古史当注重“古书”。他说:“例如《论语》一部书,自然是一个‘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几百年‘累层地’造成的”。而“《诗》的作年,恐怕要分开一篇一篇的考定,因为现在的‘定本’,样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改变,而字句之中经流传而成改变,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他进而向顾颉刚建议:“我们研究秦前问题,只能以书为单位,不能以人为单位。”[15](462、472页)[19]
到1930年,傅斯年又写出《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提出“我们切不可以后来人著书之观念论战国文籍”,因为战国时“‘著作者’之观念不明了”,且当时“记言书多不是说者自写,所托只是有远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罢了”。故“战国书除《吕览》外,都只是些篇,没有成部的书。战国书之成部,是汉朝人集合的”。次年,罗根泽发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长文,也申论“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王汎森先生认为,“以上两篇文章标志着疑古辨伪方向之转变”,信然(注:傅斯年文初刊于史语所集刊,罗根泽文收入他自己编的《古史辨》第四册,均引在王汎森文中,参见王汎森:《对〈文史通义·言公〉篇的新认识》,收入《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5年(印刷中)。)。
大约同时,“伪书”的形成及其与辨伪的关系也引起学者的关注。陈寅恪以为:“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实际上,古书之真伪“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20]。
以辨伪著称的顾颉刚此时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他在《古史辨》三册自序中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很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故“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辨伪不过是把所辨之书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顾先生以为,要这样处理一般视为“伪的材料”,才算是具有“历史的观念”[21]。
蒙先生更明言,“必皆先有伪书之学,而后有伪学之书”。作伪有其原因,且也像古书形成一样有个过程,非一人所能为。他具体指出:“王肃好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所为经注,异于郑氏,虑不胜,然后有《孔子家语》、《尚书·孔传》之伪,有《论语、孝经·孔传》、《孔丛子》之伪。汲冢出书而《纪年》、《周书》皆被改窜,则伪之非一人一时所能为,所由作伪者又以郑、王两学相争之故,故书虽伪而义仍有据,事必有本,凡此作伪,皆南学之徒为之,实为王学而作伪。校郑、王两派异同,足知伪书之伪安在,其不伪者又安在。《纪年》、《周书》伪而所据以作伪之材料不必伪。”[22]
而且,作伪也有家派之分,“有一家之学,然后有一家伪作之书”;故辨伪应知求其“学派所据”,辨明“作伪者属于何学、果为何事,一书之间孰为伪、孰为不伪”,而不当“以作伪二字抹杀古代之书”[22]。把“伪书”提高到“伪学”产物的层次,则对“作伪”这一社会进程及其思想学术背景就有远更深入的认识。如果伪书“所据以作伪之材料不必伪”,则里面“真材料”的价值就不仅可以“移置”回其产生的时代,它也很可能是所依托之时代的真产物,还要依据其他材料以辨析确认之。
这样对“伪书”和“伪学”的多层次认识,是许多龂龂于辨析某书是否为某人某时所作者迄今忽视的真知灼见。章学诚已说过,“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下焉者“泥迹以求之”,故“窒于心而无所入,穷于辨而无所出”;高明之人则“不滞于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23](辨似,74页)。蒙先生即主张,有时史无明文也未必实无其事,当从蛛丝马迹寻觅,以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他举例说:“汉行均田无明文,可能因王莽的‘王田’制度与之相似,且也行得不彻底,故不见记载。晋虽也行得不彻底,但因唐行均田,故修《晋书》时特载其事。汉虽无明文,但也不无蛛丝马迹,不能因史无明文遂以实无其事。如这样,历史就被割断了。”[5](29页)
一般而言,如蒙先生所说,“时代稍后的历史记载可信的成份就减少了一些,最初的史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24]。但也不尽然,有时则要看后出之史料所具有的特性而定。如傅斯年、蒙文通等都指出《吕氏春秋》是可以考定的战国“著述”,过去多以其为编纂之“杂书”而轻视之,其实后出杂书的好处正在于所记广泛,蒙先生便据其中的记载以证明《楚辞》、《山海经》等原以为荒诞不经的材料之可靠性(注:散见于蒙先生论证上古文化三系的众多论著中,后面还会述及。)。则以唐代后出之制度而论证晋代,进而考论汉代,同样充分体现出:只要史家善于运用,后出史料也可转证前事。
三、因事证明:制度和理论
考察思想、学术不仅要细绎其义理,也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史事中得启发,关键还是要落实在是否实有其“事”之上。过去研究周秦思想,每从义理入手,言人人殊,难以依据;但许多古事却可考定,由史事而反观诸子之言,可对理解各家义理有进一步的认识。
蒙先生曾自述其“撰《经学抉原》,专推明六艺之归,惟鲁学得其正。又成《天问本事》,亦可以窥楚学之大凡也。兹重订《古史甄微》,则晋人言学旨趣所在,亦庶乎可以推征”。三篇循环相通,然还只是基础性的工作,盖“《经学抉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此皆学问之粗迹。制与事既明,则将进而究于义,以闸道术之精微;考三方思想之异同交午,而衡其得失”[25]。他在河南时,便“比辑秦制,凡数万言,始恍然于秦之为秦,然后知法家之说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孔孟之说为空言,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这就足以看出秦、汉之际的儒生已是与孔孟有别之“新儒家”,终梳理出“战国以来诸子学术发展之总结”(注:这方面具体的论述见蒙文通:《古学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经史抉原·孔子和今文学》。)[5](4页)。
这本是近代蜀学的传统,蒙先生一再强调,他的老师廖平最擅长据礼制以“权衡家法、辨析汉师同异”;并“确定今古两学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为纲,而今文各家之说悉有统宗;以《周官》为纲,而古文各家莫不符同”。许多聚讼经今古文学而辨析不清者,多因其“不探两汉今古文之内容而专事近代今古家之空说”。其实“究空说则今古若有坚固不破之界限,寻实义则今古乃学术中之假名”(注:蒙文通:《经学抉原·附:议蜀学》、《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廖季平先生传》,均收入《经史抉原》,101—145页,引文在119、120、114页。)。
蒙先生则通过区分“经”、“史”来处理周秦之间的制度和空言,即“有周之旧典焉,所谓史学者也,有秦以来儒者之理想焉,所谓经学者,实哲学也”。故“不以行实考空言,则无以见深切著明之效,既见秦制之所以异于周,遂亦了然于今学之所以异于古”。而汉儒口中的“《春秋》‘一王大法’”又不同:“《春秋》师说者,一王之空言,《礼》家师说者,《春秋》之行实也”,故“所谓‘《春秋》经世’、‘为汉制作’者,正以鉴于周、秦之败,而别起‘素王’之制,为一代理想之法。不以《礼》家之说考《春秋》,诚不免于‘非常可怪’之论,不以周、秦之史校论‘一王大法’,则此‘非常异义’者,又安见其精深宏美之所存”[26](189-190页)!
盖“有素朴之三代,史迹也;有蔚焕之三代,理想也。以理想为行实,则轻信;等史迹于设论,则妄疑”[26](165页)。蒙先生后又以白话重申其意说:“汉代经学虽然是继承先秦儒家(和诸子)而来,但其学术思想的侧重点则各不同:先秦重在理论,汉代详于制度。只有理论而没有制度,理论就是空谈;只有制度而没有理论,制度就会失去意义。故理论和制度必须综合起来研究,而后才能认识其思想全貌。”[13](213页)
这是蒙先生治学方式中的一个基本取向,在他20世纪30年代末所作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及50年代末所作的《孔子和今文学》中,皆通过条举分析汉代经师对井田、辟雍、封禅、巡狩和明堂五种制度的不同叙述,以清理出“哪些制度是历史的陈迹,哪些制度是寄寓的理想”(注:参见蒙文通:《古学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177—188页;《经史抉原·孔子与今文学》,177—199页,引文在176页。)。在《古史甄微·自序》中,蒙先生为证明“儒家言外,显有异家之史存于其间”,以《孟子》书中的十四件古事(后又增论一事)为例,列举了齐鲁、三晋、楚三系对同一史事的不同说法,以见“三方史说互异”,而“北人所传近真”。结论是“孟子所称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责者翻若可信”[25]。他指导其堂弟蒙季甫研究古代礼制,也是让其看书时将各书对“同一问题所据不同经文和各家异说都分别条列出来”[27]。
司马迁曾引孔子之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此语过去常被引用,然多未论及“空言”和“行事”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蒙先生则以战国秦汉间思想和制度的具体例证落实了“空言”与“行事”的指谓,并揭示和说明了两者的互动互补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要素,叶德辉就很赞赏《左传》的作者“于圣人笔削褒贬之心可以因事证明,得其微旨”[28]。若以广义的往昔立言者取代特定的“圣人”,这里正有方法论的启示:只有对往昔之人、事以实证方式“因事证明”,然后可解悟立言者之“微旨”。
四、内外解读:文本和语境
其实“行事”也是多层面的,立言本身是“行事”,因何立言及怎样立言也是“行事”。思想史自当以表述“思想”的文献为基本素材(在精英起主导作用的时代和地域,更当凸显经典文献的重要性),离此便难说是思想史。学术史亦然;学人之间的往还及其相互的评议、学术的著述形式和出版方式、学术怎样传承、学派的得势与式微、与学术相关的经济因素、以及更广阔的学术与社会的互动等面相都非常重要,都是过去相对忽视而今后可努力探索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同样重要,不过向来较受重视),但表述出的“学术”本身仍是不可须臾疏离的主体。
故思想史和学术史自当侧重具体的思想、学术文本(text),循其言说的内在理路以探索立言者之所欲言。其实也可稍广义地将具体史事皆视为文本,而特定文本前后左右之书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即构成语境(context)。有时专就文本看文本,可能出现偏差;若转而从语境方面着手,语境明则文本的理解也会更容易(注:关于文本和语境的互动关系,西人所论甚多,窃以为从史学的角度讲得最好的,还是剑桥大学的Quentin Skinner。其主要相关论述均收在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29]他可以接受不甚顾及文本作者及其时代而就文本论文本的“说梦”取向,然自己大致还遵循着孟子的思路,重要的是他特别提请文本诠释的接受者明白两种取向的不同。
清人恽敬批评汉儒说:他们“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结果其所立之说“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实未必理解圣贤真意[30]。这番话自有其特定的尊圣立场,我们可以不置论。但恽氏在这里提出的察凡庶(注:主张取法乎上的中国文化的精英意识一向甚重,但同时圣贤之道又无不融汇于人生日用之中,故恽敬能意识到察凡庶可以知圣贤的路径。20世纪下半叶西方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史学(history from below)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一乾嘉时代的主张暗合,不过其目的未必是了解上层。)、赴时势、考通方等几种取向,都是今日治史学者应该参考的。尤其关于立说不仅要推之一家一经而通、必须要推之众家众经皆通的主张,正是前后左右读书法的另一表述,与西人的文本语境说亦颇相通。
后来美国文化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论文本解读,以为旧式的诠释是想要知道文本的意谓(ask the text what it means),而新的分析则要了解其怎样起作用(ask how it works)[31]。詹明信1985年曾在北大讲学,并出版轰动一时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在该书的《台湾版序》中,他又论及怎样分析“理论”,主张“不仅是理解理论,衡量其真理性与启发意义,而且同时思考作为症状的用途所在”。也就是“同时坚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待理论文本,……一是内层解读,这正像旧式哲学一样,目标是发现并建立其内在的创新和效验;一是外层解读,视其为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外在标志或症状”[32]。
这样的内外解读法与蒙先生所云颇有近似之处,我们当然不必循晚清“西学源出中国说”的思路,说蒙先生已开西方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先路(毕竟双方有许多大不相同的讲究)。实际上,从社会视角观察和探索历史上的思想、知识、学术在西方已渐成风气,许多具体研究与“后学”并无直接关联,而更近于所谓“新文化史”(注:关于西方的“新文化史”,可参阅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Peter Burke,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尽管后者的范围不止于“新文化史”,其中不少内容实际构成对前者的补充。当然,“新文化史”似乎愈来愈体现出其与“后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参见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lutur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从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的发展看,思想史的社会取向可以说已成“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注:参见Robert Darnton,"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in idem,The Kiss of Lamourette: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Norton,1990,pp.219—52;Fritz K.Ringer,"The Intellectual Field,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Theory and Society,vol.19(1990),pp.269—94.柏克(Peter Burke)近年关于16—18世纪“知识”的“社会史”颇可参考(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0,此书已有中译本:《知识社会史》,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尽管其讨论的“知识”不全是我们思想史通常处理的“思想”,倒有些接近梁启超和钱穆那两本《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的“学术”。)。
对中国大陆史学界年龄稍大之人而言,詹明信的表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另一段耳熟能详的话:“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33]詹明信是名副其实的左派,熟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论他的内外解读法是否与恩格斯这一具体见解相关联,他的整体思想的确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
过去我们多将恩格斯上面的话运用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若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广到思想史研究上,或可以说,不仅要认真研读文本的内容,还要注重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和语境的互动,更要具体考察文本在其时代语境中起了什么作用及其怎样起作用。后者可以揭示一些仅仅研读精典文本之“哲学思想”未必能够获得的消息,这些消息反过来又有助于理解文本所反映的时代“思想”。经过这样的考察,对于文本意谓的领悟或许会比单纯研读文本更进一层。
既然文本和语境互通也互动,有时转换视角跳出文本之外,则片言即可获殊解。蒙先生自述其“从前本搞经学”,1923年自西蜀南走吴越,“期观同光以来经学之流变”;到了江南始知那里的“故老潜遁”,在经学“讲贯奚由”的情形下,乃改“从宜黄欧阳大师问成唯识义以归”[34]。可知在那时原为经学大本营的江南,经学之正统已衰落,佛学等异军正突起。但这一论域的转变尚未完全传到经学仍潜居主流的巴蜀,颇具“礼失求诸野”的意味;而蜀地饱学之士并不了解江浙的变化,其认知中的经学重镇仍在吴越之地,并对其寄予厚望。这样的重大学术转向,自然也可沿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去探寻;然蒙先生求学的例子说明,文本之外同样可见学术之走向。
对史学来说,这一研究取向还有更切实的一面。以蒙先生所说的老子、孔子之学为例,既存史料总是有限的,除少数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如新出土前人少见的史料)外,任何人研究孔、老思想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是相同的,然视角的转换常可以“盘活”许多原不为人所重的史料,史学的理解也就更进一层。如孔子曾自称“述而不作”,盖其视“作”极高,或以为没有根本突破性的大创造不可言“作”。其言婉转,然谦退中也有几分自负:他虽未必算已“作”,至少也有所“述”(注:许多学者迄今还在考证和争论孔子是否编定或写定“六经”,若我们采信他老人家的“夫子自道”,则其进行了某种类似的工作,或大致可立。)。
进而言之,“述而不作”一语的是否采信,直接牵涉到也提示出另一个大问题:孔子所处的时代究竟是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还是思想典范基本维持其既有功能的小变动时代?康有为已思及此,他干脆认为此条内容经刘歆篡改,说孔子删《诗》《书》、作《春秋》等皆“受命改制,实为创作新王教主”。康氏并引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以证孔子“何尝以述者自命”。然而,反方向的解读者同样可引孔子说“予欲无言”来支持他确实“述而不作”。故若专在文本的“哲学思想”上做文章,有时而穷,不如转向“社会”层面去考察。
章学诚便大致从此看,他引孟子“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的话,证明“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若一言以“蔽孔子之全体”,则“学周公而已矣”。盖“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故“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注:章氏并从祭祀制度考察,指出“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这一从学术之外的制度观察思想和学术演变的创意,实在值得后人效仿。)[23](原道上,36-38页)。章氏进而从学术传承方式一面申论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故“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23](诗教上,18-19页)。
对于讨论古代思想谱系都要述及的《庄子·天下篇》,章学诚就特别强调孔子与诸子在意识层面“态度”的大不同:前者自称“述而不作”,后者则“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他据儒家的立场说:“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23](原道中,40页)且不论周公所传之“道”是否已“易”,章氏至少观察到“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的社会现象,由此视角看,时代思想观念确已有所更易了。
一般而言,要既存思想典范仍能起作用并在起作用,才可述而不必言作。薛瑄说朱子的历史作用,以为“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注:薛瑄语引在胡适1923年4月3日的日记,见《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册,7页。当然,从清季革命党人开始,就有人将“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解释为朝廷以尊朱学来限制或“控制”士人思想的举措,虽不无所见,至少未必皆如此。),便很能说明这个意思。若从这方面理解,只要采信“述而不作”一语,则孔子之时“道”也不能说不明;于是孔子非教主,乃传教士,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康有为想做的“路德”,尚可推敲(故康氏不能不从根本上否认“述而不作”)。到庄子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而诸子“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时,便是典范转移的明证。有关这方面的名家名论已多,然依蒙先生所说侧重观察思想风行之原因及其所起的作用,似还可续有新知。
思想如此,学术亦然。如“考据”是否可以算一种“学”,自“考据学”名称兴起的乾嘉之时,便有争议。焦循曾力辩说考据根本不能名学,然他注意到“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自惠栋、戴震以下,“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35]。其余袁枚、孙星衍等,也各从学理上界定何为“考据”。若转从社会视角看,既然有这许多学者对“考据之名目”聚讼不休,尤其著书授受者已不下数十家,这些人也多自名其所治为“考据学”,则以时人眼光言,考据确呈独立成“学”之势(注:说详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
实则考据更多是一种治学方法,乾嘉人就“考据学”这一学术门类是否成立进行辩论,提示着一种新因素的产生:尽管中国传统不甚讲究学科分类,但也存在不少以“某某学”称谓的名目(多为大体言之,分界不甚严密)。历来学者对这类称谓皆以其所治对象名之,今则以相对抽象的治学方式方法名之,显然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即某种带有广泛适应性的“方法”从各具体的学术类别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学”(虽然还有个确立的过程)。这一转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还可以深入探索(注:此时的“考据”可以成“学”,很可能是20世纪初年那一股“方法热”的远因(按清季学制改革时,部分或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那时的发凡起例者都特别注重“方法”,其课程设置中似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方法热”)。而乾嘉人似并未意识到或至少未能充分意识到这里所牵涉到的治学内容和方法的差别,也缺乏相关的论证,故“考据学”这一学术门类是否成立,后来仍有进一步的辩论,一直延续到民国,详另文。)。
外篇:前后左右则史无定向(注:外篇的基本意思已见于《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开放时代》2003年5期)一文,大致是在该文一些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特此说明。)
上面所言思想史的社会视角,核心是要厘清思想学术的时代精神和学脉渊源,其基本立意是要开拓而非限制对史料的采用,以增进对史事的认识。不论是侧重文本还是兼顾语境,不论是内层解读还是外层解读,都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取向;探索的途径愈多,则愈可能广泛深入地理解往昔。进而言之,前后左右治史的取向,既渊源于重广博而尊通识的传统学风,也与近年颇受提倡的“跨学科”主张相通。
本文开头说到,民初关于博览的论述已近于今日所谓“跨学科”的含义。的确,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常可听见类似“跨学科研究”的主张(注:如章太炎在1902年即说,“心理、社会、宗教各论”,皆能“发明天则”,故“于作史尤为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31页。此后类似的表述不绝于耳,海峡对岸通常将这一取向称为“科际整合”,近年热情似已较大陆稍减,发展情形也不甚同,本文所论主要为大陆的现象。),这可能提示着某种“学族”意识的存在。从社会视角看,特定学科的“独立意识”多也带有一定的排他性。今日史学各子学科的畛域尚较明显,各专门史的区分甚至较前更受关注,不时可见关于“什么是某某史”这类论题的持续辨析,其实就是希望划出或进一步划清学科的“边界”(注:这类正名努力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史,各种相关看法可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18页。)。
各专门史的划分是否当依据其研究对象而定?这样宽泛的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或可以说,史学各子学科已存在相当一段时期,自有其功用甚或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也当注意,这些“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为强化的。根本是史学本身和治史取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藩篱(注: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前几年关于“脚注”的专书(The 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视野颇开阔,按我们所谓专门史的划分便较难“归类”,却是一本得到广泛认可的佳作。)。尤其要避免刘勰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文心雕龙·知音》)之见,切勿因学科的划分限制了对史料的采用。
边界明晰的学族认同原非治史的先决条件,根本言之,史学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科。我倒倾向于相对宽泛的从各种方向或角度看问题,而不必管它是否属于某种专门史——思想、学术问题可以从社会视角看(即所谓social-oriented approach),政治、外交问题可以从文化视角看(cultural-oriented approach),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必须固定从一个方向看。《淮南子·泛论训》说:“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此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
“无所不通”的高远境界或不适应今日急功近利的世风(注:如今学问的程度当下就要证明给人看,以学术为“职业”者都必须面对特定时间之内的升等问题,要向年轻人提倡厚积薄发的高远取向,真是难以启齿,恐怕也只有如陈寅恪所说的“随顺世缘”而已。),且既存知识的范围也太广泛,非“生而知之”者大概只能有所专而后可言精(注:如严耕望所说,“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当然,他也不忘指出,专精必须与博通相结合;“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严耕望:《治史三书》,7页。)。若不计“治学精神”而仅就“治史方法”言,治史者固不妨有其专攻,倘能不忘还有其他看问题的视角可以选择,境界亦自不同。钱锺书也认为:“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17](266页)正与蒙先生所说的“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相类,大致皆发挥孟子论世以知人的主张,提倡开放视野,以超越于就思想看思想的惯性思路。
其实历代思想精英的表述不必皆是经典性的“思想表述”,而社会视角也未必要求什么特定的“社会”史料——上面引述的内容率皆出自精英之口,同样告诉我们不少有关“社会”的消息。正如夏悌埃(Roger Chartier)所说,“对社会世界的表述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什么外在于“社会”的因素(注:他的原话是"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cial world themselves are the constituents of social reality."出自其1982年的论文"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The French Trajectories,"转引自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in idem,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p.7。几年后夏悌埃在界定其所用“文化”一词的定义时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见解,参见Roger Chartier,"Introduction",in his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trans.by Lydia G.Cochran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11.)。丹屯(Robert Darnton)也指出,印刷出的文献常被史家视为所发生史事的“记录”,实则它们本身就是“正在发生的史事之组成部分”[36]。既然思想和学术(作品)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则精英表述虽未必皆经典,亦未必非“社会”(注:探讨“社会”和“社会史”的涵义是近年大陆学界一个“热点”,历年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中皆常见为“社会史”正名的论文(参见前引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3—218页)。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只有运用某种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会史”,否则便只能算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史学;即使是后者,也渐已形成某种众皆认可的认知,即应该以社群(通常隐约带有大众化的或反精英的意味)和特定范围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不少读者受此影响,对“社会史”已具有某种预设性的期待,未见其所预期的内容便感觉未曾看到“社会”。而西方的走向似更复杂,其“新史学”的自下而上取向与所谓“语言学转向”大致同时而暗相牴牾,盖“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正在于“文本”之上,很容易偏重于上层精英文本,有意无意间可能导致对平民大众的忽视(参见William H.Sewell,Jr.,"Whatever Happened to the'Social'in Social History,"in Joan W.Scott and Debra Keates,eds,Schools of Thought:Twenty-Five Years of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209—226)。这一牴牾很可能是侧重精英文本的思想史在西方衰落的一个原因,故当辅之以从社会视角观察思想的“外层解读”取向,而前引恽敬提出的通过察凡庶以知圣贤的路径更提示出一种“上下通”且互不排斥的思路。)。
说到底,今日能见的史料都不过是往昔思想脉络的片段遗存,在此意义上厚重的文本和只言片语基本同质。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这是《庄子·天运》中所言,义甚悠远:一方面,既然先王之陈迹未必是其“所以迹”,则后现代文论所谓文本的独立生命似亦可由此索解;鲁迅之不排斥“说梦”的取向,而希望读者知其所读为“说梦”,或即从此考虑。更重要的是,要理解领会六经之文本,便当往“所以迹”的方向努力探索“履之所出”的一面,多少还是接近“论世”的意思。
在司马迁的记载里,老子这样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37]此语或本《庄子》,而意有所移(按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虽亲近今人所谓道家一脉,他自己却比其父更“尊孔”而近儒)。从史学角度言,司马迁的态度更积极。其意或谓言在,固未必非人在不可也(这里的“言”不必一定落实在文字之上,任何人造物体皆能反映也实际反映了制造者的思想,亦皆其言也)。治史者在深究前人所遗之“言”时,倘能尽量再现立言者之“人与骨”及其周围环境,则其理解必更进一层。
章学诚没有那么乐观,他也认为“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但很多时候“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古人“有其忧与其志”,要使其不至于“湮没不章”,就要能“忧其忧、志其志”[23](知难,126-127页)。故他把孟子的论世知人说提高到“文德”的程度,强调“临文必敬”和“论古必恕”两种基本态度。章氏特别解释后者说,“恕非宽容之谓”,是指“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即“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60页。英国史家柯林武德也特别提倡与昔人“心通意会”的治史取向,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242—250页。关于柯林武德与中国历史思想特别是章学诚思想的相通之处,参见余英时:《章实斋和柯灵乌的历史思想》,收入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167—221页。)。
的确,若不论世知人,很容易“接以迹而不能接其心”,态度稍不恕,无意中可能曲解前人之心。王充据孟子所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提出,孔子作《春秋》,不过“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但当时《公羊》、《谷梁》二传的“俗儒”,则傅会出不少新奇的解释,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其实都“非孔子之心”[38]。在王充看来,这些汉代“俗儒”本意或尊经,实可能“非圣”;皆因其将文本虚悬而深究,致出现后人所说的“过解”(over-interpretation)。不幸类似倾向今仍存在:
南宋绍兴年间,朝廷拟推行经界法以均平赋役,遭到各地反对,据说以四川最甚。前往四川调查的王之望后上奏说:在东南一带,确传闻“蜀中经界大为民害”,但川内则“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经界,与峡外所闻不同”。盖“蜀人之至东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则公吏与富民尔。其贫乏之徒,固不能远适;虽至峡外,亦无缘与士大夫接。故不愿者之说独闻,其愿行者,东南不得而知也”[39]。何忠礼先生据此说:“这份奏疏深刻地揭露了一个事实,即历史记载可能充满着假象。”[40]
应该说,当时在川与旅外的不同身份的川人各自表述的对立见解,皆其自身对经界法的切实感受,正是真相而非“假象”,不过均非全面,不能代表“全体川人”而已(注: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几百年后另一时段旅外川人与在籍川人对时事见解的异同,可以参看。)。所谓“深刻揭露”、“充满假象”等,更多是后之治史者自身的过度诠释,乃使“径直之文”生出“曲折之义”!稍具诡论意味的是,这样一种“过解”却是出于辨析史料的谨慎意图,隐约可见疑古辨伪风气的影响,致使动机和目的之间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史家操术,得勿慎乎!
主张“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的梁启超曾说,“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41]。这里所谓“历史”,实指史学。他显然是遵循司马迁的积极取向,认为只要有“巧妙之技术”,就可以再现“过去人类之活动”。我们今日可能没有梁先生那么乐观,但其所说的“再现”确体现了不同时代对史家的不同要求。
在一个学术社会化的时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老话有了新的社会含义:今日治史者不仅要自己能“知”,还不能不“再现”给人看。故不仅在研究时要从研究对象的前后左右去论世以知人和事,期能将其前后左右的史事关联熟烂于胸;在表述时恐怕也要有意识地将被表述者始终置于其前后左右的语境之中,使“陈迹”透出其“所以迹”,庶几接近“再现”之境界。
蒙文通先生治学气象博大,在众多方面提倡和实践了不少治史取向,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不过是其中之一。我在1994年返母校四川大学任教,承蒙默老师赐赠《蒙文通学记》和《蒙文通文集》第1卷(即《古学甄微》)各一册,即常置案边,启迪良多。蒙先生《文集》后几册出版,也曾购而学之,每读皆深感“开卷有益”。然我的浅陋理解是否符合蒙先生原意,实未可知。适逢母校纪念蒙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谨以此读书札记就教于方家。
标签:国学论文; 傅斯年论文; 儒家论文; 读书论文; 思想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孔子论文; 墨子论文; 古史辨论文; 顾颉刚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