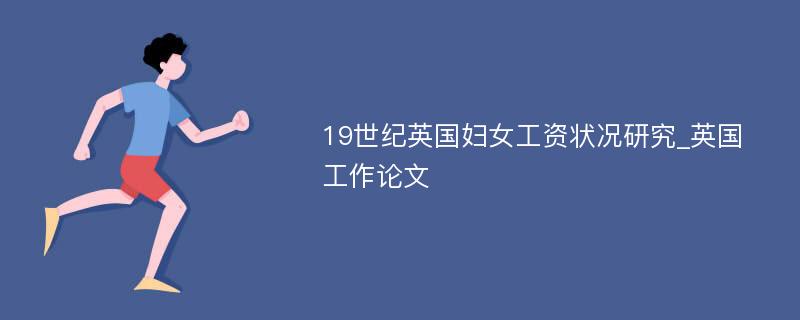
19世纪英国妇女工资状况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妇女论文,状况论文,工资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74(2005)06-0034-07
19世纪英国劳动妇女的工资状况直接影响到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关系到对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评价,以及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总体评价。该问题受到从事英国经济史、社会史、妇女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关注。尽管妇女雇佣劳动状况往往没有完整地登记在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国内学者较少涉及此问题的研究,但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正确处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两性关系,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具有借鉴作用。
一、妇女的工资状况
在19世纪英国现代化进程中,妇女迅速被边缘化,大部分人就业于家内或家内劳动的延伸部分,属于非熟练的、报酬低的行业。1851年,80%的劳动妇女就业于纺织业、成衣业、家内服务业等行业。其中,家内仆役占妇女从业人数的40%。一般来说,与男性群体相比较,大多数妇女长期处于低工资状态,而且更容易受物价波动和劳动时间不足影响。妇女的工资水平在不同的行业、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对女工人数较多的几大行业女工工资状况作一整体考察。
纺织行业是19世纪英国的第二大女性职业。该行业的妇女只能在梳、织等脏、累、低技术、低工资的部门工作。即使与男性就业于同一工作部门,妇女往往做辅助性工作,或是在男工监督下保证机器满负荷运转。几乎所有的熟练工种,女性都受到排斥。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般妇女的工资是男性工资的1/3至1/2,最高的也只是男性的2/3。[1] (P.25)1834年兰开夏成年女工的工资大约是男工的40%左右(见表1)。
表1 1834年兰开夏成年女工与男工的工资[2] (P.251)
男性 女性
年龄
人数
周平均工资
人数
周平均工资
16-21岁 736
10先令2又1/2便士 1240
7先令1/2便士
21-26
612
17先令2又1/2便士
780
8先令5便士
26-31
355
20先令4又1/2便士
295
8先令7又1/2便士
31-36
215
22先令8又1/2便士
100
8先令9又1/2便士
36-41
168
21先令7又3/4便士
81
9先令8又3/4便士
41-46
98
20先令3又1/2便士
38
9先令3又1/2便士
46-51
83
16先令7又1/4便士
23
8先令10便士
另据1859年一个棉纺织厂的情况:该厂女工占74%,男工的平均周工资是18先令6便士,女工是10先令2便士。[2] (P.250,251)
“血汗行业”指缝纫、针织等手工劳动部门,也是女性就业数量较大行业之一。在“血汗行业”就业的女工工资低于工厂制女工。如19世纪30~50年代伦敦的成衣业中,年轻的女裁缝每年收入约12~20英镑。一个年轻的女日工,每周工资收入约7先令,一年只有7~8个月时间能工作。做裤子女工每周净收入是4先令5便士,而衬衫工每周净收入只有2先令3便士。[1] (P.47)到1901年,14,910名成衣业女工中,最高周工资是18先令1/2便士,最低工资是2先令4.5个便士。[3] (P.29)
家内服务业是女性就业人数最多的工作部门。家内服务业女工分长期受雇用的女佣和临时性钟点工。两者主要从事烧、洗、清洁室内,洗烫衣服、照看孩子等家务劳动。男仆主要从事户外工作,如修理花园,赶马车、马夫等,有些人充当男主人的随从。与男仆相比,女佣的工资很低,大部分人年薪在8~20镑之间。[4] (P.147)一个男仆,如果他主要的工作是在餐桌旁侍候主人,他就可以拿到衣服、小费等额外收入,而且年薪一般在50英镑。而一个烹饪女工,需要一定的技能,年收入却不超过20英镑。[5] (P.177)许多女佣,她们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1862年《爱丁堡评论》报道:“400,000名侍女,年工资几乎没有人超过10英镑,许多人不超过8英镑,而当时一个女孩最普通、经济的服装化费,农村地区年平均是6英镑,城镇地区是7英镑,女佣几乎没有剩余的钱可以与家人共享。”[6] (P.176)
由于19世纪大量新农具、新耕作方法的发明应用,如饲养家畜的新方法、新农机与化肥的使用使妇女失去了受雇用的机会,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被边缘化,成为季节性工人。她们的工资处于低水平状态。妇女史学家伊维·品契贝克统计,19世纪,农业女工的平均日工资为:西南各郡,冬季5~8便士,春夏两季7~10便士,晒草和收割季节8便士至1先令,外加一、二品脱的苹果汁。其他地区略高一些,如肯特、萨里、苏塞克斯等地,妇女干大田普通农活是8~10便士,晒草10便士至1先令,收割1先令3便士至1先令6便士;在约克郡,收割季节中,女日工的工资有时能达到1先令6便士。[7] (P.95)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农业女工处于无业状态。1843年“农业地区妇女儿童雇用委员会”声称“农业女工是最低收入的群体”。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白领革命”,职员人数大量增加,1851~1911年,职员人数从95,000人增加到843,000人,他们在整个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2%上升到4.6%,女职员从2%增加到20%。[8] (P.154)但从总体上看,女职员主要集中在诸如打字员、电报员、话务员、分类、检查数据等知识、技能含量较低的工作部门。与其他行业一样,女职员的工资只是男职员的25~50%。据史学家艾伦统计,男职员年收入达180镑、215镑或350镑不等,而女职员的收入从未达到过同样的水平。1891年,200名就业于商业部门的女职员,其中只有17人在工作的第四年年薪达60镑以上,工资最高的女职员年薪也只有90镑,男职员在20多岁时,工资就可自动上升到150镑。[9] (P.74,75)即使男女职员从事同一工作,男性的工资也高于女性。在罗伯特的小说中有这么一段对话:男职员罗伯对女职员尼尔说:“很惭愧,很惭愧,你工作比我辛苦,比我好,你的工作时间比我长,而你的工资只是我的一半,为什么?尼尔。”尼尔说:“因为我是个女孩子。”[8] (P.162)邮电系统是当时职员人数最多的工作部门,19世纪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玛琳·荷尔梅斯(Marion Holmes)提供当时该部门性别工资状况:较低级别二级男职员,年薪是70~250英镑,较低级别二级女职员,年薪只有65~110英镑,高级别二级男职员,年薪250~350英镑,一级女职员,只有115~140英镑。[10] (P.4)
上述可见,19世纪英国劳动妇女走出家庭,作为独立的工资劳动者走向劳工市场,她们就业于低技术、低工资部门。大量妇女因而不能养活自己,不得不把结婚当作逃避失业,维持生计的途径。贫穷的女孩子可以接受任何条件的婚姻,甚至非法婚姻。因为对于她们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母亲鼓励女儿结婚,以减轻家庭负担。许多教区官员为了推卸本教区的救济责任,强迫妇女结婚,但又禁止本教区的男人与有麻烦的妇女结婚。
一般的劳工家庭把女孩子看成是家庭的负担。1892年,吉夫里丝(jeffries)写道:“如果一个农妇生了个儿子她会很高兴,这不是说她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男人,而是感谢他不是女孩子……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农妇说她宁可要七个男孩也不要一个女孩子,因为前者能成为小伙子,出去挣钱养活自己,但是女孩子你永远都不知道她何时能自立……女孩每一天都感觉到身为女孩是一种错。”[11] (P.32)这样,男性构成了工业社会的主体,甚至有学者认为性别分工、性别歧视在工业化中加强了。
二、妇女低工资原因分析
为何存在性别分工和性别工资?有些学者认为,妇女天生体力弱、怀孕等因素使她们的工作时间低于一般男性,从而影响了家庭、社会对她们的人力资源投资。而男性则通过多种途径比女性接受较多的技术训练,掌握更好的技能。因此,妇女的就业和工资都处于弱势。另一些学者认为妇女天生能力不如男性,她只能享受低工资待遇。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女性主义学者都认为妇女作为廉价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是现代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笔者认为,妇女低工资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就19世纪而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是英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分工、性别工资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英国社会认为男性的骄傲、自尊意味着勇敢、强壮、独立,而女性的骄傲和自尊则是纯洁、守家和母性。因此,“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模式最能体现男女各自的性别特点,妇女当好全职太太,男人外出挣钱是最好的家庭角色分工。对于妇女来说,做好家务工作,给丈夫带来快乐,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是她们最大的责任。舒适的家庭可以阻止男人酗酒,让全家得到更好的物质享受。否则,男人干家务会使他们变成没有男性气质的人,家庭会陷入混乱。议会调查员威廉姆·都德(William Dodd)在1842年写道:“这是可悲的,男人照顾家庭和孩子,忙于洗、烤、带孩子,为在工厂中的妻子准备低劣的晚饭。”[12] (P.101)因此,人们把婚姻和做母亲当作妇女最好的归宿。男孩与女孩从小就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社会处处表现出给男性更多的机会。
在教育问题上,尽管一些宗教团体与教育机构从理论上强调给男女同等的教育机会,而实际上,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更重视男孩子的教育。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的大门对女孩子关闭,直到19世纪后期才有少数妇女进入大学学院学习,但是作为英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牛津、剑桥大学还是迟迟不给她们授予学位。19世纪80年代,在牛津大学讨论是否给妇女参加学位资格考试时,一位牧师对牛津大学的妇女发表这样的演讲:“当上帝造人时,你们比我们低劣,你们的低劣要保持到世界末日,你们不要破坏这种格局。”[13] (P.126)直到1893年,牛津大学才让妇女参加所有学位课程考试,剑桥大学到1948年才同意授予女子学位。
在中等和初等教育中,劳工家庭把女孩子作为赚钱的机器,在北部工业区,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大,在普通人看来7~8岁的女孩子就应该自己养活自己。因此,女孩子很早就被送进工厂,没有机会入学。
男孩、女孩不同的入学率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伦敦的倍德温(Baldwin' s Gardens)学校,1812~1832年登记在册的学生中,男生7089人,女生4262人。[11] (P.55)男生几乎是女生的一倍。
同时,与男生相比,女生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入学的女童也不能拥有男孩那样的在校学习时间。她们必须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尤其是在家人生病期间,或是母亲外出或是母亲帮别人接生时。一些女子学校为了让女孩入学,不得不允许她们缺课,甚至默许她们把年幼的弟妹带到学校里来。1842年,一位观察员在利物浦的学校中发现十几个小孩子跟着姐姐上学。如果说19世纪工人因为缺少闲暇时间、缺少钱,所以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妇女比一般的男性工人拥有更少的空闲时间、更少的钱、更少的受教育机会。
在教育目标上,大部分教育家和理论家们都强调性别差异教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女子“所学的一切,无不明显地具有一定有用目的:增进她肉体上自然的丰姿,形成她内心的谨慎、谦逊、贞洁及节俭等美德;教以妇道,使她将来不愧为家庭主妇等等”。[14] (P.3387)这就是说,妇女,尤其是中上层妇女,唯一的经历是成为妻子和家庭主妇,她唯一可做的是用自己的性别吸引男性。对于男孩子来说,学校的教育是让他们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和各行业的生产技能,成为家庭的挣面包者。19世纪40年代,教育委员会所推荐的教育男孩子的课程中包括历史、地理、如何挣钱、哲学、政治经济学,普通天文学等基础课程。他们比女孩子接受更多的宗教教育、数学和写作的训练。
对女孩子来说,教育始终与长大后做母亲的角色联系在一起。她们从小不是像男孩那样接受生产技能的训练,而是进行简单的知识教育和家务技能训练。一些教育家认为:“一般人相信高标准的普通课程学习会影响女孩子的道德与家务劳动技能训练,把女孩子的知识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对她是有利的。让女孩子过多地接受诸如地理与语法之类的学科教育,会影响她为家庭服务。”[11] (P.110)另一些教育观察家们还建议女子教育要把知识教育与家务工作联系起来。如数学教育要结合统计购物的账单,写作要与怎样炸羊腿等家务工作联系在一起,化学讲的是通过烹饪实践,让女主人掌握在什么样的温度下能做出最好的食品。19世纪70、80年代,初等教育部正式认可在初等学校中,对女子实行家庭技能教育,如烹饪、洗熨衣服等。19世纪50年代后期不列颠公立学校课程中,学习读、写、算术、地理、历史、音乐、绘画等课程的男生比例超过女生,机械、物理、代数纯属男生课程,只有针织纯属女生课程。显然,性别差异教育的目的是为女孩子成为贤妻良母创造条件,为男孩儿参与社会竞争做准备。
这样,男性可以在工业化中迅速建立自身的技术优势,维护性别工资。工业化开始后,掌握操纵与监控新机器技术是工人建立行业支配地位的关键,而这些技术要靠一定时间的专业训练才能获得。男性拥有更多的训练机会和训练时间。他们在工业生产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迅速掌握新的劳动技能,成为工匠和技工,从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如:在18世纪70、80年代,纺纱机应用于家庭,由高工资的妇女操纵,后来蒸汽走锭精纺机得到应用,妇女的体力、技能都不能胜任,男性技工代替女性,逐渐垄断了该工种。19世纪,在纺织业的各技术部门,妇女进一步受到排挤,这不仅意味着她们没有足够的实践知识,而且雇主也难以找到足够的熟练女工来代替男工。在毛纺织业中,几乎所有的技术性工作都是由男性来完成,很少有妇女与男子从事同样的工作。在丝织业中,成年男工的工作增加了技术含量,并且支配着该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享受高工资,妇女丧失了上百年来在该行业的支配地位。西兰开夏纺织业提供的证据进一步证明“熟练”这一词不是简单地对工作性质的客观描写,而是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的区别。女性主义者巴巴拉·泰勒(Barbara Taylor)说,“女工在工厂中的屈从身份确定了她工作的价值……技术意味着特定的性别和权力,技术与男人联系在一起,缺少技术与女人联系在一起,男人处于技术中心地位,性别的技术界线与妇女缺少权力相关”。[12] (P.62)结果,在劳动力市场中,妇女与男性竞争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观念构成工资理论与工会活动的基础。“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在经济学家那里,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性别工资范式。亚当·斯密提出性别工资“两分法”:即“最下级普通劳动者,为供养儿女二人,至少须取得倍于自身所需的生活费,而其妻子,由于需要照料儿女,其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己。”[15] (P.62)在亚当·斯密看来,两性对家庭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工资标准。女性的责任是照料儿女,从事家务劳动,不能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她们的最低工资只要能维持她本人生存,可以处于人类最低生存需要的微薄状态,而男性要供养本人、妻子、一定数量的孩子,他的工资即使在最激烈的竞争状态下,也不能处于与女性同等水平。工厂主把这一理论作为压低女工工资,获取高额利润的工具。
男性工会把“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作为排斥妇女竞争的工具。让工作的妇女回家,维护男性挣面包者的角色,这已成为19世纪工会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中,男性面临妇女廉价劳动力的威胁。为了维护男纺纱工的利益,“纺工总工会”(The Grand General Union of Spinners)通过了约翰·多哈特(John Doherty)提出的,把女孩和已婚妇女排斥出组织的议案,成为早期典型的坚持性别隔离的组织。19世纪30年代,工人政治运动的直接目标是缩小全日制雇用妇女的范围,维护传统的两性分工,提高工人家庭生活质量。1834年,9000名裁缝工人举行罢工,其目的就是为提高工资,取消计件工资,结束妇女在该行业中的支配地位。裁缝们宣布:“以妇女受雇用为条件同情女裁缝,这使她们逃避女性的责任。这分明是制造一种家庭内部战争。”[12] (P.125)同年,矿工协会提出:“让妇女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促使男性拥有高工资的机会。”[12] (P.15)宪章运动和争取10小时工作法案过程中,男性工会主义者进一步表达了这一男性霸权主义思想:“已婚妇女更好的职责是管理好家庭,而不是围着机器疲惫不堪地运转……妇女涌入劳动力市场,不仅离开了更需要她们的领域,而且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标准”。[12] (P.128)他们试图通过官方立法,保证男性权利的实现。
19世纪中期以后,工会运动继续强化了上述男权思想。19世纪70、80年代,男性熟练工人为维持护自身的就业垄断权而建立新规则,以阻止妇女的竞争。“不列颠工会大会”领导人亨利·布罗特哈斯特(Henry Broadhurst)在1877年的工会年会上明确提出,男工会会员作为男人和丈夫的责任是努力达到让妻子回到适合她的家庭,不再为生活而卷入与强壮的男性竞争的局面。1876年工厂法委员会和1889年男性链条制作工人都向上院选举委员会陈述妇女回到家庭的好处。“当已婚妇女进入车间,成为丈夫的竞争者,结果必然是男人和女人一起挣她不参加工作时,男人独自挣到的那份工资”。[11] (P.68 )同时,委员会还声称男女一起工作会造成妇女道德败坏,失去女性的特性,破坏人类的幸福。1894年,“妇女工会同盟”主席吉启德·托克维尔(Gertrude Tuckwell)建议在孩子长大到能自己照顾自己前,禁止母亲工作。该同盟反对五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工作。
在工会运动的影响下,许多妇女参加工会运动,也认同男性是挣面包者的观念。1853~1854年布里斯顿的罢工斗争是由于两个女工被解雇而引起的,但在运动中,妇女接受了已婚妇女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建议。一位妇女代表玛格丽特·福莱切(Margaret Fletcher)表示为妇女离开家庭去工作,男人留在家里而感到悲哀。她宣布男性是家庭中的挣面包者。
实际上,这种理想的两性分工对于男人来说,有一个全职太太,可以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会生活得更舒适。就妇女而言,虽然承担了家务的全部责任,而经济上只是依附者,享受不到诸如国家保险金之类的社会保障,更得不到社会立法的保护,只能处于第二性地位。
同时,工会运动又促使国家立法维护男性特权,强化“男主外女主内”观念。19世纪30、40年代的工厂法规定:妇女与儿童一样需要保护,妇女每天劳动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包括就餐休息不少于1.5小时,而且工作时间只限在早上5点至晚上9点。1842年煤矿法案规定:禁止10米以下的矿井雇用妇女和儿童。1867年农业法案禁止雇用8岁以下的儿童和妇女与男子一起组成田间劳工队。这样,农村妇女不得不回归家庭。1844年的安全法案规定机器保养工作由成年男性担任,这确定机器修理调整工属于男性工作性质。
这些工厂立法中的许多内容强调单方面地给妇女提供保护,实际上没有真正起到保护妇女利益的作用。被工厂法排挤出工厂、矿山后,大量妇女处于失业状态,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亲属,有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进入不受工厂法保护的“血汗行业”,如针织业、火柴制造业等。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在家庭小作坊中进行,工作环境更差,工作时间更长,报酬更低。
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立法刺激妇女为婴儿和儿童的福利负责,而不鼓励社会为儿童提供设施。实际上,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让她们跌入低工资行业或失业的陷阱中;而男人则通过立法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而且享受较多的闲暇时间,他们是工厂法的真正受益者。历史学家K.荷尼曼认为,立法所产生的规范化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是性别分工建立过程的组成部分。
上述可见,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影响下,整个19世纪,男性通过教育、工会活动、工厂立法重建男性的就业优势,维护性别工资,从而确立了他在家庭、社会的优势地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妇女的从属性并不是工业社会的新现象。前工业化时期,劳动妇女从事辅助性工作,没有独立的工资收入,她们劳动所得包含在家庭男性的收入中,而且,妇女儿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是前工业化时期家庭经济扩张的基础,这与工业化时期,大量廉价雇用女工童工情况不存在质的区别。但是,不可否认,工业化使妇女以独立工资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是妇女解放,实现两性平等的先决条件。当然“男主外女主内”作为男性霸权主义的观念、一种社会行为,渗透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主宰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它不可能随着现代化中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结构变化而迅速瓦解,因此,性别分工、性别工资、妇女从属于男性现象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改变。直到当代社会,这种观念继续影响着妇女的工作和生活。彻底冲破旧观念束缚也是当代社会解决性别不平等状况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