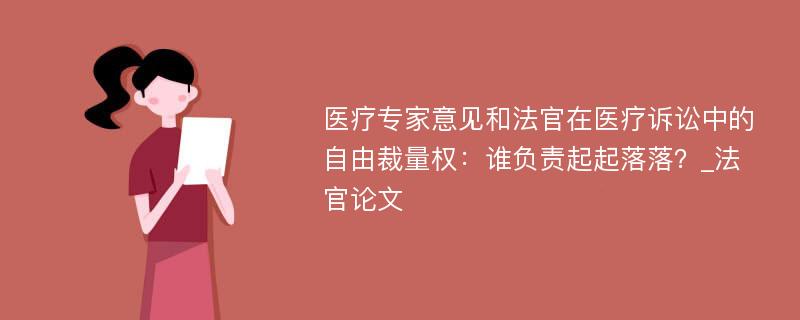
医疗诉讼中的医疗专家意见和法官自由裁量:谁主沉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医疗论文,法官论文,主沉浮论文,意见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2007-
【中图分类号】D9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3-0169-13
在侵权法中,在判定被告过失方面,除了主观判断,法官往往会参考一些既存的外部证据,比如某一行业的普遍做法,或某一行业的行业规范,或某一行业的专家意见。此种做法是有道理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期望法官去知晓各个行业的规范和术语,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较强、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如医生、律师、建筑师等)。依照或参考行业做法和专家意见是一种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期望某一行业的执业人员远离行业标准而去“孤独地行走(plough a lone furrow)”①。利用行业一般做法去衡量其成员的行为是一种合理需求。不过,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些专家意见或行业做法在法官对注意义务和过失乃至因果关系的判断上究竟应被置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在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义务上的违反从而构成过失方面,法律所适用的是一个“合理人”的标准。此标准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合理人”标准应用到诸如律师、医生、会计师这样一些需具有特殊技能(special skill)的领域便演绎成了一个“合理执业人员(reasonable professional)”的标准,而不再是公共汽车、地铁或大街上之人的标准。再具体一点讲,在医疗领域法律所适用的标准通常是一个“合理医生(reasonable doctor)”的标准。那么,“合理医生”的行为标准是否也以医疗某一领域专家的意见或行业做法为依归呢?这也是医疗侵权法发展到细微之处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
一、英国Bolam案——治疗领域、医学不同观点、对医学观点的极大尊重
(一)案情及系争点
在Bolam案②中,原告(John Hector Bolam)曾是被告方Friern医院(精神病医院)自愿入院的病人,他因抑郁症于1954年8月16日再次自愿入院。根据其病情,医院分别于8月19日和23日对他实施了电抽搐治疗(E.C.T.)。在电抽搐治疗中,需要将电极置于头部的每一侧,让电流通过大脑。让电流通过大脑的后果之一是会突然产生剧烈的抽搐运动,此种抽搐运动可表现为痉挛和肌肉收缩。如果在治疗前向患者实施了弛缓药物(relaxant drug),肌肉的反应会减少以至到很难辨别出的程度。问题是,在本案中,医院在实施治疗时并没有事先施以弛缓药物,而患者在治疗中的肌肉抽搐运动中遭受了伤害。在8月23日的治疗中,该医院的Allfrey医生,根据其通常的做法,对患者实施的是“未加控制的(unmodified)”电抽搐治疗,即没有事先施以弛缓药物,也没有施以任何形式的手工控制。在实施此种治疗时,医方所做的是仅是让患者躺在一个长沙发椅上,采取了些支持其下巴和双肩的措施,并在患者口中放置了塞口物,治疗时护士站在沙发椅的两侧,目的是防止患者从上面摔落下来。结果是,患者在治疗中因剧烈的抽搐运动导致了其骨盆骨折。
原告诉称被告在以下方面存在过失:(1)未能事先对患者施以适当的弛缓药和/或麻醉药物来预防或控制剧烈抽搐;(2)未能配备足够的护士来控制痉挛时的抽搐运动;(3)在没有事先施以弛缓药或提供手工控制的情况下,允许实施电抽搐治疗;(4)未能警告他此治疗的风险,特别是,未能警告他医方将在没有弛缓药物和手工控制的情况下实施此疗法。被告拒绝上述过失责任。
在本案中,需要回答的问题是,“Allfrey医生,遵循他在Friern医院习得的做法,遵循Bastarrechea医生展示给他的技术,未采用弛缓药物,这是否存在过失:在决定不使用弛缓药物的情况下,他只是采取了支持肩部和下巴、使用塞口物、背部下放置枕头的措施,除此以外而未采取任何手工控制患者的措施,这是否存在过失”。③
(二)原被告专家意见
本案的一个特点是原被告双方在是否使用弛缓药物和手工控制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代表原告方的专家(Randall医生)认为,在实施电抽搐治疗时,应当使用弛缓药物和麻醉药物,这些药物可预防肌肉对电流刺激的反应从而减少骨折的风险。该专家讲道,在1953年前他只是在某些场合下使用弛缓药物,而自1953年以来他已经在所有的电抽搐治疗中使用弛缓药物。不过,他承认,尽管他倾向于使用弛缓药物,仍有为数不少的执业人员对此持不同意见。对于此种职业上的不同意见,他表示了尊重。该专家认为,还不能说,一个1954年实施电抽搐治疗的执业人员仅因为未能使用弛缓药物就判定其医疗行为低于一个合格的医疗人员所应有的注意标准。该专家的个人观点是,如果不使用弛缓药物,某种形式的手工控制应是必要的。他认为,在既不施以弛缓药物,也不施以手工控制的情况下就盲目实施电抽搐治疗是愚蠢的。他讲道,上述观点已得到其他人的认同。不过,他承认,在医疗行业中存在另一种不同看法,该种看法认为,对患者的控制或限制越多,骨折的可能性就越大。
被告方的专家Bastarrechea医生则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实施电抽搐治疗中他不主张使用弛缓药物,原因是此种药物的使用可带来致命的风险(a risk of mortality),而“未加控制的”电抽搐疗法所内含的骨折风险则是微小的。因此,在权衡两种做法所隐含的风险之后,他倾向于在ECT治疗中不使用弛缓药,除非存在特殊情形。另外,来自其他证人的证据表明,在实施电抽搐治疗时,医疗界的控制做法不一:有使用起限制作用的被单的,有使用弛缓药物的,有使用手工控制的。但是,他们都认为,医疗界存在一种通常情况下不使用弛缓药物的观点和做法。被告医院也认为,他们在1951年之前曾使用过手工控制,但是1951年后便放弃了这一做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他们的经验,对在实施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限制越少,骨折的风险就越小。
另外,证据显示,原告所遭受的伤害是并不常见的(exceptional)。
(三)法院观点
本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上述医学专家意见分歧是否会影响法官对被告行为的认定。
在McNair法官给陪审团的指示(direction)中,McNair法官首先明确,在判定专业人员过失问题上,“测试标准是行使和声称拥有那种特殊技能的通常的熟练人员所应达到的标准(the standard of the ordinary skilled man exercising and professing to have that special skill)”;“一个人不需要拥有最高的专家技能,既定的法律规则是如果他行使了操守那种特定行业的一个通常适格的人的通常技能,这已足矣。”④当然,注意标准的适用也有个时间维度。就本案而言,所适用的标准应是1954年事件发生时的标准,而不是1957年案件审理时的标准,“不能用1957年的眼镜来观察1954年所发生的事”。⑤
McNair法官显然意识到了本案中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医学观点和临床做法的存在,这是否影响到过失的认定呢?在推出自己观点之前,法官引用了苏格兰案子Hunter v Hanley中的一段论述:⑥
在诊断和治疗领域,存在许多真诚的不同意见。很明显,一个人不能仅因为他的结论与其他职业人员有异就认定其存在过失……在诊断和治疗领域认定医生过失的真正的测试标准是,是否他被证明他应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对于此种行为一个具有通常技能的医生若行使合理注意是不会承担责任的。
对于此问题,McNair法官的表述是:
如果他按照一个做法行事,而该种做法被熟知那种特定技能的一群负责任的医疗人员(a responsible body of medical men)接受为适当,他就不应负过失责任。……换句话讲,如果一个人按照这种做法行事,不能仅因为存在一种相反的意见应认定他有过失。
因此,在此案中,法院的立场是:(1)在医疗领域,测试医疗人员是否存在过失的注意标准是行使和声称拥有此种特殊技能的通常的熟练人员所应达到的标准;(2)如果一位医生按照一个被当时熟知某一特定治疗的一群负责任的医疗人员接受为适当的做法行事了,他不应仅因为存在一个主张使用不同方法的不同的医学观点和做法而去承担过失责任。在职业界存在两种不同做法和观点的时候,需要决定的事不是两种做法孰优孰劣,而是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一群负责任人员的做法,“是否遵循了已经业已被认可的某一学派的观点(school of thought)”。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位医疗人员可以固执地和愚蠢地去坚守一些旧的做法,如果这些做法被证明是有违实质上真实存在的不断更新的整个医学观点的话”。⑦根据以上标准,陪审团最后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认定。
(四)评析
Bolam案建立了测试一位医疗执业人员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标准——“行使和声称拥有那种特殊技能的通常的熟练人员所应达到的标准”或者“一群负责任的医疗人员”所应达到的标准,此种测试标准不受业界不同意见的影响。Bolam案在很大程度上正视了医学这一学科的性质、医学发展的特点和医学界的现状。案中McNair法官非常钟情于Denning法官在Roe v.Minister of Health一案中所阐述的一番话:⑧
医学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是跟随这些益处的是相当可观的风险。每一个外科手术是伴随着风险。我们不能只获取益处而不去面对风险。技术上的每一个进步也同样伴随着风险。医生,就像我们一样,需要通过经验去学习;而经验经常是一种残酷的方式获得的。……如果我们让医院和医生对所发生的任何不幸事都承担责任的话,这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利益。这将会导致医生考虑更多的是他们的自身安全而不是患者的利益。干劲将会被抑制,自信将会被动摇。
Bolam案在医事法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和价值已被下列事实所证实:Bolam测试标准曾被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数次援引作为判定医疗过失责任的试金石。⑨它也被英国的枢密院(Privy Council)所认可,从而被推广到整个英联邦国家。⑩而且,Bolam 测试标准没有被限于医疗行业,而是一个具有普通适用性的可适用于需要专门技能、知识或经验的其他职业的规则。(11)
根据Bolam测试标准,如果一位医生按照一个被当时熟知某一特定治疗的一群负责任的医疗人员接受为适当的做法行事了,他就不应去承担过失责任,哪怕行业里存在一个主张使用不同方法的不同的医学观点和做法。总体来看,Bolam测试标准更多强调的是一个通常(ordinary)执业人员的标准,它对职业观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Bolam案曾援引过英国早年的Marshall v.Lindsey County Council一案(12)。在此案中,Maugham就认为,“如果一种行为符合人类的一般做法,就不能认定它是缺乏合理注意的”,“如果他能表明他的行为符合一般的、经认可的做法,被控存在过失的被告就可能洗清自己了”。同样,在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v.McDaniel一案(13)中,来自英国枢密院的Alness法律议员也认为,“如果一位被控以过失的被告能证明他遵循一般的、经认可的做法(general and approved practice)行事了,他便可以‘洗清自己的双脚’”。
尽管有人士认为在Bolam案中McNair法官的本意也许并非赋予行业观点以决定性,但是从Bo-lam案以后的案例看,他实际上是被演绎成了这样一层意思以至于到了Sidaway案中Scarman这位英国法律议员眼中注意标准仅“是一个医学判断问题”了。Scarman法官认为,“Bolam原则可以这样描述为这样一个规则:如果一位医生遵循了当时一种负责的医学观点认为适当的做法,不应判定他存在过失,哪怕其他医生遵循另一种不同的做法。简单地讲,注意义务是法律所赋予的,但是注意标准则是一个医学判断问题”。(14)
二、英国Sidaway案——传统的Bolam测试标准在知情同意领域的延续
除了治疗(treatment)领域(15)和诊断(diagnosis)领域(16),Sidaway一案(17)可以说是Bolam案所建立的测试标准在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领域得以适用的一个见证。在Sidaway一案中,原告因颈部、右肩和双臂疼痛于1974年在被告处做了一个手术,手术是有一位资深的神经外科医生做的。该手术,即使投入了适当的注意和技能,仍内含有一种风险,对脊柱和神经造成伤害的风险,此风险的发生概率较低——只有1~2%。潜在的风险在原告身上发生了,导致了其严重瘫痪。原告诉称被告在以下方面存在过失:未能向她披露或解释该手术内含的风险。在初审法院,Skinner法官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因在于,在1974年,不向患者告知上述风险是被一群尽责的、有技能的、有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认为是适当的一种做法,法官根据Bolam测试标准做出了上述判决。上诉法院肯定了初审法院法官的决定。争端被上诉至了英国上议院。英国上议院仍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在此案中,医生的职业功能被划分为三个领域:诊断、建议和治疗;而本案所涉及的是第二个领域,需回答的问题是在医生就治疗方案给出建议(即履行告知或风险警示义务)方面,法律是否应给出不同的衡量医生注意义务的标准。也就是说,英国上议院需要考虑Bolam原则是否应当适用到诊断和治疗领域之外的信息提供领域(知情同意领域)。在此案的诸多法律议员中,多数派意见持有者Diplock法律议员算是Bolam测试标准较为忠诚和坚定的支持者,它更认可Bolam测试标准的广泛适用性。在他看来,知情同意领域与诊断、治疗领域应适用同一的标准——Bolam测试标准:“决定什么风险应向患者主动地告知以及在考虑警示的后果后此种警示(如果有的话)应以何种方式给出这些问题仍是职业技能和判断(professional skill and judgment)的行使,这与医生需要全面地对患者负注意义务的其他领域是一样的,因此在此问题上专家医学证言应得到同样的对待。Bolam测试标准应得以适用。”多数派意见持有者Bridge和Templeman法律议员(18)对Bolam测试标准进行了知情同意领域的修正,但尚不能构成革命性的演绎。比如,Bridge法律议员首先肯定的是“医学临床判断”在知情同意领域仍然需发挥主导作用,然后才是法官在某些场合下对“医学临床判断”的再判断:
……决定什么程度的风险告知最能帮助特定患者就是否接受某一特定的治疗做出合理的选择必须首要地(primarily)是一个临床判断(clinical judgment)问题。也就是说,在特定案件中未披露行为是否应被谴责为对医生注意义务的违反这一问题是一个主要根据专家医学证言适用Bolam测试标准来决定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此种方法需要‘将警示义务的范围整个问题,包括是否存在此义务的违反问题,转让给医疗业来做决定’。当然,如果在一个负责任的医学观点是否同意特定案件中的未披露行为问题上存在证据冲突,法官应去解决这一冲突。
……我认为,法官在特定情况下也许会得出结论说,对某一特定风险的披露对患者做出知情选择来说是如此明显地必需以至于不会有合理谨慎的医疗人员不去做它。我想到的此类案件可能是含有会产生严重负面后果之巨大风险的手术,比如加拿大案件Reibl v.Hughes(1980)114 DLR(3d)1中所涉及手术中10%的风险。在此案中,在对于为何不对患者告知问题上缺乏一些中肯的临床原因的情况下,一位应承认并尊重患者决定权的医生很有可能认识到有必要对患者进行适当的警示。
与Bridge法律议员相比,Templeman法律议员看起来更不太情愿让来自医学界的观点主宰在知情同意领域对注意义务和过失的判断,他认为,“法院必须决定向患者提供的信息是否足够充分以向患者警告实际上遭受到的严重伤害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两位法律议员还是赋予了医生很大的具有实质性的权力空间,让他们有权力根据“医疗特权”和所谓的“患者最佳利益”来决定是否向患者披露相关风险。本案的多数派意见仍然认为,在决定被告的未告知风险行为是否构成注意义务的违反这一问题上,Bolam原则应得到适用。即使两位法律议员的上述看法算是对Bolam测试方法的修正,此种修正在适用范围上也是有局限性的。在Gordon v.Wilson一案(19)中,Penrose议员就谈到Bridge议员的意见只限于信息披露领域,他并没有意图对Bolam测试方法做出限制。倒是Sidaway案中的不同意见持有者Scarman法律议员较为彻底地否定了Bolam原则在信息提供领域的适用,他认为初审法官和上诉法院法官的意见是令人困惑的,它们,
将法定义务的决定权留给了医生去做判断。负责任的医疗判断也许确实可以提供给法律一个可接受的标准来决定一位医生在诊断或治疗领域是否遵守他的义务。但是是否也应当让医疗判断来决定是否存在一个警示风险的义务以及义务的范围呢?如果法院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法律一方面毫无疑问地应认可患者在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所建议的治疗上所享有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又允许医生来决定要求医生警示他所建议的治疗中潜在的风险这样一个义务是否产生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产生,这将是一个奇怪的结论。……
依我看,不做警示是否构成了对患者所负注意义务的违反这一问题不应根据当时现行的尽责的和称职的职业观点和做法来独断地决定,尽管它们当然是相关的考虑因素。这一问题而是应有法院的观点来决定。法院应看医生在向患者做出建议时是否根据法律要求考虑了患者根据相关信息就是否接受所建议的治疗做出决定的权利。
尽管存在不同意见生存的缝隙,英国Bolam案与Sidaway案基本上是对医疗行业“普遍做法”的传统认知主宰主流意见的判例。Bolam案、Whitehouse v.Jordan案(20)、Maynard案(21)和Sidaway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案例群,让Bolam测试方法很快就贯彻到了医疗的所有领域——治疗领域、诊断领域和信息提供领域。这些案例都给予医疗界通行的意见和做法以及被告的简单遵循很大程度的尊重和肯定,尽管一个人遵循通行做法也许仅仅是出于便利、成本或习惯的考虑,而与一个人的合理注意并无关系。在这种思维中,法官对注意标准和过失的认定几乎沦落成了对医疗界专家意见的简单依附。“医生的行为只要与一个尽责的职业人员认为适当的做法一致,他就可以脱责;换句话说,法官或陪审团没有空间再去认定一个标准的医疗做法存在过失。法律通过用医疗界设定的标准替换通常的合理注意标准的方式,实际上是赋予了医疗界一个其他同样需要专门技术的职业——诸如会计师、律师——所没有的特权。”(22)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司法局面,其中原因耐人寻味。也许与无法期望法官和专业外人士去知晓精深的医学专业知识有关;也许是为了防止出现美国那样的因医疗诉讼泛滥而导致的“防御性医疗(defensive medicine)”现象;(23)也许是“惧怕陪审团会同情受害人而将医疗人员置于难以预料的旋涡之中”(24)。但是,上述思维和方法并无很强的合理性。一方面,一位医疗人员遵守了行业内的普遍做法并不等于他尽了一个合理人的合理注意,业内人士的通常行为标准不同于一个合理人应当具备的行为标准。另一方面,上述方法会迁就医疗业也许并不高的通常行为标准,使一些医疗人员安然地享受着同行观点的庇护,而将患者的利益置于不利的境地。正如Coyne法官在Anderson v.Chasney案(25)所说的,“一群经营者通过采纳某种做法、通过采纳并继续使用一种明显有过失的做法就可以在法律上将他们置于对公众应负的过失责任之外…”。另外,既然法律已经在医疗业外的其他职业责任(professional liability)案件中适用了法院可认定行业普遍做法为过失的方法,(26)没有理由单挑出医疗这一职业而适用不同于其他职业的方法。
三、澳大利亚Rogers v.Whitaker案和加拿大的Reibl v.Hughes案——普通法系中的不同声音
在对待Bolam测试方法的态度上,虽然同处于普通法系和英联邦法律体系之下,澳大利亚一直保持与英国司法态度的距离。在专门技能人员的注意标准问题上,澳大利亚传统的司法观点是这一注意标准不是唯一地甚至不是主要地由一群负责的职业人员所支持的做法所决定的。(27)即使在医疗执业人员的专业中心领地——诊断和治疗领域,英国Bolam 原则也不总是得到适用。(28)更不用说在信息提供领域了。早在Sidaway案之前,在F.v.R.案(29)中,南澳大利亚州最高法院就信息提供——风险披露方面拒绝了Bolam原则。此案的King法官认为一个职业内某种做法的出现并不总是为了它所服务的对象的利益的需要,而可能是出于该职业的利益需要,因此,一个职业有可能采纳一种不合理的做法,法院有义务去审查职业做法以确保它与法定合理标准的一致。该法官谈到:
最终的问题,不是被告的行为是否符合他所在的职业或部分职业领域的做法,而是它是否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合理注意的标准。那是一个需由法院决定的事情,决定它的义务不能让渡给社区中的任何职业或团体。
在澳大利亚的Rogers v.Whitaker案(30)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也明确否定了英国Bolam案和Sidaway案的适用。在该案中,被上诉人(原告)Whitaker是一位患者,许多年来她的右眼一直不好,几乎失明。上诉人(被告)Rogers是一位眼科外科医生,他为被上诉人(原告)做了一眼部手术。在手术前,他告诉患者此手术不仅可以达到祛斑美容的效果,而且很可能很大程度上恢复右眼的视力。但是,手术后,患者的右眼视力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手术也导致了患者左眼感染从而使左眼完全失明。因此,患者几乎双眼都失明了,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患者因手术遭受了灾难性后果。患者左眼的感染是因交感性眼炎(sympathetic ophthalmia)导致的。有证据表明,此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约是14 000例手术1例或更高一点,且通常情况下不会导致视力丧失。此案中对于被告在手术中的技能和注意并没有争议,原告起诉医生的是在手术前未能向其披露交感性眼炎这一风险。案情显示,患者对右眼手术对其左眼的影响非常关注。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被告未能向患者警示手术风险是否构成注意义务的违受。对于此种风险的披露,医疗界存在着观点和做法上的分歧。根据一群“声誉良好的”医疗执业人员的正言,当时的一种医学观点认为,如果患者没有明确问及,医生可能不去理会它,而根据本案情况,医生不会向患者警示交感性眼炎这一风险。但是,根据另一群“声誉良好的”医疗执业人员所提供的证言,另一种相反的医疗观点认为,在本案中,他们会向患者提供警示。基于此,被告企图借助Bolam测试标准而脱责。
在批判性地审视了英国的Bolam案和Sidaway案之后,本案的多数派意见(31)否定了被告的辩解理由。多数派法官一方面肯定了医疗人员在诸职能领域注意义务的不可分割性,认同此注意义务是“一个单一的综合性的义务(single comprehensive duty),涵盖了所有的需要医生行使其技能和判断(skill and judgment)的领域”(32),这些领域不仅包括对患者的检查、诊断和治疗,也包括信息提供;(33)另一方面也指出在决定医疗执业人员是否违反注意标准问题上,法院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是关于诊断、治疗的还是关于信息提供的——去考虑不同的“因素(factors)”:
诊断和治疗与给患者的信息提供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在诊断与治疗领域,患者的贡献仍限于对症状和相关病史的陈述,诊断与治疗是由医疗执业人员根据其技能水平来提供的。然而,除非存在紧急(emergency)或必需(necessity)的情况,所有的医学治疗都是以患者对治疗的选择为先导。……由于对治疗的选择需要患者做决定,而患者的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是由医疗执业人员而不是由患者所知,因此,如果认为医疗人员应提供的信息量仅仅由执业人员或者医疗职业界的视角所决定,这将是不合逻辑的。要解决一位医疗执业人员是否依据适当的注意标准实施了某一特定治疗这一问题,负责的职业观点将发挥有影响的(influential),通常是决定性的(decisive),作用:但是,在决定是否提供给了患者所有的相关信息让其选择是否接受某种治疗这一问题上,侧重次序应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它不是一个由医疗标准或做法来回答的问题。除非存在对所有相关信息的提供会伤害一位异常敏感或情绪不易控制的患者这一特定的危险,对信息的披露,包括对拟定治疗所含风险的披露,不需要专门的医疗技能(special medical skill)。
本案的另一位法官Gaudron(同意意见持有者)对Bolam测试标准适用面上的限制则更进一步。此法官认为,说医生在负“一个单一的综合的义务”是一种高度概括的说法,它没有考虑在诊断和治疗与信息和建议提供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概念上和实践中的不同”。此法官同时认为,即使在与诊断或治疗有关的案件中,“特定风险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可预见性也不是绝对地属于医学知识或专业领域内的事项”,实际上它们“通常是简单的共同常识(simple commonsense)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关于某一特定预防措施的合理性问题也是共同常识问题,因此,即使在诊断与治疗领域,“也没有合法根据去借助被称之为‘Bolam测试标准’的规则来限制责任”。
在Naxakis v.Western General Hospital一案(34)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再次肯定了Rogers案,测试医疗过失的标准不是其他医生在相同的情况下会如何去做。(35)来自澳大利亚的司法声音同样也在加拿大上空回响。在Reibl v.Hughes一案(36)中,加拿大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Canada)认为:
让专家医学证言来决定什么风险是实质的因而应得到披露以及,相关地,什么风险不具有实质性就是将披露义务之范围这一整个问题,包括是否存在义务违反问题,交给了医疗界来回答。在认定所建议的手术或其他治疗内含的或导致的风险这一问题上,专家的医学证言是相关的。它也与风险的实质性有关联。但是这不是一个仅基于专家医学证言便可以得出结论的问题。需考虑的问题与医生是否根据可适用的职业标准实施了其职业活动这一问题不是同样性质的问题。这儿需考虑的患者知晓实施特定手术或其他治疗之风险的权利。
前述对行业做法的定性在程序法上会有什么意义呢?在澳大利亚另一案件Lowns v.Woods(37)中,Kirby法官认为,“如果被诉的医疗执业人员已经证明了他或她已经遵守了所涉专业内的通常的医疗做法,法庭上的负担便转移给了患者,应由患者来向法院证明,尽管如此,通行的做法并没有达到在此情境中法律所要求的合理注意。”Mahoney法官则指出,“要说服法院得出这样一个事实上的结论:那些在某一领域有专长的人所说的[比如]应该或不应该实施某一特定治疗的结论是错误的,是需要有说服力的理由(cogent reasons)的。这可以做成,但是事实上的说服负担通常情况下是很重的。”
四、英国的Bolitho案——Bolam测试标准在治疗领域的更新
在Bolam测试标准和医疗界“普遍做法”的性质问题上,英国权威性的司法意见的转折发生在1997年的英国上议院。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同,此种转折没有发生在较具特殊性的知情同意案件中,而且发生在了医生需有运用专业技能的中心领地——治疗。这便是著名的Bolitho v.City and Hackney Health Authority一案(38)。此案的案情很简单:一位两岁的男
孩因呼吸困难而住院。在入院后的第二天下午12:40,小孩的呼吸困难突然恶化,护士电话通知了主管小孩的医生,但是医生没来,小孩最后恢复了。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了下午2:00。下午2:30,小孩因呼吸系统衰竭而出现虚脱,并导致心搏停止。当小孩的呼吸和心脏功能恢复后时,他已遭受到了严重的脑部损害。原告起诉被告存在过失,认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在第二次出现呼吸问题后会安排预防性的插管来提供呼吸通道以避免心搏停止和其他损害。被告承认在事件后未到场问题上存在过失,但却在因果关系上做起了文章,辩称即使到场,也不会采取插管措施,心搏停止和脑部损害无论如何会发生。因此,在此情境中,医疗上是否应采取插管措施成为关键。但是,在此问题上,医学上的意见并不统一。被告所提供的被认为代表“一个尽责的职业观点”的专家称,在案中情境下,他不会采取插管措施。相反,为原告出具证言的五位专家则称根据案中情况,他们会采取插管措施,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种预防损害的措施。尽管最终还是做出了对被告有利的结果,英国上议院的思维较Sidaway案却出现了重大转折,从而推出了新的Bolam测试标准。
在代表英国上议院出具的判决(39)中,Browne Wilkinson法律议员同意,“法院不应受约束地去认定,一位被告医生仅因为提供了数位医学专家的证言——这些专家真诚地认为被告的治疗或诊断符合恰当的医疗做法——就可以摆脱对其过失治疗或诊断应负的责任。”议员注意到了英国Bolam案和Maynard’s案中对相关医学观点的限定词——“负责任的(responsible)”、“合理的(reasonable)”、“值得尊敬的(respectable)”,认为这些形容词的使用意味着法院应确保医学界的观点应是“有逻辑基础的(logical basis)”。在援引了Hucks v.Cole案(40)和Edward Wong Finance Co.Ltd.v.Johnson Stokes & Master案(41)后,议员指出:
这些案件显示,在涉及诊断和治疗的案件中,也会出现即使一种职业观点支持被告的行为,被告也可被恰当地认定对过失负责(这里我考虑的不是风险披露的问题)。根据我的判断,这是因为,在一些案件中,法官不能满意地认为所依靠的此种观点是合理的或负责任的(reasonable or responsible)。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在某一领域知名的专家持某一种特定观点这一事实本身将会显示此种观点的合理性。……但是,在一些较少见的案件中,如果显示职业观点是不能经得起逻辑分析(logical analysis)的,此时法官有权去判定此种观点并不是合理的或负责任的。
此种对专家证言“逻辑基础”的要求反映的是“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要求。此时,法律的关注点不再是证言出自“专家”以及专家责任而是“证言(opinion)”本身。(42)不过,在认可了司法界对医学界观点的干预之后,Browne Wilkinson法律议员强调指出:
法官将会非常少见地得出正确结论说一位称职的医疗专家所真诚持有的观点是不合理的。对医疗风险和益处的评估是一个临床判断问题,在此领域没有了专家证言法官正常情况下不会做出此类判断。正如Scarman法律议员之引用所指明的,不能错误地允许将此种评估退化为寻求说服法官去采纳两种都能得到逻辑支持的观点的一种。只有在法官满意地认为一种专家观点一点也不能得到逻辑支持(logically supported),此种观点才不能成为评判被告行为的标尺。
由此可见,在新的规则下,尽管法院保留了对被告行为评判的最后的发言权从而向医疗业的自主发出了挑战,但是法院对医疗专家意见的再次判断和置之不理还是相当谨慎的。不管如何,Bolitho案是英国司法中的一个标志性案件,它基本上扭转了英国司法界在职业侵权诉讼中一味迎合职业流行观点和做法的局面。自Bolitho案之后,英国的司法观点与澳大利亚(43)和加拿大(44)的司法观点逐渐一致起来。
在后来的Marriott v.West Midlands HA一案(45)中,新的Bolitho规则得到了适用。在此案中,原告因摔倒而遭受头部损伤并失去意识达约半小时之久。原告入院,但在经过X光照射和神经学上的观察之后,第二天让其出院。在家中,原告出现了嗜睡、头痛和丧失胃口现象。这种症状一直没有改善。摔倒后的第八天原告的GP(全科医生)来到原告家中,GP进行了神经学检查,但并没有发现异常。GP向原告的妻子做出建议:若病情恶化请打电话,对于头痛建议服用止痛药。四天后,原告的病情突然恶化,在经过紧急手术后,原告出现瘫痪和语言障碍。对于让原告留在家中而没有及时收入医院的做法,存在一种支持它的医学观点。初审法院认为,此种观点不是一种合理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案涉及一种原告摔倒后头部内部损伤的风险,此种风险虽然小但后果会是灾难性的,此时唯一的一个合理谨慎的做法是让原告再次入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上诉法院支持了初审法院的意见,认为法官有权拒绝被告的专家证言。法官在考虑被告行为的合理性时,权衡了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以及医院中进一步的检查设施是否随时可及等情况。
目前,在对待医疗行业“普遍做法”问题上,英国的司法态度是:(1)来自医疗界的关于一般做法的专家证言在判定过失方面并不具有结论性,特别是在不需要专业技能和经验的领域:(46)医疗界其他同行会有相同行为这一事实对被告来说,只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47)应由法院最后决定被告是否存在过失。(2)尽管不具有终局性,来自同行的专家证言和通行做法是决定被告是否行使合理注意的证明力较强的证据。法院不会随时准备着对医疗通行的做法进行谴责。正常情况下,只有在一种风险对被告来说是如此明显(obvious)以至于忽视它是愚蠢之举的情况下,法院才会做出干预。(48)一旦证明被告行为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法院就不应去认定其为过失行为,哪怕存在另一种不同的医学观点和做法。(3)如果案件不涉及较难的或者不确定的医疗问题,或高度技术性的科学问题,而只是涉及一种明显的、简单的预防措施是否采取,法官会更加容易去形成自己的判断,专家的做法,尽管并不是不相关,更容易被弃之。(49)与此相反,如果案件涉及较为复杂的、不确定的、高度技术性的科学问题,如果在某一领域的医学知识存在严重分歧,法院最好不要去轻易去认定符合同行业观点的做法存在过失。(50)(4)对于行业做法或专家证言,法院可以根据通常的可信度(credibility)原则来决定拒绝采信专家证言,比如在专家证言不具有独立性的情况下。(51)被告所援引的医学标准应是“在某一特定医学领域令人尊敬的(respectable)、尽责的(responsible)、有经验的(experienced)专家”所持有的医学观点,应是具有“实质性的一些人所持有的医学观点(a substantial body of medical opinion)”。(52)医学观点或专家人数的“实质性”不能以纯粹的数量来衡量,在全国1000多个矫形外科和神经外科医生中,11个专攻于脊椎外科的医生可以代表一种负责任的医学观点。(53)
五、行业普遍做法——“重要性”但非“决定性”证据
某一职业内存在的普遍做法(common practice)在评估被告行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Dunedin法律议员在早年的Morton v.William Dixon一案(54)中所言:
在雇主的过失是一种我称之为疏忽的过错,我认为,这种疏忽过错的证据,绝对有必要,应是两类情况的一种:或者证明他所未做的事是一种处于相同情境的其他人一般会做的事,或者证明这件事是如何明显地必要去做以至于任何人不去做均是蠢事一柱。
在解决了法官关注“普遍做法”和行业规范的必要性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类普遍做法的性质如何?它是不是一种具有终局性的证据?法官在此类“普遍做法”面前,有没有可以行使自由裁量的空间?
首先,此类“普遍做法”和行业行为规范在判定被告过失方面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力度很强的证据。也就是说,被告遵守了此等“普遍做法”和行业行为规范将是一个很有利于被告的证据,原告需承担很重的举证负担才能证明被告存在过失;(55)同样,反过来,如果被告未能遵守此等“普遍做法”和行业行为规范,这将是被告缺乏注意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56)因此,“如果存在一个业已认可的和一般的做法(a recognized and general practice),此做法在相似的情境中已经被遵循了很长一段时间而没有发生不幸事(mishap),[被告]有权利去遵循它”(57);即使发生了“不幸事”,如果此风险是“此行业不可避免的特征之一(an inescapable feature of the industry)”,去遵守此类行业规范也是有道理的。(58)不过,对于此等“普遍做法”的遵循,尚有几种限制因素:(1)如果该“普遍做法”,“根据共同意识(common sense)或较新的知识,明显是错误的”,被告无权去遵循它。(59)(2)“如果存在发展中的知识(developing knowledge),[被告]须合理地不停地了解此种知识并尽快应用它”(60),如果“怠于寻求了解一些本身并不明显的事实”(61),这可能产生过失。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普遍做法”。这一点在艾滋病感染案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62)随着医学对艾滋病病毒了解的逐渐深入,在此一时并不存在过失的做法在彼一时便成为疏于注意的过失行为了。
其次,此类“普遍做法”和行业行为规范在判定被告过失方面并不具有终局性,法官保留着最终发表意见的机会,由法院根据案件事实最终决定被告是否存在过失。也就是说,法院的认定“并不仅仅基于职业的一般做法”,“法院可以得出结论说,证人所证明的标准并未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标准——从事此项工作的一个合理的和谨慎的(人)所应达到的标准”。(63)一方面,法官可以自由地宣布某一做法存在过失,尽管该做法符合该职业的一般做法。(64)另一方面,未遵守某一行业的一般做法本身并不表明过。(65)
六、风险—益处分析—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的体现
根据“合理医生”标准,法律对医疗人员的考察适用的是一个“合理人(合理医生)”的标准。只有如同一位“合理人(合理医生)”尽到“合理注意”的医疗人员才会摆脱法律上的指责。对医疗人员是否尽到“合理注意(Reasonable Care)”从而达到“合理人(合理医生)”标准的考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演绎过程,它需要具体到被告(医疗人员)所在的具体情境和其具体医疗行为,判断在特定情境下其行为是否合理。在判定医疗人员行为的合理性,法律一般会考察以下两个基本问题:(1)案中所涉的风险是否是一个合理人(合理医疗人员)可预见的,即风险的可预见性;(2)如果所涉风险是可预见的,一个合理医疗人员会如何去做去避免或减少此种风险。在考察第二个问题时,法官的思维过程即是一个多种因素权衡的过程。这些因素包括4个:(1)风险的可能性;(2)风险的严重性;(3)采取预防措施避免风险发生所需的成本和代价;(4)被告行为的目的/助益/社会价值。其中,前二个因素可能会形成对被告不利的因素,但是后两个因素则会形成制约前两个因素从而对被告有利的因素。
医疗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于其专业性,法官往往会依赖医疗行业的专家意见。这一特点不会减损上述因素权衡——风险评估的价值和必要性。正如上文要阐明的,专家意见在法官的判决意见形成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法官的思维仍可能是风险评估的过程。
(一)风险的可预见性
风险是否是可预见的是考察医疗人员行为是否合理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是可预见的风险,才牵涉到行为人是否应采取措施避免风险发生的问题。风险是否是可预见的是以合理人为判断标准的。如果一个风险是不能被一个合理人所合理地预见到的,它便是一个不可预见的风险,便不能期望行为人去采取措施去避免或减少风险发生。在判断一个风险是否可预见这一问题上,应把握一个时间维度。只能用事件发生时的知识去衡量风险的可预见性,而不是用事后的发展的知识去衡量过去的事件。在Roe v.Minister of Health案(66)中,原告因麻醉剂被污染而遭受伤害,在事件发生时(1947年)此种麻醉剂被污染的方式是不可预见的,因此,法官在1954年审判时并没有“戴着1954年的眼镜来观察1947年发生的事件”从而让被告对此承担责任,尽管此类事件若在1954年发生很有可能被定为过失事件,因为在1954年医学界对此类风险已基本上众所皆知。
(二)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根据一般的侵权法规则,即使一种风险是可预见的,被告也并不是对每一个可预见的风险均应负责;如果一种风险发生的概率非常之小,被告可以合理地忽视一个非常遥远的风险而不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在预防措施之成本非常之高的情况下。(67)被告的注意程度是与风险程度基本上是成正比的。一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发生后所带来的后果越小,被告越有道理不去采取进一步的避免风险发生的措施。反之亦然。(68)这一原则在医疗责任领域同样适用。正如Jacobs法官在Battersby v.Tottman案(69)中所言:“在风险的程度和注意义务,特别是注意标准,之间存在一种清晰的关系。任何拟行的治疗措施所涉及风险越大,医疗执业人员在决定诉诸此种拟行治疗方案之前就应越加谨慎和勤勉地去权衡和考虑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在Glasgow Corporation v.Muir一案(70)中,Macmillan法律议员亦言道:“那些参与到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手术中的人必须采取一些若是参与到通常日常生活的人则不会要求他们去做的预防措施。”因此,如果一位麻醉师处置的是一种高度易燃的物质,而他知道手术室中静电火花可产生的危险,他必须相应地负很高的注意义务,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对患者造成伤害。(71)
在衡量医疗人员行为的合理性时,风险的严重性是一个重要的砝码。HIV感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提升血液提供者注意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72)一些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虽不大,但若一旦发生所带来的后果异常严重,这种严重的风险后果也会使法官的价值判断发生倾斜。在Reynolds v.North Tyneside HA一案(73)中,一位母亲因生孩子而住院,当时存在着一种脐带脱落的风险。此种风险被界定为“低风险”,只有1比250~500的发生率。但是风险潜在的后果却非常严重,它会导致婴儿低氧症进而导致死亡或大脑损害。在本案中,不幸的事情真正发生了。孩子因严重的脐带脱落导致了大脑瘫痪。原告起诉助产士,称其面对这种可预见的风险未能采取即时的阴道检查。被告则辩称,脐带脱落的风险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可以完全被忽略。但是此案的Gross法官并没有同意被告的意见。在法官看来,虽然天平的一边是脐带脱落的低风险,但是天平的另一边则是沉甸甸的风险发生可带来的严重后果,天平向何处倾斜可想而知。另外,在本案中,天平向不利于被告的一边倾斜的因素还有阴道检查是一件非常简单且很便宜的事情。“实施即时的(阴道检查)的简单易行和经济(低成本)”也使得完全忽视风险存在而不采取此种预防风险发生的措施变得不再合理了。
(三)采取预防措施避免风险发生所需的成本和代价
采取预防措施避免风险发生所需的成本和代价是衡量医疗人员不采取此种预防措施而对风险听之任之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如果剔除风险的行为所带来的成本并不高、简单易行且不会带来不利益,一个合理的人是不会去忽视一个风险的存在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风险。(74)如在Coles v.Reading and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一案(75)中,法院就判定被告没有给患者提供抗破伤风注射的行为存在过失,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简单的预防措施,而患者感染的后果则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如果剔除一种风险隐含着巨大的成本和困难,一个合理的人更有理由去忽视风险的存在而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Hardaker一案(76)中,Burnton法官就认为,被告未能利用其“毫无疑问有限的资源”来致力于治疗原告较为罕见的疾病并非是过失。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采取预防措施是合理地、客观地需要的话,被告的财力不支并不能形成有效的抗辩理由。比如,在PQ v.Australian Red Cross Society一案(77)中,McGarvie法官就认为,如果客观上需要被告采取措施来避免原告从血液制品输入中感染HIV,被告实际上是否存在或缺乏这样的资源并不是与考虑预防措施可行性相关的因素。
(四)被告行为的目的/助益/社会价值
被告行为之目的/益处是评估被告行为合理性的一个考虑因素。目的在于挽救患者生命的行为会更有可能使冒险行为合法化。(78)医疗行为对患者所带来的益处越大,法律对风险漠视行为的容忍度就越高,哪怕是较大的风险。在Battersby v Tottman一案(79)中,一位医生给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开了非常高剂量的药物。此种药物会导致严重的和永久性的眼部损害。但是该医生认为如果不予治疗该患者会有自杀的危险,药物对患者的益处超过它所带来的风险。法院认同了医生的看法,而认定医生明显超过正常建议剂量开药的行为并不存在过失。
七、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不具有终局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2003年1月6日)中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申请和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
医疗事故鉴定只能作为法院审查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
依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医疗机构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失的证据。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专门的鉴定机构对医疗单位所致损害事件进行技术鉴定所作的认定意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属于证据材料,如果对其进行归类的话,属于民事证据材料七种中的鉴定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第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申请和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可见该通知也是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属于证据材料,在证据的分类上属于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人民法院依证据规则审查属实后可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它是专家证言,是民事诉讼证据之一,因而是案件的事实范畴,而不是法律范畴。既然它是事实范畴,那么,法官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就应有权进行审查。法官对鉴定结论有审查权,可以依据审判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另行组织专家鉴定组重新鉴定。
注释:
①Thompson v.Smith Shiprepairers [1984] QB 405 at 416,per Mustill J.
②Bolam v.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 [1957] 1 WLR 582.
③Bolam v.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 [1957] 1 WLR 582,586,McNair J
④Bolam v.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 [1957] 1 WLR 582,586,McNair J.
⑤Bolam v.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 [1957] 1 WLR 582,588,McNair J.
⑥Hunter v.Hanley 1955 SLT 213 at 217. 此段论述也得到了英国上议院的认可。参见Maynard v.West Midlands RHA[1984]1 WLR 634,638; Sidaway v Bethlem Royal Hospital Governors [1985] 1 All ER 643,660,per Lord Bridge.
⑦Bolam v.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 [1957] 1 WLR 582,587,McNair J.
⑧Roe v.Minister of Health [1954] 2 Q.B.66,83,86.
⑨Whitehouse v.Jordan [1981] 1 All ER 267,[1981] 1 WLR 246 (HL); Maynard v.West Midlands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1984] I WLR 634; Sidaway v Bethlem Royal Hospital Governors [1985] 1 All ER 643; Bolitho v.City and Hackney HA [1997]4 All ER 771.
⑩Chin Keow v.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67] 1 WLR 813 (PC).
(11)Gold v.Haringey HA [1987] 2 All ER 888,894 (CA).
(12)Marshall v.Lindsey County Council [1935] 1 KB 516 (CA).
(13)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v.McDaniel (1934) 152 LT 56.
(14)Sidaway v.Governors of the Bethlem Royal Hospital [1985] AC 871 (HL),at 881,per Lord Scarman.
(15)Whitehouse v.Jordan [1981] 1 WLR 246 (HL).
(16)Maynard v.West Midlands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 [1984] 1 WLR 634 (HL).
(17)Sidaway v.Governors of the Bethlem Royal Hospital [1985] AC 871; [1985] 1 All ER 643 (HL).
(18)此外,还有Keith法律议员。
(19)Gordon v.Wilson [1992] 3 Med LR 401,426 (Court of Session).
(20)Whitehouse v.Jordan [1981] 1 WLR 246 (HL).
(21)Maynard v.West Midlands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 [1984] 1 WLR 634 (HL).
(22)Fleming,The Law of Torts (9th ed.1998),p 121.
(23)Kennedy & Grubb,Medical Law (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 430.
(24)Fleming,The Law of Torts (9th ed.1998),p 121.
(25)Anderson v.Chasney [1949] 4 DLR 71,85 (Man CA); aff'd [1950] 4 DLR 223 (SCC).
(26)Lloyds Bank v.Savory & Co [1993] AC 201,203; Edward Wong Finance Co Ltd v.Johnson,Stokes and Masters [1984] AC 296;Roberge v.Bolduc (1991) 78 DLR (4th) 666 (SCC).
(27)比如 ,Florida Hotels Pty.Ltd.v.Mayo (1965),113 C.L.R.588,at pp.593,601.
(28)Albrighton v.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 [1980] 2 N.S.W.L.R.542,at pp.562-563.在此案中,法院认为,“如果所有或者大部分悉尼的医疗执业人员都会习惯性地不采取一种可及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对患者可预见的伤害风险,那么就没有医疗人员会被认定为过失。上述说法不是法律。”
(29)F.v.R.(1983)33 S.A.S.R 189.在此案中,一位妇女接受了一种绝育手术—输卵管结扎术,但未成功而怀孕,她起诉医生未能向她警示此种手术的失败率。
(30)Rogers v.Whitaker (1992) 175 CLR 479 (HCA).
(31)Mason C.J.,Brennan,Dawson,Toohey and McHugh JJ.
(32)Sidaway v.Governors of the Bethlem Royal Hospital [1985] AC 871,at p.893,per Lord Diplock.
(33)Gover v.South Australia (1985),39 S.A.S.R.543,at p.551.
(34)Naxakis v.Western General Hospital,[1999] HCA 22; (1999) 162 ALR 540.
(35)Naxakis v.Western General Hospital,[1999] HCA 22,per Gaudron at [18] and [19].
(36)Reibl v.Hughes [1980] 2 SCR 880 (SCC),at pp.894-895; (1980) 114 D.L.R.(3d),at p.13.
(37)Lowns v.Woods [1996] Australian Torts Reports para 81-376 (NSW Ct App).
(38)Bolitho v.City and Hackney HA [1998] AC 232 (HL); [1997] 4 All ER 771.
(39)对此,Slynn、Nolan、Hoffmann 和Clyde法律议员持同意意见。
(40)Hucks v.Cole[1993]4 Med.L.R.393.
(41)Edward Wong Finance Co.Ltd.v.Johnson Stokes & Master[1984]A.C.296.
(42)Malcolm Parker,Chinese Dragon or Toothless Tiger? Regulating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Journal of Law and Medicine,Volume 10,February 2003,285-295,at 294.
(43)Rogers v.Whitaker (1992) 175 CLR 479 (HCA); Lowns v.Woods (1996) Aust Torts Reps 81-376 (NSWCA); Naxakis v.Western General Hospital (1999) 162 ALR 540 (HCA).
(44)Reibl v.Hughes [1980] 2 SCR 880 (SCC).
(45)Marriott v.West Midlands HA [1999] Lloyd's Rep Med 23.
(46)Anderson v.Chasney [1949] 4 DLR71,85 (Man CA); aff'd [1950] 4 DLR 223 (SCC).
(47)Hucks v.Cole (1968),[1993] 4 Med LR 393,397.
(48)Paris v.Stepney Borough Council [1951] QC 367,382,per Lord Normand; Morris v.West Hartlepool Steam Navigation Co Ltd[1956] AC 552,579,per Lord Cohen.
(49)Anderson v.Chasney [1949] 4 DLR71,86-87 per Coyne JA (Man CA); aff'd [1950] 4 DLR 223 (SCC); Chapman v.Rix (1959)103 SJ 940 per Morris LJ (CA).
(50)ter Nenzen v.Korn (1993) 103 DLR (4th) 473,506 (BCCA); aff'd (1995) 127 DLR (4th) 577 (SCC).
(51)Murphy v.Wirral HA [1996] 7 Med LR 99,104; El-Morssy v Bristol and District HA [1996] 7 Med LR 232,240; Wiszniewski v.Central Manchester HA [1996] 7 Med LR 248,254,262.Also see Code of Guidance on Expert Evidence,Civil Procedure (2003,Sweet & Maxwell),vol 1,35PD and 35.16.
(52)Hills v.Potter [1983] 3 All ER 716,728,per Hirst J.
(53)De Freitas v.O'Brien [1995] 6 Med LR 108.
(54)Morton v.William Dixon,1909 SC 807 at 809.
(55)Baker v.Suzuki Motor Co (1993) 17 CCLT (2d) 241.在此案中,一位遵守行业普遍的设计标准的生产商被认定为行使了合理的注意。
(56)Doern v.Phillips Estate (1995) 2 BCLR (3d) 349,on appeal (1998) 43 BCLR (3d) 53 (BCCA).在此案中,尽管警察关于追赶超越车辆的政策本身并不设定注意标准,但是未遵守此政策却是决定注意标准是否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57)Stones v.GKN [1968] 1 WLR 1776 at 1783,per Swanwick J.
(58)Thompson v.Smith Shiprepairers Ltd [1984] QB 405,at 415,per Mustill J.
(59)Stones v.GKN [1968] 1 WLR 1776 at 1783,per Swanwick J.
(60)Stones v.GKN [1968] 1 WLR 1776 at 1783,per Swanwick J.
(61)Thompson v.Smith Shiprepairers Ltd [1984] QB 405,at 416,per Mustill J.
(62)Dwan v.Farqubar[1988]1 Qd R 234(1983年的输未经检测的血的行为不存在过失);Walker Estate v York-Finch General Hospital(1999)169 DLR(4th)689(Ont CA)(在1984年末在献血中心未能使用有关AIDS的专门小册子,存在过失)。也可参见,Robb Estate v Canadian Red Cross Soc(2000)1 CCLT(3d)70.
(63)Sulco Ltd v.E S Redit & Co Ltd [1959] NZLR 45 at 88 (CA).
(64)Edward Wong Finance Co Ltd v.Johnson,Stokes & Master (a firn) [1984] AC 296 (PC).
(65)Brown v.Rolls Royce[1960]1 WLR 210(HL).在此案中,原告得了皮炎,他诉称此病是因在工作中其雇主(被告)未提供防护性乳剂而接触油所致。法院认为,被告未提供防护性乳剂以避免皮炎的做法并不存在过失,尽管它有违于行业的通常做法,因为医学上对于此种做法的效果存在重大分歧。
(66)Glasgow Corporation v.Muir [1943] AC 448,456.
(67)Grits v.Sylvester (1956) 1 DLR (2d) 502,511 (Ont CA); aff'd (1956) 5 DLR (2d) 601 (SCC); Darley v.Shale [1993] 4 Med LR161,168 (NSWSC).
(68)Roe v.Minister of Health [1954] 2 QB 66.
(69)Bolton v.Stone [1951] AC 850,863,per Lord Oaksey; Overseas Tankship (UK) Ltd v.The Miller Steamship Co Pty Ltd (The Wagon Mound (No 2)) [1967] 1 AC 617,642.
(70)Read v.J Lyons & Co Ltd [1947] AC 156,173,per Lord Macmillan
(71)Battersby v.Tottman (1985) 37 SASR 524,542.
(72)E v.Australian Red Cross Society (1991) 105 ALR 53,77 (Aus Fed CA) per Sheppard J.当然,这一说法也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限制。比如是否具有检测HIV的方法。在上述案件中,被告在诉讼中并没有失利,原因在于当时(1984年)并没有专门检测HIV的方法(此种方法直至1985年3月才出现),因此被告无法采取措施来避免HIV感染的发生。另一个限制因素可能是血液使用的场景。为了挽救生命而实施的输血会使风险承担增加些合理性。
(73)Reynolds v.North Tyneside HA [2002] Lloyd's Rep Med 459.
(74)Overseas Tankship (UK) Ltd v.The Miller Steamship Co Pty Ltd (The Wagon Mound (No 2)) [1967] 1 AC 617,642; Chin Keow v.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67] 1 WLR 813 (PC).
(75)Coles v.Reading and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1963) 107 SJ 115.
(76)Hardaker v.Newcastle HA and the Chief Constable of Northumbria [2001] Lloyd's Rep Med 512.
(77)PQ v.Australian Red Cross Society [1992] 1 VR 19,33 (Vict SC).
(78)Watt v.Hertfordshire County Council [1954] 1 WLR 835.
(79)Battersby v.Tottman (1985) 37 SASR 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