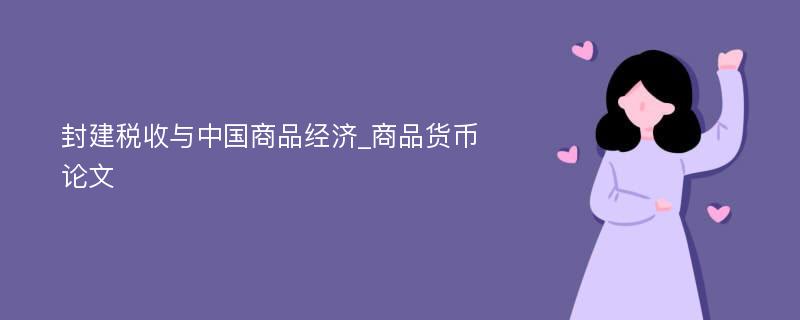
中国封建赋税与商品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税论文,商品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封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2)01-0051-09
在1999年夏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刘志伟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封建贡赋的基础之上,呈现出贡赋经济体制下的商业繁荣。2000年我在一篇论文①中引申他的观点指出:消费需求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三大基本消费群体,即具有贡赋收入的封建国家,具有地租收入的封建地主,和具有生产收入的农民。他们的消费需求共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他们的作用却是各不相同的。从秦汉到唐代中叶,封建国家通过贡赋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主要由贡赋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所拉动。唐代中叶至明代中叶,地主制经济有长足发展,地租总量大大超过赋税总量,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主要由地租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所拉动。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农民的商品生产普遍发展,他们的消费需求日益扩大,遂与封建国家、封建地主的消费需求一道,大致形成了一种“三分天下”的格局,共同拉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观点都是需要具体论证的。本文拟先对秦汉至唐代中叶封建赋税拉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作点粗略探讨。
一
国家政权的存在有赖于赋税,组织财政收入是赋税的主要任务。秦汉至唐代中叶,地主制经济不够发展,全国耕地主要掌握在自耕农手中。他们是封建赋税主要的征课对象。封建国家通过征课贡赋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巨额的贡赋收入形成庞大的有效需求。皇室、贵族、官吏、士兵以及由他们供养、为他们服务的各色人等,以通过赋税分配和再分配所获得的收入,与工农业生产者(包括从事商品生产的地主和商人)的生产品相交换,拉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市场是商品经济的主体部分。封建赋税拉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从发展商品市场的丰度、广度、容量和功能上表现出来。首先从提升商品市场的丰度来考察,市场丰度是指投入市场的商品总量、结构与质量。商品总量增加,商品质量提高,商品结构优化,标志着市场丰度的提升,是商品市场发展的中心内容。
从秦汉至唐代中叶,封建赋税制度及其演变,是提升商品市场丰度的重要机制。秦汉税制以税人为主,税产为辅;征货币为主,征实物为辅。汉代,田租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成年人出算赋,人百二十钱,未成年人出口赋,人二十三钱。成年人不服徭役则出钱代役,“钱月三百”。这在汉武帝时成为定制。农民需要出卖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以交纳赋税。正如《盐铁论·本议》所说:“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当时他们出卖的产品主要有粮食,晁错说:“当具有者半价而卖”②,就是指出卖粮食。其次是纺织品,“众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③。汉武帝实行均输时,也“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④,与民为市。当时农民纺织绢帛尚不普遍,主要是纺织麻布。此外还有禽畜果蔬之类。如《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彘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汉代以后,货币赋向实物赋演变。先是西汉元帝时,贡禹曾建议“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⑤,未被采纳。东汉章帝时,尚书张林建议“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⑥,短暂施行后作罢。这都是由于征调布帛条件尚不充分的缘故。降至曹魏,始行户调,“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⑦。曹魏统治的黄河流域地区,是丝织品传统产地,所以有条件实行绢帛征调。西晋继续户调绢绵,东晋及南北朝则调绢与布。隋至唐代前期,改户调为丁调绢绵布麻。唐代是丁调绢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绢者调绵三两,输布者调麻三斤。丁岁役二旬,不服役收庸,每日三尺。自曹魏之后,绢布成为封建国家实物征课的重要物资。
在征调布帛的同时,布帛又成为货币。布帛是民生必需品,早已成为商品。由于它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民间已将它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赋予它一定的货币功能。王莽时“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布帛开始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东汉末,谷帛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主要货币。曹魏更以“谷帛为市”。两晋南北朝并出现绢帛排斥其他实物与金钱兼行为币的明显趋向。到唐代,封建政权多次申明,对绢布绫罗丝绵诸物在市场交易中,“令钱物兼行,违者科罪”。布帛的法定货币地位始终稳定。从汉至唐,货币赋演化为实物赋,布帛更成为货币,实由金属矿开采不足,通货短缺之故。征帛实际是征币,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回归自然经济。封建国家征调的大量绢布,除直接使用一部分之外,大部分是要进入市场的。征调布帛与布帛货币化相配套,更加增了布绢与市场联系的必然性。
汉代农民为了交税出卖谷物布帛禽畜果蔬之属,随家所有,品种数量都是不确定的。曹魏之后,布帛作为附加值高的产品,需要依户或丁按一定数量交纳与国家。并且随着人口增加,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交纳布帛的总量也会增多。汉武帝时,收入“均输帛五百万匹”,《史记》大书特书,称连同租粟收入,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唐玄宗天宝间,据杜佑估算,每年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大量的绵与布尚不在内。与汉代相比较,赋税制度演进的本身,就推动着商品市场丰度的提升。
但是,提升商品市场丰度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赋税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当时皇室、贵族、官吏等都居住在城市中。他们的消费需求主要靠把商品从各地农村运向城市的贩运贸易来满足。地区间的贩运贸易是当时商品市场最重要的贸易。由于皇室、贵族、官吏等人既有充足的支付能力,而且其消费需求弹性也小,因此,从秦汉以至隋唐,民间贸易、特别是农村贸易相对地不甚发展,而立足于贩运贸易的城市商业却始终表现繁荣。如南北朝时期的刘宋,农村商业是“一夫躬稼,则余粮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城市商业是商贾“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⑧,形成鲜明对照。
皇室、贵族、官吏等人的消费,既有生存资料,又有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后者大都是贩运商品。在汉代,“山西饶材、竹、榖、緯、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毡裘、筋角、铜、铁”。这些土特产品都“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⑨又如,“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毡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⑩。这些著名的贩运商品,大都是自然产品,是气候和土壤多样性所形成的自然产品多样性。当时的贩运贸易就主要是建立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地区分工的基础之上。
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就发生变化。天宝初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的韦坚,曾“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运送京师,供皇室、贵族、官吏消费。天宝二年,他用赋税和义仓粟采购了如下一批“轻货”:“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广运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背栿上堆积广陵郡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蚒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11)。韦坚的这个“轻货”货单,实际上就是当时皇室、贵族、官吏所需贩运贸易商品的货单。
到唐代,茶已成为重要贩运商品。饮茶之风,起于东晋,至唐始盛。唐以前,茶主要采自野生,至唐才真正成为人工培植产品。茶产于南方江淮一带,商人贩运销售各地。虽有“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2)的说法,但主要是流向城市。有人说,开元以后,“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13)。特别是质优价高的茶叶,当然更是销往城市。
这些贩运商品与汉代相比较,茶、茶釜、茶铛、茶碗、名瓷,为汉代所无。锦、绫衫段,官端绫绣、罗、吴绫、绛纱、方文绫等,标志着丝织品品种、质量的升级。与汉代大多是自然产品不同,这些产品又大多是附加值高的加工产品,更标志着产品结构的优化。这都说明,无论在贩运商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商品结构上,从汉至唐,商品市场的丰度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二
其次是扩展了商品市场的广度。商品市场的广度是指商品市场的空间范围,特别是指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空间范围。因此,国外贸易及少数民族地区、边郡等松散、单向的贸易联系均不拟涉及。
汉代的基本经济区主要在黄河流域,即《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西、山东、龙门碣石北等地区。而所谓江南地区,即长江流域的地区,经济落后,尚待开发。“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14)。因此《史记》所说,“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尽笼天下之货物”,实际上主要是指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商业活动。东汉特别是东晋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商品市场的发展遂亦步亦趋地向南推进。下面通过几种重要贩运贸易商品来加以考察。
汉代“千里不贩籴”,粮食尚未进入长途贩运贸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和地方驻军的增加,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粮食逐渐成为重要贩运贸易商品。如以南朝刘宋时为例,当时江南地区开发之后,粮食生产发展,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15)。所以刘宋大将吴喜到荆州作战,“从西还,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16)。加以庶族地主开始发展,拥有大量谷物地租。元嘉时大旱,徐耕以米千斛助赈。他所在晋陵郡,“虽弊犹有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陈积之谷,皆有钜万”(17)。娄湖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也向刘宋朝廷“献钱千万,谷万斛”(18)。这都为粮食贩运贸易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人说“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19)。各朝京师供应,大都由漕运粮食解决。粮食贩运贸易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州郡所属大中城市。这种情况至唐五代犹然。如唐开元以前,长安和东都洛阳所需粮食,主要是漕运河北、河南和江淮租粮供应。各地地主通常是“船载麦,溯流诣州市”,或“舂谷为米,载诣州市货之”(20)。
粮食和籴亦兴于此时。北魏太和间,接受李彪建议,用州郡常调和京师度支岁用之余,年丰籴粟于仓,以备水旱。明帝时,“自徐扬内附之后,收纳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21)。至东魏迁都于邺之后,“常调之外,逐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充国储”(22),和籴遂成为常典。唐代更有大规模和籴,下面将予讨论。
绢帛也是重要贩运贸易商品。战国以来,黄河流域是传统桑麻之地。西汉时,齐“宜桑麻”,鲁亦“有桑麻之业”(23)。“蜀汉之布与齐鲁之缣”(24),是当时著名产品。东汉时,陈留襄邑又成为重要绢帛产区,“襄邑俗织锦,钝女无不巧”(25)。同时蜀锦取代“蜀汉之布”成为市场名品。“江东列代尚无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26)。蜀汉就靠外销蜀锦以支付军国开支。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27)。
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土分裂,战乱频仍。但丝织品为国课所系,仍继续发展。黄河流域继续保持传统优势。“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罗绫之工,大优于江东也”(28)。颜之推此说也透露了南方丝织品已在发展。南朝刘宋时,荆扬二州“丝锦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9),此语虽嫌夸大,但绢帛生产发展却是事实。江南地区户调本来以布不以绢,此时浙东蚕桑之区已开始调绢。“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此”(30)。刘宋时大吏孔觊的两个弟弟,“请假东还”,“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士流”亦作“贾客”(31)。这都说明绢帛市场在长江流域的扩展。
唐代是中国丝织品大发展时期,在北方,河北、河南两道仍是重要产区,并呈向西扩展之势。开元天宝间,“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32)。在长江流域的江南、江淮地区,丝织品生产突飞猛进,呈后来居上之势。唐前期长江下游18个州进贡的丝织品已达19种,唐后期更达到38种(33)。越、宣、扬、润诸州的发展尤为突出。这在韦坚所运“轻货”中即有反映。天宝之后,唐皇朝已是“辇越而衣,漕吴而食”(34)。到大历年间,浙江东道,“风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35)。这里已是“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蚕税鱼盐衣食半天下”(36)。汉代以来丝织品生产的发展,当然包括官手工业、私营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作用在内。但农民生产应属主要部分,特别是普通的绢帛。北魏以至隋唐都实行均田制,保证了农民的桑田;隋唐以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走向松弛,这都有利于农民发展丝织品生产。同时,封建国家征调实物的资源配置机制与绢帛货币化的经济激励机制相结合,也有利于推动绢帛生产的发展。就是在唐代实行两税法之后,由于封建国家需要绢帛,加以通货不足,“货轻钱重、征税暗加”之弊始终无法解决,税钱折收实物势在必行。终唐之世,两税折纳实物的情况有增无已。钱谷两色实际上已成为钱、谷、帛三大色。封建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使农民生产绢帛的作用仍在继续,一直到五代都是如此。
据陆羽《茶经》记载,唐代茶叶生产已遍及江南、淮南、四川等地。江北蕲黄舒寿各州,江南润常宣歙各州,江西袁吉各州均产茶,即所谓“江夏已东,海淮之南皆有之”(37)。茶叶贩运贸易大盛。江淮间,“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38)。如在祁门,“编籍凡五千四百余户”。“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税,悉恃此”。“每岁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39)。
在地区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贩运商品增多,商品市场的空间范围更有长足发展。唐代贩运商品,盐铁为禁榷之物,可不予论列。粮食、绢帛、麻布、茶叶之外,“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瓶,端溪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40)。贩运贸易的空间范围是:“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谐闽越,七津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41)。又说:“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谐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州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42)。商品市场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全面推进,实为这一时期市场一体化最重大的成就。
三
再次,增加了商品市场的容量。市场容量是指市场的接纳能力,可以用市场成交商品的总价值量来表现。赋税决定有支付能力的商品需求总量。赋税总量遂与市场容量呈正相关。这是需要作数量分析的问题。由于文献资料的稀缺,对市场容量作准确的数量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根据能找到的一些数据,从赋税总量的粗略估算中,以推求市场容量。
据桓谭《新论》记载,东汉初年,“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又《后汉书·梁冀传》记载,东汉桓帝时,梁冀被诛,“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这是说,东汉时,封建国家一年的赋税收入总额大约为四十余万万至六十万万铜钱。
唐代天宝年间,据杜佑估算,唐皇朝年收租粮一千二百六十万石,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庸调布与折纳布共约一千六百余万端,另有户税收入约二百余万贯(43)。据《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所提供的物价资料匡算,唐开元天宝间,物价稳定,正常粟价大约在每斗20-30钱上下。元结说,当时“粟一斛,估钱四百犹贵”。如按每斛三百钱计,租粮一千二百六十万石,共约为钱37.8亿钱。当时绢一匹价约400-500钱上下。元结说,“帛一匹,估钱五百犹贵”,如按450钱一匹计,调绢七百四十余万匹,共约为钱33.3亿钱。唐代绵一屯重六两,绵一屯价通常为200钱左右,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共约为3.7亿钱。赋用麻布每端400钱左右(绢一匹为四丈,布一端为五丈,故二者售价相差无几),麻布一千六百余万端,约共为钱64亿钱。加上户税20亿钱。唐天宝间赋税总收入共约为158.8亿钱。与东汉赋税总书入40-60亿全相比,前者为后者的3.97-2.65倍,扣除铜钱购买力的差额,其增长仍应可观。
据《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所收集的粮价资料估算,东汉光武帝时,粮食最低价为每斛一千二百钱至万钱,最高价为数十万钱,非正常粮价,难以利用。东汉桓帝时,无粮价资料。顺帝离桓帝时间较近,其时粮价最低每斛百钱,最高价每斛数千钱。如按最低价计算,租税六十万钱可折粮六千万石。唐天宝间粮价也按最低价加以调整,据《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提供的资料,当时京师粮价最低时为“米斗之价钱十三”,即一百三十钱一斛。租粮收入一千二百六十万石,共约为钱16.38亿钱。加上前述绢、绵、布和户税收入,赋税总书入共约为137.38亿钱。按最低粮价计,共可折粮1.06亿斛,为东汉桓帝时赋税收入折粮的1.77倍。
这些估算无疑都是很不准确的。或可断言,自东汉至唐的数百年间,随着人口的繁殖,耕地的垦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封建国家赋税收入有成倍增长仍是可能的。封建国家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官俸与军费两大项。视具体情况不同而比例不同。汉代是“吏俸用其半”,唐代中叶是“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44)。封建国家的财政支出会转化为两个部分,一是皇室、贵族、官吏、士兵等直接消费的部分。征调来的粮食与绢布都是可以直接消费的。另一部分则经过上述各种人等的手进入市场购买商品。这是形成市场容量的主要因素。皇室、贵族、官吏、士兵等人口粮与衣著的消费有限,并且弹性很小,后者所占的比例总是大大高于前者。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赋税收入增加,如前述直接消费部分与进入市场部分的比例不变,投入市场的部分也是会增加的,从而导致市场容量的扩大。我们可以推断,从汉代到唐代,商品市场容量大致也会有成倍地增长。市场容量是商品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市场广度的扩展,正是市场丰度提升和市场容量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外,封建国家官手工业的产品投入市场,以及盐、铁、酒、茶等商品的禁榷,都可形成财政收入,扩大市场容量。但这些都属于工商业利润,与赋税的性质根本不同,故不予论述。
四
第四,发挥了商品市场的功能。商品市场一经发展,市场的不稳定,如商品价格波动、商品供求关系失调和商品流通阻滞等等,都难以避免。这些都会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封建国家必须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加以解决。赋税是国家进行这种宏观调控的物资力量和经济手段,商品市场的功能也就在这些国家干预中得到发挥。稳定物价是封建国家经常遇到并着力处置的市场问题。汉武帝元封元年,“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这是在首都长安建立一个“平准”机构,接受各地交纳的贡物,和均输官从各地收购来的物品,以及财政部门掌握的其他物资。当市场物价发生波动时,“贵即卖之,贱则买之”,通过吞吐货物,调节供求,以平抑物价,使“万物不得腾踊”,以便把物价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并且企图将其作用向外辐射,以利于“抑天下物”(45)。效果如何,文献记载虽无直接评价,但上述司马迁的行文语气,实含正面肯定之意。
汉代平准主要是稳定市场物价,特别是稳定首都长安的物价,而农村市场物价的波动,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尤为剧烈。南朝刘宋滥铸钱币,通货贬值。继起的南齐,因矫枉过正而实行通货紧缩政策,不敢轻易铸钱,因而“圜法久废,上币稍寡”,以至“农桑不殷于曩日,粟帛轻贱于当年,工商罕兼金之储,匹夫多饥寒之患”(46)。永明五年,封建政权决定实行农产品大采购,以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齐武帝诏书说,“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47)。这是要求以公平价格和现金向农民收购国家赋税所宜、城市所缺的农产品。次年对采购金额和产品品种作出了具体安排。“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绵锦文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南徐州二百万,各于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五百万,郢州三百万,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二百五十万,南兖州二百五十万,雍州五百万,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于所在市易”(48)。这次政府大采购范围广,数量大,品种多。成效如何,缺乏记载。《资治通鉴》说,永明六年,“上以中外谷帛至贱,用尚书右丞江夏李圭之议,出上库钱五千万及出诸州钱,皆令籴买”(49)可能确已实行。这就会比较合理地发挥市场调节供求、分配收入以至配置资源的功能,稳定整个社会经济。
调节物资供求也是封建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唐代至武则天以后,由于边境用兵,官僚机构膨胀,京师宿卫开元间又由府兵改为骑,军粮由士兵自备改为国家供应,粮食消费剧增。原由漕运粮食解决,而漕运路途遥长,水运陆运兼有,“每计其运脚,数倍加钱”,即使如此,河北、河南、江淮各地漕粮“数倍于前,支犹不给”,迫使皇帝要“数幸东都(洛阳)以就贮积”(50)。唐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剧,关中地区尤甚。地主手中掌握大量谷物。加以关中地区连年丰稔。开元二十五年,唐政府遂在关中实行和籴。《资治通鉴》说,“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51)。为了在关中地区大兴和籴,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和军需供应,唐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令“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令“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资课”(52)。天宝八载,又令诸州县“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53)。这都是把租粮改征绢布,在通常用途以外,主要用作在关中和籴的本钱。同时,又令“关内诸州庸调资课并宜准时价变粟取米”(54),即把关中地区征调绢布钱改为征收粟米,以与和籴互补。当时在关中地区实行和籴,与唐中叶后的情况不同,一般不是强行抑配,丰年粮贱时还加价而籴。如开元二十五年在关中始行和籴时,“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万斛”(55)。开元、天宝间的和籴,不但关中地区如此,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如开元二年,规定全国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开元十六年,规定各地“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米”(56)。开元二十九年规定,全国诸州“及时每斗加时价一两钱收籴”。天宝四年规定,在河北、河南诸郡“于时价外另加三五钱,量事收籴大麦贮掌,其义仓亦宜准此”。“诸道有储粮少处各随土宜,如堪贮积,亦准此处分”(57)。在关中地区实行和籴之后,“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58)。至天宝年间,关中和籴已形成制度,“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平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京仓者百余万斛,米贱则少府加价而籴,贵则贱价而粜”(59)。唐政府调整赋税政策,通过折纳、和籴等办法,发挥了市场调节粮食供应关系的功能,既满足了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又保持了粮食市场价格的稳定,使开元、天宝间京师粮价始终保持在一个低廉的水平之上,成效是显著的。封建国家还可以利用赋税作为经济杠杆,以引导某些重要产品生产的发展,如五代南唐的蚕桑生产的发展。“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宋)齐丘说知诰(徐知诰即李)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余税悉输谷帛。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知诰从之”(60)。以后并对勤于农桑者给予奖励,“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61)。这些措施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是江淮之间旷土尽辟,桑拓满野,国以富强”(62)。徐知诰暮年“保有江淮,笼山泽之利,帑藏颇盈”(63)。
五代楚国马殷也是调整赋税政策促进了蚕桑和茶叶生产的发展。首先是改货币税为实物税,以促进蚕桑生产的发展。“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凑”。“湖南民不事蚕桑,(高)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64),还有人说,“机杼遂于吴越”(65)。
更有成效的是促进茶叶生产的发展。五代时各国大都禁榷茶盐。楚国马殷调整政策,让农民自产自销,从而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后梁开平二年)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66)。还有人说:“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户置邸阁居茗,号八床主人,岁入算数十万,用度遂饶”(67)。或说“于中原卖茶之利,岁计百万”(68)。南唐和楚国通过赋税政策的调整,改变了农产品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正是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结果。
五
商品经济包括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封建赋税拉动商品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会拉动商品生产的发展。
《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通都大邑”商人经营的商品有:酤、醯酱、浆、牛羊彘肉、谷、薪稿、船、木、竹、轺车、牛车、漆木器、铜器、素木铁器、栀茜、马、牛、羊、筋角、丹沙、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蘖曲、盐豉、鲐鮆、鲰、鲍、枣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果菜等等。其中许多土特产品,系由各地贩运而来,已如前述。但其中有许多商品,如禽、畜、鱼、果、蔬以及柴、米、酒、醋之类,为城市居民日用所需,须按日供应,需求量大。“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帝都之市,屠杀牛羊日以百数”(69),当时农民的商品生产尚不够发展,单靠农民就难以保证供应,必须由地主组织生产,方可济事。所以《史记·货殖列传》又说,“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栀茜、千畦姜韭。此其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这就是地主大规模组织商品生产的反映。许多事实印证,《史记》所说并非虚构。如汉卜式入山牧羊,“羊致千余头”(70)。西汉末樊重在湖阳广开田土百余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漆桑麻,闭门成市”(71)。东汉陈广汉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另有羊豕鹅鸭果蔬肴蔌无算”(72)。陈留郡“蓝田弥望,黍稷不植”(73)。东吴李衡在“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柑桔千株”(74)。这些都是所谓“牛蹄角千”、“千足羊”、“千亩栀茜”、“千树桔”等等的实证。城市居民生活所需商品,很多是鲜活商品,难以长途运销,需要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因此地主组织的这些农畜产品的商品生产大都位于城市近郊。所以《齐民要术》强调:种葵应是“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种蔓青要“近市良田一顷”。种荽胡要“近市附郭田”,红蓝花也要“负郭田种一顷”。当时贵族、官僚地主发展,许多贵族、官僚地主的庄园邻近城市,所以他们从事农产产品商品生产的人很多。西晋悯怀太子司马遹“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75)。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货之”(76)。潘安仁“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资”(77)。北魏广陵王元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78)。所以晋代江统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79)。
进入隋唐,庶族地主兴起,他们从事商品生产的逐渐增多。唐代汝南卫庆,“家世游惰,至庆乃服田”。后“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他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80)。杜牧堂兄杜诠,“自罢江夏令,卜居于汉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三年后“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于垦荒,不假人一毫之助,而成富家翁”(81)。他们如果只从事自给性生产,而不从事商品生产,是不可能成为“富家翁”的。不但传统的蔬果种植仍在发展,新产品茶的种植也在兴起。陈陶在洪州经营农业,“植花竹,种蔬菜,并植柑桔,课山童卖之”(82)。而九陇地主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庸功者杂处园中”(83)。
中国地主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三结合,可以把最稳妥的生息形式和最大化经济收益揉为一体,具有巨大的财富增殖力量。在三者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从秦汉以至隋唐,它以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84),和地主“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的两条途径发展,并打上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历史烙印。把资本投向商品生产,就是当时这种三位一体的显著特征。“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85)。樊重“善农稼,好货殖”,既广开田土三百余顷,又从事农林渔牧生产,复“假贷人间数百万”(86)。都是这种特征的写照。
结束语
唐代以后,地主制经济发展,封建地租收入向上位移,超过封建赋税而成为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但是,封建赋税也在不断增加,仍然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前述拉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作用仍在继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始终是大中城市商业繁荣的主要支撑。《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一类书籍,就透露了其中消息。同时,封建赋税制度经过重赋轻役和役并入赋入的改革,特别是经过“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以及赋税的货币化,都扩大了自耕农的经营自由,更有利于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总之,终封建社会之世,封建赋税拉动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是不应忽视的。当然封建政权的横征暴敛,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成过危害。但这终究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可点到为止。
[收稿日期]20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