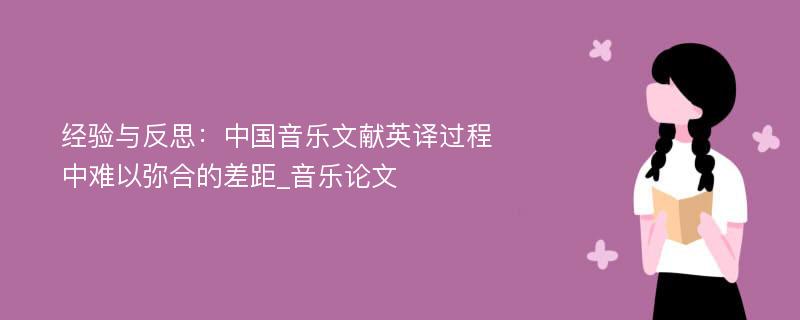
体会与思考:中国音乐文献英译过程中难以跨越的鸿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沟论文,过程中论文,中国音乐论文,文献论文,英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59; 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89(2011)02-0007-09
长期以来,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继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之后,源于西方的学术思潮也成为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动力之一。就音乐学术领域来说,后现代、文本、互文性、语境、局内、局外、双视角、双重音乐能力,等等,这些来自于西方的学术概念对我国的音乐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概念的引入,我国音乐学术的新动力从何而来?应该说,概念的创造是学术发展的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学术成就的标准。概念的广泛流传体现着学术思想的流传与影响,在此方面我国的音乐学术对世界的贡献是有限的,国际影响力也很小。我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者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成了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的基石,也成为了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音乐时最可依赖的文献和研究模版。不仅如此,在中国音乐的研究上也有这种倾向,西方学者的有关中国音乐的研究也成为了中国学者需要参考的理论依据。
中国有着悠久的音乐学术传统,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思想史中有很多是与音乐相关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杨荫浏等学者开创的中国音乐研究成绩斐然。从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史资料的研读、中国音乐考古的发现、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的探讨,这些不仅构成了中国当代学者解读中国传统音乐的途径,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时的主要依据。随着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焦点不仅仅局限在中国自身音乐的研究,也包含西方音乐和世界各国音乐的研究。中国学者已经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思维,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各种研究方法,使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研究的深入,现在我们有了想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愿望。其实,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仅成为中国学者的渴望,也是世界学术界的需求。我们并不奢望让“他们”向“我们”学习,只想相互间的交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交流“只有在双向的流动中才能真正地成为可能”。至此,在把大量的西方学术成果翻译成中文的同时,已有把部分中文的成果翻译成外文的呼声。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探讨音乐文献翻译的理论与方法,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成果。2007年在郑州大学还召开了“外国经典音乐论著翻译出版研讨会”。当然,大部分文献探讨的是外文中译问题,但所提出的理论与问题对中译英也有参考价值。如薛范在其《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一书中说道:“一首歌曲译配得优或劣,主要取决于配歌者的诗词文学功底和音乐修养。在歌曲翻译的领域内,极少发生错译、误译等现象,译品的拙劣大多表现在诗味的欠缺、脱韵、破句、倒字等等方面,也就是说,都属于配歌范畴的缺陷。”[1]
陈然然、杨健著有《音乐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对英语音乐文献翻译理论的思考》一文,文中划分了“艺术派”和“科学派”:
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直译派”与“意译派”、“神似派”与“形似派”、“艺术派”与“科学派”之间的争论。大致说来,这些派别又可以概括为两大派,艺术派认为翻译是艺术,实践中比较重神似,而且大多偏爱意译;而科学派则认为翻译是科学,实践中比较强调形似,大多喜欢采用直译:从实践效果来看,“艺术派”的译文以明白晓畅为特色,容易为读者所喜爱。但是,由于不拘形式的缘故,难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严谨的缺陷;而“科学派”的译文虽以忠实、严谨为特征,但容易出现生硬拗口的弊端,读起来不是十分顺畅。[2]
近几年来,我们在此做了一些尝试,已经出版了《中国音乐术语英译900条》(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Discourse in Music(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文集第五集英文版,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China-Africa Music Dialogue(第二届中非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美国MRI出版社,2011年)也即将出版。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中国音乐辞典的翻译,计划在2011年可完成初稿。通过以上的工作实践,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从工作中得到了一些认识和实际的感受,而其中最主要的感受是把中国音乐文献翻译成英文近乎于跨越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
一、鸿沟的来源
在对西方音乐的研究上,由于学术传统、思维方式和学术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解读和分析相同的材料上可能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如果说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音乐时所提供的是“局外人”的独特贡献的话,中国学者对西方音乐的研究也有着相同的功能。然而,一般的外译和学术性的外译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困难往往并不来自于语言本身,而更多地是来自于对中文原文含义的理解、中文语言表述中的抽象和中文文化背景的缺失,所以,中文才是翻译中难以跨越的“鸿沟”。
1.我们真的理解了中文的含义了吗?
许多年前,我们曾经试图制作计算机作曲软件。软件工程师问:作曲的规则是什么?能否用语言一条条地列举出来?我们列举了一些,但总是不能囊括,囊括就是穷尽,作曲原则是不能穷尽的,所以作品是无限的。计算机作曲是要由人来总结作曲原则,并以编程的方式使计算机能够操作这些原则。问题是人并不能穷尽这些原则,人工智能怎样替代人的艺术创造力?所以,计算机作曲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代替不了人的创造性。
以上的例子是说人要首先了解自己,才能告诉“他者”自己是什么!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从语言的特征上来看,各种语言至少具有四方面的特点:符号、发音、语法和语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书写符号,不同的语音,以及不同的语法结构,这些是不能转换的,但不同语言所表达的语义具有可换性,否则不同国家之间的人际沟通就没有可能性了。所以,所谓翻译实际上是语义的传递过程。在中文外译的过程中,对中文原义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
孔维锋在《语篇层次的音乐文献翻译》中说道:
理解是进行翻译的先决条件。无论进行何种翻译活动,理解原文总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译者要译好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就得在一定的语境中,对由若干个句子组成的语篇进行分析,确定整个语篇的含义,再确定其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的确切含义,然后才有可能动笔进行翻译。[3]
问题是,在许多的情况下中文的含义是模糊的,使得翻译近乎不可能。比如,在相关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文章中涉及到许多古代文献,对文献的解读本身有不同的理解,对其的翻译就显得非常困难。在《周礼·春官·笙师》卷24中记载:“(笙师)掌教吹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舂牍、应、雅,以教械乐。”其中的“械乐”是何意?是否是“器乐”之意?下面的翻译是否符合中文原义?
The sheng master(sheng shi) is in charge of playing yu (big mouth organ),sheng (mouth organ),xun (clay flute),yue (pan pipe),xiao (vertical bamboo flute),chi (tranverse bamboo flute),di (bamboo flute),guan (pipe),chongdu (big wooden box),ying (an ancient barrel drum supported on a stand) and ya (a drum used for dance accompaniment),and to teach instrumental music.
在此翻译中,“械乐”被翻译成“器乐”(instrumental music)。
没有对中文原义的确切理解,翻译将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翻译中首先要深刻理解中文原文。有时候,中文原文本身非常晦涩,无法直译,必须对音乐问题本身进行研究和学习,之后再用英文表达其内涵,这时候,基本上就不是翻译了,而是重新写作。如下文:
《律吕正义》以为:“合黄钟者,为太簇之半律。”意即宫音合黄钟律时,清宫却非清黄钟,而为清太簇。照一般的十二律律制,自宫音(黄钟)至清宫(黄钟半律),不计清宫所合之律(黄钟半律),共得十二律。而康熙所制的律制,自宫音(黄钟)至清官(太簇半律),不计清宫所合之律(太簇半律),即黄钟至大吕半律,共得十四律。[4]
虽然这段文字看起来很晦涩,但仔细阅读还基本上能够理解其字面含义,即当宫音从黄钟开始时,其高八度的宫音(清宫)并不在高黄钟(清黄钟,或黄钟半律)上,而在高太簇上,由此而构成了十四律。问题是为什么高八度的清宫不在清黄钟上,而在清太簇上呢?经过对该条目后面所列举的音分表格的分析发现,原因在于“变徵”音与“徵”音之间以及“变宫”音和“宫”音之间差两律,构成大全音的关系,而非半音关系,由此而多出两律。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当然很难回答,这需要做大量研究,这就使得翻译的困难不在翻译上,而在对中国音乐的这些律制问题的学习上。
2.语义的抽象
所谓“语义的抽象”即指某些作者在写作上比较善用抽象语言,使含义虽有指向性,但并不明确,中外均有很多学者有类似的写作风格。其原因一方面有作者的写作风格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化程度。在学术研究中,当对问题的认识走向深入后,往往会对现象背后的本质性内涵进行挖掘,而这时候,语言会显得力不从心,现有的词汇不足以表达深层的内涵,这时,学者往往会自造某些词汇,形成新的概念。而在阐述这些概念时,由于是深层结构中的内容,在论证上就会显示出抽象性。这类语言,一是不易理解,二是多为体验性,意会性,而非直接表达。中文是如此,英文也是如此。那么,在中英文之间就有了双重性的意会,这样的转换就显得更为困难。如,嵇康有一段名言:“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其中“太玄”指什么?
I watch the swan fly away,I play my wuxian gladly and as my body sways with ease,my mind is touring the Tao.
在此翻译中,“太玄”被翻译成了“道”,因为“道”在国际上是被广泛理解的词汇,属于道家哲学的概念,而“太玄”(Taixuan)对于外国人来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太玄”和“道”也并非完全一致,如果把“太玄”翻译成“太空”(universe)又缺乏了哲学的味道,因为“太玄”本身是一个可体味却不能明确表达的奥妙之词,而英文表达中需要具体的所指对象。所以,如果中文词汇是虚拟的和抽象的,这时的翻译就很难准确表达。
此类的情况更多地发生在曲名、书名等词汇的翻译上。中国传统的曲名多有意会之特点,给人一种感觉,一种导向,如果直译的话就会失去原有的“美感”。如《春江花月夜》,在其词组的构成上有多种可能,即可以是“春江+花月夜”,也可以是“春+江+花+月+夜”,或“春江+花+月夜”,这些在修辞关系上是不同的,名词与形容词的应用关系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春江+花月夜”,英文翻译上可以是:Spring River and Flowery Moon Night。如果是“春+江+花+月+夜”,英文翻译可以是“Spring,River,Flower,Moon and Night”。如果是“春江+花+月夜”,英文翻译上可以是“Spring River,Flower and Moon Night”。虽然在基本的词汇上含有五个词汇,即“春、江、花、月、夜”,但在中国人的心理并没有形成相互间的修辞关系,只有一种感觉,一种美丽的、宁静的、夜晚的、湖水的感觉,然而翻译成英文则许多确定词汇间的修饰关系,是春天的江水,还是春天+江水,这给听众的联想导向和心理暗示是不同的。
有许多曲名可以说是完全不能翻译。如民间乐曲《小开门》,当中国人听到这样的曲名之后会产生一种对民间音乐的联想,曲名的含义更多地指向了乐曲的类别与性质。而翻译成英文后给听众的导向更多地指向了乐曲的曲意与内涵。国外的听众很难从“Opening the Small Gate”一词中看出这是一首民间乐曲,也不能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名称。在传统的曲牌中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如《玉娥郎》、《红绣鞋》、《红纳袄》、《高阳台》,等等,这些曲名几乎不能被其它语言来表述。《将军令》中的“令”是“命令”之“令”,还是“小令”之“令”?如果是前者,其含义是“来自将军的命令”,如果是后者则为“将军的乐曲”。《广陵散》之“散”是何意?“故事”?还是“乐曲”?许多书名也是如此。《风宣玄品》是抽象化的,每一个字中所包容的内涵极为丰富,不可能用一个对应词来表述;《太和正音谱》中的“太和”怎样翻?而《太音大全集》中的“太音”又怎样翻?能否把“太和”翻译成“universal harmany”,而把“太音”翻译成“supreme tones”?这类词汇的翻译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因为词汇中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审美情趣与审美理念,具有一种抽象性的哲理表达,这很难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转述。
在当代中国学者的文献中此问题也存在。在明言的文章《世纪交响——中国新音乐百年奏鸣如是说》① 中有这样一段话:
过度的“创新”、“探奇”,一味的“领风”、“哗众”,未免会导致新音乐的发展进入新奇而不厚重的误区;过分的“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实现自我”,未免会导致新音乐的发展产生“投机”、“奴性”的弊病;一味的“逆反”、“叛逆”,过度的“揭露”、“鞭笞”,未免会导致新音乐的发展陷入尖刻而不厚道的泥淖。
虽然这段话并不晦涩,也比较好理解,但翻译上也遇到某些词汇不好翻译的问题。如其中的“不厚重”、“奴性”是指什么?“不厚道”又指什么?经过反复思考,我们采用了这样的翻译:
Excessive innovation and novelty,or blindly "innovating for innovation's sake" and "seeking attention" will cause new music to become excessively original,but lacking weightiness; excessively "seizing the hour" ,"conforming with trends," and "self realization" will cause new music to become speculative and servile; while blindly rebelling,opposing or excessively exposing flaws or "herding"will cause new music to sink into acrimony and insincerity.
在这段中,“厚重”译成了"weightiness",“奴性”译成了"servile",而“不厚道”译成了"insincerity"。再看此文章的另一段:
笔者以为:以上的视觉符号系统属于“音本体”范畴,对应着的是阐释学的“文本”概念;在此基础之上便生发出“乐本体”范畴,该范畴对应着的是阐释学的“本文”概念。在这个范畴、概念的递进关系理顺以后,便可以引申出音乐艺术的“本体”问题。音乐艺术的“本体”就“存在”于作品乐谱的视觉符号、音乐演绎的听觉音响和听众心灵接受的“三方互动”过程之中。从本质上看,音乐艺术是人类心灵间“互动”的艺术,是作曲家、演奏家与听众心灵间“对话”的艺术。只有通过乐音、音响在时间中的运动,这种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展开。所以,要想把握音乐作品“本体”层面的综合信息,就应当在分析乐谱视觉符号系统的基础上“竖起耳朵”、“打开心扉”。由“觉音”而“悟乐”,再进而“喻理”。
在此段中出现了“音本体”、“乐本体”、“觉音”、“悟乐”、“喻理”等词汇,它们初看起来在中文理解上似乎没有问题,但具体解释起来就会有困难,“音”是什么?“乐”又是什么?“觉”和“悟”和“喻”有什么不同?而“理”是什么方面的“理”,是“乐理”?还是“道理”?在翻译之间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些词汇之间有何不同,然后才能寻找到合适的英文词汇。
In my view,the visual symbol system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sound ontology",corresponding to the hermeneutic concept of the text itself; "music ontology" is conceived on this basis,corresponding to the hermeneutic concept of the meaning of text.Once we have combed through these concepts,we can discuss the ontology of music.The ontology of music "exists" in the visual symbols of the notation system,the acoustics of music interpretation,and reception of the audience.It is a three-sided interactive process.Essentially speaking,music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spirits; it i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composer,performer and listener.This dialogue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sound flowing through time.Therefore,if we want to grasp 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of the ontology of music,on the foundation of analyzing the visual symbols of musical notation,we should listen carefully and open our hearts:first,"perceive the sound",then "understand the music",and finally "comprehend the truth".②
由译文可见,“音”译成了"sound","乐"译成了"music",“觉”译成了"perceive",“悟”译成了"understand",“喻”译成了“comprehend”,而“理”译成了"truth"。不知道这样的译法是否符合作者的意图,但从中可以看出对原文内涵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而学术性文章常常在含义上具有抽象性。在把外文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通常的做法是创造一些新的词汇,随着学术的发展这些词汇逐渐成为了中文词汇中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把中文译成外文的时候,作为非母语的译者很难在外语中创造出能够被母语国家的人能够接受的词汇,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能,但危险性大。所以,音乐文献翻译如果缺乏对音乐学术(即中文之内涵)的理解是不可能进行的。
3.文化的差异
(1)结构性
由于文化的特性,有些音乐术语中所包容的内容不仅具有语义性,而且具有语言本身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来替代的,翻译后必然要丢失。比如,中国的诗词,每首诗词既有词句内容,与此同时,还有格律和文词节奏。所谓格律即包含每个字的平仄格式,也包括每行间的韵脚;而文词节奏即指在词语间的相互组合关系。京剧的唱词是齐字句,以七字和十字为主,而七字的组合方式是2+2+3,即“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的节奏律动关系,而在第三分句中的三个字又分1+2的节奏。如“娘子不必太烈性,卑人言来你试听”,其字词的组合是“娘子+不必+太烈性,卑人+言来+你试听”。中国的曲牌音乐,如昆曲,采用长短句结构,每行间的字数不同,每个字的平仄不同,加之韵的应用,形成了“词谱”。词谱本身是词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词的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体现出了中国诗词的文化内涵,而这些在翻译中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涉及到声乐作品,特别是古代的声乐作品时,翻译只能限定在语义的范畴内。一般来说采用的方法是用音译的方法,另加注释,以表明大意。
(2)词语的不对等
翻译过程中最容易的就是两种语言间有对应的词汇,如:音乐,英文是music;调式,英文是mode,等等。有些词汇在两种语言里含义相近,如中文的“慢板”与外文中常用的“lento”相近。但是,大量的词汇在中英文之间没有对应的词汇。不同的音乐文化往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品种,用独具特色的概念来表示,在其他的音乐文化中由于没有相类似的音乐品种,也就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在这类词汇中,有诸如乐器名,对此基本上没有翻译的可能,也没有翻译的必要。但是,在音乐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由于我国对西方音乐的自觉引入,所以许多西方音乐概念,包括乐器名称等,均已中国化了,其具体体现就是西方的术语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中的不可缺少的概念。如小提琴、钢琴、大提琴、长笛、单簧管、奏鸣曲、歌剧,等等,离开了这些术语,我们似乎不能再谈论音乐了。而当我们说起宫、商、角、徵、羽、移宫、犯调、板式等概念时似乎觉得很陌生。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对于二胡、琵琶、古琴、竹笛、笙等名称来说更是不能形成对乐器的基本想象,所以只有音译还是不行,一般来说要套用国外相类似的乐器,以对乐器进行基本的定性和描述。如把二胡翻译成two-stringed fiddle,琵琶翻译成four stringed lute。Fiddle是弓弦乐器,two-stringed fiddle说明是一种两根弦的弓弦乐器;lute是抱弹类的乐器,four-stringed lute说明是四根弦的抱弹类乐器。严格说来,这并不是翻译,而是说明。音乐在二胡和two-stringed fiddle或琵琶与four-stringed lute之间并不是对应关系,并不是特指,也就是说two-stringed fiddle和four-stringed lute还可以用到别的乐器上,如板胡、中胡、高胡,或中阮、柳琴等。相比较violin和小提琴,cello和大提琴,piano和钢琴就不同了,它们之间是对应关系,没有别的含义,也不可能有另外的指向。这是西方音乐国际化的一种体现,中国音乐和世界其他各国的音乐都不能与之相比。由此也造成了翻译上的无奈。
如果说乐器名还可以解释的话,有些词汇就基本上无从入手了。比如曲牌、声腔、律吕、黄钟、阿口、板眼,等等,这些词汇体现着中国音乐的精髓,然而在英文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英文说起来即no equivalent。如果单纯是词汇翻译则容易多了,因为可以对其进行解释,如曲牌可以翻译成才“labeled pieces”,是有标签的乐曲。西方没有此类作品,所以读者也不会理解什么是“labeled pieces”。
(3)文化背景的缺失
文章写作是要考虑到“语境”的,语境既含上下文的关系,也含读者对象。中文写作,其读者对象是中国人,写作中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普通常识是无须在文章中交代的,但是当把文章翻译成英文后,假定读者对象变成了外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不一定了解,由此而造成翻译上的许多困难。如在翻译戏曲名《断桥》时就有这样的问题。“断桥”即“断桥残雪”,给中国人形成一幅美丽的想象,然而如果把其翻译成“Broken Bridge”,这会给外国读者造成一种非常可怕的联想。“断桥”,西湖十景之一,并非是坏了的桥,而是残雪覆盖桥的一边,看上去像断了的桥,也象征了天上与人间的两重世界。这种美感如果没有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是很难理解的。在翻译中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加注释是一种方法,但如果说清楚整个故事,注释的量就会非常大,没有了主次之分。下面一段引自萧梅的文章《“樂”蕴于身——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观》③:
无论是南管、冀中“音乐会”、西安鼓乐、十番鼓、十番锣鼓、十二木卡姆、乃至侗族“嘎老”……
其中,作者在提及“南管”、“音乐会”等概念时是假设读者知道这些概念的内涵的,而这些在英文中当然是没有现成的词汇可以用,必须进行解释,如下: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nanguan (southern pipe popular in Fujian province),yinyue hui (folk music society popular in Hebei province),Xi'an guyue (drum music of Xi'an),shifan gu (ten variations drum music popular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shifan luogu (ten variations percussion music also popular in southern Jiangsu),shi'er muqam (twelve suites of muqam),or galau of……
译文中既包括了音译,也包括了意译(括号中的语句即意译),所谓意译实际上是一种解释。这样一来,文章中因为对这类词汇的解释过多,就造成了与文章主题并不太相关的内容过多,过长,所以有时候需用注释的方式。无论怎样,读者阅读这样的文章就会觉得很累,因为有过多的相关背景知识需要预先了解。所以,怎样使得学术性文章翻译后能够阅读得比较轻松是一个很费工夫的工作。
二、翻译中的对策
1.翻译是一种解释过程
对于中文外译来说,翻译是把中文文章翻译成外文文章。表面看来,这是语言的转译过程,但通过上面的叙述可知其中还包含着多种多样的问题,而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文章的阅读对象。如上所述,用中文写作时,论题本身是从中国的学术语境来考虑的,讨论的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和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而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有所贡献。在论证中,对材料的引证主要考虑中国学术界对材料的了解情况,如果是普遍了解的材料往往不在进行赘述,因为该材料已为学术界所共知。所以,论述的繁简是经过作者思考和选择的,而选择中主要考虑读者对这些材料的了解程度。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文献中,如果提及西安鼓乐、江南丝竹等概念往往是不需要解释的,解释了则显得多余。中国的乐器名、乐种名、乐曲名、书名、人名以及乐理术语等,大多是不需要解释的,而这些名称、术语对于国外读者来说却是陌生的。
把文章翻译成外文其目的不是让中国读者有了阅读另一种语言的可能,而是使国外的读者能够读到这些文章,了解中国音乐研究的状况,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所以,翻译后读者对象不同了,原本为中国读者所写的文章要翻译成为外国读者所写的文章,这样一来,单纯地只是从语言到语言的转译就显得不足了,还要对文章进行重新加工。然而,加工后就会与原文产生差异,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忠实原文,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读者的变化。比如,上文所提到的对“断桥”一词的翻译:Duanqiao,broken bridge。在此翻译中,首先用了拼音Duanqiao,以强调对中文原词的认识;broken bridge是直译;之后,为了使读者理解“断桥残雪”之美景又加入了附加性的说明语句:
Duanqiao (broken bridge),depicts a bridge half covered with old snow,giving the impression it is in two pieces.
在此翻译中,强调的主要概念是“Duanqiao”,而把broken bridge放到了括号中,是“断桥”的字面翻译;下叙是对“Duanqiao”的解释,说明了“断桥”由残雪所致。再看下面的语句:
从乐曲的实际分析中可发现有两种调式。一是六字调,相当于[b]E调,绝大多数乐曲用此调演奏,另一种是背调,同[b]B调。
其中,“六字调”是什么?对于学过中国传统音乐的人来说是无须解释的,但是如果把此段翻译成英文就要考虑到“六字调”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是陌生的。这时候所涉及的问题是,是否需要解释?怎样解释?解释后能被理解吗?如果不能理解怎么办呢?请看下面的翻译:
One is based on the six-syllable key equivalent to [b]E major,which is used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tunes.The other system uses the back thumb hole.which is in a key that is equivaleut to [b]B major.
在翻译中,“六字调”译成了"six-syllable key"。这是一种直译,很难被理解。理解“六字调”,必须要解释“工尺谱”。这样在翻译中又加上一段解释文字,如下
Gongche notation,a traditional Chinese notation system,uses seven syllables for the seVen pitches in a Scale:shang,che,gong,fan,liu,wu,and yi,which respectively function as do,re,mi,fa,sol, la,and si."Liu",which literally means "six" in Chinese,functions as the fifth step in the scale."Six-syllable key" refers to the scale that uses "liu" as the tonic.
如果把此翻译再译回汉语,为:根据工尺谱——一种传统的记谱法,七个汉字:上、尺、工、凡、六、五、乙用来代表do、re、mi、fa、sol、la、si七个音符。"liu"汉字的含义是“六”,代表音阶中的第五级。如果该音符为主音,则该音阶为"six-syllablekey",即六字调。这样,译文中就比原文多了一段。所以,音乐文献英译时,一是要忠实原文的直译,另外是翻译中的“重写”,即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必须的解释,以使读者能够对原文有更好的理解。段落翻译时如此,有的时候简短的词汇翻译也需如此。如下例:
音乐会所用的笙为圆笙,17管,11簧,“凡”字不用。
“凡”字也是工尺谱中的谱字,中文很清楚,无须解释,但译成英文后则成为:
The sheng utilized by the Music Association has seventeen pipes and eleven sounding reeds,but among these,"fan"(the fourth step in the gongche scale) is not used.
其中括号中加写了"the fourth step in the gongche scale",译为“工尺音阶中的第四级”,使阅读更加顺畅。这样一来,翻译者在理解中文原文的基础上,主要是站在外国读者的立场上来审视对文字的处理。
黄忠廉在其《变译理论》中把变译界定为“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5]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立场,译者必须懂得和理解两种文化群体中学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哪些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而哪些是不需要的。对于那些不了解到底是汉代在前,还是唐代在前的读者来说,加上确切的年代数字也是必要的。翻译再次超越了单纯的语言问题,进入到了两个学术群体之中。
2.拼音的应用
中国音乐术语在数量上很多,加上乐器名、人名等,在文章中如果都使用拼音的话文章将很难懂,有些国外的学者曾跟我们口头说过,他们不太喜欢看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章,中间出现的拼音太多,不好懂;而如果不用拼音的话会造成中文原文的丢失,看了英文后不知道是哪些中文词汇;如果拼音和英文翻译同时应用则使句子非常长。这看上去又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衡量起来,拼音和解释同时应用对于某些词汇的翻译是最佳选择,即便是使得句子很长,句子看上去很不英文化也只好如此。如“民间工尺七调”,如果只用拼音:minjian gongche qidiao,英文读者是没办法理解的。如果译成:seven folk keys(“民间”译为"folk",“七调”可译为"seven keys"),中间缺了“工尺”;如果译成"seven folk gongche keys",大部分人不会知道其中的"gongche"是什么意思。探究起来,工尺有两种含义,一是工尺谱,是一种记谱法;另一种是“工尺字”,是工尺谱中所用的谱字。“民间工尺七调”中的“工尺”是说运用工尺谱时所产生的七种调高系统,而且是用工尺谱字来标明的。“民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因为昆曲等也用此调名法,所以英文翻译为:The seven-key svstem used for traditional music using gongche notation。再直译成中文为:工尺记谱法应用时所用的传统音乐的七种调高系统。尽管如此,英译文中的"gongche notation"是什么意思仍然没有解释,这样加上一句定语从句:The seven-key system used for traditional music when using gongche notation,a kind of aditional pitched notation。这样,加用了“一种传统的音位谱”一句来解释什么是工尺谱。这种解释还可以更加详细,如下:
The seven modes system used for traditional music when using gongche notation,a kind of traditional pitched notation us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f shang,che,gong,fan,liu,wu,yi as do,re,mi,fa,sol,la,si.
虽然这样的翻译比较清楚,国外读者比较容易阅读和理解,但已看不出来是原文“民间工尺七调”的译文,所以,在译文的开始加用“minjian gongche qidiao”,以使原文概念不丢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词汇的翻译基本上是音译+意译+解释的方式。解释可粗略,也可详细,这要根据具体文章中的具体需求而定,如果没有解释的部分译文是很难理解;但丢失了拼音会使中文概念不确定,特别是对于乐器名的翻译来说更是如此。乐器名如同人名是不能翻译的,但是,只用拼音读者会不理解。如"erhu",到底是乐器,还是什么别的?如果是乐器,是哪类乐器?这时候需要加上必要的解释。解释也是可长可短,根据需要而定。如可以是:erhu,Chinese fiddle(二胡,中国的弓弦乐器);也可以是:erhu,two-stringed Chinese fiddle(二胡,两根弦的中国弓弦乐器);还可以是:erhu,two-stringed Chinese fiddle with a hexagonal sound box covered on one side with snake skin(二胡,两根弦的中国弓弦乐器,有一个六角形的音箱,音箱一边用蛇皮覆盖)。当然,还可以把乐器描述的更加详细,这样一来,二胡一个词就有了一大段的译文,所以,解释部分的详细与粗略应由作者视情况而定。
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可知,中国音乐文献的英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译过程,实际上是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两种学术传统和两种思维方式下的学术“操练”过程。这里借用“操练”一词是因为学术论文写作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述过程,也是学术的研究过程,写作中包含了作者对所研究问题的思考与认识,以及材料的交代、逻辑的推理、陈述的方法、材料间的相互支撑、哪里需要进一步阐述、哪些材料可以引出进一步的问题,而这些在中文与英文间的要求上是不一样的。中文写作中用中文的思维方式,英文写作中用英文的思维方式,在两种思维方式下审视和对应,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操作过程,是一种很好的学术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总结出如下要点:
(1)对专门词汇,如乐器名、书名、理论术语等,用拼音+解释的方法。使用拼音可使中文不会丢失殆尽,增强中文原概念的推广。
(2)强调中文原义的直接翻译,如“红绣鞋”即"Red Embroidered Shoes";“颐和园”可为"Joyful and Harmonic Palace",当然颐和园并非音乐词汇,用在此只为说明翻译上的问题。翻译后从英文的角度来看可能感觉很别扭,不知所云,但却交代了中文原本的内涵,对中文词汇中所包含的内在思维和文化品性的理解有帮助。
(3)增加解释性语句,即对直译的概念和语句进行解释,交代文化背景,阐述这些概念和语句的真实内涵。如在“红绣鞋”的整个译文为:
Hong Xiuxie,Red Embroidered Shoes,the title of a Chinese labeled pice (qupai)。
而“颐和园”可译为:
Yihe Yuan,Joyful amd Harmonic Palace,the Summer Palace of the royal famil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解释类话语在中文原文中是没有的,但对于许多音乐术语来说,特别是乐器名,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解释。
收稿日期:2011-06-10
注释:
① 此文将发表在China-Africa Music Dialogue(第二届中非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
② 本文的初始翻译者为孔维峰。
③ 此文将发表在China-Africa Music Dialogue(第二届中非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