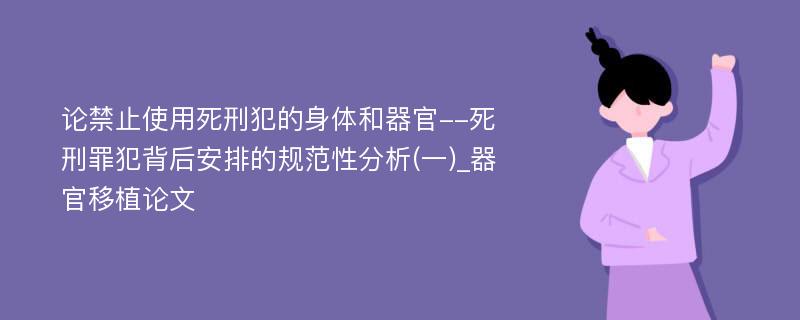
论禁止利用死刑犯的尸体、尸体器官——死刑犯安排身后事的规范分析(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刑犯论文,尸体论文,器官论文,身后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原本没有的,或者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人文、道德的冲突以及公民人权意识的觉醒等等诸多因素,而成为真正的问题,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就是如此。其中,死刑犯的尸体与尸体器官利用问题,则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具体问题。
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对于规范分析来说,确定关键词语、概念的确切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我首先明确几个重要概念。一、死刑犯,是指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人,而无论刑事判决是否已经确定,也不论死刑是否可能或者已经被执行。二、人体器官,是指自然人除血液、精子、卵子、胚胎之外的人体器官和人体组织。三、利用人体器官、尸体,主要是指为了医疗、医学研究以及教学等目的而利用人体(包括死体)器官移植以及利用尸体进行医学教学、研究。器官移植包括活体器官移植和死体器官移植。活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活人的器官,移植给其他急需救治的患者的情形。死体器官移植,是指医生摘取已经死亡人的尸体之器官,移植给其他需救治之患者的情形。另外,尸体、死体、遗体在本文中的含义大致相同,但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略有差异。
现今的中国是否必须立即废除死刑,可能需要成湖的墨水去论证。但是,政府和社会能否利用死刑犯的尸体及尸体器官则是一个范围明确、条件清晰的具体法律规则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不应当使用一瓶的墨水,答案要么是肯定的要么是否定的,且必有对错之分。
在我国,关于死刑犯的人体器官、尸体器官、尸体利用问题,研究文献以及公开、确定的实证资料极为匮乏,这方面的讨论也没有充分展开。(注:我主张在我国全面废除死刑,而且越快越好,明天最好。但是真正深入地探讨进而说服我的同胞,实非易事。但是,一则媒体广泛报道的新闻以及《法制日报》记者随后对我的采访,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此问题,我与十余位法学教授交换过意见,除一名著名法学家坚定而自信地支持我的意见外,其他法学家并不同意我的意见,有的还十分强烈地反对我的意见。随后,我又与许多法律实务者——法官、检察官、律师交换过意见,情况大致相同。鉴于这些讨论均是口头进行,而且话题由我挑起,这些法律家并没有深思熟虑,也许以后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且还有为辩论而坚持意见的因素,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说出他们的名字,只是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从我下面所引用的以及没有引用的媒体报道(特别是记者)的意见以及倾向性意见来看,可以利用死刑犯活体器官、尸体器官、尸体,似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意见(共意),这促使我写下这篇文字。)所以,本文就从一则新闻及其所引发的讨论谈起。应当指出,类似的新闻其实并非仅此一则,这起新闻报道之前已有多起类似报道,不过这一则新闻更为典型、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而已。我没有把握用这么一点点墨水能够说服读者,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本文能够引起读者对于我国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规则体系的疑问,进行细致的规范分析,以及为有效的规范分析进行实证观察以积累知识,避免用粗糙的道德直觉来直接肯定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的做法。
二、一则新闻
《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22日报道,河南濮阳市清丰县一中高三年级学生张红伟去年底患肾衰竭,今年3月28日晚,关押在濮阳市看守所的死刑犯王继辉偶然在当地媒体看到了相关报道,第二天即向看守所申请捐肾。不久,另一名在押死刑犯张玉海也向所里提出了捐肾的申请。4月13日,负责肾移植手术的某医院专家对王继辉、张玉海分别进行了配型化验,结果表明王继辉的血型和抗原、抗体与张红伟的完全相同,基本具备肾脏移植的条件,该院决定为张红伟实施肾移植手术。又据2005年6月1日《法制日报》和6月10日《北京青年报》等报纸的报道,原本定在4月26日就进行的手术,一直没有进行。患者在经济极其紧张、需依赖社会援助的情况下,每天在医院里花着高额的费用等待手术,心急如焚。而呆在监狱里的犯人,也早就做好了随时手术的准备,却一直接不到手术通知。但是,医院最终却接到了来自看守所“叫停”的通知(因有关法院不同意),手术没有实施。
三、专家的呼吁
河南省著名法学专家、中国刑法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刘德法教授认为,我国没有二审诉讼期间死刑犯人捐献器官的先例,缺乏相应的法律条文可供参考,是法院顾虑的主要原因。虽然对老百姓来说,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做,但对公权来说,法律没有规定就说明没有授权。因此,刘德法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刘德法同时认为,有行为能力的犯人有权处理自己的器官。让判决没有生效的死刑犯脱离监管场所去实施捐肾手术,确实存在较大危险,如自杀、自残等。但如果在安全措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死刑犯捐献器官的行为还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对社会有利的。
刘德法说,如果在手术过程中,由于医院在活体肾脏移植时导致死刑犯死亡,也只能按一般的医疗事故处理,与作为监管单位的看守所和手术批准单位的法院没有关系。如果捐肾手术成功,不管捐献者出于什么动机,按照《刑法》有关规定,这种捐献行为都属于重大立功表现,存在二审改判的可能,但并不是必然。(注:《北京青年报》2005年6月10日。)
四、知名律师的意见
北京市从事刑事辩护的知名律师、法学博士许兰亭主张,死刑犯捐献器官应当允许提倡、应当鼓励。
许兰亭认为,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或临刑前提出捐献自己身体的某些器官,如眼角膜、肝、肾等,这种做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应该不存在问题。不论死刑犯的出发点如何,他捐献器官的愿望应当予以满足。在实践中,死刑犯捐献器官的例子很多。与其让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不规范状态继续存在,还不如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对此加以明确和规范,避免混乱状态,避免消极作用。他建议,立法上应明确规定死刑犯自愿捐献身体器官的,应当允许,且要予以提倡和奖励,其亲属有权获得适当报酬。这样规定,有许多积极意义:
一是符合立法精神,刑诉法第212条规定,指挥执行(死刑)的审判人员,对罪犯应当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然后交付执行人员执行死刑。这里的“遗言”,实际上就是死刑犯临刑前对身后事的交待与安排。死刑犯捐献器官实际上也可以视为“遗言”。一般财物可以安排,那么对自己的身体器官作出安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二是既满足了死刑犯的愿望——不管是其真诚悔罪,为社会作贡献,还是其想为家里作点贡献,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又满足了需更换身体器官的病人的需要,挽救了他人的生命。
三是立法上明确规定后,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采取务实态度,做到严肃规范,公开透明,避免私下交易,暗箱操作,接受监督。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我们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实际上,允许并满足死刑犯捐献器官的愿望也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其人权的具体体现,既符合立法精神,也符合人权保障的国际潮流。(注:郭恒忠:“人体器官移植法律缺失法学专家呼吁尽快立法”,《法制日报》2005年6月1日。)
五、记者的困惑
张红伟在医院里苦等,而王继辉也不能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捐肾救命卡壳?一个报社记者百思不得其解。该记者看来,这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搞得如此扑朔迷离,着实让他费解。该记者试图通过采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寻找最后的答案。5月25日,记者拨通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传处王伟的电话。“你们不要报道这件事了,最高人民法院早就有关于死刑犯器官移植的规定。”记者问:“如果是当事人主动提出来捐献器官,也不允许吗?”王伟说:“这个案子还在审理期间,在二审结果还没出来之前,没法说。”(注:《齐鲁晚报》2005年5月27日。这种“困惑”不仅为这位记者心中所独有,其他报社记者也有类似的疑惑。限于本文的主旨与篇幅,仅随机选择了这位记者的困惑,作为媒体和一般民众心中困惑的代表。)
六、法学理论上的不同观点
对死刑犯处决后的尸体器官能否加以利用,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肯定论者认为,在可供移植的器官奇缺的情况下,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能够挽救因器官衰竭濒临死亡的病人,这对死刑犯无任何伤害,对社会和他人有益,可以视为其赎罪的一种表现。否定论者认为,死刑犯可以被剥夺政治权利,但民事权利并没有完全被剥夺,对自己死后的尸体仍然享有处分权;为了保证死刑犯处决后的尸体能有效移植,医务人员往往必须在行刑前对死刑犯的身体作一些处理,而医务人员参与此事,有悖其救死扶伤的天职;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来移植,还有可能促进器官商业化,并引起医务人员和执法队伍的腐败;况且,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来移植,只可一时缓和器官供不应求的局面,反而会使开辟正当器官来源的工作得不到重视。更有否定论者提出,应当绝对禁止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也就是说,不管死刑犯生前是否表示同意捐献器官,也不管其亲属是否愿意,对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一概不能作器官移植用。其主要理由是:死刑犯处于弱势地位,即便是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愿。在笔者看来,死刑犯的尸体也应受到法律保护,死刑犯生前可以作处分决定,其亲属也对之享有一定的权利。而器官捐赠是一种民事行为,对死刑犯也应该适用同样的自愿捐赠原则。如果死刑犯生前不同意死后捐赠器官,或者生前没有作明确表示,被处决后其亲属不同意捐赠器官,就不得摘取其器官作移植用。否则,在不具备紧急避险条件时,就是非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盗取死刑犯的尸体器官作移植用,同样有可能构成盗窃尸体罪。不过,笔者并不赞成绝对禁止利用死刑犯的器官供移植。除了紧急避险时可以利用之外,死刑犯案发前作过真诚捐献器官的承诺,处决前未撤销承诺的;特别是死刑犯提出要把自己死后的某种器官捐赠给正需要移植器官的亲友时,显然没有理由不允许。另外,如果死刑犯主动提出捐献器官(不存在引诱、威逼现象),那么,我们为何又不满足其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真诚愿望呢?(注:http:// www.xingbian.cn/ template/ article.jsp? ID=4770&CID=166829717,刘明祥:“器官移植涉及的刑法问题”,2005年7月15日访问刑辩网。)
七、我的主张
医生为移植器官而摘取活人器官、尸体器官,应该以被摘取人自愿捐赠为原则,不能违背捐献者本人或其近亲属的意愿,否则就是非法的。但是,对于死刑犯来说,即使死刑犯自愿,也不能进行尸体器官移植,更不能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社会,不应当接受死刑犯的器官捐献,未来立法时,应当禁止死刑犯器官移植——无论死刑犯自愿、同意与否,惟一可以考虑的例外情况是,允许死刑犯自愿地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自己的配偶、近亲属。(注:郭恒忠:“人体器官移植法律缺失法学专家呼吁尽快立法”,《法制日报》2005年6月1日。)
八、一个规范文件及其解读
(一)《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
关于死刑犯的人体器官利用问题,法律并无外在的阐明规则——实定的法律规则。但是,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作出《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于本文十分重要,所以抄录其全文作为规范分析的标本和根据。《暂行规定》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卫生厅(局)、民政厅(局):
随着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一些医疗、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单位为进行科学研究或做器官移植手术,提出了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要求。为了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移风易俗,在严格执行法律规定、注意政治影响的前提下,对利用死刑罪犯的尸体或尸体器官问题,特作规定如下:
1.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必须按照刑法有关规定,“用枪决的方法执行”。执行完毕,经临场监督的检察员确认死亡后,尸体方可做其他处理。
2.死刑罪犯执行后的尸体或火化后的骨灰,可以允许其家属认领。
3.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
(1)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
(2)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
(3)经家属同意利用的。
4.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应按下列规定办理:
(1)利用单位必须具备医学科学研究或移植手术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经所在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审查批准发给《特许证》,并到本市或地区卫生局备案。
(2)尸体利用统一由市或地区卫生局负责安排,根据需要的轻重缓急和综合利用原则,分别同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和利用单位进行联系。
(3)死刑执行命令下达后,遇有可以直接利用的尸体,人民法院应提前通知市或地区卫生局,由卫生局转告利用单位,并发给利用单位利用尸体的证明,将副本抄送负责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和负责临场监督的人民检察院。利用单位应主动同人民法院联系,不得延误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法定时限。
对需征得家属同意方可利用的尸体,由人民法院通知卫生部门同家属协商,并就尸体利用范围、利用后的处理方法和处理费用以及经济补偿等问题达成书面协议。市或地区卫生局根据协议发给利用单位利用尸体的证明,并抄送有关单位。
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单位利用的,应有由死刑罪犯签名的正式书面证明或记载存人民法院备查。
(4)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一般应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确有必要时,经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5)尸体被利用后,由火化场协助利用单位及时火化;如需埋葬或做其他处理的,由利用单位负责;如有家属要求领取骨灰的,由人民法院通知家属前往火化场所领取。
5.在汉族地区原则上不利用少数民族死刑罪犯的尸体或尸体器官。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执行本规定时,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惯。
(二)主要规则
《暂行规定》不属于立法,自不待言。虽然《暂行规定》的发布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两个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但是《暂行规定》总体上显然不属于司法解释,因为它没有任何实定之法律作为其解释的根据,即没有法律明示之原则、规则作为其解释的前提。本文将《暂行规定》称之为规范性文件,这是因为它实际上起着规范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的作用。当然,本文将该文件称之为规范性文件,并不是说它就“规范”,相反,仅从形式上看,该规范性文件的条款安排并不规范,所以本文引用该文件的具体规定时笼统地称之为某条款。
综合分析《暂行规定》,该规范性文件具体阐明了以下利用死刑犯的尸体、尸体器官的主要规则:
1.执行完毕死刑后方可利用死刑犯的尸体、尸体器官。根据《暂行规定》,利用死刑犯的尸体及尸体器官必须严格执行法律,主要是必须以法定的方法执行死刑,执行完毕后方可利用死刑犯的尸体或尸体器官,以及为利用而做必要之处理。无论是将《暂行规定》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结合起来分析,还是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结合起来分析,严格执行法律均属于一种原则(具有政策导向的原则,因而也可以称之为政策,而且称之为政策更为适当),严格执行法律的原则(政策)在《暂行规定》中仅仅具体化为以法定的方式“执行完毕死刑后方可利用死刑犯尸体器官”。按照这一规则,先摘取死刑犯的人体器官而后杀死他(“先摘后杀”)或者通过摘取死刑犯人体器官的方法致使其死亡以完成死刑的执行(“以摘为杀”)均被绝对禁止。
2.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犯尸体及其器官可以直接利用。也就是说,“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犯尸体”属于“可以直接利用的尸体”。这一规则可以称为“直接利用规则”。“直接利用”的意义是,利用这类死刑犯的尸体器官、尸体,不受任何单位、个人的干预,惟一需要考虑的是“注意政治影响”、“严格保密,注意影响”之弹性政策要求。
3.死刑犯自愿。自愿,必须有由死刑犯签名的正式书面或记载存于人民法院备案。自愿,乃自己愿意。但是,死刑犯如何会自己愿意,死刑犯所处之羁押环境与医学、医疗环境相去甚远,死刑犯怎样知道有器官移植、尸体利用之医疗、医学需要,是死刑犯偶然地从媒体上看到(像前述那则新闻报道那样),还是法院、看守所、医学医疗机构专门有人告知、提示、引导、教育,如果是后者,这些人员具体怎样去做,才能表明是死刑犯自愿而不是死刑犯同意——自愿与同意显然有重大之差异(《暂行规定》还特别暗示了这一点),并无更进一步的规则。
4.死刑犯家属同意。在这里,将“家属”理解为死刑犯的近亲属,似乎没有问题。联系到《暂行规定》(三)1条款可见,死刑犯的“自愿”表示优先于其家属“同意”,从《暂行规定》的上下文来看,在死刑犯自愿捐献的情况下,法院和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利用单位没有必要就此事通知其家属并同时再取得其家属同意。所以,在死刑犯有自愿表示而其家属不同意的情况下,死刑犯的尸体器官和尸体是可以利用的,死刑犯的个人决定优于其遗属的权利主张。(注:这一规则得到另一则新闻报道的印证,一死刑犯自愿捐肾,但是家人不同意,最后该死刑犯的器官还是被利用。见阎世德、董开伟:“死刑犯器官被捐献家属有无知情权?”《兰州晨报》2003年9月23日。)
5.卫生部门得与死刑犯家属协商。“得”的涵义是:在死刑犯没有作出是否捐献死体器官、遗体的自愿意思表示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既有权力又有义务将意图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之事通知其家属。但是,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必须与死刑犯家属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如果死刑犯家属不同意或者反对,则不能利用死刑犯的死体器官或者尸体。
6.死刑犯家属有权获得经济补偿。这可以视为死刑犯家属之于死刑犯遗体权利的具体内容之一?值得注意。但是按照《暂行规定》的精神,在死刑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情况下,死刑犯家属不能获得补偿。《暂行规定》并没有规定补偿的数额,这可能与我国地域差异性大有关。至于实践中卫生行政部门如何与死刑犯家属协商,怎样“讨价还价”,目前缺乏实证资料,需要法社会学做进一步的观察与分析,从而为规范分析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
7.在汉族地区原则上不利用少数民族死刑罪犯的尸体或尸体器官。这意味着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似乎有什么“不好”的内容,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呢?值得思考,思考的方向可能指向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制度安排的禁止性规定,需要从那些禁止性规定中寻找答案,当然,答案可能并不全部存在于那里,这也需要法社会学做进一步地挖掘。
8.卫生部门刑场摘取死刑犯尸体器官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这是一条禁止性规定,属于确保“严格保密,注意影响”这一弹性政策的硬性规定。
9.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这一规则是针对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而言的。该规则与前一条规则的意义相同,既可以确保摘取手术不为外界干扰而顺利进行,也可以满足“严格保密,注意影响”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暂行规定》规定的仅仅是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而没有规定活体器官捐献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暂行规定》将禁止利用死刑犯活体器官移植作为未阐明的潜在规则呢?回答恐怕是否定的。从《暂行规定》标题和内容的字里行间,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上述新闻中,有关法院之所以叫停活体器官移植,并不是因为有禁止利用死刑犯活体器官的规则,而是在没有规范性文件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认为自己不能贸然行事。
(三)权力与权利的制度安排
在没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法律加以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暂行规定》(四)1至5条款实际上对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的做法进行了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权力与权利的安排。
权力的安排。《暂行规定》(三)1至3条款规定三种死刑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可供利用”的意义有二:一是授权,且授权并无明确的规则限制;二是裁量,是否利用由利用单位(医疗、医学机构)、卫生行政部门、法院三家共同决定。具体包括:
1.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特许利用权,即授权具备医学科学研究或移植手术的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的单位,经所在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审查批准后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
2.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利用统一管理权,即市或地区卫生局负责统一安排尸体利用,并根据需要的轻重缓急和综合利用原则,负责同执行死刑人民法院和利用单位之间的联系。
3.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利用批准权,归执行死刑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同时也负责协调工作。
4.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利用监督权,归执行死刑之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主要是死刑执行完毕,经临场监督的检察员确认死亡后,尸体方可做其他处理。
《暂行规定》关于权力的制度安排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医疗机构和医学科研部门对于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的利用有着更大的积极性,是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利用的主要“受益者”。《暂行规定》开宗明义:“随着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一些医疗、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单位为进行科学研究或做器官移植手术,提出了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要求。为了支持医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移风易俗”——这与国际范围内医学界更热衷于推动脑死亡(标准)立法以及器官移植一致,所以上述最高司法机关、最高检察机关、最高行政主管机关联合发布《暂行规定》决定利用死刑犯的尸体、尸体器官。
二是,上述权力安排表明权力主体之间传统上的同质化、一体化特点。《暂行规定》中有“利用单位应主动同人民法院联系,不得延误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法定时限”、“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的规定,这些规定不仅表明利用单位与人民法院之间发生过或者容易发生矛盾,更重要的表明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利用不仅仅是利用单位自己的事情,也是法院的事情,是上述机关、单位共同的事情。我们前面引用的那则新闻报道说医院已经做好了移植手术准备,在二审法院迟迟不予批准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反映出较强的不满情绪,而有关法院尽管自认为占理却并没有理直气壮地反驳,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在另一则新闻报道中,一位执行死刑的法官关于死刑犯捐献遗体办起来“很劳神”的说法,(注:一位叫孙小钢的死刑犯自愿捐献遗体,但是没有如愿。有记者报道说,据参与执行孙小钢死刑的法官介绍,虽然孙小钢本人写出了愿意捐赠的书面申请,但说起捐赠遗体,程序复杂,“很劳神!”该法官进一步解释道,有时能碰到已经宣判了死刑的罪犯,提出要捐献器官或整个身体,要捐献的话,需要提前很长时间,由看守所上报情况,法院再联系相关部门,有的部门还不太愿意配合。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可能涉及到去询问罪犯最真实的意图,与罪犯家属恳谈,与医疗系统的许多单位打交道,有必要的话,法院还要出面给罪犯进行体检,需要公证的还得办公证,甚至还要跟踪到所捐赠的器官最后到了哪里。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面对死刑犯提出的捐赠要求,法院现在还是选择不做。原因在于:一是法院的职责在于审理、宣判、执行案件,而法规并没有规定法院有处理罪犯捐赠遗体的义务;二是罪犯身体是否适合捐献,是否能找到需要得到捐献的器官接收人,这些都很难说;三是,几年前,也有一名死刑犯想捐献遗体,家属也同意了,法院也努力去联系,结果其他方面联系得差不多了,家属却提出要钱,搞得很不愉快。见郑淳、吴蔚:“死刑犯捐遗体引出法律碰撞”,《华商报》2004年10月22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法院司法独立性的加强,一些法院并不愿意参与利用死刑犯尸体与尸体器官,这也许表明国家司法机关与政府机构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间隔性的加强和关系的疏远,《暂行规定》毕竟是20多年前的规范性文件,能“暂行”到现在着实不易。
三是,《暂行规定》没有任何文字涉及到人体器官移植的分配机制。相反,行使利用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统一管理权的市、地区卫生局,“根据需要的轻重缓急和综合利用原则”负责管理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的利用工作,实际上意味着人体移植网络以地级市为范围,这无助于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至全国范围内形成合理、公平、透明的器官分配网络和分配机制。当然,上海市、深圳市、福建省等省、市已经制定并颁布实施遗体、人体器官捐献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法规在人体器官移植分配网络和分配机制方面的规定尽管依然不够具体细致,但是进展还是有一点的。
家属权利的安排。死刑犯尸体、尸体器官利用规则4.、5.,特别是规则5.,意味着承认死刑犯家属之于死刑犯遗体的权利。至于这种权利包括哪些内容,《暂行规定》的性质与内容决定了它自然不能完全反映,如死者家属以尸体为媒介表达哀思的权利。对于死刑犯尸体的归属,《暂行规定》(二)条款规定:“死刑罪犯执行后的尸体或火化后的骨灰,可以允许其家属认领。”“可以”一词,应当理解为死刑犯家属有权,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实定规则作为保障,《暂行规定》也无进一步的权利保障规则,“可以”又可以被同质化的权力机关、单位自然地解释为,可以“任意”地给尸体或者骨灰。汉语当中的“可以”本来就同时包涵可能、能够与许可、认可两层含义。实际上1984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正确处理死刑罪犯遗书遗物等问题的通知》就早已有同样的规定:依照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55条第5款的规定,将罪犯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罪犯家属可以在限期内领取罪犯尸体或骨灰。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具有强烈血缘伦理观念的死刑犯家属自然会要求领取尸体而不是骨灰。如果死刑犯的尸体器官被利用,尸体会比较(或者很)难看——是比较难看还是很难看主要是死刑犯家属的观感,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法院基于“注意影响”和“注意政治影响”的政策考虑也会倾向于给死刑犯家属以骨灰而不是死刑犯的尸体。所以实际结果只能是,权力机构任意选择给尸体或者骨灰,而不是死刑犯家属要什么给什么。(注:例如,实践中有一例,死刑犯的尸体被利用后,家属要尸体,而执行死刑的法院并未予以满足。目前的死刑执行实践,给死刑犯家属的多是骨灰而不是尸体。阎世德、董开伟:“死刑犯器官被捐献家属有无知情权?”《兰州晨报》2003年9月23日。)值得关注的是,《暂行规定》(三)1条款的表述是否意味着——按照习惯——死刑犯家属有收敛死刑犯尸体的权利?死刑犯的家属可以领回死刑犯的尸体或者骨灰,这是一种“成文规定”(相对习惯而言,《暂行规定》也可以称之为“成文”)如果习惯上认为死刑犯家属有收敛权,那么这一习惯权利与死刑犯家属“可以领回死刑犯的尸体或者骨灰”的权利安排结合在一起,法院执行死刑后就必须满足死刑犯家属的要求,死刑犯家属要求领回尸体的给尸体,要求领回骨灰的给骨灰,死刑犯家属什么都不要的,死刑犯的尸体便成为“可以直接利用的尸体”。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习惯上并不充分重视习惯,习惯规则被承认主要是在民法领域(排在法律、法规、政策之后)和国际法领域,在公法领域,政党、国家、政府习惯上可以基于习惯行使某些权力——有的权力还基于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信仰为不可动摇、不可怀疑,而公民往往并不能基于习惯享有某些不可动摇的权利。在尸体并无医学上的利用价值相反是一种负担、累赘的时候,死刑犯的家属自然可以认领尸体,但是当“有个别人,借机为被处决的罪犯举丧滋事,扰乱社会秩序”(1984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正确处理死刑罪犯遗书遗物等问题的通知》)时,法院便基于政府维护治安的需要以及移风易俗的政策需要,只给骨灰而不给尸体。当然,死刑犯家属可以认领“尸体或火化后的骨灰”仍然有规范意义,这就是对于少数民族死刑犯的家属按照少数民族丧葬习惯要求认领尸体的,应予同意。综上所述,死刑犯家属之于死刑犯尸体的权利是一种弱的权利。
死刑犯之于尸体、尸体器官的权利。首先的问题是,器官捐赠是一种纯粹的民事行为吗?换言之,人们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人体器官吗?随后的问题是,死刑犯可以同普通人一样处分自己的器官、遗体吗?前引知名律师许兰亭博士就是把尸体器官看成是物(似乎与一般、普通之物并无区别),所以死刑犯有权处理这样的物。这应当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人体器官、尸体器官、尸体与一般物、普通物毕竟不同,其物的价值因医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是现代医学科学发展所产生的一个与哲学、伦理学密切相关的法理学问题。
有民法学者指出:
人体器官移植的利用,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及健康,涉及社会伦理及道德问题,国家立法尤其是民法必须进行立法规制。人体器官是特殊的物。从民法角度来看,人体具有特殊的属性,是人格的载体,不能将其视为物。但是,人体器官一旦脱离了人格的物质载体,也就与民事主体的人格脱离了关系,也就不再具有人格的因素了,不再是人格的载体,具有了物的属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能够与人体发生分离的器官定位为物。脱离人体的人体器官,是指从人体分离后,在植入新的人体之前的人体器官。在没有脱离人体之前,人体器官属于人体;在输入或者植入新的人体之后,又成为人体的组成部分,具有了人格。在这个期间存在的人体器官,是物的形态。但是,这种物是否就与普通动产一样,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流通,则值得研究。(注: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参见郭恒忠:“人体器官移植法律缺失法学专家呼吁尽快立法”,《法制日报》2005年6月1日。有学者主张,公民对于自己的人体器官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流通,而且应当买卖。参见黄文艺等:“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法理学讨论”,http:// dzl.legaltheory.com.cn,2005年7月10日访问“正来学堂”网。)
从刑法的角度看,从“活体”摘出肾脏、部分肝脏等器官,有可能触犯故意伤害罪;从尸体上取出死体器官则可能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因此,刑法上需要解决从“活体”中摘出脏器、以及从死体上摘取器官是否能够正当化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目前的活体器官移植主要是肾脏移植。“在中医看来:肾的主要功能是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主水,主纳气,而西医说的肾脏只是一个以调节水盐代谢、排泄代谢产物为主,兼顾部分内分泌功能的器官。陈实教授认为,正常人体有两个肾脏,捐出一个肾脏对健康状况不会有明显影响。”(注:苏敏:“专家呼吁完善立法鼓励活体器官捐赠”,《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15日。)在日本,“一般地,因为像心脏这样的单一器官与死亡直接相关,所以难以被正当化;而在摘除一个肾脏的时候,因为对本人健康不会带来重大的危险,在可以挽救他人生命的时候,以事先作出完全说明为前提,法律承认同意摘除的有效性。”(注:中山研一著:《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日本法的特色与背景》,丁相顺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在得到死者或者死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死体器官移植在刑法上没有什么问题。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法律必须从制度上、技术上充分地保障捐献者个人出于自愿,保证捐献、移植的无偿性或者说非利益性,并且在政府的主导下与社会一道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器官移植分配网络和分配机制,防止人体器官被非公正、非正义地利用。器官捐献、移植涉及的基本法律关系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捐献者个人与社会(例外是与自己的近亲属)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通过政府组织)与接受器官移植的个人即患者之间的关系,而完全不同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同于传统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总而言之,人体器官是作为人的尊严、人格、健康等权利之载体即人体的整体的一部分,与一般之财物有重大的、根本的区别,公民自由处分自己的人体器官可能“抽象”地侵害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器官捐献、移植应当由法律来调整,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处于无法规制的状态。一句话,人们显然不能像处分一般财物那样来处分自己的人体器官。同样的道理,人们不能像处分一般财物那样来处分自己的遗体。
死刑犯是否可以像其他普通人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人体器官和遗体呢?看来是不行的。前述知名律师的观点,认为利用死刑犯捐献器官符合立法精神,因为:
刑诉法第212条规定,指挥执行(死刑)的审判人员,对罪犯应当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然后交付执行人员执行死刑。死刑犯捐献器官实际上也可以视为“遗言”。一般财物可以安排,那么对自己的身体器官作出安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注:郭恒忠:“人体器官移植法律缺失法学专家呼吁尽快立法”,《法制日报》2005年6月1日。)
这是一种不适当的类比推理。遗书、遗言的处理与遗书、遗言内容的实现是完全不同的,遗书、遗言的处理并不费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不会影响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也就是说,死刑犯捐献自己活体或者死体器官的意愿表示(口头或者书面),确实应当视为死刑犯的遗言。但是,讯问死刑犯有无遗言、信札,并分别不同情况对遗言、信札加以处理,与按照死刑犯遗言、信札的内容去做以满足其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984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正确处理死刑罪犯遗书遗物等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死刑罪犯的遗言、信札,应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及时进行审查,分别作出处理:1.涉及财产继承、债务清偿、家事嘱托等一般内容的,交给其家属,同时复制存卷备查。2.属于诽谤性质和反动言词的部分,不交给其家属。3.有喊冤叫屈内容的,应迅速查明事实,依法处理,喊冤叫屈部分不转交其家属。4.凡涉及案件线索、证言性质和有关方面的工作问题的,应抄送有关机关,这一部分不交给其家属。”按照《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应当对死刑犯的遗言、信札作出适当处理,但是没有义务满足死刑犯遗言、信札中的民事领域的具体要求,而是将遗言、信札交给死刑犯家属或者其指定的人负责按照死刑犯的遗愿处理。
死刑剥夺的是罪犯的生命,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同时还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许多学者和律师认为,死刑剥夺死刑犯的生命和政治权利,除此之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被剥夺,所以死刑犯依然像一般公民一样享有其他权利,进而推论死刑犯有权处分自己的遗体,并进一步得出死刑犯有权捐献自己活体或死体器官的权利。例如:
贾宇:关于遗体,特别是死刑犯的遗体处分,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单从法律角度,我个人认为,人有各种权利,死刑犯的生命权利虽然被剥夺,但他临终遗愿想捐献他的遗体,或者他的器官,这些都不违背法规,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
张冬生:死刑犯被剥夺的只是他的生命权和政治权,除此以外的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当他的生命和政治权被剥夺后,他应当受到的惩罚已经全部领受,他的其他人格权利,包括遗体的处分权,与我们自然人毫无区别,也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注:郑淳、吴蔚:“死刑犯捐遗体引出法律碰撞”,《华商报》2004年10月22日。)
本来,沿着这一思路的进一步的推论应当是,同普通人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样,死刑犯的遗体同样不受侮辱、侵害,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不被强制或者推测同意捐献尸体、尸体器官。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暂行规定》中的“直接利用规则”是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条思路是,必须考量死刑犯法律地位上的特殊性,进而考虑法律应当给予死刑犯怎样的特别保护。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利用死刑犯捐献的尸体、尸体器官乃至于活体器官,是否能够与其他政策、原则、规则协调一致,是否可能产生其他不利之后果,等等。
任何一种刑罚方法不仅仅包含实定法所明示的剥夺,还可能自然地派生出其他剥夺效果,例如自由刑自然地导致罪犯的某些民事权利无法实现。历史上,有些国家的死刑不仅剥夺罪犯的生命、自由,而且根据习惯同时剥夺死刑犯的所有民事权利。在我国,实定法明示剥夺罪犯的生命和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还自然而然地剥夺其人身自由,除此之外,应无其他剥夺。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死刑被依法剥夺了什么的命题出发直接得出死刑犯有权捐献自己的尸体、尸体器官。死刑犯当然有权安排身后事,但是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死刑犯安排了怎样的身后事,政府应当给予怎样的帮助、服务?政府是否有权力、有义务、有能力给予这种帮助,这属于积极保护罪犯权利的范畴。
一般地说,政府只要不去拿走罪犯的某些不应拿走的利益、不去剥夺罪犯的某些不应剥夺的权利,即可实现对于罪犯人权的消极保障。但是,对于罪犯人权的积极保障则要政府积极地做更多的事情、提供更多的便利,也就是说,意味着需要成本支出与制度安排。具体到死刑犯活体器官捐献,我国目前的羁押制度和刑事诉讼程序就没有预留任何空间。抽象地讲,死刑犯当然有权处分自己的器官和遗体,但是死刑犯活体器官捐献面临着看守所监管制度上的巨大障碍,死刑犯受严格羁押的状态自然而合理地阻碍了他正常地行使这一权利。为了死刑犯捐献器官而停止哪怕是暂时停止审判,无疑会延缓、乃至于冲击、干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因此,死刑犯请求法院批准其活体器官捐献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法院并没有义务满足这一要求。或许会有人说,暂且中止刑事诉讼进行活体器官捐献以满足死刑犯的良好愿望,岂不是更好地保护死刑犯的权利。这又涉及到及时、迅速、公正地审判(当然需要穷尽所有救济程序)与死刑犯利他愿望满足之间哪一个优先的问题,毫无疑义,应当以前者为优先。目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急需大力加强的是包括死刑犯在内的所有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以及免受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的侵害,而不是怎样保障死刑犯捐献尸体、尸体器官甚至于活体器官的利他性“权利”的实现。
实际上,即使再钢性的规则也会有例外。我主张应当禁止利用死刑犯的活体器官、尸体、尸体器官。如果这一规则真的成为现实的规则,那么应当是钢性的规则;但是依然可以存在例外,就是可以考虑允许死刑犯临刑前自愿地将自己的死体器官捐献给自己的近亲属。但是,目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依然没有满足死刑犯要求捐献活体器官给自己近亲属的空间——如果有死刑犯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法院也难以满足之。我相信,以中国目前的人权发展水平,未来的器官移植立法不大可能做这样的安排: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前可以自愿捐献活体器官给自己的近亲属。现在,我来做一个假设——情感反对我做此不幸的假设,一个死刑犯的近亲属急需肾移植手术,该死刑犯向法院提出活体捐肾给自己亲人的要求,法院当然会拒绝,媒体与民众的意见又会如何呢?还会像现在的讨论这样希望法院满足死刑犯的权利要求吗?我几乎不怀疑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共识:这个罪大恶极的死刑犯被判处并且应当立即执行死刑,也就自然地丧失了这样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