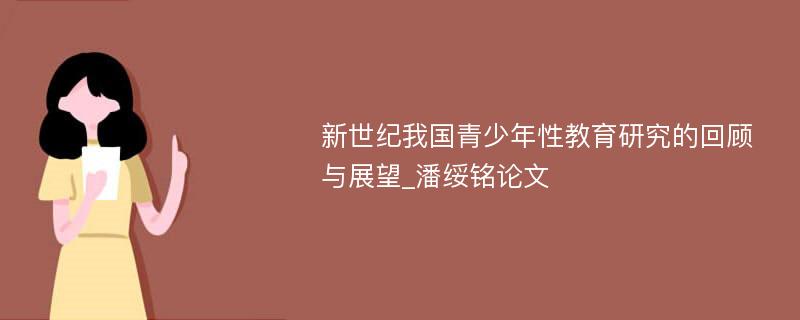
新世纪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性教育论文,中国青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青少年需要性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共识。然而,对于青少年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国人争执不休;对于什么才是最适合中国青少年的性教育,大家众说纷纭;对于采取什么样的路径大力推动和发展性教育,众人也是各持己见。2010年春夏,笔者先后参加了四次中国青少年性教育“高峰”论坛,最大的感受是中国教育界广泛、平等、开放地推进性教育的理想尚未实现,实践的基石还不稳健的时候,性教育的政策决策、性学专家以及学校性教育者之间的分歧已有显露;守贞教育、性科学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综合型性教育的种种主张均各有市场。当性教育挣脱出中国传统教育的教条桎梏,走进大学、中学甚至小学校园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性教育的实质和内容究竟是否真正呼应了青少年的需要?
二、文献概况
通过梳理中国知网500余篇1982年以来的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相关中文文献和PsyINFO、Medline、ProQuest等英文数据库1977年以来30余篇相关英文文献,我们认为,中国性教育研究型文献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概述性、介绍性的描述为主,无论是历史解读、还是概述国内性教育现状、抑或介绍国外性教育的做法、中外性教育的比较的相关研究,都以介绍国内外先进经验并推进国内性教育实践为己任(胡佩诚,1997:36-39; 2008a:50-57;刘文利,2008b:9-12;刘文利,2008c:17-20);二是以定量为主的实证研究,调查内容主要关注性生理发育、性心理发展、性知识、性态度、性观念和性行为(涂晓雯等,2008:668-672;程艳等,2010:344-348)。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学生、家长和老师,对于流落在学校之外的青少年缺乏关注,其中学生群体中又关注儿童、青少年和大学生等不同人群,力图阐释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性教育的方法与策略(胡珍,2000:72-79;陈晓等,2009:88-91)。与研究型文献并行的一种性教育文献,是由很多学者以一种杂文体的形式,从自我观察和评论的角度进行阐述和评议(彭晓辉,2006:26-27;潘绥铭,2007:38-41;张玫玫,那毅,2004:25-26)。
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表现如下:定量研究发现多以描述性为主,缺乏深入地影响因素分析的相关文章;以小样本方便性抽样为主,缺乏全国性随机抽样的研究,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只有两个全国随机抽样的研究,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全国14—17岁总人口:性教育效果的实证分析》(潘绥铭、黄盈盈,2011:05-09),另一个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10年的《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在定量研究中,干预评估类论文非常缺失,上海计生研究所的高尔生、楼超华等组成的研究团队(Cheng et al.,2008:184-191; Lou et al.,2006:720-728; Tu et al,2008:249-258;涂晓雯等,2005:76-79;楼超华等,2003:283-290,2004:149-153;等)率先在这一领域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他们分别在上海、重庆、河南等地研究了干预前后青少年的性知识、态度、技能的变化;仅有少量的英文论文关注了中国不同模式的性教育(Hong et al.,2007:161-169; Li et al.,2009:549-551; Liao et al.,2010:409-419),然而无论是家庭性教育、网络性教育还是社区性教育都只有零星的文献,还没有开展深入、系统、不同模式比较的研究;质性研究缺失,缺乏对于性教育者的困境的关注,同时青少年成为定量研究的被试,他们是性教育的主体,但是他们的声音在性教育研究领域却是缺失的。
三、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现状
瓦茨(Watts)2004年在国际知名学刊《柳叶刀(Lancet)》中对于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现状的刻画可谓一针见血:中国性教育落后于青少年的性实践(Watts,2004:1208-1208)。学者们一贯的思路是列举青少年的各种问题行为表现,包括初次性行为提前,不安全性行为比例高,非婚和非意愿性怀孕和人工流产比例成增高趋势,性病艾滋病感染率增高等等,来例证开展性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而瓦茨的论点将这一逻辑调转,生动形象地指出了青少年的性教育在面对身心需求、家庭背景、教育理念、社会环境种种张力下的冲突和纠结。下面我们将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再次阅读,尝试解读性教育之所以“落后”于性实践的背后那丰富且多元的社会、文化、教育等意涵。
(一)青少年性早熟但性教育滞后
世界范围内青春期发育提前的趋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青少年普遍早熟(高尔生,楼超华,2008:92-129)。然而,我国目前学校开展青春期教育普遍较晚,大多安排在初中二、三年级进行,这就造成青春期教育落后于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发育的现状,所开展的青春期教育基本上属于补漏式教育,缺少超前意识(曾燕波,2008:5-8)。目前在北京、成都等地的一些小学已经开始了性教育的探索和尝试①,其中成都人北实验小学的学科渗透式性教育已经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成都的中学愿意招收人北实验小学的毕业生,因为与没有接受过性教育的青少年相比,他们相对容易平稳顺利过渡青春期。②此外,北京、成都、深圳等地纷纷开发中小学的性教育校本教材,例如成都人北实验小学2005年开发的《成长路上陪你走》;北京师范大学刘文利团队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市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流动儿童性健康教育的实践工作,并编写了《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计划6个年级不同内容,目前已经出版一年级上下册③;首都师范大学张玫玫团队的小学校本教材《成长的脚步》,因其朴素直白地介绍受孕过程的语言,引来铺天盖地的争议④。虽然越来越多国内外专家们指出性教育要越早越好(Haberland & Rogow,2007),但是小学阶段的性教育仍旧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二)学校性教育依旧发展缓慢
科比等(Kirby et al.,2005)对于83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性教育的干预项目的综述指出,三分之二的项目都能有效地降低一个或多个危险性性行为(Kirby et al.,2005:11-37)。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成人主导的、学校性与生殖健康教育(adult-led,school-based sex and HIV education)仍然是世界公认的、最为有效和最便于开展的性教育模式。
然而,中国的学校性教育这块阵地上还有很多荒芜的土壤。我国学校性教育工作起步较晚,在师资、教材、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方面都还不能保障性教育的顺利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性教育没有纳入国家课程计划,也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开设,课程、师资、教材都未从其他教育当中分化出来。这些情况直接导致了学校性教育开展方式、方法、水平、程度上的尺度不一,学校性教育常常流于单纯的生理知识教育或单纯的道德教育(王雪峰等,2005:46-48;刘文利,2011)。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10年针对22288个15-24岁的青少年全国性随机样本的调查中发现,如果将青春期教育或相关课程,预防性病、艾滋病讲座以及避孕节育知识讲座都视为学校性教育的三种模式,不足40%的青少年自报参加过这三类课程,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讲座都不能算是正规的学校性教育(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10)。潘绥铭、黄盈盈针对1593个14-17岁的青少年全国性随机样本的调查中发现,73.5%的少年认为,学校几乎没有讲授过性知识;86.6%的少年认为,他们几乎很少从父母那里获得性知识。学校性教育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离学校性教育成为义务教育的距离还很遥远,还远远不能满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潘绥铭、黄盈盈,2011:05-09)。
(三)父母支持性教育但害怕成为教育者
刘文利等(2006)对北京、上海和西安三城市的84l位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进行了关于家庭性教育的问卷调查,该研究有趣且矛盾地发现,大多数父母不仅掌握了一定的性科学知识,而且对在家庭和学校开展对青少年的性教育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但85%的家长自称,他们从来没有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刘文利等,2006:76-80)。张(Zhang et al.,2007)和赵双玲等(2003)的研究佐证了刘文利等的发现:张等于2001年在成都对682名15—19岁青少年进行了自填式问卷调查表明,青少年和父母之间关于性的交流较少,话题局限性大(Zhang el al.,2007:138-147);赵双玲等(2003:1136-1138)认为,父母没有能力对于子女进行性教育是这一问题的关键,他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好意思开口与子女谈性相关问题。同时,在笔者针对北京年轻人的强迫性性行为的质性研究中也发现,当女生们经历了不安全性行为、非意愿怀孕或强迫性性行为之后,她们害怕父母知道,更不可能寻求父母的帮助(Wang & Ho,2011:184-200)。在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转变和传统文化规范难以调和的情况下,要发展健康的家庭性教育,让父母放下包袱、坦然面对子女谈性,依旧是个很大的挑战。如何建立一种支持性的社会氛围来帮助家长提升自身的沟通技能是性教育工作者未来的一项长远的任务。
(四)青少年性实践超前但性观念落后
青少年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第三次性革命的时代(潘绥铭,2006),面对各种复杂、矛盾、纠结、多元的社会话语,他们仿佛可以自主、可以有很多选择,但又似乎有些无所适从:当“不赞成、不反对”还是校方对大学生谈恋爱的主导态度,当中学的“早恋”话语虽然松动但仍是主流,当学校性教育仍以禁欲和防病为主要导向,那么,性压抑依旧根深蒂固、性禁忌仍然没有打破,“只做不说”似乎只能是青少年的唯一选择。再者,青少年似乎在所谓“纯洁”的学校和泛性化的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纯洁”的学校性教育,如孙云晓所指出,依旧在关键的知识点上躲躲闪闪、似乎以孩子弄不明白为己任(孙云晓,2007),另一方面,青少年还要面对媒体和社会上无处不在的性信息的冲击——电影电视上的大量亲热裸露的镜头、电线杆上随处可见的性病防治广告、街头花红柳绿半遮半掩的成人用品商店等等。很多研究指出,青少年的性知识的主要来源是网络(Hong et al.,2007:161-169),然而网络上的性知识和所谓的“性教育”的正确性、科学性都是令人质疑的。与其让青少年在黑暗中自我摸索,不如让成年人做出有方向、有目标、科学的引导。此外,青少年处于一个进入成年的过渡时期(transitions to adulthood),大多数父母和教育者总倾向于将他们看成天真无邪的孩子,然而却不理解青少年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与生俱来的模仿力以及对于“禁忌”行为的感知能力。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2001-2009年的《深圳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需求现状定性研究》中,曾向小学生们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黄色信息的来源有哪些”,小学生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但又相当准确,例如“网上、夜总会开在青少年宫门口、外国电影曝光过头、三陪、包二奶、某些洗桑拿”等等(陶林、张玲,2009)。
在这种复杂矛盾多变的环境下,青少年性实践超前是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我们在与北京四所高中(普高和职高)的性教育者和学生们的接触过程中发现,与青少年性实践超前不相对称的是,他们的性观念还是相当保守,尤其是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和性的双重标准根深蒂固,仍然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和行为。国外大量的研究指出,有害的行为并不仅仅来自知识的欠缺,而更常常与亲密关系中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和不平等权力关系紧密相联。不同的研究也纷纷指出,当青少年固着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态度,他们更有可能有更多的性伴侣(Karim et al.,2003:14-24),更有可能经历约会暴力(dating violence)与强迫性性行为(sexual coercion)(Wang & Ho,2007:623-638,2011:184-200),较少采取安全性行为,更有可能感染性病、艾滋病(Wang et al.,2006:227-235)。性教育强调社会性别视角、提倡性别平等的观念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路途。
四、争论与反思
纵观中国性教育现状与发展,我们认为目前在这一领域,有两大最为核心的论争:一是究竟是要发展性科学教育还是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性教育,另一是究竟要发展禁欲式性教育还是综合全面的性教育。只有对这两个论争进行深入的剖析,才能更好地指引性教育发展方向。
(一)基于社会性别的性教育:全新的范式转型
潘绥铭曾指出,“在对‘正规性教育’的欢呼中,有一个词汇的上镜率奇高,那就是‘科学’。这种科学崇拜还有一个貌似毫不相干的产物,即闭口不谈社会性别的问题”(潘绥铭,2007:38-41)。确实,目前很多活跃在国内性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及最先在大学里开设性教育课程的性教育先驱们所受的专业训练都以生物科学和医学为主,在最初性禁忌和性禁锢的年代,运用“科学”的旗帜来证明性教育的合法性以谋求一席之地是合理而又自然的,这一做法沿袭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性教育最初引入中国的策略(Aresu,2009:532-541; Larson,1999:423-450)。以彭晓辉(2002)的《性科学概论》和胡珍、王进鑫(2008)主编的《大学生性健康教程》这两部在中南、西南地区被广泛采用的大学生性教育课本为例,科学教育为其核心,内容包括性科学、性文化、性生理、性传播疾病、性审美、性法律、性心理、性行为、性观念、性道德等。这样的课程设置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以传授性相关知识为己任,性似乎被抽离出来,与中国既定的社会文化情境相脱节;正如性社会学家方刚对这一现象的批判:
今天我们谈性教育的时候,主要是在sex(生理的性)意义上谈性教育,至多是在sexuality(社会的性)意义上谈性教育。性是有社会性别的性,性教育应该是有社会性别的性教育。忽视社会性别的性教育,在于没有认识到许多性问题本质上就是社会性别问题,是社会性别问题在性上的表现。(方刚,2007:6-13)
二是更为关注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缺乏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学过程不能将个人的行为和观念置于社会情境中让学生去反思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性别刻板印象、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并学会建设更加健康的亲密关系。陈亚亚主张青少年性教育应当——
进行性别平等观念和责任感的培育,倡导一种负责任的性自治观,而不应将异性恋婚姻制度以外的性都认为是危险有害的,更不应该教导一种固化的性别刻板印象。(陈亚亚,2010:97-102)
从全球范围来看,众多的研究显示,传统性别规范和父权制下的性别权力不平等深刻地影响所有青少年的性态度、性行为及其健康(Rogow & Haberland,2005:333-344),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仅仅聚焦于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也不足以挖掘隐藏青少年性行为和健康背后的深层的社会性别态度和行为。联合国已经将性别平等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将其纳入千年发展目标的八大发展目标之一(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2000),认为实现性别平等是抗击艾滋病、减少非意愿怀孕和安全避孕的关键。国内现有研究也显示,男生和女生接受性教育的渠道有所不同,阅读材料、广播、课堂讲座和与父母沟通在女生中更为广泛,而同伴交流、互联网和个人的性探索及实践在男生中更为广泛,相比之下,女生更偏好较私密的性教育信息传达方式,如阅读等(Li et a1.,2004:128-133),这些不同的特点要求在性教育实施过程中,性教育者应该充分考虑到男生和女生的不同需求和偏好以及培养青少年学会批判性的思维去打破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对于他们的禁锢和束缚,使得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利——拥有“尊严、平等、健康、负责、满意的性生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11)。确实,知识只是性教育的第一步,面对中国性教育落后于青少年性实践、青少年性实践超前性观念落后这一客观事实,传统的性科学教育已经不能回应青少年的需要并改变这一现状,现在到了中国性教育全新的范式转型的时候了——应大力发展基于社会性别的性教育。由美国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资助,哈伯兰和罗格(Haberland & Rogow,2009)主编并出版的《It's all one curriculum:Guidelines and activities for a unified approach to sexuality,gender,HIV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是一个体现基于社会性别的性教育课程设计的典范。这一套教程目前已经被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翻译并引入国内,取名为《青春健康教育指南——性、性别、艾滋病和人权教育统一行动指导和活动手册》,希望能够促进国内性教育界对于社会性别议题和促进性别平等的进一步关注。无论是英文书名还是中文翻译名称,我们都能够看出,每一个强调性别平等并注重社会性别视角培育的性教育必然是综合全面的性教育,这又和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另一个论争有着紧密地联系。
(二)禁欲型性教育还是综合型性教育?
在美国,禁欲型性教育(abstinence-only sex education)和综合型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经历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受基督教影响,禁欲型性教育主张青少年的性交应绝对被禁止,尽量回避整体上对“性”的评价,强调婚前守贞,强调婚姻外的性活动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性交从社会、心理、生理各方面都是有害的,认为一夫一妻制度是唯一符合人类自然规律、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的性生活标准模式。然而,综合型性教育认为性行为是正常、自然、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虽然青春期具有不稳定性,但青春期出现包括性交在内的性活动是非常正常和普遍的,在本质上不应该受指责。不同文化、宗教、族群对“性”的态度和认识,综合型性教育主张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准则,异性恋家庭、同性恋结合、单亲家庭都是社会现象,不应该受到歧视(方刚,2010:90-96;王友平、邓明昱,2005:84)。
与美国深受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实施禁欲型性教育的原因不同,中国的性教育从没有宣称是“禁欲教育”,但是受根深蒂固的性禁忌和沉默的性文化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意义的性教育,内容本质是禁欲教育,章立明曾总结了这一类型性教育的特点:
教师只教给学生生理器官的名称、位置和解剖功能,以怀孕和感染性病的危险来劝阻青少年不要参与性活动,以此压抑青少年的性冲动。(章立明,2010:12-23)
近来,很多学者深刻批判禁欲型性教育,大力提倡发展综合型性教育。例如方刚写道:
禁欲型性教育是“恐吓式”性教育,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他主张综合型性教育,向学生呈现全面的性信息,包括被掩盖的性信息,进行性的安全教育,从而鼓励学生正视性,接受美好的、负责任的、自主的性。(方刚,2010:90-96)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发展综合型性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早在2001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亚洲性教育大会上,“大力发展综合型性教育”已经成为了会议宣言,号称要帮助年轻人理解性文明与健康、性与道德、性与责任之间的关系(Aresu,2009:532-541)。然而,虽然高举着“综合型性教育”的旗帜,在日常教育实践中,不称为禁欲的禁欲式性教育依旧大行其道,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安全性教育常常是缺失的一个环节,强调自我约束和性道德依旧是主流。这一矛盾纠结的立场最为明显地表现在“性教育该掌握怎样的度”的论争上。确实,在目前国内各种类型关于性教育的研讨会上,关于度的讨论时常浮现,支持者不停在说——要适度、要恰到好处——“度”的讨论背后在说,对于青少年性教育,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信息应该在什么时候说。关于度的讨论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议题,在性教育中如何处理性小众群体(LGBT)的议题,一些性教育者认为,在中学阶段,青少年如果过度接触这方面的议题,会对自己的性取向产生怀疑,甚至带来负面的后果。
我们要尽量杜绝由于漫画、影视作品中对同性恋的唯美表现和现实中负面报道同性恋现象,加强对青春期少男少女进行性教育以及同性恋的知识教育。否则,直接的后果就是少男少女会在违背自己性取向的情况下,对同性产生强烈的性冲动,而并非本意地对同性有性欲。这种矛盾心理,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这也是我们有必要告诉青少年同性恋相关知识的重要原因之一。(闵乐夫,2010)
闵乐夫的观点展现了中国的性教育者如何在这一议题上左右为难,看似力图保持度的平衡,结果必然是遮遮掩掩、语焉不详。这样的论点背后的逻辑正如最初反对性教育的势力所批判的那样,性教育导致性实践,所谓“过早”同性恋等相关议题会激发青少年的同性性行为。然而国内外的研究都已经证明,性知识的正确程度不会增加性交的可能性(潘绥铭,黄盈盈,2011:05-09)。针对“度”的论争,性社会学家的态度是:
性教育是义务教育,故必须遵循义务教育的一般规律:第一,所有义务教育都是“超前”的。第二,所有义务教育在当时都是“没用”的,但却非学不可。第三,所有义务教育都是“强制”的,不但强制学生,也强制家长,还强制政府。第四,如果真教育,就必须满足学习者的需求,激发学习者的兴趣。第五,一切义务教育的“度”只有两个:一是政府希望后代成为什么样的人;二是被教育者能不能学得会。(潘绥铭,2007:38-41)
确实,强调“度”的性教育,有时候是性教育者在面对应试型教育体制和相对保守教育环境的妥协和策略。但强调“度”的性教育也有可能成为禁欲型性教育的变形,过于强调预防疾病和过早发生性行为的危害,却很少涉及性权利、性多元、性身份以及性愉悦等。潘绥铭认为,性教育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即帮助所有的个体,尤其是下一代,都尽可能多地获得“性福”。在这个目标下,性教育的“受众”的权利和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潘绥铭,2007:38-41)。然而,强调“度”的性教育常常是从性教育者的主观立场出发,容易坠入性教育的陷阱和误区:主观臆断地猜测“受众”的需求,用一元化的思路来设计贯彻实施性教育,进而忽略了个体差异以及不同个体在发展中的多样可能性。
目前国内性教育界还要警惕的另一个思潮就是海外宗教势力试图在中国推广禁欲型性教育,代表性事件就是2008年4月浙江大学从美国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引进的“婚前守贞教育”项目和2010年8月云南省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接见爱家协会代表准备加强合作。彭晓辉对此做出激烈的批判:
爱家协会在中国推广“守贞”教育,是西方宗教的“守贞”道德理念和东方封建专制文化的“贞操文化”(男性霸权的产物)的嫁接。如果仅仅用“婚前守贞”来开展性教育,就是加强这种封建的专制文化。(彭晓辉,2010:55-61)
总而言之,虽然推广综合型性教育已经成为国内性教育界的共识、潮流和趋势,但在日常实践中,根深蒂固的禁欲式性教育依旧积习难改,西方禁欲型性教育势力也在向国内拓展力量,在中国发展和落实真正的综合型性教育还面临很多的挑战。
五、总结与前瞻
通过这一文献综述,我们梳理了中国青少年性教育,尤其是学校性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种种争论与反思;文献之后的研究空白和亟须发展的方向也随之在这一过程中凸显出来。当我们认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基于社会性别的综合型性教育必将成为一种主流和趋势,顺应这一需要,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研究亟须在如下几个方向大力发展。
(一)大力发展干预评估类定量研究
有限的干预评估类论文使得性教育研究者很难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性教育对于增进青少年的性知识、延缓青少年的性行为、促进青少年采取安全性行为有良好的效果,进而不利于性教育公共政策的倡导。科比和罗勒里(Kirby & Rolleri,2007)给全球范围内综述干预评估类的文章,曾给出一个选取该类文章的标准,其实也在指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干预评估研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1)具有实验或半实验的设计,有干预组和对照组,有前测和后测;2)至少有100个样本;3)通常测量项目对如下因素的影响:初次性行为、性行为的频率,性伴侣的人数,使用避孕套和其他避孕措施的情况,不安全性行为,怀孕率,出生率和性疾病感染率;4)测量那些可以改变很快的行为,有一些行为例如性频率、性伴侣的人数、使用避孕套,采用避孕或危险性行为要看至少三个月的变化,还有一些行为如初次性行为,怀孕率、疾病感染率要看至少六个月的变化。此外,今后的评估研究还不应只关注教育的效果——性知识是否增长、性行为是否推迟、安全性行为是否增加——这些都是非常局限性的成果指标,而要更多地去关注性教育对于男生和女生的不同的影响,对于他们的社会性别意识有没有提高,是否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亲密关系,是否尊重个人的性权利和多元差异。此外,干预评估类的研究还要将视点转向不同性教育的模式比较研究,以便得出切实可靠的数据,为目前倡导基于社会性别的综合型性教育提供这一教育模式优越性的证据。
(二)大力发展质性研究
目前性教育领域以定量研究为主,关注的焦点聚焦在青少年的性态度和行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相对于量的研究而言,质性研究是开放的、深入的、具体的、更加能够捕捉全景画面和处理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就质性研究而言,我们认为以下几个类型的研究目前最需要大力的发展。
1.对各相关利益持有人(stakeholders)的质性研究
从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性教育政策完善但是教育实践落后,可是为什么有着这样的反差,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相关利益持有人进行访谈——包括政策制定者(教育部门和计生部门)、政策执行者、校长、学校性教育者、社区性教育者、父母、学生——只有进行这一利益相关分析,才能将盘根错节的关系厘清,寻求国家公共政策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落差,进而寻求政策与实践相互促进的道路。
2.对青少年的质性研究
青少年在中国现存的性教育研究中一直处于“被试”的角色,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他们的声音没有得到倾听。质性研究方法将青少年视为能动的主体,他们的所思所想、行动和经验都是开展性教育的丰富的材料和资源。
3.运用焦点小组的方法
在我们与北京四所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同学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焦点小组是个非常好的研究方法,用来收集青少年对性教育的需求、现状及其期望等态度和观点。焦点小组采用研究者和被访者开座谈会“一对多”的形式,弱化了个人访谈中研究者与被访者“一对一”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此外,青少年成员之间的互动也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捕捉他们在生活中的真实状况。
4.运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混合路径
我们发现,很多国际大型项目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混合路径的研究方法,例如《柳叶刀》2006年发表的一篇泰国青少年性教育需求的论文是采用这一路径开展研究的典范,他们选取六所社会经济背景、宗教信仰和地理位置不同的初中,访谈关键利益持有人、分析关键政策文件、向青少年发放2301份问卷并开设二十个焦点小组、向家长发放351份问卷并开设两个焦点小组,然后将定量数据和质性访谈的资料分别采用统计分析和主题分析的方法,然后再进行综合(Vuttanont et al,2006:2068-2080)。
(三)大力发展性、社会性别与亲密关系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
性教育研究的发展和性教育实践的完善都离不开国内关于性、社会性别与亲密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力发展。长久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关注阶层、劳工、移民等宏大的命题,相对而言,性、社会性别与亲密关系的相关研究不受重视。与西方文献相比,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点——恋爱暴力、强迫性性行为、儿童性侵犯、艾滋感染女性、性侵犯、婚内强奸、非意愿怀孕和堕胎、LGBT以及性少数群体权益——不胜枚举。然而这些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是性教育研究发展的基础,它们可以为青少年性教育提供鲜活的案例、帮助研究者和青少年灵活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批判性的思维看待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倡导个体的性权利并尊重性的多元选择。
注释:
①陈薇,《样本:四川人北实验小学的八年性教育》参见“凤凰网资讯”的“中国新闻周刊”(http://news.ifeng.com/shendu/zgxwzk/detail_2011_09/13/9138423_0.shtml)。
②信息来自与胡珍的私人交流,胡珍,成都大学教授,四川省性教育领军人物。遗憾的是,没有研究对人北实验小学的性教育进行追踪的干预评估研究,否则的话,得出“早期性教育有利于青少年青春期平稳过渡”这一发现的意义,就如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的理论意义那样重大。
③信息来自与刘文利的私人交流。刘文利,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副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的中国专家。
④http://education.cqnews.net/html/2011-08/23/content_790909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