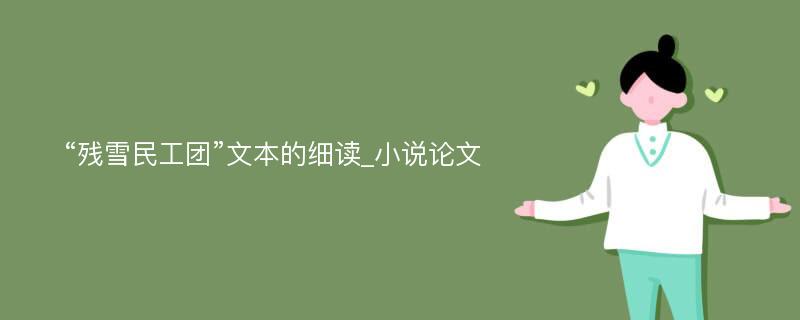
残雪《民工团》文本细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残雪论文,民工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解读残雪,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一般读者,也困扰着大多数的评论家。残雪的小说一向以晦涩著称,充满了荒诞、象征和怪异,是非常典型的先锋派小说。但另一方面,残雪的小说也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自我欣赏的文字游戏”[1],“甚至连情绪性的方向也找不到”[2]。我也不主张过分夸大所谓残雪的心理不同于常人心理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残雪的个人经验过于独特,具有不可通约性,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认为普遍的阅读经验是无效的,“不仅读不懂,而且无任何阅读意义”[3],这并没有真正理解先锋小说的实质,实际上还是按照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在衡量残雪的小说。
我认为,残雪的小说是有意义的,只是这种意义不象传统小说包括一些现代主义小说那样清晰、明确和单纯,残雪的小说不论是在对话上,还是在情节上都有太多的空白,所以它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与传统的小说相比,残雪的小说给了读者更多的创造和想象的空间。残雪小说的确具有反时间性、反空间性和反逻辑性(即非理性),但仔细地分辨和搜寻,我们是可以找到其深层逻辑的,是可以清理出其时间结构和空间顺序的,只是残雪小说的时间和空间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它不是直接叙述和交待的,而是隐蔽在意象和情节之间,具有抽象性,隐喻性,高度“蒙太奇”化,其“坐标”是隐形的,不符合我们的俗常感觉。
对于残雪小说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用传统的“懂”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很难说我们完全理解了残雪,也很难说我们完全理解了她的作品。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此把残雪小说的意义无限地神秘化、模糊化、虚化,我们虽然不能直接把残雪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具体地复述出来,但我们能够感觉到它们的方向;我们很难明确地把握作家的写作意图,但我们能够感觉到作家写作中的情绪方向;我们虽然不能清晰地复述小说的情节,但我们能够体味到作品在叙事上的内在紧张;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描述和分析其作品的主题,但我们能够大致感受到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我们能够感觉到作家想在作品中表达某种抽象的哲理。残雪的小说实际上只是提供了某种意象和情节的框架,只是营造了某种情绪的氛围,而大量的空白,包括情节的空白、细节的空白、形象的空白、意义的空白等则需要读者去想象、去创造、去补充从而予以填充,残雪的小说在文本上是未完成或者说是残缺的,因而是开放的,这和传统小说的封闭性、完整性、透明性、逻辑性以及高度的形而上学性是有很大不同的。《民工团》是残雪的一篇新作,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在这篇小说的后面,有两篇评论。对于残雪小说的解读来说,这种很空泛、很主观而具有某种随意性的解读是合理的,并且很具有策略性,但我总觉得这两篇评论对于小说解读得过于玄虚。所以,本文尝试对《民工团》作另外一种解读,并且试图通过这种解读表达我对残雪的另一种理解。
这篇小说与残雪过去的小说有所不同,但又一脉相承。相同在于,写得晦涩、朦胧,意象荒诞,情节荒诞,意象和情节一如既往地缺乏逻辑的连贯性,有太多的空白。内容上表现暴力,气氛压抑、郁沉。不同在于,小说的时空相对稳定,故事的轮廓相对清晰,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感,并且具有内在的紧张性。我认为,小说大致表达了在恶的世界中的“不恶”的挣扎和失败这样一个主题,但这个主题表现得非常朦胧,以至于我不敢绝对地肯定它,只能给它以“解读”的定性。对于残雪的小说,我们是不能象对待传统小说那样进行主题、情节、细节、人物性格分析的,我这里使用这些概念其实具有“权宜性”,按照德里达的方法,这些概念其实都应该打叉。下面我主要采取“讲解”的方式来对这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
小说的开头部分写得非常俗常,也很故事化,其中第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是2月3日跟随大队人马到达这个大城市的。我记得那天傍晚天下着大雪,整个城市阴沉沉的,街上行人稀少。走一段就看见一个高档的餐馆,里面热气腾腾,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为头的带着我们这一群人在雪地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信的地方,我们的行李铺盖全都被雪花弄得湿淋淋的,脸都被冻得麻木了,说话结结巴巴的。
这种很“现实主义化”的开头在残雪从前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残雪从前的小说,多数第一段话就非同凡响,给人强烈的荒诞感,同时也为小说定下一种基调。比如《雾》的开头:
自从降雾以来,周围的东西就都长出了很长的绒毛,而且不停地跳跃。我整天大睁着双眼,想要看清一点什么,眼睛因此痛得要命。到处都是这该死的雾,连卧室里也充满了。它们象浓烟一样涌进来。从早到晚占据着空间,把墙壁弄得湿漉漉的。白天还勉强能忍受,尤其难受的是夜间。棉被吸饱了水分,变得沉甸甸硬邦邦的,而且发出一种“吱吱”的叫声,用手一探进去冷得直哆嗦。家里的人一齐涌向储藏室,那里面堆满了湿津津的麻袋。角落里放着一个电炉子,烤得热气腾腾的。妈妈一进去就把门反锁了,大家挤在一处流汗,一直流到早上。
《民工团》为什么要以俗常化的方式开头,林舟先生的解读是:“随着小说的展开,你会逐渐意识到,开头的朴素和常态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过渡性平台,让你不至于一开始就被吓跑。”[4]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说法,且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愿意作另外一种解读。我认为,小说开头部分很现实化的叙述和描写实际上是一种交待、一种背景。“我”(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从后面的叙述中知道姓瑶)随民工团来到一大城市打工,被安排在车库地下室的宿舍里,六个人一个房间(约10平方米),工头(后来知道姓杨)非常凶恶粗暴,清晨三点过五分就吼叫我们起来去干活,第一天的活是背水泥,背了几趟之后脚就发软了,稍有闪失便有生命危险。这种交待和背景为小说的主题以及故事情节奠定了基础,也使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它让我们的理性和感觉相对集中而不至于过分游离,它使我们的阅读和理解始终在一定意义范围内滑动。
民工每天清晨三点就起床干活,其累或痛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能够换取轻一点的活,民工中流行一种告密的风气,告密者可以得到奖赏,即干轻一些的活,而被告密者则要受到惩罚,即干更重的活,这是“民工团”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规则”在小说中非常重要,小说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我却不遵守这一“正常”的生活伦理,既不告密,也不反击告密,这样就打破了民工团的生活“规则”,造成了不和谐,并且危及民工团的安定,冲突由此而起。杨工头终于沉不气了,有一天主动找我谈话,第一句话和烧饼铺老板娘的话一样:“我说你啊,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呢?”然后诱导我告密,并且希望我告灰子的密。所谓“落到这步田地”其实是给我的生活现实予以定位,同时也是告诫我,既然到了民工团,就应该按照民工团的方式生活。但我并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是不管别人的事的,我只想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
灰子住在我的上铺,他现在总是躲着我。一个中年汉子告诉我有人告了我的密,果然我又被派去背水泥,但我并无怨言,也不打听是谁告的密。晚上在回地下室的途中,工头突然从轿车里冒出来,告诉我说是灰子告的密。并且特别让我休息一天,不过不是在宿舍,而是在公园。自此,小说就完全进入了荒诞和离奇的景况,故事也在这种荒诞中紧张地展开。
晚上我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起来之后杨工头让我去伙房吃饭,吃小灶,菜很好,厨师也不催(从前是稍吃慢一些,师傅就夺碗)。吃完饭后,杨工头派了一辆吉普车专程把我送到“公园”。我上车时,司机没有和我说话,到了“公园”时,也不叫我下车,“我等待司机对我发指令,可是司机绷着一张脸不吭声,忽然他站起来,上半身越过我,用他的拳头‘嘭’地一声打开了我这边的车门。”“见我不下车,司机就火了,他抡起一把扳手要来砸我,吓得我滚了下去。”最后司机给了我一句话:“我五点钟来这里接你回工地。”冷漠、暴力、敌视,这在民工团中是“正常”的生活方式,对于司机的描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它不过是顺便性地强化了民工团的现实。小说中,杨工头是一个凶狠、粗暴、野蛮的人,这时他对我很友好,这是“反常”的,这种“反常”从另外一方面显示了民工团的平静被打破了,这说明,在杨工头这一方,冲突也正在激烈地展开。杨工头正常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恶”或“暴力”的方式,但他现在采取了“善”的方式,由此也可见冲突的激烈。
所谓“公园”,其实是“劳改农场”,但“劳改”对于民工团来说,恰恰是“快乐”,所以被称为“公园”。也正是因为如此,作家对这个地方在空间方位上写得很恍惚。司机把我拉到郊区的一座红色的牌楼下面,这里是大片的黄土,没有房屋,没有树。我失去了方向,漫无目标地走,“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走到牌楼下面。抬头一望,右边是一个皮革服装厂,左边是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群汉子在打牌赌钱。那些汉子也是同我一样的乡下汉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当中有两个人似乎有点面熟。”我向一个年纪大一些的汉子打听如何到城里,他说:“你不会去问灰子么?”原来灰子在皮革厂。我找到灰子时,灰子正站在染皮革的黑水里。灰子带我到一个杂屋(即灰子的住处),到了房里,“灰子吃吃笑个不停,我问他笑什么,他好半天才停下来,回答我说,他不是笑,他是在打嗝,可能受了凉。我一摸他的手,比死人的手还冷。”灰子就睡在废纸里。在这里,灰子告诉我,他告了我的密,但并没有得到奖赏,原因是他没有满足工头的愿望,小说是这样描写的:房间里很冷,我就和灰子一起跺脚,跺脚时“我”伸手触了触他的胸膛,那里头有个圆东西在往外鼓,很吓人。
“这是什么?!我指着他一动一动的衣服前襟问道。”
“是,是我的心嘛。”他喘着气回答,“我的心是长在外面的,我娘做了布袋子帮我兜起来,这事村里只有几个人知道。前天工头看见了它,要我解下来让他看个清楚,我没同意,他就决定送我来这里。”
灰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民工团人,完全适应了民工团的生活,并且生活过得“平静”、“谐意”(他后来抱怨我把他的生活搞乱了可以为证)。手比死人手还冷以及心装在布袋里,都具象征性,这特别让人联想到《百年孤独》中人长猪尾巴的意象。
我从灰子那里出来之后,又漫无目标地散步。“便民超市”的老板告诉我,这里根本就不是公园,而是劳改农场,只有犯了错误的人才到这里来,如果五点还不能被车接回去,就要参加赌博,如果赌输了,晚上就要发生血案,所谓“血案”,小说中没有交待,但它实际上就是说有可能被杀死。但五点钟时,车按时来接我,并且准确地停在我的身边,奇怪的是司机已经不是早上的那个司机。这一回合的较量,对于杨下头来说,似乎是一种心理战,与前面的利诱不同,它更带有威胁和恐惧的意味,但我无动于衷。至此,斗争还处于胶着状。
回到宿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汉子占据了我的床铺,晚上我和汉子两人挤在一起睡觉,床很窄,根本没法睡觉。我骂了句粗话,汉子马上问:“你一定对上级有很多不满吧?”我赶快否定,说是骂从前的一个坏人。早晨我发现灰子的床是空的,我建议汉子以后上去睡,但汉子不同意,说是杨工头交待的:“这不是由我决定得了的。上铺的人有可能冷不防就回来了,杨工头就是这么说的。”后来知道,灰子晚上果然曾回来在床上躺了一个多小时,随后被吉普车强行拉走了。汉子显然是工头的间谍,用来监视我、骚扰我、引诱我,收集我的罪证。我和汉子挤在窄窄的床上,不堪忍受,而上面灰子的床铺正好是空的,这是一个明显的陷阱,一方面是逼我上去,一方面是引诱我上去,只是我上去,我马上就是犯了错误,但我就是不上去。我骂了句粗话,汉子马上如获宝贝,问我是不是对上级不满,但被我巧妙地否定了。我仍然死抱“我从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这一宗旨,以不变应万变,不犯错误,不给对方以“把柄”从而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
小说在下面就进入了最为精彩的部分,同时也进入了最为动人心魄的冲突。上午回宿舍换鞋子,发现同铺的汉子还躺在床上(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他的任务是来监视我的),他对我说:“没有用的。”“这么拼死拼活工作,没有用的。工头在心里已经把你除名了。”但我的态度仍然非常坚定:“呸!除名!又没犯错误!我昨天还领了工资呢!”残雪的小说常常有很多省略,这里也是这样的。“没有用的”作为一句对话的开头,似乎很突兀,但联系具体的语境,它的意思其实非常明确,并且具有简明性。它其实是汉子劝我向工头投降,向民工团这一现实投降,即按照民工团的“规则”行事,包括巴结工头、告密、尚恶、尚暴力、视痛苦为“正常”等。“没有用的”一语也反映了汉子的无奈。
吃晚饭后,在食堂门口碰到烧饼铺老板娘,她说有个宝贝让我去看。她把我带到一间房子里,我看到“屋梁上垂下一根绳子,绳子上绑着一个小伙子,他的长头发遮住了面部,在半空晃荡着。”老板娘解释说:“这是我儿子,我请人将他挂上去的。他呀,哀求我几天几夜了。你说,谁能经得住这样死缠不休啊。现在他的企图得逞了。你站到一边去,不然他会朝你吐唾沫,他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家伙。”老板娘还特别叮嘱,这件事不能向外人说,否则她儿子会感到没有面子的。第二天吃晚饭时我又想起这件事,再次来到烧饼店,这次迎接我的是儿子,而吊在房梁上的是老板娘,儿子向我解释说:“她总算生了我,也没有枉活一世了,对吧?这种关起门来的秘密活动,除了你这种多事的人,别人也不会注意到的。我妈不是一般的女人,有好多年了,我帮她做烧饼卖钱,我们赚了些钱,她的心思不在这上头,她属于那种心高气傲的。现在我要去把她解下来,她就会大发雷霆,因为还没到她忍耐的极限。”儿子还告诉我,他们娘儿俩只喝水,不吃饭。(这再次让人想起《百年孤独》中的不吃饭,只吃粘土的细节。)老板娘是杨工头的情妇,但更是杨工头的一个帮手或工具,向我展示“以苦为乐”或者说“自虐”不过是杨工头的另一个预谋,但我对此不以为意,并不欣赏,也丝毫不为所动,这使老板娘感到很没有面子,感到很失败,这大概是她后来出走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再见到老板娘时,她的脸“肿得像紫茄子一样,鼻子歪向一边,被人打歪了似的。”精神也不振,眼神暗淡。
我同铺的汉子仍然不停地对我展开心理攻势:“你这样刻苦,其实没有用。”但我仍然我行我素。对于杨工头来说,斗争事关民工团的命运,也威胁到自己作为工头的地位和威信。但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杨工头对我毫无办法,我的“无动于衷”、“泰然处之”明显处于上风,而杨工头则明显气馁、心虚,有一种失败感。他总是躲着我,经过我身边时也不看我。但杨工头并没有放弃,而是采取了新的攻击策略,这一次是他亲自上阵。
晚上汉子带我来到一处院落,里面到处都是叹息声和哀嚎声,阴森恐怖。杨工头也在这里。
“他要有这雅兴,让他站在那里旁听一下也是件好事。”
那是杨工头的声音。他的声音很快就被窒息了,我听见了“啊……啊……”的挣扎声,似乎是有人在掐杨工头的脖子,可能是起先说话的那个人。房里大乱,一片桌椅翻倒之声,同铺的汉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杨工头昏过去了,这些人叫我过去帮忙做人下呼吸。
我战战兢兢地摸到那群人面前(好象有五六个人)。他们将我牵往躺在地上的杨工头,要我将他的脖子托起来。那脖子软绵绵的,脑袋怎么也扶不正。他们说不管他的呼吸了,先做心脏按摩再说。于是七手八脚扒掉他的上衣。他们都不动手,要我做,说是往他胸口拳击就行了,用脚踩也行。我心理发悚,脱了鞋,勉强踩了几下,我感到自己像踩在一堆柔软的烂泥上一样。
“好!!”他们齐声称赞我。
我鼓起勇气又踩了几下,大家又说好。但是我害怕极了,我觉得工头已经死了。我这样践踏他,是为了报复他对我的迫害吗?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报复他,毕竟,他没有从肉体上折磨过我,也没扣过我的工资,怎么谈得上迫害?
所以我停止了动作,但明显遭至了批评,有人说:“看来老瑶对他的工头评价不高?”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杨工头说话:
“打我的脑袋吧,你们打啊,用力打!给我一把刀,让我把脑袋割下来!”
“他说得多么动听啊。”有一个嗓子尖尖的人称赞道。
有人按住工头不让他动,他又用力挣扎起来。这一次,连床都弄翻了。工头的力气真大啊,三个人都按不住!于是又掐脖子,又喊救命。我想趁乱逃跑,就开了门。
但我又被守门人拖了回来。守门人告诉我,这是私设的刑堂,并且夸耀说:“有些刑具的花样没人能想得出。”但我还是走了。我走时听到杨工头仍然在求人打他的脑袋。在整个小说中,这段情节最为扣人心弦,也最令人心醉神迷。所谓“刑堂”,就是暴力世界的“天堂”,这根本就是一个和现实颠倒的世界,在这里,一切以残暴为准则,以痛苦为乐事,不仅以施暴和它虐为快,而且以受暴和自虐为快。杨工头的自我摧残,承载痛苦以及享受痛苦赢得了众人的喝彩,我加入这样一个暴力的世界,拳击杨工头的胸,用脚踩他的身体,得到众人的齐声称赞,相反则遭到批评。花样翻新的刑具本来是罪恶和恐怖的象征,但却被炫耀。把我引入行刑室,这显然是杨工头的一个预谋,是一种“网捕”即陷井,但我并没有陷进去。“看来老瑶对他的工头评价不高?”实际上是说我并不欣赏杨工头的“受刑”表演,杨工头的暴力极尽展示并没有征服我,这对杨工头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于民工团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所以,这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民工团因此而完全失去了惯常。
吃早饭的时候,同铺的汉子显得很萎靡,他哭丧着脸对我说:“你昨天那一跑啊,把工头害苦了。”“你这种态度让我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上午劳动的时候,葵叔说我“已经占了上风”,“你昨天那一走啊,搞得他没脸见人了。你那一招真厉害啊。”整整一天,工头都远远地躲着我,站在原地方看着我干活。第二天又是这样,他甚至不再直接给我派活,而是通过别人传达,活也很轻,我做得也很慢。上厕所在民工团通常被当作是偷懒,而我上了两次厕所,杨工头也不管,相反,他自己决不上厕所,整整一上午都像雕塑一样站在那里。
我实在不好意思,主动找他表示歉意,我说:“真对不起啊,那天夜里的事!”工头倒抽了一口冷气,眼神变得呆滞起来,问我:“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诚意?”我问:“你真的想死吗?”他点了点头。我说:“那就去死罢。”他却又摇头,脸都发白了。工头迟疑了半天才说:“你,对我失去了信心么?”说完这话,他绞着双手,显得异常沉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话的权势完全在我这边,相反,杨工头在精神上可以说彻底崩溃了。小说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议论:“此地是一个大冷库,不管谁到了这里,他的心都要被冻僵。然而还是有原因不明的激情在暗中活动。工头啦,灰子啦,厨师啦,葵叔啦,不论是谁,都怀着这种古怪的激情,也许他们仅仅为这而活。”现在的杨工头可以说被我弄得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激情。后来的事也印证了这一点,老石告诉我,上午工头肚子痛,痛得从脚手架上栽了下去,幸亏下面是个沙坑,才没有受重伤。
晚上灰子突然回来睡觉了,灰子埋怨我把杨工头搞得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了,杨工头现在不管他了。第二天早上灰子躺在床上不起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对他来说生活已经没有意义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中有一个细节:狼不被猎人追打时,反而失去了灵性,失去了矫健、勇猛和威严。这两个细节其实具有相同的象征意味。灰子曾说过一句话,“有人劝我回去,他们根本不了解我。”灰子是独子,回家其实可以过得很舒服,这是人们劝灰子回去的原因,灰了说别人不了解他,表明他实际上对生活有另一种理解,他并不愿意过舒适的日子,而愿意过民工团的非人生活,正是在残暴和痛苦中他体会到一种生活的激情。“我看见他吐出的全是红色的东西。我心里想,他活不过这个冬天了。现在他就是愿意干活也干不了了。当我仔细观察他时,我发现他并不沮丧,甚至还有点兴奋的样子。他同汉子站在那里,脸上的神气就好象他们是某桩事情的主谋策划者,那种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我对他的怜悯全是多余的,他很有主见,太有主见了。他使自己的身体受苦,甚至致残,其实是为了达到一个我没法了解的目的。”灰子的人生信念现在完全变成了嗜恶,所以当灰子知道“行刑”这件事之后,异常兴奋,非要我带他去,后来即使只看到了断垣残壁也激动不已,嘴里不停地说:“来得真是及时啊。”
老板娘的儿子是一个著名的恶棍,现在也来民工团做工。这家伙什么也不会做,但整整一天他都不停地指责我、讽刺我。这显然是杨工头用来对付我的又一个手段。但我的一句话就让他萎靡了,我说:“你前一阵可比现在显得年轻啊。”这句话击中了要害,原来,他妈妈出走了,“她把铺子留给我了。我可继承不了她的事业,没这个能耐,所以我就成了闲汉。”笔者的解读,老板娘的儿子整天游荡、到处干坏事时,充满了活力和激情,但一旦让他做正人君子的时候,他便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便精神萎缩了,人一下子也变老了,这让人联想起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天山童姥这个人物。这之后的杨工头很久都不训人了,他每天都坐在工地上的空坪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晚上来查铺,态度出奇地好,满脸堆着假笑,说话也非常客气。显然杨工头已经彻底没有了信心,完全失败了。
但故事情节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我感到太累了,感觉到快要倒下了,鼓起勇气向杨工头求情,杨工头真是喜出望外,最后安排我一个非常轻松的活。我的工作就是呆在正在修建的楼房顶层的值班室里,晚上通宵把灯开着,不做任何事情,不用管事,也不负任何责任,当然也有限定,就是不能下楼,活动限于平台上。每天有人把饭菜送上来。我在这里过得非常舒服,就象住在疗养院里一样,也非常平静。但第四天的时候,出现了一只狼狗,我认定它是一条疯狗,“本来我如果闩上门呆在房里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可是我的意念出现了偏差。不知道根据什么我自信地认为我可以除掉这只疯狗。于是我拿起放在门后防贼的木棒出去了。”结果,狗当然是被打死了,但我的腿也被狗咬伤了。我试图下楼去医院,但出不去,腿变得麻木,再也站不起来,呼吸也很困难,伤口还向外溢出黄色的泡沫,后来就昏睡过去了。再后来是杨工头把我推醒,老板娘给我治腿伤,治伤的方式也是典型的民工团方式,她用匕首在我的小腿上剜下一块带血的肉,小说接下去是这样描写的:
我的小腿那里出现了一个洞,却并不流血,我甚至看见了里面的白骨。经她这么一刺激,所有的感觉全恢复了,腿钻心痛。
“你可以试着站起来走一走嘛。”她得意地看着我说。
趁我没注意,她猛地一把将我拉起。我晃动了一下,居然站稳了,当然那种痛是没法形容的。我本能地要坐回床上,可是她不让,她横蛮地将我拖到房子中间,拽住我手不放。我牙齿磕响着,告诉她我受不了。
但老板娘根本不管我,还说我娇气。并说已经把我治好了。这之后,我的腿一直剧痛,不断晕过去,又不断醒来。最后是慢慢适应了这种剧痛。
对于狗是如何出现的,小说当然有一些交待和推测,但这明显都是一些伎俩。狗在这里应该是一种象征和工具。至于它具体有什么含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也变得恶了,变得残暴了,变得富于攻击性了。我也陷入了痛苦之中,慢慢学会承受痛苦了,并且在承受痛苦的过程中慢慢习惯了以痛苦为“正常”,小说是这样结尾的:“我的伤口到今天也没有痊愈,但也没有更进一步恶化。正如它所给我的疼痛的感觉一样。发生变化的只是我的适应力。现在我已经把自己看作一个正常人了。有些重活我已经不能干,但我能够胜任的活还是很多的,所以工头也用不着为派我的活伤脑筋了。我的裤腿遮挡着伤口,别人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是当风太大从伤口那里吹到骨头上时,我的全身就会发起抖来。”我成了残暴而能够承载痛苦的人,一个标准的民工团人,并且是“民工团的宝贝”,其原因自然是这种改造来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杨工头曾特别自豪地向新民工介绍说:“这个老瑶是你们的同乡,你们以后就要同他共事了。他刚来的时候也是跟你们一样,什么都不懂,现在他已经变成老狐狸了。到了他这个份上啊,就是不干活,我们也要花钱养着他!你们好好在这里学习吧。”这句话实际是暗示了小说的主题,包含了小说的冲突过程,也是对故事结局的一个总结。
我作为“异端”被征服之后,民工团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一切都走入了正常。“工头又变成了一头凶残的狼,他将双手背在后面,鼓起金鱼眼,手一挥一挥地向这些人训话。”烧饼铺又重新开张了,老板娘又回到铺子里去了。我也“正常”地回到了工地,我虽然疼得每走一步就象踩在刀尖上,但却没有昏倒,伤口也没有恶化。“自从老板娘用匕首从伤口剜出腐肉之后,伤口还从来没包扎过呢。那个深洞始终没长拢,骨头就这样露着,看一眼都让人毛骨悚然。”但我慢慢习惯了。
所有的小说都是不能叙述的,托尔斯泰曾说:“如果我想用词句来说出我原想用一部长篇小说去表现的那一切思想,那么,我就应当从头去写我已经写完的那部小说。[5]对于残雪小说来说尤其如此。《民工团》的故事虽然相对残雪其它的小说来说比较清晰,但仍然非常隐秘,以上的叙述不过是笔者的一种发掘或解读,是以大量的遗漏作为代价的,所以误读在所难免。但笔者并不以“误读”为错误,因为残雪的小说充满了荒诞,再加上非理性、模糊、意象的跳跃、意义的空白等特点,它根本就没有所谓“正解”,误解不仅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同时还恰恰是一种创造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对《民工团》进行了另一种解读。
残雪深爱鲁迅,从这篇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作家受鲁迅影响的痕迹。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篇仿拟《狂人日记》的作品,但这种仿拟只是形式上的,而在艺术精神、思想内容上都有实质性的差别。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现实主义的,而残雪的《民工团》则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狂人是反抗的,而我则是无奈的,最后都是失败,但失败的性质不同,狂人是病好了,而我则是斗争的失败,是屈服。小说的冲突是紧张而激烈的,但这种紧张和激烈是内在的,即心理的。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