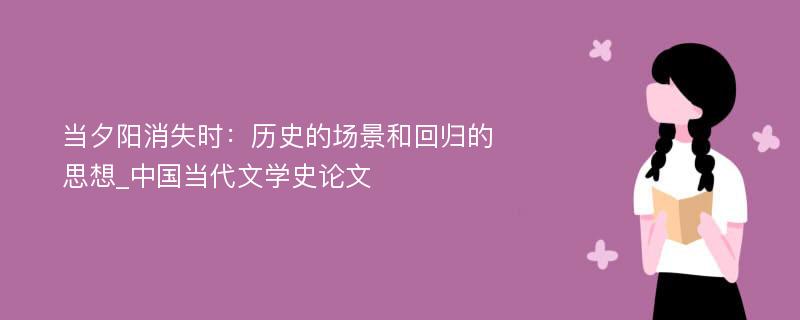
《晚霞消失的时候》:历史现场与重返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霞论文,现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何成为手抄本 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晚霞消失的时候》通常被置于“文革”潜流文学或者“地下文学”的框架中进行论述。如洪子诚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将《晚霞消失的时候》与《波动》、《公开的情书》同列为“文革”后期手抄本小说的重要作品。具体论述中,《波动》与《公开的情书》的版本与流传过程均有呈现,而当论及《晚霞消失的时候》时,却略去了这一部分的内容,代之以文本分析。在2007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修订版中,手抄本小说的复杂性被注意到,即在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仅以抄本形式获得传播,或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小说“严格说并未成为当时的‘文学事实’”①,除去部分文本分析的增删外,手抄本小说的篇目与评价与1999年的版本基本一致。 然而,《晚霞消失的时候》确是一部手抄本吗?2002年《青年文学》第1期刊载礼平的《写给我的年代——追忆〈晚霞消失的时候〉》,在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小说从构思到写作直至完成的过程。故事的雏形始于1976年春节的朋友聚会时的讲述,“这时,距离周恩来总理去世刚刚过了不过一个月,社会上各种各样非正式也不确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遍地走,政治笑话泛滥”。②(笔者注:1976年1月31日为农历大年初一,周总理逝世于1976年1月8日,那么礼平讲述故事的时间约为1976年的2月初。)但此时礼平无意于动笔写出这个故事:“我不敢。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笔力毫无信心,同时也怕惹上麻烦。所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只是一再地故伎重演:聚集一些谈得来的朋友,在一个充满诡秘气氛的环境中,偷偷摸摸地讲一个‘暗中流传’的故事。”至少在1976年2月初其后的数个月中,这个故事并不存在一份纸质的小说文稿,更谈不上以手抄本的形式进行传播。礼平回忆道:“这一年后来又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粉碎‘四人帮’,令人生厌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终于结束。但有一件事还在进行着,这就是继续批判邓小平”③,而动笔的契机则在并未随“文革”结束而停息的“批邓”大会④上到来:“两个月以后,我完成了这部小说”。⑤ 乔世华曾以这篇回忆性文章作为主要依据,认为:“礼平真正动笔开始写作它已经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批邓’大会上”,“从实际写作时间来看,《晚霞消失的时候》无论与‘文革后期’、还是与‘手抄本小说’都毫无关联,最多算是‘文革’末期曾在小范围内口头相传的故事。”⑥对照礼平2002年的文章所提供的细节,可以说,乔世华的论断是有理可据的。然而,在近年的对话中,作者就小说的创作过程,呈现出与此前并不完全相同的言说。在与王斌的对话中,礼平有如下表述: 1976年1月8日,我在清晨的广播中一听到哀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周总理去世了。随后便是痛苦与愤怒的一周。一周后,总理遗体火化,丧事结束,我的情绪突然翻江倒海般崩溃了。我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哭过,好像一生的泪水都在那一天倾泻了出来。从傍晚到深夜,我哭了四个多钟头,嚎啕大哭,哭得战友们全都莫名其妙,甚至连我自己至今都不能理解我这辈子竟会有这么一哭。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决定要写文革,写我的感受,写我的思考,而不管它写出来后会是什么。这时整个中国还没有一篇关于文革的小说,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相信,我应该是第一个拿起笔来描写文革的人。半年后,这篇小说在批邓运动中完成了,所以它是在文革末期的漫天阴霾中写出来的。⑦ 时隔七年,礼平关于小说写作时间的叙述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2002年的回忆性文章中,故事在1976年2月初首次被口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有口述而并未成文。到了2009年的对话中,决意提笔书写的时间提前到1976年的1月中旬,最终的完成时间也大为提前。写作时间的前移又与对写作风险的强调联系在一起:“我再强调一个事实,文革后,当‘伤痕文学’兴起的时候,危险和威胁都已经结束,哭诉和诅咒这个‘革命’在粉碎四人帮后成了光荣的时尚与风潮,整个社会的赞赏和同情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可是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并且正是最疯狂的时候。”⑧ 《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十月》首次刊载时,文末标注着:“一九八〇年五月于济南”⑨。它的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81年3月首次出版,小说的末尾,也标注着写作与修改的时间:“初稿: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再稿: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定稿:一九八〇年九月”。⑩初版时的明确标注,更接近于礼平在2002年的回忆:这是一部初稿完成于“文革”结束后的作品。那么,礼平在2009年对小说写作时间的前移就缺乏说服力。然而无论认定哪一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并不曾以手抄本的形式获得过传播,那么,它是如何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成为”手抄本的? 杨健出版于1993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是较早关注文革公开文学之外创作的论著,在他看来,手抄本小说奠定了“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基石,他列举出《九级浪》、《波动》、《第二次握手》等作品,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并未被提及。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出版于1998年,他将《晚霞消失的时候》置于“‘文革’后期传抄的几部中篇小说”一节中进行论述:“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也是在‘文革’中动笔,后正式发表于《十月》1981年第1期,并出版了单行本”(11),但他并未叙述传抄情况。到洪子诚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晚霞消失的时候》正式获得了手抄本小说的文学史命名。许子东出版于2000年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一书中,对于这部作品作出如下评论:“这是一部前红卫兵写于文革期间,后来作为手抄本广为流传,发表后又引起有关青年信仰问题诸多争论的作品。”(12)但对于小说的手抄本形态,以及如何广为流传,许子东并没有作出论述。 此后,《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手抄本归属基本上成为文学史常识,涉及对手抄本的评价,往往会论及这部作品,而手抄本形态的查无实据、作者前后的叙述差别、研究者的含糊其辞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这一在文学史中定型已久的“常识”。 二、八十年代争鸣中的《晚霞》 据礼平自述,《晚霞消失的时候》刚一发表,就引起冯牧的关注,获得转述中“才华横溢,思想混乱”(13)的评价。纵观八十年代,这部作品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与解读。(14)较早作出评价的是郭志刚,他肯定小说的艺术水准,又认为它在思想情调与人物描写上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15)。相比于郭文的意识形态化,于建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感性色彩,他将小说归结为一个梦境的表达,指出却并未苛责其中“淡淡的宗教迷雾”与“薄薄的宿命色彩”(16)。叶橹的评论则对小说的精神指向表示不解与质疑:“难道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这一切,只好改变信仰而另有所求?”(17) 随后,《青年文学》编辑部为小说召开“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并将调整后的发言稿刊载于该刊的1982年第3期,批评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南珊、楚轩吾的人物塑造和宗教倾向上。面对外界规约,礼平则表现出一种配合性甚至是主动性的自我规约:“这部小说的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检讨红卫兵的过失而写的。对‘血统论’和‘大清算’这两个方面的批评,主要是通过对南珊和楚轩吾这两个人的申辩和同情来体现的。至于在情节的发展中纳入一些所谓‘哲理’的对话和旁白,则完全是一种发挥。”(18) 而礼平在批评声中自我规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的小说单行本中更明显地体现了出来。相较于1981年第1期《十月》所刊载的小说,单行本除去细节的增删和语言的润色外,还针对受到批评的几个主要方面作出修改。 首先是对于楚轩吾的形象描述。期刊版本中,当李淮平听完楚轩吾对于战争的回忆后,抄家时的气势汹汹一扫而光,对老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仔细端详着楚轩吾,端详着这个已经苍老,但依然筋骨刚健的老军人,心中突然感到他是这样的慈祥,威武,亲切!”(19)而到了1981年的单行本中,褒义性的表述删去了,变为“我仔细端详着楚轩吾,端详着这个已经苍老、但却依然筋骨刚健的老军人,心中突然感到一阵恍惚……”(20) 与此相类似的更改也表现在对楚轩吾一家的评价上。期刊版中,李淮平在车厢里无意中听见了楚轩吾一家人临别的对话,意识到:“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不是我配去同情与怜悯的。不,这祖孙两代的全部人格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21)而到了中青社的单行本中,钦佩则被迷惘所替代:“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不是我所能同情与怜悯的。对此,我几乎陷入迷茫和不解之中。”(22) 其次是饱受指责的宗教观。期刊版中,李淮平在游泰山的过程中巧遇南岳长老,同行的一番长聊之后,慨叹道: 是的,这并不是一种迷信,并不是一种对虚妄传说的膜拜,而是一种充满了理智的信仰。从外表看,那信仰似乎是毫无根据的,似乎完全是受了一系列古老故事的欺骗。但是那些并不真实的说教,却可以在精神上发挥一种奇妙的作用,使这位佛门弟子在他可能经历过的复杂人生中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安详与和谐。”(23) 在单行本中,前述的第一句话被删除。同时为了使南岳长老的形象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与情节有所勾连,礼平还增加了对长老身世的暗示性描述。 再次是对于南珊的评价。在期刊版中,当与南珊的相遇即将结束时,满眼泪水的李淮平感到: 我不能再用任何缠绵的语言来回答她这样坚强的意志,我不能再用任何无力的举止来面对她这颗火热的心灵!南珊,她在我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和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于我的人生正在开始发生无比巨大的影响力的崭新的信念!(24) 而在修改后的单行本中,南珊不再被抽象化和神化,李淮平的崇敬之情也大为削减: 我不能再用任何缠绵的语言和回答她这样坚强的意志,我不能再用任何无力的举止来面对她这颗火热的心灵!南珊,她在我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和一个人,而是一种对于我的人生正在开始发生巨大影响的因素!”(25) 礼平的自我规约并没有使外界的批评终止。在当时的语境中,围绕这部小说的更深入的争鸣产生在单行本出版的两年之后,1983年9月27日和28日的《文汇报》连载了若水(王若水)的长篇批评文章《南珊的哲学》。王若水认为小说的历史态度是抛却是非善恶的不可知论,在他看来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同时批评了楚轩吾形象的拔高与抽象人性的表达,以及小说通过南珊和长老所表现出的宗教倾向。 礼平则以《谈谈南珊》一文表达激烈的反驳。对于备受批驳的宗教倾向,礼平辩解道:“在这里,宗教被看成是一个陷阱,一个深渊,南珊由于生活的不幸要走进去,李淮平则发出了痛心的呼喊。这不是一个宣传宗教的意思,即使你不把它看成一个批判宗教的意思。”(26)他否认小说的宗教倾向,认为自己是用文学的方式在宣扬马克思主义,并向王若水发问“这里是在用先哲和导师的话批评南珊的思想,但南珊的思想与他们有什么真正的差别呢?”(27)他进而举出若干例证,试图证明长老对于宗教的反叛,抱怨道:“我在座谈会上曾特意补充了这个意思,说长老的思想反映出‘愚昧无知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论正呈现出深刻的危机’。无奈这些同志真是死也不肯相信。”(28) 或许因为理念与书写的距离,或许因为辩词自身的空洞无力,礼平的反驳更像是狡辩,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也构成了削弱和伤害。1985年6月24日的《文汇报》摘要刊登了王若水的再商榷与礼平此前的《谈谈南珊》。在王若水看来,“作者企图给南珊插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以为是大可不必的”。 1985年之后,随着批评语境的转变,针对《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单篇评论大大减少,代之以宏观的定位和论述。评论的一个方面是将它放置在新时期小说的整体状况和文学思潮中进行评说,如李洁非和张陵将它定位于“反思”小说,认为与“伤痕”的直观反映所不同,“《晚霞》成为一种思辨”(29);高尚认为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窥见“新时期”小说的一种深度模式,即“对外部环境和故事情节的弱化,突出对主观感受和内在情绪的抒发”(30);董之林将它列入“知青小说”的框架中,认为“知青小说从它的开始阶段就表现出对于他们那一代人自身命运的反思”(31)。 评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将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例证,考察新时期文学与哲学、宗教、美学的关系。如巴文华认为它是“以存在主义思潮为指导”(32)的作品,樊星从“宗教与人心”的角度比较《晚霞消失的时候》与《金牧场》。1986年《文学评论》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栏目中,刘纳认为这部小说“有对宗教问题的充满理性气息的思考”(33);张韧认为“南珊形象的美丽和它的缺陷,全都包容在她对人生哲学的思考”(34);李洁非从“对性格的自我选择的肯定”这一意义上认为“南珊的哲学和勇气值得推荐”,楚轩吾则显现出悲剧这一“被唤醒的美学意识”(35)。 在新角度的考量中,《晚霞消失的时候》获得了更多中性或是褒扬性的评价。而相较于此前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礼平的态度则变得沉默,对自己这部在当代文坛引起争鸣的作品并没有作出更多的言说。同时,在创作上,礼平在1985年之后发表的小说《无风的山谷》、《小站的黄昏》、《海蚀的崖》也未能引起如此前一般的关注。 三、《晚霞》重现的方式 1997年,张旭东在《重访八十年代》中阐述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与八十年代的关联,就曾经的“西学热”、“理论方法热”等问题的认识上发出重返呼声。在他看来,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与纯化:“目前知识圈里流行的自恋、返祖和观念拜物教虽然为回顾八十年代提供了背景,却不应让我们把那个十年简单地想象为一个天真时代。”(36)1999年韩少功在与《天涯》的访谈中提出了需要反思八十年代启蒙/再启蒙所造成的“思维的简单化”(37)以及由此衍生的简单的现代化想象。 而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返八十年代”成为热点则是在2005年,程光炜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的《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提出了“重返”的必要与方法。2007年李杨发表于同一期刊的《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的访谈》则对研究理路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除了《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都陆续集中地刊载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者的集体返回中,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被用作价值中立的理论资源,“重返”的维度包括对文学思潮和重要作品的分析、对文学制度和传播过程的考察、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关系的梳理。王尧、杨庆祥、贺桂梅、赵黎波等学者也撰写论文探讨“重返”的方法与路径。除此之外,还包括并未明确有“重返”口号却有诸多“重返”实践的研究者,如张志忠以八十年代的作品为例思考当代文学有待展开的可能性,何言宏对文学史“正典结构”以其形成机制的追索等。在广义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视域中,《晚霞消失的时候》以八十年代争鸣作品或是文学史“正典结构”中被遗忘者的身份重现,成为备受瞩目的个案。 程光炜认为《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班主任》同样属于“伤痕”题材,境遇却大相径庭:“它尽管也像《班主任》一样受到责难,但文学界却并未像处理‘《班主任》现象’那样最终为其‘拨乱反正’地‘正名’,所以后来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始终未把它列入‘正典’文学。直到九十年代后,始有人重新提起它,不过仍然将其放在‘前伤痕文学’之中,而没有对已然形成的‘文学史常识’有任何僭越和质疑。”(38)尽管“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者宣称“我们的工作不是‘重写文学史’”(39),但在程光炜面对《班主任》与《晚霞》不同境遇的评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对已有文学史叙述的不满以及进行“重写”的强烈意图。然而,对将《晚霞》置于“前伤痕文学”的质疑,并没有首先建立在资料的重新整理上,即“前伤痕文学”的定位由何而来、是否可信,而是先直接给出一个否定的预设,再对之进行论证,这与“重返”宣明的来自于“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有所背离,从而成为一种建立在对文学史成规直接否定之上的捷径式返回。 在这一研究背景中,《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境遇与逝去的八十年代截然不同,与它的重现伴随着的,几乎是一片褒扬之声。在与《班主任》等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作品的对比中,这部小说被赋予了某种意义上的先锋性,这也重新形成了另一种“成规”般的叙述: 《晚霞》并不满足于这种“揭露”、“呼吁”式的叙述,它对造成悲剧的历史成因和人的命运中所潜藏的存在主义命题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固定化的“文革”叙述框架中,它引出一对恋人兼仇人李淮平和南珊的“特殊身世”,并且对四十年代那场“大战”的“意义”刨根问底;同样是控诉和展示“伤痕”,但作品却执意超出社会学的禁忌,而将命运与存在,宗教的终极价值做令人不安的深度互动。(40) 礼平曾提到,在小说初稿完成,经历不断修改的几年中,他处于封闭的环境中:“我根本不知道从1978年开始,许多文学期刊已经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重新出现。我的部队在偏僻的驻地,就像一只蛰居土中的泥虫,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涌动着怎样的春潮。一直到有一天,我在青岛中山路新华书店无意中看到了一本漂亮而且厚实的大型文学期刊,才知道社会上已经出现这样多的小说了。这本期刊的名字叫《清明》。”(41)按照这一说法,彼时的礼平并不熟悉“伤痕”文学所谓的“揭露”与“呼吁”式的叙述、或者固定化的“文革”叙事,那么也就谈不上是否满意于、是否试图超越于这种范式。 而且《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否能够在“命运与存在,宗教的终极价值”呈现出具有深度的互动与碰撞也需要质疑。礼平在事过境迁后的夫子自道,在某种程度上嘲讽了围绕这部小说的“思想性”解读:“我读了很多书么?我没有读多少书。读者觉得这个作者读了很多的书我想是一个错觉,因为我在小说中提到的很多书我都没有读过,甚至没有见过……”(42) 重现之时所获得的褒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八十年代主流批评的不假思索的反拨上。无论是八十年代的争鸣、还是新世纪的重评,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小说以哲学、宗教论述所构建出来的、与主流价值观所截然不同的思想性。而这种“截然不同”却又恰恰是被作者本人所否定与轻视的,在远离八十年代言说禁忌的当下,礼平所重申的仍然是这部小说的“正统性”: 实际上我的小说是一篇标准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品,它的一切都那么符合正统思想的需要。它反对文革,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在文学作品中如此细腻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进本远离的小说大概还没有过吧?(43) 固然写作理念与文本常常呈现出差距,但礼平在在重申的“正统性”也有理由让人质疑对这部小说的重评是否有所拔高,是否掺杂着评论者的过度阐释。《晚霞消失的时候》中虽存在着“异质”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抗者的姿态来源于八十年代评论家通过批评所实现的再塑造。这种再塑造所形成的印象,也让它更容易进入重评的视野,重评者通过简单的、反拨式的肯定再次加固了小说反抗者的姿态。此外,在“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中,获得重视的独异性文本(如《波动》、《公开的情书》)大多属于“地下文学”的序列,他们被视作对文学史“正典”的超越,这实际上暗含了对于“地下文学”的顺理成章的崇拜。若是剥除了《晚霞消失的时候》被误解的时间归属,其独异性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而且,在对《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公开的情书》等个案的集中关注之外,八十年代更多具有异质因素、越出主流叙述范式的文本仍然遭到忽视。譬如韦君宜发表于1979年的小说《参考资料》,以屠格涅夫式的代际冲突来反映“文革”创伤,母亲在儿子的不解中回首往昔,表达出对革命之路的反思与怀疑,发出“到底哪条路是对,哪条路是错?”(44)的自问。再如林斤澜发表于1983年的小说《乡音》,叙述了“退休宴上的第五个故事”:“饭铲头”政治风雨中的惨痛往事在被讲述得稀疏平常,对抗苦难的力量并非政治性的救赎,而是绵延不绝的乡音,是那种“悠悠地,韧韧地,久远久远地生存下来的力量”(45)。对这些作品的忽视,会影响到个案重评时的定位与分析,影响到对八十年代文学整体发展的把握。考察范围上的狭窄化,也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当下的语境中获得了过高评价影响因素。这也可以反映出“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用何种方法论重返、以何种角度评价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局限。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②③⑤(13)(41)礼平:《写给我的年代——追忆〈晚霞消失的时候〉》,《青年文学》2002年第1期。 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于1975年11月,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方才宣告结束。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⑥乔世华:《关于〈晚霞消失的时候〉》,《粤海风》2009年第3期。 ⑦⑧(42)(43)礼平、王斌:《只是当时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⑨(19)(21)(23)(24)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十月》1981年第1期。 ⑩(20)(22)(25)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 (11)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版。 (14)从数量上,小说发表的前三年间评论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在1983年,随着“清除精神污染”的开展而达到高峰,它受到了集中的关注与批评。争论并未随着运动的迅速结束而停息,直至1985年才逐渐减少。到了1986年,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回顾的背景下,小说又在整体性的审视中获得了较多的评论,评论数量在1988年以后逐渐减少。 (15)郭志刚:《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谈〈立体交叉桥〉等中篇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第39页。同年8月8日,这篇文章又以《文艺创作需要崇高的思想境界》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 (16)于建:《人生价值的思索——读〈晚霞消失的时候〉》,《读书》1981年第8期。 (17)叶橹:《谈〈晚霞消失的时候〉创作上的得失》,《文艺报》1981年第23期。 (18)礼平:《我写〈晚霞消失的时候〉所思所想》,《青年文学》1982年第3期。 (26)(27)(28)礼平:《谈谈南珊》,《丑小鸭》1985年第5期。 (29)李洁非、张陵:《小说在此抛锚——对当代中篇小说所处位置的解说》,《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30)高尚:《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31)董之林:《旧梦与新岸——论新时期知青小说中理想命题的嬗变》,《小说评论》1989年第3期。 (32)巴文华:《现代派在我国影响概观》,《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 (33)刘纳:《新时期小说与宗教》,《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34)张韧:《文学与哲学的浸渗与结盟的时代》,《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35)李洁非:《被唤醒的美学意识:悲剧》,《文学评论》,1986年第12期。 (36)张旭东:《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 (37)韩少功:《反思八十年代》,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38)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39)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的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程光炜、李杨在2007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的《重返八十年代·主持人的话》中,杨庆祥2010年第1期《文艺争鸣》发表的《“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中都有着类似的表述。 (40)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44)韦君宜:《参考资料》,《人民文学》1979年第8期。 (45)林斤澜:《乡音》,《人民文学》1983年第3期。标签:中国当代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晚霞论文; 小说论文; 当代作家评论论文; 公开的情书论文; 班主任论文; 波动论文; 十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