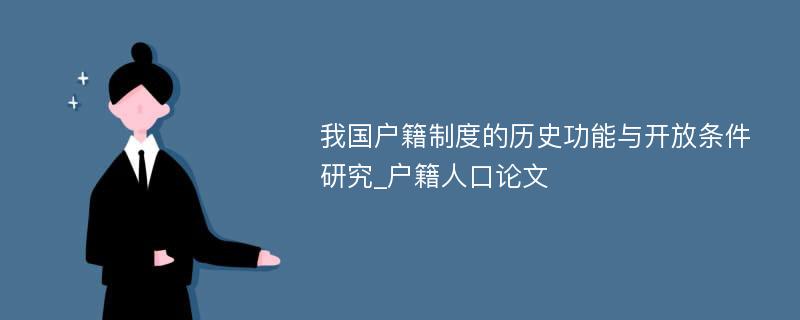
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开放条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户籍制度论文,作用论文,条件论文,我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 1672-2035(2006)04-0064-03[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 B
户籍的概念是“地方民政机关以户为单位登记本地区内居民的册子,转指作为本地区居民的身份”。相应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指建国后逐渐发展形成的一套户口管理制度,1958年1月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为了限制所谓“农村盲流”进入城市,切实加强全国户籍管理,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形成的标志,自此,从制度上,城市人与乡村人便有了一个事实上的身份等级。1964年,为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籍迁移的规定》草案,不但没有改变城乡隔离的局面,反而彻底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自此中国开始了长期实行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的法定隔离制度。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
户籍制度在形成初期并没有包含对个人的迁徙自由加以严格的管制的内容,制度的内容基本上体现出尊重个人自觉自愿的原则。按照那时的政府文件规定,户籍管理的主要目标是“证明公民身份,便利公民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统计人口数字为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建设提供人口资料;发现和防范反革命和各种犯罪分子活动,密切配合斗争”。人们仍在较大程度上享有户口变更、迁移、转换的自由。
从20世纪50年代末,户籍制度就把我国居民彻底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序列。实行这样严格的“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有其当时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一是社会供给不足,城市难以容纳大量农民进城,二是为工业化的积累,必然要限制消费,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稳定。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国能否度过物质空前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和秩序空前混乱的“文化大革命”的难关。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
首先,建国初期,国家受到内忧外患的困扰,国民党和各反动残余势力仍然垂死挣扎,进行破坏;国外的敌对势力进行经济封锁,并且不承认新中国的成立。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户籍制度在对稳定社会治安、加强对公民的控制和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犯罪现象有所减缓,社会秩序持续好转。
其次,当户籍制度发展到60年代,城市人口开始由国家统一供应商品粮,有很多优待措施,同时工业品价格实行与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国家以此来集中财力,发展国民工业,发展城市。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便建立了一大批国家企业。当代中国户籍制度配合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复苏,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民主化建设。
再次,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国城市的人口问题、发展问题日益严重,给政府和其他纳税公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解决问题,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减少城市人口,精简职工,大量干部和城市居民被疏散到农村。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职工2600万人。这就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又缓和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同时还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的落后的大批劳动力。
最后,文革过后,由于新政策的出台,户籍制度已经显露出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方面,但也在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公民的身份证明、社会治安维护等方面;由于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从80年代起出现了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改革试点城市的所谓“民工潮”现象,迅速增加了城市人口,引起了一些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中必然的问题,由此国家加强了对“农转非”问题的控制,有效地控制了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在一定的时期内解决了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二、我国的户籍制度应该改革,但户籍闸门的放开需要一定的条件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它本身就显示着一种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甚至还违反法律的现象,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不适应性日益突显,并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为此,1984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的通知》,尽管附带“口粮自理”的条件,但第一次使得农民进城成为了可能。1985年7月,公安部颁发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居民可以以合法身份在非户口所在地长期居住。从2001年5月1日起,国家取消了《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同时住房、医疗、养老制度正在改革,招聘也已经由企业自己做主。但目前,多数城市的户籍开放并不包括在农民可移居的城市范围。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户籍闸门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敞开,但这适当的时候究竟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出现?什么时候城市的大门才能完全敞开?
1.户籍闸门开放的理论基础——社会理性。所谓社会理性,是指以社会运动和人的社会运动为依据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互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意向和规律。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地涌入城市,城市之间的人才流动目标地也倾向于发达地区,这么庞大数字的流动人口冲击了城市就业,加重了城市的负担,影响了城市人口总体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社会治安。同时,城市化的浪潮也席卷着农村,小城镇蓄势待发,这么多的因素形成了一股整体力量,推动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这就是社会理性,它在客观上需要人口的自由流动,并能缓解部分发达城市的压力。
2.户籍闸门开放的“实践性前提”。现行的户籍制度虽然造就了城乡“二元”分割现象,但它从来没有绝对化的禁止城乡之间的交流。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不断有农业人口通过招生、招干、招工甚至走后门的形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具体的方式如: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进入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务工经商、干部培训、投靠亲友、婚姻迁移、读大学等。详细情况见以下两表:
表1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概况表:(单位:万人)
年份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人数92.0 66.0 68.2123.0150.2166.5166.8159.9
年份1989 1990 1991 1992 1994 1995 1996 1997
人数
120.0118.0140.0160.0195.0220.0210.0190.0
表2 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途径(%)[2]
指标 工作调动 分配录用 务工经商 学习培训 投亲靠友 退休退职 随迁家属 婚姻迁入 其他 合计
合计 5.8 4.0
35.8 15.3 12.8 0.4
11.9 6.1 7.8 100
男 6.9 4.7
43.9 17.6
8.6 0.47.8 1.4 8.7 100
女 4.3 3.0
24.2 12.1 18.9 0.2
17.8 13.0 6.5 100
城市 3.5 3.2
41.7 17.3 13.7 0.38.5 4.7 7.1 100
市郊 9.6 0.9
20.0
9.1 12.0 0.6
15.9 18.4 13.0 100
镇 8.2 6.4
31.8 14.2 11.7 0.4
16.0 4.1 7.2 100
资料显示,早期的“农转非”数据为后来更多的“农转非”提供了实践上的基础,并为后期一系列户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现实经验。户籍闸门的放开,需要这样的前提。
3.户籍闸门进一步放开的现实条件。“广东省户籍制度的改革,迈出了我国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变革有实际意义的一大步。相信有不少省市,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将纷纷仿效。在此,我们提醒有意取消城乡户籍差别的地区,一定要根据本地发展水平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可行则行,条件不成熟则暂缓,切不可盲目攀比,否则,操之过急,极易招致混乱。”这是《法制报》2002年2月的一篇评论中的一段话。
(1)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距过大,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于国际标准,国内各地区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更是相差甚远(表3),这样的现实严重地制约着我国户籍闸门的敞开。农村地区的落后必然导致农业人口的外流,他们的第一站便是小城镇,但小城镇在我国只是农村和城市的过渡地带,实质与农村差距不大;农民自然要往城市流动,而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水平无法容纳过多的外来人口;发达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必然是理想目的地,然而人口的迅速集中增大了这些地区和城市的压力,并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3] 由此,人口流动的任何一环都是存在问题的,并且隐藏着盲目性和无序性,给社会及其发展造成很多隐患。因此,必须首先进行城市化建设,大力发展小城镇以作为全面实现城市化的过渡,使得城乡达到一体化,社会经济发展得到平衡,这样才能避免上述的层层问题,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才能成为可能,公民的自由流动才能够现实、有效。
表3 1995年城乡收入与消费比[4]
项目 人均GDP
城乡居民城乡居民
地区(元)
人均收入比消费比
(农民为1)
(农民为1)
东部2372 1.802.09
中部1337 2.182.50
西部1166 2.732.91
(2)户籍制度改革要与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一方面,城市化进一步发展作为一种必然趋势,既要求城市有更强的人口吸纳能力,也要求有更多的农村劳动者更加安全、体面地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城市建设。而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力资源。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也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人口向城镇和城市集聚的过程。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其生活成本应当得以降低,其子女就学应当得到保证,其社会保障应当得到妥善安排。只有达到这样的条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能得到稳定的保障[5]。
(3)我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单向流动,即在一段时期内的人口流向是城市——农村,另一段时期内是农村——城市。1958~1960年的大跃进,从农村转移4000多万劳动力人口进城,到1962年以后,下放城市的劳动力人口6000多万。又如1966~1976年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插队1600万,再如1988年开始进行“治理整顿”7000万进入城镇兼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刚刚从农村转入城镇从事工商业不到三年,大多数又解甲归田,这些都是从城市流向农村;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虽有提高,但和城市相比还是差距很大,因此大量农业人口开始流向城市。无论人口的流向是什么,单向流动都是不正常的,它说明了社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反城市化路线”的单纯流向农村体现了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体系都不协调的现实,而现今的疯狂的“农转非”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如交通、住房、犯罪等等。[6] 因此,只有当实现城市化,社会经济发展平衡,城市和农村没有差别,同时进行人口流动,即双向流动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现实才能够让户籍闸门完全放开。
综上所述,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我们的社会现实,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不具备立即进行彻底的户籍改革的条件,因此,户籍改革要循序渐进,走由农村——小城镇——城市逐渐过渡和发展的城市化模式,只有具备城市化和双向流动这样两个条件,户籍闸门方可完全放开。
